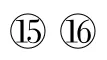评“杜甫基督关系说”并与张思齐教授商榷①
2015-07-04韩晗
韩 晗
作者:韩 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后,100091。
杜甫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亦是唐代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历来为学界所重点研究、关注,并产生了百花齐放的观点。而在“网络狂欢时代”的当下,杜甫也被许多学者以另辟蹊径的形式予以“发常人未发之声”式的解读。其中,近年来最具争议的观点就是武汉大学教授张思齐先生所主张的“杜甫基督关系说”。
张思齐教授曾在《大连大学学报》(2013 年4 月,第34 卷第2 期)刊文《从咏鹅诗看基督精神对杜甫潜移默化的影响》 (下文简称《从》文),认为杜甫的《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三)与《舟前小鹅儿》等五篇诗作,通过与《马太福音》的“相互比参”以及景教在唐代的传入可知“白居易的闲适诗得益于基督宗教的浸染,杜甫的闲适诗也得益于基督宗教的浸染”,甚至推而广之“凡有人处皆有基督,凡是人民的作家皆富有基督精神”,其原因在于“圣灵一直在工作着,而且圣灵的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息,这些才是人民性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
如果这篇文章的目的只是对宗教教义的宣传,我想应该是无可厚非的。《从》文所言“凡有人处皆有基督”与“圣灵一直在工作着”符合基督精神。譬如《圣经》中的“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旧约·诗篇》104 章30 节)、“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旧约·约伯记》33 章4 节)等词章皆可为证。但作为学术论文,笔者认为, 《从》文的这类断言,或许有值得商榷之处。藉此,笔者以相关史实、史料为基础,从辩证的逻辑出发,结合《从》文所重点论述的如下两个问题,献疑于张思齐教授。一,“景教”是否可以代替基督精神?二,“咏鹅”是否可以构成基督精神之联想?在这两个问题之上,笔者意图不揣浅陋,就《从》文所采取的比较文学方法论向张思齐教授再度请教,期盼学界诸先进予以解惑。
一
《从》文论述杜甫所受“基督精神”的影响,该文认为,此处的“基督精神”乃是附着于“景教”之上的。那么第一个问题所衍伸出的分支问题就是:景教当时在中国有多大的影响?
景教,历史地看确实是天主教早期的一个派别,是“聂斯托利派”(Nestorian Church)的一支,亦称“东方亚述教会”,由叙利亚裔的君士坦丁堡牧首聂斯托利(Νεστóριοζ,386 -451)创建,后通过丝绸之路,在隋唐之际传入中国。
现在景教在唐代活动的具体细节情况,已不可考,唯一可以参照的史料有二,一是《从》文中反复提及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块碑刻于唐建中二年太蔟月(即二月)七日,记载了景教来华传播的史实;二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 -1945)在1908 年于敦煌藏经洞所发现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景教在唐代的传播文献仅此两件,但景教在宋、西夏及至元明清的传播文献、文物,却时有发掘。通过对这两份文献的分析,我们发现,景教当时来到中国是有特殊背景的。
唐代贞观、开元年间,西域客商凭借丝绸之路,来到洛阳、长安从事交易,他们迫切需要宗教场所举办宗教活动,而当时景教的传入,实际上满足的并非是中原人的宗教需求,而是来自西域的客商。唐高宗确实下诏,认同景教的合法性,并且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但这只能证明,景教可以在当时合法传播,而非唐代的“国教”。
但当阿罗本、罗含、普论等在中原传播景教时,曾获得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唐玄宗李隆基、唐肃宗李亨、唐代宗李豫的直接关心,以及房玄龄、郭子仪等高级官员的扶持,甚至在“景教寺”里还供奉着唐朝皇帝的画像。在唐代社会的高层,景教确实有一些教徒,但宗教只有落入民间才有发展空间,束之于庙堂高阁,结果就是“景教教务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发展”。公元845 年“会昌法难”时,唐武宗让“勒令大秦景教信教者三千余人还俗”,结果“此后景教在内地绝迹”,三千教徒(当中还包括一些西域客商)之于唐朝总人口九千万(唐玄宗天宝年间)来说,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即使与高峰期近七十万人(韩愈撰写《论佛骨表》前后)的佛教徒来说,也相当稀少,可见景教在唐代根本没有什么影响。
由此可知,景教是以客居中原的西域人士为主要传教对象的,在少数中国信教者中,也以皇亲国戚、权贵世家为主。这样一个受众不足三千人的“微型教派”,可否在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里形成基督精神?而且,只是在西域客商、达官贵人中小众流传的宗教,可否将基督精神潜移默化地带给杜甫这个只做过“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这种微官的落魄诗人?这一切,都很难说。
其次,从西方宗教史来说,景教及其创始人聂斯托利本身被亚历山大宗主教区利罗一世(Cyrillus Alexandrinus,376 - 444)视作异端,而是与当时聂斯托利提出“基督二性连接说”有关,他否定基督单纯神性的一面,这是与当时的正统观念相违背的。而且,《从》文所不断援引的《马太福音》亦有失偏颇,《马太福音》虽然成书于公元60 年前后,但真正被列入“四福音书”并成为天主教与新教(Protestant)之经典,却是在公元十世纪前后。尽管《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中的一些故事情节与《马太福音》第17 章中的若干内容有相似处,但以《马太福音》来反观杜甫所受基督精神之影响,仍似为附会牵强之笔。
因此,《从》文从景教入手,研究杜甫受基督精神本身证据不足,而且从史实、逻辑的角度来看都存在着诸多漏洞,难以自圆其说。
二
《从》文独辟蹊径、立意别致,从杜甫的“咏鹅”诗歌入手,谈其与基督精神的关系。杜甫所咏之物甚多,鹅只是其中之一。 “托物言志”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为何《从》文单单选鹅?而不是竹、山、江、雁等其他意象?笔者纵观《从》文全篇,又未言及“鹅”与基督精神之联系。
在古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曾记载女神皮尔洛波豢养了20 只鹅。巴比伦时代,鹅曾是寺庙的守护者。公元前390 年,高卢人偷袭罗马人在庞贝城内的丘皮特神庙(tempio di jupiter),神庙内一群鹅发出报警的叫声,惊醒了睡梦中的罗马人,使得神庙免遭荼毒。在西方文化史中,鹅向来不是陌生之物。
我们不妨再来爬梳一下《圣经》与鹅之关系,据香港董思高圣经中心统计,《圣经》中曾出现过31 种鸟类,其中次数最少的就是鹅,只在《列王记》中出现一次,而且是以“肥禽”之名“疑似出场”的。与雄鸡、鸽子、老鹰相比,鹅可以说是《圣经》中最不知名的鸟类。因此,“鹅”虽然频繁地出现在西方文化史中,但将“鹅”与基督精神相联系,却几乎没有任何必然性。
有趣的是,“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颇为知名,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出场次数最多的“鸟”之一(假如家禽也算鸟的话)。在原始社会这一远古时代,地处东亚地区的人类将野生的鸿雁驯化为“鹅”。由此以降,鹅即为家禽之一种,为人们所熟悉。
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就有“曲颈雁”的玉器,这是鹅的雏形。汉代李巡注《尔雅》时中就曾论及“野曰雁,家曰鹅”。及至西周,已经冶炼出了“鹅”状的青铜酒器、带钩,并以玉鹅陪葬于虢国墓葬。近年来,亦有西周时期的玛瑙鹅、金鹅出土。汉魏时期,鹅型的青铜鐎斗、带钩、陶器更是不胜枚举。两晋时,爱鹅成癖的王羲之有“一笔鹅”书法传世,而王献之亦有千古名帖《鹅群帖》,至于骆宾王之《咏鹅》更为家喻户晓,鹅已经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化史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符号。
究其根本,乃是“雁” “鹅”在意象上同源,人们会把对鸿雁的赞美、夸耀寄托在鹅的身上。雁是候鸟之一,也是上古时期人类识别气候、辨析方向的重要依据。《诗经》中早有“鸿雁于飞,肃肃其羽”的辞章。《汉书》更是将雁符号化, “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此为“鸿雁传书”的滥觞。至于“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曹操《蒿里行》)、“巫峡啼猿数行泪,衡阳归雁几封书”(高适《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与“雁声远过潇湘去,十二楼中月自明”(温庭筠《瑶瑟怨》)等与“雁”有关的名句名篇,更是不胜枚举。此外,在印度佛教中,也有摩揭陀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僧人“埋雁造塔”的典故,这也是西安“大雁塔”得以落成的原因。由此可知,“雁”是东方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符号。
现代生物学也证明,“鹅”是“雁属”分支下的一种鸟类,英文的雁即为wild goose,即野鹅,只是欧洲人所驯化为鹅的雁是灰雁而非鸿雁。由是可知,“雁”与“鹅”有着难舍难分的联系。杜甫写诗寄情于鹅,亦反映了他感时伤怀、托物言志的诗歌创作。
此处暂以《从》文中列举的《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三)为例:


再以《舟前小鹅儿》为例,此诗完稿于广德元年(公元763 年)的汉州(今四川广汉),该诗还有一个副标题,叫“汉州城西北角官池作”,官池即“房公湖”,“房公”为房琯,武周时宰相房融之子,曾为唐相,后贬为汉州刺史,曾与杜甫交好。
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
引颈嗔船逼,无行乱眼多。
翅开遭宿雨,力小困沧波。


因此,杜甫所观之鹅与杯中之酒实际上构成了一种与友情、礼仪共生的符号,犹如日本文化中的菊与刀。只是此诗之后,蜀中人将“鹅黄酒”泛指好酒,苏轼《追和子由去岁试举人洛下所寄·暴雨初晴楼上晚景》中便有“应倾半熟鹅黄酒”一句,而陆游在《感旧绝句》中亦有“鹅黄酒边绿荔枝,摩诃池上纳凉时。”
而且,据说房琯喜欢鹅,曾赠送过杜甫一群鹅,杜甫在与其有关的诗中曾两次将鹅作为描述对象(另一首是《得房公池鹅》)。而《舟前小鹅儿》后面几句,则从写意转为写实,描述了鹅群为舟所困的景象,堪称生花妙笔。实际上亦为杜甫自己困顿江湖,壮志难酬的内心写照,实际上与杜甫一贯的诗风有着极其相似之处。
由是可知,杜甫的几首“咏鹅”(其中还有并非是“咏鹅”而是咏雁)的诗作,实际上是取材于中国传统文化,并有着鲜明杜诗风格的作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与基督精神没有任何的必然、偶然联系。因此,杜甫的“咏鹅”诗难以让人引发与基督精神有关之联想。
三
《从》文中所列举其他几首杜诗中的“咏鹅诗”,亦是如此。譬如《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之二)中,有“休怪儿童延俗客,不教鹅鸭恼比邻”一句,此处“鹅”与“鸭”并称,实为并列式语法结构,犹如“花草”、“树木”等等,“鹅鸭”在这里泛指喜欢啄咬生人的家禽;在《摇落》一诗中,杜甫用“鹅费羲之墨”一句,此处“鹅”乃是援引王羲之“一笔鹅”之掌故,并无他意;而《得房公池鹅》一诗中,更是将“鹅一群”与“王右军”相提并论,既体现房琯爱鹅、自己珍惜友情之意,亦将爱鹅的房琯与王羲之相提并论。
由是可知,杜甫的“咏鹅”诗,其精神既来自于传统典籍、经典掌故,也受其自身的交游、境遇所决定。从杜诗乃至整个唐诗的大格局来看,杜甫的“咏鹅”诗不但是杜诗的一个组成,也是唐代“咏鹅诗”中的翘楚。但要说它们是受基督精神影响而成,恐怕两者关系相去何止以道里计。

但是在《从》文的第三个部分,作者话锋一转,从比较文化的研究范式转向了史料考证,从景教在华传播入手,认为杜诗与基督精神岂止是可以比较,乃是受其影响。即从比较文化学中的比较研究直接过渡到了影响研究。殊不知,比较研究重文本,而影响研究却是重史料。如果只是《从》文所言之“比参”即比较、推测、猜想,那么这就难以得出影响研究中值得让人信服的结论。
《从》文认为,景教东传(成都有景教教堂遗址),杜甫忠君(景教是唐代皇帝认可的宗教)构成了杜甫受到基督精神影响的要素



不宁唯是,站在人类发展的高度,我们可以发现东西方在许多问题上实际上都有相似的共性,譬如前文所论,东亚人与西欧人在原始社会同时将野雁驯养成为了家鹅,使得“鹅”成为中西方文化中一个共同熟悉的符号。而这根本不是谁影响了谁的问题,而是人类进化到一个程度之后所进行的共通的选择。
在没有全球化的时代里,人们就曾拥有相同的一面,在全球化时代重新分析人类的这一共性,这是比较文化学应该关注的问题。譬如《老子》中的“小国寡民”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理想国》中对于“正义”的定义、 《论语·颜渊》中“政者,正也”以及墨子的“兼爱观”与基督教的“圣爱观” (agape)以及晚明启蒙主义思潮与欧洲文艺复兴等等,它们之间的异同关系都是这一问题下的分支问题,但是要分别找到它们各自有什么样的相互影响,我想这既非必要,也无可能。

如果基督教是张思齐教授的信仰,我完全尊重“凡人处皆有基督”这一观念,但是作为文学研究者而言,“凡人处皆有人性”是否也应该是我们共同信奉的准则呢?
注释:
①感谢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孙康宜教授对拙文初稿的指教,笔者铭感至深,特此致谢。
②④⑱⑲㉓㉔㉕㉖㉗张思齐:《从咏鹅诗看基督精神对杜甫潜移默化的影响》,《大连大学学报》,2013 年4月第2 期。
③《圣经》(领导事奉版),香港汉语圣经协会有限公司2015 年版,第66 页;第190 页。
⑤王书楷:《天主教早期传入中国史话》,湖北省蒲圻市第一印刷厂(内部资料)1993 年版,第40 页。
⑥周燮藩:《中国的基督教》,商务印书馆2000 年版,第12 页。
⑦James E. Bradley:Church History:An Introduction to Research,Reference Works,and Methods. Michigan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1995,第39 页;第40 页。
⑧Sheila Dillon,Katherine E. Welch:Representations of War in Ancient Rome.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第89 -91 页。
⑨李巡注、黃奭辑:《尔雅李巡注》,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 年版,第90 页。
⑩班固:《汉书·苏武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1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