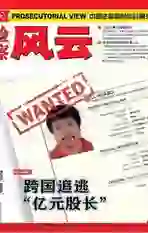那些年,我们这样办党刊
2015-07-01晓今黄辛
晓今 黄辛
作为一名抗战老兵、老新闻工作者,年届95岁的丁柯最近特别忙。适逢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位1938年参加革命,曾经在抗战时期,任浙东游击纵队《战斗报》主编的老人,成为媒体竞相采访的对象。“对于那段历史,那些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可歌可泣的真实故事,我们挖掘的太少,宣传的太少”。为了在有生之年留下亲历的历史,丁老一直借助笔记史料和回忆,笔耕不止。

丁老自称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从事党的新闻工作。所以,面对本刊记者的采访,他谈的最多的就是新闻工作应该如何发扬一些好的传统,深入基层,反映民生,办成读者喜闻乐见的报刊。
用“红色报人”来称呼丁老,似乎非常贴切。军报出身的丁柯解放初期参与了上海《解放日报》的创刊,并担任了编委;上世纪50年代,他在担任《支部生活》主编的同时,又奉命创办了上海市委主办的《党的工作》,成立名噪一时的“党刊”编辑部。
记者的访谈就是从“党刊”的创办开始的。
记者:丁老,您是新闻界的老前辈了,提到您的名字,老报人们都会将您与党刊联系在一起,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党刊”的背景。
丁柯:好的。党的新闻工作曾经是我党非常重视的一项宣传工作。解放后,作为编委,我参与了上海《解放日报》的创刊,并分管理论和党的工作宣传这块出版报道。
当时华东局接管城市以后,党的宣传工作抓得很紧,后来学了苏联《真理报》的经验,专门将报纸的第二版辟为“党的生活”栏,以加强党的宣传。当时的《解放日报》平时只有四个版面,重要的时候才出六个版。
1956年6月,我突然接到市委办公厅的通知,要正式调我到市委去,而且不仅是调我一个人,连《解放日报》的“党的生活”组整个班子都要一同调去,这是非常大的动作。我事后了解到,这是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重大决策。
记者:您最后带了多少人马离开解放日报社去了市委报到?
丁柯:这里有个小插曲。当时报社的年轻人不像现在那样喜欢往机关挤。我们大多数同志都不愿意去市委,认为到了市委不自由、很严肃。我呢,很犹豫。因为正值《解放日报》领导班子改组之际,我是副总编的合适人选。为此,《解放日报》的总编杨勇直特意找我谈话。我说我是部队出来的,部队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既然上面要我,我当然去咯。个别同志鬧情绪虽然不对,但,下面的实际情况也是需要考虑的,因为党的宣传是《解放日报》党报的一大重要任务,将这部分编辑记者连根拔去了,就没有人能接上去了。我建议留几个人下来,倒不是因为他们闹情绪,而是考虑《解放日报》的后续发展,我能够带多少人就带多少人走。
我的这个建议,得到了《解放日报》编委们的支持,也很快得到了市委的同意。
最后,1956年的6月,我带了七个人去了市委筹备“党刊”。
记者:一个单位的创立离不开人、财、物,党刊的筹备阶段您碰到什么困难吗?
丁柯:因为市委的重视,党刊的筹备工作出乎意料地顺利。记得我去报到那天,市委秘书长张静涛、副秘书长马万杰接待了我,他们说柯老到北京去参加党的八大,临行前,特别关照他们接待我一下,落实办公场所及其他后勤保障工作,《支部生活》还是按原来的标准先出,我们还有啥意见,等他回来再讲,办公厅先把前面的工作落实下来。
当时的市委是在华山路28号,现在的贵都宾馆的原址上,对面有一片六幢小洋楼,有农业局等市委下属的机构在那里办公。我到市委后,秘书处专门给我们安排了一幢三层楼房,我们当时还只有七个人,而且马上给我配了辆车子。
这也说明当时市委对我们这些做新闻工作人员的尊重,不仅是口头上的。
记者:柯老从北京参加八大回来后是否马上接见了您,他给您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丁柯:“八大”是我们党的转折点,开始考虑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抓经济工作了,邓小平在八大上作了一个党的工作报告,至今我党对八大的评价还是很高的。“文革”是对八大的反动。
1956年10月,柯庆施开完会从北京回来,还没完全传达会议精神,他就接见我了。
柯庆施的办公地当时在延安西路33号,原来是德国人的一个俱乐部,小洋楼。他住在四楼,办公室不到20平方米,外面有个很小的衣帽间,供秘书办公用。他的办公室只有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和两个沙发,一个茶几,非常简单朴素。
记得柯老与我第一次见面时,他就站在桌子前面的沙发边,很随和的样子,问了我许多具体的问题。我和柯老要相差20岁了,他个子比我还高点,要一米八十多,但他背有点驼的样子,看上去跟我就一样高了。我在杨勇直那里听说“我们背后都叫他‘柯大鼻子’”,他鼻子长得比较大,到了市委后,普遍都叫他“柯老”了。
他说现在市委要开会贯彻“八大”精神,决定要办一份刊物,这个刊物由市委直接管,你考虑下,这个刊物究竟该怎么办好,等市委讨论好了以后,我再找你谈。
他把秘书长找来,说丁柯现在调来了,那么办公厅要成立一个机构,叫什么机构呢,你们办公厅去考虑,丁柯是这个机构的头。
那天,从柯老办公室出来后,秘书长叫住我,说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但以后要注意把你这双鞋子换掉。我当时穿了一双军用皮鞋,就是那种大头皮鞋。在《解放日报》我们也都是穿皮鞋的,但在市委不妥。秘书长意思是你以后经常要出入柯老这里,你穿这皮鞋声音“咔咔咔”的不行。
记者:丁老,您记得当时“党刊”的读者是怎样定位的?
丁柯:其实,为什么要办《党的工作》这份党刊呢?当时上海市委是有设想的。市委那时已经有个刊物叫《上海工作》,专门登中央的文件和市委的文件,没有其他文章的,这是党内的,它有一定的规格。我们党内看文件当时规格很严,哪一级能看哪些文件都有规定,一般科级以上的干部都能看《上海工作》。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份《支部生活》,是面向大众的宣传物。
柯老说,我们现在要办份党刊,也可叫中级党刊,是对干部的,目的是上传下达,我们现在市委领导听不到下面的直接声音,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意见不能直接反映到市里面,要通过层层会议,我们市委的许多意见也不能直达,要通过系统传达,变成了城市里的“新疆”。所以,希望这个刊物既不能泄密,又能以尽可能快的速度传达到下面去。柯老对我说,现在我们上海的党的工作一定要抓得紧,上海是个繁华的城市,党员干部容易受到腐蚀。所以,党的思想教育一定要抓得紧。党内一定要严格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我希望办个党刊就是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批评不要变成沙发椅子,软绵绵的,要有棱角。
当时的读者定位是,《党的工作》以科级以上的党员干部为主要对象,基层单位限于车间支部书记、生产大队支部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还有应工作需要的市、区领导机关的党员干部。《支部生活》的读者对象是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是群众性的,以培养先进分子入党为主要宣传对象,要变成“不开口的支部书记”。那时的阶级斗争观念重,说是地富反坏不能订《支部生活》,但后来调查发现恰恰是地富反坏的子女特别要订,因为订了以后,让人觉得他们也是先进的,腰杆子就好像硬了许多。
当时我们有意将《支部生活》做成32开的小开本,因为流行穿四个口袋的中山装,《支部生活》刚巧可以放在下面一个口袋里,口袋外正好露出“支部生活”四个字。所以,在工厂里,有的人会将一本《支部生活》一直插在那个口袋里,让人感觉他是先进分子。
记者:“党刊”的发行靠红头文件吗?
丁柯:当时市委领导提出用党费来征订党刊,但我说我不主张党刊用党费来办,我们可以自费发行。我算了一下,加上印刷费和内部机要渠道的发行费,《党的工作》如果能发行到5万份左右就能保本了,10万份左右的话,是有盈余的,没必要用党费来支撑。
我的这个提议,引起了柯庆施极大的兴趣。他兴致很高的样子,让我具体说说。我说,党刊如果用党费订阅发下去,办得好与不好没有一个检验标准。如果是自费的,一旦读者不认可,他就可以不订,这样我们办刊就会有压力,这是一种鞭策。
柯庆施非常欣赏我的提议,后来,为这件事书记处还专门作为新生事物来加以表扬和肯定。
记者:听说当时市委“党刊”编辑部名气很响,规模很大,口碑又特别好,您能不能详细介绍下?
丁柯:呵呵。我们当时的一些做法,现在看也没有期刊能做到。比如,为了激励大家办好党刊,《党的工作》从第一期开始就将发行数印刷量打在刊物上,这样也便于市领导及时掌握发行情况。我跟柯老汇报说,您不用问党刊发行情况的,您每一期只要看封底下面印的发行数就知道最新的发行量了。《党的工作》发行第一期就达到了5万多份,以后一直在上升,最后发行到10多万份,上海的科级干部几乎人手一册。后来,《支部生活》也采取自费订阅,向支部申请,由支部开名单到邮局订阅。
我们最多时有在编人员66人,除了五名后勤人员,其余都是党员。党刊之所以后来影响很大,我想,一是市委领导的支持、力挺;二是信息渠道畅通,作者、通讯员队伍来自各行各业,非常庞大。我们有几千个通讯员,遍布各区,信息很快。因为信息渠道畅通,所以党刊逐渐成为市委的“第二信访部”,我有当时保留的原始材料,可以提供一些数据来佐证。编辑部收到的来信来搞和接待读者的来访的数量,除个别年份外,逐年增长:1957年,1.48万件;1958年,1.93万件;1959年,4.83万件;1960年,5.27万件;1961年,7.36萬件;1962年,6.35万件,1963年,9.11万件。之后,更是平均一个月要处理来信来访1万多件。这是现在的党报党刊无法想象的,可以说是当时的“大数据”了。
记者:在这些枯燥的数据后,一定藏着许多生动的例子。
丁柯:那例子是很多的。我记得有位汤生皮鞋厂的工人,吃了领导的批评,思想上想不通,半夜四点钟,就来坐在我们编辑部的门口等开门上访。从那以后,我们就规定编辑部有人住宿,定出了日夜接待的制度。我们还在徐家汇特约了一个旅馆,当天谈不完的,就帮他们安排住宿,一般为自费。这在一般的新闻单位是很难做到的。上世纪80年代,我在《民主与法制》社当社长时,也这样规定过。
记者:党刊要让读者自费掏腰包,吸引读者的报道恐怕必不可少。
丁柯:是的,党刊每一期都有热点问题的报道和讨论。我最近一直在回忆,那个时候,我们党有很多不足,但是,也有许多好东西正是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
柯庆施认为记者就是要“脚头勤”,人家休息放假,记者不能有这个概念。有一年春节,柯庆施突然打电话给我,让我马上到他办公室去一次。我们当时上班和住的地方都在康平路上,很近,我家也有红机,我放下电话就跑到他的办公室,他一脸严肃地问我,你在家里做什么啊?春节你们都蹲在家里干什么啊?你手下那些人呢?
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明白不了他的意图,直接回答说春节放假了呀。
他有点光火了,说你党刊不是要联系群众的吗?春节是最好的时机嘛!我听懂了。回去后连忙电话把下面的同志找来了,布置任务。我们当时的同志纪律性都非常好,部队作风,我让他们到各个区去联系通讯员和值班的人,把了解的情况出了份情况书给柯庆施,他这才表示满意。
第二年春节,我们有了经验,有意识地安排了一些活动。我组织了静安寺街道能够弹弹唱唱的小青年们,由我们编辑记者带队,送戏下乡,来到金山永久大队茶馆店演出,走群众路线,走基层。
记者:这不就是现在文化宣传领域提倡的“走、转、改”嘛,没想到,“文艺下乡”党刊当时就搞了。
丁柯:刊物的生命力根植于基层,根植于群众。
现在我们强调的一套,其实就是要恢复传统的那套贴近群众的工作作风。记得市委搬到海阁饭店(音)后,就是现在的华山路口,静安面包房那里的转弯处。这个地方当时每天停满了等客人的三轮车,50年代马路上都是人力三轮车接客的。柯庆施早上上班经过这里,看见大门口都是三轮车等在那里,车夫们没事都在打扑克,他关心起我们的党刊宣传作用了。
那天一上班,柯老就让秘书把我叫下去,那时柯的办公室在五楼,我在九楼,到他办公室后,他就问我,你看见门口的三轮车吗?我说看到的。他又问你注意到他们都在做什么吗?我说没有。他说他们都在打扑克,你不是说《支部生活》发行量很大吗,为什么不叫他们看《支部生活》呢?我一下子被问住了。我说我真还没想到这点,怎么将《支部生活》推销给这些三轮车夫们看。他说,那你们快去抓抓看,如果都是在看《支部生活》,那就比打扑克好。
从今天的意义上来讲,这就是如何抓好意识形态工作,如何抢占各个领域的制高点的问题。
那时,有个三轮车行业的党总支部,我们与他们取得联系后就过去了解情况,问三轮车工人中有没有《支部生活》的读者,政治上要求进步的那类人。他们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叫程德旺的三轮车工人,说他不是《支部生活》的读者,但表现很好,属于先进模范类的,建议我们是否可以去采访他一下?
派记者下去采访后,发现这个人身上果然有不少闪光点,我们将他的先进事迹登在《支部生活》上,这个人很快出了名,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这件事在三轮车行业里反响很大,由此《支部生活》成为三轮车总支推荐的读物,党刊的宣传就这样慢慢渗入进去了
五六十年代,上海的很多劳动模范、先进个人都是通过党刊宣传出去的。
记者:党刊的政治地位显而易见。作为党刊社的总编,您有没有设计过一些活动,开展编读方面的业务培训和学习,让党刊成为一块“磁铁”?
丁柯:那时《支部生活》影响很大,我们就想出一个点子,开个《支部生活》读者讲座,放在陕西南路上的文化广场,为期一周,请市委领导到这个会上去作报告。那时候,文化广场是上海最大的会场,可容纳1万多人。
听的人不是凭级别发的入场券,而是按《支部生活》的读者身份来领票子。结果票子全部发完,全场坐得满满的。请谁呢,请市委领导陈丕显、曹荻秋等来讲形势。
那时公安部门还来警告我们,说你们这样大规模组织活动,如果有坏分子搞破坏怎么办,有治安问题存在。那我说你们要管好的呀,要保证交通通畅。当然,我们也做了很多这方面的预防工作。来参加会议的读者都是兴高采烈的,能够来听市委的报告,看到市委的主要领导,有些区委书记可能都没见过陈丕显,而这些读者却有机会见到,非常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