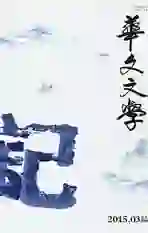钟理和日记与创伤记忆
2015-07-01计璧瑞
计璧瑞
摘 要:本文尝试以“新版钟理和日记”为分析中心,从所记录的事件、风物、生活细节和情感经验去探究钟理和的记忆轨迹和精神状态,借用“创伤记忆”论述说明钟理和日记其实是作者人生创伤记忆的记录,兼论日记与书简的不同功能。本文综合钟理和日记的写作时间、地点和写作时的生活状态,将其划分为四个时段,说明不同时段日记的书写内容和关注点也各有不同;“创伤记忆”是贯穿钟理和日记后三个时段的中心内容,它们不断叠加、难以摆脱、重复再现;钟理和正是以书写的方式宣泄和纾解创伤记忆导致的精神痛苦,写作和记录就是一种精神的疗伤。钟理和个人的“创伤记忆”在后人的持续论述中成为隐喻,成为台湾文学的集体记忆。
关键词:新版钟理和日记;创伤记忆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5)3-0066-09
《新版钟理和全集卷6·钟理和日记》(2009年高雄县政府版)①相较1976年远行版在篇幅上多有增补;两者相隔的30余年中,台湾文学发生了剧烈演变,对文学史资源的重新解读所在多见。在此之前的全集1997年高雄县立文化中心版和2003年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版,就日记部分已经做了增补,增补篇幅为远行版日记的五分之一;2009年版又再次增补了1942年的4篇日记,成为迄今为止收录日记最完整的版本。其实早在1976年版《钟理和日记》出版之际,今天的绝大部分增补也已为人所知,在一些研究论述中已经可以零星见到它们的身影,只是顾及当时台湾的社会禁忌才为编者所割舍;所以增补部分大多并非新近出土,它们与先前辑录的部分一起汇成了钟理和日记较为完整的面貌。当然,新版全集并非绝对的增补,个别地方也存在删改的痕迹,从删改内容上看应该也与世事变化相关。②尽管如此,从现有日记的写作频率看,增补后的日记肯定也只是钟理和日记的一部分而绝非全部。现存最早的日记始于1942年,至1959年日记终了,期间有多个整年和长时间的空白,现存日记恐不能展现日记主人所记录的全部生活;通过它们呈现钟理和的日常思考和记录的脉络,肯定也会有一些环节的缺失。因此,本文仅就现存日记所作的说明很可能与历史现场存在距离,这也是研究者无可回避的宿命。不过增补后的日记仍然为读者提供了相较以往更丰富的内容,填补了原有的部分认识空间,例如228事件发生前后的日记就显示了当时钟理和的所见所闻所感,可为后人对事件的感知提供个体经验。
日记作为作者对自身日常生活与思考所作的点滴记录,内容零散繁杂,大至历史事件、社会风云,小至日常琐事、情感波动,不一而足;时间因循自然进程,日积月累,逐渐描绘出作者的人生之旅。更重要的是,日记没有预设读者,其个人性、私密性远胜于任何其他文体,它是作者对自己人生记忆的真切复制,虚构、矫饰、说谎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对作家日记的研究实为在文学文本之外探寻其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重要途径,最终会有助于对其文学世界的理解。此外,作为台湾文学的一面旗帜,钟理和已经被持续讲述了半个多世纪,研究成果不可胜数,完成了经典化过程。他的小说世界的方方面面都有众多研究者做出精彩阐释;而日记文本的探讨似还有余地。如果说小说文本呈现的是作者希望呈现给读者的、经过艺术加工后的文学想象,那么日记则是作者本人真实、赤裸的精神记录。鉴于此,本文尝试以新版钟理和日记为分析中心,从所记录的事件、风物、生活细节和情感经验去探究钟理和的记忆轨迹和精神状态。
一
新版钟理和日记始自1942年10月16日,终于1959年12月1日,共计272篇;其中写于大陆时期的有65篇,其余为返台后所写;现存写作篇目较多的年份有1945年52篇、1950年59篇、1956年21篇、1957年57篇、1959年20篇。从写作时间和地点来看,这些日记可大致分为大陆时段和返台时段,后者又可分为台大医院、松山疗养院时段(1947-1950)和美浓尖山时段(1950-1959)。最后一个时段由于时间跨度较大以及作者生活和精神状态的改变,又可再分为前期(1950-1956)和后期(1956-1959)。综合写作时间、地点和生活状态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写作时段,书写内容和关注点也各有不同。
大陆时段最集中的写作是在战后的1945年秋冬至1946年初,此前的现存日记只有1942年10月的4篇,记述了钟理和前往北平房山的良乡和周口店的所见所闻。当时的大陆正值抗战的艰苦时期,破败的乡村和萧瑟的秋风展现了钟理和眼中的北方风情,正所谓“飞沙扑面”、“秋色凄凄”、“荒凉万状”,此时的钟理和应任职于“华北经济调查所”,除记录乡野景色、村民举动,发思古之幽情外,没有关于个人心境的说明。大陆时段的其余日记写于1945年9月至1946年1月,共61篇,记述了大量光复后北平的社会现象、世态人心,也抒发了个人在时代转折期的感慨,不仅涉及在北平台湾同乡会的活动、因战争而失散的人们的相互寻找、一些投机分子的见风使舵、战后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冲突,还有国际时事、个人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
对战后时局和人心的忧虑感慨是钟理和本时段的心境,他感慨“自唱政治革新,官吏肃清以来很久了。但似乎‘官场现形记尚有重写的必要。也许在中国是写不完的一部小说。”(1945.10.13)“摇身一变的时代与摇身一变的人们。什么都是摇身一变,都在摇身一变。只差变得像与不像而已。”(1945.10.3)而他在世事剧烈变化前的迷惘、不打算从事投机的意识也有清晰的表达:“战胜与战败而今已闹了一个多月,然吾尚未由此获得清楚、而且实在的意义、感觉与态度,是不是吾于‘诚字尚欠程度,即是否自己未曾完全把自己推进汹汹的现实里面,抑或因为时局变得太快,并且太过超越了想象而使自己追随不上。”(1945.9.23)朋友劝他加入“新中华日报”(应为《新中华周报》——笔者注),“但我意未决。我想此项事业对我不甚适合。其最大目的与其说在求真正奉任或贡献社会,无宁说是在争名逐利。”(1945.9.15)从中可见钟理和在光复初期从最初的兴奋瞬间转为迷惘困惑的心理变化,他意识到在时代遽变的表象下许多事物并未改变,甚至更令人不安:“亦只有‘平‘京二个字的改换而已。上至紫禁城之大,下至街头乞丐之微,以及跳舞场、麻将、香槟、戏子、妹妹我爱你、高德旺在广播电台说相声、各个院子的秽水和脏土使主妇们皱起了眉头……这些这些,一点儿不改旧样。所异乎从前者,只觉得夜里有需要把门窗关得要比以往严些,和在无线电与报纸上多发现些前此不很常见的‘告××书之类,如此而已。”(1945.10.29)一边觉得在变化的社会面前自己不能适应,一边又深感光复没有带来真正的社会进步,因此他感到失望,决定回到自己的文学写作生活中去:“本来我是打着不干涉任何公事与政治活动的旗帜的。然则我现在正可本着自己的内心的要求做点自己的事。来日方长,且此后只有实力充足的人才可能站住脚,否则过眼烟云非遭到时代的淘汰不可。”(1945.9.13)“而今我只能在艺术里,在创作里找到我的工作与出路、人生与价值、平和与慰安。我的一切的不满与满足、悲哀与欢喜、怨恨与宽恕、爱与憎……一切的一切在我都是驱使我走进它的刺激与动机。”(1945.10.25)钟理和曾经在大陆开启了他的文学旅程,现在也是在这里确立了他未来的理想。
不过,虽然有诸多不如意,钟理和的北平生涯仍然是他一生中难得的轻松与自由的时段,不但完全看不到后来造成他后半生贫病颠踬、抑郁困顿的创伤记忆,就连曾经的“同姓之婚”的痛苦也在北平的相聚相守中被隐去——奔赴大陆本是为了摆脱这一痛苦;从日记上看,他做到了。在光复后的北平,钟理和有着相对丰富的文化生活,观剧、读报、看电影和展览、去桌球室、到太庙和中山公园游玩、与台湾同乡频繁往来、接待来客和访问友人、表达对五四运动和鲁迅的理解、臧否各种社会现象等等,构成了他短短几个月中的日常生活。他敏于观察外部世界,不愉快的感受并不来自自身,思考也有外向和开放的特点;对未来,毋宁说他是怀抱希望的。
1946年返台后,钟理和身染肺疾,这一时段的日记正是从他1947年入住台大医院开始的。这一时间点不但是钟理和个人生活的转折点,也是台湾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刻,疾病与事件双重影响下的生活,构成了自入院到出院三年间钟理和日记的基本内容。现存返台后的第一篇日记就写作于1947年2月28日,这一年的全部3篇日记均围绕这一时刻,他从病院内观察着外部的动荡,记录了冲突的场面、本省民众的愤怒和外省民众的委屈,基本没有主观评价,只是通过景物描绘和人物对话,流露出对事件的倾向性认识:“街道静悄悄地没有多少行人,望出去全街死气沉沉,有如死市。公园的树木在没有星月的黑昏月光里耸立着,有如一丛丛的黑椎,地下全是这些树木所投下的黑漆漆的影子。这些黑影一个个都像藏着无穷的恐怖。”(1947.2.28)“我由此想起了枝水对我说的:就是没有二二七的事情,过几天也免不了要发生某种事情的。”(1947.3.2)联系到此后钟和鸣和表兄邱连球因事件系狱,以及多年后钟理和对钟和鸣的思念,可以判断228事件不可能不在钟理和内心留下惨痛记忆。不过228事件对他个人的影响并不直接。
跳过1948年的空缺,1949-1950年在松山疗养院的日记记载了钟理和人生的又一重大创伤。此时,疾病已迫使钟理和丧失了工作能力,被隔绝在充满死亡气息的疗养院中。日记记录的天地仅限于病院窗外的风景和病室中的人与物。他心如止水却时有涟漪,窗前的茶杯仿佛鼓满风帆的船,“谁敢说它是没有意志的?我守望着这只满孕着西北风的小小的帆船;洞开的窗台,对它是无限广阔的大海呢!它是会完成他的航程的!”(1949.5.10)他以这样的联想传达内心的希望。然而希望之门依然渐渐关闭,疾病日渐沉重,而且“肺病的悲剧,肺病人的苦恼,在疾病自身者少,在患病之故而引起的心理的和环境的变化者多。有大决心,大勇气的人庶几能安然渡过,但病好之日,也许只剩两袖清风,孑然一身;反之者,则就可悲了!”(1950.4.16)他感到被世界遗弃,这是以往未曾体验的;他用诗意的、充满渴望的文字诉说着心中对健康生活的期盼:
不是吗?看吧!油加里树的那向,人类的生活展开着它的内容;在田垅间工作着的、在唱歌的、在想吃东西的、还有小贩们神气而调谐的吆呼;那条沥青路上,汽车由两边开过来,点点头像吃惊的,慌张的又开过去了,周围的工厂的烟突,向空吐着拖着尾巴的黑烟,这不正说明了外面正在进行着和经营着人类的生活么?到了夜间,便是这些地方,灯火辉煌,明灭地,组成地上的星座——人间是这样美丽的!
但是这些都与我们无份了!
据说我们是有了病的人,已经是和社会断绝情缘了,于是在我们周围筑起了一道围墙,隔开来。墙内与墙外是分成两个世界了;这里有着不同的生活、感情、思维。而墙前围植的如带的一环油加里树林,则不但加深了两个世界的距离,而且是愈见其幽邃和隐约了。
我们由掩映的树缝间望出去,人间即在咫尺;由那种我们失去了的生活、人情、恩爱、太阳、事业,不断向我们招手。
——1950年4月28日
这个时段的钟理和时常夜不能寐,他时而灵魂出窍般地从外部审视自己的躯体,时而痛苦地咀嚼着内心的纠结,在家庭责任、义务和对亲人的内疚中挣扎。妻贫子病、现实的死亡威胁、肉体禁锢和经济窘迫,使他无暇顾及其他,他的文学理想已经远去。每日在冰冷机械的治疗、近在眼前的死亡、病友的惨状、失望和绝望间不停穿梭,钟理和的精神陷入困顿。如果没有读过这段病院中的日记,是很难体会疾病带给钟理和的绝望和恐惧的。他仍然向外部世界张望,但自己却不在其中;他远离亲人,孤立无援,只有靠自我诉说来战胜恐惧。不少日记篇幅较长,不但记事,更记录情感与心境。临近手术之际,疾病导致的痛苦、生死未卜的巨大心理压力唤醒了尘封的创伤记忆,汇聚为最为动人的给妻子的遗书。这是钟理和日记中少见的向他人倾诉的部分,这篇长达数千字的日记回顾了曾经决定他人生轨迹的爱情婚姻,他在生死存亡之际希望借助曾经的果敢和力量战胜病魔,绝处逢生;也以对创伤记忆的回顾与倾诉抒发压抑已久的激情:
我们的爱是世人所不许的,由我们相爱之日起,我们就被诅咒着了。我们虽然不服气,抗拒向我加来的压迫和阻难,坚持了九年没有被打倒、分开,可是当我们赢得了所谓胜利携手远扬时,我们还剩下什么呢?没有!除开爱以外!我们的肉体是已经倦疲不堪,灵魂则在汨汨滴血,如果这也算得是胜利,则这胜利是凄惨的,代价是昂贵的。……你,我,灰沉天气,霏霏细雨,和一只漂泊的船……这些,便是当日参加我们的‘结合典礼的一切。别人的蜜月旅行,却变成我们的逃奔了。逃到远远的地方,没有仇视和迫害的地方去。
——1950年5月10日
这是钟理和日记中第一次出现对刻骨铭心的同姓之婚的诉说,以往的苦痛此时涌上心头,过去抗争宿命的悲壮,化为今日再度抗争的体验。
重获新生的钟理和于1950年底回到家乡,至1956年,他在疾病、困苦、寂寞中度过了闭塞孤独的岁月。乡人的生活、家居的困窘、次子的病亡、风俗、气候、农事、典故、传说、谚语等等组成了本时段日记的内容,这是一段平凡庸常的日子:“越来越是觉得一切都是如此的简单无聊,就是生活也是如此,而且平凡。没有惊奇,更没有思索的内容,好像凡有的事物都是向人毫无掩饰的翻开了底面,告诉人那里面并没有什么东西。所以毋庸思想,不,或者它已变成了多余的东西了。然而果然如此么?那不是意味着心灵的迟钝和空白么?迟暮的又一例证——也许有需给自己唱挽诗了呢!”(1953.7.25)虽然如此,故乡的自然美景为他灰色的心境带来一抹亮色:“一仰首,瞥见了被夕照染成金黄色而透明的竹子,几令我疑为火烧。夕阳由山坳外,像手电筒似的照在东山上,山变成了一匹黄缎。向阴外,则幽暗而溟濛,有深深的静谧。崇美而庄肃的黄昏!我很少见到如此美丽的夕景。”(1950.12.22)尽管钟理和感受到故乡的封闭与沉闷,但却毫不迟疑地表达他对故乡的爱:
尖山到龙肚这一段路,已有十多年不走了。从前,我在这条路上走过多少,就问问路旁的那些小草,人家的槟榔树和石块,该还记得的吧!我还清楚记得那些,沉默的桥、曲折的流水,隐在山坳,或在树阴深处,隐约可见的和平的、明净的、潇洒的人家,横斜交错的阡陌,路的起伏,给行人歇息的凉亭,绿的山,古朴的村子……这一切,不拘在什么时候走起来,或者走了多少次,是总叫人高兴的!愉快的!多少幽情为他呼唤!多少惦念为他悬挂啊!
——1953年8月6日
如果没有这样的深情,他也不可能在病痛中写下本时期的《同姓之婚》、《笠山农场》和《大武山之歌》,或许正是这种故乡情和对写作的执着,支撑着钟理和度过了这段平凡沉静的时光。中国现代小说,包括左翼作家作品的阅读也被记载于日记中,可由此窥见钟理和写作的一部分文学资源。他的生活范围和人际交往相对固定,也促使他进一步走向内心。
之所以将美浓尖山时段的日记以1956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是因为1956年是钟理和开始寻求重返文坛的时刻,同年3月2日、4日、5日、7日、15日、24日、4月2日的日记中都记载了他尝试,虽然写作恢复的时间要更早;这一年也是《笠山农场》获得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长篇小说奖的年份。接下来的1957年,由于与文友的交往和参与《文友通讯》的活动,钟理和的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果结合与友人的书简来看,此时的钟理和开始重燃对生活和文学的激情,时时表达文学意见;文学交流也带给他莫大的振奋,他的文思、精神又开始汇入社会,实现写作理想的希望被再度点燃。还是在1956年,关于疾病的记录在中断几年后又再度出现,说明疾病又开始攫住他,成为他生命最后几年的梦魇。
本时期的日记除了继续对风土民情、家居生活、自然风光的记录外,还有对因谋生而影响写作的焦虑,比如曾多次表达对代书工作的不耐和质疑,并引用李荣春的话当做自己生活的写照:“我的一生为了写作什么都废了,至今还没有一个自主的基础,生活一直依赖于人……为了三餐,将宝贵的时间几乎都费在微贱的工作上。”(1957.5.9)虽然也为自己追求理想而牺牲家人的幸福而产生罪恶感;更多的是对文学生活的向往、期待和参与,一些文学评价在日记中得以表述:“廖清秀著《恩仇血泪记》完。刻划生动,性格创造亦颇成功。惟以省籍人而初习写作,造句遣词,稍嫌牵强生硬。”(1957.3.13)“杜斯妥也夫斯基,是我所不喜欢的作家。他作品的夸张、矫情、不健全、不真实,令人不生好感,他写的东西和我们的生活很少关系。他不关心地上的生活。……他所全心关注的是天上的存在者——神。”(1957.12.4)现存的最后一篇日记是阅读海明威的《战地春梦》和关于写作风格的理解:“表示一个作家的独特的风格,可说是那些必不可少的文字之外的铺张,敷衍,繁复等文字,如把一篇作品删到或压缩到只剩下必不可少文字比方像新闻纸上的报导,那就没有风格了,也不会再有风格了。”(1959.12.1)类似的内容占据了本时期日记相当多的篇幅,说明文学是钟理和生命晚期思考的重心。他对自己获得的承认也感到欣慰,在1957年4月25日的日记中就抄录了当时《文坛》杂志对他的评价“作者的语言文字虽然略有生硬之处,但描写优美深刻,人物均有极显明的个性,文字中洋溢着一种崇高的思想与感情,处处都见出作者对文字有精湛的修养”;“《竹头庄》在各文友间获得如此好评,是我意料之外的事。”(1957.10.11)也可见文友的鼓励让他喜出望外。
这一时期的钟理和一方面拓展了他的文学天地,无论是写作成就还是文学活动的参与,都达到了他一生中的高潮;另一方面,他的内心感悟和纠结也更加深入,理想的实现已经看到了曙光,而病痛对生命力的削减也与日俱增,两者间的冲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他试图以佛家思想参悟生死(1957.5.23),他甚至感觉到死亡距离他如此之近(1959.5.21)。“钟摆是永远没有停止的,因为更合理、更安全、更舒适的生活总是在现在的后边。人类的灵魂便这样永远追求下去。等到他已舍弃了追求的欲望或者终止了他的追求,他便死去。于是钟摆停摆。”(1957.5.7)他以这样的沉思为生命与理想的关联做了说明。
二
从钟理和各个时段的日记中可以发现,他自始至终满怀文学理想,却因疾病和贫困而几经蹉跎;大陆时段和美浓尖山时段的后期,是他思维活跃、社会参与较强的时期;后者更是他的文学创作最为活跃的时期。日记较为详尽地记载了钟理和所经受的艰难困苦,相比小说文本的折射和加工,这些苦难更直观,更真切,令读者更直接地发现真正影响他的生活、心理、精神和写作状态的因素。本文将这些因素称之为创伤记忆,它们可能存在不同的形态,有的虽然发生在过去,但记忆仍然延续,例如曾经的同姓之婚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创伤;有的发生在当下并一直持续,如病痛、贫困和写作得不到承认的苦恼。同样,有的来自外部,如文化传统给予同姓之婚的压力和1950年代本省籍作家被压抑的现实;有的来自自身因素所致的贫困和疾病。创伤记忆的不断持续又会使当事人将不同的记忆叠加,形成因果链条,并加重其面对新的创伤时的痛苦。在钟理和日记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形:同姓之婚→颠沛流离→疾病→贫困→难以实现文学理想。
创伤(trauma)与创伤记忆(traumatic memory),前者指的是“灾难性事件、暴力、严重伤害事件对受害人所产生的长远而深入的伤害和影响。”“受害人所受到的伤害往往不仅是身体上的,而且最终会侵入精神,并在精神深处对受害人产生巨大影响,所以,创伤其实就是心灵上、精神上的创伤。”③如果说创伤是某个伤害性事件作用于某个时段的某个人或群体的话,那么创伤记忆就是创伤导致的精神影响。“精神创伤是由某一事件所引发的一种不断重复的痛苦,同时又体现为从这一事件现场的一种不断别离……要倾听产生此创伤的危机,并非只倾听这一事件的本身,而是如何静听别离。”④这里的“别离”“是指人试图在精神上或者情感上摆脱某种困扰而不能。这种‘别离可能充满着某一难忘事件给人留下的强烈印象、思想和情感,这种‘别离还可能成为一种无法证实,但又似是而非地‘让人想起一件尚未被完整地经历过的往事,但主体却要摆脱它,正处于试图‘别离却又不能的状态,所以,才给人带来了精神的无法选择,这种无法选择也就成为心灵的创伤。精神创伤是人在受到伤害后,留给主体的记忆。他试图摆脱这种记忆,却又处于不断记忆和不断摆脱之中,精神创伤成为主体的一种心理状态。”⑤“当一个人面临一种困扰自己的伤害时,或者说当一个人面临他或者她难以承受的思想和情感时,由于无法整合太多或太过强烈的刺激,他或者她就会选择逃避伤害,转到与伤害无关的思想和情感上去。于是,与伤害有关的概念就会被撇开,或与正常的意识相脱离,成为‘固着的观念。这些‘固着的观念,其实就是创伤记忆,虽然越出了意识,但是仍存留在受创伤者的观念范围中,并以某种再现伤害片段的方式(诸如视觉意象、情绪条件、行为重演)继续对他或她的思想、心境和行为施加影响。……尽管对于受害人来说,他或她试图摆脱创伤记忆,却又以一种更加内在化的方式记忆着创伤,这时创伤记忆进入了人的潜意识中,继续对人发生着潜在的作用。”⑥对创伤记忆的描绘存在这样一些关键词:“刺激、固着、重复、再现”。⑦就是说,人所经历的伤害事件一定会在后来的人生中形成某种难以摆脱的记忆,或不随时间的推移而削减其影响、并不时再现的某种症候,这种记忆和症候会被称之为创伤记忆。
和上述关于创伤记忆的论述相对照可以发现,钟理和日记其实就是他大半生创伤记忆的记录;同姓之婚导致的伤害是他人生所遭遇的第一次重大精神创伤,“被压迫的苦闷和悲愤几乎把我压毁。”⑧虽然曾经试图忘记,却终于成为“固着的观念”,不断在他的生命中重现。这一精神创伤之刻骨铭心,除在北平的一段相对放松的岁月外,这一记忆从未远离过他;当他因疾病而陷入焦虑、恐惧和窘境之际,这一记忆更是死死地缠住他。他在文学书写中的不断重复,如小说《同姓之婚》、《贫贱夫妻》、《笠山农场》;他在面临生死关头的回想,如手术前写给妻子的信;他在遇到人生挫折时的感叹,如日记中记录的遭遇生活磨难、不幸事件时产生的被诅咒感;他在与友人对话时的诉说,如书简中对个人境遇的描述,都闪现着这一巨大创伤的阴影。更有甚者,钟理和的创伤远不止如此,致命的疾病和经年的治疗,不但摧毁了他的健康,也摧毁了他的信心和家人的幸福;抱病写作的艰辛和无数次被退稿的沮丧等等,都在原有的创伤记忆之上不断叠加。这些叠加的精神和肉体的创伤甚至还未来得及转化成记忆,而是时刻面对的体验,当他通过日记或其他方式将之记录下来的时候,体验才转化为记忆,这种从体验到记忆的周而复始,直到他的生命走向尽头才告终结。
很多时候,创伤记忆往往被视作国家、民族或群体的记忆。在中国大陆,“人的‘创伤记忆其实是人的‘国家观念的‘创伤记忆,与人终隔着‘道德之性,记忆的创伤化未化到个人的生存论根底。”⑨即便是一些个人化经验,也一定与国家、民族的大叙述相关,否则,这种创伤似乎是缺少意义和价值的。这种认识在强调文学社会功能的时代是十分普遍的,它忽略了相对单纯的个体经验对作家精神心理的巨大影响。在钟理和这里,他的创伤记忆最直接的来源是非常个人化的,并非可以复制于同时代的其他人。由于疾病的制约,也由于性格因素,钟理和并不擅长书写社会重大矛盾和问题,他的写作也曾经被认为与时代精神结合不够紧密,⑩这显然是以经典写实主义的社会使命感和道德要求来评价钟理和,今天看来存在着症结不明的问题(不仅是认同或立场的问题);如果从创伤记忆的角度看,钟理和所经受的创伤是如此强烈,以至于直接剥夺了他关注时局、关怀社会的可能,反过来增强了书写创伤、反抗宿命的执着,因此他的文学写作集中于曾带给他刻骨铭心记忆的爱情婚姻主题实在是自然不过的。在他未生病时的大陆时段日记中,短短几个月就记载了国共之争(1946.1.4)、政治协商会议(1946.1.11);思考了政治与国家的关系(1945.10.25),借媒体报道评论社会问题,比如教育问题等(1946.1.5),甚至谈及香港的归属(1945.10.5),不时臧否时事,虽有他者眼光,却也有参与精神。这对于既没有机会投身日据台湾的社会运动,又与大陆的全民抗战没有直接关联的钟理和来说,他的社会关怀其实并不弱。即便在返乡后深受疾病困扰、与外部世界交流相对困难的日子里,钟理和也在关注如台湾托管问题(1950.3.21)、原住民问题(1950,3,27)、地方选举(1957.4.18;4.21)、刘自然事件(1957.6.15)等等,还在旁听演讲、参与乡里活动等等。可见钟理和已经尽其可能表达着对外部世界的关注。
那么,钟理和的文学写作执着于爱情婚姻主题就有了特别的意义。首先,写作是他的人生理想,他必须用写作证明自己的生命价值,他不可能采取其他的方式继续生活;第二,疾病和贫困限制了他的活动空间与时间,在维持生计都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他没有充足的精力参与社会,日记和书简中曾多次记录了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阅读不易,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以谋生的日常生活;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个人的创伤记忆在钟理和心中具有压倒一切、无可回避的重要位置,因为“创伤记忆在某种条件也是一种受创个体的个人思维形式,它会不由自主地面对诸多日常事物与日常事件表现为对过去某种创伤性经历的回忆,所以,这种记忆从思维层面上来看,是绝对个人的、孤独的、非社会性的。”“这种精神的创伤必将寻求表达的方式,在表达时,或者是受体无法适应生活,或者是受体经过巨大的努力能够有所摆脱,但再现却成为一种必然。”{11}钟理和的表达方式就是通过书写宣泄和纾解创伤记忆导致的精神痛苦,写作和记录就是一种精神的疗伤。而乡土,不但是他的实际生活空间和生活内容,也是他疗伤的良药,无论是日记中的自然美景还是《笠山农场》里世外桃源般的故乡风情,都是他为治愈创伤所设定的场景,他在这美好的场景中讴歌爱情、净化心灵,以此获得对创伤记忆的超越。日记中频繁出现的乡野间的各种飞鸟,似乎也在暗示着作者将自由飞翔的欲望寄托在它们身上。
在钟理和被重新发现的年代,人们大都会把他的个人创伤与社会问题相联系,这不但出于当时的文学功能观和为台湾文学寻找本土资源的动机,也存在着客观的缘由,毕竟钟理和的颠沛流离、历经磨难不能脱离大时代的左右,而他“倒在血泊中的笔耕者”形象也象征着同时代本省籍文学人的艰辛处境。因此钟理和的创伤记忆不仅仅属于本人,在他生前及身后,这种创伤的隐喻性随着他的人生和文学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知,以及对他的研究的不断强化和绵延而持续维系,创伤记忆始终没有淡去。逐渐地,它成为台湾文学乃至台湾社会的集体记忆。1970年代,《钟理和文集》(1976年远行版)的出版与乡土文学运动几乎同步,钟理和的被重新发现实在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甚至与乡土文学运动相得益彰;它也让钟理和个人的悲情汇入了本土台湾的悲情命运之中,成为一个巨大的隐喻。倒是钟理和逝世之初王鼎钧的纪念短文提到了疾病与钟理和写作风格的关系,认为这是他“在观察人生时,他的眼珠是灰白的”和“笔调苍凉、低哑,字里行间有不尽的悲悯之情”{12}的原因,将理解侧重在钟理和个人的创伤记忆上,这一点也被今天的研究者所注意。{13}
说钟理和的创伤记忆是一个社会隐喻,正如将结核病和贫困相联系的隐喻一样,其实也是一个通常的自然联想,“结核病被想象成一种贫困的、匮乏的病——单薄的衣衫,消瘦的身体,冷飕飕的房间,恶劣的卫生条件,糟糕的食物。”{14}更何况在钟理和的生活中,结核病和贫困是真实的存在,完全不需要联想和引申;这种事实加上他的弱势、他的被压抑、他的孤苦和抗争都非常适切地与台湾在地争取权利的意愿相吻合,人们能够从钟理和的创伤记忆中移情而感同身受,将他的创伤当作自己的创伤,乃至社会的创伤。实际上,钟理和日记在隐喻与真实之间作了残酷的划分,真实与隐喻互为因果。这里的疾病隐喻并非将社会现象以疾病意象来隐喻,而是将真实的疾病状态挪移为现实社会的隐喻,不是以疾病的隐喻义来隐喻社会,而是以个人真实的疾病来唤起社会联想,以改善病人的处境、提起对某个时期或某个群体的注意,它不是一个形容词、一个意象,而是一个名词、一个存在。
有研究者提出了“苦难如何经过创伤记忆向文字转换”{15}的问题,虽然论者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尝试探讨这一问题,与本文的论述中心不尽吻合,但或许可以由此引发对钟理和创伤记忆表述的不同层次的认识,钟理和日记应为原初的、本真的记忆表达;书简为第二层面的、面向小众的表达;小说则是第三层面的、面向大众的表达。三者间除有无读者或读者群之大小之区别外,还有纪实与虚构、作者情感投入多寡之差异;日记中情感最强烈的“遗书”恰恰是预设妻子为读者的,归根结底还是文体功能的不同。人们会看到,当存在倾诉对象或读者的时候,情感或意愿的表述会更加丰满。从创作心理来说,作者当然期待将情感或意愿传达给他人,唤起他人的共鸣。这里不妨再就纪实文本创伤记忆的不同层面做出思考,即对日记与书简的不同功能作进一步说明。
“新版钟理和书简”{16}的起始时间与日记美浓尖山时段后期的开始大体接近,即他与《文友通讯》诸位本省文友相识的1957年。与日记相比,钟理和现存书简在时间上更集中,也更接近他生命的终点,{17}从最初致廖清秀信的1957年3月8日起,至1960年7月21日致钟肇政信止,总计只有3年多的时间,共121封;最后的书简距他的离世不到半个月。它们与日记一起营造了钟理和人生晚期的社会活动场域,补充了日记对本时期生活和思考的描述,且更集中于文学活动。书简的绝大部分是给文友钟肇政和廖清秀的,合计103封;其余不到20封分别给其他文友和家人。对照书简和日记可以发现,书简的意愿表达要强烈得多,在1957年9月6日给廖清秀的信中有这样的表述:”我们若有刊物,当会有更广大、更深入、更确定的发展,因为我们可以打进社会里去。届时,我们的文艺活动已不再是私人间的事了。只作为发表作品的园地的看法,我认为将不是我们全部的目的,那后面应该还有更远大的视野——台湾文学!”类似的表述在日记中很少见到。书简中常见的急切的诉说和请求,也表达了钟理和在长期的孤寂之后与同道相遇,并期待理想实现的迫切心情。
或许是给文友的信占据绝对数量,钟理和书简的基本内容也主要围绕文学问题展开,如关于方言文学的讨论、本省作家的生存状态、文友交流、阅读心得、投稿事宜、参与征文等等,同时抒发因贫病导致的困顿、沮丧和绝望之情绪。一些话题多次出现,如《笠山农场》书稿的命运、疾病的反反复复、要不要投稿和怎样投稿的犹豫困惑等。总体上,书简仍然是创伤记忆的再现和补充,那些文学活动导致的痛苦和屈辱——一次次的退稿、艰苦的写作条件、因病痛而中断写作和改变计划等等——时时制造着新的创伤记忆;但与日记相比又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这些新的特征与书简的功能相关。
首先是对话性质和信息交流的特点。书简写作必定存在对话的需要,是小范围内一对一的交流,写作者和接收者是诉说与倾听的关系,甚至能够从一方的诉说中大致推测到另一方的信息反馈,因此书简不是“独语体”,它存在的前提是对话关系和交流需要。这决定了内容的相对集中,即围绕某个主题展开,有特定的目的。就钟理和书简而言,读者也可从中看到他的社会活动轨迹和交往记录,以及他与文友的文学理想。这方面的内容相比日记有所拓展。
第二,由于书简的上述性质,它成为钟理和向他人诉说其创伤记忆及抒发情感的重要方式,也是他寻求精神寄托和实际帮助的基本途径。他在书简中诉说自己的遭遇并提出许多请求;大量的倾诉式话语和请求不但是情绪宣泄的表达,也有寻求文学活动支持的考虑。书简是他文学生命的生存需要,是他将创伤记忆与友人分享以纾解痛苦的需要;是一个生活困顿者寄希望于以文学拯救人生所发出的求救信号。这也是日记文体所不具备的功能。试举例如下:
我的情形很坏。我不知道今后和兄等共同奋斗的日子尚有多少?……
我很寂寞,请兄多多来信以慰病怀,暂时我恐怕不能多写信了。
——1958年1月12日给钟肇政的信
我时时这样麻烦你,心中着实不安,……但我又没有办法不麻烦你,而且此后还有一段长时间必然要继续麻烦你呢。
——1959年12月27日给钟肇政的信
由我开始学习写作起,一直至今,既无师长,也无同道,得不到理解同情,也得不到鼓励和慰勉,一个人冷冷清清,孤孤单单,盲目地摸索前进,这种寂寞凄清的味道,非身历其境者是很难想象的。现在,忽然发现身边原来还是有这许多同道,自己并不是孤军奋斗,这对精神上的鼓舞是很大的,高兴尤其大。
——1957年3月22日给廖清秀的信
这些书简冲破了日记面对内心的独语形态,开始将创伤向外部投射;与小说相比其读者十分有限,但在非虚构意义上它们与日记一起构成了创伤记忆的前两个层面,共同承担了创伤记忆的实录。至于书简的文字表述与日记相比来得典雅和书面化,倒不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书简的写作考虑到了特定读者的存在。
上述简略的分析从创伤记忆的角度考察钟理和日记并兼及书简,尝试以未加想象和虚构的日记文体探讨钟理和的精神世界,尚未充分讨论纪实文本与虚构文本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的对应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对创伤记忆的不同表现。创伤记忆对钟理和来说不但是他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他文学写作热情的来源,是成就他作为重要小说家的基本底色;这些记忆可以从日记和书简中找到真实的印证。
(本论文初稿宣读于“第一届文化流动与知识传播——台湾文学与亚太人文的相互参照”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台湾大学台文所,2014年6月28-29日)
① “新版钟理和日记”为钟怡彦编:《新版钟理和全集卷6》,高雄:高雄县政府文化局2009年。以下涉及日记的内容和引文的部分,除标注日期外,不再一一注明出处和页码。
② 远行版全集日记1945年10月31日所记“蒋主席的诞辰!愿主席与祖国同老同光荣。”一句在新版中被删去。见张良泽编:《钟理和全集6·钟理和日记》,台北:远行出版社1976年,第43页。
③{11} 卫岭:《奥尼尔的创伤记忆与悲剧创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26页;第28页。
④⑤ Cathy Caruth: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the Jone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p.153. 转引自上书,第26页。
⑥⑦ Pierre Janet, LAutomatismepsychologique, Felix Alcan.1973, Paris, Societe.转引自卫岭:《奥尼尔的创伤记忆与悲剧创作》,第27页。
⑧ 《钟理和自我介绍》,《新版钟理和全集卷8·特别收录》,高雄:高雄县政府2009年,第277页。
⑨{15} 张志扬:《创伤记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41页。
⑩ 叶石涛曾有这样的评价:“在《笠山农场》里,他本来有很好的机会发抒他对时代的反映,可是他好像企图在逃避什么,而把重心放在他本身的恋爱故事上,再加上山光水色就完了,我们看不出什么时代意识来,甚至文学作品中最起码的背景也交待不清,这实在是很可惜的事。”见叶石涛、张良泽对谈,彭瑞金记录:〈秉烛谈理和〉,原刊《台湾文艺》第54期,1977年3月;转引自应凤凰:〈钟理和研究综述〉,应凤凰编选:《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钟理和》,台南:台湾文学馆2011年,第70页。又唐文标曾论及“在当时日本欺凌中国人,以及伟大的民族抗日战争,他没有采取更积极的立场,没有参与更建设的行动,更很少看他提及,这一点不能不说他的世界观太狭隘,只能在个人的爱情生活转迷宫之故了。”史君美(唐文标):〈来喜爱钟理和〉,原刊《文季》第二期,1973年11月;转引自应凤凰编著:《钟理和论述》,高雄:春晖出版社2004年,第74页。上述论者的评价当与1970年代的文学功能观有关。
{12} 方以直(王鼎钧):《悼钟理和》,原载1960年8月11日《征信新闻报》,转引自《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钟理和》,第95页。
{13} 应凤凰的《钟理和研究综述》曾论及《悼钟理和》一文,认为“文评家亦如预言家,把40年后钟理和研究的新面向预先呈现出来。”见《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钟理和》,第65页。
{14} 〔美〕苏珊·桑塔格(Susan·Sontag):《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16} “新版钟理和书简”为钟怡彦编:《新版钟理和全集卷7》,高雄:高雄县政府文化局2009年。以下涉及书简的内容和引文的部分,除标注日期外,不再一一注明出处和页码。
{17} 现存的日记止于1959年12月1日;现存的书简最晚的是1960年7月21日给钟肇政的信。
(责任编辑:庄园)
The Traumatic Memory: A Reading of the Diary of Chung Li-ho
Ji Birui
Abstract: Based on analyses of the new version of the Diary of Chung Li-ho,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Chung Li-hos spiritual status and the trajectory of his memories, and to use the concept of“traumatic memory”to demonstrate that Chung Li-hos diary is a record of traumatic memories in his life. This paper synthesizes the times, the places and the living conditions when Chung Li-ho wrote his diaries, divides them into four periods, and illustrates that the content and focus of the diary varies from different periods.“The traumatic memory”are the common thread running through the last three periods of the diary. This kind of memories continuously overlapped, difficult to avoid, and constantly reemerged. It is through writing that Chung Li-ho gave vent to and relieve his spiritual sufferings resulted from traumatic memories, and thus writing and recording became his spiritual therapy to the traumas. The individual“traumatic memory”of Chung Li-ho has become a metaphor through constant discussions and narratives of later Taiwanese writers, and has been turned into a collective memory of Taiwan literature.
Keywords: the new version of the Diary of Chung Li-ho, traumatic mem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