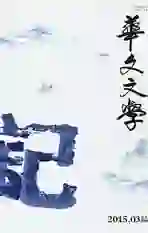严歌苓早期作品与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
2015-07-01蔡小容
蔡小容
摘 要:本文集中讨论严歌苓在1980年代的早期作品“女兵三部曲”,将它们置放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大背景中,与同时期其他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与分析。这三部作品,尤其是《雌性的草地》,其中已包孕着她下一时期创作的核心与精华,深入研究她这一时期的作品对把握她后一阶段的创作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严歌苓;军旅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性文学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5)3-0051-09
从1981年发表小说处女作《七个战士和一个零》算起,严歌苓的小说创作历程已经长达三十余年。如果要把她三十年的创作生涯做一个基本的划分,出国就是那一道分水岭。出国之前,初露端倪;出国之后,气象迥异。一般认为,严歌苓的重要作品都发表在出国以后,但她在1989年出国之前写就的《雌性的草地》不容忽视。
严歌苓的早期作品“女兵三部曲”的前两部《绿血》与《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小有成就,分别获得1987年“全国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和1988年“解放军报最佳军版图书奖”。它们可以用《白蛇》中的一句话来概括:“……一次次演出:全身心投入;每场虽有即兴发挥,大部分却是规定动作。”①这两部作品定位明确,毫不溢出1980年代军旅文学、反思文学的基本框架,完全可以置于当时的中国文学坐标系中一起讨论。
一、绿色的血脉:《绿血》与
1980年代的军旅文学
以题材、风格论,《绿血》是一部纯粹的军旅小说。它于1986年问世,恰好处于军旅文学的“第三次浪潮”的潮头②。1980年代的军旅文学有两部界碑式作品:《西线轶事》和《高山下的花环》,《绿血》与它们有着互补同构的关系。
1980年代的文学生态环境良好,“伤痕”、“反思”、“改革”、“寻根”等文学潮流不断演进,军旅文学亦步亦趋,也呈现出相应的文学格局。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为军旅小说提供了新的题材和机遇。老作家徐怀中1980年发表《西线轶事》,年轻一辈的李存葆1982年发表《高山下的花环》,这两篇小说都以对越反击战场“南线”、“西线”为背景,发表后反响强烈。严歌苓的《绿血》创作于1984年,出版于1986年,也是“南线”战争背景的小说,它对前两部作品所开创的军旅小说的一些新的表现手法和境界不无借鉴之处。
《西线轶事》只是一个短篇小说,但一经发表就赢得极高声誉,被评论“为1980年代军旅小说的基本格局埋下了最初的伏笔”③。它“一改以往军事文学的作风,独辟蹊径,不拘囿于写战场本身,而是把笔触伸到战场以外,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④作者徐怀中当年谈自己创作中的探索,已将其中的独特奇巧道明:“炮火硝烟只是战争之树的树冠,是一眼就看得见的。而一棵树,据说在地下的根部和树冠一样大小,如同它的倒影,把那些看不见的微细根须连接起来,可以缠绕地球多少圈。”⑤避开人人眼中常见的“树冠”而用力挖掘“树根”,这种开拓性的文风,对后来的军旅文学作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高山下的花环》对此有完美的承继和发扬。《西线轶事》是一个突破口,《高山下的花环》扩大和巩固了这个突破口,在思想上、艺术上有新的崛起和突进。它们两者题材相似,风格并不相同:《西线轶事》清新、细腻,如着色淡雅的水彩画,《高山下的花环》悲壮、浓烈,如浓墨重彩的油画,《绿血》更接近前者;在具体选材上,《高山下的花环》描写的是正面战场,《绿血》与《西线轶事》选取的都是战场的侧面,如同正与副的关系,又相辅相成,共同组成南线战场可歌可泣的多幅画卷。
除了挖掘“树根”给读者以“历史纵深感”,《西线轶事》的柔美风格也令军旅小说的面目焕然一新。写战争而笔触婉约,表现人性美和人情美,孙犁早在1940年代就这样做过,但是经过了建国后几十年间军旅作品风格一律的豪壮雄浑,尤其“文革”中对人性的禁锢,《西线轶事》的出现显得难能可贵。徐怀中是一位有扎实的艺术修养和美学追求的老作家,起点高、眼界宽,熟谙外国文学作品,前苏联著名作家鲍里斯·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定为他所喜爱,因为《西线轶事》与之颇为相似:它们都描写战争中的女性,不仅写她们在战场上经历枪林弹雨,也写她们战前的日常生活,二者交织,笔调明快、活泼、委婉、隽永,充满人情味。瓦西里耶夫自谓,他让女兵们成为小说的主人公,可以“使作品更洋溢着深刻的激情……使我有可能赋予作品以更突出的道德含义和更强烈的感情色彩”⑥,道出了女性与战争的关系在文学作品中的美学价值。《西线轶事》写女子总机班的六个女兵上战场十七天,去架设电话线。她们克服了种种困难:高温烘烤、毒蛇袭击、蝎子蚂蝗叮咬、就地如厕、和衣宿营、忍受生理不适急行军——这一切都是违反女性天性的;也在磨炼中飞速成长:起先越军的尸体都是她们跨不过的障碍,后来勇敢地跟敌人短兵相接并俘获了对方。《绿血》也与此相似:严歌苓以自身经历为素材,写一群进入战区作为“宣传队”的七个文艺兵的遭遇,他们在丛林、河滩、甘蔗田、淤泥地里跟敌人的生死周旋。话务兵、文艺兵,都是非主流的战士,活跃在战场“前沿后方”的侧面,《西线》是短篇,《绿血》是长篇,可都是截取几天的长度浓缩地表现战争。或许是出自女作家之手的缘故,《绿血》里浓雾中的孤身女兵,“这呆然的树,这浓浓的雾,像恶梦一样难以摆脱”,女性的情韵更得《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神韵,贯穿在情节中的对爱情的思索和感悟,如:“爱情是否也有它的演化过程呢?就像此刻,它表层的亮度熄灭了,而内核的比重在增加”⑦,也使作品带上了鲜明的女性特点。
这三部作品,虽然都是以女兵为主,却都设置了一个重要的男性与她们相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里是瓦斯科夫,《西线轶事》里是刘毛妹,《绿血》里是杨燹——“一群女兵和一个男兵”,是它们的共同模式。杨燹和乔怡的爱情是《绿血》的主线,他们聚散的一波三折反映着时代的嬗变,这也可视为“历史纵深感”的一种。
《绿血》对英雄群像的塑造,则类似于《高山下的花环》。《花环》中的梁三喜、靳开来、赵蒙生等人物没有一个是概念化的化身,而一旦被作家李存葆创造出来后则成为战场上性格鲜明、血肉丰满的英雄形象,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艺术典型。《绿血》中的人物也是人各其面:性如烈火、黑似“赞比亚”的杨燹,恬静聪慧、灵魂丰富的乔怡,自视甚高的音乐天才廖崎与挚爱音乐却毫无才华的季晓舟,朴实善良的田巧巧与自卑畏缩的“小耗子”黄小嫚等,不仅气息如真,还颇具戏剧性对比。
《花环》的笔法是扎实的写实。《绿血》则大量运用时空交错的手法,长篇幅地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意识流,将宣传队的青年人在战场上几天的横截面、在“文革”中的宣传队生涯、和战后的重新聚首三个生活平面串联在一起,几乎是无处不剪辑、无处不拼贴,在不同时空的接合处都有相同人物、或相似情节的契合对应点,可谓深具匠心。然而,在通过战争来表现社会的广度上,在揭露军队内部的矛盾和阴暗面的力度上,《绿血》显然远未达到《花环》的高度。《花环》只是一部8万字的中篇小说,而作家敏锐地抓住了这场战争的特点,对战争与当代生活的关系进行了一次立体交叉扫描,将前方与后方、高层与基层、人民与军队、历史与现实有机地勾连起来,大刀阔斧地揭示了军队的历史伤痛和现实矛盾,令人振聋发聩。如两发制造于“文革”的“臭弹”,在战场上的千钧一发之际竟然哑然,这个情节的设计正好比“系千钧于一发”,仅此一笔,就多么有效率地控诉了十年动乱对整个经济建设,包括军事工业在内的严重破坏及其恶果!相比之下《绿血》的笔力弱很多,它写军中高干子弟的飞扬跋扈,这与《花环》中高干为子女安排“曲线调动”、乃至上战场前把电话打到前线指挥所去“开后门”,程度不可同日而语。《绿血》主要表达的是战争对人的精神和心灵的巨大震撼和净化作用,这与《花环》一脉相承。战友们在血与火的战场上结下的赤诚情谊消除了生活中的过往恩怨,大家带着全新的精神风貌一起走向新生活。这个主题严歌苓圆满完成,如她借书中人物之口阐释书名的寓意:“军人的队伍像强大的绿色血脉,流动、循环……”⑧。所以《绿血》是一部纯粹的军旅小说,风格清新,但局限明显。太明确的主旨,和情节的过分戏剧化,“使得文本没有了可供二次阐发的空白点”⑨,可见严歌苓这部长篇小说处女作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还是比较稚嫩的。
二、纷扰的思绪:《一个女兵的悄悄话》
与1980年代的反思文学
1986年出版的《一个女兵的悄悄话》是严歌苓“女兵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以发展的眼光看,这个“之二”对“之一”、“之三”恰好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绿血》全书洋溢着理想主义的青春激情,到《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青春成了被回忆、被反思和祭奠的东西,后者的思想容量明显较前者为大。小说以主人公陶小童身陷泥石流、生命垂危之际的纷扰思绪和内心独白来组织,这一构思也比《绿血》要复杂和高明,给了作者以极大的转圜空间。这种以人物的意识活动为叙事线索的结构和表现方式,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为多位作家所采用,如谌容的《人到中年》,以陆文婷大夫在病危时的意识——包括回忆和幻觉——来组织结构,不同的是谌容对“死亡之门”的描摹比较现实,比较逼真或“仿真”,这与小说的主题,即对中年知识分子的关怀,对他们早逝命运的忧伤,是基调一致的;而《悄悄话》中对主人公走近死亡的事实却用的是调侃和荒诞的口吻:
我动不了的另一个原因大概是:我快死了。对这点我特别明智。不过我还是想动一动,这个姿势死起来太不舒服了。我几乎被倒悬着。山势很陡,我头朝下坡躺着,不久前那场泥石流就这样不负责任地把我搁在这儿。
……我的死,多少有点马虎。本来挺壮烈的事,搞得像不了了之。
……我得设法改变一下首足颠倒的睡姿。谁有团支书哪个本事?他酷爱拿大顶,并多次介绍:拿大顶能使身体得到最有效的休息。⑩
调侃英雄形象,是《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通篇的基调和主要问题。
在反思的背景和内容上,《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可以和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1984年)和毕淑敏的《昆仑殇》(1987年)放在一起讨论,它们都对极“左”年代中的荒唐行为进行了旗帜鲜明的反思。
《山中,那十九座坟茔》{11}以极“左”年代为背景,揭示了军旅生活中造神运动的严重存在和严重后果。那些淳朴的战士,一个个胸怀理想、积极进步,然而他们冒死修建战略坑道只是为了某些领导捞取政治资本铺路。为了在地质条件极其不利的山体重建一条“地下长城”,一个“锥子班”几乎全部覆没,山中堆起十九座新坟。战士们死得毫无意义,他们“把生命的圣水倒进了‘龙须沟里”。战士们牺牲后,上级要做的事就是采访、报道、宣传,编造他们临终前的“时代最强音”,给“英雄集体”中的每个人,无论死了还是活着,都戴上一顶“英雄帽”。英雄集体中的每个人都有了封号和“英雄帽”,唯独这集体中最值得歌颂的英雄——营长郭金泰,他什么也没有得到,他没有进入烈士的行列。
无独有偶,《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中有个郭金泰,《昆仑殇》{12}中有个郑伟良。这两篇小说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的故事发生在1968年,《昆仑殇》的故事发生在1970年,都是描写生活在极“左”年代的军人,荒谬地服从一切命令,执着地遵循极端政治教条所宣扬的生存方式,直至跌入生命的悲剧而不自觉。《坟茔》中是挖坑道,《昆仑殇》中是拉练——徒步、背负辎重、吃忆苦饭、听从号令,穿越海拔5000公尺以上、摄氏-40℃、缺氧、无水的死亡地带“无人区”,结果是一个个鲜活年轻的生命在狰狞的自然环境和人为的“革命”环境中陨落。参谋郑伟良对他的司令“一号”提出了对拉练行动的反讦和反思,思考力明显超前的他也在拉练中牺牲。“反思文学中的英雄几乎都是恶风浊浪中的独醒者”{13},郭金泰、郑伟良是那个时代中真正的英雄,他们与极“左”年代中大肆宣传的“英雄典型”有着本质的区别。
基于此,严歌苓在《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中写道,所谓“英雄”,在那个时代铺天盖地的宣传中是“一个教条的形象,一个公式化的形象”,“好像每个英雄都有一模一样的文章等在那里,只等他们一牺牲,就登出来”{14}。陶小童被抢救过来后,立即被记者们包围,让她说她失去知觉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什么。他们连追问带开导,终于写出报道,他们报道的英雄陶小童连陶小童自己也不认识了:一个浑身闪耀着理想之光,充满可望不可即的优秀品质,一心想着献身献身,不顾一切去送命的人。陶小童身陷泥石流之时运用的荒诞和调侃语调,与此构成联系,而这种认知,也是经过了一个过程才达到的。陶小童本是一个感情细腻、善于思考的女兵,她身处的时代对个人提出的要求,个人只有掩藏、扭曲真实的自己才能达到,人们不断地让她“丢掉你那一套”,于是她真诚地这样做了,像蜕皮一样接受改造,不再写日记、诗歌,不再顺从自己的心去爱个性鲜明的徐北方,撇下相依为命的阿爷,她“出操、扫地、喂猪、冲厕所,猛烈地干着这一切”,而她的内心却备受煎熬,因为这一切都有违常情与本心。她终于真正内化了全套的信仰,完全符合了那套标准,变成一个面目全非的人,成为英雄。在濒临死亡的时刻,她清醒地意识到,为了追求信仰,人生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都被她丢失了。她“在精神上经历了一个从‘我到‘非我的历程;从一个纯朴真诚的自然天性,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否定,终于被化成了一个‘左的典型而面目全非了。”{15}
《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的荒诞基调,严歌苓在后记中的自述说得很透:“十多年前,我们存在于这些生活之中,毫不怀疑它的合情合理,而多年过去,当我的目光几经折射去回望时,当年合情合理的生活就显出了荒诞的意味。于是,我便对同龄人整个青春的作为感到不可思议。十年,我们赤诚而蒙昧。反常的社会生活必产生反常的心态,种种不可思议的行动便是反常心态的外化。因此‘悄悄话一眼望去,满目荒唐。”{16}
三、越轨的笔致:《雌性的草地》
有人说“没有资料显示严歌苓在国内是一颗有潜质的文学新星”{17},此言反映出当时的大陆文坛忽视《雌性的草地》的事实。《雌性的草地》1989年出版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内鲜有反响。陈思和教授认为严歌苓“从《雌性的草地》开始显露独特的语言才华”{18},严歌苓自己至今仍然说是这部小说最大程度地表现了她的才华。就是从这第三部开始,严歌苓有了“越轨的笔致”。
1. 题内闲话:“怪胎”与“性感”
《雌性的草地》是1988年的作品。“女兵三部曲”的写作时间的间隔大致均等,这第三部的进步幅度与前两部之比却不是匀速的,而是呈几何级数的跨越。此前不可预测,两三年前的写作风格还属于清新、单纯一派的严歌苓会突然诞生这样一部复杂、深邃、致广大而尽精微的作品。严歌苓自己形容这部小说是个“怪胎”{19},她的好友陈冲则赞美它“性感”{20},这两句出自作家、艺术家的话不“学院”,但准确,触及到了这部作品的两个核心:难以界定性,还有性的主题。
由于题材、主题和手法取向上的多极性,《雌性的草地》难以在文学流派上给予明确界定,它与军旅文学、知青文学、性文学都有着丰富的联系,同时又区别明显,经常体现出特异之处。
2. 军旅背景让位于草地空间
《雌性的草地》几乎不让人觉得它是一部军旅小说。但严歌苓1989年因这部小说应邀赴美参加“20世纪战争文学研讨会”,说明这部小说按某些标准依然可以被归入战争、军事题材的范畴:小说中女子牧马班牧养的是军马,那群姑娘理论上也属于军事编制。军旅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色彩浓郁的题材类型,其自身有着较为明晰的价值判断和道德立场;又由于其所依托的战争和军营文化的特殊性,具有迥异于其他题材类型文学的独特功能。部队是一个特殊的地方。理想是它的魂魄,精神是它的支撑,主流意识形态是它的主导思想,军人更是以服从为天职,他们追求崇高的精神和纯粹的理想信念。“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形象性、具体性转化,对军营特殊文化场域的构建,对广大官兵的宣传教育和思想意识赋形都需要军旅文学以一种含蓄但却明确的道德化文学立场加以巩固和阐扬,进而逐渐形成一种集体性的自觉意识,最终内化为军旅文学最基本的思想方式。”{21}按这样的理论依据,《雌性的草地》就显得“越界”。
新时期的军旅文学歌颂军人平凡或不平凡的业绩,展示军人丰富的情感世界,《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都是杰出的例子,《绿血》也是。敢于突破禁区书写人性,是1980年代以后军旅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一特点也是以《西线轶事》为发轫:“全篇弥漫着浓厚的人道主义关怀,并将人物的英雄壮举和人性美的光辉完美融合……带动了一大批军旅作家在这个方向上展开创作,使那一时期的军旅小说中的英雄主义开始从神性的高度回到人性的平面。”{22}从多个侧面探索军人的人性深度,有不少军旅作家都做了这样的工作,如乔良的《灵旗》写逃兵的痛苦,女作家于劲的《血罂粟》、《蛐蛐儿的年代》写女兵的性心理和性意识。然而这些都仍隶属于“军人丰富的情感世界”的主题之下,并不溢出军旅小说的基本框架和美学品格。《雌性的草地》则有别于这一主旋律,它在性的方向走得更深更远,集中写性、雌性、人性,性就成为这部小说非常夺目的主题,盖过了军旅背景。
从故事的背景上,《雌性的草地》也从部队组织脱逸了出来。牧马班的姑娘们是被输送到川、藏、陕、甘交界的一片草地上去牧养军马,这里地老天荒、与人烟隔绝,虽然有一名领导她们的指导员“叔叔”,但她们与组织的联系松散,等到她们牺牲了青春、美丽、亲情、恋情、乃至生命终于把马“牧”成,才得知部队已经取消了骑兵建制,军马不再被需要,她们也早已被遗忘在那片让人无法生存的草地上。这样,女子牧马班事实上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她们被播洒到无人的草原,被缺席的组织和自觉的信仰引导着,唯一与她们亲近无比的是大自然,她们与天、地、畜、兽都建立起了奇特的关系。如此,小说就脱去了军旅背景,而代之以草地空间,组织纪律让位于自然法则。
3. 理想主义的牧场
按题材划分,《雌性的草地》也可以归类为知青文学。梁晓声、张承志、史铁生等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家都曾是时代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对那一段知青生活中的情感记忆难以忘怀、矢志不悔。他们固然明晓“文革”、上山下乡不过是一场掩盖在革命口号下的骗局,但他们憎恨的只是骗局本身,而对自己当年献身边区的真挚热烈的情感和行动并不感到后悔。他们注重并怀恋那些岁月中的无私与崇高,作品中也充溢着向往、眷恋和对英雄主义的赞颂。他们插队的地点,梁晓声在北大荒,张承志在内蒙,史铁生在陕北。延续我们刚刚说到的草地空间的话题,可以选择张承志的《金牧场》来与《雌性的草地》类比。
张承志是名副其实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自小接受的共产主义理想教育深入骨髓,使他形成了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人格模式,和庄严的责任感、崇高的使命感。“文革”后期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红卫兵运动的继续或变奏曲,那一代人凭借着类似于宗教的热忱和浪漫主义的激情涌向农村的“广阔天地”,去“接受再教育”。“由于脱离了政治雷霆和精神风暴的中心,由于原始而艰苦的生活本身的磨难,这一代人出现了第一次精神分化。大部分人开始从宗教执迷中清醒过来,他们回顾自己走过的歪斜的脚印,滋生出前所未有的迷惘和历史沧桑感。然而也有一些人如张承志笔下的主人公,却一直未挣脱宗教热忱的缠绕,他们在继续维护其理想的纯洁度和崇高性中,不知不觉地与‘广阔的天地、与那里的大自然同化了。”{23}张承志的理想主义,由社会理想升华为人格理想,“那种理想已经是一种人生境界,而不再是一个政治目标”{24}。
严歌苓没有当过知青。她写作《雌性的草地》的最初冲动源自一个真实的“女子牧马班”的事迹。1974年,她随军到达川、藏、陕、甘交界的一片大草地演出时曾采访过这群女子,两年后,“女子牧马班”成为全国知识青年的优秀典型,报纸上大幅登出她们饱经风霜的年轻老脸,她们被誉为“红色种子”、“理想之花”。“当时我感到她们的存在不很真实,像是放在‘理想这个培养皿里的活细胞;似乎人们并不拿她们的生命当回事,她们所受的肉体、情感之苦都不在话下,只要完成一个试验。”{25}这实验是从一位老首长随意说出的话衍生而来:“男娃女娃都一样,女娃也可以牧马”,——从而将几个来自城市的女知青组成女子牧马班,输送到那个环境严酷连当地牧民也无法放牧的高原草地去牧马。然而在这群“铁姑娘”心中,这不是荒唐、荒诞,而是神圣、圣洁,她们怀抱着理想、信仰心甘情愿地献祭。对于知青那一代人的真挚热烈、无私崇高,《雌性的草地》有着充分的理解和表达:“这个集体从人性的层面看是荒诞的,从神性的层面却是庄严的”{26},这与《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中的人们为了博取时代的认同而做表面文章完全不同,严歌苓对她们的认知也深刻许多,不只表达单一的荒诞感。然而,“正是这份荒诞的庄严扼杀了全部女孩,把她们年轻的肉体与灵魂作为牺牲,捧上了理想的祭坛。因此这份庄严与荒诞的理想便最终被认清为罪恶”{27}。所以,《雌性的草地》一方面如实地描绘一批极“左”的典型,一群把青春献给信仰的人们的真诚的激情,另一方面,它表述的目的并非为了赞颂,而恰是为了否定。这就与《金牧场》的立场有着根本的不同:《金牧场》中的理想是“庄严”、“美好”、“幸福”、“温暖”的,《雌性的草地》中的理想是“庄严”、“荒诞”、“罪恶”、“残酷”的。
从“女兵三部曲”的历程上看,《雌性的草地》延续了《绿血》的激情和《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的反思,在累积之后发生质变,形成飞跃。它仍在反思,但已去除了如《悄悄话》般的“十分明显的政治反思和批判的倾向”;它激情犹甚,但不是“那种最能引发人们同情的,为知青说话的功利性极强的激情”{28}。延续严歌苓自己的比喻,既然这个女子牧马班是一个“试验”,那么她这部小说就是聚焦这个“培养皿”,观察这群“活细胞”的生长和变异过程。由“试验”的过程和结果指引,导致小说的主题有了这样的走向:这群年轻女孩在常人甚至无法活下去的草地上牧马,抵抗烈日、暴风、狼群、豺狗和土著的游牧男人,她们为了生存与“革命”,必须去除自己身上合乎人性的部分、属于雌性的部分。严歌苓描绘这群铁姑娘的非常境遇和情感,目的是为说明:“人性、雌性、性爱都是不容被否定的”{29}。从而,《雌性的草地》在主题上比一般的知青小说有所超越,更加复杂。
4. 草地空间中的有利元素
对知青运动的亲身参与者张承志来说,草原是向他“洞开的宝藏”。他在草原深处生活多年,潜心体悟;若干年后告别草原,重返都市,他发现草原文化已有力地重塑了他。在他为自己塑造的坚强男人的内里,横亘着一个细腻、纤敏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在作品中被投射成大草原的壮美、纯净与大爱包容。对草原,严歌苓也足够熟悉,不只是一个旁观书写者。她年轻的时候,曾经六次进藏:“西藏给了我很多。在我青春的时候,西藏使我成为今天的我。它那种景观,让你对人和自然的关系进入了最初浅的思考。为什么我能写出《雌性的草地》,人啊,狼啊,狗啊,马啊,鹰啊,羊啊,种种的生命。我在写这个小说时大概30岁,而在我十几岁进入西藏时,我已经在好奇了。西藏让我震撼,那样的山川不是哪里都有的。只有西藏。”{30}正因为“那样的山川不是哪里都有的”,西藏这片神奇、灵异的土地,使得《雌性的草地》中的许多情节成为可能,倘若脱离这一独特的地理环境,小说就不能成立。草原,“草地空间”,不仅作为故事中知青生活的大环境而客观存在,还是她主观上大力倚仗的有利条件,她最大限度地利用它来推动情节发展、制造戏剧化的场面。
草地是女子牧马班经受磨炼的场地,自然环境极其严酷。小说中正面描写草地的自然环境有二十多次。那里气候恶劣,每年只有三天的无霜期,烈日、暴风剥蚀着少女的脸,夏天下冰雹,绸缪的雨让帐篷不断起锚。人烟稀少,沼泽地、砾石滩遍布,狼、狗、羊、鸟、草形成食物链,跟女孩们做伴的是她们含辛茹苦牧养的几百匹马。“把一伙最美丽最柔弱的东西——年轻女孩放在地老天荒、与人烟隔绝的地方,她们与周围一切的关系怎么可能不戏剧性呢?”{31}草地的自然环境是小说构建的基础。
沈红霞是女子牧马班的灵魂人物。在牧马的过程中她逐步牺牲了一切:青春容颜(冻伤灼伤的黑紫硬痂)、下肢(为了救红马陷在冰冻的沼泽地,导致双腿瘫痪)、嗓音、眼睛(夜盲症),最终她把心爱的红马也牺牲了出去(阉割,以便成为合格的军马)——这些牺牲都是在草地的严酷环境下造成的结果。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她为了驯服红马,甘愿被它拖着,死不撒手,她的身体在砾石滩上拖出一条血槽,半片身子磨掉了皮肤,一侧的头发没有了——在这一情节中,砾石滩就是必须的因素,“看似静态的草地本身就是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动力因素之一”{32}。伴随着沈红霞这种令人惧怕的牺牲,她的精神飞升着达到了非人的地步,她在牧马班的地位也不断攀升,直至成为精神领袖。女孩子们最先只感到她与她们有种隐隐的分歧和隔膜,后来逐渐认识到,正是她那完美的品德、行为、情操,她对自身、对集体的残酷的要求(比如“饿死不吃马料”、“军马比生命重要”),对她们步步紧逼,把她们的生活搞得苦不堪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中的陶小童经历的是一个从“我”到“非我”的过程,内心煎熬;《雌性的草地》中的沈红霞经历了从“人”到“非人”的过程,而她满怀甘愿。
由于沈红霞一心追寻崇高、神圣、精神永存,严歌苓行了大胆的一笔,触目地设计了两个先辈“魂灵”来与沈红霞展开对话:一个是过草地时牺牲从而永远留在了这片草地上的女红军芳姐子,一个也是牺牲在这片草地上的青年垦荒队员陈黎明。正是这片草地,与这两个“魂灵”密切相关,虽然她们是“另一种生命形态”,但在地理逻辑上是成立的。“沈红霞知道,这片草地在三十年前被荡平过。红军像翻耕土地一样将草地揭去一层皮,之后草地在他们沿途铺下的身体上更旺地新陈代谢。”十多年前的青年垦荒队也曾在这片什么都不长的草地上开垦,他们使用过的康拜因还留在场部:“一堆机器的尸骨”,垦荒队员的墓碑也在姑娘们打草时被刨了出来。西藏又是一个笃信神灵、魂灵的地方,“魂灵”的出现,艺术性想象也有现实依据。严歌苓尽情张开艺术想象的翅膀,让两位革命先辈的“魂灵”来与在精神上始终追随她们的女子牧马班成员沈红霞不断展开对话,探索苦难的意义,因为“理想这类话题只有与牺牲者交谈起来才感到不空洞”。一心要为理想献祭的沈红霞甚至超越了这两位革命先烈的境界,令她俩也心生惭愧,同时又未必认同,这样作者反思的态度就有了多个层面。
用牧马这种艰苦卓绝的形式达到一种伟大的实现,沈红霞在这个角度上像是张承志的代言,然而牧马班的真实结局,决定了严歌苓小说的反思走向。
小说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小点儿,她的出现也与草地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这个出现时只十六岁的女子,在“文革”的混乱年月中犯下命案,只身脱逃,潜入这片草地。只有在这片地老天荒与世隔绝的草地她才有可能躲避天罗地网的通缉令,藏匿起来。小点儿一身的毛病:不良的出身教她从小就会偷会骗,毒辣、淫荡,寡廉鲜耻,富有心计和手段,这些毛病使她具有顽强的生存能力,得以混进女子牧马班这个集体;同时她的美貌又命中了指导员叔叔心中的软弱部分,他不由得在政审之类的关卡上打了马虎眼,让小点儿留下了。小点儿在牧马班里给大家做饭,政治神经敏锐的沈红霞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放牧点,跟小点儿没有照面的机会,给了小点儿相当长的一段潜伏期。最终,还是沈红霞认出小点儿是通缉令上的罪犯,而那时小点儿在这个集体中逐步受到浸染,已经洗心革面成为新人了。小点儿在暴露身份之前,许多的情节也必须依靠她来展开:一个美丽又邪恶的女性参加进一个女修士集体,会有多么激烈的人性冲突从中发生。
草地是牧马的地方,所以女子牧马班的姑娘们来到此地;草地远离社会和人群,草深长茂密,又引来了负罪的小点儿。草地上除了人,更多的是狼、狗、马、羊这些动物,它们身上也同样发生着生命的故事,与人类构成类比的关系。连草地中的草,无边无际半人多高的野草都会突然与那里的人相纠缠,造成一个情节的环扣。草地是这一切的关键,把这一切都集束起来。
由此可见,草地空间中的“每一个部件都可以成为情节发展的机关,同时也制造出或精彩或惊心动魄的戏剧化场面”;草地这一空间也“像一个磁场,将小说中零散的角色吸引汇聚,像连锁反应一样制造出富有戏剧性的场面并推动情节不断向前发展”{33}。
5. 归结于性
基于草地空间的性质与格调,小说《雌性的草地》具有粗犷、雄浑、冷峻、神性的风格。牧马班的姑娘们是它要表现的焦点,而草地上的其他生灵:马、狗、狼等,也都被有意识地摄入焦距,它们都被集中在写性的主题之下。
1985年前后,中国文学创作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性意识的觉醒与高涨。文学在表现人的时候,从人的社会属性转向人的自然属性,从人的理性内容转向非理性内容,从文明的人转向自然的人。小说对人的关注不再仅限于政治、经济、道德等方面,而是以极大的热忱转向人的生命——生命力和生命状态。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写了人性的两大根本问题:食欲、性欲,写它们的满足与否对人的影响。张贤亮不是孤立地探讨性的问题,而是把它与其他的问题结合在一起来表现,比如人的性功能与社会创造力的关系。他以“性”为视角,抨击严重扼杀人性、扭曲人性的社会政治力量。单纯写性的是王安忆,她的“三恋”及《岗上的世纪》,淡化性爱之外的一切社会历史因素,把性爱写得淋漓尽致。她阐述她的创作意图是“性爱本身就反映人生”;“如果写人不写其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真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我是想知道,当人类,当两性彻底摆脱开一切社会的功利和金钱的困扰后该是怎样的”{34}。随后还有贾平凹的《黑氏》,铁凝的《麦秸垛》、《棉花垛》,刘恒的《伏羲伏羲》等大量作品,都不约而同在性的领域进行了探索。性意识迅速地向各种题材和主题的作品渗透。
《雌性的草地》在性的方向走得深而远。它集中写性、雌性、人性,包括与人的性相通的动物的性,严歌苓说她写这部书是为了“伸张‘性”,“性爱是毁灭,更是永生”,“以血滴泪滴将一个巨大的性写在天宙上”{35}。
回到她的草原上,对于草原,严歌苓和张承志都有触及本质的把握——马,并有浓墨重彩的抒写。“假如说草原不能说明它自身,那么只添一匹酣饮的马,就使草原的概念明确了。”{36}马是草原的精魂。《金牧场》和《雌性的草地》里都有一匹最神骏的马,是那种草原上不会有第二匹的马,在《雌性的草地》里,它是红马。红马奔跑起来没有蹄音,如同一个惊叹,是草原上所有骑手的美梦。红马的伴侣叫绛杈,也是一匹红马,严歌苓特别说明她起这个名字因为它有草原风格,并说“我笔下每一个生命都是因为悲剧需要”。这两匹马在草原上两情缱绻,宛如神仙眷侣,而沈红霞为了让它成为一匹合格的军马,不顾所有人反对使它承受了被阉割的命运,这是全书最令人扼腕的悲凉一幕:
红马悲惨长嘶一声。它看着苍天,天不是蓝色,而是紫色;紫色渐暗变黑,一滴巨大的雄性血渍溅在天幕上。它不动了,不挣扎了,疼痛一过去,什么都平息了。随着苍天上那滴血越来越大,它感到世界彻底变了个样,平平的草滩,淡淡的山影,全都惨白惨白。原来就是这样一个单调平淡的世界,一切生命都还这样兴致勃勃地活在其中。它感到乏力、乏趣。当它慢慢支撑起身体,天和地调整了位置。那巨大的血滴干了,成了块不干不净的血痂。它站稳,同时感到了毁灭和新生。……
……人后面走来了那匹红色的母马。你欢蹦乱跳什么呢?你这匹傻里傻气的母家伙。我走了。人要我往哪走我就往哪走。烦恼和欢乐一齐去掉,也挺好。别这样跟着我,别来烦我,以后属于我的就是吃喝与卖命。请离开我吧,因为我再也不认为你美。{37}
从此之后,红马神采尽失,直至默默死去。这一情节有力地说明了全书的主题:“要成为一匹优秀的军马,就得去掉马性;要成为一条杰出的狗,就得灭除狗性;要做一个忠实的女修士,就得扼杀女性。”{38}
马有马性,狗有狗性,狼有狼性。牧马班中唯一做过母亲的女性柯丹,有一只老母狗姆姆与她彼此理解,互相映衬,从中凸显的是母性。姆姆外表丑陋,令人嫌弃,但它善于生养,生产过无数漂亮优秀的儿女。当人们把它这架生育机器最后产出的不合格产品——一只小怪胎处理掉时,它拼了老命去护犊。与此情节平行,柯丹怀上了叔叔的孩子,她在恶劣的环境中想尽办法掩藏,在雪地上把他生下,伪装成是一个捡来的孩子。所以,柯丹一眼就看出大家想杀来吃的姆姆正怀着孕,而姆姆也同时看清瞒过了所有人的柯丹“身体里正成熟着什么;她因负载着另一个生命而显得庞大且丰满”。这种彼此的理解是一个雌性的世界,一个感性的世界,这个雌性世界有另一套准则,迥异于那个时代的准则。严歌苓谈到,她写作《雌性的草地》时,将主义、理想作为“雄性体”,与雌性形成对立关系。而小说不局限于雌雄关系的对立,它写出了草地上的人与畜、人与荒野之间存在着的相互吸引、相互钟情、或相互敌视的关系,这是更广泛的意义上的性{39}。
小说对狼的描写尤其精彩。那一对被姆姆叼回来喂养大的狼崽,其中一只“金眼”结合了狼和狗两种动物的优秀属性,高贵、孤傲、忠实、自尊,却被人当作非狼非狗的东西消灭了;另一只“憨巴”因为历经了狗的生涯、了解狗的屈辱而不愿做狗,它蔑视它的兄弟违背天性的忠良,最后它顺从自然回归原野,重新成为狼,甚至成为狼王。严歌苓在小说中展示的对狼和狗的深刻理解,令人联想到杰克·伦敦,他正是她幼年时最喜爱的作家。杰克·伦敦的名作《野性的呼唤》写狗变成狼的故事,《雪狼》则是狼变成狗的故事。《雌性的草地》中的这一对狼/狗,它们的命运也是奔向小说的主题的:金眼去除了自己身上本能的狼性,对人类忠心耿耿,结局却是身名俱灭;憨巴回复了天生的狼性并充分发展壮大,虽然最终也是一死,被人高高吊起示众,它脸上却是一副仰天大笑、不枉此生的神情。
人物的命运,也是同样走向。小点儿从前一身缺陷,却是一个完整的人性。她进入女子牧马班的集体中,被她们的精神和生活一点点感染,一点点改变,尤其一场纯洁爱情的洗礼,使她涤尽了生命中的污渍,灵魂得到了净化。她改邪归正的过程,恰是她渐渐与她可爱的人性、迷人的缺陷相脱离的过程。与她两相对照的是沈红霞,她一心朝着理想去奉献、牺牲,放弃人的天性,虽然出发点是最善,结局却是残酷、幻灭。女子牧马班的失败告诉人们:人性、雌性、性爱都是不容被否定的。
《雌性的草地》在结构上庖丁解牛,在叙述上扑朔迷离,富有现代派的特色。写作手法上的某些创新如“故事的剖切面”等,可见它在艺术性上的匠心独具。但是《雌性的草地》在大陆的初版没有引起关注,几近默默无闻。严歌苓出国前写作的“女兵三部曲”,前两部是被挟裹在文学潮流中,这突破性的第三部,要等到她将来声名大噪之后才被给予应有的重视。而写完《雌性的草地》后出国留学的严歌苓,随即步入了文学的新天地。
① 严歌苓:《白蛇》,《白蛇·橙血》,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② 可参见朱向前:《中国军旅文学50年1949—1999》,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朱向前先生对当代军旅文学做了“三个阶段”和“四次浪潮”的提法。“三个阶段”对应于学界通行的关于当代文学的划分标准,将当代军旅文学细分为“前十七年”、“新时期”、“90年代至今”。“四次浪潮”之说,延续了刘白羽先生前两次浪潮的提法——分别指1950年代中期和五六十年代之交的两次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出版和阅读热潮,将1980年代中期军旅小说的全面繁荣称为“第三次浪潮”,1990年代军旅长篇小说的螺旋式上升称为第四次。
③ 朱向前:《从建构辉煌到对抗消解——转型期的军旅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 闫顺玲:《军事文苑中的两朵奇葩——综论〈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和〈西线轶事〉》,《哈尔滨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⑤ 金汉:《中国当代小说艺术演变史》,浙江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版。
⑥ 李万钧:《外国小说名著鉴赏》,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⑦⑧ 严歌苓:《绿血》,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18、418页;第480页。
⑨ 张洁:《严歌苓小说论》,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第11页。
⑩{14} 严歌苓:《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3、5、9页;第330、362页。
{11} 李存葆:《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昆仑》1984年第6期。
{12} 毕淑敏:《昆仑殇》,《昆仑》1987年第4期。
{13} 李新宇:《突围与蜕变——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观念和形态》,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5页。
{15} 蔡葵:《从“我”到“非我”——读〈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解放军文艺》1988年第4期。
{16} 严歌苓:《“悄悄话”余音》,《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73页。
{17} 陈晓晖:《另一种海洋——略论美华女作家严歌苓的三篇小说》,《华侨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18}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7页。
{19} 严歌苓:《一天的断想》,《波西米亚楼》,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20}{25}{26}{27}{31}{35}{36}{37}{38} 严歌苓:《从雌性出发》,《雌性的草地》,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第3页;第4页;第5页;第2页;第4页;第167页;第304、305页;第4页。
{21} 傅逸尘:《重建英雄叙事》,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22} 朱向前、唐韵:《军旅文学三十年(1978-2008)》,《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23} 杨经健:《一个理想主义英雄的精神漫游——兼评张承志小说的宗教意味》,《中国文学研究》1991年第4期。
{24} 樊星:《当代文学新视野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
{28} 黄国柱:《留恋芳草地——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读后》,《雌性的草地》,台湾尔雅出版社1993年版,第487页。
{29} 严歌苓:《从雌性出发》,《雌性的草地》,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30} 陈黎:《严歌苓:死了都要爱》,《南都周刊》2006年7月9日。
{32} 王冠含:《〈雌性的草地〉中的草地空间》,《世界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
{33} 王冠含:《〈雌性的草地〉中的草地空间》,《世界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
{34} 王安忆、陈思和:《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上海文学》1988年第2期。
{39} 可参见严歌苓:《性与文学——为芝加哥华人写作协会所做的一场演讲》,《波西米亚楼》,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120页。
(责任编辑:庄园)
The Early Works of Yan Geling and the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1980s
Cai Xiaorong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A Trilongy of Women Soldiers”, the early works in the 1980s by Yan Geling, this article places them in the context of a literary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alytically comparing them with the works by other writers in the same period. of the three novels, Cixing De Caodi(The Female Grassland)in particular, contains the core and essence of her works in the subsequent stage. A study in depth of her works in this period is of great valu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her works in the subsequent period.
Keywords: Yan Geling, military literature, reflections literature, educated youth literature, sex liter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