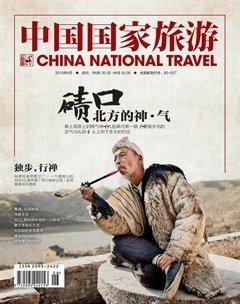气候与生命
2015-06-26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凡是肩负伟大使命,而使命又需要他全力以赴的人,对气候和居住地点的选择尤其严格。气候对新陈代谢的影响(使之延缓或加速)是相当大的,以致在选择地点和气候方面的任何失误,不仅会使人与肩负的使命相异化,而且可能完全阻止其使命的完成。他根本无法正视这种使命,身上永远不具备足够的动物性元气,以取得那种汹涌冲击最具精神性的事物的自由。只有具有这样的元气,人才会认识到:唯有我能胜任些事……
轻微的内脏惰性一旦成习,就足以使天才变成平庸,一种德国式的东西;德国气候本身足以使强壮的、富于英气的内脏意志消沉。新陈代谢的速度,是精确地与精神步伐的轻快或迟滞成正比的。的确,精神本身只不过是新陈代谢的一种形式。我们可以列举出曾经产生过,或正在产生人杰的地点:那里,诙谐、狡猾、阴险属于幸福的一部分;那里,天才必有宾至如归之感,他们大家都能呼吸干燥爽快的空气。巴黎、普罗旺斯、佛罗伦萨、耶路撒冷、雅典——这些地名证明:天才都是赖于干燥的气候和晴朗的天空,即通过快速的新陈代谢,通过坚持不懈为自己获取无穷力量的可能性。
我想起一个例子,一位具有伟大而自由心智的人,仅仅由于受气候的影响,缺少了自然本能,结果成了狭隘委琐的专家和抑郁的人。假如,我不是因病被迫认识理性,思索现实性中的理性,那么我本人最终也会是这个下场。现在,我依靠长期的实践(就像依靠一架极其精密可靠的仪器一样)认识了气候和气象起源的影响,从都灵到米兰的短途旅行中,根据自我心理体验测出了空气湿度变化。
我惊恐地想起一件可怕的事实,那就是,我的一生直至最近10年——有生命危险的年代——总是在一些错误的、于我极不相宜的地点度过的。瑙姆堡、普福塔文科中学、图林根、莱比锡、巴塞尔、威尼斯——就我的生理状况来说,这都是些不幸的地点。假如说,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没有给我留下任何令人愉快的回忆,那么在这方面强调所谓“道德上的”原因未免愚蠢——认为似乎无可争辩地缺乏足够的社交。因为,直到今天为止,我一如既往地缺乏社交,可是也没有妨碍我的开朗和勇敢。但对生理问题的无知——讨厌的“唯心主义”——我生命中的真正不幸,其中还有多余和愚蠢的成分。从这里面产生不出任何优良的东西,因为没有相抵和相消的东西。
从这种唯心主义产生的后果中,我找到了用以解释一切失利、伟大的本能的失误和同我生命的使命相背离的谦恭。比如,我成了个语言学家——起码要问,为什么我没有成为医生,或别的什么令人眼界大开的人物呢?呆在巴塞尔的时候,我的精神生活方式,包括每天的时间分配表在内,完全是对我精力的极端荒唐的滥用。我消耗的精力得不到任何补偿,甚至连耗尽和添补的问题想都没有想。过去,我没有一点敏感的自私之心,没有丝毫对独断本能的保护,那时,不论同谁都是平起平坐,一视同仁的。“忘我性”,一种对距离感的忘却——这是我永世不能原谅的东西。当我几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时,因为我几乎已经走到了尽头,我才开始思考我生命的这种基本的非理性——“唯心主义”。唯有疾病才使我接近了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