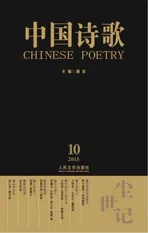方块字:尘世记
2015-06-26瘦西鸿
□瘦西鸿
方块字:尘世记
□瘦西鸿
诗人记
坐在一个词的肩上
众多的词散失一地
像铺在山坡上的白羊
我热爱诗歌善待这些词
在天黑之前我会找出一只头羊
领着它们回家
我会圈好月光这一场场虚幻的爱情
还会点燃篝火这生命里持久的激情
现在我撒手坐在栅栏边
细数着这些词我警惕地看护着
不让它们打盹
我还会制止它们多余的想法
让它们维系传统中的秩序却又不呆板
让彼此的呼吸更加鲜灵
组成一片呼啸的海洋
写作者
我只是从指尖喷射出身体里的血液
这些堆在纸上的方块字
有我思想殷红的腥味
我只是看见了眼睛看不见的石头
像从白天掉到地上的盲鸦
除了你们厌恶的黑还有伤心的抖
我只是用笔和纸的道具在时间的舞台
磨炼我日渐苍老麻木的手摸过万物
最终摸到厌倦摸到遗忘摸到灰
我只是在有生之年坚持这样的劳作
像一只狗寻到时间的骨架
先将它舔到无色无味再把玩它的无知无觉
我只是一粒一粒收集着这些方块字
像吹着几块发红的木炭
把自己煨热
阅读者
推翻一个词摆脱他对视域的奴役
和对思想的统治必须借助另一个词
选出另一个暴君目光们如此盲目
却也甘心情愿地维持了阅读
阅读者在春天的下午内心敞亮
目光犀利有些慌乱的手
在一些字的身体旁不住地抚摸
暧昧的光线竖在肉眼与词语之间
仿佛有故事发生激动的除了人和书
所有的文字都屏住了呼吸
翻一页书如转到另一个房间
揣着惊奇的心跳蹑手蹑脚
阅读者如一盏跃跃欲试的烛光
面对陌生把内心的火焰捂了又捂
当目光成灰手成为化石
文字之间的战争犹未结束
翻书的人左手抱着一个火药库
右手慢慢捻出一根点燃的导火索
受奖辞
毫无疑问我现在真实地站在这里
向曾经来过的人致敬向你们致敬
我代表我的身世和传说回忆与梦想
来接近你们但你们都回去了
因此我致敬的只是你们的肉体
其实我们的肉体是一样的因此我的致敬
已毫无意义就像自己为自己默哀
我一直都在虚度光阴怠慢激情
借用一些文字把一张张白纸弄脏
却无意获取了这样的光环
仿佛一枚月亮被乌云遮蔽才有了光晕
现在我在这光晕中昏厥自以为是
尽量显得和你们不一样你们这样接受我
实际是你们推举了另一个自己站在自己面前
心甘情愿接受伪装和愚弄的真相
毫无凝问我即将离开你们
请为我鼓掌为我们寂寞的人生赏赐一些声响
浮世记
三角梅把她妖艳的红沿着枯瘦的藤茎
献给木质栅栏的尖顶献给一粒粒奔跑的尘埃
身下便是悬崖便是我担惊受怕的孤独
坐在阳台上我一丝一丝消耗着阳光
睡眠的虫子花朵般爬满我的全身
总是一个人守着这雨后的静谧守着无形的消遁
浮世就在周围声色葳蕤
总是像一个被遗忘的古陶怀抱前世的叹息
怀抱几多殷红爆燃在春天又不为人知
我终将像一朵三角梅飘零于尘世爬上时光的悬崖
用自己的红颜独自承担它灰暗的洗涤
然后以苍白的身躯给沉默的泥土献上芬芳
献上不为人知的消亡
轻与重
我不知道身体里的血液与骨头
哪个更轻哪个更重
骨头支撑着我直立行走
血液撞击着我四处奔波
但他们都是道具
真正的主角是生活让我不停地劳作
而当我沉睡在夜里
血液不再需要力气骨头也失去重量
如果有一天我被烧掉
血液的河流会化成烟缕
骨头的枝干会化成灰烬
一切都轻了只有一个看不见的盒子
重了盛着那么多虚无的回忆
夜百合
夜百合在黑夜里坚守着自己的名字
但在人们的视线里它没有守住白
打瞌睡的女子为一身的清白她不敢入睡
因此而虚耗掉一生的容颜
前朝诵书的少年在朝廷官做到了七品
但留在乡间背篓里的书籍已经发黄
它漏掉那么多光阴还是那么黑
还是那么距白有不可企及的远
仿佛一只耳朵被黑塞满所谓的夜百合只活在白天
在夜里看过去无非是黑的一部分
桃花巫
她的面孔一闪点燃三百里的桃花
三万张粉红的稿笺一格格浮出她的脸
春风行刑揭开枯枝里的暗蛊
三万朵红唇追喊他的名字
被闪电插在地上的人在伞下把雨嚼碎
满嘴泥泞烟岚捆着的身子
漏出几道裂缝背负一生的罪洒得满地都是
谁没做过负心郎残忍地割开她的低泣
一枚桃核装满符咒被她咬在牙齿上
绝望的天空洒尽最后一滴泪
桃花盛开一笺笺诉状风生水起扶摇直上
被三百朵雷霆宣读细雨的绳子反复捆绑
三万朵桃花蜜蜂般歇在他的眼睛里
他不再申辩低头成为自己的囹圄
空酒杯
这里住着粮食天气酒窖和酿酒师
住着友情红酥手发白的唇和恩怨情仇
住着烛光音乐言辞和雾一般的目光
住着火候
但更多的时候这里住着空
穿着玻璃的外套透明的女子
把她的身世托给了沉醉
一只手弄碎了玻璃
便有更多的玻璃住在这里
每一片都拥挤不堪那些旅客
一些去了一些还在来路上
而只剩下缝隙满满地
尘世记
面对尘世我背转身去
树木褪掉年轮花朵脱下香气
辽阔的暮色中天堂是蓝色的
一辆火车没有跨过河流
它的影子掉进水里泛起泡沫
炉火继续喂养水蒸气
漫天大雪落满灰白的头颅
血液在天地间走动
孤单的孩子找不到体温
果实悬在树枝上洗礼的人
在献诗中把手弄皱
那一池旋涡淹没多少年华
又荡漾了数不尽的拥抱和触摸
我拖着影子继续尘世的行走
身后背着一条蜿蜒的小路
路上尘烟四起水声咆哮
我只是路过人间
干干净净珍爱着这受伤的肉身
敲钟人
把钟敲醒的人转身又陷入了
木檐下更深的睡眠高耸的银杏树
用一枚枚金币赎走了静虚的秋光
目光空于走廊的寺童误把一朵阳光
认作蝴蝶他慢慢捉过去的手
只捉到一把暗影
经书在木橱里自己默诵自己
一粒粒灰尘被细微的声音诱过来
身不由己地扑上去
堂前叩拜的人为许下的誓愿
献上额前的皱纹躬起的身子
是一张皱巴巴的功德
清油灯长明舔走敲钟人脸上的春色
而他袖着的手仍然牢牢抱住
一串比念珠更圆润的秘密

木鱼稳坐堂前口中的声音
踮起脚尖悄悄跟随那位女子
径直走到山下去了
青苹果
那一树苹果在早上便红了
秋天跟着红起来还有雾
还有雾中比羞涩略低一些的脸蛋
一树的苹果都嫁人了
那一棵树比秋天还空旷
只有一只青苹果一个脸上有雀斑的女子
高高地挂在树梢
像一只灯盏在一棵树上高高举起
这需要多大的勇气一个少女背着家
在秋天流浪她仰着头
向天空向流云向飞抵老家的雁翅
喃喃着她的眷恋
一场雾包裹了那一棵树
一场雾带来的风把树摇了摇
高高地挂在树梢的那只青苹果
突然不见了
仿佛一个女子离家出走
空荡荡的家中盛满的已不是思念
而是一望无际的阴影
中药铺
几十年前的老阳光
躲在暗抽间的一格里
仍用僵硬的手指,一点一点拿开灰尘
菖蒲是邻居,蝉蜕也是
只有相思子,深居在二层的阁楼上
闻得见香气,见不到影子
一拨又一拨的孩子长高了
他们搁在柜台上的颈子犹在
两只探寻的目光,游走在他乡问药
那只从暗地里伸过来的手
不需称量,便把准了一场病
所需的几两几钱引子
只是现世的病理已深入心底
而老阳光的手臂干枯
切不准流行的药引
惟有把抽屉一格一格展开
像检查一个人的内部结构
并把一点一点的幽暗,悄悄移开
偏头痛
下午一些乌云在天空积聚
但它们只在右边的天空里像一朵蘑菇云
时紧时慢时浓时淡地聚合
它可能包藏了整个夜晚的雨水
但此刻为时过早它们为一场夜雨所孕育的
是不紧不慢的一阵阵痉挛
有一只鸽子把左边天空的阳光抬高
它银色的翅膀像一把扫帚
使那一片天空如此开阔而干净
其间一定会有一道缝隙像生死界限
但凡俗的人看不见凡俗的人们说
东边日出西边雨
而东边正在日落西边只有积雨的云
这样的下午头脑被分成阴阳两半
一半疼痛一半麻木
就像共同生活着的人群经过漫长的岁月
大多数人习惯了向善只有一小部分人
他们把自己的头颅倾斜于骨头里的阴暗
读画记
一滴墨沉默着悬坠星际
山水兀自暗度时日喧嚣已逝
声音涌入眼睛如展开一张微黄的徽宣
夕阳尖叫一滴墨应声而落
山水被打湿那一盏孤灯似的背影
在暮色里划出一道浅浅的回音
这线条比视线疏朗
在明月中折断那一道深深的沟壑
装满脑中盈盈而出的啁啾
此时的画家如一只鸟身披月色
在徽宣上起伏一滴墨将纸灼出一个洞
他躬行潜行身后回旋着渺茫如雾的水声
输血记
一个词其实我一直背着它副词的那一部分
在生活中我彻彻底底地输了
一面苍白的床单即将包裹苍白的我
一个词当我用到他动物性的一面
那个偷盗的人失踪了我看见一辆马车
拉着血粒向我的血管奔跑
这驻进我身体的血到底是谁的血
他是输家还是赢家勇者还是懦夫
是否也像我曾在岁月中低下高贵的头颅
这流进我生命的血到底是什么血
生存的养分还是生活的杂质
是否有过骨缝中惊悸后的寒凉
像一截空心的木头我接受点滴的恩赐
却惊起灵魂的猜疑即使我强健如初
我迎风奔跑中抛洒的汗滴还会不会
是自己的我是在替别人惊喜
还是为自己悲泣如果有一天我死去
会是血管中的哪一部分血不愿安息
遗憾记
如果听见我在夜里的三声咳嗽
你当披着月光出门做好三件事
沿着家门扫开一地虫鸣
让月光晒着我的脚印
直通到后山的茅草丛边
掀开茅草找到曾经被它划破
从指尖滴到草根的那粒血
把它拾起来吹开上面的灰尘
捧着它走进旁边的庙里
要绕过钟磬声和香烛的烟尘
直接供在神龛上
然后退到门外作三个揖
回家后不要洗手也不必开灯
沿着我的咳嗽继续依着我躺下
别害怕我身体的冰凉
请用手紧紧捂住我的嘴
我会最后咯出几句梦话
好好握在手里吧
这些烫手的遗憾
背叛书
我要背叛人群的分类拔掉高贵的伪饰
与乞讨的浪人为伍
去听他们的心跳跃去应和他们的梦想
我要背叛那些秩序的黑夜
点燃手指照亮寒冷的忧伤
从时光的间隙我要把夜晚打磨得比白天更亮
我要背叛既受的教育回到人之初
用赤裸的纯洁和简单的干净
去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
我要背叛面前的这张白纸
是它盖住了真实的黑暗
并诱惑我作最美的图画
我要撕碎这张白纸
让黑暗复原哦多么真实的幸福
多么明亮的黑暗
被想念
她在她自己的生活里夜以继日
做一个被爱的女人被抒情和抚摸
被反复猜疑和盘问
挂在睫毛上的露水又被吻干
在月光下散步把独自的脚印
糊在那些相携相挽的脚印上
拒绝几个电话回到家中
摸黑点燃一根香烟坐在客厅里
像一缕无凭据的烟
在时光中消散没有故乡
也没有想到再去什么地方
她站起身然后又坐回体温里
一个没开小差的女人也没有回忆
像一只空着的花瓶
坐在黑夜里干净空落
散发着纯净的瓷的暗光
那些红
我不认识那些红那些低头的女子
蕾一般隐在各自的身世中
还未被我认识已被他人命名
她们走在自己的微微痛和悄悄的痉挛中
不为人知但她们依旧一脸的笑
像趴在墙头的杏
告诉人们她们就是那些红
那些红色情地混乱在一起
没有人愿意条分缕析没有人把哲学
和那些红理智地联系在一起
那些红被瓜分被不同的家伙
悄悄领回家然后从一个红
抚摸着其他的红
那些红的身体动了一下就开始流泪
空气潮湿起来那些红
也潮湿起来
陌生人
我的眉毛从秋风里的枯草上借来凉意
一滴滴打湿视线这被别人霸占的梯子
上面轮流爬动的是谁的世界和神示
我只能把自己交给视线的轨道和异乡
我的手指上面缀满陌生人的体温
曾经的一握攥紧的不再是情谊
那随血液脉动的心悸
撒向所有人类的手掌而成为一片海洋的潮汐
我的心脏是植物的我的肺是彗星的
我的肠我的胃属于被吞噬的一切
我的脚仍在行走沿着所谓的路
它没有目的但总是不停地移动着
把我载向陌生的地方
就这样我每天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
穿过人世和时空只有我自己知道自己
认识自己了解自己而对于我之外的一切
我多么孤单而执拗啊这个陌生人
画蝇记
一只苍蝇趴在玻璃上偷窥我
阳光给它的翅影镶上花边儿
从屋子里望出去它几乎是透明的
而我呆在阴暗的屋子里内心也是阴暗的
我想画下一只苍蝇的明亮隔着玻璃
先画下它清晰的轮廓画下那抹阳光
再画它清澈的眼睛一片幽深的纯黑
又一只苍蝇歇在玻璃上我画下它
再一只苍蝇歇在玻璃上我画下它
一群苍蝇歇在玻璃上我已画下一群苍蝇
现在玻璃上歇满了苍蝇
而在玻璃的背面我也画满了苍蝇
苍蝇们像在照镜子隔着玻璃一动不动
仿佛一个人在水面上打量自己的影子
突然一只苍蝇飞走了所有的苍蝇飞走了
我画下的那些苍蝇也飞走了
剩下我一个人独自滞在玻璃上
黑压压一片
石头记
和一块石头凝视良久它竟长出眼睛
隔着旷朗的时空它紧紧盯着我
仿佛要从我的心底找出不再生长的石纹
一只盲鸦在暮色里找不到归途
它停留在石头上获取了更多的孤单
停留在我肩头犀利的尖嘴啄食我的体温
旷野合拢来我掏空心中的块垒
与石头相依而坐我的眼睛渐渐模糊
融入了石头坚硬的沉默
沿着黑夜幽深的甬道我们盲目地坐着
自暴自弃甚至放纵骨髓里的磷火
大雪一般纷飞满地撒满寒凉
而在白天我们又相互隔绝在时间之外
它像一座坟茔埋葬着与人厮磨的隐私
我像一团尘烟飘散在一无是处的人间
挑刺记
曾经有一根刺扎入我童年的手指
新鲜的痛痒痒的逼着我找来一根针
挑开幼稚的皮肤和鲜嫩的肉
慢慢将那根刺从身体里挑出来
之后用一点盐封住伤口
或是把手指吮进嘴里那些痛
就慢慢被肉体埋了
而当一柄闪电刺进我如今的眼眸
却没有痛只有割不断的眩晕
在眼睛里疯狂生长
此后我的视线也似一柄柄闪电
扎进我所看到的所有事物
只是我不知道它们会不会和我一样痛
只是我再也找不到一根针
从万物中挑回我的视线不让它们
随着万物一起腐烂
鸟巢记
几茎枯枝在雪中伸张天空被飞空了
鸟的影子似雪无声地落入零度以下
那悬在空中的巨大鸟巢张开寒风的翅膀
一排排飞成落日般的句号
天地在浑沌中合拢鸟在飞翔里失踪
剩下那些挂在树枝间的时间的荒冢
寂静漫延如闪电从林子里刺过
鸟巢微微颤动盛满温暖的子弹
这被击中的一只小鸟探出它的头
嫩绿的茸毛复活了整个北方的林子
秋雨书
一场秋雨拍打红叶清洗的天光
忽而黯淡忽而明亮声音也忽远忽近
远时像梦中出现的亲人
近时像突兀而至的陌生者
一场秋雨赶了多远的路才把早年
我一声叹息哈出的气体凝结
才聚成化不开的怜惜空运到我眼前
但那时的我已远去背着的那些重负
早已抛弃了我如今是另一个我
像他拖在身后的阴影时有时无
一场秋雨引来我的前世
我剖开雨滴看见一个脆弱的我
孤零零无助地望着苍老的我
我只好奉上两滴泪珠再把他包裹起来
一场秋雨正是这样的神
穿越时光让无数在时光中死去的我
借它的身体再度活下来
秋夜书
一片叶子动身了背负整个秋天
大地比熟睡的梦境更空旷
零乱的脚印像涣散的鼾声
一片叶子飘浮在滚涌的血脉之上
另一片叶子的静谧是整个天空的蓝
搁置在时光最顶端的抽屉上
里边藏着的鸟鸣偶尔啄一下钟声
另一片叶子在待嫁的妆奁中渐渐红润
此刻瓷器盛着烈酒红唇疏于交谈
细雨笼住虫子的低吟
两双手在午夜摸索彼此交换体温
又落叶般领回各自的孤单
一个人动身了另一个人原地滞留
他们搅动着时光的藤蔓像一根疼痛的闪电
一些向上迎纳纷至沓来沸腾的夜色
一些抽搐着滴落血管中沉默的浆汁
山鹤传
那一声锋利的长唳惊飞满山落叶
树枝伸长颈子啜饮流云
一山的静谧水雾般弥漫
双翅抖开整个天空尘世的喧嚣
掩埋着人群翅影漏下的日光
一一擦亮眼睛里的阴郁
驮着一座山的飞翔如此轻盈
鹤把山顶的白塔收进痉挛的爪缝
塔内的钟声惊起一阵冷汗
腾翔在时光之上一只鹤内心的虚无
幻为朵朵翻滚的白云被孤单的闪电击中
目光的雨滴遍洒凡尘
沿着闪电的轨迹一只鹤终将飞进自己的翅膀
片片羽毛积满白雪积满天地间
一阵阵拂过人心的寒风
而在时光之上它已是一位无法抵达的神
睁着太阳与月亮的双眼无奈地打量
尘世间落叶般生息的人群
旷野树
当最后几片树叶鸟一般飞走
旷野里的树像一个手无寸铁的人
连羞耻都捂不住了
寒风运送的刀子磨亮绝望的锈迹
霜白一般从早晨的雾霾堆到暮色的雾霾
惟有那些根须还在泥土里摸索
就像一个人用指甲狠狠掐着自己
看看是不是还活着
寒夜拉了拉衾被这棵光着身子的树
始终不敢入睡始终担心会被死亡强暴
直到早上他用一块冰焐热枯瘦的身体
才慢慢在浓雾中蹑手蹑脚地
抖落埋藏了一个冬天的锈迹
落雪记
雪落了一上午仿佛不是整个天空
在落宇宙在落
而是我的视野在落体温
在落
坐在家里前窗在落后院
在落外面全部在落
仿佛全世界在落我的眼皮
在落
我慢慢燃着香烟烟灰
在落仿佛指甲在落
天空只剩下这些雪我只剩下这些
灰烬
雪落了一上午仿佛我身上的骨肉在落
梦里的血液在落梦外的白马
拉着的一车时间
在落
尘埃乱
花朵开出粉末蝴蝶的翅膀上
有人偷偷篡改春色
从一片叶子偷走迷醉
春风酿酒酿九十九道断弦的关口
年代倾斜流泄浓香的月光
滚动的露珠天空中的不明飞行物
一抹蓝蕊闪烁这旷世的火焰
凡尘中十世单传的药引
众多的生命在痛乱作一团
散沙飞逝露出岁月的骨架
两列队伍一红一白
迎亲的欢喜送葬的悲泣
在一瓣花影中会合
他们迅速散开
留下新娘的眼泪另一边是已寒的尸骨
风微微吹蚂蚁的牙齿闪着寒光
尘埃沉睡人世安详
那个挑灯穿巷的更夫
一锤一锤敲出时光和荒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