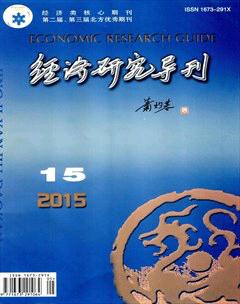清代流人对嫩江流域经济社会的贡献
2015-06-25赵忠山
赵忠山
(齐齐哈尔大学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
嫩江流域,地处我国的北部边陲,因松花江第一大支流——嫩江而闻名,形成了东北著名的经济文化带。嫩江(NenRiver),古名难水,明称脑温江,清初名诺尼江。是全长1370公里,出山后进入松嫩平原,在吉林省三岔河镇汇入松花江。在古代,这广袤嫩江流域,是少数民族集居地,空旷荒凉,人口稀少,蛮荒未凿,当地的土著人过着“渔猎”生活,穿的是鱼皮衣,用的是木制器皿,当时土著人称鄂伦春人为“山岭上的人”,鄂温克人为“大山林中的人”,赫哲人则被称其为“鱼皮部”、“使犬部”等。生产生活方式尚处在半原始状况,经济文化十分落后。
鉴于此种情形,满清入主中原后,即开始实施实边政策。一方面,官方招垦,即将关内的居民掠夺或迁移到边远的嫩江流域。虽然进行了几次招垦,但终因人数有限,加之嫩江流域路程遥远,环境恶劣,基本未有多少人至此。康熙七年(1668年),清政府撤销了招垦令,移民来嫩江流域垦殖的政策停止。事实上,这一政策在嫩江流域并未受益。另一方面,又把大量“流人”发配到这里,借以实边。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主政期间,鉴于黑龙江空旷荒芜,人烟稀少,生产落后的现状,多次向清政府要求向黑龙江遣发流人,以发展经济、强化边防,增加人口。请求得到了清政府的首肯,于是大量流人不断涌来,嫩江流域外,特别是当时的卜魁(现齐齐哈尔),成了流人的集中之地,这一地区成为清政府“没有屋顶的大监狱”。
说起流人,不得不谈一谈清代沿用明代迁戍实边的流刑制度。
《大清律例》主刑分为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主刑之外还有枷号、迁徙、充军、发遣、凌迟、枭首、戮尸等随时所加之刑。对连坐者有斩立决、为奴、徙流等。所谓流刑,在西方被称为“不流血的断头台”,为“流者谓人犯重罪,不忍刑杀,流去远方”,由此可见,流放的刑罚程度仅次于死刑。流人,顾名思义,即为流放之犯人的一种。
人犯被判流刑,正常情况下,是按照罪人所犯罪行的轻重以及身份等不同状况,根据律例,判定为“安插”、“效力”、“ 管束”、“ 圈禁”、“ 当差”、“ 为奴”等,后按里程发遣到边远地方,并且有不同的“劳动改造”方式。流人抵达发遣地后,经衙门刑司接收验明身份后,例由将军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是留在本城,还是发往外城。迁徙,“应迁徙者迁离乡土一千里外。”流,比迁徙为重,分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个等次。充军,较流为重,分“附近二千里,近边二千五百里,边远三千里,极边、烟瘴俱四千里”五个等次。发遣,较充军等均为重,认为罪不至死,而充军等又不能尽其罪,将犯罪人发往边疆地区给驻防官兵为奴,多适用于政治性案犯。“流犯,初制由各县解交巡抚衙门,按照里数,酌发各处荒芜及濒海州县。嗣以各省分拨失均,不免趋避拣择。乾隆八年,刑部始纂辑三流道里表,将某省某府属流犯,应流二千里者发何省何府属安置,应流二千五百里者发何省何府属安置,应流三千里者发何省何府属安置,按计程途,限定地址,逐省逐府,分别开载。嗣于四十九年及嘉庆六年两次修订。然第于州县之增并,道里之参差,略有修改,而大体不易。律称:‘犯流妻妾从之,父祖子孙欲随者听。’乾隆二十四年,将佥妻之例停止。其军、流、遣犯情原随带家属者,不得官为资送,律成虚设矣。”[1]然而,满族人犯罪却可免发遣:“凡旗人犯罪,笞、杖各照数鞭责,军、流、徒,免发遣……”这也说明了《大清律例》的不平等性。流放的人中,有挟仇诬告者,有反抗满清压迫而起义的回教徒,有反清复明的前朝遗老,有追随三藩叛乱的通谋人,有为官不正、或失职得咎、或渎职得罪、或官场角斗失宠的官员,也有因若聚众20人以上,为首绞决,为从发往烟瘴地带充军。
由于明末清初,嫩江流域气候恶劣、荒蛮落后,人迹罕至。因此,清政府就将这里钦点为“流放地”,不断将各种的犯人流放到这里,主要集中在卜魁(今齐齐哈尔)。这些流人的到来,一方面强化了清政府的统治,巩固了边疆的稳定,另一方面,对清代嫩江流域的经济社会的开发与构建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流人促进了嫩江流域的农业发展
清初的嫩江流域,空旷荒凉、人烟稀少。正如《黑龙江外记》中记载的那样:“黑龙江地利有余,人力不足,非尽惰农也。为兵者一身供役,势难及于耕耘。而闲处者,又无力多购牛、犁以开荒于数十百里之外。故齐齐哈尔等城不过负郭百里内。有田土者,世守其业,余皆樵牧自给,或佣於流人,贾客以图温饱。而膏腴万顷,荒而不冶,曾无过而问之者,盖亦势使之然也。”这里是游牧民族聚居的地方,尚保持着半原始状态的粗放型耕种方式,农业生产极其落后。据《龙沙纪略》记载:“卜魁四面数十里,皆寒沙,少耕作。城中数万人,咸资食于蒙古糜田。蒙古耕种,岁易其地,待雨乃播,不雨则终不破土,故饥岁恒多。雨后,相水坎处,携妇子、牛羊以往,毡庐孤立,布种则去,不复顾。逮秋复来,草莠杂获。计一亩所得,不及民田之半。”半原始状态的耕作方式,靠天吃饭的落后生产观念,使得嫩江流域的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影响。清初,就出现了连年的灾荒,粮食产量严重不足。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前后,随着清政府刑罚政策的进一步实施,发遣到嫩江流域的流人已达数百人。时任黑龙江将军的傅玉。“为边防(陲)积储粮谷计。”请示朝廷“在齐齐哈尔增设官屯数处,所需农器牛具,由各城库存粮银拨给。初种之年,免其缴纳,翌年交半,三年交清。”得到清政府批准后,齐齐哈尔官庄进迅速兴起,开始了大规模地开垦耕地,正所谓“辟地日多”。这期间,流人们将中原的先进耕作技术、农具、籽种等带到嫩江流域进行农业生产。“今流人之赏旗者,且倍于兵。依而行之,则岁征粮不啻万计。而桀骜之辈使皆敛手归农,又策之至善者。守土者,宜亦计及此也。”[2]“汉人操作则不然,汉人之耕作有分休闲、轮作二法。若砂碱地则用休闲法,每年耕作一分,休闲一分。至轮作法,最为普遍,即高粱、谷子、黄豆之类,每三年轮作一次。又名翻茬。”由于采用了休闲、轮作等先进的耕用方式,嫩江流域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的局面,耕作技术的变革,使得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大垧十亩得粮四五石,多者七八石”已不少见。卜魁文化流人方登峄在其堪拟塞北之《豳风》的诗作《糜子米》中写道:“糜子谷,粒碎黄金粟。边人匹布换一斛,挽输城外车音续。糜子生,糜子熟,炕头压席焙新粮。妇子横陈粮上宿,夏云罩地雨如注。播种不耰人尽去,毡帏木栅秋霜白。草根细软牛羊陌。今年锄地向城南,明年移家种城北。”[3]就是对这种生产状况的真实描述。
不仅如此,流人们还改变了粮食和蔬菜种植品种单一化的局面,使粮食和蔬菜品种多样化。原来的嫩江流域粮食品种仅有糜、粟、稗子、铃铛麦等,流人们的到来,带来了小麦、高梁、黍等品种:“流人辟圃种菜,所产惟芹、芥、菘、韭、菠菜、生菜、芜荽、茄、萝卜、王瓜、倭瓜、葱、蒜、秦椒。茄长而不圜,王瓜长者几二尺,皆四月后上市鬻之。然亦惟齐齐哈尔如是。墨尔根、黑龙江皆自食不买。呼伦贝尔、布特哈俗重肉食,无菜色也。”甚至,连以渔猎为生的索伦、达呼儿,也都“渐知树艺”[4]。可见,由于流人的涌入,清代嫩江流域种植业的发展超过了东北的其他地方。极大推动了嫩江流域农业的发展进程,奠定了嫩江流域近代农业发展的基础。
二、流人促进了手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流人带来的先进的耕作技术,促进了耕地面积的扩大和产量的提高,流人带来的采蜜、制糖、制蜡、煎盐等用工技术,同样促进了用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当时齐齐哈尔出碱,城东有碱厂,流人相聚煎晒,通行吉林。“扫土为盐,味稍苦,色黑。去卜魁东西各百余里,地名喇嘛寺,产此。三城皆食之。白盐则来自奉天。”[2]这种作坊式的生产是嫩江流域较早的手工业集体生产的雏形,甚至,应视为东北手工业的肇始。
遣戍嫩江流域的许多流人是工匠出身,为了谋生计,运用自己的技术,充当工匠、手工制作者,在嫩江流域从事建房、抹墙等杂活。如筑拉核墙(干打垒的泥房),挂泥壁。尚有更多的流人,则受雇佣于店肆,借以谋生。虽然“工匠皆流人,技拙而值贵”[2],但是不能否认的是,的确对当时的手工业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这既是嫩江流域早期的手工业,也是嫩江流域服务业的发端。
三、流人促进了商业和贸易的发展
嫩江流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除了农产品外,貂皮、人参、海东青等当时就驰名中外,“虽山蔬野簌,无不佳者。”然而,当地的少数民族除了作为贡品与自用外,并不懂得交易,即使有交易,也“无市井买卖,不用钱,惟以物相贸易”。因此根本就谈不上商业贸易。直到流人的大量遣戍到这里,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当时的流人开始从事商业活动,虽然范围很窄,但却开辟了现代商贸的先河。这些关内的流人要么将自己从关内带来的物品与当地人交易,换取生活日用品,并使当地人“知市贾”;要么将自己的劳动产品卖出。如卜魁“流人辟圃种菜……四月后上市鬻之”;要么将关内之物品贩运到东北销售,均是“稍涉贵重”之物。据《龙沙纪略》记载,“卜魁西北二百里山崖,松、柞蓊郁,江冰后,作炭者乃往,故值贱于冬。”许多流人靠采摘木耳、榛子等卖钱为生。还有的流人在发遣期满后从事东北与关内之间的贸易,从中获利。
“清代的齐齐哈尔,不仅曾经有过楚勒罕大集和后来的北关大集,还有过很多庙会,成为流人生活的一个依托,或做些买卖,或在其中扮演伶人的角色得以糊口。一些逃走的流人混迹于边贸之地,据《黑龙江外记》记载:‘商贩旧与鄂伦春互市地,名齐凌,转为麒麟,因有麒麟营子之号。后将军傅玉搜获逋逃无算,乃禁互市。’”[“5]文人富则学为贾,贫而通满语则代人贾,所谓掌柜者也。”清代流人在嫩江流域为商贸活动中,是主力军和引导者,起着重要的作用。不仅刺激了嫩江流域的经济和社会的繁荣,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嫩江流域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同时,行商大贾接踵而至,商品贸易空前繁盛。方式济在《龙沙纪略》中这样记述:“入土城南门,抵木城里许,商贾夹衢而居,市声颇嘈嘈。”可见当时齐齐哈尔街市贸易之繁荣,嫩江流域商品贸易活动之兴盛。
四、流人促进了邮递业的发展
17世纪中叶沙皇俄国乘清军大批入关,东北边防削弱之机,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窃据了尼布楚和雅克萨等地,当时清政府把主要力量用于解决内部矛盾上,无力加强东北边防。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了“三藩之乱”和二十二年(1683年)攻下了台湾,使国内形势趋于稳定后,清政府才开始加强东北边防,反击沙皇俄国的侵略。当时的皇上康熙认为:“罗刹(沙俄)扰我黑龙江、松花江一带三十余年,其所窃据,距我朝发详之地甚近,不速加剪除,恐边徼之民不获宁息。”因此康熙在巡游乌喇(现吉林市)泛游松花江和乌拉虞村(今乌拉街)一带山川地理形势后回到北京,总结了过去(1652年和1658年)抗击沙皇俄同入侵没能取胜的原因,认为是交通不畅不利于集中调运兵力;信息不是,不利于战争指挥。于是,重新开始了抗击沙俄侵略的准备工作,在瑷珲等地建城成兵的同时,在黑龙江城、呼伦贝尔、齐齐哈尔、墨尔根等地陆续增设边防卡伦、轮兵巡察。1685年命藩院恃郎明爱向墨尔根至雅克萨设驿站,首先从吉林(乌喇)至瑗珲建驿站道计1700余里,设驿站25个。驿站设站丁,负责传送文书、谕旨、奏折、护送官员、输送粮食、接送兵员等。每一驿站均发马20匹左右,耕牛30头左右、壮丁20~30名,即站丁。后称为站人。肇源县的茂兴站是松花江对岸由吉林进入黑龙江的第一驿站,直达瑗珲城。1735年雍正在古驿道上开辟了乌兰诺尔(肇源县新站镇)至呼兰府的边台,设6站。实际上是由呼兰去齐齐哈尔者可由博尔济哈台(肇源县头台镇)直奔乌兰诺尔站北上,不必绕道去茂兴。去伯都纳者,可由博尔济暗台直奔茂兴南下。不必绕道去乌兰诺(可见博尔济晴台(头台站)成为连接第一驿道的三夏口)。这两条驿站在清政府抗击外来侵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历时两年的雅克萨战役,六千里的军情战报,仅用半个月就能送到康熙皇帝御前,其速度何止“八百里加急”?黑龙江除开辟了境内将军与副都统城守尉所在地之间的道路外,又加强了与北京、盛京之间的联系,共有五条通往北京。一是瑗珲至北京道;二是齐齐哈尔至北京道;三是珠克特依至北京道;四是草地至北京辅助道;五是茂X至法库道。到清末共计开辟十条驿道。
1906年11月清政府裁撤驿站、边台,改设文报局。这些古老驿路才结束了路马传驿的使命,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可见,清政府在嫩江流域的卜魁(现齐齐哈尔)设置了驿站,“ 吴、尚、耿三藩旧户,站丁居多。 ”据《 龙城旧闻》记载:“ 砖城之西,旧有卜奎站,更有茂兴站,为南行大道。墨尔根站为北行大道。故统名西站。”这些站丁里,许多为遣戍的流人,“站丁多云贵人……由山海关内匀拨而来江,充邮卒,当苦差,世为站丁,不与满、蒙贵族通婚姻。”这些驿站,不仅用于军事,同时也服务于民事,成为嫩江流域后来民用邮递的基本雏形。
五、流人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
嫩江流域地处祖国的北部边陲,旅游业一直处于低迷状态。随着流人的踊入、文化教育的发展,当年荒芜的嫩江流域不仅具有独特的北国风光,更具有了诸多独特的人文景观:
吕氏故宅——即清初著名思想家吕留良后裔所居之地。是嫩江流域唯一的流人住宅遗存。
西泊——现劳动湖。光绪初,提督陈国瑞因事流放齐齐哈尔,闲暇西泊垂钓,名其钓处为“虎溪”,自号“虎溪钓客”。民国初,多有人以诗凭吊者,诗尚存。
梅花、菊花诗社——清光绪年间,山西荣河知县王性存流放卜魁,曾被水师营总管海昌聘为经义书屋主讲。 王性存有诗名,他不仅自己吟咏,还积极倡议在卜奎的文人集会,发展诗词事业,因而创立了“梅花、菊花”两诗社,结社唱和,一时间齐齐哈尔“文风”四起。“以道义相尚,并结祠社,暇日咏歌,称一时之盛。”“塞外始有弦诵声。”可见他对当地文化的发展做出的一定贡献。
普恩寺——俗称娘娘庙,《黑龙江外记》、《龙城旧闻》均有记载。 该寺建在城西三里许,“地据沙阜,形如龟。林木翳荟,西望嫩江如带。”其“宫殿崇闳,院宇轩敞”。纵长为三十一丈,横宽为三十六丈。寺中供奉的是碧霞元君,民间称天仙娘娘,农历四月初八为其诞辰,此日来庙里烧香祈求后嗣者极多。“春秋游览之所,此为第一。”嘉庆年间这里已是齐齐哈尔重要的踏青、游览地。按照描述,该寺东临西泊,西倚嫩江,应是建华区文化路与中华路犄角处的原黑龙江省图书馆,即原由齐齐哈尔大学管理的职工宿舍。
海粟亭——乾隆四十八年(1703年),流人刘廷耀在普恩寺前建置一亭,并且自书“霞蔚云兴”之匾额,但没有给该亭命名。同时期因甘肃冒赈案被流放的安定县知县黄道作为襄助,书写了“浮幻因缘”的匾额。一说景致,一说世事,相得益彰。嘉庆十三年(1808年)春,时任黑龙江将军衙门银库主事主政的西清,以一个季度的薪俸重修小亭,提名为海粟亭。旧址在今齐齐哈尔市桥西小学南侧。
这些流人遗址,构成了嫩江流域流人文化的旅游景点,并形成一条旅游古遗址旅游线路,推动了嫩江流域旅游业的发展。
[1]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清]方式济.龙沙纪略[M].
[3]方登峄.葆素斋集·今乐府[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4]西清.黑龙江外记[M].广州:广雅书局,1900.
[5]张守生.齐齐哈尔流人研究[M].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