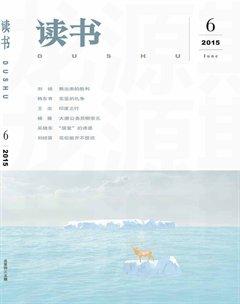日常抗争与中国研究
2015-06-11罗东
罗东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以研究前资本主义的农村社会而著称于西方政治科学界。他在《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一书中提出的“日常抗争”(everyday resistance)是解读底层抗争的一个研究范式,同时也将他推向了学术争议的中心。
先来看看斯科特提出“日常抗争”这一范式的基本脉络与逻辑。
该书源于斯科特在马来西亚一个村庄为期十四个月的田野调查。他把它取名为塞达卡(Sadaka)。塞达卡在一九七二年引入双耕(double-cropping),同许多地区的“绿色革命”一样,这里的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严重的阶层分化使穷人(小农)不断被边缘化,也加深了他们的阶级矛盾意识,但令人意外的是,这里并未就此而出现集体的反抗、斗争、运动或革命。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它是一个没有任何抗争印迹的和谐村落?斯科特敏锐地察觉到,没有看得见的反抗并不是就没有抗争行动。看似宁静,但已暗流涌动。抗争正在默默地进行—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人们利用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形式进行着持续的、不断的日常抗争。他们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非直接地与权威对抗,同时规避了来自利益集团的政治风险。
从斯科特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弱者的武器经常是奏效的。用他的话说,正如成千上万的珊瑚虫杂乱无章地形成珊瑚礁一样,成千上万的以个体形式出现的不服从与逃避行动构建了自身的政治或经济屏障。
但遗憾的是,这种对抗形式在以往的抗争研究却是被集体性忽略的。在西方中心主义下,有关抵抗或抗争的一切图景限于社会运动、革命等集体行动。
斯科特的研究功不可没。他把底层社会微观权力的运作逻辑与过程首次完整地呈现出来,这样的敏锐洞察使得那些“未被书写的反抗史”得以见天日。权力与政治不再仅是宏大的、组织化的叙事,还可以是微妙的、隐藏下来的日常抗争策略。后者扎根于日常生活和支配中,持续性和耐性更强。
但另一方面,斯科特和他的“日常抗争”框架也遭到了西方学术界的批判。
比如,科隆-汉森(Christian Krohn-Hansen)就指出,斯科特在得出他这一解释框架前就预设了一个非常值得商榷的假设:社会中的成员个体是能动的(详见Dialectical Anthropology杂志一九九五年第一期,71—94页)。巴亚特(Asef Bayat)提出了同样的批评,即由于没有对抗争的清晰定义,对底层日常行动可能会出现过度解释或过高估计的问题。这似乎可以给人一种错觉—任何行为都可以被视为抗争(详见International Sociology杂志二○○○年第三期,533—557页)。换而言之,连偷懒、开小差或取绰号等这样的行动都可被视为一种反抗,那还有什么不是抗争呢?是否过于高估了农民的能动性?这或许是读者最大的一个疑问。
对于科隆-汉森和巴亚特的质疑,斯科特在他“何谓反抗”一章已经给出他的预设性答复,他一直在努力走出现有的“反抗”定义。他认为,阶级的反抗包括从属阶级成员所有如下行动:有意识地减少或拒绝上层阶级(如地主、大农场主、国家)的要素(如租金、税款、声望)或提高自己对于上层建筑的要求(如工作、土地、慈善施舍、尊重)。赛达卡的行动是有反抗意义的,尽管他们有时是为了基本的生存而采取的类似偷窃这类行动—他在更早即一九七六年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中译本可见译林出版社二○一三年第二版)中将之表述为一种“道义经济学”(moral economy)。抗争是一个社会事实,但不再局限于西方知识架构中的集体行动,而是有了一个更为开阔的外延。斯科特的预设答复还不止于此。接下来的问题是,何种意义上,个体的反抗才可以成为一种抗争行动或日常抗争?斯科特用“珊瑚礁”做了一个比喻,“珊瑚汇聚成珊瑚礁”,也就是个体抗争不再是孤独而是普遍存在的历史时刻。从斯科特的考察来看,尽管日常反抗的形式是个体在行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相互间没有协同。作为个体的农民,日常抗争的使用,总是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契约,同家人、亲戚朋友等群体成员的态度是密切相关的。行动不再局限于个体的意义。如此看来,日常抗争不是别的,或正是社会运动或阶级革命的前奏。到那时,这些细小而零散的武器不再是无组织、非系统和个人的,不再是机会主义的和自我放纵的,不再是没有革命性的后果。比如,有学者如阿德南(Shapan Adnan)在研究孟加拉的农民抗争中就看见了这种向革命行动转换的存在(详见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杂志二○○七年第二期,183—224页)。
中国学者在借鉴“日常抗争”这一范式(或视角)的同时,也对它表达了质疑。
对于海内外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而言,这么一项外来的研究范式,首先将面临它解释力的边界问题。郭于华在二○○二年将尚未有中译本的《弱者的武器》介绍到中文学术界的两年后,于建嵘就根据他在湖南的调查而提出,斯科特的解释框架固然是十分有效的,但他的研究对象为东南亚地区,在具体的借鉴之中存在文化的差异问题。中国农民的抗争已不再是日常抗争(详见《社会学研究》杂志二○○四年第二期,49—55页)。这同欧博文(Kevin O’Brien)和李连江提出的判断一脉相承,中国农民的抗争不是日常的形式,而表现为一种依法抗争,即外在的、理性的,且偶或还表达为组织化的行动。法律、国家政策文件等已成为他们的武器。于建嵘还将这一判断继续推前,中国农民的抗争不仅不再是“日常抗争”,还超越了“依法抗争”,而进入了他称之为“以法抗争”的阶段。抗争不限于具体的权益,还表现出了一定的政治性。两年前,笔者本人基于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到来,也具体地对斯科特“日常抗争”及“公开的文本”、“隐藏的文本”的二分法提出了解释力的适应性问题(详见《香港社会科学学报》二○一三年秋冬号,33—67页)。近来,在网络讨论中,有观点认为,在中国乡村秩序之内,“乡村混混”是一个影响力颇大的群体,一旦他们当权,以暴力执法、统治,这时的农民表现出来的不是反抗而是服从。这是因为,这些混混出身于农民群体,对后者的行动逻辑或策略十分熟悉,以至于日常抗争不再发生作用。但事实上,这样的一些质疑,莫不是基于一定的空间、时间等维度的,是否拥有较为普遍的意义,还不得而知。这是因为,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状况仍然没有改变,社会空间非常狭小,强大的国家致使抗争的合法性困境仍未改变。只不过,鉴于中国国土的辽阔与区域情况的差异,底层抗争或可能出现“依法抗争”或“以法抗争”。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差异,同是研究中国抗争政治的另外一位学者应星又根据他的调查,对“以法抗争”提出了他的质疑,认为于建嵘的政治热情致使他过于高估了农民行动的组织化和政治性(详见《社会学研究》二○○七年第二期,1—23页)。孰是孰非?情况的复杂和差异可见一斑。这里的问题在于,他们寻找和研究的个案仍然脱离不了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除了个案的特殊性以外,笔者这样说,还因为于建嵘等将日常抗争与他们发现的抗争形式在理论框架上对立起来,非此即彼,但事实上,即使是同一个区域,在不同的抗争对象或事由中也可能存在不同的反抗形式。因此,对于乡村混混消逝了日常抗争这一判断来说,这样下定论还为时尚早,这在于:(一)“日常抗争”本身是一个策略性的反抗,这里的服从是否意味绝对的服从,还是说只因研究者没有发现服从背后的反抗形式,都还有待商榷,否则又将重蹈覆辙地将人民大众置于无效的地位;(二)“弱者的武器”的内容是丰富的,在斯科特看来,意识形态也是这些武器中的一部分,如流言、起外号等。它们同样可以销蚀这些乡村混混的合法性。
除了解释力的边界问题外,有关理论及方法论,中国学者同样提出了对斯科特及“日常抗争”这一范式的质疑。这样的质疑甚至来得更尖锐。赵鼎新在他的《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一二年版)中就提出,斯科特归纳出的这一范式,属于典型的解读传统(interpretation tradition),限于用特定概念来“说故事”,这些概念往往只能抓住事物或现象的一个或数个不太重要乃至是错误的侧面。换言之,在他看来,“日常抗争”是一个静态的描述,无助于加深对一场具体的农民运动动态的整体性理解。他同时不屑地在该书第十一页中写道:“我不相信每个智力正常的人会没有注意到这一无处不在的社会现象—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这类现象的话,像磨洋工、怠工这类词汇就不会成为日常用语。”在笔者看来,赵氏的质疑或批判实则折射出的是一个更大层面的讨论,即解释(explanation)与解读(interpretation)之间长久以来的争议。孰优孰劣,各执一词。同时,这样的批评还因为他们研究的反抗类型不同。赵氏热衷于政治运动、革命等外显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s),斯科特关注的则是日常抗争等隐形的个体行动。事实上,两种行动表现,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也谈不上相互矛盾。
回过头来,再来看中国学者对斯科特及其“日常抗争”的质疑或批判,无论是围绕理论边界还是方法论等问题,都没有置于“国家—社会”这一根本关系下。这样的后果在于,对于围绕理论边界来讨论的研究者来说,他们的质疑仅仅是基于不同的空间或时间维度,但贸然地得出日常抗争已经消失或失效的结论,重新将人民大众看作无效的、被动的阶级;而关于方法论的批判,则没有注意到日常抗争这一弱者的武器在中国语境下的现实意义,在中国当下的“国家—社会”关系框架下,它绝不是毫无价值的“解读传统”。
在笔者看来,斯科特的“日常抗争”对中国研究正保持有不可低估的解释框架作用。它同中国情况保持了极高的契合性。
这至少是因为:(一)“国家—社会”关系中,中国社会行动空间十分受限,国家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因而对于诉求、维权或抗争行动中的人们即行动者来说,合法性困境仍然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二)同时,同自由等西方权利不同,中国人的权利观念是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归纳的“道义的经济学”,即对生存权、福利的追求(详见Perspectives on Politics二○○八年第一期,37—50页),这种观念支撑下的诉求或抗争,是基于个人的生存而不是针对国家的权威挑战,同日常抗争这样的抗争形式有着高度的亲和力。正是如此,它仍然在被人们艰难而又策略性地使用着。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合法性困境始终是理解中国抗争政治一个十分关键的节点。这当然不意味着日常抗争作为解释框架是普遍可行的,但至少,它不该在还保持解释力的地方被低估、被抛弃。我们仍然看到,斯科特提供的解释框架及敏锐的洞察力,将有助于中国学者更深刻地理解处于转型期中国的诸多社会问题。
尽管笔者并不赞同赵鼎新对于该框架提出的近于刻薄的批评,但他同时又说了这么一个令人深思的意思,即这种类似日常抗争的解读传统下的第一本书或还有它的价值,但是“后面照猫画虎的工作马上就会变得越来越无聊”,这一说法有它的一些道理。当偷懒、取绰号等反抗形式已被概化为日常抗争,接下来的工作多是寻找案例来验证,如果研究止步于此,结果将是受制于既定的解释框架,难以在理论中突破。多年来,对于那些借鉴斯科特及其日常抗争的研究而言,鲜有实质性的突破。但中国香港学者潘毅(Pun Ngai)在对“长三角”的劳工研究中就令人称奇地提出了日常抗争的另一种形式—“身体抗争”,即女工阿英在遭遇现行体制、全球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三重压迫下,在夜晚睡梦中的尖叫与梦魇。潘毅称之为“抗争的次文体”。该文先后以英文和中文发表,后收入到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Duke University Press and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5)一书中。尽管潘毅没有说明是否受到斯科特的影响,但所揭示的这一抗争形式已超越了斯科特定义的日常抗争,拓展了它的外延。这种超越体现在,如果说偷懒、开小差或取绰号等形式还是行动者有意识的反抗,“抗争的次文体”则进一步突破了意识的界限,已不再是意识层面的行动,按潘毅的说法,尖叫或梦魇等次文体介于意识与无意识之间。日常抗争的形式或外延得到了拓展和丰富。潘毅的超越给了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这样一些学术启示,日常抗争不仅出现在农民反抗中,还可能广泛地存在于劳工等其他领域,同时它的形式并不局限于斯科特书写的那些基本类型。如果将这些日常抗争的形式在类型学上归为一般形式与意识形态生产两类,对于中国研究的现实意义就更加明了了。正像斯科特所言的那样,一般日常抗争形式将可能是矛盾集中爆发的前奏,在集体行动出现前就洞察到存在的反抗问题,有助于缓解和解决矛盾。同时,至于意识形态,它同样是日常抗争重要的一环。特别是社会化媒体空前发达的当下,大众通过网络匿名化表达出来的谩骂或绰号,同是观察中国矛盾的一面镜子。
日常抗争根植于特定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为的是规避“强国家与弱社会”带来的可能风险,而不是挑战国家政治。
(《弱者的武器》,詹姆斯·斯科特著,郑广怀等译,译林出版社二○○七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