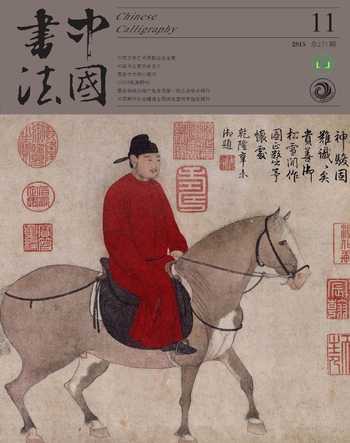沈门蓬溪五人展
2015-06-10



时间:十月二十八日
地点: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
主办单位: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
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院、四川省书协
成都画院、蓬溪县人民政府
学术支持:中国国家画院
承办单位:莲溪县委宣传部、蓬溪县文广新局
蓬溪县旅游局、蓬溪县投促局
『中国书法之乡——沈门蓬溪五人展』『北京展』十月二十八日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开幕。今年六月二十八日—七月八日,『沈门蓬溪五人展』首展在四川省蓬溪县举行,开启了全国巡展序幕。
何开鑫、文永生、杨曼、黄胜凡、陈刚来自四川省蓬溪县,先后在中国国家画院沈鹏先生工作室学习。近年来,他们植根传统,融入时代审美要求,致力于探索属于自己的个性化表达方式,成绩斐然。
蓬溪位于四川盆地中部偏东,东晋置县,已有近一千七百年的历史。一九九五年《中国书法》第四期对『蓬溪书法现象』进行专题介绍,并组织召开『蓬溪中青年书法发稿座谈会』,由此,蓬溪书法成为全国书画界关注的重点。(编者)
何开鑫:
我的老家在四川蓬溪奎阁广场口上,亦称水井湾,因有一口百年老井而得名,井泉似乳,清冽沁心。四五十年前,没有电扇和空调,每至夏天异热之时,家家户户都在井里打水,泼街退凉,晚上整条街蚊帐相连,鼾声梦呓此起彼伏,月光照时,帐帏明辉。多少年来,无论外面怎样干旱,井水依然甘洵如常,泉涌淙淙。
清代建筑奎阁,飞檐耸立,文藻流芳,阁下文化馆里的老师们常常挥毫泼墨,笔走龙蛇;听他们讲『奎星点斗,鳌屿河晏』之类的掌故。晚晴钟山秀,霞映溪河清。奎阁前是一排当时蓬溪最宏伟的建筑,工业、农业、科技展览常在那里举行,尤其是经常举办一些美术展览。我自幼喜好写写画画的兴趣由此养成。奎阁后面是柚园和芝溪河,河上一座墩子桥是儿时戏水的场所。桥两边两棵黄桷树扇硕如掌,枝荇交横。芝水湾环似玉带,柚花开时香半城。及长,写画兴趣渐浓。乡泥滋性,翰墨培心,上山下乡,戎旅边陲,一幅笔墨伴随我走进了耳顺之年。
二〇〇七年,是我学习书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全国范围内我被选拔进入中国国家画院首届沈鹏书法精英班。一年半的学习使我获益匪浅。老师的教诲,同学之间相互切磋、深入讨论,这一切使我体会到:如论书法,首先要讲『性灵』,它犹如船之舵、钎之锥、果之核、花之蕊。性灵由识、悟、思、定四位一体组成,性灵最终要看是否达到格物致知,慧心明澈。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其次要讲『技』。它是书法本体的基础和终端元素。书法也可说是『线』的艺术。书家的一生就是摆弄笔墨、摆弄线条和汉字造型。犹如『水之重船』,单纯而丰富的线条,承载着无限的内容。第三要讲『气』。『一切艺术的闷葫芦都是气韵问题』,我一直喜欢林语堂先生这句话。『胸罗万象秉高鉴,腹有诗书气自华』,笔墨之气大都来源于人之气。书法中其他诸气均可,但不能有『浊』气。势贯于上下,气通于隔行,神附于点画,韵生于笔墨。这些都要靠作者胸中酝酿出的人之气导源出笔墨之中的『朝气、书卷气和灵气』。但使笔砚经日月,留将萧瑟叹云泥。
文永生:
我一直以为风格的确立和逐渐成熟,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艺术本身是排他性的,有我无他,有他无我。王羲之再好也只需要一个,模仿得再像也最多相当于一个复印机,所以沈鹏先生提倡『原创性』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内含深意。但是,『原创性』说起来就这么几个字,做起来确实需要下很大的功夫,也可能下了一辈子的功夫也无法摸到边。
所谓『原创』,并不是另起炉灶、从头再来,而是在深入研究传统经典的过程中,逐漸积累个人感受并下意识表达在作品里,这需要具有对传统非常深的分解和整合能力。首先要分解,要把不同的经典分开揉碎,然后重新按自己的心性和体会整合组装成形,最后变成自己的一个东西。它是从传统中来的,每笔每划都需符合传统的规范,但整合在一起又是全新的面貌,已看不出具体是从何碑、何帖而来,但风貌独具,韵味悠然。这就是李可染先生所说的『用最大的功夫打进去,又用最大的功夫打出来』。但现实是,好多人打进去了就再也没能打出来,也有好多人根本就没打进去就跑起来、飞起来了。所以书法学习实际上就是一个终身修练、终生悟道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持之以恒,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当然还需要一点天才的基因,方能有所成,除此别无他法。
杨旻:
二〇〇七年下半年,蒙曾来德先生举荐,我进入中国国家画院沈鹏工作室书法精英班学习,忝列沈门,心有惭愧。沈鹏先生第一堂课就送给我们这样一句话『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振聋发聩。
简言之,书法就是汉字造型艺术。反思自己,觉得我只是一个平庸的书写者,缺乏从事造型艺术最重要的能力——空间结构的想象力。当时我很沮丧。我该怎么办?通向理想的路在哪里?我曾尝试过学习绘画,从临摹《芥子园画传》的《兰谱》开始,冀以提高自己的空间结构能力,但半年下来,一无所获。
二〇一〇年,我已年届不惑,突然感到不能再浪费时间了,需要把精力集中在书法上。于是,我几乎拒绝一切社会活动,让自己安静下来,以最大的勇气、最大的决心向经典法帖迈进。五年来,我系统地临习了王羲之、王献之、张旭、颜真卿、怀素等晋唐诸家法帖,旁及《石门颂》和日本『三笔三迹』。这种临习不是年少时的浅尝辄止,而是有计划的『功课』。我买了三种不同版本的《淳化阁帖》,分置三处,日日为伴。在几乎每日半个时辰以上的临习中,我感受到那些伟大的书写者笔下勃发的生命力,常常为一丝精妙细微的墨痕、一个出人意表的字型而惊叹,并从中揣摩他们的书写姿势、入笔角度、下笔轻重、运笔速度、转折处如何提按、收笔时如何引带,从而找到用笔、结字的规律。当我逐渐领悟到一些『王氏家法后』,才真正明白赵孟頫《兰亭十三跋》第七跋『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的意思。因此,我豁然开朗‘‘就书法而言,空间结构的想象力需要笔法来支撑。笔法通,无往而不利,空间结构的想象力表现就没有障碍了。
再次反思,我没有沮丧,只是汗颜,我觉得可以用一个字概括二〇〇七年以前的书法经历——急!草草临习几个字,便急于出帖、急于创作、急于参展、急于成名,偶有『作品』入展,就洋洋得意;遇到高人批评,便以『笔墨当随时代』掩饰,自诩为创新,甚至自以为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真是无知者无畏!
五年的『蛰伏』,五年的补课,让我隐约看到了自己的理想,她远在天边,又近在咫尺,但通向理想的路明白而坚定,我还在路上,路就在笔下。
二〇一四年春,曾来德先生回乡,提议举办展览,我诚惶诚恐,斗胆应承下来,一年来边临帖边创作,小有收获,后来又创作了一些少字数大字作品,这就是『沈门蓬溪五人展』我的作品构成:第一板块临帖,第二板块行草书小字书,第三板块少字数大字作品。
黄胜凡:
对于书法,我不敢有更多的奢望,只希望书法能给我带来一丝情绪上的愉悦与美好。
书法如果仅限于汉字书写的方法,那就太简单了,时间堆积即可得到,但这样的书写,可能比馆阁体还馆阁体,电脑字的初始就是这样来的,但艺术需要的是境界和味道。电脑的普及,快捷了汉字的实用功能,但影响了书写性的传承与发展。既然书法是艺术,审美当为主要其功能。我的理解,书法应是用汉字进行的审美创造。汉字从一开始就是以记事、表意为目的,其审美的成分随人类文明的进化而渐进,以至发展成为以审美为主要功能的书法艺术。
古人留下来的经典,不是一滴水,应是一条河,它是一个流派发展的结果,它有源头和流经过程。帖是真实的,但成因、过程是虚幻的。只单纯就帖临帖,难有实质性的收获,并且还可能误导学习者,不少人说临帖临得已很像,但离帖就一片空白,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当下一句时髦话:走『进』古人。其实古人是走不进的,古人的环境回不去,古人的内心走不进。一千多年来,学习《兰亭序》,前赴后继,跨这么长的时空,事实上《兰亭序》仍然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说明后人仍然没有对其解码、没有超越,《兰亭序》的形成,应是魏晋书法发展到了一个至高点。要从《兰亭序》里得到更大的收获,得追其成因,否则难于接『近』。就艺术过程而言,中国书法和中国绘画一样,自古以来就是师徒传授,就因为要亲临、亲历书写和作画的实践过程。种种原因,包括战争、文化等等的革命,造成了文化传承的无数次断裂,古人的书写过程没有有序、无缝地传递,后人对古人经典的分析,大都是断想,并且是本位经验下进行的推想,与本体的距离不知有多远。没生过孩子的人是没法讲生孩子的滋味的。
书画相生,书法可以解决大写意中国画的诸多问题,反之亦然。书法的核心是笔法和章法,章法在绘画中即是构图、构成。如果能把书法中的笔法用于大写意中国画,把构成用于书法,两者不仅同源,而且互助。我喜欢大草,大草畅神,更爱写丈二、丈六,尺幅大,打得开,身心联动。心手双畅是我需要的状态。大草写气,谢赫提出气韵生动,并放在『六法』之首,潘天寿先生讲画气不画形,均同理。气,是大草的核心所在。气,来自作品的势,势是大草突出的特征,势的形成需要好的技法作支撑,线条需要多种畅气的组合。当然,技法的成熟是随着艺术的精进而到位的。草书的技法构成因素很多,讲得清、看得见的技法不是技法,至少不是高级的技法。大草的技法,既是静态的,也是动态的;既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既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大草的线和音乐相似,形式与现代诗歌相通。我写大草喜欢以音乐营造环境氛围,在旋律中寻找线的感觉。我喜欢和诗人交流,诗歌讲究形式,善留『白』,惜字如『金』。我的大草常在诗歌里吸取营养,大草如诗。
陈刚:
对于书法,我想得很恬淡。因为我的学识、身份、才气决定了我不可能取得多么高的成就,所以平时写到哪儿就在哪儿歇。反过来又想,既然走上这条道路已三十年了,写得太孬,恐人耻笑。抱着这样的心态,在求艺道路中昏昏浊浊前行。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十年的历程有二十五年是在跟着感觉写。看別人写碑,就临《广武将军碑》《古塔铭》《龙门二十品》,临得似像非像就把笔当刻刀用,写得吃铁吐火的。偶尔发表甚至入展更加强了这种写的信心和力量;看见别人写帖,又临米芾、苏东坡,写得甜美秀丽,把从碑那里舀得的一点墨水又抛洒得千干净净;听见别人说还是碑帖结合好,就又追求粗壮式的秀丽,偶尔划出点方笔,以为就碑帖结合了。
二〇一一年,应该说是我对书法追求的转折之年。当年九月,我进人中国国家画院沈鹏工作室书法精英班学习。看别人,想自己。三个月后,居然无法写字了。原来的纸不合适了,而且按照原来的写法无法再创作了。是我参加学习错了,还是原来书写一直都错?我百思不得其解。一日,与杨曼在露天坝喝茶,风和日丽,不冷不热,正是谈书论道的好时候。杨曼说:『古人怎么写的都没搞懂,你何谈学习古人?!一句点醒,原来我学书的技术问题都是错的。于是,我又老老实实从技法学习开始,大量阅读和研习晋唐法帖,每天对临、空临、意临,先把写字的方法整对。
如今,我有两点感悟:一是必须学习古人用笔。因为笔法是可以学来的。古人笔法不能上手,永远都不可能得法。至于字的结构、作品章法,我觉得是天赋,是个性,正如幽默与生俱来一样;二是笔墨当随时代。因为个人是无法孤芳自赏式独立于这个时代的审美的。
年近天命,终于醒悟:学古人笔法,写自己个性,融书进时代。『沈门蓬溪五人展』述评
曾来德:
蓬溪地处川中,风光奇丽,毓秀钟灵。高峰山之云雾,凝萃三教哲思;赤城湖之烟水,浩淼百里方圆。自东晋建制以来,文教昌明,人才辈出,有『五史之乡』『梓东邹鲁』之誉焉。明清之际,蓬溪科甲尤盛,一时冠盖如林,杰俊蜂出。如明代礼部尚书席书、清代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张鹏翮,皆位极人臣,扬历中外;又有蜀中诗冠张船山,一代风流,名播巴蜀。汲乎国朝中兴之际,又有『蓬溪书法现象』享誉寰宇,其非前贤文脉蕴而属之耶?
『蓬溪书法现象』之兴起,赖二三前辈导夫先路,后进之士,类聚结社,砥砺碑版、琢磨法帖,乘当代书法复兴之历史浪潮,独揭奇崛跌宕之书风,引起全国之注目。其探索之过程,筚路蓝缕之艰辛,可感可歌。蓬溪书法诸家中,有何开鑫、文永生、杨曼、黄胜凡、陈刚五子,书艺成就,尤为突出,其艺术风格,亦各具特色:如何开鑫之浑厚苍茫、文永生之奇崛灵动、杨曼之书生意气、黄胜凡之真力弥漫、陈刚之优雅古淡,面目虽各异,然皆深具传统之功底并富有个人面目,而五子作品所体现吾川奇逸灵秀之地域文化特色,又可见其文脉传承与艺术理路之内在统一。
自二〇〇七年始,五子先后负笈京华,问教于当代书坛泰斗沈鹏先生门下。沈老一代宗师,入选其门者,皆各地书法界之领军人士,其中不乏当代书坛重要人物,可谓名家荟萃、高手如云,蓬溪以一偏远小县,能有五人入选,亦可谓一段艺坛之佳话耳。经数年之学习深造,五子眼界心胸,日渐拓展,书学成绩,亦得以勇猛精进,早非吴下阿蒙,亦诚当刮目相看者也。今五子欲联袂展览,并嘱予为序。予与五子,论交且三十年,于其艺术之成长进步,历历在眼。今不计工拙,聊作喤引,记其因缘本末,并致赞叹祝贺之意云尔。
本文为《沈门蓬溪五人展作品集》序
王鲁湘:
因为曾来德,两次到蓬溪。一次上高峰山,拍摄道教的八卦迷宫,观蜀中建筑之奇;一次到县城,则是为『沈门蓬溪五人书法展』而来。
蓬溪书法现象曾引起全国瞩目。一个川中小县一时间竞涌出这么多书法爱好者,其中多人在全国各类书法大赛和大展中拔得头筹,不由人不啧啧称奇。有文化人称之为『中国书法界最壮美的乡愁故事』。
何开鑫、文永生、杨曼、黄胜凡、陈刚,都是蓬溪籍的当代书家,也都先后进入中国国家画院沈鹏工作室深造。沈门精英荟萃,五子得以忝列,足证蓬溪书法势头之盛与基础之厚。五人书法展是在蓬溪体育馆举办。我在开幕致词中说:『几根中国书法的线条,就撑起了一座钢铁现代建筑。』成都诗人闻之,击掌叫好,说这两句是诗,道出了中国书法的魅力和她在当下语境中存在的可能。
五子中何开鑫,稍年长,刚进耳顺之年。经多年的学习悟到书法首讲性灵,次讲技,三讲气。所谓性灵,重要的是想象力。『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这是沈鹏先生对精英班学员的教诲。当然,这是对已经烂熟书法史且已有相当书法造诣的书法学习者的棒喝,让他们从因循古人中跳出来,牢记中国书法也是一门想象力的艺术,所以,沈老给书法精英班确定的十六字教学方针的头八个字就是『弘扬原创,尊重个性』。数十年的人生历练与勤奋临池,何开鑫的书法已然隐隐有苍茫气象,其大草既有征旗猎猎的边塞秋高之意,又有雨林长藤的生死纠缠之韧,总体上给人苍茫悲壮之感。
文永生是个很内敛很执著的人,他的书法暴露了他的个性。他是个很文静很不喜欢张扬但我行我紊特别追求个性的人。他喜欢在可以控制的腕径之内写行草相杂的小字,每一笔,每一字,都有姿态。这姿态,半正半邪,半醉半醒,半嗔半狂。看上去收敛、柔顺、弱小,站不稳,立不住,一碰就倒。但是你真去碰他,每个字都很硬,很倔,很犟,每一笔都是乱扭的钢筋,扎人。他好用焦墨和宿墨写字,行笔短小艰涩。如果上阵打仗,我坚信,文永生使得最好的兵器是匕首。这种人,对于个性,对于风格,很敏感,排他性强,对书法的大形式外形式不会太着力,但对于结体与使转之间的精细微妙之处,极有会心。照书法界的行话,文永生是个往里写书法的人。
杨曼可能刚好同文永生相映照。杨曼的字写得大,文永生的字写得小;杨曼的字写得方正,文永生的字写得欹斜;杨曼是那种长胳膊长腿个头高大的重量级拳击手,中国武术中的北腿,文永生是那种小肌肉群特别发达的精干有力的轻量级拳击手,中国武术中的南拳;杨曼使的是长枪大戟,文永生使的是匕首短刀;杨曼往外写,文永生往里写。这种比较没有优劣之分,只是特点不同。文永生风格的排他性很强,杨曼尚在广泛的吸纳学习中,包容性很大。我个人意见,杨曼那种开张奇逸的书风,似可将石门颂、经石峪、颜真卿、伊秉绶、康有为打通,往外写,开拓空间结构,以势取胜。
五子中黄胜凡是画家,擅大写意花鸟。他学习书法的目的性很强,就是要解决自己绘画中的线及题款的质量问题。他的绘画老师是姜宝林,姜宝林的艺术主张是『既要笔墨又要现代』。这八个字恐怕也是黄胜凡学习书法的指导思想。他喜欢大草,他的大草更像抽象绘画,绘画性强于书法性。他也常写一两个字的书法,用心之处在黑白虚实的关系,玩的是空间构成。但他确实也老老实实写王羲之和褚遂良,把帖的流丽和碑的爽利结合得相当到位,是书家字而不是画家字。黄胜凡这个人外拙内巧,气很盛,可谓真力弥满,内心充满诗人的激情,很不安分,时时都有创造的冲动,但又肯下笨功夫。用孟子『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的语句来期许他,是不会落空的。
陈刚,是个才子型的书家。性情幽默,为人洒脱,其字让人想起舞台上的小生,风流倜傥。他的字从结体到用笔,都透着一股俊气。字的重心高,挺拔;点划正奇相生,明明是高门大户子弟,故意要来点不拘礼法的反常举止。他的书法,熟中生,拙中巧,还处在寻找本来面目的过程中。他是一个巧人,但向往朴拙,这就像孔门弟子曾参,画家李可染,需要在深刻认识自我并有了『存在的觉醒』后,以『自明誠』的终身修养功夫,克己复礼,终成正呆。
蓬溪五子书法,五人五品,在中国当代书法家群体中很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