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坦 接受语言的事实
2015-06-02
意识在任何空间都会被人们主动的抛出,并且它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样貌——交错并非一致。对徐坦而言,意识就像一种语言,然而语言的特征恰恰是要接受语言的事实,因为可变构成了事实,它看起来比单一更具特征。所以意识在今天已经无法再发出单音,出于人的控制,它的多音变的可变、可被传递。徐坦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使这些纯粹意识活动里的东西变的可视。
从徐坦的“关键词”、“社会植物学”,能看到他投身到人文、社会等各个学科覆盖的地域进行调查,这与很多直接介入社会活动的艺术的区别在于他所介入的调查和艺术的知识生产有关——在介入社会和对知识生产的提取之间置入了他个人的写作。徐坦这里的“写作”有别于社科调查的“写作”,他把自身创作方法论中的调查现场、资料研究、展示现场,甚至录像都定义为可视性言说的写作。
关键词——如此微观的意识缩影,又是很快被消费的东西。徐坦从对采访的素材中提取关键词并做研究,把研究看成是艺术家和社会发生关系的方式。他把对知识生产的调查设定在有具体社会方位、主题的与关键词有关的工作中。这种长期的研究工作鉴于艺术概念来看它具有丰富性和填充性,而只是与生活保持了某种平行关系的艺术介入,刚处于停滞状态,这反倒会显现出一种艺术概念的匮乏。
I ART:你曾这样说到,“在早期创作中和现在工作中的相似性在于,认知和表达的一致性要求,既:认知活动一直是艺术活动的重要部分。”那么针对你的“关键词”项目和“社会植物学”项目的工作中,把“认知”放置到社会生活基点中的位置,与早期创作相比所关注的不同点在哪?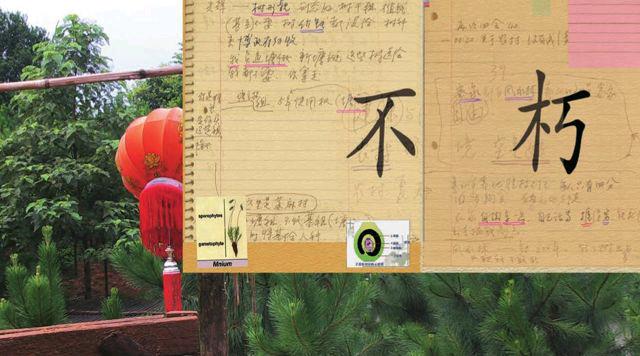
徐坦:以往的创作关心的是存在问题,即我们的生存问题,这个阶段大部分是直觉性的工作,而之后的工作都是有针对性和专门性的。举个例子,早期有一件作品《关于广州三育路14号改建和加建》,“广州三育路14号”是一所老房子,是抗战之后建的,属于私人财产,但是之后共产党要收归国有,一直到改革开放,才将这所老房子归还给前房主。在我到了那个地方之后我对这些问题是很感兴趣的,我觉得这都是艺术和美学表达的重要内容。之后还有一件作品《问题》,是关于土地占有权的国际法的讨论,我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来读相关的书籍。在当时我基本上没有找到更恰当的方式介入到这些社会议题里面,只是会读很多书,我认为读书很好,但是读书不是一种真正的能与社会生存的问题直接发生关系的方式。所以在“关键词”开始时,我基本上选择了采访的方式,之后对采访的素材做研究。2005年开始“关键词”的工作到现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把研究本身看成艺术家与社会发生关系的一种方式,不仅仅是调查,重要的是调查之后艺术家所要做的工作。“社会植物学”实际上是“关键词”项目的一个分支——关键词实验室“社会植物学”。“关键词”项目本身在一个长时间的实践中是发生了变化的。关键词实验室是2011年之后的项目,它与“关键词”项目最初的两个部分“关键词学校”、“可能的语词游戏-徐坦语言工作室”不同的地方在于关键词实验室是一个有具体方向、在具体社会分类里面工作的、主题性的项目。社会植物学的方向当然是很宽泛的,所以我的工作针对的是在这个范围中具体的分支的方向,以社会调查为基本的方法,之后再做研究,所以我称之为公共的实验室。
I ART:比如你针对“关键词”项目扎根到社会生活所做的调查,这确实贴近于生活,但你作品的表达又好似鉴于平行的生活调查基础上抽离出一种“认知”的艺术可能性(意识、思维等方面),那你能谈谈这种切实调查与“认知”的艺术可能性之间的抽离关系吗?
徐坦:我的工作首先介入到生活,与生活中不同的人群、群体发生一种交流,但是社会植物学在交流的基础上又深入了一些内容——观察他们具体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我的工作一直强调的是与艺术的知识生产有关,不是直接的对社会生活的介入。我工作过的地方都是人文、社会各个学科覆盖的地方,还包括面对同样的时代对象,在同样的地域得到不同的发现,这是特别重要的。社会植物学这个词本身是“关键词”项目生发出来的。我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经过查阅,这个词是不存在的。包括在工作中与华南植物研究所找过很多科学家讨论过这个问题,有社会学、植物学、城市规划等各种各样相关性的学科,但是社会植物学的概念是在这些概念之间的。我发现作为艺术家还是有可能在不同学科之间工作的。有的人会说我做的工作与人类学、社会学很像,那是不是就是做的这样的工作?其实恰好不是这样。
今年参加上海双年展的作品《社会植物学,种(2)》呈现的是近期研究的工作,以录像、写作、现场装置这几个部分构成。那么这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我做的工作与学科类科学家所做的工作不同的地方在哪?科学家或者学者他们很明确的表示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呈现就是写作出版,而对于艺术家而言,虽然我也是在写作,但是主导方式不是通过文字、印刷,而是通过我们的媒介。所谓我们的媒介首先是现场——与不同群体现场的交流,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在现场,大家有一种互相交换产生。我把它看成是行为艺术。现场也是收集资料的过程,而同时也是一种美学表达,两者是重叠的;第二部分是录像——作品中的录像是多屏幕的录像装置,另外我的写作中有一种写作被我称之为可视性言说。我的写作分三种方式,一是手写,另一种方式是打字,第三种方式就是可视性,我想些什么,就打开摄像机、对着摄像机说话;第三部分就是写作的文字——我在展览现场会呈现写作的文字和关键词的分析以及记录的研究;第四部分就是现场的装置、现场的发生——可以作为workshop出现。这是我基本的方式,我把所有的路径都称之为写作,包括做录像也是写作,艺术家通过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媒介去写作。
I ART:感觉你在做“社会植物学”项目时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置身主流艺术之外的艺术认识和艺术方法论的态度上,那你能谈谈今天当代艺术与切身生活的发生之间的缺失和必要性联系在哪?
徐坦:这里可能存在对艺术基本概念的不同认知。今天的当代艺术,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出现了某种趋势——艺术家把对世界、日常的认识纳入到艺术中后变为一个概念,并独据这种方式。对此我是不认同的,我觉得这个做法是上世纪概念艺术的特点,而那个时候的概念艺术是很前卫的,它是一种开创。但是面对这种开创,我们在今天如果仅仅是沿用不去延伸的话,其实便失去了开创者的精神。对我来讲,我觉得我的工作是对艺术的延伸。对于某一概念的使用,有可能会使这个概念更加丰富也有可能导致这个概念变得非常贫困。例如我在做“关键词”项目时,我还想做一个社会论坛,让各种各样的人参与进来。我做这件事其实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方向——我向社会宣称我做了这个论坛,人来多少、或者来不来都无所谓,我已经占有了这个论坛,这就够了;但是在我想做这个论坛的时候,我是真的邀请二十或三十个社会群众真正参与这个论坛。我做这件事真正关注的不是对社会论坛的占据,而是这个论坛自身真正的表达。社会论坛这个概念在两种方向中是一个概念,但是却能派生出两种状况——一种是贫困的概念;一种是充实化的概念。所以在今天当代艺术中,存在很多的贫困概念,他们并不关心切身的发生,而只是在做一种占据。对于我而言,我的工作是在超越概念艺术。
I ART:你这次参与到“六环比五环多一环”项目中,出于哪一点态度与他们达成共识?
徐坦:我跟二楼出版机构有很长时间的交往,此次项目的出发点我是认同的——直接面对、介入社会。
I ART:你觉得“六环比五环多一环”项目中以艺术的视角进行调查与你之前作品中的调查有怎样的区别和联系(可以针对作品说明)?
徐坦:我本身是艺术家,但是当进入社会中时,这个身份是被我忘记的,我并不在表达中强调自己是艺术家。但是艺术家的教育背景、工作背景带来的认知、方式是我的基本方式,而这种方式是贯穿在我持续的工作中的。我始终在介入社会时有一种“想知道”的基本动机,我对每一种东西都持有想了解、想知道的心态,在这点上“六环比五环多一环”的工作与以往的工作没有什么不同,那么区别可能是在方式方法上存在项目的具体限制。
I ART:我觉得你对任何社会现象中人的“意识”或者普遍的“意识形态”很关注,按照你的艺术认知,你认为它们在你艺术线索里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徐坦:人的意识活动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我所有工作重要的对象。关于“意识”,我对接了它的过去,在古汉语中是没有这个词的,现代汉语白话文以后才有了这个词,“意”和“识”放在一起。中国五四运动以后一直是在革命,而革命对中国语言的影响非常大。“意识”最早的意思相对于英文的“Consciousness”,包括现在的词典还是这样的翻译。但是我在做“关键词”项目的过程中发现“意识”已经不仅仅对接的是“Consciousness”,所以我常常使用“意”和“识”的拼音。我们大学、中学、小学都在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习时,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句话——存在决定意识。但是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存在决定意识”说明了我们的思想是由社会的存在和自然世界所有的物质存在所决定的,这是我们的教育,久而久之在我们的脑子里就有了两个大的概念——存在、意识。在我们的概念里,存在就是世界,意识就是存在着的人的所有的精神活动,包括概念、感性、欲望等等。所以在这样的认知中,“意识”就不再是“Consciousness”,在中国的教育背景下,意识是一个对我们总体价值、思想、思维活动的描述。所以“意识”很大,艺术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如果要了解某个人怎么想问题,那就要了解社会意识和人群意识,我是出于这个原因重视“意识”的。
曾经我在美国遇到一个人类学家,他批评我,说我将“意识”不等于“Consciousness”是因为我们的环境污染了这个词,因为社会的意识形态,社会的教育导致了词语的变形,他说我应该还原这个词语原来的意思。我的回应是,你错了,语言的特征恰好是必须接受语言事实,就算是污染,如果现在大部分人都在接受,我们就应该接受这种改变,而不是因为污染要回到源头,这也是不可能的。像今天出现的网络语言,不论它是否合适,都在成为一种事实。
I ART:我认为今天艺术的“媒介”不只是一种媒材的属性关系,它更像是一种提供参照和介入的通道,根据你的经验来谈谈这个问题?
徐坦:我同意你的说法。我的工作在介入社会,那么行动本身就是媒介。(采访/撰文 :李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