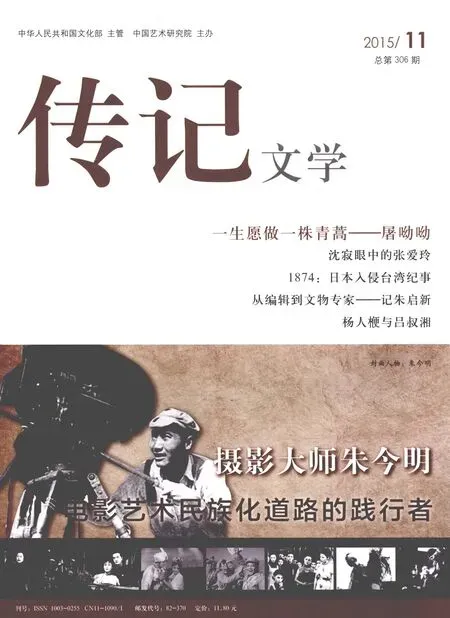族魂
——林连玉的华教事业
2015-06-01林阿绵
文 林阿绵
族魂——林连玉的华教事业
文 林阿绵

林连玉
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州福建会馆管辖的福建义山墓地里,有一座高大堂皇的墓园,正中是栩栩如生的林连玉先生的浮雕,上嵌“族魂”两个大字,左右翼刻着林先生亲笔书写的诗句:“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搏虎头。”绿瓦覆盖,极为壮观。
1901年8月19日,林连玉出生在福建省永春县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他7岁入私塾,16岁时,父亲让他到厦门当了3年学徒。正值陈嘉庚先生的集美学校师范部扩大招生,林连玉以优异成绩考取,从此他便与教育事业结下不解之缘。他以优秀的成绩毕业后留校教学。
1927年前后,林连玉渡洋南下,开始了他在东南亚一带的教学事业和社会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林连玉加入雪兰莪医药辅助队,在新加坡参加马来西亚保卫战时,两度几乎丧命。马来西亚沦陷后,为了逃避日寇的迫害,他躲在一个树胶园里养猪过活。
恢复华文教育
地球上海水能到达的地方就会有华人,有华人处便会有华文教育。尤其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为了继承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坚持不懈地维护母语的地位。
林连玉一生最辉煌的业绩,便是“二战”后,为了恢复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备受摧残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极待振兴。当时,华人约占马来西亚人口的半数,他们的当务之急是恢复尊孔中学。尊孔中学位于首都吉隆坡的市中心区,“二战”前办有高级中学、初级中学、师范班和小学,拥有1000多学生,号称雪兰莪州的最高学府。马来西亚沦陷期间,学校停办,校舍被日军占作军部,所有设备荡然无存,连空壳的校舍也是门破墙穿。其他华校已纷纷复课,尊孔中学的现状令人们十分焦急。临危受命,林连玉被聘为校长后,全身心地投入修复校舍的艰苦工作。他除了动员一些热心教育事业的人士捐款外,便是把自己在沦陷时养猪积存下来的几千元钱,全部奉献给学校。一面修葺校舍,一面购置教具,一点一滴重新建设。两年的辛劳奔波,终于使得尊孔中学焕然一新,于该年12月21日举行了开学仪式,林连玉功不可没。
林连玉当时的经济情况非常拮据,有时候可以说是达到三餐不继的地步。他的一位学生曾在文章中记述道:“为了尊孔,林先生的私人事业早已牺牲净尽了……终于,有一天,在我们的教室门口上演了这么一出悲剧:那是一个六月的早晨,当林先生在第一节课踏入教室时,我便发觉到他的脸孔正给一团忧愁的云雾遮盖着,他那无神的眼睛很明显地表露出睡眠不足的神态。后来,他终于直截告诉我们,他的太太病了。昨天回来学校时,口袋里只有五毛钱,吃了一碗面,再买一包香烟便不剩下一个铜板了。他太太的病又是那么沉重,不晓得如何是好……”后来,学生们捐集了一点钱送给他,他起初拒绝,经劝告才肯收下,不禁流泪对学生说:“吃教育饭是死路,我老早就打算退出教育界了。可是,我始终没有这样做,这是因为良心不许我这么做……”
面对着华校教师十分清苦的境况,林连玉决心把他们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以自身的力量谋求自己的福利,经过积极筹备,于1949年组织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他连任了十年的主席职务。这期间,他筹建会所,使教师公会经济基础永固,实行福利制度,使退休、去世的会员家属不致陷入绝境。他为华校教师争取公积金,争取新的薪津制,使教师能够安于教学,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通过教师节宴会提倡尊师重教,提高教师地位。
正当林连玉为进一步保卫华校教师的权益,发展华语华文教育事业积极展开工作时,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英殖民政府恶毒地抛出了一个所谓巫文教育报告书,妄图以“国民学校”取代“方言学校”,也就是企图用英文、巫文(即马来文)教育来消灭华文教育。华文教育厄运当头。正当生死存亡之际,林连玉领导的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在其他州教师会的要求下,挺身而出,召集全马华校教师会代表大会,坚持反对英殖民当局消灭方言学校的报告书。并决定成立马来西亚联合邦华校教师总会(教总)。

1954年,当时在尊孔中学服务的林连玉与高中毕业班师生聚餐合影
华教史上的“林连玉时代”
1951年12月25日,教总的成立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运动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大马华教运动进入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全新时代。可是林连玉并不热衷于权力。教总成立后,他功成身退,把主席职位让给他人,自己只居第二线,以一名理事的身份积极参与会务工作,并发挥他的巨大影响力,以大无畏的精神,掀起了反对殖民政府立法会制定的不利于华教的教育法令草案。他率领教总代表团与英殖官员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他说:“我们所争的是整个民族的权利,并不是个人的饭碗。”
1953年12月的教总第三届大会上,林连玉出任教总主席,从此开始了教总以至大马华文教育史上的“林连玉时代”。他首先提倡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提出列华文为官方语言。这一建议,不仅石破天惊,也开启了一个十多年争取华语华文列为官方语文的运动。他以教总名义发表了《反对改方言学校为国民学校的宣言》,犹如一颗原子弹,震惊了整个殖民政府。
在一个细雨霏霏的夜晚,林连玉突然来到一个学生家中。那天他穿着一件白色的夏威夷T恤衫,T恤衫上和额前还留着浅浅的水渍。在那间狭窄的饭厅里,淡黄色的灯光映照下,他的面厐更显得瘦小、苍老,活像个刚从饥饿阵走出来的老难民。马来西亚虽属热带,可在夜里10点,又下着雨,冷气逼人,他却不以为意。学生递过毛巾给他,又找出一件羊毛衣来。他摇摇手说:“我不冷,羊毛衣不必用。”只见他一边擦额前的水渍,一边说道:“最近,为了反对政府不利华文的教育法令,我经常代表教师会与殖民地官员争辩。今天争得非常激烈,结果不欢而散,政府很可能把我送进监狱或赶出境。我应先有准备,万一被送出境或坐监,腾方兄已答应维持我太太的生活费,你们只要不时到我家看看就够了。”那位学生笑笑说:“哪会这么严重,英国人是讲民主的。”他不以为然地说:“英国人在他本国是讲民主,在殖民地是无民主可讲。一位华校教师教学生唱一首有民族意识的中国民歌,或批改作文时有‘帝国主义’四个字,而被逐出境的例子已经不少。” 林连玉越说越激昂:“我是代表教师公会争取华文教育应有的权利,是代表全民华人的意愿,绝不怕坐狱和出境。再说现在世界的潮流,已是争取独立和民主的时代,各处殖民地纷纷宣布独立,马来西亚的独立为期不远了。我相信,如果殖民地政府把我抓入狱里,我们马来西亚民主政府便会释放我出来,若是赶我出境,也会接我回国。”这些从他内心说出来的话,可见他是多么热爱马来西亚,多么寄望于未来的民主政府呀!英殖民地政府审情度势,在退出马来西亚之前,没有再兴大狱加害林连玉。
1954年底,当马来西亚联合邦正酝酿自治——独立时,林连玉领导的教总,改变过去华人团体不问政治的传统,发表宣言表明“衷诚支持”马来西亚的自治,“并将加强工作,训导学童效忠于马来西亚,与各民族平等,共建和平乐土”。同时他明确指出:“假如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它的第一语言是巫语,第二语言则为华语。”当国家由自治走向独立后,他又挺身而出为华人争取公民权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在宣言中宣布:“我们的子子孙孙将世世代代在这可爱的土地上,同工作,同游戏;在遥远的将来,更可因文化的交流,习性的相染,把界限完全泯灭,而成为一家人。我们当前的责任,就是要为我们的子子孙孙,打好友爱与合作的基础,培养成共存共荣的观念。”
由于林连玉领导教总取得一连串成就,挽救了华文教育,使他个人和教总声誉鹊起,连英国殖民政府的官员都不得不承认,林连玉是“当前联合邦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

1972年1月5日,林连玉在雪兰莪医药辅助队30周年纪念宴会上吟诗之影
不屈不挠
马来西亚独立多年后,华文问题仍未彻底解决,华校教总当然要继续向政府争取,而且斗争的气氛更猛烈。万万没想到,林连玉未被殖民政府抓进监狱,也未被赶出境,而民主政府竟于1961年首先取消了他的教师注册证,逼迫他永远离开毕生为之奋斗的教育事业。1964年,竟然把他的公民权也剥夺了。这是林连玉终身遗恨的事。
当消息传来,群情悲愤,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而林连玉则处之泰然,将自己的得失置之度外。他在向尊孔中学师生告别讲话中,一再劝慰大家,应当以学业为重,安心学习,不可为他个人的遭遇而忧憾。至于加诸于他本人的不公平的对待,将遵循法律途径,继续与当道者周旋到底,绝不低头。
林连玉为保存他的公民权,被迫展开了长达3年的法律斗争。官司从吉隆坡打到伦敦,又从伦敦打回到吉隆坡,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从此,林连玉被迫离开了华教教育界的领导岗位,直到去世的20年间,他虽然患上眼病,仍然关心着华人的教育事业。在临终前3个星期,由于听到统治者写了歪曲历史事实、污蔑教总的文章,他还写文章《驳东姑》加以申斥,指出:“争取民族的权益是神圣的任务,我们永远不会屈服的。即使不幸遇到滥用权力者棘手摧残,仍然昂起头来,顶天立地,威武不屈地奋斗到底。”
生荣死哀
林连玉实践着自己的誓言,他是战斗到最后一息的,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与邪恶抗争到底。1985年12月18日,这位伟大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因哮喘不治,终于离开了人间。当天,教总等15个华团为他组成治丧委员会。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打破了60年的惯例……将大厅辟为灵堂。全国华社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哀伤……不分阶层、不分职业、不分党派、不分老少,为失去一位导师、英雄、斗士而黯然神伤。遗体停放的3天里,每天都有大群来自各地的社团代表和公众人士瞻仰致敬。人们热烈响应15华团的号召,捐献“林连玉基金”,以发扬他的精神,贯彻他的理想。尽管政府剥夺了他的公民权,人民却给予他以人民英雄的最高荣誉。
下葬当天,他的灵柩在万人陪送下,从大会堂出发,环绕吉隆坡市区游行5公里。炎日高照下,送殡队伍在长长的街道排成1里多长的阵容,肃穆庄严地慢慢前行着,直到福建义山入土为安。
1986年,庄严肃穆的墓园隆重落成,“族魂”永垂不朽。
1985年12月18日,林连玉的忌日被定为“华教节”。华人社会世世代代将永远铭记这位民族英雄的丰功伟绩。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