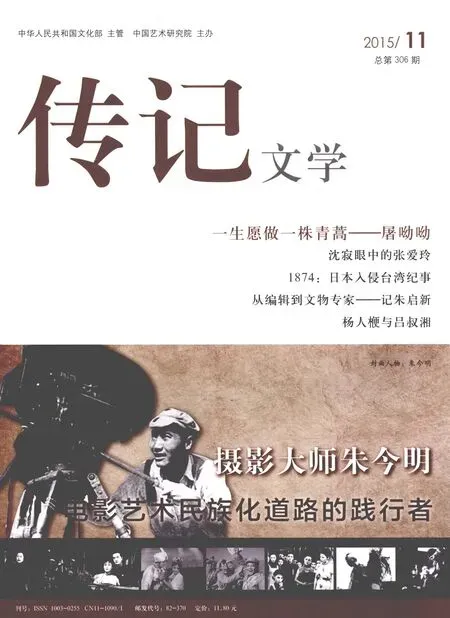朱今明:艺术的精致追求者
2015-06-01赵春晓
文 赵春晓
朱今明:艺术的精致追求者
文 赵春晓


《南征北战》剧照

《一江春水向东流》剧照
朱今明先生是中国电影史上的摄影大师,是我国电影摄影艺术的奠基者与掘井人,由他拍摄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三毛流浪记》《南征北战》《风暴》《烈火中永生》等作品,都是中国电影史上赫赫有名的经典,有着极强的典范意义。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历经动荡的政治年代,仍对自我、对艺术保持有较高的追求,痴心不改,上下求索,为中国电影的民族化影像叙事、现实主义的风格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一
朱今明(1915-1989),原名朱镜明,1915年农历八月十四日生于江苏重埠南通,是家中独子。
朱府曾是书香门第,父亲朱子宾是清末秀才,教过书办过学,为使幼子有更好的生活,养其成才,便在衙门谋了官职,以期生活有所转色。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身正气的父亲因触犯贪官锒铛入狱,母亲为搭救父亲,四处奔走,积劳成疾,终一病不起撒手人寰。世事不公,痛失慈母,原本活泼好动的朱今明变得内敛而沉默,他开始将无数个苦闷的夜晚交付于文学世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的大批进步文学作品,像一泓清泉浸入少年的心田,润物细无声,朱今明幼小的内心暗流涌动。
1927年,朱今明从崇敬小学毕业进入崇敬中学读书,与总角之交赵丹、顾而已、钱千里成为同学。当时的南通文化荟萃,不仅“国剧”(京剧)在一些名门望族的扶持下盛极一时,且常有上海的文明戏、歌舞团、魔术团在南通演出。浸润在热烈的文化气氛中耳濡目染,朱今明渐渐在沉寂中打开自己,他开始对戏剧和电影产生浓厚兴趣,对艺术世界心驰神往。
1928年春天,赵丹的父亲开设新新大剧院,剧院承接各种演出,也放映电影。有赵丹的关系,朱今明总能免费进出,他与同窗好友结伴,如鱼得水一般热切地投入到各种演出与放映当中,几乎场场不落。每次热热闹闹观影过后,剧中人物便成了赵丹等一众小戏迷争先模仿的对象,尤其赵丹,演得惟妙惟肖,常惹得旁人捧腹。朱今明不爱演,却很喜欢动脑筋,他找来一个美孚润滑油的洋铁皮箱子,三两下便改装成了“摄影机”模样,有模有样地摇着发条,给大家当起了“摄影师”,赵丹常亲切地称他“洋箱子”。
1930年上半年,受艺术潜育蠢蠢欲动,朱今明与赵丹、顾而已、钱千里组建了“小小剧社”,几人各司其职各有专攻,兴奋地将共同的志趣投入到具体的实践中。在剧社里,朱今明负责幕后工作,是剧社的骨干。他天资聪颖,动手能力极强,场务、道具、布景、音响等繁杂工作被他做得有声有色。不仅如此,他还常在舞台上客串角色一二,戏到动情处,往往声泪俱下。
他们自编、自导、自演的第一出剧目《阎瑞生》在学校礼堂演出即引起轰动,之后他们又相继排演了《艺术家》《热血忠魂》等脍炙人口的剧目,甚至走出校园,举办公演。12月14日,小小剧社假座新新大剧院举行了第一次公演,演出有《不平鸣》《中东血》《卖花词》《卖饼词》以及歌舞等16个节目,观众千人蜂拥而至,反响热烈。小小剧社声名大噪,不仅名扬南通城,也很快受到上海左翼剧联的关注。
1930年春,由上海左翼剧联领导的上海摩登剧社来到新新大剧院演出,朱今明与赵丹等剧社成员有幸接触到上海的进步戏剧工作者。这次非同寻常的会面使朱今明受到先进戏剧理念的启发,对之后的创作方向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自1931年起,小小剧社受上海左翼剧联的重点帮助,开始由几位年轻人兴趣使然的创作转入更为成熟有担当的创作,演出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反帝反封建反旧制度的进步话剧《山河泪》《铁蹄之石》《黑暗中的红光》及《乱钟》等,成为上海左翼剧联南通分盟的重要力量。
1933年6月,小小剧社第7次公演演出了洪深的进步话剧《五奎桥》,因剧中带有鲜明的反封建意识遭到政府当局禁止,剧社的骨干力量纷纷秘密转移,朱今明随后背井离乡,怀着无限憧憬前往革命的前沿阵地上海。
同年7月,受章泯同志介绍,朱今明正式加入左翼剧联,从民间社团走向了名副其实的革命文艺之路,人生的崭新篇章悄然打开。
二
初到上海,朱今明一边在上海电机厂做工,一边在电机专科夜校学习,同时还坚持参加剧联领导的一系列活动,到工厂、学校等地演出,宣传抗日。
1933年夏,为提高工资待遇,朱今明与上海电机厂的工友们秘密计划罢工。在一次冲突中,前来调解的朱今明意外受到牵连,被以“罢工带头人”的罪名强行押送南市公安局,两个月后,才因证据不足无罪释放。出狱后,朱今明被工厂开除,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但他并未消沉,每日以大饼油条充饥,继续与剧联的战友们搞戏剧工作。此时的上海已被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所笼罩,四处暗藏密探,剧联的演剧活动开始受到很大影响,工作开展十分不顺利。
1934年,国民党假借大专院校对抗左翼话剧运动,对中共进行文化围剿。朱今明受剧联赵铭彝指派,与顾而已、梁腾阻止国民党鼓动的话剧演出,遭人暗中盯梢,被以共产党嫌疑犯的身份关押老闸捕房,囚禁七十余日才得以宣布开释。
两次特殊的经历,使朱今明在磨难中迅速成熟,并对革命文艺工作有了全新的认识,他深切体会到民族救亡之迫切,革命工作任重而道远。
出狱后不久,经赵丹介绍,朱今明进入明星公司学习摄影。在明星公司做练习生的日子十分艰苦。朱今明时刻不放松学习,除了摄影,与制片相关的各个工种他都极力尝试,认真钻研。为全面熟悉电影制作的流程和工艺,他还观摩了大量的苏联电影,为日后的电影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业余时间,朱今明仍没有放弃话剧工作,经常积极参与左联的话剧演出。
1934年春,为拓声剧社演出奥尼尔的名剧《天边外》布景时,朱今明巧妙利用布幔、布条,与不同的道具搭配出不同的环境与意境,使有限的舞台延伸出无限的美感,被称为“象征派”布景。在这次演出排练过程中,一块悬挂在舞台上方的废弃银幕,使他意外发现了光的神奇作用,关于“天幕照明”的设想初现端倪。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朱今明不断翻查资料做实验,钻研技术,并找来同样在明星公司当美工助理的汪洋,两人分头设计、画图、制作灯具、跑工厂,终于在1936年11月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的《大雷雨》中,实现了这一伟大创举。演出时,天幕上一会儿群星璀璨,一会儿乱云飞渡,一会儿电闪雷鸣,如一场充满诗情画意的视觉盛宴,给观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感官震撼,现场掌声如鸣,媒介舆论纷纷称道。这次意外的发现,开创了中国舞台艺术的新纪元,朱今明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第一位舞台照明美术家。
1936年下半年,朱今明离开明星公司,正式加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出任舞台部主任,全身心投入到戏剧舞台中去,《娜拉》《钦差大臣》《欲魔》《醉生梦死》等多部作品都由朱今明负责舞台灯光设计及布景工作。戏剧舞台的实践,令朱今明对艺术造型有了全新的思考,他不再因循传统道具与灯光照明的使用,而是在其中寻找情境的突破,简陋的道具和设备经由他精心设计,焕发出无穷的诗意。
1937年,正当朱今明的戏剧事业如日中天时,“七七事变”爆发了。与很多有志进步工作者一样,朱今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救亡演剧三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全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去。他们从上海出发,高举救亡演剧的大旗,沿京沪铁路一路演出,辗转经过常州、无锡、镇江、武汉,最终抵达山城重庆。从田间到城市,朱今明一行人排演了《放下你的鞭子》《塞上风云》《夜光杯》《最后的胜利》等活报剧、抗战戏剧,真正使革命宣传的触角深入民间百姓,所到之处,反响热烈。
1938年10月,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山城举办第一届戏剧节,朱今明积极参加了各项演出活动。1939年5月,重庆在日军轰炸中陷入动乱,工作开展力不从心。朱今明等人陷入了新的苦恼。一次偶然机会,他们从书中了解到新疆的社会巨变,大力推行“亲共”“亲苏”政策,文化事业蒸蒸日上,革命气氛大好,几个人一拍即合,决定再度启程。他们斗志昂扬,马不停蹄,一路奔赴大西北,一心想要在新疆施展戏剧理想,以期从新疆前往苏联,学习先进的艺术理念。
经历了一个多月艰苦车程,朱今明等人风尘仆仆抵达新疆迪化,见到了慕名已久的茅盾先生。早在1937年,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新疆即开始内招贤良,许多文化名流包括茅盾先生应邀前来,在新疆支援教育与文化建设。生活半年有余,茅盾早已看透微妙时局,心中自明,情况并非几位年轻人想象中简单明朗,他再三暗中叮嘱大家,务必小心谨慎开展工作。情势复杂,包括朱今明在内的文艺工作者,瞬时遁入茫茫然,然而既来之则安之,他们还是很快投入到当地的抗日救亡戏剧运动中。
1939年“九一八”8周年国耻纪念日,由朱今明担任舞台美术设计与督导的抗日战争话剧《战斗》与观众见面,轰动了迪化全城,演出长达半月之久。1939年10月初,新疆文化协会正式成立了新疆第一个职业话剧团体——新疆实验剧团,朱今明开始更多地忙碌于舞台幕后。与此同时,新疆学院增设戏剧科目,作为年轻有经验的专业工作者,朱今明承担起了舞台技术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在朱今明等工作者不辞辛劳的努力之下,新疆的抗日救亡戏剧运动如火如荼,星星之火迅速发展成燎原之势,将全民戏剧运动推向高潮。工作开展得顺利,几位年轻人沉浸在单纯美好的喜悦中,几度忘却了时局险恶。
1940年秋,军阀盛世才叛变,制造了轰动一时的“杜重远事件”,并捏造了莫须有的罪名,将赵丹、徐韬逮捕入狱。形势越来越复杂,朱今明见好友入狱妻儿离散,几近家破人亡,主动与王为一、易烈为好友四处奔走救援,甚至联名致信盛世才,终不得结果。
1941年2月,敌人的魔爪伸向了朱今明,他又一次深陷囹圄,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之后漫长四年的牢狱之灾,实在是他始料未及。长夜漫漫,黑暗潮湿的牢狱环境使他患上了严重的牛皮癣,身心长久地经受折磨,往日风华正茂的铮铮男儿逐渐形销骨立,没了模样。经历了毫无结果的苦痛挣扎与殊死反抗,朱今明也渐渐学会隐忍与等待,苦难磨砺了他的心性,他开始潜心学习俄文,以学习寄托精神与相思,等待重见天日实现自我的艺术理想和抱负。
1945年“五一”前夕,盛世才在新疆的独裁统治垮台,朱今明等人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营救,终于重获新生,返回重庆。
1945年8月,作为在新疆动乱中幸存的文艺界人士,朱今明等人受到了重庆剧人的热烈欢迎。不久之后,朱今明受到组织委派,与赵丹、徐韬、王为一同志一起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这次见面使他大受鼓舞,本心不泯的创作热望再度重燃。他再一次重操旧业,回到了自己阔别已久的话剧舞台。
1945年,茅盾先生为在新疆动乱中劫后余生的文艺工作者量身写作了剧本《清明前后》。9月26日,该剧以“中国艺术剧社”的名义在重庆青年馆与观众正式见面。朱今明照旧担任舞台美术与照明工作,与老搭档赵丹等工作人员一起,为山城人民贡献了一出精彩卓绝的演出。据1945年11月10日重庆《周报》称,这部戏创造了年度票房的最高点,当之无愧票房之冠。演出结束后,剧场里久久回荡着热烈的掌声,给了朱今明巨大的信心。
内战爆发后,阳翰笙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上海建立电影阵地,文艺工作者分批归沪参加电影工作。朱今明离开重庆前往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昆仑影业公司,担任电影技术方面的相关工作。也就是从这时起,朱今明正式从舞台幕后走向电影幕后,得以踏上他人生中最为重要且星光璀璨的电影摄影之路。
三
虽然之前在话剧舞台上小有成就,但除了在明星公司一年多的练习生经历,朱今明并没有太多电影摄影方面的实践经验,要重新接触机器,熟悉并熟练使用,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这时,导演陈鲤庭正筹拍新作《遥远的爱》。他大胆启用新人,把朱今明介绍给当时已在电影界成绩斐然的老一辈摄影大师吴蔚云,请两人共同担纲该片的摄影工作。得到前辈的扶携与悉心指导,朱今明干劲十足,大胆无畏地开始了对陌生领域的探索,逐步掌握了摄影机和场景布光,边学习边实践,从简单的掌握技巧到创造性地运用技巧,朱今明花了很短的时间,但却投入了巨量的心血和精力。
在拍摄中,他不负众望,影片无论从影调的控制还是演员的纵深调度,光线设计、镜头运动、画面构图都十分考究,并未流露丝毫稚嫩之气,而处处显得游刃有余。吴蔚云对这位后起之秀的表现赞赏有加,随即鼓励并力荐朱今明加入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剧组。
1946年9月,由蔡楚生与郑君里编导的史诗巨片《一江春水向东流》正式开拍,朱今明首次独立肩负摄影重任。有蔡楚生导演的指导,朱今明做足了功课,对镜头、画面、光线反复思量、加工、锤炼,真正使摄影机超越了复刻现实的基本功能,深入影片主题与人物内心,镜头画面处处流露深意。他手中的老式贝尔浩摄影机虽然只有一个镜头,却饱含了朱今明对那个时代的关切,大量纪录片式镜头画面穿插进入叙事,增强了影片的历史真实感,深厚沉郁的现实主义风格应运而生。
在拍摄过程中,朱今明注意体会导演的用意,极力实现导演的每一个设想和创意。当时“昆仑”的摄影条件十分有限,三本五本从商人手里购买的过期胶片不时断档,工作时长被延滞。而朱今明并没有因为设备的局限放弃尝试。蔡楚生导演想要一个表现张忠良淫逸堕落、一个跟头跌进王丽珍皮夹的镜头。朱今明便冥思苦想,与布景师进行多方沟通与尝试,最终利用模型接景、逐格拍摄法、多次曝光的摄影技法,出色完成了导演的要求。蔡楚生对这个镜头十分满意,但出于对电影整体风格的考量,最终忍痛割爱,删掉了这组镜头,即便如此,朱今明的特技尝试现在看来仍是进步的。除此之外,朱今明还充分发挥了自己在舞台灯光处理时的能力与悟性,对光影、影调处理进行了独特的思考与设计。影片中有许多月亮的镜头,为表现人物复杂的内心活动,呈现出丰富的意境,他用特制的架子绷上纱布,又用形态各异的棉花点缀纱布,随着镜头移动,纱框随之移动。物景生意境,情景交融,丰富的意境美跃然而出。诸如此类独具匠心的摄影技术处理,在影片中比比皆是。
这部长达190分钟的电影,一经上映便轰动了整个中国影坛,作为摄影师的朱今明即刻收到了来自舆论各界的关注和褒奖,赞誉声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31岁的朱今明在电影界迅速崭露头角,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摄影新星。而这部电影,也就成为了朱今明艺术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1948年,“昆仑”影业公司转变创作思路,召集人马拍摄沈浮导演的新作《万家灯火》。作为该片的摄影师,朱今明采用了朴实无华的具有强烈生活实感的影像表达方式,在几乎不变的狭窄环境中,利用镜头创造出了丰富的内涵与意义,实现了创作者从小处着眼感悟时代隐衷的创作初衷,真实再现了战后国民党统治区的生活面貌,从百姓生活琐碎中叠加出现实意义。
朱今明在工作时总是十分投入,他不断思考如何为不同遭遇下的主人公寻找到最为贴切而巧妙的表达方式。影片中有一场戏是主人公受人诬陷遭殴打,步履踉跄地走进一个深巷。朱今明在处理这个情节段落时,将24英寸的灯打进胡同,使逼仄的空间萦生出一种冰冷孤寂的气氛,又将摄影机三脚腿架在一口锅脐着地的大铁锅里,拍出了摇摇晃晃的主观镜头,纵身大远景表现人物跌跌撞撞的背影。这样一组精彩的画面组合,恰如其分地诠释出主人公走投无路的心境状态,将人物内心难以言说的苦痛展示得淋漓尽致,堪称经典。朱今明还是一个精益求精的人,每天拍摄任务完成后,他总是迟迟不肯离开。待当日拍摄的1000多英尺胶片全部洗出来,他便拿着放大镜在一旁一一仔细检查对焦、曝光,工作态度十分严谨。正是对自己艺术水准的高标准严要求,使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像一件精致雕琢的艺术品,耐人寻味。
1949年,继《万家灯火》之后,朱今明又陆续参与拍摄了《希望在人间》《三毛流浪记》。几部影片拍摄的时间,正是1949年解放上海前最黑暗最恐怖的时刻,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垂死挣扎,特务四处虐行,许多进步人士受到迫害。《三毛流浪记》的制片人韦布在筹拍电影阶段便收到恐吓信,以死相胁不让将三毛搬上荧幕,恐怖的氛围笼罩着电影界,尤其是朱今明所在的一度拍摄进步电影的“昆仑”。朱今明十分清楚自己肩负的责任,他在工作中没有丝毫的怯懦,凭借之前作品的摄影经验,反而在拍摄中更加有的放矢。在《三毛流浪记》中,他大胆使用偷拍手段,用隐匿起来的摄影机,跟随流浪的三毛一起,拍摄到了真实的熙熙攘攘的上海街头,画面风格朴素而又生趣盎然,细节处理可圈可点,整部影片亦庄亦谐。
1949年春,解放大军百万雄师下江南,国民党全线溃退,上海即将解放。朱今明突然接到吕复同志的秘密任务:中共上海文委想利用朱今明手中的摄影机拍摄国民党撤退时的狼狈影像,记录他们的罪恶与丑行。接到任务,朱今明毫不犹豫开始了准备工作。他将摄影机放入一个自制的特殊木匣随身携带,冒着生命危险走上了街头。他还大胆地提着木匣登上自由女神像的石阶,居高临下地拍摄了外滩的混乱局面,国民党丢盔卸甲仓皇溃逃时的真实景象被永远地记录在了中国电影的历史镜头中。这些珍贵的影像在解放后被编入了纪录片《百万雄师下江南》。该片在1950年第5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获纪录片荣誉奖,朱今明也因此片被文化部授予优秀影片一等奖奖章。
四
上海解放后,朱今明在上海军管会文艺处领导下参加了电影接管工作。1949年9月,朱今明接到组织命令,参加筹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相关工作,接任制作委员会主任、技术处处长及总摄影师职务。
1950年,朱今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51年,朱今明配合从延安回来的沙蒙导演拍摄完成《上饶集中营》,随后转入《南征北战》剧组。在此之前,朱今明从未接触过战争题材影片。为更好地完成拍摄任务,他跟随导演成荫深入鲁中南地区,从山东益都步行到沂蒙山区,并随组下到连队,与战士们深入接触,实地采访。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他不断在头脑中结构整部影片的摄制方案,时时与导演切磋,虚心与剧组人员商讨,最终以高水准的镜头画面为这部战争片呈现了不同的思想与艺术气质。

拍《烈火中永生》时,导演水华与摄影师朱今明研究拍摄角度
正是在这部影片中,朱今明创造了中国电影第一代升降机。为以更加完整的视角呈现出人民解放军的英勇进攻、敌军的狼狈溃逃、军民一派欢腾庆祝胜利的精彩画面,朱今明模仿跷跷板原理,利用树墩等有限资源,由重力控制摄影机的升降变化,实现了这个难能可贵的技术创举,将多元的拍摄主体通过摄影机的运动和画面内部的场面调度巧妙组合,形成完整连贯的视觉效果,画面雄浑壮阔又丰富细腻,极富视觉冲击力。
1952年秋,文化部下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电影界马上开拍彩色电影。同年年底,上海电影制片厂开始筹拍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因为技术不过关,朱今明组织领导了试验彩色胶片的工作,经过不断研究与反复试验,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完成了“阿克发”系列彩色片的拍摄与洗印试验,促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彩色电影的诞生。
1954年9月底,朱今明受组织抽调,跟随中国电影实习团赴苏联进行学习考察。在莫斯科国立电影学院学习的日子,给他们授课的老师均是苏联著名的电影大师及电影技术方面的专家,课程包含了彩色片色彩处理及洗印技术、摄影、照明、美术、特技等等。面对如此系统的学习机会,朱今明日日沉醉其中,勤勉有加,做了许多本笔记。为了掌握宽银幕电影技巧,他还参与了《伊里亚莫洛维茨》摄制组的工作,破译了当时还很神秘的宽银幕曝光和构图规律,这些都为其以后的电影创作以及摄影教学提供了宝贵经验。
1956年1月,朱今明结束学习,满载而归,经由电影局部署决定,留任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技委会主任和总摄影师,同时也兼任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主任。当时的北影厂刚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分离出来,除了两台旧阿莱新闻摄影机,几乎没有能够用来拍摄故事片的摄影设备。为了改变简陋的摄影条件,朱今明一边紧锣密鼓加强基础建设,培养工作人员,一边做计划向上级打报告,切实依据实际情况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由他主力从英、法、美买进的大中型摄影机,成了之后北影的主要装备,拍摄出了大批高水准的故事片。朱今明一向视摄影机为珍宝,爱护有加,他教学徒了解机器构造使用方法和技巧的同时,也总是严格要求他们要像战士爱护武器一样爱护机器。
1958年到1959年间,北影厂管理体制改革,根据创作人员的特点、风格进行组合,成立了四大创作集体,朱今明被留在了第一集体。在北影工作期间,他相继拍摄了故事片《上海姑娘》《飞越天险》《风筝》,纪录片《苏联艺术大师——乌兰诺娃》等多部影片。在这些风格、题材各不相同的影片中,朱今明游刃有余地践行着自己的现实主义艺术追求,镜头语言运用愈加舒畅自如,与聂晶、钱江、高洪涛并称为“北影四大金刚”。
在1959年10月的“新片展览月”中,由朱今明担任摄影的《风暴》一片表现出众。影片开拍前夕,导演金山便向时任北影厂厂长的汪洋提出要求,点名要求与经验丰富的朱今明合作,帮自己把好摄影大关。于是朱今明从第一创作集体被借调到第二集体,他的加入,不但弥补了导演金山在艺术造型上的不足,更为影片带来了不同寻常的效应。整个拍摄过程中,朱今明为导演贡献了许多真知灼见,时常就拍摄细节与老友金山争论得面红耳赤。也正是这样自由平等的创作氛围,使朱今明有更多的空间进行艺术创新。在这部影片中,他出色完成了中国电影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造型佳句——“施洋说理”。这个长达4分01秒的长镜头足足耗用了362英尺的胶片,10个调度点,180度摇镜头场面调度,主客观镜头交替进行,完整连贯一气呵成,准确追踪演员走位,与金山在剧中的精彩表演相得益彰,创造了摄影艺术史上的又一个经典,被誉为朱今明继《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后的第二个创作高峰。
1964年,彩色电影已经成为电影界主流,而朱今明却一反常态,说服了厂长汪洋、导演水华,将北影的重点片《烈火中永生》创作成黑白片,以便更好地呈现出笼罩在黎明前黑暗中的重庆。艺术上的良苦用心,未料却成了朱今明被江青等人批斗的“祸根”。江青曾在观影成片后对影片大加苛责,提出了数条不满,其中一条不满便是“黑白片”。文化大革命期间,该片被江青一伙人以莫须有的罪状污蔑为“大毒草”,创作者们相继受到无情的政治迫害。
1966年夏,朱今明与水华导演同行,在河南兰考为新片采风,“文革”风暴如狂风骤雨突降,一道急令将朱今明揪回了北影。紧接着,朱今明被冠以“文艺黑线人物”的罪名,遭到了关押与审讯。八年的痛苦折磨,令朱今明痛不欲生,但他坚信组织总有一天会还自己清白,正是这样的信念支撑着这位革命者,终于在1973年重见光明。
此时,他已年近花甲,八年宝贵的创作生命被无情剥夺,对于一位艺术工作者来说,代价是不可估量的,然而朱今明并没有太多的时间感喟命运抱怨生活,而是潜心回归创作,争取利用有限的时间,创作出更多的艺术精品。
五
1974年春末,朱今明从干校调回北影厂,被分派到董克娜导演的《烽火少年》剧组担任摄影。历经动荡岁月,能够重新扛起机器恢复创作,朱今明满心欢喜,更十分珍惜。虽然体力已大不如从前,但在工作中,他仍兢兢业业,即使条件再艰苦,都亲自掌机,敬业精神和工作态度丝毫不输当年。只可惜,时局并不遂人意,由于“四人帮”未被清算,摄制组依然受到极“左”思想的控制,朱今明的艺术创作又受到干扰,十分力不从心。
1976年,朱今明拍摄完成影片《牛角石》,参与了反映保卫南海的影片《西沙儿女》的拍摄工作。影片因为一些政治原因,还未拍完便被告“流产”,几个月的努力付诸东流。
经历了许多不如意,朱今明开始尝试自己做导演。早在60年代初,朱今明曾想过将苏联舞蹈家古雪夫为北京舞蹈学院排练的舞剧《海峡》拍成电影,后来,他又准备将我国民间神话传说《白蛇传》改编为舞台艺术片《白娘子》,甚至写出了电影文学剧本《白娘子》初稿,且已进入编舞阶段,而这两部影片最终都因为种种原因和条件限制未能完成。唯一成片的舞台纪录片《东方歌舞》又因为政治原因在送审时受限,被搁置北影冷库,经历了政治浩劫的年代,底片早已尽失。

晚年朱今明
1977年,朱今明的导演愿望终于得以实现。为缅怀郭沫若先生逝世一周年,向国庆三十周年献礼,朱今明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演多年的优秀剧目《蔡文姬》搬上了银幕。这部舞台纪录片既保留了舞台艺术的风格,又不失电影艺术的美感,电影语言精致考究,使郭老的文本散发出别样的艺术魅力。
1981年,朱今明又筹拍了神话故事片《孔雀公主》,这是朱今明在苏联学习时期就心心念念想要拍摄的电影类型。在这部影片中,他利用神话寄托生活思考,以神话的类型外壳承载生活的真谛,内容与形式相辅相成,互为表里。该片以浪漫主义色彩和浓郁的民族风格,获得了1983年马尼拉国际电影节特别奖、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儿童片首奖“水晶蝴蝶杯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特技奖。这些奖项是对朱今明导演与摄影艺术的双重肯定,也是其多年深厚艺术积淀的最终结果。
1985年,朱今明离休,本应在家颐养天年,而他却仍然不忘电影事业。他时时追踪国内外电影界的最新动态,也悉心研究巴赞的电影理论,精读电影经典,常为自己一生所致力的中国民族化影像叙事思考新的发展路径。他甚至对许多现实题材感兴趣,还想着有生之年再创作几部佳片。然而1987年到1989年,朱今明的身体每况愈下,前后三次住院。每有同志们来看望,他总是念念不忘“电影”,他拼着力气对前来探望的同仁说:“要搞真正的艺术,要拍好片子……”真正体现着一个老电影工作者对事业的纯粹痴心与敬业热忱。
1989年6月10日,朱今明因心脏病突发仙逝,走完了他坎坷的艺术人生,享年74岁。
朱今明先生30年代参加革命文艺工作,从话剧界到电影界,从“昆仑”、“上影”到“北影”,对艺术的热爱始终如一。他曾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创新精神不可无。”在他的艺术人生中,始终保持着对艺术与技术的好奇,从不因循传统拘泥于成规,更不愿重复自己的老路。他总是孜孜以求砥砺求索,勤勉致知,厚积而薄发,不断突破时代与技术局限,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艺术奇迹。
在工作中,朱今明还十分注意提携和关怀后辈,更将自己摄影中的完整电影理念传授给年轻摄影师。他告诫后人,摄影工作不能只关注光圈、灯光、调度等分内的事,更应该关注戏本身,导演的意图、演员的表演、美工、细节等等都应该有所兼顾,要有完整的电影的观念,不单纯为技巧而技巧,而是从电影整体上去进行艺术考量与创作。
在艺术创作时,他总是能将艺术造型处理建立在充分理解文本、理解人物的基础之上,创作方法自由灵跃,风格独具,每一部作品都力求精致与完满,真正用艺术智慧践行着毕生所追求的现实主义艺术理想。无论舞台美术领域还是电影摄影领域,他都高标一格,鞠躬尽瘁,尤其在电影摄影艺术中的研究与实践,将中国电影摄影推至到新的境界和高度,为后来者开拓出了崭新的通途,为中国电影艺术和技术的发展做出了不朽贡献,他是真正的艺术的精致追求者。
责任编辑/斯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