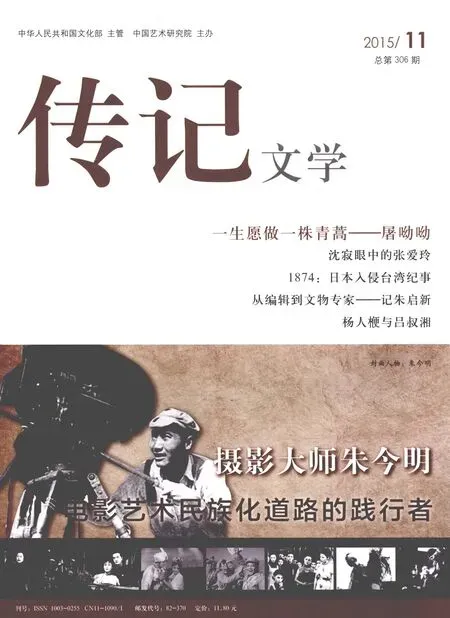“北外”1967 (五)
2015-06-01田润民
文 田润民
“北外”1967 (五)
文 田润民

外交部91人亮相保陈毅外语学院“掘墓人”隐身批谢
1968年2月13日,外交部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题为《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有91人签名,他们中大多是大使、参赞、司局级干部,其中著名的人物有刘新权、符浩。这就是“文革”中名噪一时的外交部“91人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总结了1967年4月至8月外事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指出一小撮极“左”分子借“打倒陈毅”的口号否定我国建国17年以来的外交路线,破坏和干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所制定的对外工作方针、政策,制造了一系列损害国家荣誉的事件,使我国在国际上陷于被动和孤立。大字报最后表示,欢迎陈毅同志回到外交部主持工作。
陈毅本人得知这张大字报以后喜忧参半,他说:“天下自有公道在,有人出来说公道话当然好,但弄不好这张大字报又是给我帮倒忙啊!”
果不出陈毅所料,“中央文革小组”把这张大字报定性为“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作”,并在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点了名。周恩来总理也不得不违心地批评“91人大字报”是“右倾回潮”。在大字报上签名的干部被迫作检讨,并不同程度地受到批判。直到1971年11月8日,毛主席接见我国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成员,得知符浩、陈楚就是当年“91人大字报”的签名者时,说“我还是喜欢‘91’”,才了结了这桩公案。
外交部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影响到外语学院。“91人大字报”贴出不久,外语学院贴出了一张“炮打谢富治”的大字报,大字报指控谢富治是“造反团”的后台,是外事口极“左”思潮的鼓动者和支持者。“91人大字报”批极“左”时最多点了王力和姚登山的名,而这位署名“掘墓人”的学生竟敢和权倾一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叫板。“掘墓人”的真实姓名叫冯志军,法语系一年级学生,甘肃宁县人,父亲曾是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后因作战负伤而休养,母亲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名战士,王树声大将的老部下。70年代初,他翻译了一部名为《风流女皇》的畅销书,讲的是俄国历史上有名的女皇帝叶·卡特琳娜二世的故事。冯志军北外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90年代曾任我驻布隆迪大使。这位红军后代用他那支犀利的笔揭露谢富治在“8月黑风”中的表现,大字报篇幅不长,但分量很重,贴出后,吸引了校内外很多人的关注。
外语学院贴谢富治大字报不是孤立的事件,不仅受外交部“91人大字报”的影响,还和整个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形势有关。当时,北京市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分成两大派,一派是以北京大学聂元梓为首的“天派”,另一派是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为首的“地派”。“天派”是反谢富治的,“地派”保谢富治。外语学院“红旗大队”属于“天派”,“造反团”则属于“地派”。3月18日,北京大街上出现大标语:“揪出变色龙,扫除小爬虫!”“变色龙”指的就是谢富治。3月23日,“地派”组织上街游行,高喊口号:“击退反革命右倾翻案风”,“捍卫以谢富治副总理为首的北京市革委会”,“为二月逆流翻案没有好下场”。
此时,谢富治成为一个焦点人物。
正当“天派”和“地派”为“倒谢”和“保谢”问题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3月24日,发生了“杨、余、傅”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最为离奇古怪的一桩事件。这天夜里,陈毅等几个老帅接到通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军队干部大会,他们在会场等了将近两个小时才开会。在等待期间,只见主席台上的工作人员一会儿把椅子搬上,一会儿又撤下,搬上来和撤下去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既然是军队干部大会,身为军委副主席的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却没有被安排上主席台,只坐在台下,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以及林彪的几位亲信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叶群却坐在了主席台上。文化大革命中座位和名次的安排大有讲究,此时此刻,一上一下,所透露出来的政治信号不言自明:老帅们没有发言权了,只有听讲话的份。
大会开始后,林彪首先讲话,宣布免去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的职务。在讲他们的错误时,没有提到政治路线上的问题,多是人事矛盾。说到杨成武时,林彪说杨一心想去掉那个“代”字,说他总想把和他职务级别差不多的几个将领拿掉;说余立金反对吴法宪,傅崇碧反对谢富治。江青在讲话中则杜撰了一个傅崇碧带人冲击“中央文革小组”驻地的故事,即使在当时,很多人都不相信。陈毅参加完会议后感到,在会上讲话的人谁也没有说清楚杨、余、傅到底犯了什么错误,这三个人被打倒实在莫名其妙。陈毅说的也是当时大多数人对“3·24”会议的感受。吴德在回忆“杨、余、傅”事件时说:“文化革命中没头没脑的事太多了。一些人都战战兢兢,朝不保夕,谁知道会飞来什么横祸。”吴德这番话代表了相当一批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心态。
实际上,“杨、余、傅”事件是反击“二月逆流”的继续,也是“中央文革小组”和以周恩来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斗争的继续。杨成武和傅崇碧因为在“文革”初期听总理和几个老帅的话,特别是在拿下“王、关、戚”三位干将和保护老干部中起了重要作用,因而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康生总是在关键时刻用直截了当的语言道出“中央文革小组”的真实意图,他在“3·24”大会上就恶狠狠地说:“我相信杨成武背后还有后台,还有黑后台。”3月29日,天安门出现了一条醒目的大标语:“揪出杨成武的黑后台!”接着,开始批判“多中心论”和“山头主义”,矛头直指聂荣臻元帅,因为杨成武、傅崇碧都是原晋察冀和华北军区的干部,长期在聂帅领导下征战。
纵观文化大革命的10年,每当批极“左”进入高潮的时候,突然会来一个急转弯——批右,这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个让人吃惊的突发性事件。1967年9月至1968年2月,当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批极“左”时,3月下旬突然转向,大批右倾,接着出了个“杨、余、傅”事件。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开始在各个领域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极“左”错误,全国开始第二次批极“左”,然而,不久调子变了,说林彪不是“左”而是右。1973年11月底至12月初,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判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右倾错误”,197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莫名其妙地把林彪和孔子联系起来。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再一次批判极“左”,整顿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乱局,没有过几个月就被说成是“右倾翻案”,1976年发生了“四·五天安门事件”,全国开始了“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
“杨、余、傅”事件以后,保谢富治那一派高兴,因为被抓起来的傅崇碧有一条罪状是反谢富治。消息传到北外,“造反团”腰杆子一下子硬了起来,在广播中天天批判“红旗大队”炮打谢富治、为“二月逆流”翻案。
工宣队进校形势陡变支一派打一派“红旗”受压
1968年8月下旬,《红旗》杂志刊登了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工人阶级领导各级学校的斗批改,并要永远领导学校。根据这一精神,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向外语学院派出了由北京第五建筑公司所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与此同时,海军也派出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同时进驻外语学院,领导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军、工宣传队进校,意味着由北京市直接领导外语学院,切断了外语学院和外交部的关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是谢富治,他一贯支持外语学院“造反团”。所以,宣传队进校以后,政治倾向性十分明显。
军、工宣传队进校以后,首先是造势,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名义把对毛主席的崇拜和神化推到了极致。第五建筑公司所派出的工宣队负责人姓刘,他一上台讲话,不厌其烦地先要说上一通“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然后才开讲。开会过程中,“万岁”、“打倒”的口号声要持续很长时间。每逢“最新指示”发表,都要游行,放鞭炮、开大会庆祝。海军宣传队还带头搞起了一个绣“忠”字活动,让人们用刺绣方式表达对毛主席的忠诚。有一位从基层来的海军战士上街购买刺绣用的针线,不幸遭遇车祸身亡。在造势过程中,“五建”一个工宣队员向全院师生员工做“忆苦思甜”教育:“万恶的旧社会,穷人受尽了苦!”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随着台上的血泪控诉,台下口号声此起彼伏。这个老工人年约50岁左右,络腮胡子,瘦高个,自从这次“忆苦思甜”报告会后,他经常怀揣“红宝书”,胸前戴着闪闪发光的毛主席像章,吃饭的时候跑到学生食堂要给大家念毛主席语录,还要尖声怪气地唱上一段样板戏。那样子十分滑稽可笑,但当时谁也不敢说,还得违心地说:“工人阶级对毛主席感情最深。”后来查出这个人是什么“阶级异己分子”。“文革”中,这种荒唐事比比皆是。
工宣队进校不久,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在大操场东边修建了一个绘有“毛主席去安源”的水泥纪念碑,并强迫所谓的“阶级敌人”、“牛鬼蛇神”每天在这里向毛主席请罪。这是工宣队给外语学院留下的纪念物,可惜,不知什么时候被弄掉了。
在紧接着的“斗批改”中,军、工宣传队支持“造反团”、打击“红旗大队”的态度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1968年10月,在大操场举行了一次批斗大会,将刘柯(院党委副书记)、杨淦春(法语系总支书记)等“西院”的干部和教授拉出来公开批斗,还把这些人由几个壮汉分别押着绕着大操场跑步示众。当时他们都是50多岁的人,一个个被折腾得气喘吁吁。12月初,在二饭厅大礼堂,又举行了一次“批判汪、雷反党集团”大会,支持“红旗大队”的法语系教师汪家荣、学院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雷之礼被拉出来公开批斗。雷之礼是支持“红旗大队”的院级干部中级别最高的,这个人长得又瘦又小,满头白发,平时给人一种弱者的印象,如今低头弯腰,更显得十分可怜。我和雷之礼曾有过多次接触,对他印象不错,看到所熟悉的人遭此凌辱,心里实在不爽,没有多看,便离开了会场。
在深挖所谓“红旗大队”的幕后黑手和坏人的同时,宣传队也解放、结合了几个革命干部,其中有党委政治部主任王某和英语系党总支书记蔡某,他们都是支持“造反团”的干部。
工宣队在外语学院搞的这种带倾向性的“斗批改”,在干部和教师队伍中造成一片恐慌。这个时候的恐惧和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同,那个时候是不懂事的中学生乱造反,是明显的胡作非为,人们虽然感到害怕,但心里都明白这种情况持续不了多久。而1968年的恐怖局面则是自上而下有组织、有领导的行为。工宣队这些人以大老粗自居,鄙视知识,粗暴地对待那些专家、教授,侮辱人格,动辄骂他们“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其无理和荒谬使很多知识分子感到绝望。“五建”工宣队进驻北外不久,就发生了俄语系一位老教师服“敌敌畏”自杀事件。有人统计过,文化大革命中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科学家、艺术家自杀最多的时期就是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领域后。北京大学副校长、著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就是1968年12月份自杀的,这是“文革”中最黑暗的一段时间。宋天仪同志在1968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阶级斗争日趋白热化,凶杀、自杀者颇多。据说北京大学几天内就发生5起,其中有历史学家、副校长翦伯赞夫妇。昨晚,全市戒严,街上到处是解放军巡逻,荷枪实弹,气氛森严。”
在北外最恐怖的日子到来之前,1968年12月9日,我们英语系部分同学到唐山军垦农场劳动锻炼——“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临走之前,看到政治高压下老师们忧郁的表情,没有文化的“大老粗”们颐指气使的神态,动辄用“语录”教训人,大家从心里发出一阵厌恶的感叹:“这哪里像大学的样子!”
很多老师和同学为我们在“乱世”中离校而感到庆幸,有人私下里悄悄对我说:“你们总算超脱了,等待我们的还不知道是什么命运呢?”
到唐山没有多久,就传来英语系原党总支副书记吴璞自杀的消息。
风萧萧兮寒气逼人烈女子悲愤跳运河
长达110公里的京密运河犹如一条美丽的飘带环绕着北京城,她源自密云水库,经怀柔水库、颐和园的昆明湖、玉渊潭,流经北京市5个县区(密云县、怀柔区、顺义区、昌平区、海淀区),把甘甜的淡水输送到生活在城区和郊区的千家万户。这条运河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市一项浩大而闻名的工程,是人工建成的一条保证首都北京用水的生命河。京密运河第二期工程即颐和园昆明湖至玉渊潭这一段开始于1965年冬季,有6万人义务参加了工程建设,北京外国语学院师生是其中一部分,我和我的同学也是运河建设大军中的一员。如今,这条运河不仅成为北京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水源,而且沿途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旅游景点。在享受着她给人们带来美好生活的时候,一方面我为自己曾洒下的汗水而自豪,同时不免想起一个人——吴璞,46年前,她冒着寒风,跳进冰冷的运河,结束了自己刚30出头的生命。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知道她名字的人越来越少。然而,写北外的“文革”史,吴璞是绝对绕不开的一个人物。
关于她自杀的文字记载,少之又少,我只能从她的好友章含之书中看到星星点点:“记得吴璞投河那天是个什么庆祝日。那时候凡是公布一条毛主席最新指示,就要全体出动,敲锣打鼓,游行庆祝。那天晚上,可能是又一条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我依稀记得也好像是又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总之,全校师生员工都集合起来游行庆祝。我当时被管制在学生宿舍。学生们都去游行,因而也必须带上我。我记得冬日的夜晚来得早,大约8点钟,有人急匆匆到我们队伍中叫走了几个身材高大的男学生。我看那几个红卫兵头头神色紧张,耳语了一阵就走了,只听他们说要带几根长的竹竿。我预料发生了什么大事,但怎么也不会想到那是吴璞!”(《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第20页)
经查,1968年12月27日我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2月28日晚上广播以后,群众欢呼游行。吴璞跳河自杀当是1968年12月28日!
吴璞自杀,之所以在外语学院引起那么大的轰动,首先,她确实是一个好人,同时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她的中学是著名的北师大女附中,考入北外以后不久就加入了共产党,接着担任团支部书记,还没有毕业就提前留校,担任英语系党总支副书记。那个时候担任系领导,除了政治上强以外,还必须在业务上拔尖,要不,那些专家、教授怎么会服你?吴璞无论是学生时代还是当了干部以后,都是又红又专的典型,她作风正派,为人正直,口才好,英语水平很高,在英语系教师和干部中享有很高的威信。1966年10月,在批判工作队的一次全院大会上,吴璞上台发言,她口齿伶俐,有条有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她的自杀,不仅悲壮而且悲惨!
据英语系一位老师回忆,吴璞在投河的前几天,这位老师还请她在苏州街饭馆吃饭,庆祝她的生日,席间她还偶尔露出微笑回应这位老师的问话。这位老师万万没有想到,此时此刻,她已经下了结束自己生命的决心。
据知情者回忆,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不久,吴璞被隔离审查。在被解除隔离审查的当天,她进城回家看望了年迈的父母和5岁的女儿,然后返校,但没有回到学校,而是直奔离学校不远的京密运河。她把自己的双手捆住,一头跳进了冰冷的运河里。又有人说,她是举着《毛主席语录》那本小红书跳进结着薄薄浮冰的运河,周围的农民发现时,那小红书还在她身边。第二天,军宣队、工宣队组织了一些人,押着吴璞的丈夫,在运河岸边,对着吴璞的遗体开了一个批斗会,逼迫她丈夫高喊“打倒反革命分子吴璞!”批斗完以后,用一辆卡车将吴璞拉去火化,连骨灰都没有保留!
如果说1966年运动初期出现这样的情况,人们会说那些中学红卫兵无知、狂热,被人利用。而军宣队和工宣队为什么要这样干?人死了,竟然还要面对尸体开批斗会,竟然还要逼着死者的丈夫去喊“打倒”的口号?莫非军、工宣传队也丧失了理智?有人说,比起首都其他高等院校,北外在“文革”中还算比较文明。仅就吴璞之死来看,我看不出有任何文明的迹象。
事情到了极端,就会走向反面。吴璞之死深深刺激了章含之,她又一次拿起笔来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亲自过问外语学院的运动,外语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又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吴璞自杀为什么会促使章含之向毛主席写信?原来她们俩是大学同学,后来又是同事,平素是好朋友,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是同一派组织“红旗大队”的战友。军宣队和工宣队进校后打击的重点是教师和干部队伍中的“红旗大队”成员,如英语系的章含之、吴千之、吴璞、郑刚、梅仁毅等,从1968年10月份开始,对这些人进行隔离审查达3个月之久,要他们交代所谓“二月逆流”和“里通外国”问题。军、工宣传队用逼供手段从他们身上榨取所谓的“揭发交代”。吴璞就是在遭到这种高压逼供隔离审查后自杀的。她死后,事情并没有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指责她“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面对这些大字报,章含之写道:“我直直地愣在那里,不敢相信吴璞真是自尽身亡了。我们同窗四载,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宿舍。后来又共事10年!为什么她竟会绝望到如此地步而轻生呢?我的心为吴璞哭泣,但在人们面前却不仅不能露出悲伤,还要在接踵而来的会议上被逼表态‘谴责’吴璞‘自绝于人民’。”
章含之坦承:“吴璞之死对我刺激很大,朋友们一个个落难使我内心的愤慨越来越超过了恐惧,使我难以抑制。……我意识到如果我们不站出来为我们自己挣得公道和正义、人格和尊严,我们只能被欺压、蹂躏,甚至丧失我们最起码的生存权利。”
她认为,只有毛主席说话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外语学院这种迫害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局面,于是决定再次上书毛主席,便私下和张幼云老师商量,张老师不仅赞成,而且表示愿意和她一起签名。她们在信中讲述了军宣队、工宣队在外语学院包庇极“左”势力,迫害干部、教师情况,请求毛主席派人调查外院情况。
(待续)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