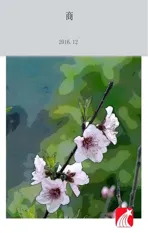精神科学的方法论疑难
2015-05-30崔志恒
崔志恒
摘 要: 伽达默尔在他的重要哲学著作《真理与方法》的开篇提到,由于归纳逻辑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运用,精神科学在19世纪西方世界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和过分依赖于经验材料的气象学一样,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精神科学一直以来也因其不精确性,而显得极为特殊。十九世纪的人们,在德国以赫尔曼·赫尔姆霍茨和狄尔泰为代表,极力想维护精神科学的独立性,让精神科学成为一门独立于自然科学的科学群。但由于他们深受自然科学模式方法论的影响,这种努力并未能取得实质性的效果。伽达默尔指出,如果我们只是以这样一种对于规律性不断深化的认识为标准去衡量精神科学,那么我们就不能正确的把握精神科学的本质。社会—历史认识的理想应是,在现象的一次性和历史性的具体关系中去理解现象本身。
关键词: 精神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论;归纳逻辑;自然科学模式;历史学派;教化
1.归纳逻辑运用于精神科学
精神科学,国内一般称为哲学社会科学,在19世纪的西方世界得到了实际的发展,在德国,精神科学的兴起,精神科学这一概念的流行主要通过约翰·斯图加特·穆勒《逻辑学》的德文翻译者。约翰·斯图加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是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继承者。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在理论上首先由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提出,经由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1685-1753),最终在大卫·休谟那里逐渐成熟。他的著作《人性论》的导论对此做了最为卓越的表述。《逻辑学》是穆勒的主要哲学著作之一,在这本著作中他表明,作为一切经验科学基础的归纳方法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有效,在精神科学领域也应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在这本书的附录中,穆勒补充性地概述了归纳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可能性。
这里所提及的归纳方法,根植于经验材料。从经验材料中提取规律性,运用于具体的现象。穆勒认为,社会科学的基础也在于认识的齐一性,规则性和规律性,正是这种规则性和规律性使得预测个别的现象和过程成为可能。在这里对归纳法的使用,对于普遍性规则的强调,是摆脱了一切形而上学假设的,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虑具体的社会现象是怎样来的,具体的人又是怎样看待,不用去寻求某种特定结果的具体原因,而是简单的确立规则性和相关性,然后凭借规则性和相关性去推断所期待的现象。至于我们是否相信精神科学领域下存在内在的意志自由,这完全无关紧要。自由意志的加入并不破坏合规则的过程。这就是我们关于社会的自然科学理想。在过去的19世纪这种精神科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社会心理学便是这一理想的典范。
2.自然科学模式完全支配了精神科学的自我理解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既使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内,由于用以归纳规律性的材料并不是完全都能被充分得到,所以通过规则性的认识去预测个别现象的目的也无法到处以同样的程度得以实现。比如气象学,尽管气象学所使用的方法完全类似于物理学,但是由于它的材料不充分,它的预报也就更为靠不住。这一点完全适用于社会现象。这里存在的问题虽然抵制了自然科学模式,但以归纳逻辑和普遍规律为特征的自然科学模式仍完全支配了精神科学对自身内在逻辑的自我理解。
(1)非精确科学和赫尔曼赫尔姆霍茨
十九世纪精确科学的代表人物,德国自然科学家赫尔曼·赫尔姆霍茨(Hermann Helmholtz,1821-1894)觉察到了精神科学的独特性。但他也只是站在自然科学精确要求的角度,把精神科学称为“非精确科学”。他区分了两种归纳法:逻辑的归纳法和艺术——本能的归纳法。他指出,逻辑的归纳方法是一种对自觉铁定的程序的遵从,除了自然科学研究者的归纳能力运用以外,并不存在其他要素,相反,精神科学的艺术——本能的归纳法是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家的自觉地逻辑归纳的,它是一种无意识的推断,与独特的心理条件联在一起,它要求一种机敏和其他精神能力。他本想反对那种由自然科学的归纳方法出发,去制定一套普遍有效准则的企图,但很显然,除了归纳方法以外,他并未能掌握其他描述精神科学程序的方法。对于赫尔曼·赫尔姆霍茨来说,归纳逻辑仍是科学方法的典范,正如他援引穆勒的这句话所表现的那样:“最新的归纳科学对逻辑方法的进展所做出的贡献比所有专业哲学家还要来得多。“当然,他后来觉察到了历史认识归纳方法的特殊性,并且试图说明为什么精神科学的归纳方法不同于自然科学,在此他使用了作为康德哲学基础的自由和自然的区分,这样在精神科学领域就不存在自然法则,而只存在对实践法则的自由依循,对律令的自由依据。这种说法并不具有本质的说服力。经验主义的精神科学和经验主义的气象学一样,因其飘忽不定的不精确而仍遭到科学的摒弃。可以这样说,十八世纪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新科学的范例,被赫尔曼赫尔姆霍茨视为是卓有成效和理所当然的。对于他来说,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理想既不需要历史学的推导,也不需要认识论上的限制。而实际上,新科学在17世纪的产生是根植于相应的哲学——历史条件的。法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哲学家,著名的科学理论约定说的代表人物,P.杜恒(Pierre Duhem,1861-1916)的著作《莱奥纳多·达芬·奇研究》清楚地表明巴黎的奥卡姆学派曾对新科学的产生有重大影响。
(2)历史学派和狄尔泰
赫尔曼赫尔姆霍茨并没有注意到,早在1843年,德国语言学家,古希腊文化史的研究者J.G德罗伊森(Wilhelm Scherer,1841-1886)就曾写道:没有任何一个科学领域,会像历史学那样无意于理论上的证明,限定和划界。”他还卓越的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被更深刻把握的历史概念应成为中心,在这样的概念中,精神科学动乱不定的根基将得到稳固并且有继续发展的可能性。”德罗伊森在此提出的科学模式,似乎为我们提供了非归纳逻辑的另外一种描述精神科学逻辑的方法。他要求精神科学自身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群被建立起来。他的《历史学》就致力于此。
德国的另一位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狄尔泰,虽深受自然科学方法和英国经验主义的影响,但他却继承了历史学派的观点,保留了精神科学概念中思辨—唯心的要素。他深刻理解了是什么使得历史学派区别于一切自然科学的思维。他写道:“只有从德国才能产生那种可取代充满偏见的独断的经验主义的真正的经验方法。穆勒就是由于缺乏历史的教养而成为独断论的。”显然,狄尔泰想反抗穆勒在其《逻辑学》中所主张的归纳逻辑对精神科学的试用,并为精神科学方法的独立性进行辩护。实际上,狄尔泰几十年的艰辛工作正是为了此。但是,由于深受自然科学模式影响的缘故,他的努力也并未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效。有两个证据可以说明这一点。其一是,狄尔泰在评价德罗伊森时,曾经流露出这样的一种关于历史认识的观点,他认为,消除一种与生命的联系,获得一种与自身的距离乃是科学认识的基础,是历史能成为对象的条件。这种认识深受康德按照自然科学模式而规定的科学和认识概念的影响。第二点则显得更为明显。狄尔泰通过对精神科学对象的考察卓越地把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区分开来,实现了精神科学的独立性。但在他对精神科学方法的独立性进行说明是,却引用了古老的培根派的话:“只有服从自然法则,才能征服自然。”又完全认可了普遍性法则的效力。这完全倒退回了赫尔姆霍茨素朴断定之后。现代科学的方法,普遍性的法则仍是到处同一,并且自然科学仍是其中的典范,精神科学并未获得自己特有的方法,虽然狄尔泰极力的想维护精神科学的独立性。
3.伽达默尔的评语
伽达默尔认为,如果我们只是以这样一种对于规律性不断深化的认识为标准去衡量精神科学,那么我们就不能正确的把握精神科学的本质。即使社会—历史的世界经验包含普遍经验在个别对象的实现,历史认识也不应力求把具体现象看成某个普遍规律的实际例证。历史认识的理想其实是,在现象的一次性和历史性的具体关系中去理解现象本身。具体的去理解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现在是怎样的,是如何成为今天这样的,而不是去研究人类,民族,国家一般是怎样的,虽然在这其中可能有很多普遍性的经验在起作用。
理解某物是这样而来的,从而理解了某物是这样的。对于十九世纪的人们来说,虽已承认这样的一种认识理想与自然科学的方式和目的根本不同,但是由于他们深受自然科学模式的影响,因而只能站立在自然科学传统中以一种的否定的方式为之辩护。
伽达默尔指出,他们跟随康德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所规定得科学和认识的概念,并且在艺术的要素中找寻精神科学与众不同的特殊性,所给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充分的。当赫尔姆霍茨否定自然科学研究中有类似于灵感这样的心理因素,而只把其视为”自觉推理的铁定程序“时,这种自然科学的图景也是相当片面的。实际上,精神科学根本不会认为自己从属于自然科学,相反,在对德国古典文学精神遗产的继承中,更多的是要发展成为人文主义传统的真正继承者,根植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下的更本质的东西。我们在赫尔德身上看到了这一点。他以“达到人性的教育”这一新的理想超越了启蒙运动至善论的理想并因而为精神科学在十九世纪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当时精神科学的自我理解完全受到自然科学模式的支配,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在十八世纪占据主导的“教化”概念,确实奠定了十九世纪精神科学赖以存在的基础。因此,伽达默尔认为,如果我们想正确的理解和把握精神科学的本质,我们就要超越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框架而进入到历史性的教化的观念中去。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参考文献:
[1] H.G.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3。
[2] H.G.伽达默尔:《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3。
[3] S.E.斯通普夫,J.菲泽:《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修订第八版)[M],匡宏,邓晓芒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红狼出版。
[4] H.G.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5] 何卫平:《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 伽达默尔哲学思想研究》[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
[6] Hans-Georg Gadamer:truth and method[M],translation by Joel Weinsheimer and donald.G.Marshall ,second,revised edition,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