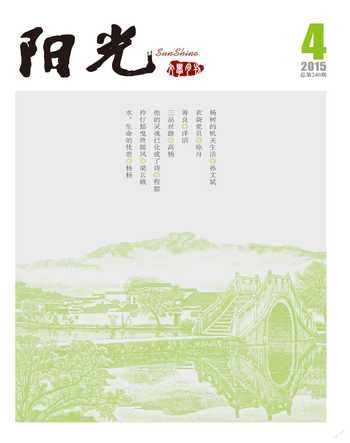水,生命的忧患
2015-05-30杨杨
杨杨
水是地球的血脉,也是生命延续的依赖。
假若没有水源,注定会荒芜一片。
——作者手记
在河北省西北部,在坝上高原,特别是张北、沽源、康保、尚义四县,近年来,随着错季蔬菜大面积种植,地下水资源严重匮乏,并且逐年下降,浪费更是异常的惊人!
据了解,每年种植蔬菜从育苗到成熟,需要水灌溉至少三至六个月,每亩需要抽取水源覆盖厚度至少一米多。
10亩,就是一潭池,100亩就是一汪湖,1000亩就是一片海!
据保守数字,张北种植蔬菜至少38万亩,沽源种植至少45万亩,康保至少22万亩,尚义至少16万亩。加起来就是221万亩。相当于900多个西湖的面积。何况,坝上蔬菜种植从1992年开始,至今20多年,形成的规模可想而知。一年用掉900多个西湖,20年,就是18000个西湖在消失。而这些水源的供给几乎全都是地下水。有效的降雨或蓄水灌溉几乎为零。
依然是保守数字,张北蔬菜种植现有机井4900多眼,沽源5400多眼,康保3900多眼,尚义2600多眼。加起来就是16800多眼,将近两万眼机井遍布221万亩的蔬菜地里,平均每亩有70多眼机井,犹如蜂窝一般。而且,全都是150多米的深水井。这样的数字还在逐年递增。每年至少增加3000多眼。似乎不需要任何审批手续,想怎么钻就怎么钻。一年四季,钻井队总是奔波忙碌着。一天24小时,源源不断的地下水资源被无情地抽取,形成了滴灌、喷灌、大漫灌……
于是,就有无数的人感叹:坝上的蔬菜,其实就是水!
海拔1600多米的坝上高原原本就缺水,十年九旱。祖祖辈辈困扰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祈求着雨露甘霖,渴望着五谷丰登。然而,每年能够得到的降雨仅有300多毫米。现在,不足30毫米。大致为夏秋两季,也就三五场雨水而已。实在是少得可怜!
当地有谚语:“春雨贵如油,夏雨卡脖旱,秋雨转眼干。”可见雨水的稀少,水源的紧缺!
很显然,靠天吃饭,似乎没有多少指望了,种植蔬菜,远比粮食作物紧俏,尤其赶上旺季,一棵西芹三五元,一斤甘蓝八九毛,一个萝卜两三块,实在是诱人!
于是,大家都来种。种来种去,不能缺了水。即便是蔬菜上市的那一天,即便是装车的那一刻,一条条的皮管子就像老龙吐水似的喷在了蔬菜上,冲着、洗着,为的就是鲜嫩,为的就是水灵,为的就是卖个高价。
于是,沟里淌的是水,路面淌的是水,地里淌的是水……
为了蔬菜种植,为了眼前的利益,那些菜农、菜商、菜贩们,再也顾不了什么生态平衡,科学管控,更来不及考虑子孙后代的生存。终极目的就是赚钱,哪怕把地下的水源全都抽干,也要恣意赌拼。赌好了,一亩地收入五六千元甚至上万元。50亩就是五六十万元,100亩,辛苦三五个月,就是普通工薪阶层一辈子的收入。
而种植的各种蔬菜,更是被甲胺磷、锌硫磷、氯化钡、1605、氟化乐果等等的剧毒农药喷洒着,即便是生命力顽强的蚯蚓、蚜虫、蚧壳虫、潜叶虫、红蜘蛛以及蚊虫等等也休想生存。所谓的“绿色蔬菜”,只不过是一个憧憬中的概念。人类的各种疾病或癌症等等,就是最好的见证。
那些原本肥沃的土地,硬是被井水和农药浇成了一块块的“铁板”,多少年以后,都将无法耕耘。留给子孙的只能是无望的苍白和永远的伤痛了。
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坝上注定将会失去水源,移民迁徙。甚至还有专家推断,近20年时间,坝上12480平方公里的面积将整体下陷,导致地壳结构严重裂变。未来很有可能发生翻江倒海的地震。绝不是危言耸听!
尤其是21世纪初,首都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水土保持项目的实施,就在坝上。
坝上是京津冀风沙水土流失治理的源头,是首都北京的屏障。
生态一旦失衡,几百年甚至几千年都难以恢复。生存环境将会受到严重威胁。自然灾害将会频发。诸如沙尘、雾霾、干旱、洪涝,甚至地震、瘟疫、疾病等等,造成的后果无法想象。什么天蓝、地绿、水净等等都将化为梦幻和泡影。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在党的十八大放在了突出的地位,融入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的全过程,而且成为了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奋斗目标!
如今,一望无垠的草原在荒芜,数以百计的河流在干涸。
曾经烟波浩渺的安固里淖,仿佛一夜间剩下了白茫茫的盐碱,随着风沙的弥漫在抽泣;曾经,华北最大的察汗淖尔,魔幻似的龟裂成了泥巴,裹着腐烂的鱼虾在烈日下散发着悲怆;曾经神话般的月牙湖,几乎成为了臆想中的描摹,再也没有了诗意的壮美与雄奇;曾经蜿蜒的鸳鸯河,竟然等不来一场山洪,更没有了戏水的野鸭;曾经涟漪荡漾的太子湖,不见了鸥鹭的飞翔,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而被遗忘成了苦涩的忧伤;曾经轱辘车演绎的康巴淖尔,已经觅不到了昔日的浪涛,竟然划不动一叶小船;曾经美丽的天鹅湖,只留下光秃秃的山丘,环抱着一段久远的故事,再也不见了渔歌唱晚的桨橹;曾经的滦水源头,汹涌的闪电河,远远地望去,没有了鸟儿的栖息,也不见了摆渡的艄公,更没有了文人笔下的一泄千里……
如今的坝上高原,尽管拥有了湿地保护措施,充其量也就是沙漠里渴望绿洲,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即便投入上亿元的经费,也休想砸出一个响亮的水泡。
坝上的水源,至少经过了千万年的涵养和沉淀。如今,短短的几年时间,水源下降得令人瞠目结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挖一口三五米的地窖,就会有水不断渗出。七八米深的一口水井,足够几代人饮用。眼下,一钻头下去,30米不见水,50米依然干枯,80米找不到湿润,120米出水,不够养殖大户一群牛羊的饮用。150米下去,基本维持现状……
这就是现实!
最早种植错季蔬菜,是从一个叫大营盘的乡镇开始,然后,辐射到了周边区县,包括张北、沽源、康保、尚义、万全、宣化、阳原以及内蒙古商都、兴和、化德、多伦等地。其规模逐年扩大,看似生机盎然,一片葱茏,生机背后却是连年的水荒。
坝头村曾是一个不足30户的地方,人畜饮水从不犯愁,常年溪水潺潺,随意用石头围一处水源,便可以用桶提了,挑回家里,清冽得犹如醇酿的美酒。品一口醉人,喝一杯豪放。牧归的牛羊撒欢的饮用。
如今,因为失去了水源,自然也就失去了家园。所有的村民全部被迫搬迁了,留下的只有那光秃秃的山丘和枯草以及低矮的茅舍。那一扇扇的门窗在夜幕中黑漆漆的、再也不见了灯光,听不到看家犬汪汪的叫声,听不到了骡马的响鼻,更听不到了主人家的鼾声或梦呓的嘟囔……
更多的时候,是那呜咽的风雪肆虐着,越加的凄冷而悲凉了。即便是乌鸦或山雀,甚至野兔子、老鼠也很少光顾这里了。
有个叫靠山村的地方,因为缺水,一口老井日夜围着村民,将一只只水桶吊上又送下,叮叮当当地撞击着井壁。能够提上的也就是半碗黄泥汤汤。更多的时候,盛到一只桶里,提回家,澄着、滤着,一不小心被圈里的羊儿嗅到了,咩咩地叫着,硬是挤破了栅栏,冲进屋子,将头伸到桶里,拼命地饮着……
这时,老牛也冲出了圈舍,哞哞地叫着,焦渴地拱着头颅……
看着这样的场景,主人只是无奈地哀叹着,双手抱头,蹲在了地上,哽咽着祈祷:这日子可怎么过呀,老天爷啊,睁睁眼吧……
后来,听说20里以外的坝下山区有一股清泉。于是,天还不亮人们就像赶集似的套着牛车或驴车,拉着水桶或水箱,一路颠簸着,七拐八绕,赶往了取水的地方。
20里的山路,赶到时,几乎已是正午了。远远地望去,长长的队列足有二里地。人们坐在车上或蹲在地头,眼巴巴地等待着……
等到一只只水桶或水箱装满了,疲惫的太阳也快落山了。看着老牛或驴子将头扎在溪水里,拼命地吸饮着,直到肚子快要胀爆,依旧不肯离去。主人的眼里湿润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在水泉梁,因为缺水,婚丧嫁娶的日子里,送去的最好礼物,就是那一盆盆或一桶桶的清水。主人见了,满心欢喜,只说:实在是感谢祖宗八辈哩。忙不迭地接了那清水,倒在水缸里。新娘出嫁,能够用清水洗一次温水澡,简直成了一生的向往。而那弥留人世的老人能在最后一刻,擦一把身子,洗一把脸,喝一口甘泉,已经是一辈子的安慰了。直到撒手人寰,依然嗫嚅着:没水的日子难啊,一定要节省啊……
“哎哎”儿孙们不住地应着,使劲地点点头,早已哭成了泪人儿。
在一个叫妈奶沟的村子里,原本有一股山泉,后来,引入了农家。最初,拧开水龙头,哗哗的泉水欢唱着,伴着乡亲们的笑声,随着那丰年的喜庆,有说不出的快乐。
之后,村子里种上了蔬菜,打了机井。泉水渐渐地少了、枯了。水龙头整天开着,嘀嗒嘀嗒,硬是淌不出一条细细的水线。没有三五个小时,休想接满一桶水。连洗锅刷碗都困难。按理说,有了机井,吃水应该不成问题了。可是,偏就指望不上。“哗哗”的地下水被菜商们浇了菜。喷灌、滴灌、大满灌……
这到底是为啥啊?人们在找寻着谜一样的答案。
在二洞沟,虽然一棵蔬菜也没种,却旱得要死。究其原因,那就是周边的机井早已把地下水抽干了。
于是,科学就解释,生态失衡了,要应对气候变化了等等。
仔细想想,确实是这个理儿。人为因素太关键了,或者说,人为破坏太严重了。自食其果啊!
村里的姑娘媳妇要洗衣服、被褥,只能等到下雨天,用盆盆罐罐接了那雨水,存到地窖里,用的时候取出来,一遍一遍地洗过。然后,澄着、滤着,依旧存放着。等到年关时,家里要杀猪宰羊了,就把存下的雨水烧开了,一勺一勺地浇在猪身上,用那巴巴石蹭了,将猪毛一点点地褪去。即便是褪猪毛剩下的脏水也舍不得浪费,继续存在地窖里,用来和泥、抹墙、修炕、砌烟囱等等,直到点滴不剩。
在后海子,村前原本是一片沼泽,一处淖水,一块草滩。不知何时,被承包商种上了成百上千亩的向日葵,不到一周的时间,淖枯了,滩荒了,藓一样地裸露着一片又一片的盐碱。昔日的山丹丹、马兰花、狗舌叶、芷棘草、河篦梳、车前子、蒲公英、扁株株等等全部消失了。即便是聒噪的青蛙以及各种水鸟也不知落到哪里。吃草的牛羊也没了去处,只能圈养着。牛倌羊倌竟然失业了。望着远天的愁云,随着野野的朔风吹过,越加的惆怅了。
得不到放牧的牛羊很快就出现了布鲁氏病菌、口蹄疫等等。这才意识到,千百年来,放牧归田,天经地义。不仅肉质鲜嫩,而且水肥草美。即便是那粒粒的羊粪蛋蛋或片片牛粪,散发出的都是旷野的温馨,天然的肥料。特别是雨水冲刷后,有益于生态,更有益于植被。
地表干燥,井水枯竭,形成的只能是恶性循环, 生态失衡,即便是野鸡山雀,猪獾狐狸之类都将无法生存。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早在1200多年前,伟大的诗人白居易就曾写下了千古绝句,生动地诠释了自然的美妙与和谐。
“哗哗”的地下水,日夜不停地抽取着,转眼间,老井一眼眼地干枯了。伏在井口,投一粒小石子,再也砸不出一波水纹。唤一声,也听不到那种激荡的回声。顿时,人们傻了、急了,只好提着水桶满世界去找水。
“谁接水,谁缴费。”村长把任务交给了纪达。
纪达是个热心人,也是个老实人。七十多岁了,办事可靠。
那天,纪达要给村委会收水费了。于是,就走进了张老太家。纪达说:“还差五毛钱水费哩。”张老太说:没钱哩。纪达说:没钱干嘛抽人家的水呀?张老太说:从古至今,没见过吃水还收费的。
两个老人争吵起来了。随后,竟然撕扯起来。老胳膊老腿,经不得摔打了。“噗通”一下,纪达倒在了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浑身剧烈地疼痛着,送到医院后,经过检查,一根肋骨断裂了。输液、住院、吃药、陪床等等,5000块钱栽进去了。
回到家里,躺在炕上,纪达拭一把老泪,思来想去,心里憋屈着,只因缺水,只因五毛钱的水费,遭受了如此大的伤痛。好端端的日子,咋成了这样啊!
那时候,家里的水缸空荡荡地敞着,缸底有一只潮虫在饥渴地蠕动着,好像在拼命地唤着……水……水……咋没水啊!
小淖台,顾名思义,就是湖泊,就是有水的地方。从东到西,一字排开,足有上百户人家。如今,常住人口也就二三十户了。淖枯了,水也没了。年轻一些的,大多离开了村子外出打工了。一些闲散的土地干脆承包给了菜商、菜贩、菜农。不计后果地经营着。于是,一眼眼的机井钻下去,直钻得人心发慌。淖台上的老井就枯了、废了。人畜饮水一下成了主要的话题。
那天夜里,老牛伯伯对小马叔叔说:这样下去,井里没水了,日子咋过呀?小马叔叔说:机井那么多,咋就没水嘛。没水人家干嘛打井呀?老牛伯伯听着听着就困惑了。于是,找到了杨爷爷去理论。杨爷爷想了大半天,捋一把雪白的胡子说:一辈子没有经历过哪!实在是不明白呀。后来,就找到了朱哥去探讨。朱哥想了想,忽然饥渴得有些困倦了,闭了眼,竟然呼呼地睡去。“真是一睡解千愁啊!”吕婶和罗嫂哀叹着,只说:“这地方实在没法待下去了。”说完,忧郁地离开了。吕婶和罗嫂很早就成了寡妇。现在,可能要改嫁了,发誓要嫁到有水的村子或城镇……
第二天,俊妞家就出乱子了。或许是女儿贪玩,或许是该着出事儿,一不小心,竟然将借来的一盆水碰翻了,洒了。俊妞一急,就在女儿的脸上拍了一下。“没水咋做饭呀!”不承想,女儿不经拍,一下就倒在了角落里,再也没有爬起来。俊妞顿时傻了。将女儿一下抱在了怀里,哭着喊着,一口气没有缓上来,转眼间,母女俩就走了。走得那么匆忙。翌日,外出打工的丈夫回来了,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呆了。然后,发疯似的悲嚎着,冲出了屋子,冲向了老井,一头栽了下去……
村人发现后,救了上来,只见鲜血淋漓着,一条腿粉碎性骨折了。
“不该救我呀!就是死,也要死在井里,做鬼也不能缺了水啊……”
人们全都落泪了,哽咽了,唏嘘着:这是甚日子啊!
在北大滩那一带,好多个乡镇因为缺水,一个又一个男女走出去,肤色都是灰呛呛的,粗糙得看不出一点儿细腻或白净。30岁的年龄就像60岁的样子。牙齿几乎都是铁锈铁锈的。原本俊秀的姑娘常常因为一嘴锈色的黄牙找不到婆家。原因就是水质变异了。涩涩的,越喝越渴。外乡人喝了就闹肚子,拉痢疾。后来听说,有的婴幼儿竟然患上了软骨病或智障。结论就是水质变异造成的。实在是令人忧虑啊!
因为缺水,很多人不再刷牙漱口了,口臭难闻。好像啥都不在意了。一年四季,干旱着,那弥漫的风沙伴着白色的盐碱,抽打在脸上、身上,就像刀割似的生疼。偶尔等到一场濛濛细雨,只好把盆盆罐罐全都摆放在院子里或屋檐下。一边接着雨水,一边跪倒在地上,任凭雨水淋个透湿,全当是洗发、洗澡、洗衣服。然后,将湿漉漉的衣服扒下来,拧干了,晾晒着,随后,用手在身上一遍一遍地搓着,将那酸酸的汗碱或脏污一卷卷地搓下来,纷纷坠落着……
雨过天晴,再到地里看看庄稼苗苗,依旧是稀稀拉拉的样子,就像谢了顶的毛发,勉强生长着。有时,遇上六月雪,陡然一场降温,一夜之间,庄稼全都冻死了。乡亲们哀叹着,眼含泪水,霜打似的回到家里,倒在土炕上,只是闷闷的抽着那浓烈的旱烟,再也想不出丝毫的办法了。
“老天爷不让人活哩。”
“怨不得老天爷。都是人造的孽啊!地下水都抽干了,能不旱吗?生态破坏了,气候反常了……报应啊,报应啊……”
“庄稼没了苗。那可咋办呀?”
“能咋办呀?花钱买种子嘛。”
于是,依旧是播种,依旧是期待。十天半月,埋在土里的种子硬是拱不破土层。心急的乡亲们只好将那干裂的土层刨开,只见那种子静静地躺着,干瘪瘪的,放在嘴里咬一口,就像石子似的硌牙……
一年的收成没有了指望。村民们只好外出打工了。都说,下煤窑挣钱哩。那就到煤窑上找活吧……
后来,就有噩耗接二连三地传来了。矿难发生的时候,下到煤窑的村民再也没有回到村子……
曾经上千人如今只剩下不足百人的村庄比比皆是。人口逐年锐减。乡亲们感叹:村里的人全都哪儿去了?哦,全都进城了。城市也在缺水啊!
是啊,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一旦缺水,危机四伏。
在坝上高原,尤其是农村,因为缺水,能出去的全都走了,只剩下了所谓的“九九三八六一”部队(老年妇女儿童)。凑来凑去,也凑不成一个加强排。再看村舍,越加的消沉而漫散了。更多的房子还没来得及住人,门窗就被土坯子严严实实地封上了。即便村委会选举,能够联系上的村民也是寥寥无几。接到通知也没几个能够赶回来的。真要回来,首先扛着一桶纯净水。不然,没法生火做饭。
现实就是这样的残酷。一眼眼的机井钻下去,到底是水多了,还是缺水了?
生活在坝上的乡亲们越来越困惑、茫然……
杨 杨:河北尚义人。著有小说、评论、散文、报告文学、诗歌等300余万字,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等文字。曾在《人民日报》《收获》《中国作家》《北京文学》《新华文摘》《中国报告文学》《大家》《作家》《中华名家》《百花园》《鸭绿江》《阳光》《散文百家》《北方作家》等刊物发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