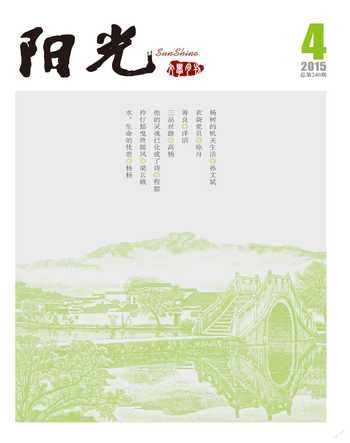忆茅屋为狂风所破
2015-05-30刘元树
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
高者挂罥长林梢,
下者飘转沉塘坳。
…… ……
这沉郁悲凉的诗篇,唤起我多么清晰的记忆:那年秋天的傍晚,我们正在田间锄草,突然天空乌云滚翻,远处雷声隐隐,大风渐起,眼看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大伙儿一起往家奔。我一开门,便被狂风推进屋内,足跟尚未站稳,忽然听见“轰”的一声巨响,“屋上三重茅”被卷上天空,天窗打开了。平时黑黝黝的屋子陡然光亮起来。我借助闪电的光亮,看见冲天的茅草越飞越多,越飞越高。“轰隆隆”,一声炸雷,吓得孩子们惊慌失措,我连忙伸开双臂紧紧地把他们揽在胸前,不让吹落的泥块、竹片砸伤他们。炸雷响过,骤雨倾盆泻下,刹那间屋内一片汪洋……
我能够亲历世人难见的这一既惊涛骇浪般壮观又天崩地裂般恐怖的场面,能够较为深刻地体会“诗圣”杜甫当年处境艰难时的博爱胸怀,还得从下放农村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谈起。
一九六九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斗、批、改”阶段。合肥师范学院(地点在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本部,而非今回龙桥的合肥师院)“斗、批”之后被撤销,大部分系科与芜湖皖南大学合并,最后更名为安徽师范大学。我执教的中文系大部分教师并入安徽师大,少数人调往他校或下放农村。我属于下放中的全家落户者。这便是我有过三间茅屋的原因,也为狂风破茅屋提供了可能性。
对于今天的中年朋友们来说,全家落户农村的准备工作也许是复杂、繁重的。而对于当年的我来说,却简单、轻松。住房和家具由所在单位配给,离校时退还便是。衣被用物就那么一点儿,几口箱子便装完了。唯有那七八百本书籍杂志,弃之心疼,带走沉重,送人无人欢迎,使我颇费踌躇。最后心一横,当废纸卖掉,每斤七分钱。
书籍杂志卖掉后没几天,一辆卡车就载着我们老小五口和包括水缸、煤球、生火的劈柴在内的全部家当到安徽省肥东县梁园公社镇东大队安家落户去了。
镇东大队在梁园镇之东两公里的梁(园)古(城)公路两侧。当年岱山湖风景区尚未开发,梁古路相当冷清。我们的卡车还未停稳,一群孩子便跑来看新奇。送行的工宣队师傅下车联系后,社员们便前来搬东西。一会儿,我们的家当全都放在高坡上的茅屋门前。到这时,我才知道,我们的“家”就“安”在这儿。
我把茅屋仔细打量了一番。坐北向南,一连三间,但未分隔。模样还周正,只是衰弱些。开门便闻到异味,入内便踏着垃圾。我们的第一件事便是清扫房子并把三间分隔开来。分隔很容易,墙壁钉上钉,用塑料布一拉就成了。清扫却很要费些力气。好在我当时还不到四十,精力正旺,铲铲挑挑,全包下来,洗洗擦擦,由老小承担。全家动手,各尽所能,大半天的工夫,便收拾停当,把家安顿了下来。
环顾四野,却心绪茫然。说不上高兴也说不上忧愁。但再听不见我听够了的“官僚腔”,再看不见我看够了的“革命脸”,实在是大快人心的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茅屋周围的社员们逐渐了解并融洽起来。
一墙之隔的邻居是一位放牛老汉,年纪不到六十。烧饭时的炊烟透过墙壁的裂缝往我们这边冒,我们刚闻到饭香,一会儿他已端着冒尖的一大碗饭蹲在我们门口边吃边拉呱了。我们递给他一条“板板”(当地人对“板凳”的称呼),他不坐,说“蹲着吃饭舒服”。
茅屋门外是一条小道,小道下面是一片农田。社员们干活歇晌的时候,常来我们家讨水喝。我们备些红汞、喹啉、黄连素等常用药品,他们也常来取用。而逢年过节,他们总是把刚炸好的油香、山芋元宵,一大碗一大碗地端进茅屋来,送进口里还有些烫嘴。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茅屋的了解也逐步加深。
茅屋原是“大跃进”中“跃”出来的大队指挥部。失宠后,生产队作为养鸭房。茅屋才十来岁,应该说很年轻。但因缺吃少穿,缺医少药,现在已成为头毛脱落、腰弯背驼的老汉了。冬天,北风从墙缝吹进来,把茅屋吹成一个冷藏库。夏天,酷暑难耐,屋子窗户少而小,且全在南墙,空气不对流,茅屋又成了一个大蒸笼。
这都不难对付。刚听到冬天的脚步声,我们就用牛皮纸裁成小条子,像旧时北方农村那样,把墙壁上的缝隙贴得严严实实。春天一远行,我们就把贴上去的小条子撕下来,还在北墙上凿两个大洞,即便盛夏只吹来一丝丝风,屋内也会感到凉爽。
最难对付的是屋漏。只要雨稍大一点儿,茅屋就要哭泣,满屋都是泪水,锅盆碗盏一起上也不管用,床更没处挪,人也没处躲。茅屋未老先衰,看来没法庇护我们了。
下放农村落户是有建房经费和木材票(由政府部门组织供应的平价购买木材的票)的。我们盼呀盼呀,问了多次,都说省里没有拨下来。仅隔两天,我去公社办事,没想到,会计突然把建房经费和木材票交给了我。这一“突然”,真似喜从天降,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
回村后,我把钱和票如数交给生产队长,并传达公社指示:“责成生产队负责新建。”过了一段时间,我在田间劳动时,队长指着一堆土坯对我说:“这是给你们盖房准备的,等晒干后就可动工了。”我对这堆土坯一下子亲切起来,渴望连出几个大太阳,把土坯晒得干干的,使我们早日摆脱风吹雨淋之苦。
某一天,队长一发话,几十个男劳力一齐上,早晨拉屋,上午动工,天擦黑时一堆人爬上屋顶铺草,新屋便落成了。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喜悦,以为从此可以安居乐业了。
喜悦的心情伴我入梦乡,也催我早早起床欣赏我们的新屋。一看,傻眼了:新屋原来如此粗陋。
南墙墙面歪歪扭扭,北墙墙身明显向外倾斜。整个墙壁坑坑洼洼,如机枪射击的弹痕。所幸山墙笔直挺拔,尚能承受横梁乃至屋顶的重压。“歪扭”“坑洼”可以不予理睬,只要不倒、不透风就行。“向外倾斜”潜伏着倒塌的危险,不解决难以安居。
我向生产队讨回盖房剩下的一块长板和几根木梢,请几位邻居帮忙,把长板横贴墙身,再用木梢分段顶着板面,下端埋入土中夯实,如园丁保护老朽欲坠的古树名木那样。
北墙加固之后,我又把目光转向屋顶。横看,茅草厚厚薄薄,很不均匀。竖看,又参差不齐,长长短短。这是昨天擦黑时分,一堆人爬上屋顶,各自为战的必然结果。联想到新屋刚落成,墙壁就需要支撑加固,屋顶经不起风吹雨打恐怕是毫无疑问的了。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新屋落成后才十来天,我的预测就应验了,而且狂风竟然把茅屋吹破,出现了本文开头所述的令人恐怖的一幕。
古时候,杜甫先生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时,孤立无援,连儿童也趁火打劫:“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他呼叫不灵,无可奈何,只有拄着拐杖长吁短叹。
而今,在我的茅屋被狂风吹破的危急时刻,两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冒着雷鸣电闪,顶着狂风暴雨,飞快地爬上屋顶,用梯子和他们的身躯压在茅草上,用绳子扎紧发头的地方,再用大石头镇住,方才避免天窗扩大,使屋顶得以保全下来。
这两个小伙子是与我们毗邻而居的邓仁海、邓仁江兄弟。我把他们的姓名郑重地写在这儿,以表示对他们的敬重和谢意。感谢他们在非同寻常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临危不惧,用胆量和智慧保护了茅屋,保护了我们的家。如果在今天,我要为他们申报“见义勇为”奖。
事后,邻队陆文仪大姐送来了稻草,生产队派人修补并加固了屋顶,又用泥抹了屋脊。这样修缮之后,比先前好不少。但若雨稍大一点儿,仍四处滴水。看来,东修西补,无济于事,只有揭掉重盖,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而我们心里明白,这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些年,我们怕下雨,怕刮风,尤其怕大雨大风。即便茅屋不再为狂风所破,风雨过后总得要洗洗晒晒,重整家园。
一天,我们正在茅屋门外拉绳子,晾晒被大雨淋湿的衣物,又把坛坛罐罐搬出来,看看豆豆果果有没有受潮,陆文仪大姐来了。她是来动员我们搬家的。她说,她们队里有空房,已和主人商量好,只要我们同意就成。文仪大姐乐于助人,言行实在,我们相信她说的全是真话。但考虑到她虽是大队妇女主任,但“搬家”却不代表大队,而是出自她个人的关心。我们谢绝了。房子没有搬成,我们对她仍怀感激,她却早已撒手人寰。孔子曰“仁者寿”,看来未必。愿她在天之灵平安!
那时我们真的纳闷过,为什么前后左右那么多茅屋经得起风吹雨打呢?那些茅屋也是社员们自己动手盖成的呀!
一天赶集,一个“老下”(当年对下放干部的通称,用今天的话说叫“下放族”)悄悄对我说:“你们盖房之前,应该请生产队干部吃一顿,再送队长一份厚礼,剩余的钱再交给生产队,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他们不会开腔的,这样,你们的茅屋就风雨不动、稳如泰山了。”当时听了这话,我很反感,认为他玷污了贫下中农。今天,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却觉得他的那番话十之八九是经验之谈,并不存在玷污谁,和我交流更是“老下见老下,一肚子知心话”的肺腑之言。不过,回想当年,我们没有用公款做交易,按照政策办事不走样,不仅不后悔,反而心中坦然。
拨乱反正的东风吹进了茅屋,我们乘东风又回到了城市,我又重上讲台。真是日月如梭,一晃整整四十年了。茅屋所在地的镇东大队已更名为镇东村,隶属梁园镇。随着新农村的建设,城镇化的推进,加以陆园果业的带动,全村的茅屋都先后拆除改建为砖瓦房,楼房也不少,别墅也出现了。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理想,经过一千二百多年的漫长岁月,总算成为了现实。值得高兴,也值得深思。
刘元树:笔名箭鸣,四川大邑人,1931年夏出生于成都。初入重庆大学,1954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合肥师范学院、安徽师范大学、安徽大学、西南民族学院任教。出版图书九部,其中专著两部。退休后,发表散文、随笔3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