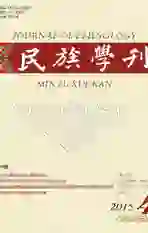麦克仑南论一妻多夫制
2015-05-30毛雪彦张亚辉
毛雪彦 张亚辉
[摘要]古典进化论学派学者麦克伦南(John·Fergus·McLennan)曾在其著作《原始婚姻》中对一妻多夫这种婚姻家庭形态进行了论述。麦克仑南对一妻多夫的基本看法是,这种婚姻家庭形态并不是一种例外和反常形态,而认为一妻多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和普遍阶段。麦克仑南的这个论点是基于他对人类早期社会基本图景的推论和分析。本文试图在说明麦克伦南关于人类早期社会与婚姻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来讨论一妻多夫制在其中的序列与价值。
[关键词]麦克仑南;《原始婚姻》;一妻多夫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5)04-0008-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理论与蒙藏佛教社会的人类学研究”(项目编号:15BSH09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毛雪彦(1990-),女,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3级人类学硕士; 张亚辉(1976-),男,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藏边研究、历史人类学。北京100081
现存于西藏与喜马拉雅山麓的一妻多夫制婚姻仍是让人类学家感到兴奋的话题。在人类学的学科史内部,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和争议持续了一百多年。人类学历史上正面对一妻多夫进行讨论的学者,最早应是古典进化论学派的麦克伦南。在他的著作《原始婚姻》(1865)当中,麦克仑南对不同形态的一妻多夫婚姻进行了正面的讨论和分析,1877年他又发表了《收继婚与一妻多夫》一文,对收继婚和一妻多夫这两种婚姻形态之间的关联作出讨论。但其关于一妻多夫制系统综合的探讨主要在《原始婚姻》中。基于对人类早期社会结构及婚姻形态发展图景的推论,麦克仑南认为,人类早期历史上必定出现过一个普遍的一妻多夫阶段。在当代的人类学研究中,婚姻制度与亲属关系依旧是一个重要的领域,一妻多夫仍是这当中的研究热点之一。特别是在西藏研究中,一妻多夫更是一个重要议题。然而,由于麦克仑南的诸多作品至今未译成中文,加上前人的一些误导,国内学界对其关注不大。或许是因为对古典进化论的忽视,当代国内外关于西藏一妻多夫研究的作品对麦克伦南的回顾较少,少数研究作品中对其评述似乎也有失公允。麦克伦南对一妻多夫制的研究或被误读或被忽视。尽管后世对麦克伦南所作出的推论和引证质疑颇多,但我们仍有必要重新发现麦克伦南对一妻多夫制的研究视角并从中获得启发。
麦克伦南是与泰勒(E.B. Tylor)、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同一时期的英国古典进化论学派学者。他出生于苏格兰,后半生一直为苏格兰法院效力。麦克仑南最初就读于艾伯丁大学,并在该校获得文学硕士。在学期间他在数学上表现出惊人的天赋,于1848年获得两项数学奖。 1849年,他前往剑桥大学求学,最初就读于康韦尔科斯学院,但随后又转入三一学院,师从柏拉图研究者W·H·Thompson[1](P.Viii)。1853年他参加了剑桥大学的数学荣誉学位考试,成绩位列全校第二十五名,然而就在同年,他放弃了在剑桥的学位离开了学校。1853年到1855年这两年,他在伦敦从事了一些文学和新闻工作[1](P.viii)。1855年麦克仑南返回苏格兰,并开始在爱丁堡大学学习法律[1](P.ix)。1857年他应召入苏格兰法院,一直到1870年他都为苏格兰法院效力,但他在法律事业上的发展并不乐观。在1857年出版的第八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他撰写了“法律”一文,这是目前可找到他最早的公开发表作品。1860年至1864年他陆续在一些期刊上发表了四篇文章,这四篇文章所探讨的主题并不集中,分别涉及苏格兰艺术、婚姻法、苏格兰犯罪率问题。1865年《原始婚姻》正式出版,在英国反响很大,有赞扬也有争议。1868年他为《剑桥百科全书》撰写“图腾”一章,从此展开了图腾制度的研究,1869年到1870年他以《动物与植物崇拜》为题发表了他对图腾崇拜的系列研究。1875年以后,他因病而难以继续工作,但这期间他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主要延续了《原始婚姻》一书中所讨论的问题,如一妻多夫、内婚制与外婚制等问题。1876年,他出版《古代历史研究:包含重印的〈原始婚姻〉》一书,除了《原始婚姻》,这本书还收录了麦克仑南前半生关于婚姻家庭及亲属制度的重要研究,它们分别是《古希腊的亲属制度》、《亲属关系的分类系统》、《巴霍芬的母权论》、《群婚》。1881年年初他身体有所好转,本打算继续投入研究和工作,然而在这年6月,麦克仑南突然在家中猝死[1](P.xii)。终其一生,《原始婚姻》是他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他的研究主要也围绕婚姻家庭和亲属制度展开, “在英国大家都认为麦克伦南是家庭史的创始者和这方面的第一个权威。”[5](P.6)
一、麦克伦南与《原始婚姻》
1857年,麦克伦南在为第八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写“法律”一文时,他就这样说:“法律可以这样说,它首先围绕着婚姻关系生长,随后它又围绕着继承秩序而生长。”在这个时期麦克伦南就已经开始关心原始法和早期社会的关系,他认为婚姻、个人人身安全、财产以及政府都是基础的社会制度。但在这个时候,麦克伦南的论点与后期《原始婚姻》中所表达的立论完全相反,他在“法律”这篇文章中这样说:“社会产生于家庭,每个人出生于一个家庭,在这样的家庭中出现了服从权威的萌芽,而这种萌芽就是文明社会的基础。一个家长制的国家必然是家庭家长制的延伸。这就好比菩提树由自己的根而生长成一片森林,而诸多家长制的家庭成为一个部落。”[3](P.67)七年后,麦克伦南在《原始婚姻》中则极力反对这种先有家庭再有部落的说法。泰勒认为,麦克伦南之所以会有这种巨大的变化,是因为在1857年后他更多的接触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风俗材料[3](P.67),在更广阔的人类活动范围内,麦克伦南开始反思那些非父权家长的家庭和婚姻形态,进而展开新的思考。《原始婚姻》以婚姻形态和亲属关系为两条线索集中讨论了人类早期社会的一般状况。在整个研究方法上,主要运用了泰勒的“遗存”这一概念,这是麦克仑南推论的重要基础,他试图通过一些现存的现象去寻找一种“结构”上的古老,从而去探究文明社会的起源和人类社会的早期发展形态。通过对世界各地婚姻形态的广泛对比,麦克仑南推论出一个具有普遍性和持续性的人类早期社会结构与婚姻形态的发展路径。
(一)从战斗同盟到部落氏族
在麦克仑南看来,最早的人类社会当中,人们以群居的形式生活在同一个营地中[1](P.63)。这个营地组织实际上是一个战斗同盟,人们之间的联系纽带是依靠战争或狩猎而形成的伙伴关系,群体之间的团结是基于共同的利益或抵御共同的风险,这些人很自然的成为一个固定的群体。在这样一个时代,由于缺乏对女性的培育以及习惯性的杀婴使得女性普遍稀缺。原始群内部为了避免因抢夺群体内部数量有限的女性而发生的战争和矛盾,达成外婚的习俗。[1](P.69)与此同时,所有的原始群都面临女性的缺失及不可调和的世仇,彼此间难以达成友好互动。因此,只能通过偷或者抢的方式来获得女性,这便成就了人类历史上最早也是最原始的外婚制。在这个时候,两性之间的关系可能毫无规范并且非常混乱,此时不存在“个体”的意识和概念,因此群体中不存在某个个人单独占有一个或多个女性的情况。
抢来的女子会被视为外族人,尽管她在抢来她的部落里生儿育女,但这些孩子也连带着被看成族外人。由于早期人类对生育的无知,这时候没有“父”的概念,子女只能确立他们和母亲之间的关系。而一旦一个人意识到自己与母亲之间流着一样的血,便能很快发现他与其他兄弟姐妹之间也有相同的血脉。因此,一种通过女性的亲属关系开始出现并得到发展。成长起来的青年子女在原始群内部附属于母亲而并非本群体,他们逐渐形成一个个独立的血缘团体,于是“所有的相同的血缘的团体开始联合成一个氏族或家屋(gens or house)[1](P.96)”。 这一转变有着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它逐渐打破了原始群维系团结的伙伴关系。原始群体的组织机制开始改变,原始群基于战斗同盟的誓约和兄弟关系瓦解。母亲及其子女不再与整个群体享有共同生活及公共居所,他们从战斗同盟的大房子里搬离,开始单独占据一个住所,并拥有独立的不属于原始群的财产,当然这些财产不过是武器、食物等。而这正是家庭生活的开端也是氏族的发端,更是人类历史上财产私有化的第一步。这样的血缘群体所建立的是一个公共家庭,通常由母亲,子女,女儿们的子女组成。此时,亲属关系通过女性来确定,这意味着家庭的血脉和财产都通过女性来传递,家庭中兄弟即便分享到部分财产,最终将由他姊妹们的子女来继承。当这种家庭在各个部落中不断增多且逐渐稳定,部落内部变得混乱,它不再只有一支血统,而是成为有多样血统的团体,于是这个群体的成员之间便可以通婚了,但事实上他们在整体上还是遵循外婚原则,以族外婚在内部通婚,因此“族外婚兴起的地方也是其消失的地方。”[1](P.100)于是,以武力劫掠群体女子的习俗暂时被取代,婚约和买卖婚就形成。[1](P.93)订婚制和婚约也在此时出现,婚礼上会出现仪式性或象征性的掠夺行为。总体来说,这一阶段原始部落在血缘上要求绝对的外婚,而在部落内部形成内婚制。
(二)亲属关系和财产继承的发展与转变
人们在原始群时代并没有忠贞或独占的观念,因此两性关系极其混乱。根据麦克伦南的推论,为了修正这种杂乱的两性关系,人们开始做出限制,规定一个女子只能与一定数量的男子建立稳定的性关系,且这些男子之间可能没有亲属关系。这就形成了最原始的一妻多夫,纳亚尔人的一妻多夫正是这种最原始形态的代表。此时,血统的传承和财产的继承都由女方一系来延续,男性一般把姊妹的子女视作自己的子女。但这种完全通过女系的继承也被逐步限制,“在一个公共家庭中,如果姐妹多于一个,母亲和兄弟将不会让所有姐妹子女拥有普遍的继承权利,而是允许长姊的子女继承,这是对女系继承的限制的第一步。”[1](P.96)在此,除了两性关系在一定范围内被限制的同时,女性在财产中的继承也逐渐被限制。
较之先前的混乱,由于性对象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男性可以大致推断出谁是自己的子女,进而产生一种自然的父子情感,基于此男性会赠送礼物给那些他们认为是自己的孩子,这是财产继承和家庭制度上的一个重大变化。随着男性越来越多地将礼物和财物送给自己的子女,这一举措的常规化,直接导致公共家庭财产继承权的变化,兄弟们不再将自己的财物留给姐妹们的孩子,而希望由自己的孩子来继承,于是女性开始从财产继承中退出,男性开始主导财产的继承。这使得基于男性的亲子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被认识到。同时女性忠贞的重要性开始被要求。因此,伴随着这种继承制度的转移,为了确保女性的相对忠诚和可靠的父子关系,相对于同外人共有一个妻子,一家当中的兄弟关系明显是牢靠的,因而会出现一个家庭中有血缘关系的兄弟迎娶一个女性。这种情况下,女子从她的公共家庭中搬离开始从夫居,这便是西藏的一妻多夫制。在这种婚姻形式中,通过男性的亲属制度开始被确立,血亲制度由女性转入男性。
随着血亲制度从女性转入男性一方,父亲的身份明显的体现并被认知,基于男性的亲属关系越来越稳固。女性对男性血缘的忠诚也逐渐向对单一男性的忠诚发展,这就产生了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麦克伦南说,最初这也可能是源于人们对部落首领的效仿,部落首领因其财富与武力可能不再与他人分享妻子,而是独占一个或多个妻子,因此“随着定居习惯的出现,财富的积累,性别的平衡,首领们成为被人们模仿的典范,并改进继承制度。”[1](P.99)在麦克伦南看来:“当血缘关系通过男性建立来确立时,首先将会对阻碍异化的过程。”[1](P.99)亲属关系通过男性来认定,则会塑造一个同种的(homogeneous)群体[1](P.99),也就是说部落内部的血统将变得单一。女子嫁出后,她便不属于原本的部落,她和她的子女都属于另一部落的血统。兄弟与不同血统的女子所生的子女都被视为同一血统,家庭的不断扩大也将血统不断扩大。同时,部落内原本不同的血统会通过对一个英雄的追溯来虚构一个共同的世系群。家庭的扩大及部落对共同世系的拟构,使得部落成员都在亲属关系范围内。女性很难再在其部落内部寻找到婚嫁对象,只能嫁到另一个部落。如果部落间关系友好,彼此间可以买卖婚或婚约来通婚,否则掠夺婚再次出现。而这次掠夺不再是因女性数量之低下,而是迫切的外婚要求。这便是劫掠婚的另一个阶段,也是为何亲属关系通过男性的地方,劫掠婚之痕迹最为明显的原因。但并不是所有的这类部落都发展成为外婚制,有些部落反而发展成内婚制,这类部落多因在征战中的胜利和自身的强大而产生一种优越感,将自身放在一个至尊之位上而将其他部落看成是下等的群体,从而拒绝和这些下等群体通婚,这种内婚集团随后发展成阶级社会,如印度的卡斯特。
(三)外婚制与国家的起源
库朗热(Coulanges)认为,家庭是古代社会唯一的社会组织,后由家族发展成胞族,胞族壮大成部落,部落再扩展成部落联盟,这些部落联盟发展成城邦或国家,在这个过程,人们的祭祀与信仰不断的从家庭中冲破,上升到更大的范围和空间中,因此,在库朗热看来国家的起源与形成在于共同的祭祀。梅因(Maine H.S.)也认为,从罗马的经验来看,家庭、家族和部落像同心圆一样外扩,国家是由团体之间的联合形成,这种联合是通过不断地拟构一种关系,从而通过收继来达成。麦克伦南反对库朗热及梅因这种关于国家起源的构想。他认为,部落很难追溯或初始化至一个个体家庭,共同的英雄祖先和神灵更多的是虚构。他批评梅因对通过虚构关系来进行收养的联合是对这种关系的滥用,在麦克仑南看来,梅因最严重的谬误在于认为人类社会之初就存在家庭和成熟的婚姻形态。
在麦克伦南看来,各部落走向国家凭借祭祀或联合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在国家形成之前,所有的部落都处于敌对和世仇状态,联合似乎是艰难的。亲属关系通过男性来认定的部落是同种的,这些同种的部落的联合将成为种群(populations)[1](P.109)。尽管这些同种部落内部可能存在一定范围内的内婚,但在这些群体的总体趋势是要外婚的。“在每个部落中,所有的男子都有相同的血统和姓氏,并受亲属关系的约束来共同行动,或在特殊的情况下与其他血统的人对抗。”[1](P.110)这样看来相互之间的联合是困难的。麦克伦南认为,由于外婚拥有相同的名字和血统氏族会在临近的几个部落中出现,这些氏族是亲属关系通过女性时代外婚的产物,由于这些共同的氏族使得这些部落之间的平等联合成为可能,并发展出国家形态。这些氏族则会联合成为一个部落的血统,拥有特权成为联合部落中的中心力量。
二、麦克伦南论一妻多夫
在人类婚姻的发展史中,一妻多夫究竟是一种反常的形式还是一种常规的形式?无论是一般历史上的记载还是当代人们生活中的见闻,一妻多夫似乎都是一种怪异而难以捉摸的婚姻形态。在麦克仑南看来,一妻多夫正有着划时代意义,它是人类亲属关系通过女性来确立到亲属关系通过男性而确立的一条中界限。因此,他坚持认为一妻多夫曾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普遍阶段。一方面,他通过大量的历史材料与冒险笔记表明很多地区都出现一妻多夫。如,他指出“凯撒告诉我们在他的时代一妻多夫流行于大不列颠人之中。”在爱尔兰的Nennius的Picts人中也有其存在过的直接证据[1](P.15)。印度史诗也暗示在早期印度历史曾出现过一妻多夫的婚姻,也就是说可能在整个印欧民族中这种情况曾经是普遍的。另一方面,麦克仑南的逻辑推论认为,人类早期群居生活当中的性结合是杂乱无章的,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必定要对之前这种杂乱的性关系进行修正,同时由于女性数量稀少,这种修正只能导向一妻多夫,而一妻多夫便是这种修正的进步体现和必经之路。
麦克伦南的研究中,一妻多夫存在于一个由低到高的序列。他认为以印度南部及斯里兰卡的纳亚尔人为代表的一妻多夫制是比较原始的(the ruder)一妻多夫形式[1](P.74),其特点是多个男性伴侣之间可能并不存在亲属关系。最高级的一妻多夫形式则以西藏型的兄弟一妻多夫为典型,这种婚姻形态在整个喜马拉雅地区及次喜马拉雅地区存在。在麦克伦南看来:“一妻多夫所有可能的形式必然处在纳亚尔人和西藏的形式中间。”[1]P.75在很多地区原始的一妻多夫与高级的一妻多夫并存,后者往往是一个地区的普遍形态,相反前者则往往是一种例外,他认为这体现了这种婚姻形式发展阶段的连续性,即西藏式的一妻多夫是由纳亚尔人式的一妻多夫进化而来的。在《收继婚与一妻多夫》一文中,麦克伦南更加明确的表示,纳亚尔人的一妻多夫是西藏式一妻多夫的准备阶段,而西藏式一妻多夫则是为一夫制和男性亲属关系之确立做准备。[2](P.694)
(一)纳亚尔式一妻多夫
纳亚尔人居住于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根据19世纪的记录,纳亚尔人的成年女性可能会有多个丈夫,但最多不能超过12个,由于纳亚尔人受种姓制度的影响,女子在选择丈夫时会有严格的等级与种姓之限制[1]P.75。通常情况下这些丈夫之间可能不存在血缘和亲属关系。同时一个男子并不是只有一个妻子,他也可能拥有很多个妻子。麦克伦南把这种婚姻形态看作是人类在混乱的两性关系中寻求秩序的必经之途,并认为这是一种最为原始的一妻多夫的典型。
在纳亚尔人的婚姻中,父亲的身份和血统极不确定。根据麦克伦南在所引用的19世纪旅行家的笔记来看,几乎没有纳亚尔人知道自己的生父究竟是谁,每个男子将自己姐妹们的孩子视作自己的子嗣,在纳亚人中“如果一个男人因为与他相爱的或与他有同居关系(cohabitation)的女子的孩子之死而表露出一种巨大悲痛,将会被视为非自然的怪物。而当他的姊妹之子死亡时他流露出这种情感则是人之常情。”[1](P.76)孩子在姓氏和血统上都属于母亲一方,并由舅舅与母亲照看抚养。因此,在这种一妻多夫的生活中,血缘关系明显是通过女性来确定的,因此在财产继承和居住原则上也由女性来主导。在居住原则上,根据麦克伦南的分析来看在纳亚尔人中并存三种居住原则,一种是女子一般会和自己的母亲及兄弟居住在一起,另一种情况是,女子在与第一个丈夫完婚后会搬出母家拥有一个属于她自己的房子,供她自己和她的子女居住,丈夫们只是拜访式的客居,不会长年与其居住。总体来说这是最原始的一妻多夫制,女性是不会与丈夫居住的,更普遍的情况是她们将与兄弟母亲同住。也有个别案例表明,会有兄弟和他喜爱的姐姐住在一起,成为一个次级的家庭。但通常情况下,生活在一个家庭中的成员分别是:母亲、兄弟、姊妹以及姊妹的子女。在继承方面,对于一个男性来说与他有牢靠血缘关系的人便是他的兄弟和姐妹,随着长期的共同居住这些人也是他最亲密的伙伴。姊妹的孩子与他的关系不仅仅是明确的血缘纽带,他对外甥义务地抚养和培育使舅甥之间也有密切的情感。因此,一个男子死后他的全部可动产都由兄弟或姊妹的子女继承。如果他有土地,那么这些土地将由健在的兄弟们先后继承,但当这些兄弟纷纷离世后,最终仍由姊妹的孩子来继承他们的土地。
根据麦克伦南的推论,为了修正群体内部的性混乱和女性缺少而带来的困扰,必然以一妻多夫的形态来进行适当的规范。更确切的说,这实际上是建立了一种平衡稳定的性伙伴关系,男女双方在血缘和财产上几乎毫无瓜葛。但在这一阶段出现了很多重大的变化。首先,从婚姻及社会结构发展的历程来看,这一阶段是正式告别群居的时代,最原始或最基本的家庭结构在此出现,这样一种家庭由母亲和子女构成且拥有一定的财产,家庭制度由此开始不断发展。其次,建立起了一套通过女性来确定的血缘关系和亲属关系,并发展出一套相应的继承秩序,妇女也因而成为社会和财产的纽带。尽管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可能并没有父亲这样一个角色,但兄弟在家庭中仍然有重要的地位,他们在生活和生产上的优势和作用非常明显。在麦克伦南的进一步推论中,纳亚尔式的一妻多夫的继续发展会有两个重要转变,即继承权和通婚权的变化。在继承方面会出现两种倾向,首先,在那些没有兄弟的姐妹家庭中,财产的继承可能会倾向由长姊继承。而那些有兄弟的家庭中,姐妹们的子女必须在舅舅们全部离世后获得继承财产的资格。其次,男性会把礼物送给那些他们认为是自己的孩子,一旦这种赠送变得频繁那么男性的血统将有被确定之倾向,那么舅甥的继承关系就会随之破裂,而终将走上父子继承的道路。在通婚权利上,如果父子之间礼物的馈赠变得频繁从而走向一种继承的倾向,那么为了保证自己的血脉和财产的传递是一致的人们会在通婚权上做出思考,而西藏型的一妻多夫形式可能会在人们心中浮现。
(二)西藏式一妻多夫
麦克伦南对西藏一妻多夫的探讨是将其放在人类婚姻家庭进化序列的一重要的位置上的,他说:“我们在西藏发现的一妻多夫制,是一妻多夫制允许的家庭制度的最高发展形式。”[1](P.78)作为最高的一妻多夫制婚姻,西藏型一妻多夫制与纳亚尔型截然不同。在麦克伦南看来,这种一妻多夫制是为一夫制和亲属关系通过男性来确定的预备阶段,由此完成了人类婚姻家庭史上的重大变革。
(一)婚姻形态与继承秩序
西藏型的一妻多夫制是一家中兄弟几人共娶一个妻子。这曾是西藏最为典型的一种婚姻形式,但并不是该地区唯一的婚姻形式[4](P.87)。从历史来看,在整个藏区除了安多农业地区没有看到这种婚姻出现的痕迹外,其余农业区和牧业区都曾通行这一婚姻制度,日喀则地区至今仍存有这种婚姻形式。在这种高级的一妻多夫制中,在长兄到了适婚年龄后迎娶妻子,长兄代表所有兄弟与妻子完婚,婚礼只举行一次,年少的兄弟无论年龄相差多少,日后相继成为妻子的丈夫。妻子婚后从夫居,无论她生下多少个孩子,长兄都是这些孩子们的父亲。兄长婚后往往在家中占有主导地位,他安排家中日常事物,并为家中各项事物做出决策,弟弟们要服从他的安排和权威。在一些极端的个案中,弟弟如同奴隶般侍奉哥哥[1]P.80。在继承秩序上,先由兄弟即“父亲们”先后继承财产,长兄死后由下一个弟弟继承其财产,同时继承家长的权利与地位。父亲们全部离世后,由长子继承财产。这种较为高级的西藏型的一妻多夫也曾出现在印度,《摩诃婆罗多》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印度Panchala的公主Draupadi嫁给了pavada的五位王子。大王子经由巫师主持仪式来完成与公主的婚礼,而其他幼年的王子随后相继成为她的丈夫。据史诗记载,当国王听到提议时感到震怒与惶恐,他恐怕这样的做法会有违《吠陀》法典,但婆罗门却告诉国王:“我们违背的律例正是祖先奉行的传统。”麦克伦南也以此为据认为在雅利安文明的一个阶段也存在一妻多夫这种婚姻形态。[1](P.87)
在西藏型的一妻多夫阶段,人类婚姻家庭及亲属制度上都迈进了一大步。首先,父亲的血统得到确定,尽管具体的父亲身份并不能专一化,但严格保证了一源的父系血统,由此,也形成一个确定的父亲之概念。其次,在相应的继承权上,尽管由父辈兄弟相继继承财产在先,但子女们终将直接继承父亲们的财产。在所有的父辈兄弟相继离世后,同胞兄弟们中最年长的儿子将继承财产和家长的身份。再次,家庭结构也再次前进一步,在这样的家庭由各位父亲、妻子及子女构成。夫妇双方开始在家庭义务与责任上形成合作分工。由于服从长兄权威父系家庭中的长兄家长制开始出现。妻子的忠贞开始被进一步要求和强调,女子不再从属于她的母家,当她出嫁后,她便而属于夫家,孩子也在夫家出生成长。女子也逐渐退出了家庭管理和领导,在继承权上她曾在有的优势也已减弱。这使得西藏的一妻多夫成为通向严格意义的婚姻和家长制家庭中的一个必要阶段。
(二)一妻多夫制继承秩序的延伸与叔侄关系
在麦克伦南的推论中,我们明显看到长兄型家长一定会先于父权家长制出现。认识到这一点很多情况就变得容易解释,典型的收继婚中弟弟有在兄长死去后迎娶寡嫂为妻并继承兄长财产的权利与义务,其起源可以在西藏型的一妻多夫制中得到解释,父权制中的长兄继承或许仍与兄弟继承有很大的关系。这种兄弟优先于儿子们的继承法规很可能是兄弟型的一妻多夫制继承法则的遗存,通常继娶寡嫂和继承财产是并行的,不能接受一方而拒绝另一方。麦克伦南甚至认为:“兄弟先于儿子继承的制度必定是在那些有或者曾经有一妻多夫的地方存在。”[1](P.83)他进而引证推论,西藏型一妻多夫曾在某个时期普遍流行于印度、古希伯来、蒙古、吉尔吉斯土耳其人以及高加索诸部当中,因为这些部落当中都存在收继婚与兄弟继承的法则。由此我们看到,婚姻家庭的发展和继承制度的发展似乎并不是平行的,很可能婚姻形态已发展到下一个阶段,而继承制度仍旧停留在上个阶段。我们把目光转向西藏内部,西藏除了一妻多夫这种婚姻形态外,同时也存在一夫多妻和一夫一妻制。在西藏历史上,继娶寡嫂的义务和兄弟的财产继承制度似乎在也其他两种婚姻形式中延续。这种义务与继承方式直接影响了西藏历史上的叔侄关系。我们将看到在西藏历史上叔侄关所呈现的两种趋势——不可调和的矛盾与传承。米拉日巴与叔父的激烈冲突,教团内部叔侄的法统传承关系。
西藏历史上明显出现的叔侄之间的斗争,这与兄弟继承制度的延续与长子继承制之间的矛盾有密切关系。上师米拉日巴的父亲在临终之前把他的妻子及儿女委托给了他的弟弟,在他父亲死后,寡嫂出于某种原因不愿嫁给他的叔父,但财产被其叔父全部掠夺,并奴役米拉日巴及母亲,米拉日巴后学习咒术报复叔父。米拉日巴的弟子热琼也有类似的命运,其父亲逝世后,他的叔父继娶其母填房,而虐待热琼。类似的记载在西藏历史上很多。首先,我们看到上述事例中的婚姻形态,已由一妻多夫转变成一夫多妻或一夫一妻,父亲的身份变得更明确专一,长兄家长制开始逐渐向父亲家长制过渡,但继承法则依旧延续了一妻多夫继承制的寡嫂继娶和财产继承,但同时要求“父亲或叔伯在儿子结婚成家和成为族长之时便要让位。”[6](P.91)这就造成了,叔父对长兄儿子的妒恨与压榨在于他必须在年幼的侄子成人前将家产归还给侄子,这是各个叔侄矛盾的事例中叔叔想方设法要毒害或虐待侄子的原因,噶玛巴八世在出生时他的叔父就试图毒死他。很明显,发展到此时,婚姻形态也已不再是一妻多夫,兄弟继承正在向直接的父子长子继承过渡,但在继承上新旧两种继承法之间的张力直接造成了叔侄之间的紧张和矛盾。
除了这种不共戴天的叔侄仇恨之外,在西藏更为典型的是叔侄的法统继承。麦克伦南在论述西藏一妻多夫时引用这样一则材料,“在拉达克,一个长子结婚时,他的父亲的财产(更可能是家庭不动产)传给他,而他负责赡养父母。如果他和他的妻子愿意,父母会与他们同住,或让父母在另一个住所居住。小儿子往往成为喇嘛。如果有更多的兄弟,他们会成为妻子下级的丈夫,不过所有的孩子被视为属于家长。”[1](P.80)拉达克的这种婚姻家庭形态在西藏或许更为普遍,兄弟共娶一妻,家中幼弟出家为僧。西藏早在墀松德赞时期就规定,如果一个家庭有许多儿子,他们便根据年龄的顺序而依次占有庄园,最年幼者遁入教门。[6](P.90)因此,兄弟相继继承财产和幼子出家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传统。出家的弟弟必然退出家族财产继承的争夺,那么他与侄子之间的关系将变得轻松。叔侄之间的关系就有可能会延续一妻多夫制时的父子关系,也就是说叔叔倾向于将侄子看做是自己的儿子,因此将自己在教团中的一切传给自己的侄子而不是外甥。
三、结语
在整个研究方法上,麦克伦南主要运用了泰勒的“遗存”这一概念,这是他立论的基础,他试图在现存的各类现象中去寻找一种“结构”上的古老,从而去探究文明社会的起源和人类社会的早期发展。与古典进化论的整体批判一样,麦克伦南的《原始婚姻》被认为随意拆解文化零件,肆意拼装进化图式。此外,麦克伦南大多数材料都是来自旅行家和传教士的见闻和记录,后期有些材料被指出是有失偏颇的,但我们仍有必要对他的研究进行重新思考。
麦克仑南关于人类亲属关系和婚姻形态的发展脉络可以分成两条线来看,而毫无疑问,婚姻形态的变化与亲属关系的进程有着直接的关联。简单的说,在麦克仑南的论述中,人类最早的亲属关系和血缘观念只能通过女性的来确立。在这之后,亲属关系通过男性来确立也发展形成,而这与财产的继承有直接的关系。最终,亲属关系由男女双方共建。此后,男系亲属制度开始发展并稳固,并成为确立亲属关系和血缘关系的重要导向。而就婚姻形态来说,在原始群居时代人们并没有婚姻的概念,纳亚尔人式的一妻多夫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婚姻,但使一个女子与几个没有亲属关系的男子结成稳定的性关系。这直接影响了家庭的结构,家庭由女性领导,而财产的继承也终究流向女方,家庭也依靠女性延续。随着纳亚尔人这种原始的家庭发展,西藏型的一妻多夫制将呈现,这时血缘的观念就和财产观念结合在一起,血缘传承和财产继承一样重要 。兄长成为一家之长,而家庭的领导由兄弟控制,在兄弟死后由最年长的儿子来承袭家长之权利。而此后很快会发展出一夫制,年轻的兄弟将不再与长兄共享一个妻子,而有独立的婚姻,西藏型一妻多夫将在此时消失,而收继婚作为其残余出现,但由于收继婚中的财产继承权与一夫制形成对立,这种婚姻也最终走向衰亡。因此,麦克伦南反对将家长制和男性亲属制看作是人类社会发端之际就已经存在的,他的论证告诉我们人们对血缘关系的认知和理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当代意义上的财产观念和基本的亲属关系也并非一蹴而就。他说:“最早的人类群体没有血亲关系的概念。”[1](P.63)但他承认,在血亲关系的观念被人们意识到之前,友爱和孝悌作为本能是普遍存在的,而这也是团结和维系早期人类社会的动力。血缘关系最早通过女性确立,父的概念也是在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后,先以群像的姿态出现,进而划分出一个明确的“父亲”分身与一套父系的血缘和亲属关系。血缘关系与财产的继承结合在一起,每种血缘制度的盛行直接限制了相关的财产继承,不同的血缘关系建立了不同的继承法则。在最原始的人类生活中,也不存在家庭,它也不可能是这些社会中的基本单位。我们也明显看到,随着不同的婚姻形态的出现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而相应的麦克伦南的社会发展图景是,先有以兄弟会为中心的游群部落,再有母系氏族和家屋,最后产生个体家庭。家庭则明显是一个分化出来的单位,它不可能是人类早期社会的基本单位。
麦克伦南对一妻多夫的独到见解在于,他并不认为一妻多夫是一种特殊的婚姻形态,在具体分析不同形态的一妻多夫制后向我们表明这种婚姻形态非但不是异端而是人类婚姻历史上的重要阶段和转折。纳亚尔人的一妻多夫代表着一种原始的形态,最初旨在规范两性生活,但确立了人类最古老的血亲制度,这种制度通过女性来确立。人类最早的原始家庭也在这个时期出现,女性可能在这个时代负责家庭的领导和管理。发展到西藏的一妻多夫,这时已建立了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婚姻家庭概念。较之先前,家庭结构出现了变化,父亲这一角色出现在家庭中,也出现了最早的父系家长即长兄家长,血缘关系由女方转向男性,女性退出了对家庭的领导和管理。麦克伦南认为一切其他类型的一妻多夫都是介于这两者之间,而很多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的婚姻中也存在着一妻多夫的诸种居住形式和继承法则。根据麦克伦南的分析,西藏的一妻多夫是人类婚姻家庭进化史上转向父系家庭和亲属制度的重要转折点,它是一夫制的母体和准备阶段。从西藏历史上来看,早在吐蕃时代,一妻多夫并不是唯一的婚姻形态,一妻多夫和一夫一妻均在王室中存在,其他两种婚姻形式很有可能是由一妻多夫发展而来。在后期,这三种婚姻形态长期并存发展,而一妻多夫制这种家庭组织方式,因为通过把后嗣主干限制到唯一一个男性,来达到保持财产整体继承的目的[6](P.116),仍被人们世代沿袭。作为一妻多夫之所以被其所属社会认可并长期延续的解释,涂尔干(mile Durkheim)在《乱伦禁忌》中的讨论也值得我们思考。涂尔干认为,兄弟型一妻多夫实际上是一种乱伦的行为。长兄成年后娶妻,幼弟要在成年后才与妻子发生性关系。在涂尔干看来,当幼弟尚未成年时并不曾与其妻发生性关系,那么幼弟和其妻的关系实际上呈现出一种姐弟关系。在任何地方亲兄妹之间的婚姻都是被视为乱伦而被禁止的。于是,在一个兄弟型的一妻多夫家庭中,除了长兄以外,任何其他弟弟与其妻子之间一旦开始发生性关系,那么都有严重的乱伦倾向。可是这种乱伦行径在一些民族中不但没有被禁止,反而具有合法性。涂尔干认为,之所以会有这种合法性背后存在宽容乱伦的动力及一种社会的必然性。社会实际上存在两面性,它既促使人们形成一种团结,同时又会制造一种分化。一方面社会把兄妹团结成一个道德共同体,同时,社会又严格排斥兄妹之间亲密的两性关系,亲兄妹之间会因为道德感对性关系有一种天然的厌恶和排斥,而当社会对团结的需求超过对分化的需求,那么社会制造的这种分化将被忽视,会有某种因素战胜道德感所产生的对亲姐妹的性厌恶,从而产生对乱伦禁忌的容忍。古代欧洲王室和埃及王室都曾容忍兄妹乱伦的婚姻,前者是基于对政治权力上的原因,后者是由于对神的过度崇拜而导致的,这两个因素战胜了兄妹之间的厌恶感,而容忍乱伦。而在西藏,究竟是什么因素战胜了这种厌恶感,涂尔干并没有给予说明和解释,这也是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探索的。
参考文献:
[1]John F. Mclennan .Primitive Marriage, The Early Sociology of The Family[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1970
[2] John F. Mclennan. Levirate And Polyandry[J].Fortnightly review, 1865(May)
[3]E.B.Tylor. The Patriarchal Theory[J].The Academy, 1869-1902(691)
[4][英]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法]石泰安.西藏的文明(第2版)[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2.
[6][美]M.C戈尔斯坦. 巴哈里与西藏的一妻多夫制度新探[J].2003.(05)
[7][法]爱弥尔·涂尔干.乱伦禁忌及其起源[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