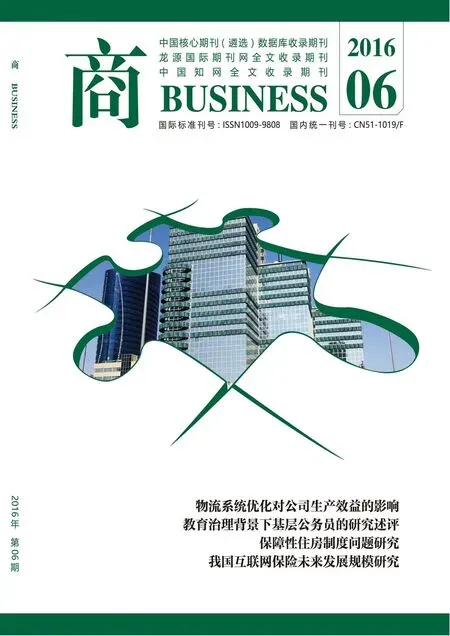读《规训与惩罚》有感
2015-05-30马腾
马腾
这本著作让我收益颇丰,但时间紧促,只是粗略地阅读了一下,诸多内容和思想领悟得还不够深刻。况且,看书就如同照镜子一般。本人才疏学浅,书里面的很多东西现在也只是初窥端倪。以后,这本书一定会常伴我左右。
在这本书中,福柯旨在通过解剖刑罚,以此角度来分析权力的存在及实现方式,从消灭肉体到规训精神的转变反映的是经济、知识发展带来的转变。与此同时,控制社会的微观权力愈发增长,几乎达到无所不在的地步。他对历史的目的、规律这类宏大命题往往表现出怀疑态度,而是比较注重人类的历史现在性,注重表现人的实际经验与实践,尤为注重表现人与人的权力关系,并在这样的辐射中找到人。在这样一种层层交织的密网中,人们通常难以获得自由并完成自我救赎。
从对疯人放逐驱赶,到将其纳入疯人院管理照顾,至现代精神病院诞生,为疯人提供舒适生活与精心治疗,无疑是文明的进步;从公开酷刑到隔离监禁,以有据可依、公正仁慈,取代任意专横、残暴严酷,更是人道的彰显。我们向来如此看待社会,评判历史。福柯却说,这些你们从来当作天经地义、与生俱来的东西,全都是被权力塑造和生产出来的。这简直就像一个恶毒的玩笑,或者像一个荒唐的真相。而他写疯癫史,写监狱史,向我们揭示了这神秘的权力是如何将人类蚕食鲸吞,所谓历史的进步,只是权力运作的自我调整。他告诉我们:疯癫不是自然现象,而是文明产物。刑罚严峻性的减弱,不过是将惩罚对象从肉体变为精神,不再制造肉体痛苦而是剥夺精神自由。二者均体现了权力的嬗变:从对肉体的征服上升至对思想的控制。
从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中心瞭望塔,人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在这里,监视权力的实施者就是匿名的,谁都可以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动机出现在中心瞭望塔里操作这个权力机器。对于这种建筑学上的视觉想象,边沁自己大为得意,他认为这种监视使道德得到改善,健康受到保护,工业充满活力,教育得到传播,公共负担减轻,经济基础得以夯实,所有这一切都是靠建筑学的一个简单想法实现的,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在由可见一斑。只顾及监视者的层面,而忽略了被监视者的感受,这完全是对问题的简单化。但有一点却毋庸置疑,全景敞视建筑所提供的功能确实被监狱、医院、学校、修道院广泛采用。
同时,这种建筑的转变也涉及了一种思想史上的观看模式的变化。古代社会讲究宏伟场面,于是罗马竞技场或者帕特农神庙都提供了一种大批人群观看少数对象的视觉模式。现代社会,随着公共生活规模的萎缩,逐渐有了让少数人甚至个人在瞬间看到一大群人的需要。在此意义上,全景敞视建筑不仅提供了一种功能性的范本,更是赋予了当代社会监视和规训的可能性。在福柯看来,这是一个从封闭的规训、某种社会隔离区扩展到一种无限普遍化的全景敞视主义极致的运动。其原因不在于权力的规训方式取代其他方式,而在于它渗透到其他方式中,以确保权力关系细致入微地散布。
权力的生产性使福柯看到了现代权力机制中的一些积极因素,即权力不是被动的禁令,而是产生许多效果的技术。惩戒权力在演变过程中,越来越强调对个人精神的治理和规训,而不是肉体的折磨与苦痛。通过一系列的权力技术,个人被无休止地编织进一种社会秩序中,为的是恢复人格,即重新生产出个体被削弱的力量、被取消的技能以及被遗忘的道德。文明史的演进始终呈现出放射的态势,为积极自由的抗争与为消极自由的筹措都是是其中应有之义。无论是寻求个人权利抑或制度保障,一以贯之的形态终究不过是专制君主与黎民黔首、知识精英与普罗大众、权力阶层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博弈。
当然,我们在生活中从不作如此想。这种权力机制胜利之处即在于这是一种自动的顺驯。肉体的枷锁内化为精神的镣铐,权力直接牵引大脑柔软的神经纤维,我们四肢听从大脑指挥而翩然起舞,却自以为正高唱灵魂自由之歌。我们总爱追问权力由谁行使,而福柯却关心权力如何产生及运作,因为在他看来,权力弥散而无形,而个人被精心编织于权力网络中。我们无从反抗,既无法挥拳攻击空气,也无法抓着头发将自己拔离地面,甚至我们从未想到反抗。我们心甘情愿被打上印记,被区别对待,被监视记录,被评估审判,发自内心地,认为这就是我们所向往的美好生活。他像是猛地揭掉世界的面具,露出一张血肉模糊的脸,然后若无其事地走掉了。留下我们还在原地目瞪口呆,以为窥见某种真相,既兴奋,又痛苦,兼不知所措。他破坏一切,却未给予任何安慰。但福柯确实没有义务给出答案。他抛出问题,便是一切价值所在,若摧毁堡垒后又重建一个自认为更好的,那与他之前所执意破坏的又有何不同。甚至他呈现的也绝非真相。或者说根本没有什么真相。面具下面的脸也许没有眼睛嘴巴,一个虚空的黑洞,遥远地呼应着某个夜里深沉的梦魇,我们似乎都曾听见远方传来的隐约的厮杀声,然而这声音转瞬之间已经淹没在现实的滚滚洪流中。
从化外昏荒的奴隶时代到万国坤舆的近世思维,时空的差异并未妨碍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实体拥有完备刑罚体系的现实。对不同程度罪责的量刑也渗透了当时的政治思维,能够被历史记载的往往是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刑罚。《史记》记载商纣王点起炭火,支上涂抹了油膏的铜柱,犯人赤足行走,受烫跌落,旋即身死。这种刑罚的游戏性质必然有预设的潜在观看者,通过观看他人痛苦的全程来实现自己的心理需求。而在《规训与惩罚》的卷首,达米安因谋杀国王而遭剥皮、灌铅、车裂等酷刑,则可视为将殷商宫闱中聊作娱乐的酷刑置于18世纪法国公众视野中的翻版。虽然时空背景转换了,观看者也由少数王宫贵族变成大批群众,但嗜血残酷的刑罚对观者所产生的视觉体验冲击却是一致的。
作为公共景观的酷刑在蒙昧时代存留了很长一段时间,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慢慢宣告终结。这种结束并非由于刑罚所提供的视觉体验不再吸引观者的兴趣,而在于盛大的惩罚仪式逐渐难容于人类的理性进步。在各种酷刑中,施刑本身如同展示犯罪,刽子手形同罪犯,法官如谋杀犯,受刑的罪犯却在这样一幅画面中成为怜悯或赞颂的对象。这种角色的倒置显然不是当局掌权者所愿意看到的,因此,对犯人肉体的施暴逐渐退出了历史,刑罚转而进入抽象的意识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刑罚图像的淡出,相反地,刑罚的视觉要素虽不再以极具冲击力的图像带给人们震撼,但却以细密的想象的方式进入政治制度。用封闭的马车取代游街时敞开的囚车,把犯人直接推上断头台,在人们难以预料的时间段内迅速处决。如果将程序复杂的极刑视作将生命分割成上千次死亡,断头台的出现无疑可作为仪式的简化版本。单一的绞刑或是铡刀都在程序上弱化了原有酷刑的仪式感和冲击力,而刻意避免群众围观似乎也是在缩小行刑场面的图像空间。
在刑法改革的进程中,一种比行刑仪式更有效的处罚方式得到认可:权力以符号学为工具,把精神当作可供铭写的物体表面,通过控制思想来征服肉体。简而言之,在群众的头脑里制造一种基于行刑仪式的恐惧,来约束其犯罪的可能性。关于规训技术,其目标不是增加人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肉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变得更顺从。这决不是一种偶然发现,它是由许许多多不那么明显的进程汇合而成的。规训社会的形成,或者说规训技术在社会中的扩散,在福柯看来与历史进程密不可分。
我们阅读福柯,为之惊心动魄。纵然明知无力抗拒那强大力量的摆布,只要我们还拥有自由思考的能力,质疑批判的精神,便不至于丧失掉最后的尊严。即使已经沙土没颈,依旧能够昂首保持高贵的呼吸。(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