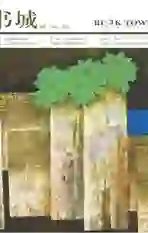长夜游:在时光河流上泛舟
2015-05-30陈丹燕
陈丹燕



乔伊斯桥畔的纸片雪花
二○一三年六月十六日晚上十点,丽菲河畔的乔伊斯之家里上演情景剧《死者》,那天下了夜雨,丽菲河面上散发出冰凉的水汽,没下雪。
乔伊斯把《死者》故事的发生地放在自己姨妈家的房子里,其实他一直喜欢把虚构故事放在能用尺子量的真实环境里,他对非虚构的地理坏境有种特别强烈的癖好,当年也许人们认为他想象力欠缺,但如今则理解他为十足现代主义的城市感。我格外喜欢乔伊斯的这种描摹现实的勇气与口味,喜欢虚构与非虚构像两块布匹那样既是不同,又是无缝缝纫的手段。我喜爱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花好月圆的黄金年代里那扎实的现代感。
二○○九年我来此地时,这栋“死者之屋”还空关着,但都柏林地图上已经标出了它的地理位置。今年已有人把姨妈家的空房子置换下来,布置成小说里描写的模样。二○一三年六月十六日,房子开门迎客,头天晚上就按照《死者》故事中的时间,在房子里上演《死者》的情景话剧。房子的底楼做了小说里的客厅,朱丽叶姨妈在门口的三角钢琴边唱了歌,加布里埃尔和爱弗斯小姐一边跳舞,一边为一个爱尔兰人的民族立场响亮地争执起来;二楼做了餐室,穿着白色小围裙的仆人李莉服侍大家喝了真的葡萄酒,因为我站在旁边的阴影里,闻到了一股葡萄酒的酸味;三楼做了加布里埃尔和格丽塔的卧室。在小说里,他们是住在至今还在营业的格里沙姆酒店。三楼就布置成了格里沙姆酒店的模样。他俩在三楼的卧室里说了高威那个早逝男孩的故事,然后,格丽塔就去床上躺下。而加布里埃尔则站在窗前,看着人造雪花从三楼卧室的窗前飘下:“他睡意朦胧地望着雪花,银白和灰暗的雪花在灯光的衬托下斜斜地飘落。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也许因为是人造雪花的缘故,它们看上去又大又厚,没有真实雪花那种寒气逼人的失重感与飘逸感,它们或许就是经过碎纸机的白纸吧,我想。但有着厚实肩膀的加布里埃尔却一直站在那里看它们快速地堕落下来。我站在他后面的阴影里也望着它们,假装没听到屋顶鼓风机风扇哗啦哗啦的声音。
停顿。亮灯。全剧终。
没适应灯光的眼睛在演员与观众们的脸上微微眯缝起来,都好像从梦中勉强醒来。演员们身上的戏服虽然也是真实的衣服,长裙与礼服,带一小块黑色网布面纱的女帽,饰有花边的白色翻领,这些包裹在演员暖烘烘肉体上的衣饰都带着与现实生活相背离的僵硬。这样的人带着小说里的名字和身份,与我站在一处,令我不得不眯缝起眼睛来。我想起上午满街飘扬的女式礼帽上的丝带,月白色的夏季西服,圆边眼镜,以及大红花裙子等等;想起那种太阳下时空的错落感,时空也许可以倒错、装扮,享受倒错带来的巨大缝隙,但时间的洪流终是飞瀑直下,人造的过去终会有种挥之不去的僵硬,这是倒错的代价。这里好像匍匐着一个巨大的哲学命题。
这是乔伊斯留给我们这些追随他的读者们的,还是意识流这种写作手法内在的哲学价值?是这个骄傲的作家用来一遍遍筛选他读者的文学素养的,还是意识流对于自己描写的人生,有比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写作手法更深邃的对时间的追问?意识流貌似可以打破时空本来设置的各种界限,但实际上,也许是令人更为痛彻地感受到时间的不可追寻。希腊人喟叹过,人不可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在意识流的时间自由流动里,这种现实世界时间的不可逆性得到了更为坚硬的证实,意识流烛照人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鸿沟。
我想起自己大学时代对意识流的喜爱,那是一个年轻作家对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好奇,是对现实主义地描写外部世界的不满足,是对自己如何讲述故事的探索。然后,借着意识流的写作手法,我慢慢地找到自己看世界的立场。我想自己一直就是个沉迷于描写的作家,那些细物,手势,眼神与光线,气味,一直都勾着我的魂,对它们的描述一直都是我纸上最大也是最经久的乐趣,就像果戈里小说里那些无所不在的思辨,那是他抒情的插笔。这种对细节的热爱,对时间鸿沟的感受,都引导我走向了意识流。在我大学的时代,意识流是一种西方作家尝试的写作手法,而现在,我意识到它是我汇通世界的立场。
由于灯光突然照亮了室内的关系,窗外的人造雪花虽然还在零星落下,但刹那就变得黯淡呆板。它们本来就是些追忆着一九○四年前的爱尔兰雪花的二○一三年的爱尔兰碎纸片,而且是被新鲜的雨水淋湿了的,很快就会烂成一坨的纸片。
坦普酒吧里的地方性与世界性
午夜的酒馆里人声鼎沸,满满都是人,我却在吧台边的墙角里幸运地找到一个座位。我要了一杯黑啤酒当宵夜,配咸花生米。那个角落很好,又暖,又暗,却看得见对面墙角靠窗的小舞台上唱民谣的歌手们。爱尔兰的这些人,只要一把提琴,一把吉他,一把笛子,他们就能引吭高歌整整一晚上,从《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一直唱到《村路带我回家》。唱到丹佛的招牌歌,一屋子的人里面,被这曲调挑出来的,都是从美国中部来的人,有人还穿着三月圣派特里克日的绿色纪念汗衫。他们引吭高歌的样子让我想起中学时代在大礼堂里,各个班级彼此拉歌比赛的情形,那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上海。
我看见女孩子大敞着的V字衣领里,雪白细腻的胸脯上泛着一团团酒精的红晕,那是年轻的身体对酒精过敏的症状。她笑得有点蠢,“林奇!什么?跟我往这边走。这是登奇尔小巷。从这里拐弯,到窑子去。她说,咱们俩去找那见不得人的玛丽所在的窑子”。这是《尤利西斯》第十四章的最后一段里的几句话。
这家酒馆正是当年乔伊斯父亲喜欢来吹牛的地方,他一高兴,就带上小乔伊斯一起来。在都柏林,小男孩喝点酒不算什么,他们从不像美国那样紧紧盯住二十一岁这条杠杠不放松。
老酒馆里此刻已挤满了人,后进来的人过不来柜台买酒,便将钱卷着靠客人们传到柜台上:“一大杯吉尼斯。”
侍应生也被困在柜台附近,他将托盘扛在肩上,上面稳稳地放着高高矮矮一大堆杯子。“阿根廷葡萄酒一杯!”他大声吼,然后,某个角落里就会有人将手高高举起认领:“这里的!”于是客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将新世界的清新葡萄酒传递过去,到了那人手里,大家都能听到一声高喊:“伙计们,谢谢啦。”
装大杯黑啤酒的,是圆圆的大肚子厚玻璃杯,所以它叫“球”;我的杯子细细长长,是小杯啤酒,叫“枪”。
如今酒馆里还有种爱尔兰式的亲热,周围不认识的人很快就能开始聊天,说自己旅行的目的,还有自己的生活。我附近的人,有从英国来的建筑师,还有两对结伴旅行的德国夫妇。大家都公认我的工作最好,旅行是为收集写作素材,最理直气壮的旅行。干什么都合适,都不浪费。但是也因为太不浪费了,所以有点乏味。
说起来,我们大家都盼着有这一夜。这一夜在都柏林的酒馆里,听爱尔兰曲子,像爱尔兰人那样饶舌,像叶芝那样疯狂地爱一个大眼睛女人—那是一个诗人爱一个新芬党人,一辈子都又伤心又无望又不能停止地爱着。爱尔兰的独立,是在被英国占为殖民地的七百年以后。爱尔兰起义者的武器,就是爱尔兰那些充满诗意的古老民谣和凯尔特图案与凯尔特神话中的圣人们,文艺与手工艺成为民族独立的基石,成为唤醒民族独立意识的武器。所以从爱尔兰来的音乐、歌词、诗歌、趣味独特的书籍装帧、黑白插画是我常年以来的心头好,当我有了更多的旅行经验,能区分英国的工艺美术运动与爱尔兰的工艺美术运动之间在文化上和表达上的不同后,我便更偏向爱尔兰。
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浪漫精神荡漾在爱尔兰那个时代的文艺里,它符合年轻时代的我对自己人生意义的期望。我背诵叶芝的诗歌,倾听充满激情的小提琴,总感到全身的血液都流得快了。人在年轻的时候,只觉得生活太平淡,只向往激情和浪漫的轰轰烈烈人生,向往为一个崇高的理想完全彻底地贡献自己。年轻的时候,每个人的血都是热的,好像烈酒,一根火柴,就能让它燃烧。那时候,每个人都能背诵“有一天,当你老了,在火炉边老眼昏花”。
说起来,当我们大家心中深深浅浅地拥有这样理想时,他在伯明翰,他们在杜塞多夫,他在海德堡,而她在西班牙的圣地亚哥。
我在上海中山西路上的红砖房子里,梳着一条马尾巴辫子。建筑师太太摸了下后脑勺,叹了声:“我年轻时代的中分长发啊。”那是伦敦街上嬉皮士的标识。
我们这一代人,有人在额头上扎过一条红布,有人则穿过紧紧裹住臀部,但在膝盖以下如喇叭般裤腿飘飘荡荡的喇叭裤。说起来,无论他在杜塞多夫,她在圣地亚哥,还是我在上海,我们都有过一条旗帜般的喇叭裤。
于是,干杯,为那条喇叭裤,和又直又多的长发,以及和叶芝的心心相印。
当我长别了青春,才有机会夜深时坐在都柏林的老酒馆里。热烈的小提琴和忧伤的笛子轻轻撩拨着我安静的血,好像一束跳跃着的小火苗,舔着做茴香酒的小酒壶。烧热红酒,是为了暖身,也为了将酒里太多的酒精蒸发掉。它使我想起年轻的梦想,我的梦想很叶芝,期待自己爱上一个革命者,而且是悲剧。这次我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我背包里除了照相机和电话,还有一本《尤利西斯》,却没有了叶芝诗集。
现在我们大家都是为了它来到都柏林。
此时一支熟悉的前奏响彻了整栋房子,它是我上大学时听过的曲子?我对正在热烈闲聊的英国人指着音乐响起的方向,一时说不出歌名,他和着音乐大力摇头,他花白的头发从耳畔飞起,他用力闭着眼睛,好像要从记忆中挤出什么来:“Dirty Old Town!我二十岁时唱的歌!”
那也是我二十岁时唱的歌呀。一九八○年,我上大学,整个中国刚刚开放大学招生,我幸运地赶上了,可大学却来不及为我们这届学生准备英文课本。我父母为我找了家庭教师教英文,她是个漂亮的英文教师,翻译了《蝴蝶梦》。我每周到她家去上课,她也没课本,我们就一起听歌,默写歌词,遇到听出来但写不出的单词,她才来讲解。我在她家默写了这支歌的歌词,我听到的版本是加拿大的罗杰·惠特克唱的,一个宁静的、温文尔雅的版本,比起爱尔兰乐队的版本,它太加拿大。但是,这就是我当年学会这支歌的声音。
那时我们大家刚刚开始能跟着VOA学习美式英语。每天晚上学校的走廊里响彻着美国之音的播音员用慢而清晰的速度朗读马克·吐温的小说,回想起来,从那么禁锢的时代里刚刚挣扎出来的人们,好像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摇摇晃晃地站在床边,听到清晨的晴空里传来了鸟叫声那样,晕眩而幸福。
“我的二十岁很不同啊。”我想这么说,可忍住了,因为我猜想退休建筑师的二十岁也是非凡的,我心里算了下他的二十岁,那正在欧洲青年的左倾狂飙之中。过了许多年,我知道每个人的二十岁,都是一个大时代。
歌手只唱了一句,整个酒馆就开始了大合唱,放眼一望,满店堂里都是半眯的双眼和大张的嘴巴,原来这是每个人二十岁时唱过的歌。虽然我们来自世界的每个角落。原来那时我们唱的就是都柏林,不管那其实是来自英国的民谣,现在是《都柏林人》那盘唱片唱红了它,它真是再合适都柏林不过了,也再合适我们这些终于来到这里的中年人不过了:
I met my love by the gas works wall,
Dreamed a dream by the old canal.
Kissed a girl by the factory wall,
My dirty old town,My dirty old town.
老运河可就是这一段丽菲河?老厂墙可就是吉尼斯酒厂外面?那么我们人生中的第一个吻是在哪里发生的呢?我的初吻发生在一个二楼的阳台上,长久以来我以为自己已经不再爱那个人了,现在想起来,原来还是爱的。
这些歌词里的介词曾经是我的英文老师用来教学的重点,特地点出来要我注意。我的英文老师喜欢用英文歌教英文,但她最喜欢的是“有烟熏味道的风”这个意象,她似乎又在教我写作。那时她住在上海老城区,她家的空气中常常也有烟熏的味道。我知道她不久就带着女儿去了美国,她现在又在哪里呢?那时候在她的写字桌上,我看到了一张黄色的明信片,上面是架飞在云端的飞机。那时飞翔在云端的外国飞机是如此稀奇,似乎凝聚着一种失而复得的感激,她将它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
歌声鼎沸酒馆里的中年人,人人都高唱自己心中的青春,那是一派世界主义的共鸣。
丽菲河畔的酒馆还在《尤利西斯》小说的地理位置上,但实际上已经不同了。乔伊斯故事里在酒馆里那些湍急的谈话无法找到,现在从世界各地来的乔伊斯迷占领了这些古老的酒馆,大家带来了全球化的午夜。当大家跟着一个爱尔兰清亮的声音纵情合唱时,也许心中再现了各自心里藏着的旧时代,各自闻到了各自老城老街道和自己成长的老屋里的气味。我家春末四处弥散的旱芙蓉花香好似就在鼻尖上,但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回忆,不知是倦怠,还是礼貌,或者是无从说起,我相信大声跟着唱歌的人们,是用同一句歌词在述说完全不同的汹涌回忆。
如今我们再也无法像乔伊斯故事里的人那样口若悬河,我们每个人都只在心中汹涌,这是因为我们如今可以在这拥挤的人群中传递一大杯吉尼斯黑啤,可以一起高唱二十岁时唱的歌,但彼此都不相信可以湍急地交换内心回忆的波涛。如今我们各自的时空只是交集,不曾融合,也无法融合。
我们现在都知道在都柏林酒馆深夜的全球欢聚,内心有界限。也许我们要是有更多时间相处,我们也能像乔伊斯父亲的那些酒友们那样滔滔不绝,辽阔地展现社会和人生的各种细节。乔伊斯的父亲当年就喜欢在烟雾腾腾的酒馆里高谈阔论,那是爱尔兰特有的本地公共空间,温暖放松,百态丛生,乔伊斯让布鲁姆和斯蒂芬在酒馆里相遇,就像爱尔兰的两代人在精神上的相遇。我相信在二○一三年六月十六日午夜到都柏林酒馆里来的人,也都带着这样相遇的幻想。但现在飞机太容易,时间太宝贵,人们相见太容易,相持太难,如今我们都只有一夜的相聚,相聚时可以一起即兴唱一支老歌,但来不及在一起讲下流话。如今我们越过千山万水,但相逢也只有干这一杯的工夫。
在这六月十六日的午夜,有人拍拍我肩膀:“麻烦叫一杯热可可。”那人指了指人群深处的一位金发女士,她正用目光追踪着这卷成一团的五欧元纸币,我们彼此微笑了一下。我将她的钱递给酒保时专门问了句:“热可可还是艾普斯牌速溶的吗?”
“现在是雀巢啦。”酒保麻利地斩断我的联想。他显然也知道艾普斯可可的典故,所以他忙中偷闲认真地瞪了我一眼,他是个面容温暖的黑发年轻人,让我想起上午带着我在老城布鲁姆游的文学博士科诺来,“但你仍能在这种联想里得到一些乐趣。”他接下那卷钱,安慰道。
是的,意识流包含了在心中感受时间流淌与断裂的双重感受,断裂与再生也是一种乐趣,这是一种对人生逝去与重获的认同,一种更为成熟的世界观。
乔伊斯中心的气味
睡意深沉的伊塞克街上,乔治教堂的尖顶此刻好像一根手指那样直直指向夜空。乔伊斯少年时读书的学校在夜色里是一大坨黑乎乎的影子,好像一大摊正在发酵的生面团。名人读过书的学校常常让我有如此的感受,我想起在大雪飞扬的下午看见普希金的皇村中学时的感受。面团在那些古老的学校旧址里发酵,因为那个日后的伟人在这里是个脸上长着令人尴尬的青春痘的少年。不论学校当时是否善待了天才,现在它们总也逃不掉攀附的样子。
北乔治王大街上,乔伊斯中心门里泄出长长一道灯光。
早晨的热闹散去了,下午的热闹也散去了。隔着玻璃窗往里看,闻到一股冷却的咖啡的味道。
在《尤利西斯》第一章里,“当他脚步轻盈地在厨房里转悠,把她早餐用的食品摆在盘底儿隆起来的托盘上时,脑子里想的就是腰子的事。厨房里,光和空气是冰冷的,但户外却洋溢着夏晨的温煦,使他觉得肚子有点饿了。”在乔伊斯中心里,厨房改造成卖品部的一部分。几年前,我在楼上阅览室里读各种按照《尤利西斯》里的场景拍摄的都柏林摄影册,当我离开乔伊斯中心时,已超过了中午时分,卖品部的女职员正在做咖啡喝,满室暖香,可是,那不是可可的香气。
“喝完可可后,布鲁姆和斯蒂芬都沉默下去了吗?”书里这样问。
“沉默下去了。”书里这样回答。在寻常的厨房里他们相互用自己肉身的镜子照着对方的脸。彼此在镜中照见的是对方的,而不是自己的。在厨房里,这两个人终于综合成为一个人物—爱尔兰人,既布鲁姆又斯蒂芬。有时布鲁姆和斯蒂芬,会让人想到《圣经》里的那些使徒,可有时又令人想到,冬天时在浴室里独自对着镜子,洗澡前的自己,躯体上污秽尤存。这大概也是乔伊斯对爱尔兰人的判断,比叶芝世俗,又可以说比叶芝壮阔与结实。
此时书里再描写厨房,已不是像第一卷那样简单明了,这章是对一九○四年的都柏林厨房以及与厨房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经济、政治、人心、自然环境带来的食物特点,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水准和精神面貌以及社会学意义上的食物构成,等等的华彩乐章。乔伊斯索引的天分像洪水般倾泻在这间普通的厨房里,将它变成一九○四年爱尔兰食物百科全书,关于食物,关于烹调手法与习俗,关于食材,关于传统手法与殖民时期媚俗的口味,然后,广泛的食物社会学,中产阶级家庭厨房里不为人知的审慎和精明。
《尤利西斯》是永远不会让读者忘记译者的,乔伊斯的译者同时也一定是强势的注释者,他们得搀扶读者走过乔伊斯著作中岔路无限的森林,那是无尽的索引与隐喻,无尽的时空错乱后的类比与联想,无尽的希腊神话典故,《圣经》典故,爱尔兰历史与现状,欧洲各国的历史与语言,世界文学史的独特见解,莎士比亚戏剧的变化与歪曲,各种语言的中古形态和现代形态,消失了的凯尔特古语,只在书本上存在的古拉丁语,对世界文明史上各种文体的模仿、戏仿和颠覆,甚至各种流行在当时知识界的小道消息集锦,其中最为简单的,是我的这种地理阅读的方式,也是我能力所能及的方式。
我得不停地翻到后面去查注释。
即使是乔伊斯已经写到了最后一章,他仍保留着蓬勃的精力去细细描写布鲁姆家的碗柜。他不知道这时已经在考验读者的体力了。
然后我想起来上一次读到这些注释时心中的叹服。乔伊斯一定逼迫读者一次次地叹服。乔伊斯的译者也一定逼迫读者一次次地为这些注释叹服。想要读《尤利西斯》,不借助每个章节后多达几百则的注释,简直就是不可能。
不光不可能读懂,更不可能体会到它意识流的流动。我从大学时代起,便甚为喜欢意识流,但在写作中,至今我能做到的,还只是意识在感官上的流动,这种意识流的运用,靠敏感的感官和适当的语言表达,就可以大致完成,一半是拜天赋所成。
而《尤利西斯》的意识流还有丰富的知识和历史事件,政治事件以及爱尔兰现状的交织和流动,它像大洋一样广阔而且丰富,包罗万象而富有秩序感。有时它让我想到宇宙的无数自在运转的精密小循环,乔伊斯有能力不把生活简单化、脸谱化、意识化,不做合并同类项式的概括,(这些都是思维能力不够的作家通常不得不在表达时犯的错误)他辽阔地呈现了整个都柏林一九○四年六月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呈现了它们如何在地理上交织错落,呈现了上帝造世界般的秩序与运行。
借助那些令人发狂又令人不舍的繁琐注释,才能体会到乔伊斯式的意识流与伍尔夫式的意识流的不同之处,体会他宇宙般的辽阔。这是一本奇异的书,也许三十年来,你反复去读,都不能真正阅读,但有朝一日,你突然读了进去,就发现,你可以反复读,可以从任何一页开始读,每次都可以在阅读中得到不同的享受,精神的、技巧的、自省的。
现在,在乔伊斯中心里也放着一只旧式碗柜,敞开了的、漆成干净光滑的白色的、散发着复古趣味的。如今碗柜里陈列着乔伊斯中心出售的各种参观纪念品:明信片、书签、马克杯、钥匙圈、围巾和雨伞—都与纪念《尤利西斯》和它的作者有关,一切直截了当,不需要注释,但仍可以索引。所以,它们仍是擅长穿越时空的意识流发生与描绘的好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