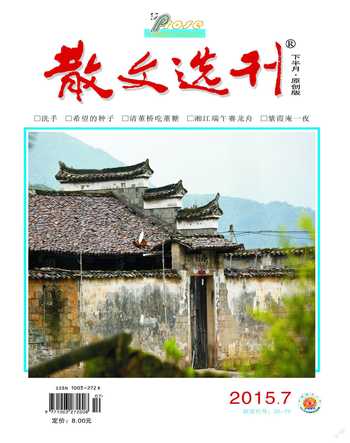洗手
2015-05-30朱以撒
朱以撒

每一次要摊开这些汉画像拓片阅读时,我都要认真地洗洗手,擦拭干净。其实指掌间已经很干净了,也还是要自觉地进入这么一个程序,算是从内心对前人作品的敬畏,还有崇仰。如果一天里要分几次阅读,那就要洗上几次手,使手在触及拓片时更有感觉。这些拓片有的很大,摊开时可以充满整个大厅,卷起来又如一大捆被子,一开一合,要费不少工夫——宣纸是最为脆弱的,总是要小心翼翼,“侍儿扶起娇无力”啊。再小心也会有磨损,有一些纸屑落下,有一些丝缕脱离。尽管手的动作已经轻柔之至,心里还是不敢松懈。那种隔着手套工作的做法,我一直不能适应,我执着以裸露的手对待这些旧时代的宝贝,生怕弄疼了它们。
这种习惯逐渐形成,对待古旧之物,大都如此。这些旧物是不可重复的,如果有人来,手上都是汗,或者手不安分,我就没有兴致拿出来分享。每一件古旧之物都是有自己的气息的,冷清的、平和的、朴拙的,却不会有时下的这么些气味。充满欲望的手一天到晚都在触摸着种种物质的皮表,要静下来阅读古帖古碑,慢慢地把玩一遍,还是需要洗一洗手,让手的温度冷却一些——这很像一个长长的过门,很郑重,很有必要。一个人在心理上做好了准备,接下来的由手展开的动作就会把分寸掌握得很好,至少不会失手。
精神洁癖——让澄澈的水来洗手,通常以此开始。生活习惯中对于洗手的要求,是在进食之前。要吃饭了,把手洗净,以免不洁的细菌随着指尖进入腹中——再草率地洗也比不洗要清洁,一个人的心理往往如此。这使得饭前洗手成为一种习惯,很自然地延续下来。一位农妇在不缺水的条件下让孩子们洗手,可能没有想到这是对自己劳动成果的一种尊重——一年到头的栉风沐雨,终于修成了黄澄澄的果实,进入了牢固的仓廪。有的时候,我在淘洗时,会有几粒金黄的小米跳到地上,我一定会俯下身来捡拾。很奇怪的是,如果白花花的大米掉落几粒,我还不会这么地迫切。我被小米的颜色所吸引,它们让我看了心动,那么微小,又那么灿烂,上苍给了它们这样的容颜,让人不忽略它们的存在。它们在等待收割的时候,一阵风来,随时会落入泥土的缝隙中,再也回不到谷仓里——还好,农夫手脚麻利,把它们从田野带了回来,无数的金黄颗粒,让人感到晕眩,把它们堆成金黄色的塔,高处的小米会扑簌簌地流动起来,像一道金黄色的河流。现在,它们从千里之外来到我的面前,每一粒都可以见出远大,岂能轻慢它们。一个人把手洗净了,坐在餐桌前,显然是沉稳的、端庄的。对劳动的果实抱有认真的情绪,缓慢地品咂,神色越发爽朗。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也是一种态度,只是劳动果实的滋味未能被细致地感受,不免有些粗率。大凡有洗手这个程序,整个行为都会克制一些、徐缓一些,以至于进程更为细腻、雅致。所谓斯文,洗手的动作也算一个吧。
很久以前,我和农民兄弟从田里干活回来,队里的妇女已经把饭做好,是少有的白米饭。那时候偶尔有这样的运气,生产队长觉得夏时盛热,收割与插秧并举,实在辛苦,便会拿出队里的粮食,让大家吃一次免费的晚餐。每个人把农具一扔,围着装米饭的大木桶,那支木饭勺从一只手急切地转到另一只手上。动作迅疾,使人处在一种期待之中——吃得饱是非常美好的。一切美丽之物都是吝啬的、有限的。很快,一桶白米饭就见底了。我相信还未吃饱的人端着碗走近木桶时,一定会有些绝望,因为他未曾料到如此短暂白米饭就消失了,把再吃一碗的热情企盼变成一片支离破碎——这一餐已经结束了。每个人的动作都很急,一下接着一下,赶路一般,这些动作的背后是忧郁的,无形的饥饿很快又会追了上来。这是一个来不及洗手的年代,手上都是泥屑,或者农家肥的气味——在田里干了整整一天,一个人的一双手触及到的物体有多少,可是,来不及洗手了。谁都知道,埋头把手洗得干净了,白米饭可能就吃不上了。孰轻孰重,一个肚里空空荡荡的人还是能分辨得清楚的。这里的人少有洗手的习惯,双手由于长期与泥土、农具摩擦,变得十分粗糙,手心手背的纹路就像旱地里的裂缝,尘泥嵌入其中,即便费力洗刷也无济于事,分不清哪一部分是皮肤,哪一部分是皮肤的附着物。只有到了夜晚,他们才进行大规模地洗涤,烧一锅临近沸腾的水——这样的温度让我十分吃惊,它显然超过了皮肤接受的限度。他们在简陋的澡房里,就用这样的水,细致而缓慢地搓动着,全体通红。这是一个农家劳力最舒心的时刻,也是他们最清洁的时刻,此时,动作非常之慢了。这是一个自我陶醉的时候,它和白日的辛劳形成了不同,日子正是在比较中逐渐推进。
从农村回到城市,我又渐渐恢复了洗手的习惯,我知道自己又要开始一些文人细腻的动作了,它们大部分是在纸面上进行的,洗手成为必然。
我回老家时,面对晚年的母亲,我会给她剪剪指甲,手指的,脚趾的。人老了,指甲也变了形态,如乱石铺街,凹凸不平,连坚硬的指甲剪都有些吃不消了。可是我别的做不了什么,就从指甲这等小事入手。剪完后母亲总会催促我去洗手,顺便把指甲剪也给洗了。在母亲看来,一件事和一件事之间的过渡,应该用洗手来区别,以示结束和即将开始。这样会使人在做一件事之前,有一些心理的、生理的准备。一个南方人的身体里附着了南方天地间大量的湿气,身体与北方人相比,可以挤出更多的水。下垂的双手,使身体的许多水汽往下端移动,最后储存在掌心和十指里。一个长辈注意了洗手这个细节,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他的下一代、再下一代。母亲总是把许多事情划分得十分清楚,她是一个善于细化的人。炊爨、涮洗是一种动作,快,麻利。接下来把手洗净,在狭窄的书桌前端坐,开始批改作业。一位农村的小学老师,面对的都是懵懵懂懂的少年,对作业的批改也尤其缓慢。煤油灯的火舌随着风的流动,闪烁着不定的光。清洁的手在作业本上移动,边改边把那些卷起来的边角抚平。对那些顽固翘起来的部分,母亲会在改完之后用一本厚厚的书把它们压住,放到第二天早晨,已是平整之至了。勤洗手是内心的需要,会更细腻一些,少一些粗率。在那些越来越热的夏天,少年的我有很多时间都在田园里奔跑,掀动墙边屋角的瓦砾,追捕蛐蛐,或者爬墙上树,弹鸟捕蝉,弄得灰头土脸。好在家中有两口老井,水量充沛,随时可以用清冽的井水冲洗,当一双手深入水桶的一刹那,脑袋清醒起来——不能老是这样子啊,应该要有一个新的走向了。
水依然这么清澈,喜欢洗手的母亲后来洗不动了,只能由别人用湿毛巾给她擦拭,由掌及指,再也不能体验亲自洗手的快感了。
我的计算得益于余先生的指导,好几年的时间里他帮助我用数字和公式建立一个抽象王国的秩序,使我从算术层次进入到数学境界。日常生活根本不需要如此复杂的逻辑、推理,小学阶段对于计算的掌握已经足够应对日常。只是我自己怀有进取的热情,拜他为师。我擅长文采,兴到偶然,管下春风,这方面长了,也就于数的计算过于愚钝,一题下来,离真相的答案总是很远。余先生则游刃有余,并以游刃于数字为快慰。不过他的日常生活却是浑沌一团,浸泡在阴翳之中——袖口总是油腻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而手是很少洗涤的。我一直以为他是以这种行为表达一种怀才不遇的情绪——在他的言说中,他认为自己的一生已经被毁掉了。我把解不开的题指给他看,他常常是这样,用手抓着食物吞咽,同时接过我的书、我的计算本,边吃边为我解题。他和他的太太似乎对咸带鱼很有兴趣,很多次是手抓咸带鱼进行指导的。带鱼的气味渗入了公式里、数字里,一本书渐渐成了气味的集合地,让人闻到气味,想起他强调指出的部分。他认为书是用来学习的,不是摆设,脏点破点无甚关系。余先生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我曾经对他的几本书进行修复,他认为毫无必要,他卷着书看,卷久了,成了环抱状再也舒展不开。由于他的不洗手,他看过的书都是不清洁的。他是不应该只成为一个普通的施工员,管理我们几十号民工,他应该是工程师那个级别的,儒雅斯文,运筹帷幄,手下一批精英在他的调度下,合力攻克着某一个难题。那个时候,他一定是坐在敞亮的办公室里,衣着光鲜,指腕清洁,有一种庖丁解牛后的得意。
洗手,也是需要情绪的。
庸常日子里的忙乱双手,每一日都在大量地抚摸之中。每一个被抚摸的对象都是有温度的,冰冷的、热烈的、粗糙的、细腻的,感受着它们在节气推移下的变化。如果没有什么禁忌,面对物体,每个人都会发出许多抚摸的欲望,抚摸使内心有了把握,判断也随之准确。在我举办书法作品展览期间,就有不少人伸出手来,或轻或重地抚摸那些汉画像拓片——他们的双眼茫然,只好用手来感受。这使我生出许多不安,他们不想通过学习来提高自己的见识,而是直接动手,似乎手能解决所有的疑窦。手的热爱抚摸,加上洗涤,渐渐粗糙起来,每个人都会察觉夏日与冬日皮肤层面上的细微之变。手套应时而出,像极了人的手形,或大或小,适宜人类所有的手。上课的时候,我见到几位女生戴着手套,执笔书写。我让她们都扯下来,让赤裸的手直接和一支笔产生联系,让那些隐藏在指掌间的敏感,重新回来。我不知道一个人戴着手套,怎么可能感受毫端在宣纸上提按、快慢的回馈,一切行为还是略去一些装饰才能存储优雅。一个想亲近古贤人的少年,吝惜自己的手,担心墨汁弄黑了手,担心冬日里的水过于寒冷,以为隔着薄薄的手套追寻古人并无不妥,实则是太自以为是了。一群人在看旧日字画,一律戴上了手套。目光尽可以随意,对一双手却提出了要求——必须隐藏在手套内部,以保证抚摸时的安全。这些手套百人戴,千人戴,内部外部早已不洁,可是没有办法,规定如此死板。如果一个人洗净了手,开合卷轴时,会对纸本的轻重、顺逆分寸把握得默契一些、周全一些。净手的低调而柔和的抚摸,被旧日的纸上纹路牵引着,进入内心最隐秘的深处。手套对于手来说,就是一层蒙翳,捂在里边久了,蔫了,不活络了,把它抽出来,洗洗,就生动起来。
又一个夜晚到来。我先是洗了一次手,坐下来整理一篇文稿。然后又洗了一次手,站着临写《杨淮表记》里的几个字。洁净的手指灵动地引导着柔韧的羊毫,点线简劲而出。我一直以为学书者不可不知汉隶,它是一个人笔下的筋骨,让一个人行笔时有了底气。接着,我又洗了一次手,意味着今夜的临写结束。
每一次洗手都是很有意义的——一个片断的开始,或者一个片断的结束,可能有递进的关系,也可能毫不相干,却都由于洗手的进行变得郑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