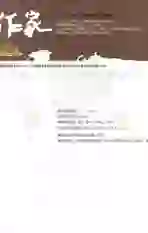《饥饿游戏》中“乌托邦”母题的继承与超越
2015-05-30王文蒲
摘要: “乌托邦”是西方文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母题。反乌托邦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乌托邦文学的结构,但在思想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因此其应该被视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苏珊·柯林斯的《饥饿游戏》问世以来常被冠以“反乌托邦”小说的标签,但实际上它更加倾向于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本文将从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关系入手,分析这部作品所具有的现实主义性。
关键词:苏珊·柯林斯 《饥饿游戏》 乌托邦 反乌托邦
《饥饿游戏》是当代美国作家苏珊·柯林斯的力作,目前已经被改编成电影,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轰动的影响。这部作品最初被视为青春文学,后有学者指出,其具有反乌托邦性,从而将其定性为“反乌托邦”小说。尽管它在结构上继承了“乌托邦”,但是在思想上更加具有现实性和批判性,因此其更加倾向于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只是披着乌托邦的外壳。
一 乌托邦与反乌托邦
“乌托邦”是西方文学一个十分重要的母题,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乌托邦”一词是由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托马斯·莫尔所创造的,“乌托邦”是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在那里人人平等,财产公有,按需分配,可以说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地方。“反乌托邦”则是一个由学者所创造出来的术语,它所针对的并不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而是资产阶级所宣扬的美好社会。例如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所针对的是以“美国梦”为核心的科学主义社会观,即认为科学技术将为人类创造出一个美好的未来。由此可见,“反乌托邦”和反资本主义具有紧密的联系,它所针对的并非是托马斯·莫尔的《太阳国》。事实上,托马斯·莫尔的《太阳国》也是一部反资本主义的革命作品。可见无论是乌托邦还是所谓的“反乌托邦”都是基于对于当前政治及由其所提供的人类救赎方案的否定而产生的。因此所谓的“反乌托邦”应当被视为“乌托邦”的一个变种,而不是它的对立。长期以来,“反乌托邦”被标签化,大量的科幻小说往往被冠以“反乌托邦”的标签。这种做法是非常简单和粗暴的,会直接影响到文学评论的准确性。
为了进一步说明“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的关系,笔者将引入一个新的术语“非乌托邦”。“非乌托邦”思想源于当代法国思想家齐奥朗,在《历史与乌托邦》一书的开篇,齐奥朗这样写道:“我想为乌托邦申辩,但当我阅读不同版本的烏托邦时,我却说乌托邦是不可能的。”齐奥朗从根本上否定了乌托邦,否定了所有的救赎模式,也有学者称齐奥朗的这种思想为“非救赎伦理学”。基于“非救赎伦理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乌托邦的特征之一是它信仰救赎。无论是托马斯·莫尔,或是赫胥黎,或是乔治·奥威尔,对于救赎他们是有信仰的。即便在最为恐怖的反乌托邦小说中,救赎仍旧是存在的。只要相信救赎,认为救赎存在,那么乌托邦和反乌托邦就没有实质上的差异,只是表现形式的不同。乌托邦和反乌托邦都只是针对某种救赎方案的否定,例如技术救赎、宗教救赎、伦理救赎及政治救赎等。尤其是所谓的反乌托邦小说,它的出发点基于的是一个错误救赎方案所可能引发的恐怖状态。它本质上,仍旧是乌托邦的,它所要反对的,不是美好社会,而是怀疑实现美好社会的模式。虽然它名为反乌托邦,实际上它并不反乌托邦。而真正可以被称之为反乌托邦主义的,反倒是以齐奥朗为代表的“非乌托邦”。“非乌托邦”实际上有着十分深刻的历史渊源,其最早可以追溯到第欧根尼的犬儒主义。第欧根尼正是处于对于一切救赎的绝望,才会提出“像狗一样活着”的口号。
二 集中营与“饥饿游戏”
《饥饿游戏》自问世以来,引发了极大的关注,拍摄成电影后,更是在全球范围内风靡。问世之处,其被贴上青春文学的标签,但其深刻的政治隐喻,显然超出了青春文学的范畴。此后,有人将其归类为“反乌托邦”文学,主要理由是其所描述的是一个黑暗的未来社会。这种做法,显然也是标签式的,并且非常简单粗暴。从形式上来看,《饥饿游戏》的确具有“反乌托邦”的某些元素,例如未来社会,极权政治。但是相比其他“反乌托邦”小说,例如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扎米亚京《我们》等,其所具有的“反乌托邦”气质要薄弱很多,后者将“反乌托邦”社会形成的原因归结为技术过度,而前者则是人类政治走向极端状态的结果。事实上,人类政治走向极端并非是一种虚构,而是现实存在的。苏珊·柯林斯坦言,她的创作灵感源自于电视媒体中的真人秀和战争报道,从中她看到一种极端政治的新形式。此外,《饥饿游戏》中的帕纳姆国,与其称之为国家,不如称之为纳粹集中营。因此,这部作品并非是完全虚构的,其真实性远远超过它的虚构性,这种真实性赋予这部作品一种史诗气质。
不得不说,苏珊·柯林斯对于当代政治的预判是相当准确的。正如当代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所言的那样:二战之后,我们都生活在集中营里。或许乍听到这种说法,会使人产生猛然一惊的感受,然后认为这只是理论家的危言耸听。但如果仔细思考一下的话,一定会发现阿甘本这种判断的精确性。资本主义从诞生之日起,便开始了它的全球化运动。从早期的殖民地到纳粹集中营,其发展过程始终贯穿着一条资本逻辑。在“赤裸生命”系列种,阿甘本采用了一种谱系学的方法,追溯了“生命”是如何一步一步被剥夺掉权利,最终沦为资本生产的基础性资料。不同于一般人的看法,纳粹集中营,并不仅仅是一个关押犹太人的场所,也不仅仅是一个屠杀犹太人的场所,它是一个庞大的生产机器,那些被屠杀掉的犹太人,在纳粹看来是多余的,是垃圾,他们只是被清理掉了。而那些有用的犹太人,被充分地调动起来,从事各种生产活动,为纳粹政治机器提供动力。回到小说中,帕纳姆国也是这样一种类型的政治机器。在十三区发生暴动时,中心城凯匹特动用自己所有的科技力量对其实施了毁灭性的打击,这种做法和纳粹实施大屠杀是如出一辙的,是在宣示主权。但这种宣示效应是非常短暂的,如果不能持续下去,必然会引起新的反叛。为此,帕纳姆的统治阶级创立了“饥饿游戏”。正如福柯所言:谁掌握生命,谁掌握了权力。的确,没有比生杀予夺之权,更加令人感到畏惧。让各区人相互厮杀,还能起到分化瓦解的作用,真可谓是一举两得。尽管统治者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但是集中营里的赤裸生命是不可能永远乖乖就范的。
凯特尼斯,一个貌似普通的女孩,她的出现,预示着凯匹特政治的终结。回到福柯提出了那个著名的命题,谁掌握生命,谁掌握权力。凱特尼斯,从一开始,就是自己生命的主权者。虽然,有残酷的禁令,但是为了生存,她一次又一次地冒险出去狩猎,从而练就了超凡的射箭技术。在妹妹被选为贡品时,她挺身而出,她选择死亡的同时,意味着她掌握自己的生命,因为死亡是内在于生命的,因此也就意味着她掌握了权力。在比赛结束的最后时刻,两者之中只能有一人可活之时,她选择死亡,由此直接否定了凯匹特对于她生命的操控。她的否定,不只是游戏规则的例外,同时也是主权的例外。因为这样一个例外,主权存在着崩溃的危险。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凯匹特的统治者,只能临时修改规则,但是这种修改一旦做出,意味着主权不再是主权了。虽然,临时修改规则,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凯特尼斯仍旧是一个巨大的隐患。为了消除这个隐患,凯匹特的统治者重启“饥饿游戏”,试图修正这个错误,由此修补主权的裂隙。
三 乌托邦与救赎的不可能性
约翰·格雷曾说:如果非要定义“西方”的话,它的历史是寻找救赎的历史。同样,帕纳姆的历史也是一部寻找救赎的历史。在帕纳姆成立之初,对于救赎的寻找便已经开始。第十三区的反抗,可以被视为公开寻找救赎的第一步。第十三区的失败,对于其他十二区的人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甚至是绝望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甘愿接受“饥饿游戏”,由此换取生存物质。但凯匹特不是一个绝对的存在,它不是上帝,它的主权不是无懈可击的。因此,它不可能永远地凌驾于人民的头上。
与“救赎”紧密相关的是“救世主”。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西方文明,即基督教文明是基于“救世主”而产生的,因此西方人将耶稣诞生之年作为公历元年。但是有“救世主”就一定能够得到救赎吗?自耶稣诞生至今已经有两千多年,西方世界得到根本上的救赎了?显然没有。从十字架到集中营,人类仿佛在走向更加深渊的恐怖而非天堂的救赎。原因何在呢?恰恰是那个令人期待的“救世主”。谁是“救世主”呢?如何确认“救世主”呢?当代法国思想家巴迪欧在《圣保罗:普世主义奠基》一书中指出,真正创立基督教的不是耶稣,而是圣保罗。耶稣之死是一个毁灭性的事件,如果不是圣保罗,基督教将不可能继续下去。而圣保罗做的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确认了耶稣的“救世主”身份。同样,在《逃离十字架》中齐奥朗指出,耶稣之死只证明了耶稣的信仰,并未证明耶稣是“救世主”。由于“救世主”的不确定性,救赎也变得不可确定。
回到小说中,凯特尼斯从未想过要成为救世主,也从未想过要救赎,她只是凭借着本能地求生意志在战斗,凭借着本能的善良在行动。在这个过程中,她获得了主权权力,她成为了一个主权者。但是她从未想过要利用这一点。虽然她不想利用,但是反抗军想要利用,最终反抗军将她打造成“救世主”,即“嘲笑鸟”。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中,凯特尼斯也经历了一次类似于耶稣的死而复生,由此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救世主”。
同耶稣不同,凯特尼斯这个救世主是高度世俗化的,她一直在战斗的最前线,而不只是作为一个精神性的存在而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凯特尼斯是坚持群众路线的,她始终与群众同在。当反抗军领袖科恩背叛群众,走上独裁之路时,凯特尼斯将正义之箭射向了他。正如上述一再提到的那样,她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主权者,她甚至比科恩更加有资格成为凯匹特的新主人。但是,她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回到群众中,过简单而平静的生活。凯特尼斯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她对于政治救赎的绝望,她藉由这种非政治的救赎实现了一种救赎。此外,她的这种救赎是具有现实性的,而非是乌托邦式的。当代法国思想家拉坏勒在《未来-基督》一书中提出这样口号:未来人人都是基督,人人都是救世主。解放人民,就是让人民成为基督,成为救世主。世界是人民的,而不是统治者的。正如马克思所言,无产阶级只有在解放全人类之后才能真正的解放自己。同时,无产阶级要保持斗争的力量,正如小说中的凯特尼斯,她时刻准备着和独裁者进行殊死地斗争。
综上所述,苏珊·柯林斯的这部作品,并非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而是一部具有乌托邦气质的政治批判小说。柯林斯在继承传统乌托邦小说母题的基础上,融入了当代政治哲学的最新成果,从而将乌托邦文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 蒋晓丽、王志华:《娱乐至死·虚实互构·全景监狱——论〈饥饿游戏〉中传媒技术的文化影射》,《当代文坛》,2014年第3期。
[2] 陈欣:《〈饥饿游戏〉反乌托邦主题解析:从小说到电影》,《四川戏剧》,2014年第5期。
[3] 冯晴:《〈饥饿游戏〉的反乌托邦书写》,《世界文化》,2014年第11期。
[4] 谭言红:《模拟自然中的生死历程:〈饥饿游戏〉中的叙事序列分析》,《英语研究》,2013年第1期。
[5] 王婷:《大众娱乐时代的电视真人秀:〈饥饿游戏〉及其当代隐喻》,《文化纵横》,2015年第3期。
(王文蒲,成都工业学院外语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