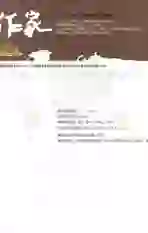《喜福会》母女关系之跨文化解读
2015-05-30张妍丽
摘要: 本文以霍尔的语境文化理论为依据对著名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进行跨文化解读,从而找出作品中母女两代人所各自代表的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原因,探讨双重文化对母女关系的影响。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我们珍视本国文化的同时,也应扬长补短,吸取其他国家优秀文化的精髓。
关键词:喜福会 母女关系 高低语境文化 跨文化解读
一、引言
《喜福会》是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的成名作,书一面世即大获成功,影响深远。关于《喜福会》中对双重文化以及母女关系分析的文章很多,对其的主要研究方向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喜福会》主题的分析,从语言学角度探析《喜福会》中的文化冲突;论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华人的文化认同问题等;关于对《喜福会》中女性价值的研究;对女性的民族身份的认同的研究等。本文着重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与高低语境文化角度对《喜福会》中的母女矛盾冲突进行分析,剖析第一代中国移民和她们的后代遭遇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文化的碰撞,及碰撞过程中女儿们对母爱的困惑以及母女关系最终走向和谐的过程,即中西两种文化由冲突到交融的过程。
二、高低语境文化及其特点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T·霍尔在1976年出版的《超越文化》一书中提出世界上的文化是复杂的,同时也是有一定规则的[1]。文化具有语境性,霍尔认为任何事物均可被赋予高、中、低语境的特征。高语境事物具有预先编排信息的特色,编排的信息处于接受者手里及背景中,仅有微小部分存于传递的讯息中。低语境事物恰好相反,大部分信息必须处在传递的讯息中,以便补充语境中丢失的部分。高语境中语义的承载主要不是语言性的,而是非语言和语境性的。绝大部分信息或存于有形的语境中,或内化在个人身上,极少存在于被编码的、清晰的被传递的讯息中。语义主要从存储的非语言及语境中衍生出来,信息不是包含于语言传输中。高语境中的信息解码更多地依赖交际者双方共享的文化规约和交际时的情景,高情境文化强调了沟通所在的情境;它们非常注意含糊的、非言语的信息。低语境的传播刚好相反,是“大量的信息蕴含在清晰的编码中”[2]。低情境的文化不太强调沟通的情境;它们所依赖的是明确的言语沟通。强调个人的主动性和个人决策。
霍尔的研究在跨文化交际领域的理论价值是显而易见的。霍尔通过研究得出结论:“中国有着伟大而复杂文化,处于高语境一方。高语境文化下的成员由于长时间身处同一文化背景下,成员获得知识的来源和途径相同,遵循着一样的传统,无需细节信息就能相互理解对方试图表达的意思,并作出恰当回应,所以通常不会出现沟通障碍。在人际交往中,成员间擅长借助共有的“语境”以及手势和表情表达感情和传递信息,即间接交流,含蓄隐晦。在书写和言谈中倾向于间接的风格,再三铺垫却不直接切入主题。依赖信任或直觉的引导,推理也倾向于迂回或间接的方法。高语境文化深深扎根于它的历史中,是一种统一连贯的文化,因此高度稳定并且变化速度较慢。
低语境文化的成员则由于缺少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很难形成非语言的沟通,他们在交往中必须更多地借助清晰直接的符号编码信息。低语境文化是个人主义导向的文化,强调自我和独立意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在低语境中,语义的主要载体是语言本身,非语言的及语境性信息对语义的影响是有限的,语义主要包含于进行交际的语言中。低语境中的信息解码主要在言语中,对语境的依赖性小,更倚靠坦率直白的方式进行沟通,写作或语言交流时他们倾向于开门见山。并其低语境成员性格外向,热衷自我表现。
当高、低语境文化遭遇碰撞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交际中的尴尬。《喜福会》中有个经典的片段——韦弗利携男友里奇参加她父亲的生日晚宴时,妈妈钟林冬对自己做的菜评价道:“这个菜太淡了,没味儿,可能不太好吃。”同处高语境文化中的人都能领会这是中国式谦虚,往往期待的是大加赞扬的回应。而来自低语境文化的里奇完全不能领会这层涵义,领会为“既然淡了,只要放点酱油就可以了。”并把酱油直接浇在鱼上,令大家瞠目结舌,更令钟母差点气晕。这种交际中的尴尬冲突的根源就在于高低语境文化的差异性。
三、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和东方文化中的集体主义
美国文化则具有低语境特性,文化成员倾向于低语境传播,属于个体主义文化。低语境文化的成员将自己看作是独立、自立的,鼓励人们追求个人的幸福和自由,人与人之间关系相对松散。孩子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学会自己思考,自由表达观点,自己做出选择,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美国是一个崇尚自由和个性张扬的国家,非常重视“自我”。在美国父母与子女是平等的,父母对子女没有绝对的权威。喜福会中的女儿们就是典型的“ABC”,在低权力距離文化的美国出生、长大,虽然是华人的外貌,骨子里受的环境教育熏陶却是美式的,接受美国文化的价值观,对中国母亲们的严格管束自然是一味反抗。所以当母亲们以忠孝观念要求女儿时,女儿们觉得不可理解,认为母亲的言行限制了她们的自由,阻碍了她们个性的张扬。
对于语境的依赖使得高语境文化成为一种集体主义导向的文化,加上深受五千多年儒家文化的影响和熏陶,高语境下的社会成员从出生起就会自觉将个体划入各种团体,“家族”“民族”“国家”,等等,相互依赖,相互合作,追求与周围环境“相一致”“相和谐”,竭力回避对立冲突,重视亲密与和谐更甚于个人目标。由于崇尚的是集体主义文化,爱国主义很重要;提倡凡事以家庭、社会和国家利益为重,个人利益在必要时可以牺牲,“集体观念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一个人的能力往往代表他所属群体的群体价值。成功之时,个人往往把功劳归于集体、环境和他人的帮助。因此在中国文化中,“关系”也变得空前重要。这样长期发展的结果是他人取向,即非常在意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也就是“要面子”,习惯谦虚忍让,“万事以和为贵”。因为过分强调自我压抑,外国学者甚至认为在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下中国人没有“自我”。
四、《喜福会》中文化冲突的体现
中国父母把孩子看作生命的延续,尤其希望孩子能实现自己未了的心愿,可谓是世界上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喜福会》中母亲们对女儿们费尽心血,做出典型的、伟大的中国式牺牲,但要求女儿们遵从自己的教导;而耳濡目染西方文化的女儿们却抱怨母亲干涉自己的生活,桎梏自己的自由。韦弗利的母亲虽然对下棋一窍不通,但在女儿练棋时,习惯地站在她身边陪伴。在中国文化里,这种付出是理所应当的,能体现家庭成员对一个人成功的重要性(支持)。而当女儿成功后母亲逢人就炫耀时,却引起女儿的极大不满。母亲是将女儿和自己视为一体的,荣辱与共。而在女儿韦弗利的角度看来,母亲的付出完全是不必要的,她不能理解这种“牺牲”;炫耀更像是“喧宾夺主”,她认为成功完全是自己奋斗得来的,是个人价值的实现,与他人无关(哪怕这个“他人”是自己最亲近的母亲)。她没有中国式的光宗耀祖的观念,所以质问也就冲口而出:“为什么你非要拿我出风头?如果你自己想出风头,你为啥不自己学下棋呢?!”这一典型的美国式言辞却深深伤了中国式母亲的心——女儿的话简直大逆不道,接下来的母女冷战进一步引发了一系列矛盾。这种冲突在韦弗利长大后依然存在——母亲经常不打招呼直接去女儿家——母亲认为母女是一家人,女儿的家就是自己的家;而在女儿眼中,她的隐私权受到侵犯,哪怕对方是母亲也难以忍受。女儿最后忍不住建议母亲以后先打电话再来,而她的话深深伤了母亲自尊,因为要一个长期在集体主义环境下长大的母亲如何理解和接受连去女儿家都要“提前预约”?母亲以后便再不登她家门了。
吴夙愿和吴精妹的矛盾也是如此,母亲为了女儿能够成材,到钢琴老师家“义务打工”以换取女儿每周一次的钢琴课和免费练习,然而女儿却对母亲的这些牺牲不以为然,并不领情。觉得母亲只不过想像捏橡皮泥那样,把自己塑造成她自己想要的样子。她痛恨母亲的“摆布”并喊出:“我不是你的奴隶;这里也不是中国!”“你要把我变成我自己不喜欢的人,你希望的那种女儿,我永远也不当!我不希望做你的女儿,我希望你不是我的妈妈。”为了抗议母亲逼自己练琴,她甚至不惜揭开母亲心底深处的伤疤来“反击”——母亲在战乱离开中国时被迫抛弃尚在襁褓中的孩子的伤心旧事。
看似不那么激烈的矛盾也存在于安梅和徐露丝中间。当安梅发现女儿在办离婚手续时,居然寧愿找一个外人倾诉(实为咨询)都不向母亲倾诉心事,觉得心里受伤了。但女儿的立场却是,婚姻完全是夫妻两个人之间的事,不需要任何人插手,这无疑导致了母女间的深深隔阂。正如母亲钟林冬所言“我希望在孩子身上看到美国的环境和中国人的性格完美地结合起来,可我万万没想到这两样东西是无法相融的。”母亲顾映映则说:“女儿和我之间似乎隔着一条河,我永远只能站在对岸看着她。”
乍一看,这些母女矛盾被称为代沟,实则不然,这恰恰是典型的中西方思维差异带来的文化冲突和生活在文化夹缝中的母女们遭遇的矛盾和困惑。《喜福会》的母女冲突是典型的高、低语境文化的冲突,同时也是母亲们所代表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忠孝”的观点与女儿们崇尚的美国文化中“自由平等”“自我为中心”的“个人奋斗”发生的文化冲突。《喜福会》中的母亲们来自旧中国,作为第一代移民美国的华裔,骨子里牢牢打着几千年儒家文化的烙印,并试图通过家庭教育将这种传统文化传承给子女们,以维系和祖国的精神联系。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家庭”既代表着家长对子女的权力,又意味着家长与子女相互依赖的温情关系。中国儒家文化提倡“百善孝为先”,家长是绝对的权威,子女反抗为大不孝。这种思想上的差异使得双方都很痛苦和困惑。究其根底是高语境文化出身的母亲们的教导得不到生长在美国低语境文化中的女儿们的理解。
五、文化冲突碰撞后的最终和解
幸运的是,《喜福会》中四对母女关系的冲突最后都以不同的方式达到了和解。吴精妹回到中国与自己同母异父的双胞胎姐姐相见,完成了已去世母亲的遗愿;韦弗利打算带着母亲去中国度蜜月;丽娜在母亲的支持下终于正视自己的婚姻,勇敢地摆脱了“宿命”(母亲的命运一定也是女儿命运),重新找到了幸福;而徐露丝则在母亲的开导下重拾了自信,在离婚时大胆争取自己的权益。母女之间关系从“严重隔阂冲突”走向“妥协理解”代表着中西文化和价值观的相互认同,实现了真正平等交流。
当今世界各民族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高语境文化的中国与低语境文化的美国之间的文化冲突比较典型罢了。赛义德认为“一切文化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孤立单纯的存在,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内部千差万别的。没有哪种文化是绝对的高语境文化或低语境文化。”所以,对待文化最好的态度就是继承本土文化,又能以开放的心态看待异质文化,理解尊重它,用平等宽容的态度试着接纳它,才有可能消解文化冲突,使世界文化走向“大同”[3],真正实现不同文化的大融合。
参考文献:
[1]谭恩美、程乃珊等译:《喜福会》,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2]Hall:《Beyond Culture》《NewYorkPress》,1976年版。
[3]程爱民、张瑞华:《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喜福会》的文化解读》,《国外文学》(季刊),2001年第3期。
(张妍丽,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