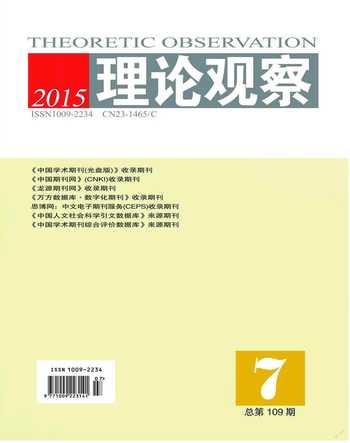政治学视角下马克思理性观的转变
2015-05-30赵根
赵根
[摘 要]对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家的理性主义思想,马克思有着前后截然相反的态度。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出发,分析马克思对于近代理性主义思想的推崇和批判,探索其理性观转变的实质。
[关键词]马克思;理性主义;推崇;批判
[中图分类号]A81;B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7 — 0011 — 02
理性主义思想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产生,当其发展到中世纪,由于教会的封建统治,经院哲学的盛行,信仰主义取代理性主义,占据着绝对权威的地位。启蒙思想家和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家对于理性主义回归的呼唤对打破教会的封建统治,发展资本主义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绝对理性盛行,诸多社会问题逐渐暴露,理性主义者宣称的自由王国与现实形成强烈反差。因此,对于近代理性主义思想,马克思由推崇转向批判。
一、 马克思对理性主义的推崇
马克思在早期的著作中一直把理性当作法、国家和社会存在的基础。我们从马克思对宗教的非理性基础的批判、对黑格尔理性观的继承以及对科学技术的称颂之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对理性主义的信仰〔1〕。马克思认为,“不应该把国家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而应建立在自由理性的基础上”,因为在他看来,国家和法的本质是自由理性,是合乎理性的存在。“国家只要成为理性的国家就足够了,不必要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那时,国家只要从人类关系的理性中产生出来就可以了。”〔2〕马克思坚持无神论的坚定立场,对宗教神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揭示了其无理性的实质,从而动摇了宗教维持社会现状的功能,瓦解着宗教神学对人们的精神束缚。
马克思对理性主义的信仰和推崇还突出表现在他对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称颂上。他认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而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好准备”〔3〕。马克思通过对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的高度肯定,表达了对人的精神和力量的高度自信,无疑是对理性主义的信仰与推崇。
马克思之所以对理性主义如此推崇,是因为理性主义从理论上论证了教会封建神学的荒谬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迎合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4〕
中世纪以来,欧洲处于封建教会的黑暗统治之下,天主教把对上帝的信仰视为至高无上的原则,要求人们的理性必须服从对上帝的信仰。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的出现,新兴资产阶级越来越强烈的感受到封建神学对自身的束缚,感觉到教会的封建统治对确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阻碍。新兴资产阶级明白,要想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市场经济,就必须解决两大问题。一是思想上要冲破封建教会的神学统治和经院哲学对人们的精神束缚,解放人们的思想;二是要使人们摆脱对封建主和教会的人身依附,获得人身自由和应有的人格尊严,在经济和政治上平等自由,解放人们的身体。
于是,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人文主义者极力宣扬要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充分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呼吁个性解放,提出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而人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主体,崇尚神学纯属愚昧无知。但丁在《神曲》中率先明确表达了对教会的厌恶和批判。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之下,许多自然奥秘纷纷揭晓,新兴资产阶级更有信心,在欧洲大地上掀起了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拿起理性之武器与封建教会的专制统治和神学思想做坚强的斗争。他们要求建立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用“天赋人权”对抗“君权神授”;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贵族等级特权。伏尔泰更是呼吁“每个人都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同骇人听闻的宗教狂热作斗争”。从此在西方哲学的历史长河中,理性主义取代信仰主义成为主旋律。这时,“哲学中理性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正是资本主义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和资产阶级这个新兴阶级形成和发展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5〕。
二、马克思对理性主义的批判
理性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理性主义哲学家们用理性所论述的国家和社会也成为人们心中向往的理想国家和社会。但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理性逐渐沦为资本主义的统治工具,社会一度陷入危机和困境之中。人们发现所谓的理性主义自由王国遥遥无期,失望情绪充斥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角落。正如马克思所述,“理性的社会和国家所带来的不是理性主义思想家所预言的人的普遍幸福和人性的充分发挥,而是种种痛苦和灾难以及人性的异化。理性在资本主义上升和革命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灿烂光环变得越来越暗淡,人们对启蒙思想家所讴歌的理性主义精神也越来越失去信念”〔6〕。恩格斯则更加直接地道出了实质“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7〕
马克思之所以会发出如此失望论调和对理性的批判,是因为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一系列令人失望的画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日益严重的失业,人们的感情生活越来越淡薄,精神危机日趋严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人们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等等灾难性后果。难怪恩格斯也认为,资产阶级思想家和革命家所倡导的理性至上原则在实践中却完成了“一副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早在运用自由理性为武器审视当时的德国社会政治现实时,马克思就因物质利益的困惑对理性产生了怀疑。马克思发现,在当时即将制定的林木盗窃法并不是由自由理性的法律所支配,而是由物质利益,尤其是少数人的物质利益所决定的。而且所谓的伦理理念和与伦理理念一致的公共利益也没有在林木盗窃法中有所体现。马克思坚持自己的理性立场,认为法律应该是事务法的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但是林木盗窃法还是颁布了,所以马克思只好无奈的表示物质利益总是占法的上风〔8〕。由此,马克思对理性主义思想便产生了怀疑,加上后来日益严重的资本主义社会困境和危机,马克思对理性主义提出了愈发无情的批判。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拉大等种种困境与危机,是因为资产阶级对理性力量过于依赖、对人类能力过于自信,妄图用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的不懈努力征服自然,战胜一切困难,从而建成他们所向往的社会。结果导致科学技术的滥用,人们伦理道德日益败坏,私欲膨胀,工具理性的极度张扬和价值理性的几近沦丧,理性俨然成为人们谋求自身私欲的冠冕堂皇的借口。马克思认为,万事万物的生成和发展都有着客观规律,物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物质,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必须要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所以,理性主义者宣称的理性并不能为所欲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是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加上剩余价值理论对资产阶级无情剥削无产阶级秘密的揭露,马克思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并且坚定了共产主义社会必将实现的信念。这一切,都是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与否定。
三、马克思理性观转变的实质
马克思由先前的对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的讴歌,转变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端和资本家丑恶嘴脸本质的揭露,实际上反映出他对理性主义思想的倍加推崇和无情批判这一前后截然相反的态度转变。这一思想的转变,源于马克思对现实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状态的观察和感受。理性主义者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自由王国的美好愿望被现实碰撞的粉碎。马克思看到的是,资本家为了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对工人无情的剥削与欺诈,人们由先前的封建主附庸转而沦为机器的附庸。广大无产阶级无法摆脱失业与饥饿的噩梦,更别提在政治上谋求些许应有的基本权利,“天赋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他们面前早已变成冷冰冰的讽刺。马克思立足资本主义社会的困境和无产阶级生活的现状,用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慷慨激昂的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实现。
马克思坚定的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有着客观规律的,人类决不能以自身理性为所欲为,资产阶级在肆无忌惮发展的同时必将为自己掘好坟墓,而广大无产阶级必将建立一个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按需分配、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大同社会。马克思俨然成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代言人,表达出了无产阶级想表达而不会表达的真实利益诉求,他宣称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要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不懈奋斗。马克思在批判、否定资产阶级理性主义思想的同时,却利用自己的理性构想出一个对于无产阶级而言的美好“理性王国”。这又逃不脱推崇自己理性的嫌疑,这样马克思就陷入了前后矛盾之中。而且,当马克思用剩余价值理论揭露资产阶级剥削秘密、用唯物史观论证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时候,他只能证明当时资产阶级制度的种种不合理,甚至是必然灭亡的,但是对于自己所坚信的共产主义社会可实现性的证明,马克思也无法说服所有人,只有等到后世来证明。他自己也不敢保证,自己当时所坚信的理想社会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会不会异化,会不会像当时资产阶级社会一样为人诟病。
作为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正为着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实现,一代又一代的努力着。虽然历经曲折,但我们始终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向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努力奋斗。
〔参 考 文 献〕
〔1〕衣俊卿.论马克思从传统理性主义向现代理性主义的转变〔J〕.浙江学刊.1992,(0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 马荣艾.马克思视域中的近代理性主义〔J〕.巢湖学院学报.2006,(02).
〔5〕〔6〕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7〕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
〔8〕关锋.论马克思的实践理性〔D〕.广州:华南师范大学,2005.
〔责任编辑:谭文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