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忆征程 (5)
2015-05-20刘仁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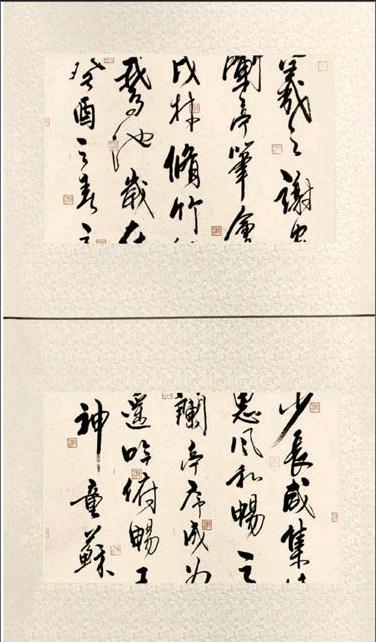

第二十一回
闯荆州,无暇顾及古遗址 走胡集,钟祥行长寻亲人
八十年代中后期,我们跑项目多了起来,一是领导放心可以独自放飞,另一方面也是国家及总行对重点项目的高度重视。那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出发前要认真准备,包括情况,问题,变化等等。庄心一负责石油,我负责化工,荆州有我经办的荆襄磷矿,也有他经办的江汉油田,我们俩在86年曾一同去了钟祥。胡集是个小镇,距离荆襄磷矿所在地王集还有几公里路程,关键是矿区通往胡集的路是泥泞的土路,打个来回不只是累,而且还会一身泥。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利用中午时间跑了一趟,我们都有插队经历,走个十里八里的不算什么。胡集集市挺大,农副产品十分丰富,特别是像莲藕、菱角、菜苔、鸭蛋等湖北特色菜蔬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也就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了菜苔,而且分为紫菜苔、绿菜苔。这趟胡集之行,让我们想起当年知青和兵团生活,那天我们聊得最多的就是农村岁月。
在钟祥县支行,鲁行长接待了我们。他开口就问,认不认识他儿子?我们问是谁?他自豪地说:鲁可贵。我们大吃一惊,怎么也想不到,在钟祥县能遇到我们的亲人。
第二十二回
云浮行,纪检组长太低调 乱弹琴,我与元章同房间
前面提到我与任行长去广东,那次同行的还有总行党组成员、纪检组长赵元章同志。元章同志是牟平人,任行长是海阳人,都是烟台老乡,在早年又长期在任行长手下工作,因此,元章同志坚决要求参加这次考察。
说那时没有统一法人的说法,还真的有事例佐证。我们到了云浮硫铁矿听过了汇报,午饭后在矿招待所小憩,到了房间门口,看见门上贴着客人的名字,一间写着“总行任行长”,一间写着“省行杨行长”,第三间写着“赵元章、刘仁刚”。你说当时总行党组成员就七位,怎么连赵元章是谁分行搞接待的同志都不知道吗?元章同志非常低调,说到没关系的,就休息一会儿,但分行杨行长的脸可挂不住了,他把接待处的小陆叫到身边,严厉批评道,这位是总行纪检组长赵元章同志,是总行行级领导,怎么能两人一屋呢?还是我跟小刘一个屋吧!再三退让,总算是进屋休息了。看得出,接待处的小陆一直没反应过来,在他心里杨行长理所当然应该独立一间,以前不是一直这样安排的吗?怎么这个纪检组长比杨行长还“横”呢?
元章同志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反倒是我却感到浑身的不自在。
第二十三回
小片会,数个皮匠凑诸葛 太阳岛,交口称赞吃三鲜
冬季的哈尔滨冰天雪地,美丽的太阳岛也没了夏日的浪漫。唯一比较显眼的就是哈尔滨分行建在太阳岛的培训中心了,俄式的建筑和异国情调也没有留住游人的脚步。凛冽的寒风似乎在提醒我们,这里是冬季的哈尔滨!那年冬天,总行投资部召集了几位分行投资处长,来到这里,共同讨论即将出台的重点项目目标管理办法。记得有北京行王平川、辽宁行白国祥、河北行程双起、黑龙江行李维先。这几个哥们共同点是健谈,有观点,敢说,加上彼此非常熟悉,所以碰到一起总会很热闹,几个人总能造出几十人的声响。但说归说,笑归笑,干起工作也很投入,很认真。我们讨论得很热烈,很接地气,所以很快就达成了共识。为了表示祝贺,东道主李维先提出晚上改善一下伙食。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提出晚上吃一顿三鲜水饺的诉求。当时还很难吃到三鲜水饺,尤其是冬天的韭菜十分鲜嫩,又是土鸡蛋,所以基本保证了三鲜水饺的质量。记得那天晚上我们都吃了很多,过去了二十多年,依然会时常想起,更成了我们几位见面时必不可少的谈资。
今年七月,我在上海碰到程双起,他又提起了这一段。不过这次见面他对我又说了一句话:“妈的这辈子都是你管我,现在我终于可以管你了”。我笑而不语,心想,看来你心里头不单单记住吃三鲜水饺的事啊!
第二十四回
老行徽,不同理解是佳话 谱行歌,传唱几年留余音
现在我们习惯了蓝色的行徽,庄重、简约、寓意很深。年轻的同志殊不知,早在二十多年前,建设银行通过全国系统内征集,层层评选,最终选定了上海行一位同志的作品,而且沿用至1996年3月26日。依我看,老行徽有这样几方面历史意义:一是出自员工之手,节约了开支,省钱。二是简单,易懂,无须解释,省力。三是无异形,制作方便,省心。但没多久,评论行徽的说法就多了起来,有的甚至成了段子。什么中间两个汉语拼音HJ,是“喝酒”啊,是“汉奸”啊。不知设计者听到这样的调侃没有,如果听到了会做何感想呢?中国实干家不多,评论家不少。
要说当时的行歌,我特别赞赏工会田春生的谱曲能力,那旋律一起,还是有一定感染力的,加上当时几位同志的填词,这首行歌还真唱了好几年。可惜现在已经没人唱了,是因为歌词过时,还是国际一流银行都没有?我不得而知,我真心希望建行在短期内创作出新的行歌,并代代传唱,有好处。
第二十五回
去静海,改革神话大邱庄 浪淘沙,走下神坛禹作敏
印象中的天津,一直都是北方最令人骄傲的城市之一。计划经济时期,轻工业品紧俏,素有“上青天”(指上海青岛天津轻工业发达)的美誉,那时候建行系统也有“湖上天”(指湖北上海天津分行出经验)的说法。事实上,天津文革时期出了个小靳庄,改革初期出了个大邱庄,这一大一小,在全国那是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小靳庄的威力并不小,而大邱庄的威力可是足够大。一时间媒体舆论对大邱庄的报道铺天盖地,各地参观取经的人络绎不绝。
我们是91年去的大邱庄。下了车我们就被眼前的一切震惊了:这哪里是农村啊?不见农具,不见农民,甚至不见农田,见到的是一排排农民自住的宽敞的别墅,是一片片厂房,我们走进一户农家,仅见到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正在忙着做饭,一打听家里其他人都在村里工厂上班,有的在炼钢厂,有的在线材厂,有的跑运输,有的跑原料。
按照规程,总会有村里的人专门负责对参观者集中讲解。当然我们也不例外。我们是仔仔细细地听,人家在滔滔不绝地讲,核心内容是说禹作敏的与众不同,有眼光,有魄力,有办法,所以大邱庄才有了今天,但我们听了半天始终没有明白,大邱庄怎么会有其他乡村无法得到的钢铁冶炼资源呢?这里是否存在无法借鉴更无法复制的独特路径呢?
没过多久,禹作敏出事了。披露的出事原因似乎与经营无关,但一路走来,大邱庄换了几个盟主,但现在已悄声无息却是不争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