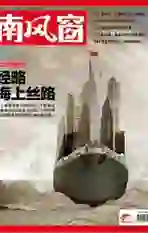来信
2015-05-13
该文使我感慨良多。因为,历时5年的新一轮医改,以侧重基层的“安徽模式”甚为引人心动。其缘由即在于该模式能够较好满足广大普通群众对于健康的基本需求,故而基层最为受益,故其向基层推开亦不足为奇。然而,以推动城市公立医改为目的的“三明模式”能否真正走出来推开去,却值得考证和期待。不过,我们应坚信一点:若“三明模式”始终坚持启动之初的良好势头,并以公益性为其坚定不移之方向,其对城市公立医改的导向作用应该是会灵验的。
—翟峰(读第7期封面报道《问诊新医改》)
我可以把这种左翼自由主义理解为“理性中的浪漫”吗?说它浪漫,是觉得它诠释了一种很理想的愿望,是道德上的满足。说它理性,是觉得它不像暴怒着的,狂吼着的,无脑的批判。女权主义运动是众多维权运动的始祖,就像许多维权运动,刚开始的浪潮,翻涌着却不够汹涌,但维护它的人是努力追求的平等自由。这些追求者们比任何人还要渴望将这些平等自由扩散至所有人,因为自身的缺失,才会体会深切,才能抛开不理智去全力追去。这的确是一种理性浪漫啊……
—Sing eagle(读第8期《“左翼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
外甥女的梦想是当医生,可面临高考填报志愿这人生最重要的抉择时,却产生了毕业后工作的忧虑,是谁让她考虑得这么长远? 我们口口声声宣扬的“读书改变命运”、“知识照亮前程”的理念在农村的遭遇常常是“水土不服”,这不是知识的无用、文化的没落,而是现实中文化知识在农村常常并不能等价置换出“力量”,而多是无助甚至失落。正是出于种种现实的考虑,在他们看来,与其劳神费财地苦心经营自己的学业,倒不如出去打工挣钱来得实际。让农民看到读书的希望、知识的重要,在当下转型期的中国,显然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耿宝文(读第8期《谁谋杀了“读书改变命运”》)
土生土长在小县城已年逾半百,怎么也想不到城市化会抹去儿时的记忆。年轻时行色匆匆没在意,如今闲下来总感怅然若失。40年前,谁家来客、谁家炒肉、谁家丧嫁,整条街都一清二楚。如今邻里姓甚名谁茫然不知。曾为脚不沾泥的水泥路高兴的人们如今为小城也堵车发愁。水泥森林在野蛮生长,青山与绿水早已远去。一茬茬拆房建楼,又一茬茬用水泥仿古。民间保留古建筑的声音从没消失,总敌不过开发商的喧嚣与打夯机的轰鸣。主街炫目的霓虹灯,总掩不住小城人内心的落寞。原住民:我的家呢?新移民:我的家不在这儿!
—沈治鹏(读第8期《“城一代”们最后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