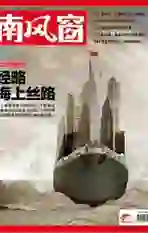城市也是受害者
2015-05-13唐小兵
唐小兵
读《南风窗》上一期封面策划“我们的精神史”较受触动,春节过去不久,《平凡的世界》还在热播,平时被冷落的乡村生活或者说乡愁突然被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这一期专题从多个层面展现了城乡流动这个历史过程造成的多重因果关联,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员流动从晚清就已开始,这其中既有自然的选择,也有战争、政治等多种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从城市到乡村的“返流”,在20世纪到如今,可能只有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等。两者之间呈现出来的自然是一种不对等的病态关系,简言之,从乡村到城市的流动被认为是正常的阶层上升流动,而从城市到乡村的流动,则往往会被认为是非常态的社会选择,意味着被城市淘汰了之后的别无选择。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所谓“乡愁”?它究竟是对乡村生活一种内在的关切,还是一种追逐潮流的“矫情”?或者是进入城市之后长久无法安顿身心之后的一种心灵病症?
如果是内在的关切,那就是无法割舍的,就像这一期报道中有些在城市里已经变成所谓“成功人士”的选择那样,千方百计也要回归乡村,反哺乡村,不将乡村作为一个包袱而渲染悲情,而是切实地从日常生活出发,为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在前些年一些乡村读书计划以及其他致力于乡村文化与社会建设的公益组织中都可以印证。若是一种追逐潮流,则是一种虚假甚至病态的乡村意识,其骨子里其实是高度认可城市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但似乎对乡村有一点点愧疚感,而谈论乡愁又显得特别“高大上”或者说有“人文情怀”,于是就人云亦云地鹦鹉学舌,这种所谓乡愁不足道也。当然,还有第三种,就是一些在城市里长久无法寻找到内心寄托的人,这些人既有失意者,也有成功者(从物质生活来看),他们的乡愁更多的是在对城市痛斥之后的一种心灵自我补偿,是寻找一种替代性的精神安慰。
这最后一种折射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城市文化、社会和意义建设的高度单一化,无论是城市的物理空间还是精神生活空间,都收到挤压,这正如《南风窗》记者何蕴琪的报道所显现,这些人即使到了大理等地方,其实仍旧是在精确地复制在广州、上海或北京等地的家庭生活模式,对于日常生活世界的自我更新和想象力,其实最大程度地限制了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的美学趣味。而没有审美趣味和多元化的自觉意识,一种表面上追逐时尚的生活,却可能是一种无意义的生活。在这一组报道中,我觉得特别有价值的是关于城市的叙述和分析,在此前二元对立的叙述框架之中,乡村总是受害者,城市总是施害者。可是,如果我们认真地对待我们的生活空间,就会发现伴随乡村在消逝的同时,一个更为多样化和原生态的城市,同样在消逝,城市同样也是受害者,这也许才是同样值得我们关切的问题。城市为什么成了让我们厌烦却无法摆脱的梦魇?它为什么不能像卡夫卡笔下的布拉格或者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或者民国时期如张爱玲笔下的上海那样,充满了日常生活的传奇感,以及鱼龙混杂的多样性,或者说一种将“都市里的乡村”和“乡村里的都市”融合起来的空间?城市为何无法将我们凝聚起来成为一个共同体,这也许是同样值得思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