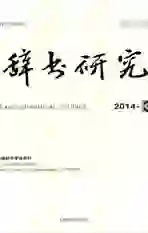汉语外来词的方言标注研究
2015-05-11陈燕
陈燕
摘要外来词兼具外来语言文化因素和固有语言文化因素,是我们观察借出语和输入语两种语言文化的窗口。通过考察音译外来词的方言特征,我们可以发现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轨迹,进一步认识不同的方言群体或社区在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但是现存的汉语外来词词典对方言音译词的标注既稀少又笼统,因而降低了这些标注在语言接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未来的汉语外来词词典应该加强方言音译词的标注,促进语言的多角度研究。
关键词外来词音译词方言标注语言接触
一、引言
外来词也称借词,是指一种语言从其他民族语言中吸收过来的词,是不同的文化发生交流与碰撞时在语言中留下的痕迹。外来词兼具外来语言文化因素和固有语言文化因素,亦即具备语言文化二重性(史有为 1991:12—16,2000:114—119),因而是我们观察借出语和输入语两种语言文化的窗口。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全面发展,汉语吸收外来词的范围和数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各种语源的外来词层出不穷。“世界上一些先进的文明国家,往往都有一批研究外来词的专家,有不少的外来语词典。一般老百姓,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查阅,既能扩大知识面,又能提高文化修养。反观我国,不无遗憾。研究外来词的专家很少,编纂成的专著和词典更不多见。广大人民群众对这方面的知识,几乎等于零。这与我们改革开放的大气候显得异常不协调。”(季羡林 1991:2)季先生的这番话,道出了外来词词典的重要性和外来词研究滞后的状况。20多年过去了,学界对外来词的关注空前高涨,在中国知网上用“外来词”“借词”搜索篇名,我们可以找到1992年以来的外来词研究论文近1500篇,其中包括一些颇有价值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此外,外来词研究专著数量有所增加,还出现了可以当作外来词词典使用的《胡言词典——关于外来语和流行语的另类解读》(胡言 2006)和《外来词》(古川 2008)等。然而,迄今为止,仍有一个问题一直为学界所忽视,即外来词的方言标注问题。在外来词词典的使用实践中,我们发现,一些用方言音译的外来词要么缺乏必要的方言标注,要么方言标签极为简略,这不便于我们研究外来词的方言特征与中外文化交流的轨迹,因此,本文将以音译外来词的方言标注为研究对象,探讨汉语外来词词典中此类标注的现状和标示的意义。
二、汉语外来词词典中的方言音译词标注调查
如果外来事物和概念在本族语中缺乏相应的表达形式,我们要么用意译的办法创造新词去指称,要么通过音译去引进,要么直接引入原文。音译原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操同一种语言的人、同一语种中说不同方言的人和同一语种中说相同方言的人都会由于对原词读音的把握不同、选字不同、省略的音节不同等多种原因而创造出不同的音译词,这正是一名多译的原因所在。正因为如此,“荔枝”一词进入英语后,被写成litchi,leechee,lichee,lichi,lychee等不同词形,chocolate一词进入汉语之后,曾有过“朱咕呖”“朱古力”“朱古律”“巧克力”等不同译名。音译词曾经困扰一些关注语言的人,比如,80多年前,石声汉发表了《关于标准译音的建议》一文,指出外来词音译时的一些问题:过去的译音有三个通病,即用方言来译音、不依原字的音来翻译、取字怪僻,其中“一个根本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方言不统一,各人依照方言译音,以致一个字有许多译法,几个字译成同一个音,纠纷错杂,很难弄得清楚”(石声汉 1933:1)。这说的是音译外来词消极的一面。然而,有一些方言音译词得到了公众的承认,在人民口头中推广开来,成为通用语的一部分,这说明它们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值得被收录进普通语文词典中,比如粤方言音译词“的士”不仅进入了汉语通用语,其中的“的”甚至已经演变成一个构词能力极强的外来语素。因此,方言音译词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语言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
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上海和广东曾是两个最活跃的地区,吴语和粤语中曾出现过大量的方言音译词,但是由于它们的使用频率可能不高,流布可能不广,有的甚至仅为当时少数人使用,因此除了极少数留驻在现代汉语中之外,大部分已经成为历史词汇,不适合收入《现代汉语词典》《辞海》这样的规范性辞书。现存的三部外来词词典中,胡行之的《外来语词典》(1936)和岑麒祥的《汉语外来语词典》(1990)均未提供外来词的方言信息,仅有《汉语外来词词典》(1984)提供了少量这方面信息。为了研究汉语中的英语借词,我们曾经把《汉语外来词词典》中直接来源于英语的外来词词目全部录入语料库,共得到4645个不同词目,其中仅154个词在释义中带有“〈方〉”这样一个简单的方言标签。为了弄清这些词的方言源头,我们首先参考了高名凯、刘正埮先生1958年的专著《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查找到其中31个词的方言源头。此外,我们查询了五卷本的《汉语方言大词典》,找到36个词的方言标注,其中23个词是高、刘二位未曾标注的。这两部文献对大部分词的方言标注是一致的,但有3个词的标注令人费解:对于“波”(ball 球)的方言源头,前者认定为闽语,而后者标注为粤语;此外,后者注明“派斯(pass 扑克牌)”属于吴语和粤语,“菲林”(film 胶卷)属于客家话、粤语和闽语。高、刘二位先生在专著中列出了少数来源于沪方言的词,但都不在这154个词之列。于是,我们又对照吴语研究专家钱乃荣先生的专著《上海方言》(2007),确定“哈夫”(half 切半)来源于吴语。最后,我们排除“波”的异体词“玻”和上述三个方言来源存疑的词,总共得到51个有确切方言区标注的音译词,其中46个词属于粤方言,4个词属于闽方言,1个词属于吴语。这样的查询结果显然不能如实反映方言外来词的历史,因为马西尼的专著《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1997)和1993—2000年间《词库建设通讯》上的多篇研究文章均已表明,这几种方言中源于英语的音译外来词总数大大超过以上统计数字。
事实上,《汉语外来词词典》收录了大量的方言外来词,只不过没有配置方言标注。比如,“那摩温”(No. 1 工头)、“拉斯卡”(last car 末班车)、“法兰绒”(flannel)、“马达”(motor 发动机)、“水门汀”(cement 水泥)、“水汀”(steam 蒸汽,暖气)、“白脱”(butter 黄油)、“麦克风”(microphone 扩音器)、“沙发”(sofa)等词均属于上海话(钱乃荣 2007:92—93),但是《汉语外来词词典》未加任何方言标注。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编纂者缺乏可靠的方言证据。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外来词的源流考释工作基础薄弱,而编纂者不可以仅靠个人的学养去妄下断言,因此,尽管其中二位编纂者已经在前期出版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1958)中注明了部分词语的方言源头,在1984年出版的《汉语外来词词典》中却仅仅采用了标签“〈方〉”来提供部分信息,但不提供方言源头,这说明编纂者在编纂原则上重视方言音译词的标注,但在编纂实践中却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
三、方言外来词标注的价值和意义
汉语方言众多,且各方言之间特征迥异,无论是作为借出语还是作为输入语,其方言特征都是值得关注的。作为输出语,汉语已经输出给外语的词在外语中是否是根据汉语原词的某种方言读音转写而成的呢?美国学者Garland Cannon在1988年的American Speech(《美国语》)第1期上发表了Chinese Borrowings in English(英语中的汉语借词)一文,对他从英美出版的八部案头词典等文献中所收集到的979个汉语借词进行了语源、义类和构词类型等方面的分析。另一位美国学者Andrew J. Moody在1996年采用Cannon的语料库,以词语被至少三部不同词典收录为标准,从这979个词中挑出196个汉语借词,分析了汉语方言在这些词中的沉积状况。对于这196个汉语借词,Moody排除了三种词:一是那些显然来自于同一汉语原词的词,如Jap,Japan,Japanese,Japanesque,Japanize,Japanology,Japlish等均为Japan的变异形式,因此全部排除在外,仅认定其根词Japan为汉语借词;二是那些用汉语音译成分加英语语素构成的词,比如black tea(红茶)和green tea(绿茶)都被排除,但将“茶”的音译成分tea认定为汉语借词;三是那些仿译词,比如paper tiger(纸老虎)、scorched earth(焦土)、Red Guard(红卫兵)、winter melon(冬瓜)等。Moody最后得到92个汉语借词,通过对比这些词与汉语原词的读音之间的照应关系,并查询英美最权威的足本词典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韦氏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1961)和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牛津英语词典》,1989)等相关资料,最终确定其中22个词是从汉语经由日语、法语、皮钦语、荷兰语等中转后进入英语的,而剩下的70个汉语借词中有37个来自普通话,13个来源于粤方言,5个来源于厦门话。从义类来看,13个粤方言借词中六成以上与饮食有关,包括kumquat(金橘)、loquat(枇杷)、bok choy(白菜)、chopsuey(炒杂碎)、chow mein (炒面)、dimsum (点心)、wonton(馄饨)、wok(锅)等词,而源于厦门话的汉语借词全部与茶有关,包括tea(茶)、bohea(武夷茶)、pekoe(白毫茶)、congou(工夫茶)、hyson(熙春茶)。于是,Moody(1996:405)得出了这样的研究结论:“(英语)从普通话中借入的词通常反映中国的‘高雅文化,即所借入的词关乎哲学、宗教、历史、政治、艺术和文学等领域。从粤方言借入的词大部分与食物有关。最后,英语中好几种茶的名称来源于厦门话,而tea(茶)一词本身是从厦门话中借入的。”这样的研究结果是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相互印证的:由于一些广东人移居海外,又由于香港与英语文化千丝万屡的联系,一些粤方言词得以成为汉语借词的拟音依据而传入英语;厦门方言输出给英语的多是茶名,是因为福建是中国茶叶的主要产地之一,在19世纪中英贸易发达的年代,厦门是福建茶叶主要的出口地。
作为输入语而言,即使在普通话获得大面积推广的今天,汉语中仍然存在一些用方言音译的外来词。汉语发展的事实表明,汉语方言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向普通话靠拢,但是普通话不会代替方言。只要方言长期存在,汉语中的方言音译词就不会消失。那么,汉语在音译外来词时是否是用方言来译音的?如果是,词典中是否做了任何标示?如果有标示,标示是否具体而准确?我们对《汉语外来词词典》所做的方言音译词调查,虽然只确定了51个音译词的方言源头,但是,各地方言中实际流通过或正在使用中的方言音译词数量是大大高于这个数字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的引进,有一条非常明显的分水岭:80年代以前,极大部分都是从上海方言中引进的;而80年代以后,则主要是从粤方言,特别是从香港方言引进的。”(邵敬敏 2000:4)外来词对上海话的影响涉及方方面面,据钱乃荣先生(2007:93)研究:“西洋近代文明无论工艺、建筑、交通、衣饰、饮食、医学、教育、音乐、体育、娱乐和生活用语等都在上海的词汇中留下痕迹。”粤方言中的外来词同样数目巨大,Mimi Chan & Helen Kwok的专著A Study of Lexical Borrowing from English in Hong Kong Chinese(《香港中文中的英语借词研究》,1982)中,收录了香港中文中来自英语的借词约350个,其中还包括一些在普通话中无对应词形的词。如果对其他方言中的外来词进行研究,或许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这些方言在外来词中留下的痕迹。
然而,如上所述,以汉语从英语借入的音译外来词为例,我们已经发现:对于方言音译外来词,专门的外来词词典要么未加方言标注,要么采取了与通用的规范性语文词典一样的处理方式,即仅仅加上标签“〈方〉”。外来词词典的这种处理方法是否合适,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像《汉语外来词词典》这样收释古今外来词的词典,本质上是一部历时专门词典,收词的范围广、时限长,必定收录一些历史上曾经在特定地区流通而现在的普通语文词典无法收录的方言外来词。对这类词做恰当的方言标注,才能全面反映其特征,完成词典忠实记录语言的职能,因此,方言标注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的,只要某个外来词是依照某地的方音转写并在该地通用过,就应该标注具体的方言区。此外,标示具体的方言区,有利于词典使用者了解音译词与外语原词之间语音上的对应关系。有一些音译词可能成词的年代比较久远,抑或因为个人的语言知识有限,普通的语言使用者可能不了解其方言特征,甚至可能望文生义,对外来词做出流俗词源解释。比如“的确良”一词来源于粤方言音译词“的确靓”(dacron 涤纶),其中的粤方言词“靓”意为“美观漂亮”(张绍麒 2000: 146),一般的语言使用者对此闻所未闻或闻之甚少,是不足为怪的。如果词典明确标示该词的方言特征,则可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再者,方言区的确切标注有利于读者了解词语产生的文化背景,更有利于语言工作者的研究。如果外来词词典给所有的方言音译词都配备了具体的方言区标注,那么我们不需要在《汉语方言大词典》中进行二次查询,就可以获得相关语料并揭示各方言区与异族语言接触的状况,而不必像Moody那样费尽周折才能确定方言源头并勾勒出语言接触的特征和概貌。
方言音译词在中外互借词汇中的沉淀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地域性特征的反映,是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活化石。我们不仅可以从中发现文化交流的历史轨迹,而且可以更进一步认识不同的方言群体或社区在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由于历史的原因,《汉语外来词词典》对方言音译词的标注不够全面和清晰,但是,从汉语外来词词典的性质和用户友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未来的外来词词典编纂者需要而且可以提供更多更准确的方言信息,比如将“水门汀”标注为“〈沪方言〉”,将“的士”标注为“〈粤方言〉”。这样的做法对于词典编纂者而言是一点细微的变化,只不过是将粗略的“〈方〉”具体化,但是却能给语言研究者提供巨大的便利,更便于他们进行多角度的研究,提高了词典信息的质量。
四、余论
方言外来词的恰当标注有赖于词典编纂者认识上的改变,更有赖于学界的研究成果。对于那些在特定地区流通的方言外来词,学界的研究还是不少的。有一部分学者着眼于个别方言的外来词研究,如谭海生(1992:47—51,1993:101—106,1995:26—30)、朱永锴(1995:50—56)、邓景滨(1997:227—231)探讨了粤方言中外来词的借入途径、主要特点、传播载体、构词方式、语种来源等。还有的学者着眼于不同方言中的外来词的比较研究,如黄长著(1994:401—408)、汤志祥(1995:103—109)、路广正(1996:101—104)、谢米纳斯(1996:44—52)、邵敬敏(2000:3—12)比较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方言中的外来词在词汇选择、音节结构、构词类型、外来语来源、存在的问题等方面的差异、成因等。随着方言外来词考源工作的加强,词典编纂者可以采信的研究成果会越来越多,而更好的外来词词典又能促进与外来词相关的各项研究工作。因此,我们不仅期待方言音译词的标注得到完善,更期待有关外来词的研究日益全面和深入。
参考文献
1.岑麒祥. 汉语外来语词典.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邓景滨.港澳粤方言新词探源.中国语文,1997(3).
3.高名凯,刘正埮.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
4.古川. 外来词.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8.
5.胡行之. 外来语词典. 上海:天马书店,1936.
6.胡言.胡言词典——关于外来语和流行语的另类解读.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
7.黄长著.从某些外语专名的汉译看海峡两岸语言使用的同与异.中国语文,1994(6).
8.季羡林.《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序.∥史有为.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 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9.刘正埮等著.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
10.路广正. 港台地区外来语译名问题浅探. 文史哲,1996(4).
11.钱乃荣.上海方言.上海:文汇出版社,2007.
12.邵敬敏.香港方言外来词比较研究.语言文字应用,2000(3).
13.石声汉.关于标准译音的建议.图书评论,1933(10).
14.史有为.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15.史有为.汉语外来词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6.谭海生.粤方言中的外来语初探.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92(2).
17.谭海生.粤方言外来词的书面化及其载体——粤方言外来语二探.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93(1).
18.谭海生.大陆粤方言区与香港地区使用外来词之区别——粤方言外来语三探.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94(1).
19.谭海生.对译借词——粤方言外来语中的一种特殊借词——粤方言外来语四探.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95(1).
20.汤志祥.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汉语词汇方面若干差异举例.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1).
21.谢米纳斯.海峡两岸外来语比较研究.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6(1).
22.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 汉语方言大词典. 北京:中华书局,1999.
23.张绍麒.汉语流俗词源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2000.
24.朱永锴.香港粤语里的外来词.语文研究,1995(2).
25.Cannon G. Chinese Borrowings in English. American Speech, 1988(1).
26.Chan M, Helen K. A Study of Lexical Borrowing from English in Hong Kong Chines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1982.
27.Moody A J. Transmission Languages and Source Languages of Chinese Borrowings in English. American Speech, 1996(4).
(责任编辑李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