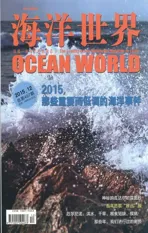江户水都难波京
—— 你没见过的另一个大阪
2015-04-22撰文摄影八哥
撰文/摄影/八哥
江户水都难波京
—— 你没见过的另一个大阪
撰文/摄影/八哥
“短短芦苇节,难波满海滩。相逢无片刻,只叹命将残。”
《小仓百人一首》里的一句诗,透出唐风里常有的古韵悲思,这里的“难波”指的就是奈良时代大阪的名字。在一个多世纪里,难波京被强行赋予了首都的角色,却没有编制太多野心家的血雨腥风。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更像是一面招牌,映照着这个岛国最平凡的生活姿态。
转瞬千年,作歌之人的姓名早已无从考据,如今的大阪湾在填海造陆的工程后,也远非从前的面貌。踏着石子路从大阪城公园走出来,对面那片开阔地上不起眼的台垣,似乎提醒着人们——大阪这座忙碌嘈杂的现代化城市里,也有厚重的曾经。
难波与难波京
说起“难波”这个名字的由来,不得不从神话时代讲起了。按照《日本书纪》的说法,相传神武天皇45岁那年,挥师自福冈一路东征,横渡濑户内海,最后抵达最为繁华的河内一带,也就是后来“大和国”的所在地。而路过大阪湾的时候,由于风急浪大,颇费了些周折,于是将这里命名为“浪速国”,后来改名成“难波”。
不过,风浪并没有影响难波成为交通枢纽。从公元3世纪起,从难波启航的帆船就承载着货物商品往来于中国和朝鲜之间,大阪也成了最大的港口城市。彼时,船只的往来还仅限于民间,并没有太多官方的船只从难波出发。直到公元7世纪左右,随着国家体系日渐成型,意在朝鲜的圣德太子授意外交官小野妹子遣隋,一方面宣布了日本对等而非称臣的主权地位,一方面也为宗教、文化甚至军事的建设汲取知识。不管初衷如何,这都为后来唐代难波津上往来不断的船只开了门户。
公元645年夏天,一番推让后,已经年近天命的孝德天皇继位。连年的权谋政变让这位已经年届50的老者下定了决心,他效仿中国,改国号“大化”,取义于《尚书》中“施教化,大治天下”的意思,也就是著名的大化革新。为了彰显改革的意愿,当年冬天,干脆宣布迁都难波——即传递出重视对外交流的积极信号。其实难波历来都有皇宫,但为了迫切地表现出改革的决心,孝德天皇仍不惜触犯“神意”,下令砍伐了神社周边的树木修建新的京城。整整6年后的12月,在两千多名老少僧侣的诵经声中,在长柄丰宫基础上建设的新宫落成,定名为难波京。
是日,天皇迁居于此。
难波宫的落成进一步促进了大阪港的繁荣,逐渐增多的民间贸易让日本政府意识到本国文化和技术的滞后。于是,第一批遣唐使从三津浦出发,满载礼品、贡物、医药和留学生的船只冒着生命危险,在风浪间从福冈跨越渤海,登陆山东半岛。此后200多年内,长安城里时常出现日本商人的身影,唐朝的礼制、法度、技艺、文教逐渐传入日本,难波京也时常会出现来自大唐的学者和僧人讲学授业,这些日后都成了日本文化演进的范本,而这种虚心求教的态度则在以后的历史沿革中,根植在日本文化中,与保守的社会传统一起构成了日本独特的民族精神。
如今,在毗邻大阪城公园的大阪历史博物馆的地下一层,可以参观到难波京的考古遗迹。同时博物馆还通过模型复原了难波京的样貌。在石制基座上,上百根巨大的梁柱撑起了每座宫殿的结构,瓦当多为重圈文,与幕府时期的菊花纹有很大不同。在日本历史上,往往可以根据不同的纹饰来区分时代和所属的政权。因此,展区内也别具匠心地制作了不同时期的纹章供参观者印鉴收集,当你浏览过每段大阪的历史,自然也就收集起所有的纹章了。同时还特意为考古爱好者设立了一个互动的区域,人们可以通过拼接陶片模型,动手测绘来亲身体验难波京的发掘过程。
町人文化
既然得名于水,难波的建设自然与港口密切相关。难波京本身离大阪湾不过咫尺之隔。难波津,也就是今天的大阪港的繁荣,在许多绘画作品中都有所体现,码头上忙碌的人群和街市,让当时的难波街市上满是生活的热闹和忙碌,冲抵了不少首都的庄严。随着堀江的开凿,逐渐消除了水流交汇入海时的常有的洪涝,激活了难波的交通。市内河道纵横交错,大小桥梁无数,水上活动十分频繁,因此也有了“大阪八百八桥”的说法。
今天很多小河道已不复存在,多数盖起了摩天大厦,但从地名上也可以揣摩出那个时代的痕迹。著名的商业中心“心斋桥”和“道顿堀”虽然楼宇如林,但仍然是人们商业生活的缩影——叫卖渔夫,兜售货品的小商贩,谈生意的商人,带刀的武士和运煤炭的工人,千百年前的角色如今都变了模样,却没有失却熙熙攘攘的氛围。难波津上,劳作了一天的人们踏着木屐,三五成群饮酒而歌,结束一天的生活。
到了江户时期,虽然政治中心迁往了江户(现在的东京),但是大阪仍然是以文化艺术以及经济中心在日本全国拥有独特的地位。定期开展的木偶净琉璃戏,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定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歌舞伎更是不言自明,至今还吸引着从工作压力中解脱出来的日本人。在大阪历史博物馆的8层,有一条按原比例建造的明治时代的小街——浪花町,还有一整片1∶20的比例的江户时代的大阪街景,真实地复原了当年的情境。缓步在博物馆的过道里,仿佛能听到和感到当时的大阪坊间那种欣欣向荣,人声鼎沸的场景。
长期与神秘莫测的海洋相伴,无疑增添了日本人对神明的敬畏。走在街市上,经常会看到住户或是小饭馆立着1米多高的小神龛,多数是该地有过“异象”,里面供奉的神明也不尽相同。神明多,祭祀自然也多,“天神祭”就是其中最有名的活动之一。7月下旬,市内各处都开展神乐(祭神时演奏的音乐)及文乐(木偶剧)等日本传统艺术表演,3000名身着平安时代宫廷装束的民众与神轿一起缓步前行的“陆渡御”,然后乘约100艘船逆流而上。傍晚,市民在河岸旁点起的灯火和烟花映着船只在水里的倒影,祈愿主司雷电的神明可以奉纳花火。
游行的终点设在天满宫,相传平安时期著名政治家菅原道真死后,京都多生雷电火灾,因此建造了这座神宫来祭奉。有趣的是,不知是不是雷神的火气太大,天满宫在建成后的千年里,却时常受到火灾的损毁。人们在节日里打着拍子唱着歌,宣扬着关西町人崇尚的生活理念——“风流潇洒,无拘无束”。要想了解大阪的精神内核,没有比参加天神祭更合适的庆典了。
今日大阪
对于第一次来关西旅行的人,京都和大阪无疑是不可错过的地区。如果把京都比作西安,看重的是古都的那份气定神闲,那么大阪就是上海,灵动变通才是这里的气质。打开手机里的APP,推荐的景点里几乎看不到历史的痕迹——巨蛋、环球影城、海洋馆、梅田购物中心......怎么看都像是来到了上海。
如今的大阪寄托的更多是活在当下的理念和对未来的期许,即便是历尽风雨,记录了毁灭与重生的大阪城,更多展示的也是清新阳光的一面。在大阪博物馆和天守阁前的广场上,各有一个标记着“时光胶囊”的球状金属容器。1968年,为了庆祝2年后举办的大阪世博会,松下电器联合《每日新闻》,选取了2098件20世纪的文化财产,将它们密封在特制的金属容器中,埋在大阪城下。其中2号仓每百年开封一次,而1号仓则要到整整5000年后才约定打开。翻阅早先的报道里,仍能找到2000年3月15日开封2号仓时的盛况,其中取出的树种如今已经在吹田的世博会纪念公园里茁壮成长。其实,某种程度上,与其把这说成是文明的传递,倒不如看作一种骨子里的率性洒脱。
坐在大阪返回京都的列车上,男人清一色的西装和松弛的领带里,是站得笔直的身体和疲惫的面容。也许这才是今天日本的写照——任你潇洒不羁,也不免被时代推进人群里,成为彼此的样子。再多的大河剧,也没法带你回到那个叫“难波”的地方,体验工业社会之前每个人的个性与细节,感受时代里如浪涌般不停歇的潮流和变迁。一如而今的日本社会,多的是循规蹈矩的日常。虽然有了生活的便利,却无形间抹去了本该激荡或沉思的时光。(责编:金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