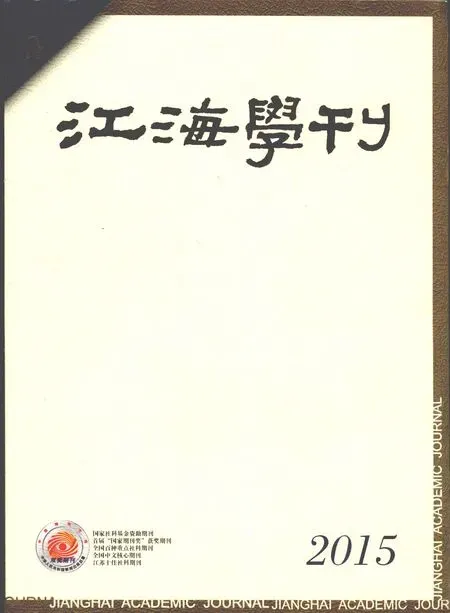《仪礼》与清代士人的文学审美建构
2015-04-18吴戬曹虹
吴 戬 曹 虹
《仪礼》与清代士人的文学审美建构
吴 戬 曹 虹
《仪礼》一经甚为难读,相关研究代不数人。自王安石以后,更与科考绝缘,备受士人冷落,其文学化进程在三礼中最为滞后。在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中,《仪礼》得到关注。经由张尔岐、凌廷堪、张惠言等学者的努力,《仪礼》的阅读障碍得到有效解除,为其实现审美跨越创造了有利条件。乾嘉以来,《仪礼》逐渐进入文学场域,为诗、骈文、辞赋提供了丰富的表现题材,仪节器物的描绘、礼学历程的梳理、礼学思想的表达成为这一时期文学表达的重要方面,并在背景铺垫、场面描写、人物刻画、主题深化方面起到了特殊的审美效果。同时礼图唱和开启了文人酬唱的新维度,体现了学术与文学的叠加融合,也丰富了学者的审美生活。晚清时期,《仪礼》在曾国藩等人手里实现了文学的选本化,并引导崇实文风的继续推进。《仪礼》的审美地位逐步确立,六经皆文亦从观念变成现实,由此可见学术与文学的深刻关联以及士人主观憧憬与现实情境的碰撞整合过程。
《仪礼》 清代 审美建构
礼与文学颇有历史渊源。《周礼》、《礼记》多处引用《诗经》语句,作为阐释的依据。《仪礼》则将不少《诗经》篇章作为礼仪展开的重要音乐背景。此外风雅颂、赋比兴等六诗其实源自《周礼》:“教六诗:曰风,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春官大宗伯·大师》)温柔敦厚的诗教亦首倡于《礼记·经解》。南北朝时期,一些有儒学趣味的文论家,开始注意礼与某些文类的衍生关系,如南朝刘勰以“宗经”的眼光认为:“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文心雕龙·宗经》)北朝颜之推亦称“夫文原者,原出五经”,“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颜氏家训·文章》)。到了中唐时期,韩、柳等古文家以文儒自任,开辟了“约六经之旨以成文”的创作方向,奠定了“六经”作为道与文结合的至高典范地位。不过,具体到三礼,韩愈在自述学文路径的《进学解》中,将《尚书》、《春秋》、《左传》、《周易》、《诗经》视为创作取法的对象,却未提及三礼,柳宗元只是笼统地提到“本之礼以求其宜”(《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尤其是唐初颁修的《五经正义》中的礼,实以《礼记》作为代表,“用《礼记》替代《仪礼》,《礼记》一跃成为三礼中最显赫的经典”①,作为本经的《仪礼》反遭冷落。这种境地历宋明时期而更为严峻,一因宋明学人注重发挥义理,对《仪礼》传习者少,“《仪礼》则全为度数节文,非空辞所可敷演,故讲学家每避之而不道也”②;二因朝廷举措偏向,如熙宁改革时,王安石宣布废罢《仪礼》,此经不再立于学官。古时科举分房阅卷,自此至清,再无《仪礼》之房。相对于其他儒家经典,《仪礼》的学术化乃至文学化进程明显滞后。
《仪礼》与文学场域之历史离合,在清代得到了重大改观。这一关涉学术与文学互渗的历史动向及其内涵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揭示③。实际上,随着清代《仪礼》学复兴之局的打开,《仪礼》与文学审美之间的鸿沟得到了有效的填补。《仪礼》中的古礼复原与践履怎样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表现题材?《仪礼》的庄敬征实之矩范如何影响文章书写避虚就实?礼政作为文章选本中的一个类别如何产生出特别的意义?诸如此类的以学为文的追求中,体现出清代士人对《仪礼》文学审美建构的卓越成就。
清代《仪礼》学复兴的基点与方向
甲申之变的深刻教训,促使明清之际的学者痛感宋明理学的空虚静寂之弊,决心以实学来拯救之,于是出现了回归经学乃至礼学的思潮。顾炎武不仅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论断,对礼的价值与功能亦有高度的认识:“礼者,本于人心之节文,以为自治治人之具……然则周公之所以为治、孔子之所以为教,舍礼其何以焉。”④他对《仪礼》十分看重,对王安石变法废弃《仪礼》深感痛心:“三代之礼,其存于后世而无疵者,独有《仪礼》一经。汉郑康成为之注,魏晋已下至唐宋通经之士,无不讲求于此。自熙宁中,王安石变乱旧制,始罢《仪礼》,不立学官,而此经遂废,此新法之为经害者一也。”⑤并用唐石经校勘《仪礼》,使《仪礼》因荒废而发生的错讹得到修正:“若天下之书皆出于国子监所颁,以为定本,而此经误文最多,或治脱一简一句,非唐石经之尚存于关中,则后儒无由以得之矣。”⑥其好友张尔岐则向汉唐注疏回归,撰述的《仪礼郑注句读》“全录《仪礼》郑康成注,摘取贾公彦疏,而略以己意断之”⑦,从而揭开了清代《仪礼》学复兴之大幕,吴廷华《仪礼章句》、沈彤《仪礼小疏》、蔡德晋《礼经本义》、盛世佐《仪礼集编》等彬彬继之,皆为一时之选。随着《仪礼》研究的不断深入,尤其是褚寅亮《仪礼管见》对元代敖继公的《仪礼集说》之谬误予以纠驳,礼学家认识到东汉郑玄注释的权威性和经典性,礼学回归郑学逐渐不可逆转⑧。而徽州一域尤为中枢,在江永、戴震、程瑶田、金榜诸大师之后,凌廷堪继起,通过归纳条例的方式来研究《仪礼》,取得了重大创获,其《礼经释例》成为清代礼学的里程碑式著作,“清儒于《仪礼》撰述极多,实无堪与匹敌者”⑨。
《仪礼》在三礼的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澄清,凌廷堪通过其坚实的研究证实《仪礼》为礼经,“《仪礼》十七篇,礼之本经也”⑩;而《周礼》为礼的支流,《礼记》只是“传”而非“经”,《仪礼》为礼之本经的观念通过凌廷堪的阐释与证实而得到广泛认同。虽然以《仪礼》为本经倡发于朱熹所引臣瓒之说,但朱熹依然以《周礼》为礼之纲领:“《周官》一书,固为礼之纲领。至其仪法度数,则《仪礼》乃其本经,而《礼记·郊特牲》、《冠义》等篇,乃其义说耳。”自凌廷堪出,《仪礼》的独特性和首要性才得到士人的充分重视。另外,清代《仪礼》学的复兴已经超出了纯粹学术研究的范畴,具有相当丰富的思想史意义。自戴震《与某书》和《孟子字义疏证》中揭露理学“以理杀人”,凌廷堪更是鲜明地提出了“以礼代理”的命题,将礼学提高到思想话语的高度,与宋明理学划清界限:“圣人不求诸理而求诸礼,盖求诸理必至于师心,求诸礼始可以复性也。”“不知圣学礼也,不云理也。”清代中后期的汉学家往往将《仪礼》视为角胜宋儒的战场,掀起了崇礼的新热潮。正如梁启超所概括,《仪礼》的研究业绩在三礼中最为突出:“试总评清代礼学之成绩,就专经解释的著作论,《仪礼》算是最大的成功。”
在这些研究业绩出现之前,如四库馆臣所云:“《仪礼》难读,儒者罕通。”但卢文弨谓:“君此书(凌廷堪《礼经释例》)出,而天下始无有畏其难读者矣。”陈澧云:“澧尝欲取《仪礼》经文,依吴中林《章句》,分节写之。每一节后,写张皋文之《图》,又以凌次仲《释例》分写于经文各句下,名曰《仪礼三书合钞》,如此,则《仪礼》真不难读,惜乎为之而未成也。”曾国藩在同治六年(1867)二月的日记中也写道:“余生本朝经学昌明之后,穷此经者不下数十人,有蒿庵之句读、张皋文之图康庄共由之道,而又有人以扶掖之,则从事甚易矣。”可见,在张尔岐、吴廷华、凌廷堪、张惠言等学者的努力下,《仪礼》的阅读障碍得到了有效的解除。作为“经学昌明”时代的读书绩效,《仪礼》切实已然进入了士人的阅读与思考的视野,拥有较之以前更为广阔的社会基础,这客观上为《仪礼》的文学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仪礼》进入文学文本和文人生活
清代以前的士人于三礼之于文学的价值,多注重对《礼记》、《周礼》的探讨。如两宋之交的吕本中阐发《礼记》和《周礼》对于“议论文字”的重要审美价值:“议论文字须以董仲舒、刘向为主,《礼记》、《周礼》及《新序》、《说苑》之类,皆当贯穿熟考,是做一日,便有一日工夫。”南宋陈骙《文则》对《礼记》、《周礼》的衍生文体、文学风格、句法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元明士人对三礼的文学认识亦不出宋人矩矱。到了清中叶,乾嘉学者不仅对《仪礼》进行了多维层面的研究,而且还通过文学手段对其进行表现和诠释,使文学成为《仪礼》思想表达与仪节诠释的重要载体。现从两方面予以展示:
其一,《仪礼》富于度数节文,这些礼节仪度进入文学场景,不啻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表现题材和庄敬气息,对背景铺垫、氛围营构、场景描写、人物刻画、主题深化也起到了特殊的审美效果。所涉内容较为丰富,兹列举如下:
1.《仪礼·士冠礼》。冠礼为礼之始,是成人教育礼,“故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故曰‘冠者,礼之始也’,是故古者圣王重冠。”(《礼记·冠义》)“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礼记·冠义》)其在礼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将责四者之行于人,其礼可不重欤!”(《礼记·冠义》)凌廷堪《辨志赋》描述了《仪礼·士冠礼》筮占的场景:
祝既毕而凝神兮,就余位于门外。群执事之具陈兮,肃衣冠而敬待。巫更布席于闑西兮,抽上韇而受辞。即席坐而书卦兮,还东面而占之。筮遇泰之初九兮,拔茅茹以汇征。上坤顺而应乾兮,三阳同志而吉亨。象既告余以攸往兮,辄诹曰而遄行。
上文对士冠礼的筮日之礼(即占筮行冠礼的吉日)进行了描绘,涉及着服就位、布席、陈器、受命、占筮、书卦、禀告等诸多方面。整个礼仪充满着对冠者的教诲和期望。且所占之卦为地天泰卦,泰卦本来就是小往大来之吉卦,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泰之初九,拔茅如,以其汇,征吉”,亦说明志于向外发展。其时凌廷堪在母亲的教诲下,准备出游四方,就师友以成学。从而借助这个郑重而吉利的礼仪表达了家人对其的殷殷期待以及自己致力向学的坚定决心,贴切而传神。
凌廷堪的诗篇《次吴石臣进士见赠二首元韵》其一主要讲述了其究研礼学的经历。其中提到“特豕酒三献,侧尊醴一甒”,前句涉及《仪礼·特牲馈食礼》,特牲馈食礼是诸侯之士每逢岁时祭祀祖父、父亲的礼仪,其中诸侯之士用一猪,即特牲、特豕,核心仪式为三献,即主人初献、主妇亚献、宾三献。后句是指《仪礼·士冠礼》,“侧尊醴一甒”实化用《仪礼·士冠礼》之“侧尊一甒,醴在服北”,尊一般有二,一为玄酒,一为醴,士冠礼无玄酒,所以称侧尊。结合诗中的上下文来看,凌廷堪通过对《特牲馈食礼》和《士冠礼》的仪节对照,不仅对仗工整,相映成趣,而且以点带面,使全诗显得形象生动,亦凸显出其对《仪礼》的熟稔和高超的文学造诣。
2.《仪礼·士昏礼》。昏礼为礼之本,“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礼记·昏义》)。在礼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礼记·昏义》)。焦循《巴贞女挽歌》讲述了巴贞女未婚守志抚孤之事。巴贞女为张子之继室,但聘而未娶,未婚夫张子去世后,留下了前妻两岁的儿子,巴贞女义无反顾嫁入张家,照顾张子前妻之子。诗中提到:“轮三周兮御者谁,襜车素白凄秋雨。”前句涉及《仪礼·士昏礼》中亲迎环节中的“婿御妇车”之礼,即新郎要为新娘驾车,轮转三周即止,然后由御者代替新郎继续驾车:“婿御妇车,授绥,姆辞不受。妇乘以几,姆加景,乃驱。御者代。婿乘其车先,俟于门外。”郑玄注云:“行车轮三周,御者乃代婿。”新郎、新郎的车均为墨车,但新娘的车有襜(帷幕):“主人爵弁,纁裳缁袘。从者毕玄端。乘墨车,从车二乘,执烛前马。妇车亦如之,有襜。”(《仪礼·士昏礼》)诗中御者谁的设问与襜车素白均暗示出巴贞女夫君去世的残酷事实。这种礼仪的常中有变揭示了巴贞女的悲惨命运,也更凸显出巴贞女临变不改守礼之坚贞与朴厚。
3.《仪礼·乡饮酒礼》。乡饮酒礼有尊贤尚齿之义,是王道教化之根本,“乡饮酒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礼记·射义》)。“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礼记·乡饮酒义》)故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礼记·乡饮酒义》)。钱大昕用诗表现《乡饮酒礼》,其《丙辰孟冬朔本县举乡饮礼忝预宾席口占呈当事暨同饮诸君四首》的前两首写道:
仙令采风修古礼,师儒诹日启初筵。衰翁本乏专门学,亲演高堂第四篇。
每曲当碑联袂行,胜它洛社会耆英。相逢不用寒暄话,竹马儿时好弟兄。
第一首中所谓“高堂”,即礼学家高堂生,司马迁称:“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史记·儒林传》)《士礼》即《仪礼》“高堂第四篇”,即《仪礼》之第四篇《乡饮酒礼》。“师儒诹日启初筵”,描绘和表现的是《乡饮酒礼》的戒宾之礼:“乡饮酒之礼。主人就先生而谋宾、介。”钱大昕本非《仪礼》专家,但却作为嘉宾参与嘉庆元年嘉定县所举行乡饮酒礼的日常践履之中,这种对照不仅富于现场的亲切感,增添了文学的审美情趣,也凸显出作者谦虚的人格风度。第二首中所谓“每曲当碑”,是《仪礼》中的三揖之一,《仪礼·乡饮酒礼》云:“主人与宾三揖,至于阶,三让。”郑玄注云:“三揖者,将进揖,当陈揖,当碑揖。楣,前梁也,复拜。拜宾至此堂,尊之。”不仅写出了《乡饮酒礼》的仪节,而且也酝酿了一种其乐融融的和谐情调。这与“和以射、乡”(《礼记·昏义》)之旨相得益彰。
对《仪礼》“笃好深嗜”的凌廷堪,撰《七戒》以明其服膺礼学之志,开篇即以《仪礼·乡饮酒礼》的仪式来作背景的铺垫,描述了戒宾、布席、陈器、迎宾诸况:
谋于致仕之老,立为乡饮之宾。当牖前而布席,中房户而设尊。上篚在禁南而东肆,下篚在洗西而南陈。缘席者缁布,覆尊者绤巾。西阶东面者介,宾东南面者遵。阼阶之席,厥惟主人。牲醴脯醢,各有司存。陈器之先,乃朝服而造处士之门。处士拜辱,立于门外。上卿门西,东面答拜。告以宾兴,敬恭而戒曰:“吾闻儒者学古以希获,君子藏器以待试。是以运隆于上,贤哲符利见之占;教成于下,庸愚有奋兴之志。今将礼子以一献之礼,吾子其有意乎?”处士曰:“唯唯。夫贸然纳交者,苦于无所择;率尔应命者,闇于不自知。辱承高训,良慰鄙怀。敢问介与众宾,其人为谁?”
上卿依次以书画、辞章、性理、经济、史学劝勉,处士均未曾动心,继而导之以经学尤其是礼学,处士怦然心动,跃跃欲试。全文借《乡饮酒礼》尊老尚贤之义,予以铺陈发挥,揭示了作者服膺礼学的心路历程,可谓水到渠成。
4.《仪礼·乡射礼》。射礼有大射、宾射、燕射、乡射四种类型,其中乡射礼是每年春秋时节由乡大夫择贤能者在州学举行的一种射礼,用以考核德艺,选拔人才,起到教民礼让,敦化成俗的效果。射礼可以观人之德行,故为世所重。“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礼记·射义》)“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礼记·射义》)凌廷堪撰有《乡射赋》,对《仪礼·乡射礼》进行了全方位的描绘与诠释。首先对乡射礼的前奏乡饮酒礼进行了概述,“惟州长之习民,择春秋之嘉日。苟审固之能娴,自兴贤之可必。主在阼而彬彬,宾当牖而秩秩。大夫方入,举旅之典未行;司正乃升,一献之仪已毕”。接下了对乐队合奏娱宾进行了说明:“县中间奏,合之者三笙;堂上工歌,和之者二瑟。于是三耦既比,射礼作焉。”之后对乡射礼的核心环节三耦射进行了重点描绘:
司射诱射,司马绳愆。下射居上射之右,上射在下射之先。其升也,惟在豫则钩于楹内;其降也,与升射者交于阶前。侯始系纲,将射之节文如是;获宁释算,初射之制度则然。尔乃设楅取矢,并洗当荣。继比众耦,再射遂行。主人耦宾,尊贤信其有等;大夫耦士,君子所以无争。射者之进退允齐,当物及物;获者之宫商悉协,举旌偃旌。既佽既调,体直而各思其鹄;不贯不释,心平而弗失其正。至于既卒射,较短长,中西数获,次第安详。司射去扑而视算,司马袒决而升堂。二算为纯,因左右而分胜负;十纯则缩,用奇耦而判阴阳。
于此,凌廷堪对第一番射、第二番射、第三番射、统计算筹等方面皆予以表现,不仅展示其仪节,且注意阐释其礼意,可谓形容曲尽。
接下来谈到了乡射礼与乡饮酒礼、大射仪的区别,“其礼不主饮酒,故谓之射;其礼杀于大射,故谓之乡”。继而表现了三番射后的旅酬饮酒礼以及主人送宾、宾拜谢主人的情况:
当是时也,胜者举趾靡矜,负者反躬宜审。钦实觯之雍雍,覩奉丰而凛凛。袭而加弛,似膺胥士之觵;袒而执张,如夺宫袍之锦。大夫饮于阶上,缘其位之已尊;宾主授于席前,所以优之独甚。大夫不胜,其耦不升;其耦不胜,升堂特饮。若夫届三射而弥文,居一篇之最后。典称乐正,攸司职在。大师所守,五终祗奏。夫驺虞九节,讵烦乎狸首?礼容乐节,奚须命中为能?折矩周规,但以循声是右;和容共尚,其余皆率初仪。退逊自甘,厥志惟祈斯酒。迨乎射礼竟,酬礼施,以下为上,由尊及卑,酬则有差,受者辩矣。爵行无算,乐亦继之。说屦乃羞,礼之成也不紊;送宾再拜,事之卒也咸宜。
凌廷堪还揭示了乡射礼的性质,“于五礼为嘉,研经师之训诂;居六艺之一,肄学士之威仪。”并表达了国家礼乐敷教的认同和赞颂,“敬五常而敷教,直跻虞舜命宫;本三物以作人,远迈姬公制礼。”这种全景式的仪节描绘与诠释是空前的。不仅体现了凌廷堪对礼学的融会贯通,也彰显出凌廷堪的社会诉求与时代自信。
5.《仪礼·丧服》。礼重于丧、祭(《礼记·昏义》),丧服制度不仅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对于伦理统系与社会秩序的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焦循《李贞女诗》中讲述了李贞女以妾的身份帮助亡夫抚养子嗣,“誓将以妾存吾夫,竟入夫家守贫窭”。显然与焦循该诗开头部分所说的传统礼制相背离:“古者不室即不父,葬不入兆庙无主。上殇立后惟大宗,士庶未昏死即腐。”“不室即不父”是《仪礼·丧服》女子为父所行之服制:“女子子在室为父,布总,箭笄,髽,衰,三年。子嫁,反在父之室,为父三年。”而“上殇立后惟大宗”的表述亦本于《仪礼·丧服》关于大宗收族不可绝后之礼:“尊者,尊统,上卑者尊统下,大宗者,尊之统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绝,故族人以支子后大宗也,嫡子不得后。”该诗通过贞女行为与传统礼制对比,揭示出李贞女超越常人的责任意识与奉献精神,从而凸显出李贞女的光辉形象。
其二,《校礼图》唱和,更是《仪礼》文学化的缩影。作为学者生活与文人生活的交叠景观,清代的访碑图、校书图等的出现及吟咏唱和饶有意味。围绕凌廷堪的《校礼图》,卢文弨及其学生臧庸为其作序和题跋;朱珪为其图题诗,阮元、王苏、钱大昕、洪亮吉、谢启昆、赵良澍、臧庸、许乔林等人均有赓和。这也是考察清人以学促文而形成交游群落的有趣素材。如朱珪《题凌仲子教授校礼图用昌黎荐士诗韵》,在礼学流衍史中,对唐宋元明《仪礼》学的衰微予以揭示,着意表彰凌廷堪在此领域的卓越创造:
《仪礼》十七篇,姬孔所教诰。圣人柔万物,节性义精到。损益兼夏殷,名物辨诏号。执肄非空文,绵蕞在师导。杂服礼斯安,相瞽缦可操。兰陵学久废,高密传亦耗。庆、悊虽分门,彦、植谁窥奥。昌黎掇奇辞,鸾铩欣鴃噪。豆笾失司存,珠玉毁儒盗。凌君起江南,便腹择履蹈。钩元有湛深,解纷无慢暴。璇玑攡九重,华离擘四墺。自求照水犀,不取籋云骜。勾股捷心能,均律悟雅好。凿空说耻骞,障澜更逾奡。源流汇朝宗,疏瀹先沟潦。治《礼》著《释名》,尊觯析酬报……
钱大昕《题凌仲子教授校礼图》推崇凌廷堪专精礼学,并引为学术知己:
我读《七戒》篇,伟哉凌君学。群言谢未能,《礼经》手目斠。《释例》十三章,大义何卓荦。古圣重人伦,以礼启后觉。揖让俯仰间,身心日追琢。教从童丱始,要使还诚悫。庄列崇玄虚,视道为桎梏。妇姑任勃溪,一室生羿浞。天未丧斯文,庆、戴守其朴。北海集大成,文字费商榷。流传二千年,学官閟楹桷。束阁置勿观,张眼等眊瞀。真儒起新安,褒然甲科擢。不嫌校官卑,说经颜峨峨。古器辨敦卣,正声叶征角,只手障回澜,功岂但一璞。我衰耄已及,废学众所嗀。忽枉瑶华诒,连城投和璞。敬亭云往还,千里途未邈。安得问字缘,黉堂许剥啄!
两人的学谊,如钱氏所称,“企慕之私,时在敬亭山色间也”,寓李白“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之意。
谢启昆《题凌次仲校礼图即送之宁国教授之任》肯定凌廷堪对《仪礼》抉发“奥义”之功,并从他与卢文弨结为学术“同好”而深感素心所仰:
《礼经》苦难读,谁能抉奥义?《三礼》既并称,二戴乃偏弃。陋儒束高阁,余唾拾文字。千载抱残阙,先生有笃嗜。茹古等珍羞,挑灯忘寝寐。校雠《十七篇》,《释名》编十二。诂言及器乐,七者循旧例。其五岀心裁,服馔官容位。考证附于后,旁通六籍备。刘、黄补疏漏,郑、贾订同异。壮年成进士,羞为刀笔吏。寒毡就一官,捧檄成夙志。宣城山水郡,北楼我所识。敬亭拓精庐,课士启经笥。古松流水间,聚讼决群议。麈尾清风来,带草媚青翠。道术湛以深,德容婉而睟。雄文六朝跨,余子三舍避。学士卢抱经,同好若笙吹。为君序卷端,欵欵敦古谊。绵蕞我未娴,披图发深媿。遥知万世后,传者非卿贰。
洪亮吉《校礼图为凌同年廷堪赋》认为,宣城因凌廷堪的到来由诗歌之乡变成了礼学大本营,实际上肯定了凌廷堪礼学的价值。赵良澍《为凌次仲二兄题校礼图后限用韩公荐士诗韵》表彰凌廷堪对《仪礼》疏释的重大贡献,认为其远绍周公、孔子、郑玄、贾公彦的礼学精神。阮元《题凌次仲教授廷堪校礼图次石君师诗韵》也是步朱珪所用韩愈《荐士》诗韵,认为《仪礼》的节文度数之中意蕴精微,凌廷堪兼小戴之学识和郑玄之操守,礼学造诣精深,其以例解礼为礼学研究辟途启钥。凌廷堪的同年王苏认为凌廷堪在《仪礼》研究方面的卓绝成就足以与郑玄、贾公彦千古对峙,相视而笑。此外还有许乔林亦参与了这次唱和,有“不从江、戴沾牙慧,高密功臣属此人”之句,认为凌廷堪的《仪礼》研究对郑学做了最好的继承与发扬。
这一时期对《仪礼》的探究乃至文学化的表现,主要是在汉学家当中形成了一定的氛围。由于这些礼学家的古礼探真具有一定的生活践履导向,他们对《仪礼》的“现身说法”中往往伴随着省思人生、指导现实的热情,这也为晚清士人进一步完成《仪礼》的审美建构奠定了基础。
礼学的选本化及引导文章“崇实”之风
由于社会危机加重,晚清士人普遍意识到作为儒家经世之学的礼学的重要性,“盖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加之乾嘉礼学成果的积淀与推广,礼学并不甘自限于经学的场域,逐渐向社会各领域渗透,其中礼学的选本化颇值得关注。魏源负责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特辟“礼政”一门,收入从清初顾炎武、张尔岐到道咸龚自珍、魏源的大量礼学文章,形成了16卷的宏大规模。魏源将这些礼学文章分为礼论、大典(上下)、学校、宗法(上下)、家教、昏礼、丧礼(上下)、服制(上下)、祭礼(上下)、正俗(上下)等几大部类。从类别设置即可看出魏源既注重学理的阐发,也强调现实的功用,体现出学治相济、体用兼备的特色。耐人寻味的是,在“礼论”部分,凌廷堪的《复礼上》、《复礼中》两篇礼学文章被放在了最前面。这说明,魏源对凌廷堪的复礼学说有着相当程度的关注。当然,魏源并无意纠缠于礼的细枝末节,贵在给社会以有形支持。如其在《文编》礼政部分,特设“正俗”一门,可见其用意所在。另外,《皇朝经世文编》无论就入选文章总数还是礼学文章数均以顾炎武最多,从中亦可窥出魏源与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密切联系。
如果说,魏源是首次系统地将礼学文章选本化作为其经世之学的重要支点,那么曾国藩则是首次系统地将《三礼》尤其是《仪礼》选本化。曾国藩对礼相当重视,他认为:“先王之道,所谓修已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在《圣哲画像记》中就将著有典章之书《通典》的杜佑和撰著《五礼通考》的秦蕙田也列入三十二圣哲之列,主要基于礼学的考虑。在《三礼》中,曾国藩甚重《仪礼》,如其《读三礼录》中涉及《仪礼》的部分最多。其《书仪礼释官后》对徽州学派的《仪礼》学予以表彰。而其同治六年(1867)二月写的日记中提到,其《仪礼》主要从张尔岐的《仪礼郑注句读》和张惠言的《仪礼图》入手。曾国藩不仅将礼学作为一种经世的重要手段,而且也清醒地意识到礼学与创作的相关性,他认为对不同经典的陶染会在文章风格上有相应的体现,“严慎而暇愉”风格的产生源自礼学的润化:“长于《礼》者,其言严慎而暇愉。”将礼学作为创作借鉴在其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得到有效落实。在这部文章选本中,曾国藩大胆收录了《周礼》、《仪礼》、《礼记》的一些篇章、段落。此外,《经史百家杂钞》还收录了韩愈的《读仪礼》、《读荀子》,王安石《周礼新义序》,曾巩《列女传目录序》,马端临《文献通考序》等与礼学关系甚为密切的文章。其中最值得重视的一点在于将《仪礼》的《士冠礼》《士相见礼》《觐礼》纳入选本范畴。且较之刘勰、颜之推、柳宗元,曾国藩更清晰立体地揭示了《仪礼》的衍生文类,曾国藩将文章分为著述门、告语门、记载门三大类,共11小类,其中“记载门”之“典志类”就颇受《仪礼》之影响,其云:
典志类,所以记政典者,经如《周礼》《仪礼》全书,《礼记》之《王制》《月令》《明堂位》,《孟子》之《北宫锜章》皆是;《史记》之八书、《汉书》之十志,及三通,皆典章之书也,后世古文如《赵公救灾记》是,然不多见。
对儒家经典进行别裁,将礼学元典纳入文章选本,在历史上尚属首次,故汪辟疆称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为“最大胆之古文选本”。其弟子黎庶昌的《续古文辞类纂》亦收录《仪礼》之《士冠礼》《士昏礼》《丧服子夏传》《士丧礼》《既夕》《士虞礼》《特牲馈食礼》,从而在曾国藩的基础上,继续将《仪礼》的文学选本化予以推进。
《仪礼》进入文章选本的视野,除了能有效弥纶唐宋八家已然恢拓的文章取法经术的创作思想体系,更值得瞩目的是,还隐然推动着一种具有经世抱负的写实或崇实的文风。诚然,曾国藩的古文之学瓣香于桐城派而不受其牢笼,所谓“扩姚氏而大之”,他一方面重视文以明道的古文传统,另一方面也善于感受时代学术风会。他能有心地对《仪礼》文学典范化加以标举,其实是吸取了清代礼学尤其是《仪礼》学中涌动的用世与征实的精神。在上述“典志类”的小序中,他看重“《仪礼》全书”等经史之著“记政典”的样板意义,并意味深长地举到曾巩《越州赵公救灾记》一文的难能可贵,其实是对“后世古文”如何贯通于礼制政典的经世征实之功提出了新的要求。
这篇被曾国藩示为“不多见”的《越州赵公救灾记》,其写作意图是详录赵抃在熙宁八、九年吴越饥疫兼作之际的救灾业绩,“著其荒政可师者”。《宋史·赵抃传》载:“吴越大饥疫,死者过半。抃尽救荒之术,疗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下令修城,使得食其力。”曾巩出任过越州通判,也出色地从事过救灾工作。全文的写作态度重在如实采摭,“予故采于越,得公所推行,乐为之识其详,岂独以慰越人之思,半使吏之有志于民者不幸而遇岁之灾,推公之所已试,其科条可不待顷而具,则公之泽岂小且近乎!”本文的意义不单单是赞美一位勤政清官,安慰越州人对赵公的思念感激之情,更要紧的是记录并推行赵公已经试行过的救灾“科条”,在面对天灾来袭时,有爱民之心的官吏不须顷刻就能拿出救灾的章程条例,那么赵公的恩泽怎么能说是很小并且只影响眼前呢?所以,这篇文章从详实于荒政科条的角度来说,正是秉承了《仪礼》等礼制典章之书的书写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晚清民国重视“写实”,似也是论文谈艺的一种风向。如孙学濂《文章二论》中强调作文的几个注意事项,其中之一即为“崇实”。再如刘师培关注什么样的书写文本称得上是“写实之楷模”:
中国古代之文体,本有数种,如《诗经》虽有赋、比、兴,而其中复有虚比;《周礼》之记官制固用实写,而只举大纲,不及细目,故二经之文体不尽为写实。然《仪礼》一书可为写实之楷模。其记某礼也,自始至终,举凡宾主之仪节方位,以至升降次第,一步一言,无不详细记载,须眉毕现。如《乡饮酒礼》于宫室制度、揖让升降,乃至酒杯数目皆描写尽致,今观其文即可想见当日之情形,此张皋文所以据之作《仪礼图》也。
对比唐代开元八年(720)国子司业李元璀感叹“《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谷梁》历代崇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仪礼》的楷模特征在于“庄敬”;宋代吕本中看到《礼记》和《周礼》作用于“议论文字”的功能,两者都尚未直接考虑到文体在“写实”层面的追求。刘师培的学术源自扬州学派,在礼学研究上融摄了徽州学系,在文统上属于推尊骈文的仪征派后劲。四库馆臣评价“《仪礼》则全为度数节文,非空辞所可敷演”,这种师法《仪礼》的写实态度经凌廷堪等人融入文学表达之中。再以刘师培提到的张惠言而论,他长于《易》、《礼》之学,阮元表彰他“以经术为古文”,且能在创作上“不遁于虚无”;曾国藩也特别欣赏张惠言“叙述朋旧,状其事迹”时,能“下笔称述,适如其量”。总之,清代中晚期的文章学,得益于学术与文风的互动关联,无论是六朝骈文系,还是唐宋八家散文系,抑或不拘骈散之文家,都对儒家经典影响场域的变动有所贡献。所以,由刘师培所表述的“《仪礼》一书可为写实之楷模”的结论,不是偶然的。《仪礼》的审美典范构建是清代经学审美化的一个重要突破点,不仅是清代《仪礼》学兴盛的投影折射,也反映了士人主观憧憬与现实情境碰撞、整合的动态历程。
①彭林:《三礼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②纪昀等:《仪礼述注提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二○,《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57页。
③王秀臣对三礼的文学价值进行了宏观论述,认为《仪礼》是仪式生活的文学实践,对《诗经》的各类诗与《仪礼》礼仪做了简单类比,但缺乏具体切实的论证。参见《三礼的文学价值及其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
④⑤⑥顾炎武:《仪礼郑注句读序》,《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32、32页。
⑦纪昀等:《仪礼郑注句读提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55页。
⑧钱大昕:《仪礼管见序》,《潜研堂文集》卷二四,《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88~390页。
⑨吴廷燮:《凌廷堪礼经释例提要》,《凌廷堪全集》第四册,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311页。
⑩凌廷堪:《礼经释例序》,《凌廷堪全集》第一册,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1页。
〔责任编辑:刘 蔚〕
吴戬,1981年生,文学博士,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曹虹,1958年生,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