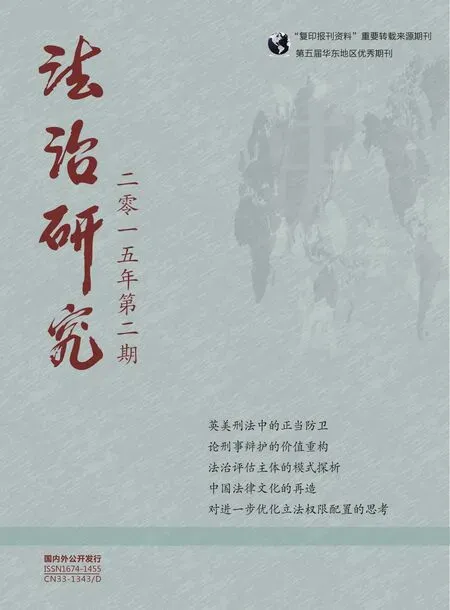论共犯与错误
2015-04-17郑泽善
郑泽善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外刑法理论界,共犯与错误关系问题,由于事关具有争议的共犯论和错误论,因此争论相对激烈。在共犯论领域,围绕共犯的处罚根据之责任共犯论、不法共犯论、因果共犯论,立论于不同的学说,有关正犯对共犯的影响程度,得出的结论往往迥异。在错误论领域,针对具体事实错误,有具体符合说、法定符合说和抽象符合说的对立;针对抽象事实错误,则有法定符合说、具体符合说和抽象符合说的争论,根据不同的学说,共犯的故意和正犯故意以及结果相异时,究竟在怎样一个范围内认定其符合,同样有不同观点的争论。①[日]中山研一等:《刑法1共犯论》,成文堂1997年版,第149页。
有关共犯论中的错误问题,应当适用单独犯中的错误理论。在共犯论中,能否恰切地适用单独犯中的错误论,对错误论来说,可以说是检验是否合理的试金石。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单独实行犯中难以想象的事例,在共犯关系中相对容易出现。需要注意的是,在共犯事例中,共犯者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独立意思主体的实行行为者的行为介入这一特殊性。因此,界定因果关系或结果归属关系的存在与否,同样具有重要意义。②[日]井田良:《刑法总论的理论构造》,成文堂2006年版,第405页。共犯与错误关系问题,主要有①同一构成要件内的错误、②不同构成要件内的错误和③间接正犯和教唆犯或帮助犯之间的错误三种情形。在上述三种情形中的①中,又有,比如X教唆Y去杀害A,被教唆者Y错把B当做A杀害(对象错误),这种认识的事实与发生的事实在同一构成要件内的具体事实错误,以及帮助犯是以帮助盗窃的意思参与盗窃行为,盗窃犯却实施了抢劫行为,这种涉及不同构成要件的抽象事实错误两种情形。在后一种情形中,由于犯罪结果超出共犯者的认识,因此,又可以称之为共犯过剩。情形②,是指错误发生在不同构成要件之内,比如,行为者出于教唆的意思实施教唆行为,被教唆者实施的结果却是帮助。这种共犯形式可以称之为“构成要件的修正形式”,由于可以将其理解为不同的构成要件(违法行为的类型),因此,共犯形式之间的错误可以视为抽象事实错误。针对这种情形,怎样把握“符合”的程度,自然成为有待探讨的问题之一。情形③,是指正犯与共犯之间的错误,由于它属于情形②的一个变种,因此,同样存在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共犯与错误问题比较常见,特别是近年来高发的雇凶犯罪案件中,由于雇凶者与被雇者对雇凶者所欲实施之罪或被雇者实际实现之罪的认识不一致,而造成了对雇凶者主观罪过认定的困难,很多判决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从而引发了学界的关注。比如,2000年发生在厦门市的谢甲雇凶杀人案,谢甲意图雇凶教训谢乙,最终被雇者却实施了杀人行为,并且发生了错误,杀死了与谢乙同去公司的经理李某,经鉴定谢乙只受了轻伤。这个案件聚讼的焦点在于:第一,谢甲的教训意图能否包括杀人的故意;第二,谢甲是否应该为被雇者杀害错误对象承担刑事责任。虽然最后判决认定谢甲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但直至今日该案例仍是学者们激烈争论的问题之一,远没有达成共识。③袁雪:《共犯认识错误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对共犯与错误问题的关注较少,即便有,也限于部分刑法教材或有关共犯、错误的专著中,研究对象只有共同实行犯、教唆犯等个别共犯形态的事实认识错误。鉴于这种理论现状,本文拟在概观、评析相关中外学说的基础上,就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探讨。
二、同一构成要件内的具体事实错误
所谓同一构成要件内的具体事实错误,是指教唆犯、帮助犯所认识的犯罪与实行犯所实施的犯罪,在行为事实情况方面虽然不符,但两者的犯罪构成要件相同。比如,甲教唆乙去杀丙,但乙误把丁当作丙杀害。像这种搞错具体侵害对象,而不同的犯罪对象体现相同社会关系的情形,就属于同一构成要件内的错误。
这种错误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①对象错误。教唆犯、帮助犯或实行犯对实行行为侵害对象的主观认识与客观现实不符,但其意欲侵害的对象与实际被侵害的对象体现相同的社会关系。比如,甲重金收买职业杀手乙杀害某房间内的一名旅客,以为此人就是自己想要除掉的丙,乙按照甲的意图杀了此人,但此人不是丙而是丁。又如,甲以为乙要去除掉自己的仇人丙,便把匕首借给乙,但乙杀害的不是丙而是丁。这是教唆犯、帮助犯对实行犯的实行行为所侵害对象发生认识错误的典型例子。另外,实行犯本人也可能搞错侵害对象。前述之甲教唆乙杀害丙而乙误把丁当作丙杀害就是其典型。②打击错误。④在日韩等国的刑法理论中,打击错误又称之为方法错误。受托于教唆犯、帮助犯的教唆、帮助的实行犯,针对某一犯罪对象实施犯罪行为时,由于失误而导致其实际侵害的对象与意欲侵害的对象并不一致,但两种对象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却相同。比如,甲教唆(或帮助)乙杀害丙,乙在对丙开枪射击时,因枪法不准而未能击中丙,误杀未能预见到的丁。③手段错误。教唆犯、帮助犯或实行犯对实施共同犯罪的手段(或工具)的性质或作用发生误解,从而未能发生预期的危害结果。比如,甲教唆(或帮助)乙用毒药杀害丙,乙却误把白糖当作毒药投进丙的茶杯中,因而未能引发预期的危害结果发生。
针对上述几种具体事实错误能否阻却教唆犯、帮助犯共同犯罪的故意,在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界,有不同观点的对立。针对对象错误来说,无论是取具体符合说还是取法定符合说,均认为不阻却共同犯罪的故意,因而主张教唆犯、帮助犯和实行犯都应对实际发生的危害结果承担故意犯罪既遂的责任。但是,针对打击错误(方法错误),具体符合说和法定符合说的结论不同。法定符合说认为,同一构成要件内的打击错误,不阻却共同犯罪故意的成立。无论是教唆犯、帮助犯还是实行犯,都应对实际发生的危害结果承担故意犯罪既遂的刑事责任。因此,按照法定符合说,区别对象错误与打击错误并没有实质性意义。⑤[日]日高义博:《刑法中错误论的新展开》,成文堂1991年版,第136页。有关这一问题,在我国的刑法理论界,主流观点倾向于法定符合说。比如,有观点认为“对同一构成要件内的错误,应采取法定符合说解决”⑥张明楷:《刑法学》(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99页。同样倾向于法定符合说的观点还有黎宏:《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07页等。针对法定符合说,在日本的刑法理论界,有观点认为,就同一构成要件内的具体事实错误而言,根据通说和判例所取的立场,即便发生的事实与行为者的认识有很大差距,行为与结果之间只要有相当因果关系,就不能阻却共同犯罪的故意,相关行为人对所发生的事实理应承担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比如,行为人教唆盗窃手表,被教唆者盗窃的却是钱包,在这种情形下,行为人成立盗窃(既遂)的教唆犯。但是,根据法定符合说,只要存在相当因果关系,作为故意犯不得不承担刑事责任,这种结果的归属,作为一种判断犯罪成立与否的基准,有可能导致处罚范围的无限宽泛。比如,X教唆Y去杀害A,实行犯Y基于打击错误将B杀死。在这种情形下,即便实行犯Y对B的死亡应负故意杀人(既遂)的刑事责任,但是,如果将这种死亡结果同样归责到教唆者的话(基于故意),那么,这种归责显然属于肯定某种连带责任,这一点从共犯从属性的视角看同样不尽妥当。针对所发生的结果,教唆者应承担故意责任的前提是,教唆者具体指示实行的方法或与实行犯一同出现在犯罪现场等,教唆者至少认识到实行犯在何种情形或用何种手段实施犯罪行为。参见[日]井田良:《刑法总论的理论构造》,成文堂2006年版,第407页。。但是,主张具体符合说的观点却认为,打击错误阻却共同犯罪故意,即针对实际发生的结果阻却故意。因此,在主张具体符合说的观点看来,区分对象错误与打击错误,针对教唆犯、帮助犯乃至实行犯的定罪和处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至于如何区分,对实行犯来说并不成为问题,但对教唆犯来说,自然成为问题。有关这一问题,有观点认为,在实行犯发生对象错误的情形下,教唆犯有可能是打击错误。因为教唆犯实施教唆行为时,并没有搞错具体侵害对象,只是由于后来的实行犯搞错侵害对象,才导致实际侵害对象与教唆犯意欲侵害对象的不符,这是一种打击错误而非对象错误。⑦同注⑤。在打击错误的情况下,对教唆犯应如何处理,又有不同观点的争论。⑧[日]浅田和茂:《教唆犯与具体事实错误》,载《西原春夫先生古稀祝贺论文集》(第2卷),成文堂1998年版,第403页以下。针对前述之意欲杀害丙而实际杀害丁的事例,有观点认为,对丙构成杀人的教唆未遂,对丁成立杀人的过失教唆;也有观点认为,构成杀人预备的教唆和过失致人死亡的正犯;还有观点认为只能按杀人罪的教唆未遂定罪处罚。
有关这一问题,本文倾向于法定符合说。在同一构成要件内具体事实错误的情形下,即使教唆者在教唆时指定了犯罪行为的时间、场所、方法,而被教唆者并没有严格遵照此要求实施犯罪,只要两者之间处于同一构成要件范围内,且教唆行为与被教唆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仍然可以成立教唆犯。比如,即使伪证者伪证的内容与教唆者教唆的内容之间多少有些出入,仍然不妨碍教唆者成立伪证罪的教唆犯。又比如,教唆者教唆行为人潜入甲家窃取财物,行为人却误入乙家窃取了衣物,此时教唆者仍然成立盗窃罪的教唆犯。⑨陈家林:《外国刑法通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27页。有关这一问题,在我国的刑法理论界,有观点认为:发生在同一构成要件内的对象错误,不阻却共同犯罪故意,无论是教唆犯、帮助犯还是实行犯,都应对实际发生的危害结果承担故意犯罪既遂的责任。因为,在这种场合,教唆犯、帮助犯与实行犯之间不仅有共同的意思联络,而且教唆、帮助行为与实行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实行行为侵犯的对象虽然不是教唆犯、帮助犯所追求的,但毕竟只有一个,并且这一对象与教唆犯、帮助犯意欲侵害的对象体现相同的社会关系,并没有超出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范围,所以,都构成共同犯罪的既遂犯。但是,在打击错误的场合,实行行为所侵犯的对象通常是两个,具有两个想象的犯罪构成:一是对实际侵害对象,教唆犯、帮助犯和实行犯都不希望或放任对其造成侵害,因此,谈不上有犯罪故意,在有过失并且刑法有处罚过失犯的规定的条件下,构成过失犯罪。二是对意欲侵害对象,各共犯人主观上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客观上教唆、帮助行为与实行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只是由于实行行为有误,才使犯罪未得逞,这属于共同犯罪未遂的情形。两者之间存在想象竞合关系,按从一重处断的原则,对教唆犯、帮助犯和实行犯一般都应以故意罪的未遂犯处罚。应该指出,在打击错误的场合,触犯的罪名虽然可能是两个,但实行行为只有一个,不可能构成实质上的数罪,因此,不能实行数罪并罚。此外,教唆犯对其所教唆的犯罪,也不可能是教唆预备。参见刘明祥:《刑法中错误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285页。
如前所述,有关这一问题,具体符合说的主张不仅与法定符合说不同,在具体符合说的内部也有分歧。笔者认为,具体符合说有以下致命缺陷:根据具体符合说,共犯与错误可以分为不阻却故意的错误(对象错误)和阻却故意的错误(打击错误),但是,这种主张未能提出具体的区别基准。比如,X教唆Y对特定的犯罪对象实施侵害行为,实行犯Y基于对象错误未能对X所意欲的犯罪对象实施侵害,而侵害了另外一个犯罪对象。针对这一问题,具体符合说的内部有不同观点的对立。其实,根据这种主张,理应得出实行犯的对象错误针对教唆者来说属于打击错误,因此应当阻却故意的结论。问题是,这种结论并没有充分的说服力。比如,X教唆Y去杀害A,基于Y的对象错误杀害的是B,在这种情形下,X对A构成教唆未遂,由于教唆未遂不处罚,⑩德国刑法有处罚教唆未遂的规定,不过只限于重罪。因此,只能构成故意杀人预备罪的教唆(不构成犯罪)和对B的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刑事责任。另外,如果这种情形发生在有关财产犯的共同犯罪,由于预备罪和过失犯均没有处罚的规定,因此,无法处罚背后的教唆者。⑪同注②,第407页。
在共犯错误的情形中,针对犯罪对象的确认,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实行犯。换言之,在这种情形下,共犯者对因果流程的支配处于弱势,很难控制一定要对特定犯罪对象实施侵害这样一个局面。因此,即便教唆者意欲侵害特定被害者,如果教唆者的故意只限于特定人,那么,以这种理由限定既遂的成立要件,显然不利于处罚犯罪。针对教唆者来说,在教唆行为终了的时点,在一定限度内已经把事态的发展交付给了实行犯,因此,对教唆者而言,重要的是能够保证对同种类犯罪对象的侵害结果的发生(基于某种程度的盖然性)这一状况本身。在此基础上,由于教唆者已经认识到这种状况,所发生的结果无非是行为者所认识到的危险得以实现的一个变种,可以说,行为人已经认识到了所意欲的结果发生。因此,将这种情形评价为教唆者的故意得以实现并没有任何障碍,即便教唆者所意欲的是特定的被害者,这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在刑法意义上并不存在决定性意义。⑫同注②,第408页。也就是说,实行犯的对象错误,并不能阻却共犯者的错误。
主张具体符合说的观点认为,如果不采纳具体符合说,有可能无法解决故意的个数问题。也就是说,比如①实行犯并没有按照教唆犯的意图杀害A,而错把B当作A杀死,当他知悉这一情况后,又将A杀死,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杀人的故意不限于A,那么,教唆者就要对两个杀人行为负刑事责任,这明显不尽合理。⑬[日]葛原力三:《共犯与错误》,载西田典之等编:《刑法的争论点》(第3版),有斐阁2000年版,第114页。然而,即便取具体符合说,恐怕也无法回避故意的个数问题。比如,②实行犯根据教唆犯的意图用长刀刺杀A后逃走,由于未能刺中要害部位,A只是受了重伤,知悉这一情况后的行为人,择日试图毒杀A,但仍然未能成功。③教唆者以为是同一犯罪对象,于是对实行犯进行教唆,但是实际犯罪对象是复数,比如,X指示Y杀害A,X以为是一个人的A是双胞胎,Y杀害其中的一个后,误以为杀错,又杀死另一个的情形下,能否成立数个故意犯(既遂或未遂)就成为问题,根据教唆者表象⑭经过感知的客观事物在脑中再现的形象。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85页。而限制故意犯的个数恐怕不大可能。在事例②和③的情形下,不同的结果均可以归属于教唆行为,因此,姑且将这种情形视为数个故意,在此基础上,在量刑阶段限定一个故意进行处罚并非不可能。另外,就事例①而言,在适用错误理论之前,可以考虑基于所发生的结果否定共犯的成立,或者根据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而否定犯罪成立的余地。也就是说,既然教唆者没有对实行犯要求不管杀死多少也要杀死A,因此,将第二个被杀的教唆归责于背后的教唆者恐怕不大合理。将超出共同犯罪意思联络(合意)之外的结果,归责于共犯者显然不尽妥当,比如,被教唆实施杀人行为的被教唆者,明知所要杀的杀害对象不是教唆者所意图的杀害对象,基于其他原因杀死另外一个人时,恐怕就不应追究教唆者的刑事责任。⑮同注②,第 409页。因为这种结果已经超出了教唆者和实行犯的意思联络之外,因此就不应归责于教唆者。
三、不同构成要件之间的错误(抽象事实错误)
有关抽象事实错误(不同构成要件间的错误)的处罚,在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界,有以下几种学说的对立。抽象符合说认为,在抽象事实错误的情形下,只能成立针对相对较轻的犯罪的故意(以故意犯处罚)。法定符合说认为,针对所发生的结果,原则上不能成立故意,作为一种例外,在其重合的范围内肯定故意的存在。具体符合说则认为,与法定符合说一样,在其重合的范围内肯定故意的存在,不过成立的范围比法定符合说宽泛,因此,这种学说又称之为具体法定符合说。⑯同注①,第 155页。当然,具体在怎样一个范围内重合,根据具体事例,无论是学说还是判例,均有不同程度的争论。
另外,这一问题与怎样理解和把握共犯的处罚根据具有密切的关联性。比如,X教唆Y去实施盗窃行为,Y实施的却是抢劫行为,在这种情形下,无论取哪一种学说,X在盗窃罪的范围内受到处罚。但是,如果取立论于责任共犯论的完全犯罪共同说,既然实行犯实施的是抢劫行为,因此,教唆者X也应成立抢劫罪的教唆,根据相关规定(指《日本刑法》第38条第2款),X的处罚应限于盗窃罪。如果取基于不法共犯论的部分犯罪共同说,教唆的认定应限于盗窃罪和抢劫罪重合的那一部分,因此X的罪名应限于盗窃罪之内。如果取立论于因果共犯论(纯粹惹起说)的行为共同说,Y基于所实施的实行行为成立抢劫罪,X实施的是盗窃的教唆,因此,与部分犯罪共同说的结论相同。
有关抽象事实错误的事例,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形:比如,X教唆Y去实施P罪,Y实施的却是Q罪,这种情形又可以分为:①Y明知自己实施的犯罪行为与X当初教唆的犯罪不同,仍然实施Q罪;②Y一开始就误解了X的意图,实施Q罪,而非当初被教唆的P罪;③Y本身很想实施P罪,由于发生认识错误,实施的却是Q罪三种情形。
其实,一般并不区分上述三种情形,不过,有关情形①和②(尤其是情形①),作为谈论错误论之前的问题,能否成立共犯或者说能否肯定共犯行为与实行犯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结果归属关系就成为问题。有关这一问题,是否成立共同正犯(共同实行犯)尤为重要。因为共同正犯的成立,主观方面要有共同实施犯罪之意思上的联络或相互之间的了解,如果主观上并不存在意思上的联络,基于部分犯罪共同说,就不具备共同犯罪成立要件中的主观要件。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形下,共同犯罪的成立要件问题与共同犯罪中的错误问题发生重合,逻辑上应当先考虑共同犯罪的成立与否。在事例②的情形下,即便共同犯罪者之间存在意思上的联络,然而,一开始就出现龃龉,比如,X基于故意杀人的意思,Y则出于故意伤害的意思,共同对A实施伤害行为(不知是谁的行为引起的伤害结果)导致被害人重伤,由于两种罪名的构成要件发生“重合”,因此,可以在重合的范围内肯定共同正犯的成立(即适用部分行为的全部责任之法理)。就发生结果而言,X成立故意杀人罪的未遂,Y则成立故意伤害罪。能够得出这种结论的学说就是部分犯罪共同说,⑰部分犯罪共同说继承了完全犯罪共同说的理念,强调共同犯罪就是数人共同实施具有相同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与完全犯罪共同说的区别在于,部分犯罪共同说并不要求数人所实施的犯罪完全相同,只要部分一致就够,即数人共同实施的不同犯罪之间,如果具有构成要件上的重合,那么,在此重合的限度之内,就可以成立共同犯罪。比如,在A以伤害的故意,B以杀人的故意,共同向C施加暴行,结果将C打死,但无法查清究竟是谁的行为引起了C死亡结果的情况下,按照部分犯罪共同说,尽管因为A并不具有杀人的故意,因此不能和B一起成立故意杀人罪的共同犯罪,但是,由于在杀人罪的故意中,已经包含有较轻的伤害罪的故意,而在杀人的行为当中,同样包含伤害行为在内,因此,A和B之间,由于在故意伤害(致死)罪的范围内具有重合性,因此,两者之间可以成立故意伤害(致死)罪的共同正犯。其中,由于B的行为超出了A、B之间重合的范围,B除了与A一起成立故意伤害罪的共同正犯之外,还要对故意杀人的结果承担责任,即成立故意杀人罪的单独犯。由于B的故意杀人罪的实行行为与A之间成立的故意伤害罪的共同正犯的实行行为,实际上是一个行为,因此两者之间成立想象竞合,可以依照“从一重处罚”的原则,成立故意杀人罪。按照部分犯罪共同说,在前述的例子当中,A最终成立故意伤害罪(共同犯罪),而B只成立故意杀人罪。有关这一问题的详细情况,可参见郑泽善:《刑法总论争议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10页以下。针对这一结论,有观点认为,比如教唆犯教唆实行犯去实施盗窃行为,实行犯在实施盗窃行为的过程中被人发现,转而实施抢劫行为。在这种情形下,对没有重合部分(基于暴力、胁迫压制对方反抗)具有故意的行为人,是否应对重合部分成立单独犯(限于强盗罪一罪,其他行为人成立盗窃罪的共同实行犯),或者对重合部分成立共同实行犯,对不重合的部分成立单独犯(盗窃罪的共同实行犯+暴力、胁迫罪⑱《日本刑法》第222条规定:以加害生命、身体、自由、名誉或者财产相通告胁迫他人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万日元以下罚金。,甚或成立盗窃罪的共同正犯加上抢劫罪的单独犯),其结论和处罚根据均不明确。⑲同注⑬,第115页。需要注意的是,共同实行犯的成立,关键是作为因果性的补充和正犯的结果归属能否得以肯定这一点,即便这一点与参与者所参与的部分犯罪行为吻合,也不影响犯罪的成立。⑳有关这一问题,在我国的刑法理论界,有观点认为处理相异构成要件共犯认识错误的基本原则是:如果共同行为人主观预见的事实与客观发生的事实不属于同一构成要件,成立相异构成要件共犯认识错误,对于主观预见的事实阻却故意的既遂,成立故意的未遂犯,对于实际发生的事实,原则上阻却故意的成立,在行为人负有预见义务且刑罚处罚过失的情况下,构成过失犯,与故意的未遂犯构成想象竞合,按照想象竞合犯的处断原则处理,如果行为人没有预见义务,则属于意外事件。但是,如果行为人主观预见的构成事实与客观发生的构成事实在构成要件上具有实质性重合,则在重合的限度内成立故意的既遂。按照这一原则,对于相异构成要件共犯认识错误的处理可以分为两种情况:(1)共犯人主观认识的构成事实与客观发生的构成事实在构成要件上不具有重合性时,排除故意的既遂。(2)共犯人主观认识的构成事实与客观发生的构成事实在构成要件上具有重合性时,在该重合的限度内,作为共同故意犯的既遂形态予以处理。杨阳:《论相异构成要件的共犯认识错误》,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总第118期),第12页。
有关抽象事实错误中的符合性判断,日本的判例和通说取的是法定符合说,这种学说的认定基准是“构成要件的实质性重合”。即,P罪的构成要件和Q罪的构成要件之间,如果实质上存在“重合”关系,那么,在这重合的范围内成立故意犯的既遂。在是否成立教唆犯的前述事例②的情形下,在P罪与Q罪之间实质性重合的构成要件范围内,X应承担教唆犯的刑事责任。作为与上述事例,即共同实行犯相似的例子,可举X教唆Y去杀害A,Y误以为是让自己去伤害A,于是对A实施了伤害行为。根据法定符合说,Y成立故意伤害罪,X则成立故意伤害罪的教唆(针对杀人行为,作为未遂教唆而不可罚)。针对法定符合说,批判的观点认为,这无非是在刑罚法规(裁判规范)的层面上要求两个构成要件的重合,而没有理论依据,同时在结论上不得不限制故意犯的成立范围,因此不尽合理。比如,判例的立场是,X和Y共谋,决定教唆公务员A去实施制作虚假公文书的行为,Y却教唆B去实施伪造公文书的行为并且成功,针对这一事例,裁判所认为,X成立伪造公文书罪的教唆犯。㉑《刑集》第2卷第11号,第1386页。针对这一判决,有观点认为,不能说判例的立场有错误,但是,在怎样的意义上两罪之间作为裁判规范具有构成要件的重合性,该判例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㉒[日]团藤重光:《刑法纲要总论》(第3版),创文社1990年版,第427页。笔者认为,其实,这里成为问题的并非作为裁判规范的构成要件的符合,而是为了肯定违反行为规范而要求的,最低限度内的“一般人所认识”的内容的重合。应当关注的是面向行为人而具体化了的行为规范,即行为人基于怎样一个意思内容实施侵害行为而违反行为规范,根据这种基准,如果基于实现P罪的意思与实现Q罪的意思发生重合,那么,在这一限度内应当肯定故意犯的成立。根据这一基准,比如,X教唆Y去欺骗A获取财物,Y却以恐吓的方式劫取财物的情形下,X可以成立恐吓罪㉓《日本刑法》第249条规定:恐吓他人使之交付财物的,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前项方法,取得财产上的不法利益或者使他人取得的,与前项同。的教唆犯。㉔同注②,第 411页。
有关抽象事实错误问题,在我国的刑法理论界,主流观点认为,实行过限和实行减少不属于共犯错误的范畴。只是由于它们与共犯错误有紧密联系,学者们通常在论述共犯错误问题时,也附带作些说明。㉕陈兴良:《共同犯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0页以下。有关实行过限对教唆犯刑事责任有无影响问题,在我国的刑法理论界,一般分两种情况来论述:一是重合性过限,即被教唆者所实行的犯罪与教唆者所教唆的犯罪之间具有某种重合性的情形下发生的过限。比如,甲教唆乙去伤害丙,乙却杀害了丙。在这种情形下,甲只负教唆故意伤害罪的刑事责任,乙则应负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就教唆犯而言,应视为被教唆的人实现了其所教唆的罪。二是非重合性过限,即被教唆的人除了实行教唆犯所教唆的犯罪之外,还实施其他犯罪。比如,甲教唆乙去盗窃,乙在盗窃之后,又强奸了女主人。在这种情形下,针对被教唆的人过限实行的强奸行为,教唆者不负刑事责任。㉖吴振兴:《论教唆犯》,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页。有关实行减少的情形下,对教唆犯应如何处理,有观点认为,对教唆犯应按所教唆的罪的未遂犯定罪处罚。比如,甲教唆乙去杀害丙,乙改变主意没有杀害丙,只是伤害了丙。那么,甲就应负教唆故意杀人(未遂)罪的刑事责任,乙则应负故意伤害罪的刑事责任。㉗同注㉕,第 385页。也有观点认为,在实行过限和实行减少的场合,由于实行犯改变了犯意,实行了与预谋犯罪不同的罪,所以,共同犯罪不能成立,狭义的共犯错误也就无从谈起。但是,从广义上讲,在实行过限和实行减少的场合,由于实行犯所实行的罪与教唆犯、帮助犯所预见的罪不符合,并且这是发生在共同犯罪过程中,也是共犯错误所要研究的问题。因此,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中的具体符合说、法定符合说和合一的评价说,认为上述情形属于共犯错误的范畴,应适用错误理论来解决,这也无可非议。只不过其具体处理办法不够妥当。㉘刘明祥:《刑法中错误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页。这种主张认为,比如,按照具体符合说,教唆者、帮助者认识的事实与实行犯实行的事实不是具体的相一致,因此,对实际发生的危害结果阻却教唆、帮助的故意,结论是教唆者和帮助者都不可罚。如果这样处理,显然会放纵犯罪。正因为如此,持具体符合说的论者又对其作了一些修正,认为在实行过限的场合,假如仅仅只是量的过限,就不阻却教唆、帮助的故意,教唆者、帮助者对其所预见的犯罪,构成教唆犯、帮助犯。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放纵犯罪的结果发生,但与具体符合说的立场并不吻合。按照法定符合说,在实行过限的场合,如果教唆者、帮助者所认识的犯罪与实行犯所实行的犯罪在构成要件上重合,则对教唆者、帮助者按其所认识的犯罪定罪处罚,这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两者在构成要件上不重合,因为阻却故意,而不处罚教唆者、帮助者,这也同样会出现轻纵犯罪的后果。另外,在实行减少的场合,法定符合说主张,对教唆者、帮助者按实际实行的轻罪定罪处罚,这又明显违反了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因为教唆者、帮助者主观上具有犯所教唆、帮助之罪的故意,而并无犯实行犯所实行的较轻的罪的故意,不存在按这种轻罪定罪处罚的主观基础。另外,按合一的评价说,在实行过限的场合,对教唆者、帮助者应以实行犯实行之罪定罪,但依照其所预见之罪的法定刑处罚。这无疑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因为,教唆者、帮助者对实行犯所实行之罪本无认识,却要以这种故意罪定罪,定了此罪而不适用此罪的法定刑,但要按其他罪的法定刑处罚,显然不合情理,也与法理相悖。这种观点继而认为,有关抽象事实错误的处罚问题,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理论界之所以有不同学说的争论,是因为一些国家(日本)的刑法规定中,并没有针对被教唆人、被帮助人没有犯教唆犯、帮助犯所教唆、帮助之罪的规定;另外,对未遂犯也以法律有明文规定才能处罚。这样一来,教唆未遂、帮助未遂往往就不可罚。为了避免放纵这类教唆犯、帮助犯,不同学说从不同的角度,将一些教唆未遂、帮助未遂解释为可以成立教唆罪、帮助罪。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立法上的漏洞,但却引起了理论上一些不必要的争论和混乱。我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明确规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教唆犯也应定罪处罚。这一规定为我们解决实行行为过限或减少的场合,对教唆犯如何处罚的问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按照这一规定,无论是实行过限还是实行减少,对教唆犯都应按其所教唆的罪定罪量刑,对被教唆的实行犯则按其所实行的罪定罪量刑。这样,既能充分体现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又合情合理。㉙刘明祥:《刑法中错误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页。
本文认为,教唆犯只有在实行犯的实行行为与其所教唆之间存在紧密关联时,才对实行犯的既遂负责。针对实行犯所造成的过剩结果,教唆犯并不负责。共犯过剩包括质的过剩和量的过剩。质的过剩,是指被教唆人所实行的犯罪完全不同于被教唆的犯罪的情形。因为质的过剩,教唆人不承担被教唆者所犯之罪的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的规定,只承担教唆未遂的责任。量的过剩,是指被教唆人所实行的犯罪与被教唆罪并不完全一致,但存在重合部分。比如,被教唆盗窃的人,实施了抢劫行为;被教唆伤害他人的人,实施了杀人行为,由于盗窃罪与抢劫罪之间、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杀人罪之间具有一定的重合关系,在教唆犯认识的事实与被教唆者实现的事实相互重合的范围内,可以认定教唆犯成立盗窃既遂、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的教唆犯。㉚周光权:《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2页。在我国的刑法理论界,同样有观点认为,例如,甲教唆乙盗窃,但乙实施了抢劫;A教唆B伤害,B实施杀人行为。在这种场合,甲、A只能在与其认识的事实相重合的范围内承担既遂责任。即甲只承担盗窃罪(既遂)的责任(不能认为乙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因为在规范意义上说,抢劫罪包含了盗窃),A只承担故意伤害致死的责任。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02页。可以说,这种主张与前述之法定符合说的结论相同。另外,有关这一问题,韩国主流观点的立场也倾向于法定符合说。详细可参见[韩]金日秀、徐辅鹤:《刑法总论》(第10版),博英社2005年版,第643页。
四、不同共犯形式内的错误及正犯与共犯间的错误
(一)不同共犯形式内的错误
不同共犯形式内的错误,是指共犯之间只是犯罪实现形态的不同,这种差异不涉及犯罪类型的本质。也就是说,共犯只是在其犯罪形式上存在差异,罪质则没有差别。因此,当错误跨越不同的共犯形式时,应成立其中较轻形式的共犯,这是日本的通说。㉛[日]川端博:《刑法总论》(第2版),成文堂2006年版,第599页。第一,就教唆的意思发生帮助结果的情形而言,行为人误以为他人没有犯罪的决意而实施教唆行为,实际上他人已经决意实施犯罪行为,行为人的教唆不过起到强化他人犯罪决意的作用。针对这种情形,通说认为应成立帮助犯。这是因为缺乏教唆的结果,不能作为教唆犯处罚。但教唆犯的意思中实质上包含着帮助的意思,因此应认定为帮助犯。第二,针对帮助的意思发生教唆结果的情形来说,即行为人误以为他人已经具有犯罪决意而意图进一步强化其犯意,实际上他人是由于行为人的行为而产生犯罪决意时,通说同样认为应当成立帮助犯。这是因为行为人既然不具有教唆的故意,就不能作为教唆犯加以处罚。但教唆行为从实质上看,也可以认为包括可视为帮助行为的部分,所以应成立帮助犯。第三,就教唆的意思发生间接教唆结果的情形而言,行为人教唆他人实施犯罪行为,但被教唆者并没有亲自实施实行行为而是教唆第三者实施犯罪行为时,通说认为由于这种错误在教唆这种共犯形式范围之内,所以不阻却教唆的故意,应当成立教唆犯。㉜陈家林:《外国刑法通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29页。
有关这一问题,在我国的刑法理论界,主流观点认为,“由于共犯的犯罪形式不同并不影响罪质,因此,关于不同共犯形式的错误,应当在有责的违法限度内,成立其中较轻的共犯形式。例如,行为人以共同正犯的意思望风,但实际上只起到了帮助作用时,只成立帮助犯。再如,他人已经产生犯罪的决意,行为人以为还没有产生犯罪的决意而实施教唆行为的,也只成立帮助犯”㉝张明楷:《刑法学》(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01页。。
如前所述,不同共犯形式内的错误,比如基于教唆的意思实施的结果却是帮助,在这种情形下,中外刑法理论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在较轻的共犯形式内成立共犯。其实,这种情形也属于抽象事实错误的一种,针对同一犯罪的不同共犯形式,不过是针对同一法益侵害行为的一个变种,因此,可以将这种情形视为“构成要件的实质性重合”。本文认为,不同的共犯形式虽然分属于不同的行为规范,但是,当它作为行为规范发生作用时,作为一种故意,在一般人的认识层面上重合,换言之,基于同一的认识内容(故意)而等同于违反行为规范,因此,可以在有责的违法限度内,成立其中较轻的共犯形式。
(二)正犯与共犯间的错误
正犯与共犯间的错误,又称狭义共犯与间接正犯之间的错误,包括基于教唆、帮助的故意而客观上产生间接正犯事实的情形,也包括基于间接正犯的故意而产生教唆犯、帮助犯事实的情形。由于间接正犯与教唆犯之间的错误以及间接正犯与帮助犯之间的错误,在处理方法上没有区别,这里的论述限于间接正犯与教唆犯之间的错误。
1.以间接正犯的意思实施教唆行为。这是指行为人由于认识上的错误,以间接正犯的意思而实际上实施了相当于教唆行为的情形。比如,医生出于杀害患者的意思指示护士为患者注射毒药,他以为护士并不知道所注射的是毒药,但是,实际上护士已经察觉到这一点而仍按医生的指示加以注射。又比如,利用者误以为被利用者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让其去实施杀人行为,实际上被利用者已经达到了刑事责任年龄,利用者的行为起到的是教唆的作用。应怎样处理上述案件,在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中,有间接正犯说和教唆犯说的对立。
间接正犯说又称主观说,这种学说认为,即便被利用者知情,由于背后者的行为相当于杀人罪的实行行为,因此与被利用者的行为发生竞合,成立杀人罪的正犯。理由是:虽然背后者的行为也成立杀人的教唆,但是,应当被正犯行为所吸收。㉞同注㉒,第 429页。针对这种主张,批判的观点认为,这种主张一方面强调教唆犯属于修正的构成要件,正犯属于基本的构成要件,两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另一方面又认为即使行为人没有实现间接正犯的结果,仍然成立间接正犯的既遂,两者之间明显存在矛盾。㉟[日]山中敬一:《刑法总论》(第2版),成文堂2008年版,第951页。针对这种批判,倾向于这种主张的观点认为,由于背后者具有实行行为,因而应当成立间接正犯。但是,既然被利用者已经知情,他所实施的实行行为就已经超出了相当因果关系的范围,因而应当成立间接正犯的未遂。㊱转引自注㉜,第630页。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既然背后者利用从一开始就知情的被利用者时应成立教唆犯,那么,即使误以为被利用者不知情,也不会丧失因果关系的相当性。因此,主张间接正犯未遂的主张也不妥当。㊲同注㉜,第 952页。
教唆犯说又称折中说,这种学说认为,间接正犯与教唆犯在客观上具有不同的构成要件形式,其故意内容也不同。但是,间接正犯的故意可以被教唆犯的故意所包摄,因而基于错误理论应当肯定教唆犯的故意。根据这种学说,间接正犯的故意包含着自己亲自直接触犯法规范的意识,而教唆犯的故意则仅包括通过他人触犯法规范的意识,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不过,由于间接正犯的故意包含较轻的教唆故意,因此,应当在客观所成立的较轻的教唆犯的限度内认定故意犯的成立。也就是说,间接正犯的故意指的是将他人作为工具加以利用而实现特定犯罪的意思,因而在广义上可以包括教唆的故意,这时的错误可以视为法定的符合。因此,以间接正犯的故意而引起教唆的事实,由于间接正犯比教唆犯的罪责更重,因此,可以成立较轻的教唆犯。㊳同注㉛,第 600页。这是日本的通说。
2.以教唆犯的意思实施间接正犯行为。这是指行为人由于认识上的错误,以教唆犯的意思实施了实际上属于间接正犯行为的情形。有关这一问题,在日本的刑法理论界,部分观点主张应成立间接正犯。但压倒性通说主张应成立教唆犯。因为行为人虽然实施了较重的间接正犯行为,但只具有较轻的教唆犯的故意,根据《日本刑法》第38条第2款,应成立教唆犯。㊴同注㉛,第 602页。
有关正犯与共犯间的错误问题,在韩国的刑法理论界,主流观点认为,这一问题可以分为两种情形,(1)被利用者有无责任能力的错误问题和(2)被利用者有无故意的错误问题。㊵[韩]朴相基:《刑法总论》(第6版),博英社2005年版,第428页以下。
就(1)之被利用者有无责任能力的错误问题而言,又可以分为①行为人误以为被利用者没有刑事责任能力,实际上被利用者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情形(误以为被利用者是精神病患者,实际上被利用者是精神正常者)和②行为人误以为被利用者有刑事责任能力,实际上被利用者无刑事责任能力的情形。在情形①,行为人利用者并没有支配被利用者的行为,被利用者本人才是行为的支配者。因此,在这种情形下,主张成立间接正犯的观点并不正确,而应成立教唆犯。由于在这种情形下,教唆者误以为在利用着“无刑事责任能力者”,这误以为本身就是主观上教唆的故意,客观上被利用者根据利用者的教唆实施了教唆行为,因此具备了被教唆者的要件。在情形②,即利用者误以为被利用者有刑事责任能力,实际上被利用者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情形下,根据利用者本人的认识,可以成立教唆犯。
就(2)之被利用者有无故意的错误问题而言,同样可以分为①行为人误以为被利用者没有故意,实际上被利用者有故意的情形和②行为人误以为被利用者有故意,实际上被利用者没有故意的情形。有关情形①,㊶医生甲欲想杀害妻子乙,甲以为护士A并不知情,让A给妻子乙注射毒药。一直爱慕(单相思)医生甲的A不仅知情,还想替代乙的位置,于是她遵照医生甲的医嘱用毒药杀害了乙。部分观点认为,在这种情形下,行为人成立间接正犯的未遂,也有观点认为,应成立教唆犯。在事例①的情形下,从结果上看,医生甲所意图的结果已然发生,因此,似乎可以成立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正犯。但是,甲的“利用行为”只停留在想象之中,A是基于自己的杀人故意实施了行为,因此,甲对A的意思支配并不存在。因此,医生甲可以成立间接正犯的未遂。由于在这种情形下,直接行为者基于自己的行为支配而丧失了工具性,不能将杀人的结果归属于“间接正犯”。有关情形②,㊷乙女将装有致死量的毒药瓶递给情夫甲,让他毒杀原配妻子。乙女误以为甲知道药瓶中的毒药足以致人死亡,并且也想杀死原配妻子,但是,甲并没有杀害原配妻子的想法,甲误以为是一般药物而让妻子服用,结果导致其妻死亡。即利用者误以为被利用者有杀人的故意,但被利用者并没有杀人的故意。针对这种情形,部分观点认为,乙不成立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也有观点认为,应当成立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在这种情形下,由于无法认定被利用者有故意的正犯行为,因而无法认定被教唆者(故意杀人罪的正犯),因此,利用者就不能成立教唆犯,同样也不能成立帮助犯。另外,根据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也不能成立间接正犯。因为针对利用者而言,并不存在利用没有故意的工具这一认识以及意思上的支配。但是,基于处罚利用者这一刑事政策上的必要性,根据《刑法》第34条第1款,可以认定间接正犯的成立。
有关这一问题,我国刑法理论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有关狭义共犯与间接正犯的错误,有以下三种情况值得研究:第一,以间接正犯的意思利用他人犯罪,但产生了教唆的效果。在这种情形下,仅以主观方面为标准进行判断是片面的,必须同时考虑主观与客观两方面;从责任的实质来看,间接正犯的故意也符合教唆的故意,故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具有相对的合理性。第二,以教唆犯的意思实施教唆行为,但产生了间接正犯的结果。例如,甲误以为乙具有责任能力,教唆乙杀人,实际上乙没有责任能力,乙在无责任能力的状态下杀害了人。就结论而言,甲只成立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既然得出甲成立教唆犯的结论,就表明教唆犯的成立不以引起被教唆者的故意为前提,只要引起乙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即可。乙确实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故甲成立教唆犯。第三,被利用者起初具有工具性质,但后来知道了真相。例如,医生甲意图杀死患者丙,将毒药给不知情的护士乙,乙后来发现是毒药,但仍然注射了该毒药。在这种情形下,甲通常是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因为间接正犯的成立要求利用者支配犯罪事实,但在上述场合,由于乙已知情,故甲不符合间接正犯的条件。其实,在这种场合,完全可以肯定甲的行为引起了乙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的意思,因而属于教唆行为,又由于间接正犯的故意符合教唆犯的故意,故对甲的行为应以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论处。㊸同注㉝,第401页以下。
笔者认为,在狭义共犯与间接正犯间错误的情形下,应当在较轻范围内成立共犯。其实,这同样属于抽象事实错误的一种情形,即事关同一犯罪的不同的共犯形式,可以将其视为同一法益侵害行为的变种,因此,在此意义上可以肯定“构成要件的实质性重合”。虽然不同共犯形式分属于不同的行为规范,当它作为行为规范发挥作用时,作为故意所要求的,在一般人认识层面上重合。也就是说,同一认识内容构成不同的(基于故意的)违反行为规范。共犯形式中的犯罪有轻有重,行为者所认识的事实与所发生的结果不同时,即所发生的结果重于认识的事实时,可以以较轻的犯罪予以处罚。
以间接正犯的意思利用他人实施犯罪行为,却产生教唆犯的效果时,由于实现的事实是教唆犯的事实,间接正犯的故意包含在教唆犯的故意中,可以肯定对所发生的事实的故意的存在,因此,可以肯定教唆犯的成立。在这种情形中,不能否认成立间接正犯未遂的可能性,然而,由于教唆犯的既遂重于间接正犯的未遂,可以把间接正犯的未遂吸收到教唆犯的既遂之中。与此相反,以教唆犯的意思实施教唆行为,却产生了间接正犯结果的情形下,由于无法肯定对所发生的间接正犯事实具有故意,因此,在较轻的教唆犯的范围内肯定故意犯的成立。㊹同注②,第 412页。比如,行为人误以为教唆某一犯罪,被教唆者基于故意实施被教唆行为,然而,被教唆者并没有领会教唆者的意图,所实施的行为并非基于故意,即成了教唆者的犯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