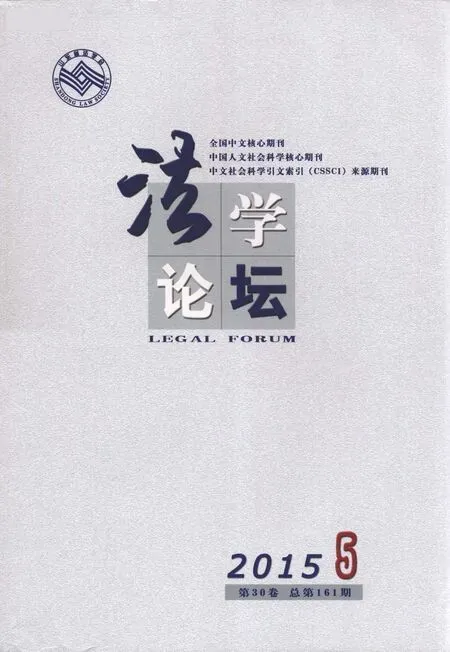儿童福利权国家义务论
2015-04-16吴鹏飞
吴鹏飞
(江西财经大学 法学院,江西南昌 330013)
【学术视点】
儿童福利权国家义务论
吴鹏飞
(江西财经大学 法学院,江西南昌 330013)
儿童福利权国家义务是由国家作为儿童最高监护人、人权义务主要主体、公共物品重要提供者等身份所决定的,主要包括静态层面的最低核心义务和动态层面的尊重、保护和实现义务,是行为义务与结果义务、消极义务与积极义务的统一。我国儿童福利权国家义务履行呈现城乡、区域(省际)以及福利机构与原生家庭多重二元结构,存在立法碎片化、行政管理虚化、救济程序缺位等问题,亟待采取立法、行政、司法、社会协同、国际合作等方式予以矫正和落实。唯有树立儿童优先理念,将儿童福利上升为国家战略,方能更好地满足儿童基本生存、提高生活质量的福利需求。
儿童福利;儿童福利权;国家义务;监护
儿童*《儿童权利公约》第1条规定:“儿童系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除非对其适用之法律规定成年年龄低于18岁。”因而,本文所指的儿童,是指年龄未满18岁之人,与我国的未成年人同义。福利权是《儿童权利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诸多国际人权公约中规定的一项儿童人权。从宪法人权角度看,儿童福利权是儿童在生存、发展的过程中,因儿童之为人的尊严而从国家、社会和家庭获得保障或服务,以满足其基本生存、提高生活质量之需求的基本权利,*从权利外延来看,儿童福利权包括生存与发展权、健康与保健服务权、受教育权、适当生活水准权及残疾儿童特别照顾权等权利类型,参见吴鹏飞:《儿童福利权体系构成及内容初探——以宪法人权理论为视角》,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2期。需要国家的尊重与保障。然而,中国始终秉承“养不教,父之过”的理念,认为家庭照顾是儿童福利权实现最直接且最重要的模式,儿童福利权国家义务鲜有提及,政府唯有在儿童完全丧失家庭抚育时方才介入。事实上,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现代家庭呈现成员的减少、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妇女就业的增加、形态的多元与异常等特点,家庭对于儿童福利权实现的支持功能日渐式微且受到限制。*参见万育维:《社会福利服务——理论与实践》,三民书局2007年版,第90-91页。同时,“儿童成长过程中对儿童福利的依赖不仅不会因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而减弱,反而会进一步强化”。*郑功成:《中国社会福利改革与发展战略:从照顾弱者到普惠全民》,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另一方面,儿童福利权之国家义务实践常常处于“被忽视”和“不发达”的状态加剧了儿童自由、快乐、健康成长的风险,一旦家庭抚育功能处于半丧失时,儿童福利权就会受到严重的侵害,甚至生命也会被剥夺;*贵州毕节流浪儿童闷死垃圾箱、河南兰考孤儿葬身火海、南京女童饿死家中、湖南衡东儿童血铅危机、甘肃正宁与江苏丰县校车安全事故等一系列悲剧的发生,无不折射出儿童福利权国家义务的缺失。“儿童福利——国家义务”对应关系的理论研究在我国出现严重“不对称”,*2015年4月13日笔者对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发现,篇名中有“儿童福利”的698条,而兼以“国家义务”为篇名的有0篇,“国家责任”为篇名的仅有3篇。对“国家义务”的长久忽视,导致儿童福利权因缺乏义务主体而被架空、虚化;儿童福利权的具体实现不可避免地遇到实践上与理论上的障碍和难题。鉴于此,有必要对儿童福利权国家义务进行梳理和辩证,以寻求妥实的儿童福利权保障与实现之道。
一、儿童福利权国家义务的理论证成
从“警察国家”走向“社会国家”或“福利国家”,国家或政府已不再是消极的“守夜人”。国家或政府的积极帮助和有效参与,已成为现代社会权利实现机制的不可或缺乃至主导性的组成部分。*参见程燎原、王人博:《权利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3-194页。换言之,国家或政府的重要职能就是保障和促进权利的实现。儿童福利权关乎儿童的生存与发展、幸福和安康。从权利性质看,儿童福利权既是儿童的人权也是儿童的一项基本权利,更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因而对其予以尊重和保护乃是国家或政府的法定义务。
(一)国家或政府是儿童的最高监护人
因亲权所系,法律曾经默许或赋予父母对子女享有几乎无限制的权力和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就此完全放任自流。因为“对特定的个人而言,从来有两个属主:一个是自然的父亲,一个是国家父亲”*徐国栋:《普通法中的国家亲权制度及其罗马法根源》,载《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儿童监护既是自然父亲的义务也是国家父亲的义务。所以,随着对这种国家亲权理解及应用的深入,国家愈来愈扮演着儿童利益最终保障者与终极监护人的重要角色,对其福利的介入与保护更是贯穿儿童成长始终。一旦父母无力或不愿承担照管子女的义务时,或当孩子受到虐待或照管不良时,国家应援用公权力剥夺父母、法定监护人或其他监护者的亲权,强制地介入、干涉儿童的成长过程,将处于急需救助和指导的儿童置于控制之内,以矫正其生活上的偏差、心理上或人格上的缺失。*参见张鸿巍:《儿童福利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此时,儿童与抽象的国家之间便建立起类似“父母——子女”的拟制关系,即国家或政府便以“代理父母”的身份全面料理儿童的衣食起居与身心健康,履行保障儿童福利所需要承担的义务。*参见Albert Roberts, The Emergence of the Juvenile Court and Probation Services,in Albert Roberts(ed.),Juvenile Justice Source Book: Past,Present,and Futur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164.也就是说,国家负有帮助儿童在自由与尊严之情景中获得身体、心智、道德、精神、社会各方面之健全与正常发展的义务。
(二)国家或政府是人权义务的主要主体
儿童福利权是儿童人权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一项权利。*就国内层面而言,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到《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儿童人权体系一直处于探索阶段,但是儿童福利权是儿童人权体系的组成部分毋容置疑。两份行动计划均提出了儿童福利权的保障措施,前者是加强儿童福利院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的建设;后者则要求推进儿童福利立法,逐步扩大儿童福利惠及面。从权利内容看,儿童人权内容涵盖了儿童最大限度存活与发展、享受健康与医疗保健服务、接受教育、获得适当生活水准以及残疾儿童特别照顾等儿童福利权之内容。从权利价值看,不论是儿童福利权的防止儿童陷入需要保护的状态,满足儿童的身心需求,积极促进儿童健康成长的目标,*参见易谨:《儿童福利立法的理论基础》,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还是儿童人权证成儿童的权利主体地位,明确儿童的权利,尊重儿童生命和人格尊严的价值,*参见管华:《儿童权利的证成》,载《西部法学评论》2014年第3期。皆为保障儿童权利,促进儿童自由而全面发展,两者殊途同归。正如谢琼博士所指出,“福利制度通过各项福利安排为维护和实现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健康权、教育权和受保护等权益提供了保障,在为儿童创造平等的起点和机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也通过对其父母提供福利保障直接实现儿童的社会保障受益权。”*谢琼:《福利制度与人权实现》,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1页。由是观之,儿童福利权具有了儿童人权的属性。
应当认识到,“国家是人权义务的主要主体”,*郭道晖:《人权的国家保障义务》,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8期。我国《宪法》第33条第3款予以了明确。一方面,尊重与保障人权不仅是国家存在的价值所在,而且是国家行使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事关国家正当性的证成;*正如洛克所说,人们将自然状态中享有的权利让渡给国家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而国家的存在亦只能是为了实现民众的和平、安全和公共福利。参见[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霍菊农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77-80页。另一方面,国家拥有足够的资源和充足的社会动员能力,能够整治社会主体之间侵犯人权的行为,实现个体的繁荣。所以,“政府应当承担保护人权的任务,保护公民免受工业社会给人类生活所带来的诸多不幸,并通过积极的政策来满足新的经济、社会需求”,*江国华:《宪法哲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69页。这一任务固然包括维护和实现儿童人权。因此,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蔡明殿言道:“确保儿童青少年人权的责任主要在于拥有各种资源的各级政府”。*蔡明殿等:《人权思想导论》,秀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16页。也就是说,国家或政府负有实现儿童福利权、保障儿童人权以及促进儿童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义务。
(三)国家或政府是公共物品最重要的提供者
理论上,萨缪尔森首次将公共物品界定为:“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这种物品消费的减少”,*Paul A. Samuelson,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36, No.4, 1954.P.387.即公共物品是指具有消费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的物品。但是,这种从物品的技术(自然)特性视角界定公共物品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其建立的逻辑前提——资源无限而消费能力和排他性技术有限——是错误的。*参见刘太刚:《对传统公共物品理论的破与立》,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鉴于此,有学者从制度(社会)特性视角对该理论予以修正,认为公共物品是国家基于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原因,以满足特定的社会公共需求或目的而从制度上赋予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性的物品。*参见[美]布坎南:《民主财政论》,穆怀朋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0页;[澳]休·史卓顿、莱昂内尔·奥查德:《公共物品、公共企业和公共选择》,费昭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W.Ver Eeeke. Public Goods: an Ideal Concept,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Vol.28,1999,p139。也就是说,没有一种物品或服务是天然或固定的公共物品,而是被赋予了特定的价值承载之后,才具有了接受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
儿童福利权不仅关系到儿童权利的保护、儿童福祉的增进,还攸关民族生命的延续、社会稳定的维护,承载了维护和保障儿童人权、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类幸福等特定的价值。也正是承载着这些特定的目标或价值,才使得儿童福利权具有了消费的非竞争性和接受的非排他性,因而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具体而言,儿童福利权具有接受的非排他性,即单个儿童享受儿童福利的权利,并不会妨碍其他儿童对此种权利的享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根本上而言,任何儿童于福利权的拥有均不可能是占有权,而只是享有权。*参见欧阳英:《试论权利与公共物品的内在联系》,载《哲学研究》2004年第9期。其次,儿童福利权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即对儿童福利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任何儿童的消费均不会影响到其他儿童的利益。虽然单个的儿童使用了儿童福利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但其他儿童仍然可以使用,而且最终不会改变其性质。正如英国学者米尔恩所言:“在任何社会里,一个儿童被否认享有该项权利,也就被否弃了踏入成年生活的希望,这是与将其视为人类伙伴成员的要求不相符的”。*[英]A·J·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夏勇、张志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1995年版,第171页。正是儿童福利权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政府在实现儿童福利权方面的义务。一方面,儿童福利权是每一个儿童固有的权利,不论其贫弱富贵与否。换言之,儿童无须为此权利付出任何对价。另一方面,虽然儿童福利权供给的主体包括家庭、社会和国家,但家庭供给是一种伦理责任,儿童福利权保障完全依赖于监护人的自觉,且“中国当代家庭的小型化趋向,致使子女抚育方面对社会机构服务或家政服务的需求在增强”,*王跃生:《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分析——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儿童福利权家庭保障日渐式微;其次,社会组织或成员供给是一种道德责任,儿童福利的供给完全依赖于其道德品质,因而在无法获取对价的情况下,“经济人”往往没有提供儿童福利产品或服务的积极性。换言之,通过私人伦理责任或道德责任的约束来实现儿童福利权的充分供给是不现实的,所以“如果一个共同体想要生存下去,它就不能忽视下一代的福利。作为共同体的利益所在,应该通过各种措施充分提供这种福利,例如,组织和维持教育,安排照顾孤儿和保护儿童免遭成年人的虐待。这样一类的事情不仅需要家庭承担义务,而且需要共同体的所有成年成员承担义务。”*[英]A.J.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夏勇、张志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1995年版,第69页。“国家必须提供公共物品”,*张世雄等:《社会福利概论》,国立空中大学2009年版,第54页。承担着保障和实现儿童福利权的义务。
二、儿童福利权国家义务的具体内容
“每一权利都有其相对应的国家义务”,*蒋银华:《国家义务论——以人权保障为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页。儿童福利权也不例外。从静态层面而言,国家承担着确保至少使福利权的实现达到一个最基本的水平,也就是儿童福利权的“最低核心义务”;从动态层面而言,国家肩负着尊重、保护和实现儿童福利权的义务,即国际人权公约所达成的国家义务之共识。公允地说,儿童福利权国家义务既包括行为义务,也包括结果义务,国家有“充分实现这些权利”之结果要求,同时也有采取“步骤”和“措施”之行为规定,是结果义务与行为义务的辩证统一。
(一)儿童福利权之国家“最低核心义务”
正如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指出,“每个缔约国均有责任承担最低限度的核心义务,确保至少每种权利的实现达到一个最基本的水平”。*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e Rights, General Comment No.3.1990,In HRJ/GEN/I/Rev,6.12 May,2003,p.16.儿童福利权的国家最低核心义务就是确保所有儿童不论在什么地方均应享有该权利的最基本的水平,这一最基本水平就是保证所有儿童能够享有“最低限度生活”。所谓“最低限度生活”,顾名思义,是指人在肉体上、精神上能过上像人那样的生活,这是人在社会生活中为确保自我尊严的最低限度状态。所以,这不是指“‘单纯地像动物般生存的、仅仅维持衣食住行必要物质的最低限度’那样的‘最低生存费’,而是具有一定文化性的生活之水准。”*[日]大须贺明:《生存权论》,林浩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页。也就是说,国家于儿童“不单是满足衣食住行等需要,而是在精神生活、营养状态、体格等方面也能够达到一定的水准,在文化的、社会的生活方面也能够享受作为人的最低限水准”。*[日]桑原洋子:《日本社会福利法制概论》,韩君玲、邹文星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75页。当然,作为确定“最低限度生活”水准时应当考虑且必须考虑的要素,结果在根本上就是处于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再者就是与此相关的国民收入水准、生活水准,以及该时期的社会与文化的发展程度。但这并不能否定“最低限度生活”内容的确定性,因而,作为儿童福利权的内容,就首先应该在宪法上得到客观的确认;而位于此水准之下的儿童,无论他是哪个层次,国家均应保护他们的生活。国家在宪法上负有此等的保护义务,且国家在履行该义务时,尚需恪守儿童利益最大化、非歧视及儿童参与等原则。
(二)儿童福利权之国家尊重、保护与实现义务
概括而言,儿童福利权国家义务包括国家或政府“应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行政和其他措施”,“根据现有资源所允许的最大限度” 以实现儿童福利权,“并视需要在国际合作范围内采取此措施”等内容。*参见张爱宁:《国际人权法专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页。遵循国际社会对于人权国家义务的划分,*国家义务的性质是什么,在国际人权条约中,使用了诸如“尊重”、“承认”、“保护”、“保障”、“保证”、“使之有效”等术语,但是兼不外乎“尊重”、“保护”和“实现”之义务。儿童福利权的国家义务可细分为尊重义务、保护义务和实现义务。
1、国家尊重义务。儿童福利权尊重义务是指国家或政府尊重儿童平等地获得福利服务的机会,对儿童福利权的享有和实现不加干涉或不予侵犯,对家庭和社会在国家实行的儿童福利之外而采取的实现儿童福利权的努力不应该干涉,*参见刘文平:《社会权实现的国家义务——以社会权的双重性质理论为视角》,载《西部法学评论》2009年第1期。是国家的一种消极义务。此种义务的前提是国家或政府必须以法律的形式承认儿童福利权,这是国家或政府承担和履行其儿童福利权义务的必要逻辑前提,也是承担和履行义务的第一步。因此,许多国家宪法和法律都对儿童福利权予以了确认。比如,《日本宪法》第13条规定,全体国民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对于谋求生存、自由以及幸福的国民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利,在立法及其他国政上都必须受到最大的尊重;《南非宪法》第28条规定,每个儿童享有适当的营养、住房、基本医疗服务和社会服务的权利。此外,许多国际人权文件也对此做出了规定。例如,《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缔约国应尊重儿童的权利,确认每个儿童“均有固定的生命权”、“受教育的权利”、“享有可达到最高标准的健康,并享有医疗和健康设施”、“受益于社会保障”、“享有足以促进其生理、心理、精神、道德和社会发展的生活水平”和“身心有残疾的儿童能在确保其尊严、促进其自立、有利于其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条件下享有充实而适当的生活”; 确保儿童“最大限度地存活和发展”和“保健服务的权利”。
2、国家保护义务。儿童福利权保护义务是指国家或政府必须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保护儿童的福利权,使儿童福利权免于遭受公权力或第三人之侵害,旨在强调国家或政府不仅应该“尊重”儿童享有福利的权利,不妄加干预,而且还需要采取各种不同措施,以创设并确保儿童行使福利权的“客观条件”,达到“保护”儿童福利权之目的,*参见李建良:《宪法理论与实践(一)》,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68-70、74页。属于国家的积极义务。为福利权受到侵害的儿童提供有效救济是国家义务不可或缺的方式。“简言之,如果有一项权利就必须有一项救济,因为虽然存在着一项被承认的权利,但当权利被侵犯时,如果受害者得不到救济,那么这种无法实施之性质的权利,就成为没有实质幻影并且不再成其为法律权利。”*Nagendra Singh,“Enforcement of Human Rights in Peace & War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1986,P.13.转引自蒋银华:《国家义务论——以人权保障为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2-163页。因此,对于儿童福利权被侵犯时的救济不加以规定或这些救济不能付诸实施,则儿童福利权的实现将是纸上谈兵。于是,保护儿童福利权免受侵犯就是国家承担的一项重要义务。如我国宪法第49条规定,“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虐待儿童”。
3、国家实现义务。儿童福利权实现义务是指当家庭和社会无法以私力满足和促进儿童的福利权时,国家或政府应当在其当前可利用的资源限度内,承担给付义务或物质帮助,以达成儿童福利权的实现和享有,*参见孙世彦:《国际人权法下的国家义务》,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2期。属于“即刻实现义务”,*杜承铭:《论基本权利之国家义务:理论基础、结构形式与中国实践》,载《法学评论》2011年第2期。是国家行为义务和结果义务的统一。儿童福利权国家实现义务实质是赋予儿童及其利益代表人有直接请求国家积极作为,以使儿童获得相应福利服务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权利,因而备受关注。比如,《韩国宪法》第34条规定:“国家负有努力增进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的义务。国家负有实施旨在提高老人和青少年福利政策的义务”。《埃及宪法》第16条规定:“国家保障人民有文化福利、社会福利和卫生福利,并特别地有步骤地为农村提供福利,从而提高那里的福利水平”。作为儿童权利宪章的《儿童权利公约》更是翔实地规定了儿童福利权的国家实现义务。以儿童受教育权为例,为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此项权利,国家或政府应当承担以下义务:“(1)实现全面的免费义务小学教育;(2)鼓励发展不同形式的中学教育、包括普通和职业教育,使所有儿童均能享有和接受这种教育,并采取适当措施,诸如实行免费教育和对有需要的人提供津贴;(3)根据能力以一切适当方式使所有人均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4)使所有儿童均能得到教育和职业方面的资料和指导;(5)采取措施鼓励学生按时出勤和降低辍学率。”*《儿童权利公约》第28条第1款。可见,就其本质而言,儿童福利权的国家实现义务是一种行政给付义务。
此外,倘若以国家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种样态为划分标准,儿童福利权国家义务还可细分为立法义务、行政义务和司法义务。
三、中国儿童福利权国家义务实现的制约因素分析
中国儿童人口数量多、地域分布广,儿童福利政策性强、制度独立性弱,以家庭责任为基本形式的儿童福利权模式难以尊重和满足儿童日益增长的生存与发展福利需求,这恰恰折射出我国儿童福利权国家义务实现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亟待予以完善。
(一)中国儿童福利权国家义务的多重二元结构
一是城乡二元结构。建国以来,桎梏于居民分为农业居民和非农业居民的逻辑,儿童福利权制度均以城镇和农村户籍为标准进行划分,呈现出典型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尽管国务院于2014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但城乡二元体制的历史固化,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参见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未来发展》,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比如,城乡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分别由《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和《农村五保供养条例》规制;儿童医疗保障分属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项目。在此种体制下,城乡儿童福利权实现公平性严重失衡。
二是区域(省际)二元结构。受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现行儿童福利权实现还呈现出区域(省际)二元结构,此种结构造成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与西部边远贫困地区之间、不同省份之间儿童福利资源配置差异悬殊。*有实证研究也印证了中国的社会福利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且差距悬殊。详见逯进等:《社会福利、经济增长与区域发展差异——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耦合实证分析》,载《中国人口科学》2012年第3期。以教育事业为例,2013年各省普通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最高省份北京为21727.88元/人,最低省份河南为3913.95元/人,两者相差5.55倍;各省普通初中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最高省份北京为32544.37元/人,最低省份贵州为6140.45元/人,两者相差5.3倍。*数据来源: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公布的《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2013年)》。
三是福利机构与原生家庭二元结构。中国儿童福利权制度的受惠对象主要局限于福利机构中的孤残儿童、困境儿童、困境家庭儿童,而对于生活在原生家庭中的儿童之福利权实现尚存诸多盲点。*参见成海军:《制度转型与体系嬗变:中国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的构建》,载《新视野》2013年第2期。目前,除孤儿供养实现了福利机构和社会散居均衡化外,儿童福利权实现还带有明显的补缺型特点,福利机构和原生家庭儿童福利权制度泾渭分明。因此,“乡土民众仍主要借助家庭关系资源来弥补社会‘福利’和‘保障’的不足”。*王跃生:《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分析——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
(二)中国儿童福利权国家义务的失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儿童福利政策主要是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旨在通过各种事后救济措施缓解或消除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儿童发展问题,实质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是基于儿童福利权本身。*参见[美]托尼·赛奇:《中国社会福利政策:迈向社会公民权》,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因此,儿童福利权缺乏权威性的立法、持续性的行政及完善的司法保障,儿童福利权国家义务一直处于失位状态。
第一,儿童福利权立法“碎片化”,缺乏专门和统一的法律。我国儿童福利权法规范散落于《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幼保健法》、《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社会救助暂行条例》、《儿童福利机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之间,表现为法律规范屈指可数,行政法规寥寥无几,部门规章多如牛毛,体系结构分散、标准不一。*参见成海军、陈晓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儿童福利法治建设及其特点》,载《新视野》2011年第3期。其次,有关儿童福利权的法规范原则性、概括性的条款较多,实际的、可操作的内容不足,执行效果有效性、差异性较大。另一方面,儿童福利权制度镶嵌在普通公民的社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医疗保险及残疾人服务和教育等制度中,尚未形成全国统一、自成体系、目标明确的国家儿童福利权实现体系,以至于生活在贫困家庭的儿童得不到生活、教育、医疗方面的切实保障。此外,目前我国儿童福利权并没有得到法律上的确认与宣示,有关儿童福利权的主体、内容及救济等未能在法律上予以明确。换言之,我国缺乏一部针对儿童福利权利与问题做出完整正面规定的基本儿童福利立法。
第二,儿童福利行政体制不健全,国家儿童福利支出过低。我国儿童的卫生、保健、教育、安全、娱乐和休闲等方面的保护职责分散于民政部、教育部、妇联、司法机关、社会团体等部门,是一种分工负责的工作机制。正是这种“九龙治水”的体制,客观上使儿童福利行政管理处于“虚化”状态,这直接造成儿童福利政策与资源的分割,也致使整个儿童福利事业的统筹规划与顶层设计、顶层推动化为泡影。*参见郑功成:《中国社会福利的现状与发展取向》,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其次,儿童福利权实现缺乏持续性、稳定性、发展性的财政支持,各种儿童福利资源供给严重不足且不均衡,致使儿童福利服务配套设施无法得到补充、更新与完善。与此同时,我国儿童福利服务仍旧延续的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单位制”模式,基本上是政府独撑儿童服务;社会组织发展缓慢,还没有形成服务社会和能够提供福利服务的能力,市场经济体制的“多元福利”模式尚处探索阶段。进而从整体上而论,儿童福利服务严重滞后,专业化进程较慢。例如,幼儿保育事业在许多地区成为社会服务的空白;儿童学前教育专业师资资源紧缺;残疾儿童特别照顾人才匮乏;等等,根本无法应对中国儿童发展的多元状态,儿童发展性福利满足程度低。
第三,权利救济程序缺失,儿童福利权实现丧失后盾。一方面,对于有条件的父母不履行保护儿童福利权之责任,或者侵害儿童福利权,司法缺乏有效的干预机制。应当认识到,当下中国连接亲权和公权维护儿童福利权的制度当属民法通则规定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有不少监护人或滥用监护权,剥夺儿童权利主体资格,甚至使监护异化为体罚和虐待的手段;或不履行监护义务,将儿童置于无人监管和照看的状态;或两者兼而有之,致使儿童福利权益受到损害。*参见付玉明、宋磊:《论我国儿童权利的法律保护——以近期几起典型案件为例》,载《法学杂志》2013年第9期。尽管2015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之司法解释对此问题给予了回应,提出通过剥夺监护权以保护儿童的权利,但仍有几点值得我们反思:一是在剥夺监护权之后,儿童由谁来照顾,其学习与生活该如何保障?二是此制度如何与现有的儿童福利制度衔接,并最终成为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三是如何破除民政部门机构建设缺位、设施薄弱、人员不足、专业队伍紧缺等困局,落实其兜底监护人的责任?另一方面,对于国家或政府不履行保护儿童福利权应尽的义务,并没有设置相应的司法程序以保护儿童接受教育、保健服务、康复服务等福利权利。比如说,民政部没有履行儿童监护的兜底责任,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未规定相应保障并实现儿童福利权的程序机制。儿童福利权制度是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的融合,法律程序的缺位致使儿童福利权之实现无法真正落实,权利保障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四、中国儿童福利权国家义务的实现路径
根据《儿童权利公约》第4条第1款规定:“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行政和其他措施以实现本公约所确认的权利”。儿童权利委员会第5号一般性意见提出:“尊重和确保儿童权利不仅仅是国家和国家管理服务部门和机构的责任,儿童、父母、大家庭、其他成人以及非国家服务部门和机构也都有责任”,“需要全社会各部门的共同参与”。*徐爽:《人权指南:国际人权保护机制、标准与中国执行情况汇编手册》,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53页。综合来看,实现儿童福利权国家义务的路径大体包括立法、行政、司法、社会协同、国际合作等方式。因而,针对中国儿童福利权国家义务实现所面临的问题,可从以上方面予以落实和完善。
(一)立法路径
尊重的前提乃承认,故承认儿童福利权的义务无疑包括于尊重之中。“拥有人权是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但享有人权必须依靠法律。”*蒋银华:《国家义务论——以人权保障为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9页。儿童福利权是儿童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权,属于儿童人权体系中的基础性权利,体现了保护儿童生存与发展的价值,理应得到立法上的确认,正所谓“权利享有是权利实现的前提”。*郑智航、张杨:《作为人权的未成年人适当照顾权及其结构》,载《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尽管儿童福利权的法定化不等于儿童福利权的实现,但应然权利的法定化是儿童福利权实现的一个重要路径。*参见郝铁川:《权利实现的差序格局》,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所以,“立法者应当审时度势、通盘考虑,将各种合理的人权保障诉求确认为法定权利,建构一套唇齿相依、相辅相成的权利体系”。*罗豪才、宋功德:《人权法的失衡与平衡》,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目前,我国还没有完整的儿童福利权法制体系,儿童福利权实现主要依靠的是社会政策和行政手段推动,缺乏强制力,统一性、权威性和稳定性不足,亟需制定一部统一的、层次较高的儿童福利基本法,明确儿童福利权的主体、内容,儿童福利的项目、标准、资金来源,儿童福利供给责任主体、儿童福利管理机构、审查监督、争议解决及法律责任等,以立法保障和落实儿童福利权的实现。首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或国务院应启动儿童福利权立法,尽快出台儿童福利法或儿童福利条例,确保儿童福利权实现有法可依;同时,立法时要特别注重儿童福利法律规则的可行性,确保法的实施效果。要以儿童福利法为基础,分别在儿童学前教育、家庭照顾、义务教育、医疗保健、特困救助等方面制定完善的法律,建立完整的儿童福利法律体系。其次,待时机成熟时,或在宪法总纲中确立“民生福利原则”,或在宪法“公民基本权利”条款中载明“国家保障公民的社会福利权”,*参见温泽彬:《美国法语境下公民福利权的证成及其启示》,载《法商研究》2014年第4期。抑或在宪法第45条增设一款“国家和社会保障儿童福利权”,夯实儿童福利权的宪法基础。应当强调的是,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不仅要确认福利权或儿童福利权,更应当明确国家于儿童福利权的最低核心义务,规定相应的检验机制以促使儿童福利权最低限度义务的落实。此外,在今后立法中应积极打破、消除户籍制度给儿童福利权实现设置的障碍,破除区域限制,实现福利机构与原生家庭中儿童福利保障合理差异的均衡化。
(二)行政路径
“行政路径的内容比较丰富,主要包括政策制定、行政行为两大类。”*王新生:《略论社会权的国家义务及其发展趋势》,载《法学评论》2012年第6期。换言之,作为国家代表的政府可通过进一步加强和延伸政策制订、管理与服务监督等方面的工作,以落实儿童福利权中的国家义务。首先,要使整个政府及各级政府都来促进和尊重儿童福利权,就必须将儿童福利权保障上升为国家战略,继续制定和实施基于儿童权利理念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同时,也必须将战略与国家发展规划联系在一起并将之纳入国家预算编制,否则该战略就有可能脱离重要决策过程。其次,中央政府各部门、不同省市和地区、中央一级和其他各级政府以及政府和社会,相互之间均需要加强协调。因此,必须借鉴国外经验,*纵观各国儿童福利行政和管理,设立国家级专司儿童福利或儿童事务管理机构业已成了保护儿童权益的共识。例如,美国有联邦儿童局,各州都有儿童与家庭服务局(处);英国设立了儿童福利与保护政策部,德国有联邦青少年家庭事务部;日本在厚生省建立了儿童与家庭部、中央福利儿童理事会;挪威有儿童与平等事务部。整合现有儿童福利管理资源,在中央政府层面成立至少副部级的儿童福利管理机构,专门负责管理全国的儿童福利事务;在省、市、县三级行政区域分别设立儿童福利管理中心,作为本级政府的职能部门处理本地区儿童福利事项的管理机构。*参见刘继同:《中国儿童福利时代的战略构想》,载《学海》2012年第2期。再次,完善我国儿童福利财政预算制度和儿童福利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落实政府的行政给付义务。一方面,要将儿童福利资金纳入到社会保障预算当中,实行专项管理;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应将儿童福利项目的支出单列,以确保儿童权益保护、儿童福利服务的发展有充分的经费保障。*参见程福财:《中国儿童保护制度建设论纲》,载《当代青年研究》2014年第5期。另一方面,在保持现行纵向支付的基础上,适当地推行直接向特殊县级行政机构的特殊支付,适当地发展横向财政支付制度,实现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儿童福利服务的均衡化。此外,还要建立健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地方福利机构有效衔接机制,杜绝各级政府受经济发展之功利主义支配下用其他方面投入挤占儿童方面的投入。
(三)司法路径
就司法路径而言,儿童福利权国家义务的落实需要国家或政府必须特别注意确保为儿童或其利益代表者提供有效的、对儿童福利问题敏感的程序,包括提供方便儿童的信息、咨询、辩护;对自我辩护的支持;使用独立申诉程序和向法院申诉的机会;获得必要的法律和其他援助等。事实上,在法庭上是否能够援引儿童福利权是检验该权利是否得到尊重的标准。因此,针对目前我国侵害儿童福利权益发现机制不健全,且仅有性侵害儿童和监护人侵害儿童权益时有相应的报告制度之现状,国家应健全儿童福利权益受损害时的强制报告程序,规定对儿童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和单位(如负有监护、教育、训练、救助、看护、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人员或单位),若发现儿童福利权益受损,就必须及时报告儿童福利专门机构,否则将面临被问责。其次,畅通权利的司法救济程序,以确保当国家或政府违背其保障儿童福利权应尽的义务时,儿童及其利益代表者享有相应的请求保障其接受教育、保健服务、康复服务等权利,有权通过司法程序获得救济。当前,我国儿童福利权难以通过司法程序获得救济,其最大的障碍是宪法权利缺乏司法化保障机制,以致许多提起行政诉讼的侵害儿童受教育权之案件,均以不属于法院行政审判之权限范围或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而予以驳回。*例如,“小学生状告北京市教委要求义务教育免费案”;“六岁半儿童状告历下区教委侵犯其按时入学权案”。参见吴鹏飞:《儿童权利一般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231页。为此,人民法院可探索建立儿童公益诉讼程序,赋予儿童保护者、机构和社会团体等主体,在国家或儿童之父母不履行儿童福利权之保障义务,其他主体侵害儿童福利权,且监护人怠于维护儿童权益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保障儿童权利的实现。应当说明的是,儿童福利权的可裁决性是以国家或政府违背其应尽义务为前提,它的功能仅在于鉴定国家或政府是否履行了法律文本中关于儿童福利权的承诺(或者说是儿童福利权国家最低限度义务),而不是去检验国家或政府福利标准本身是否具有合宪性或合法性。
(四)社会协同
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儿童是未来的劳动力和纳税人,成人年老时需要依赖他们所创造的经济效益。父母抚育儿童为国家和社会带来正的外部性,如果他们不分担相应的抚育成本,那么就是一种“搭便车”的行为。*参见Serena Olsaretti: Children as Public Goods,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Vol.41, No.3, 2013,P.228-229.因此,落实儿童福利权是国家的义务,但其实现需要全社会各部门的共同参与,包括儿童自身的参与,这就是社会协同路径的全部内容。换言之,儿童福利权实现必须要在社会政策和社会服务两方面构建起政府、社会、家庭三方面联合互动的权利实现范式。
首先,构建政府和家庭之间的交流平台,实现儿童福利服务机构的全覆盖。现实生活中,一方面,由于贫困地区交通不便、群众收入偏低、当地政府机构缺乏专业能力、难以改变的社会习俗等因素限制了儿童福利服务的覆盖;另一方面,由于弱势儿童及其家庭贫困、受教育程度低、语言障碍、信息缺乏以及对自身的耻辱感,很难获悉或者知道如何申请所需的服务;这些问题导致儿童福利权在偏远贫困地区无法得到很好的实现。因此,建立连接政府和家庭之村级社区的儿童福利机构,比如“儿童福利主任”,既能够实现社会服务体系中“最后一公里”的落实,也能够促进儿童福利权的实现。
其次,构建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的协同功效。最为重要的是国家或政府要注重儿童福利权实现社会力量的培育和引导。一是通过法律(政策)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儿童福利权保障。通过简化社会组织的登记程序及准入机制,采取免除或返还税收等税收优惠措施,激励社会组织提供儿童福利服务;*参见王素芬:《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保障的理论基础与实现路径》,载《当代法学》2012年第3期。二是改革国家直接向儿童福利服务机构拨付财物的方式,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促进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办福利的机制之形成,实施儿童福利服务政府购买制度,以提高儿童福利权实现的效率和质量;三是建立健全儿童福利行政管理专门人才和儿童福利服务人才培养机制,实现他们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例如,在高等院校开设儿童福利服务专业,培养儿童教育、保健等多层次的高级人才;健全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体系、资格认证制度以及评聘程序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协同的前提是要明确儿童福利供给中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及责任分配模式,只有家庭、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责任边界明晰,协同功效才会更强。
(五)国际合作
当今世界已是经济全球化、社会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大家庭,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援助和合作是实现儿童福利权的重要路径。为此,我国应当充分利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以及其他联合国机构与有关机构所提供的技术援助以尊重和满足有特殊福利需求的儿童,明确接受国际援助划拨给儿童的比例以实现儿童权利。另外,积极探索各种渠道,包括建立区域间统一数据库、签署国家之间的合作战略、构建地区或国家间的对话机制,以分享促进儿童权利领域的具体经验和最佳实践,促进本国儿童福利权的实现。
五、结语
翻阅世界儿童福利史,儿童福利大致经历了“国王恩赐”——“社会慈善”——“儿童权利”——“国家义务”等几个阶段。中国儿童福利权实现尚处于儿童权利向国家义务过渡时期,儿童福利权国家义务之意识仍处于萌芽阶段,儿童福利制度不可避免带有时代的烙印,即当下的儿童福利权制度和实践定位均是社会保障制度之下社会福利项目中的一个子项目,这是政府专门向特定的弱者提供的社会服务和基本生活保障,是一种典型的补缺型福利制度,而不是全体儿童福利权的保障与维护。即使是当下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之试点,实际上也只是儿童福利的对象由孤残儿童扩展到其他困境儿童,此种简单的扩大并没有包括全部困境儿童,更遑论所有儿童,制度安排的工具性不言而喻。*参见乔东平、谢倩雯:《西方儿童福利理念和政策演变及对中国的启示》,载《东岳论丛》2014年第11期。应当认识到,儿童福利权是儿童的一项人权,是儿童的基本权利,国家或政府负有尊重、保护和实现的不可推卸之义务。因此,落实国家保障权利之义务的制度设计不能以自身政治目的为向导,而应当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我国儿童福利权实现要恪守儿童权利理念,深化国家义务,增强社会协同,注重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手段。唯有如此,儿童才能拥有幸福、美好、健康的童年。
[责任编辑:王德福]
Subject:The National Obligation to Child Welfare Right
Author & unit:WU Pengfei (Law School,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chang Jiangxi 330013,China)
The national obligation to child welfare right is determined by the identity of the ultimate guardian, the main body of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and the important provider of public goods, which mainly contain statically minimum obligation and dynamic obligation of respection, protection and promotation. It is the unity of behavior and results of obligations, negative and positive of obligations. Chinese national obligation to child welfare right shows multi dualistic structures that city and countryside, among regions or Provinces, Welfare institutions and original families, and problems of the fragmentation of legislation, the dummy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nd the absence of the relief programs, which should be rectified and implemented through the way of Legislation, administration, judicature, social coordin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ly when the concept of children firstly established, child welfare raised for national strategy, the welfare needs to meet the children’s basic survival and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will come true.
child welfare;child welfare right; national obligation; guardianship
2015-07-16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儿童福利权保障制度研究》(12BFX093)的阶段性成果。
吴鹏飞(1969-),男,江西永丰人,法学博士,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法治政府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人权基础理论。
D90
A
1009-8003(2015)05-003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