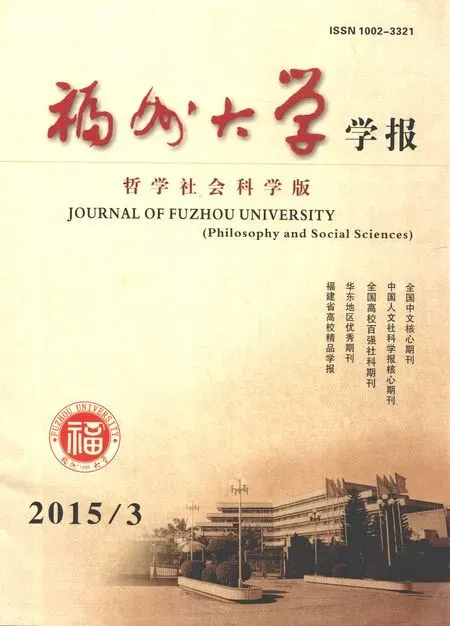闽西客家的真仙信仰与祖先崇拜:清流大丰山的象征意义
2015-04-16魏德毓
魏德毓
(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福建福州 350116)
一、引论
丰山,民间又称为大丰山,位于福建省连城县与清流县交界处,属于清流县管辖。山上有顺真道院,道院内供奉欧阳真仙,是闽西闻名一方的道教神灵。由于“乡人祀之极灵感”、“祈辄有感应”[1],欧阳真仙逐渐成为闽西清流、连城一带的地方保护神,并形成了与之有关的宗教仪式。如清流民间的迎真仙仪式就一直延续至近代,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民俗,“四月初三日,迎大丰山欧阳真仙入城,至五月初三出城,会期一个月,街道及居民、民众戏社、神案分别建醮一天。街道及民间戏曲社、神案在建醮时均举行仙公游街仪式,并集全城古董字画和各种花卉摆‘五坊’,香客川流不息。”[2]同时据笔者调查,连城的洪山、田新等村庄每年也举行到大丰山迎接真仙的香火,建年例平安大醮的仪式活动。可见,欧阳真仙信仰是闽西社会重要的社会文化资源。但欧阳真仙信仰与闽西地方仪式传统之间的关系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主要是想通过欧阳真仙信仰及其有关的丰山象征性资源,探讨地方家族士大夫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利用当地道教大丰山的象征性资源整合家族和控制地方社会,反思地方神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之间关系的探讨在地域社会秩序建立过程中的意义。
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一些学者做了探索。武雅士(Arthur P·Wolf)在其影响深广的论文《神·鬼·祖先》中,根据在台北市郊三峡乡的田野调查,将民间观念中的神鬼观作了类型学的划分,即神象征帝国科层制中的官员,鬼象征危险的陌生人,祖先象征亲属关系。[3]显然武雅士强调三者在中国人观念中的象征意义,但是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并未深入阐述。以研究道教史起家的法国学者劳格文(John Lagerwey)在南客家研究中就发现祖先和神明是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他就此解释道:“乡村生活为两种相互渗透的社会秩序与民俗所支配:其一与宗族社会结构有关;其二则与神明崇拜有关……如果神明与祖先是传统社会宗教崇拜的核心,那么举行崇拜的地方则取决于一个象征系统——风水原则。”[4]可见在劳格文解释体系中,注重风水原则在神明崇拜和祖先崇拜之间的连结关系。科大卫(David Faure)也认为神明祭祀和宗族制度不可分割:“虽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把祭祀神灵与祭祀祖先区分开来,但是,中国的广义‘宗教’,必须把祖先信仰与祖先祭祀包括在内。”与此相应,其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在于:“我们亟须做大量的开拓研究,研究人类的活动如何影响区域社会的形成……其中一个共同问题是:地方神灵与祖先何时被整合到王朝国家的意识形态之中?”[5]在科大卫的问题意识中,应当将地方神灵与祖先的关系放到国家制度体系中加以解释。
这些研究使笔者认识到,地方神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不仅具有类型划分上的意义,同时也映射了地方民众的人格建构和宇宙观想象,更是王朝典章制度的治理手段,是对中国文化历史实践的整体论。因此,本文期望通过还原连城县沈氏家族构建其始祖与丰山欧阳真仙之间的联系,建立丰山在沈氏家族中的象征意义的过程,探讨在区域社会中,地方家族士大夫是如何实践国家制度的过程,以期加深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本文所用资料,大部分来源于笔者自2004年以来在连城调查时搜集的民间文献与口述资料,一部分来源于学者的相关研究论著。
二、丰山象征意义的建立
据《连城沈氏族谱》记载,连城城关的沈氏家族于宋代由清流大丰山附近琴源村迁至连城。至明初已发展成为当地的望族,“赋税田园,强居一邑之半;缙绅豪杰,鼎食钟鸣者累累”[6]。永乐年间,其第八代族人开始积极筹划创建始祖冰洁公的祠堂。当时沈氏始祖祠堂筹建的家族士大夫代表人物是沈仲继,“字成之,登洪武甲子(1384)应天贤书,初授湖广靖州会同县学教授;祭酒张显宗荐,迁山西大同应州知州。有文武才,弥盗安民,境内以治,永乐元年,升江西吉安府知府,改广南知府,卒于官”[7]。据说,沈仲继曾经编辑沈氏族谱,但由于只记载本支,因而没有刊刻,“前明中宪大夫南庵(即为沈仲继,笔者注)公为承尧公晜孙,去先代尚近,懼久而使其真也。爰手善成编自一世至十世,皆纪本支,而支分派别者莫由搜辑,故未付梓”[8]。可见,沈氏家族在宋至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没有族谱的,这也引起家族士大夫对家族谱系、祖先事迹失传的担忧。同时,沈氏家族士大夫希望通过对家族共同世系和先人事迹的这一宗族类象征的整理,加强族人的认同,以实现敬宗收族的目的。
沈仲继在对其家族族谱梳理的过程中,可能曾有意识地重新整理始祖冰洁公的身份,将其塑造成一个辞官归隐的士大夫形象。然而,这一努力并未完全获得地方社会的认可,其挑战甚至来自于沈氏家族内部。至今沈氏家族中仍然广泛地流传着其始祖与欧阳真仙的神话故事。笔者在田野采访沈家老人时,多次听他们讲述其始祖侍郎公曾经和欧阳真仙、罗仙、赖仙一起修炼,后来他们相约一起跳崖,结果侍郎公看到了他们的嶙嶙白骨,吓得不敢往下跳,而三仙则脱胎成仙的故事。故事表明,沈氏始祖很可能曾经是个道士。这些神话故事不可能见诸正统士大夫的文献,在沈氏士大夫的笔下,我们还是可以窥探出一些端倪:“始祖冰洁公官宋侍郎检校国子监祭酒,宋乱弃官如闽,隐清流大丰山,与真人欧阳大一结侣唱傲其间,不知岁月之几何,遂醒邯郸之梦。”[9]显然,这与当时沈氏家族士大夫所做出的努力是相违背的。
为此,沈氏家族士大夫可能意识到重塑祖先的身份,仅通过士大夫修族谱时对祖先身份的重新确认,是无法形成宗族认同的。因此,需要借助于当地的道教仪式传统,将修祠与祭神相联系,并重新确立始祖侍郎公与欧阳真仙之间的关系。于是借助当时闽西名宦张显宗[10],沈氏家族士大夫的话语得到了充分展示:“丰山者,今欧阳真仙宫阙,初故侍郎沈公佳城也。公讳彪,在宋有护卫功,诰封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监祭酒,兼殿中侍御史、上柱国,御赐名勇,字见义,别号冰洁;今不从彪者,从赐讳也。公先世居杭,宋入闽,娶夫人胡氏,生子二;长永钦,家连城,为连令;次路钦,家清流琴源。而丰山为清、连界道,公素往来,间览其奇峭葱欎,林壑幽闲,若蓬岛,若桃源,徘徊久之不能去。乃构数椽,携二三友人盘桓容与,时而吞吐烟霞,时而吟弄风月。盖不知岁月几何,而飘飘羽化矣。乃卒,葬其中,即真君殿座也。时真君授吕仙秘,闻有投桃索藕之奇。迨绍兴己卯,望气云端,隐隐灵异,将卜宅于兹,而公冢存焉,则谓钦曰:‘此仙宫也。昔六祖假座具于亜仙而还其冢,功德无量,声施至今。若能为亜仙乎?当报以吉穴。’于是卜一里许迁公冢。而真君遂从原坟右坐化焉,是为今之化身岩。钦奇其事,乃构堂宇塑像祀之,复置田数亩为主持资。……于是食其士者,檀越公于左亦并祀,人人咸知有沈氏丰山云。迄今百有余载,沈氏螽斯衍荫,诜诜数万,而赋税田园,强居一邑之半;缙绅豪杰,鼎食钟鸣者累累,奚能屈指?吉穴之报,亶其然乎!余读《传灯录》,见六祖亜仙之事,每心奇之。以今观于丰山,与亜仙辉映后先,不更奇乎?余既慕其灵异,具仰侍郎公之高节,神往者屡矣。适国子博士仲继沈君重修镌石,乞记于余。余与君有师生雅,故夙所睹记者复其请。且以明鄙况,异日解带入山,与沈君登曲豆之巅,讲黄石、赤松故事,亦生平大快也。遂书以劵。”[11]该碑立于永乐二年(1404),主要参与者有仲洪、仲初、仲继、仲宗、仲信、仲举、仲旅、仲丕、仲美、仲儒、阳贤、文宣等立。
张显宗在碑记中的叙述,实际上是沈氏家族士大夫的话语。[12]因为在当时参与重修丰山仙源堂的沈氏族人中,沈仲继时任吉安知府,仲信是贡生,仲旅是赠文林郎,仲儒是国子监博士,他们构成了明初沈氏家族中的士大夫群体;同时张显宗与沈氏家族士大夫代表人物沈仲继有推荐之宜,张显宗按照沈氏家族士大夫话语撰写碑文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由于张显宗在明代汀州府拥有崇高的声望,沈氏家族士大夫请他撰写碑文隐含两个目的:一是将经过沈氏家族士大夫重塑过的入闽始祖侍郎公和其长子沈永钦仕宦身份合法化;二是借助张显宗的文笔和在闽西社会的声望,使得沈氏入闽始祖侍郎公生前隐居大丰山,逝后葬在当地,后来欧阳真仙看中这块“仙地”,为在此建仙宫用“吉穴”与侍郎公长子沈永钦交换,侍郎公由此获得檀越身份的故事更容易成为一种地方社会认可的话语,重新确立了侍郎公与欧阳真仙之间的关系,侍郎公道士的身份逐渐被隐藏。
张显宗撰写的《重修丰山沈氏碑记》后被收入历代编修的县志,成为连城士大夫一致认可的主流话语。[13]此后,这一叙述模式不断被重复,逐渐成为沈氏族人的共同历史记忆。万历年间的《沈氏重修石门岩碑记》宣称:“当侍郎公卜藏丰山,欧阳仙从公乞坐具,公许之,仙遂报以吉穴;选胜之余,复得石门。……吾宗而欲示后之人所命孟化言者,其亦犹此也夫!”[14]
沈氏家族在丰山修建祖坟、祖祠和庙宇,这是宋代祭祖习俗在明初的变异。清人全祖望指出:“设为寺、庵、院之属以守墓,宋人最盛,其登两府者则请于朝,以重其地,而放翁以为非古。明人稍易为墓庄,使佃户耕墓田以司洒扫,此变而合于礼者。我始祖侍御府君之墓,建庵于沙渚以奉香火,盖宋之旧也。”[15]这种祭神与祀祖相结合的习俗,在明代闽西的世家大族中颇为流行,如正德《归化县志》记载:“其大姓则或创庵立神佛,刻亲像于旁,内僧道而奉之。”[16]
可见,经过沈氏家族士大夫的不断努力,借助庵庙开山檀越的权力奉祀本家族始祖,丰山俨然成为沈氏家族始祖身份士大夫化的象征。丰山象征意义的确立,背后巧妙的隐藏了沈氏家族士大夫加强家族整合和实现社会控制的目的,同时也确立了沈氏家族祖先和欧阳真仙之间的关系。
三、祭神与祭祖矛盾的调和
沈氏家族士大夫修祠祭始祖侍郎公,重新确立始祖侍郎公与欧阳真仙之间关系的实践,需要相关的祭祀仪式以强化族人对这种关系的认同。为此,沈氏家族在丰山大殿祀奉欧阳真仙,左堂祀奉始祖侍郎公(即沈冰洁)。从明代以来,每年农历八月初一,沈氏族人都要到丰山举行祭祀欧阳真仙和祭祖的仪式。在《沈氏族谱》中,仍然保存有关的祭文。欧阳真仙的祭文曰:“伏以胜境非凡,垒石、围棋多异迹。仙方授秘,投桃索藕有奇灵。洪惟真仙真成宋代,道显丰山,绩着当时。兴鼻祖厌世云游。君子真人,同隐逸,功垂后世。我裔子孙营祠建庙,神居祖宇并留存。有仙分者享万代馨香之祀典。绵族类者,延千秋奕叶之子孙。神德普及人间,子姓恒叨庇下。来此,三熏三沐,修远祖素好之明禋。用先既稷既斋,报真仙乌及之厚爱。伏愿居歆是享。体通家投契之诚。更祈中锡无疆,庇合族如天之福。丕哉!暨本庙列列神祗同尚享。”[17]祭宋侍郎始祖冰洁公、妣胡夫人的祭文如下:“窃念木本水源,世世莫忘先祀,祖功宗德,人人共展孝思。洪惟始祖,披一品衣,匡国是而功昭汴宋。抱九仙骨,识事务而寄隐丰山。虽不类载仙传之丹阳沈建、吴郡沈义、九嶷沈文泰,俱登仙籍;抑犹如居隐志之海陶朱,归山李秘,辟谷张子房,不恋官途,既与真人而同俦。咸谓仙家之流亚,又绵子姓而聚族。长标祖德之高风,裔等派衍连阳,传世已将三十,乔迁姑田里,发祥亦达百家。为殷水之思,礼隆报本,爰结枌榆之社,敬共抒忱。兹屋桂朔之期,用致黍馨之敬,和声嚖嚖,展拜跄跄。愿祖灵来格来歆,爰忾如在,佑后嗣俾昌俾炽,福禄来崇。丕哉!暨本祠土祗同尚享。”[18]
族谱中保存的祭文说明沈氏家族祭祀欧阳真仙和祭祖时有专门主持仪礼的礼生参与其中,笔者对沈氏家族理事长沈朝杰的访谈也证实了这一点。显然,礼生主持的祭祀仪式遵循的是儒家的仪礼传统。[19]这是以《朱子家礼》为核心的宋明宗法伦理“庶民化”,民间接受和回应的结果。依据儒家的仪礼传统,祭祀祖先必须使用牲礼作为祭品,表示祖先享受子孙的血食,有家族血脉延续之意。据笔者调查闽西客家人祭祀祖先用的祭品与传统仪礼规范略有不同,但仍称为“三牲”,即鸡、鱼、猪,依然属于血牲之祀。据说在传统社会沈氏家族祭祖时要在大丰山欧阳真仙祖殿杀猪一头以示隆重,蕴含血脉绵延之意。
大丰山山顶欧阳真仙庙大殿奉祀欧阳真仙,左侧偏殿是沈氏家族祖先侍郎公的塑像,两者同在一个祭祀空间。而清流、连城民间祭祀欧阳真仙时用的是素品。显然祭神与祭祖的供品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应该如何调和二者之间的关系?沈氏家族对此作了如下解释:“侍郎公和欧阳真仙是结拜兄弟,一日侍郎公对真仙说,‘你是吃斋的,今后我的子孙要祭祀我怎么办?’真仙说:‘你我是结拜兄弟,今后你的子孙到大丰山祭祀可以用牲礼。’”[20]这显然是沈氏士大夫借用民间话语解决祭祖与祭神仪式之间的矛盾。于是,沈氏家族专门设计了相应的仪式:“丰山侍郎祠及抱鼓形墓,向例递年仲秋朔日为清、连两邑裔孙会祭。其中规定,预于东祠秋祭日铨缙绅备束刍登山拜祖,先酦素祭于仙殿,继陈牲馔于祖堂,再诣抱鼓形拜扫祖茔,格思孝思,两尽其诚,祭典历来弗替。”[21]如今沈氏家族到大丰山祭祖时,仍然遵循这一仪式程序。
沈氏家族士大夫对民间话语的借用,使得家族祭祖仪式既符合儒家仪礼传统,又符合地方道教文化传统。于是,沈氏家族族人在祭祖仪式的展演过程中,沈氏始祖士大夫和半山仙源开山檀越身份的认同不断得到强化。现今沈氏族人仍然尊称其祖先为侍郎公,并一再宣称其家族祖先的开山檀越权。
四、士大夫话语权的维护
沈氏在大丰山的半山建仙源堂祭祀欧阳真仙,其始祖“侍郎公”为开山檀越,但并未将庙宇作为家族私有财产,而是向欧阳真仙的信徒开放。明崇祯年间,道士吴茂淳借重新修葺庙宇之机,向其它家族募捐,并更改檀越的名称。显然,这一行为直接威胁到沈氏家族士大夫长期努力构建的话语权和丰山象征性资源。为此,沈氏族人在生员沈魁的带领下,上告知府,重新恢复了“侍郎公”作为开山檀越的地位。据《沈氏族谱》记载,当时的汀州知府判曰:“置租赡僧,供奉香火,沈能私有其庵,不能私有其仙。任人朝拜、任人施舍,于是有吴姓人塑仙像者矣。世远年湮,栋宇颓坏,于是又有托神网利、缘化十方者矣。崇祯元年冬,沈氏发银拾五两修葺,而妖道吴茂淳复募收异姓人捌两,至次年正月上梁,生员吴有照、吴维新輙标题檀越此。生员沈魁等群起讦告,其理直,其情激也。今断吴生员去梁题,明此庵堂沈氏子孙世世主。另据沈生员执称,吴之塑像尚在,恐后复有争端,但查其像自嘉靖年间塑入,祀奉八九十年载,一旦责令捧去,不几获罪阳仙乎!立借贴交付沈边,准仍祀仙,不得争庵堂,千万祀阳仙作证也。”[22]
沈氏家族在丰山仙源堂“置租赡僧”,说明沈氏家族已经完全控制该庵堂,僧人是沈氏家族的附庸。然而,仙源堂地处连城与清流交界处,离连城沈氏家族聚居地较远,沈氏家族无法对庵堂形成长期有力的监管,使得仙源堂出现“栋宇颓坏”的景象,也给周边不法之徒提供了可趁之机。所以,当吴姓在仙源堂重塑欧阳真仙像时,沈氏家族士大夫尚可容忍;但是更改檀越名,直接威胁到沈氏家族祭祀权合法化的象征,这是沈氏家族士大夫无法容忍的,因此通过诉讼维护其象征。
康熙五年(1666),土棍张仙衢等侵占沈氏祭产,沈氏家族一直告到知府才得以恢复。此后不久,又发生邓健如、钟亨我引诱道士意图侵吞沈氏祭产。为此,沈氏家族恳请汀州知府鄢翼明勒碑明禁,其碑文如下:“汀州府正堂加二级鄢为土棍屡占祀田勒石以杜觊觎事。据连城县贡生沈元奇、沈日表、沈兆阶,庠生沈登瀛、沈公彦、沈天津、沈其澜、沈象珠、沈济昌、沈士镜、沈人杰、沈毅骏、沈友龙、沈应昌、沈兆奎、沈应龙、沈济龙、沈济象、沈任圣、沈南秀、沈韵协、沈之葑、沈培菁、沈培蓉、沈恩仁、沈希韩、沈奇芳、沈先蛟、沈逢瑞、沈显鲲、沈应虹、沈元点、沈建勋、沈圣恩、沈琦、沈镜、沈斌、沈举、沈鳞等呈称:”天台法政,泽及幽显,大造仁恩,孚及神鬼。缘祖沈氏勇与欧阳真人为方外交,因建庵崇祀,施田租二千五百桶,以为仙庵香火先祖蒸尝。府志院碑朗具,自宋迄今数百余年无异。蹇因世变,于康熙五年,被土棍张仙衢等侵占,不已控告前任孟太尊送、卢二太尊审,追出归单一百余张,租交主持收作焚修之费。审单在案,案墨未干,效尤殊甚。近遭邓健如、钟亨我等或以囮诱妖道车算朘削,或乘当役包泊,庵内租税如抽盆茧,以致香火寂灭蒸尝斩绝,只得奔走宪台追出侵占契券,仙庵得以永存,祖尝得以无恙。但庵田尽属膏腴,豪强每图吞并,如仙衢之后复有健如,安知健如之后宁世刺棍,与其戚于已坏,孰若杜于未然。为此匍叩天台,恳乞给予勒石永杜奸谋,永存尝产。倘妖道再听迷惑,许乞驱逐以绝祸端,则仙人感佩于上天,祖宗衔结于下地。“等情到府。据此,合就给示晓谕。为此,示知仙庵该处人等知悉:除前免究,嗣后不许土棍诱道,侵占本庵崇祀香火尝租;如有违犯,许即指名呈府,以凭拿究,断不轻贷。特示”[23]
沈氏家族在仙源堂设立田租作为香火和祭祀始祖冰洁公的共有财产,是每年沈氏族人举行共同祭祖仪式,形成全体族人对祖先身份和丰山象征认同的基础。而不法之徒对沈氏家族田租的侵占,动摇了沈氏家族长期构建的丰山象征意义。所以此次是沈氏家族士大夫的一次集体动员,并力图通过官方的勒石明禁,断绝不法之徒的觊觎,使得始祖冰洁公开山檀越的地位得以稳固。
沈氏家族维护其开山檀越权的背后,实际上是在维护沈氏士大夫的话语权。它们通过向真仙信徒开放庙宇,使沈氏丰山的称号在更大范围内获得认可,真仙给沈氏家族带来好风水的传说也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光绪年间任南靖县训导的连城人童选青,在记述沈氏重修丰山通真殿时说:“大丰山,初为沈冰洁公之佳城,继欧阳真仙宫也。当日,真人谓公子永钦、路钦曰:”昔六祖假座具于亚仙而还具冢,功德无量。声施至今,若能为亚仙乎?当据此报以吉穴。“二公许焉。不数年,而真人羽化登仙矣。二公因创构堂宇于顶上,祀仙座于中,祀父祠于左,复置田数百亩,以给主持。事绩本末,具见府、县志及碑文、记、序,诸载靡不详悉确凿,固无俟鄙人绕舌也。然鄙人又不可无言者,何也?丰山顶上,殿宇巍然,迨至年深日久,雨坏风颓,沈姓修葺者屡矣,而终不敢私有其殿、私有其仙也。任人朝拜,任人施舍,乃往往因此而生端者,有二焉。一则灭祀争堂,饱棍徒奸僧之囊橐;一则捐金修殿,改开山檀越之姓名,致讦公庭,环生叠起。明崇祯间,府左樊公断还仙源堂,府尊笪公、邑尊李公断逐半山庵僧。本朝康熙间,府左卢公断归祀田,府尊鄢公杜灭祀碑记;连邑颜公移文,请清邑尊刘公及本省学宪汪公,断归标题梁上沈勇名字。若是者,何可屡述?乾隆间,有马君某和诸善士勷金修理。至若感仙功德、小补酬恩者,安可胜数?今沈公裔星五、仰颐,倡议重修丰山殿,非特二公子孙争先踊跃,即清、连好善诸君,亦莫不解囊勷美举。鄙人尝闻,真仙解疾厄丰稔,功德在人,与天地无终极,而山川大封名者,殆有时和年丰之意欤?今登此山者,宜乎生大欢喜,共庆丰年。是山永以大丰二字流传矣,诸善士亦可与此山俱传矣。”[24]童选青的记叙是对沈氏家族士大夫几百年来努力的总结。同时,童选青是连城人,他为沈氏重修欧阳真仙通真殿撰记,表明至迟到清光绪年间,连城士大夫已经认可沈氏家族士大夫的话语。
五、结语
如果将明以来宗法伦理的“庶民化”[25]作为区域社会对国家典章制度实践的社会历史过程,那么这项制度为沈氏家族士大夫提供了实践祭祖礼仪、实现“敬宗收族”目的的重要文化资源。在实践过程中,沈氏家族士大夫构建了家族祖先崇拜与欧阳真仙崇拜之间的关系,并使其始祖取得欧阳真仙庙的“檀越权”而合理入祀真仙庙。并且,在家族士大夫的努力下,沈氏家族的“檀越权”成为地域社会认同的话语。不仅如此,沈氏家族历代士大夫也不遗余力地维护这一特权。实际上,沈氏家族士大夫如此努力的真正目的是,利用当地道教大丰山的象征性资源整合家族力量和控制地方社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目的。
综上所述,区域社会在构建祖先崇拜和神明崇拜之间关系的、实质上是家族士大夫对地方道教传统、宗法伦理、民间话语和国家权力等多种资源的有效综合利用的复杂过程,而且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上述资源交替使用的过程。
注释:
[1][明]陈桂芳修纂:《清流县志》卷三寺观,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6页。
[2]清流县方志办主编:《清流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694页。
[3]Arthur P.Wolf,ed.,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
[4]劳格文主编:《客家传统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75页。
[5]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卜永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6、431页。
[6][7][11][14][清]杜士晋修纂:《连城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年,第232,232,230,230页。
[8]《连城沈氏族谱》,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石印本,卷之首《叙》。
[9][21]《连城沈氏族谱》,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石印本,卷之首《敦敬社序》。
[10][清]曾曰瑛修:《汀州府志》,卷三十人物“张显宗”条,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年,第608页。
[12][24]《连城沈氏族谱》,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石印本,卷之首。
[13]连城县志有嘉靖、天启、崇祯、康熙、乾隆、民国六个版本,前三志国内外尚未见存本,而康熙、乾隆、民国版本都有收录该文,依据中国修地方志的传统,此编可能被收入前三志中。
[15][清]全祖望:《鲒埼亭外编》,《四部丛刊》本,卷二十一《宝积庵记》。
[16][明]杨缙修纂:《归化县志》,卷一《建置志》,福建省明溪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1986年,第3页。
[17]《连城沈氏族谱》,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石印本,卷之首《八月初一致祭真仙殿文》。
[18]《连城沈氏族谱》,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石印本,卷之首《致祭宋侍郎始祖考冰洁公、妣胡夫人神主位》。
[19]刘永华:《亦礼亦俗——晚清至民国四保礼生的初步分析》,《历史人类学学刊》第二卷第二期,第53-82页。
[20]此故事由连城城关沈君木先生讲述,采访时间2005年10月17日。沈氏家族理事长沈朝杰也持这一说法,特此表示谢忱。
[22]《连城沈氏族谱》,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石印本,卷之首《明崇祯间与罗口吴家争仙源堂檀越经汀州二府樊公审单》。
[23]《连城沈氏族谱》,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石印本,卷之首《汀州府鄢太尊为沈冰洁公子孙杜灭祀碑记》。
[25]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2-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