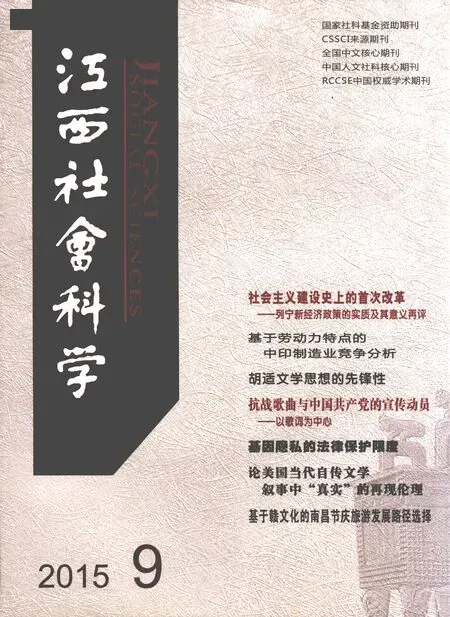音乐人类学“署名权”引发的思考
——兼及中国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回眸与展望
2015-04-14石春轩子
■石春轩子
音乐人类学“署名权”引发的思考
——兼及中国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回眸与展望
■石春轩子
20世纪初,音乐人类学在比较人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历经各阶段变革与完善,学科的名称和定义不断翻新与变换,内涵和外延不断深化与拓展。多学科融合发展成为音乐人类学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将不断促进整个音乐学学科建设更为成熟、健全和完善。
音乐人类学;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
石春轩子,华东师范大学艺术学院讲师。 (上海 200241)
音乐人类学作为一门具有独立意义的学科,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在它的学科名称、学科定义与范畴的界定上,就始终存在着诸多分歧,甚至同一学者在不同的时期,都可能做出不同甚至在个别方面互相冲突的界定。梅里亚姆曾经在1977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回顾和归纳了从比较音乐学到音乐人类学百年发展中出现过的对于音乐人类学的多种定义,并在文章的结语中总结道:
借着对这些定义所进行的历史审视,我们不仅能了解一些这一研究领域本身的历史,而且还能体会到这一学科中的思想发展。毋庸置疑,我深信今后还将继续不断地提出音乐人类学的新定义,并籍此体现出这一领域及其学者们日趋成熟的发展趋势。[1]
梅氏从音乐人类学的时间维度和历史纵深出发,对音乐人类学未来演变脉络进行大胆预测——即领域的不断扩大、视角的不断翻新将是音乐人类学必然走势,事实上,音乐人类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称作一门 “善变学科”,任何金科玉律都不足以约束它。
20世纪80年代,大陆学者开始对音乐人类学①的中文译名、学科定义、范畴和方法论等诸多方面进行探讨,特别是对“民族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二者间的区别和界定展开了颇为热烈的研讨与争论,这一争论的细节,在洛秦的《民族音乐学,还是音乐人类学——论学科认识中的译名问题及其“解决”与选择》[2]一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近年来,西方音乐人类学者已突破了学科本身定义的局限性研究,将探讨的焦点从音乐人类学的界定问题转向了对学科本身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的讨论,从而更进一步地拓展其研究的方法、范围和课题。梅里亚姆认为,由音乐人类学界提出的各种不同的新定义,彰显了本学科的发展成熟。然而,这只是看待问题的角度之一,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则可以说,其发展成熟不仅在于学科界定日趋明确固定,还在于如开放性、兼容性和吸收性等跨学科性质日渐发扬光大。以此视之,学科界线的渐趋模糊甚至恰恰说明了其发展之成熟[3]。
因此,笔者将文题以音乐人类学“署名权”冠之,实是找寻有效途径,从而以较新的思维方式来认识和评价音乐人类学众多名称的频繁变换,并为音乐人类学在我国的发展给出更为确定的指认。
一、“比较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署名权之界定
“比较音乐学”(英语为Comparative Musicology, 德语为Vergleichende Musikwissenschaft)是音乐人类学的前身,1900年前后在德国兴起,主要研究的问题是欧洲以外各民族的音阶和律制的形成过程、音乐的始源及民族乐器,并且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阐明音乐的起源、生成和音乐美德本质为最终目的”。[4](P40-43)阿德勒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在1885年创作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各民族的音阶》被公认为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标志。此时段,中国的王光祈也来到柏林,并把比较音乐学的学科方法、内容带到东方进行了广泛的传播。他以比较音乐学的方法,提出中国、希腊、阿拉伯“三大乐系”②说。要认识并探究“比较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我们不能忘记这是一门从西方引进的学科,更不能忘却将这门学科引进中国的先驱者。笔者以为,王光祈极富创造性的成果是其立足于比较音乐学本体考察之传统,并吸收相关领域(诸如民族学文化传播主义思想)的理论,提出中国、希腊、阿拉伯“三大乐系”说③,奠定了后世乐种律、调、谱、器的调查研究基础。但此后,中国比较音乐学却没有沿着西方的“纹路”勾勒,或者可以说音乐人类学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发展路径,即王光祈所述,通过整理我国古代音乐和采集民间流行谣乐,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西方的音乐科学方法,创作出中国音乐。
反观西方,自荷兰学者亚朴·孔斯特(Jaap Kunst)在其1950年所著的《音乐学》(Musicololgica)一书中将“ethno”(人种、种族、文化集团)这一前缀与“Musicology”(音乐学)一词合并后[5],便创造了一个新词 “Ethno-musicology”(音乐人类学),用于取代之前的“比较音乐学”。从此,“音乐人类学”开始在学术界内获得普遍认可,并成为此学科的新名称广泛传播。之后,不少有影响力的学者也陆续出版了音乐人类学方面的著作,如阿伦·梅里亚姆(Alan P.Merriam)的《音乐人类学》④、布儒诺·内特尔(Bruno Nettle)的《音乐人类学研究——29个课题与概念》⑤和《音乐人类学理论与方法》⑥以及曼特尔·胡德 (Mantle Hood)的《音乐人类学者》⑦等。
从音乐人类学取代比较音乐学作为独立的学术概念提出后,西方人类学家纷繁芜杂的理论和思潮、汗牛充栋的著述即不断地涌现,这一切都鲜明昭示出西方人类学家在截然不同的文化圈内“摸爬滚打”,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而这一学术趋向最终表明“音乐文化”研究是音乐人类学研究的必然。研究音乐人类学的西方学者,大多是兼修音乐学和人类学 (Anthropology)的学者,或是兼具人类学研究的学术背景。因此在音乐人类学的发展研究中,很大程度上均使用或借鉴了人类学的方法和理念。至于两者的联系,正如洛秦所说:音乐,是文化的一种表述形式。音乐中必然体现文化,文化中自然也就包含音乐。[6]
二、“民族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署名权之界定
对于音乐人类学的归属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重大的分歧,不少学者认为该学科是音乐学的一个分支,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该学科不过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是两个学科相交融而形成的独立学科,这种归属上的分歧一直延续至今,例如,新西兰最大的高等学府奥克兰大学(University of Auckland)则将音乐人类学专业设置在人类学系而非音乐系。“民族音乐学”抑或是“音乐人类学”这样一个学科“署名权”的纠纷,一个涉及学科规范最起码的问题,在我国也曾一度没有科学的标准,专家学者们各执一词。
一批大陆学者倾向于用“民族音乐学”替代“音乐人类学”,如赵沨和赵宋光提出用Sinology-mu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也就是研究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的华夏音乐,实质上是音乐人类学的一个研究方向,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与音乐人类学的方法相类似。黄翔鹏也认为“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音乐形态的差异”[7](P231)。
显而易见,这与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也是如出一辙的。也有很多学者认为,音乐就是民族的,因此不能将“音乐人类学”的界定单单限于民族音乐学,研究应包含所有的音乐以及与音乐相关的领域。还有不少学者认为,音乐人类学应立足于文化视野来看待音乐研究,重视音乐的人文性。
民族音乐学向文化人类学转型何以会障碍重重,是西方人类学艰涩的概念和玄妙的理论令该领域的中国学者不得其门而入,还是音乐人类学的思想、观念及学科的方法论在 “本土化”实践进程中格格不入,抑或是20世纪70年代末音乐人类学传入中国,中国音乐人类学与国际接轨过程中出现了偏差与疏漏?在笔者看来,其根本原因还应归于“音乐”与“文化”这对如影随形的概念,两者可谓各臻其妙,而又异曲同工,在历史进程中发生着越来越密切的关系。
根据洛秦在《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8]一文中的总结,梅里亚姆将自1980年以来的中国民族音乐学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1) The study of music in culture,即“音乐在文化中的研究”,体现为音乐≠文化;
(2)The study of music as culture,将“音乐作为文化来研究”,体现为音乐≈文化;
(3)Music is culture,即“音乐即文化”,体现为音乐=文化。
从上述阶段的划分中,我们可以看出,大陆学者对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在文化视域下来研究音乐本身及与音乐其他相关的东西,注重认知层面的探讨,不断拓宽该学科研究的延展性。
三、音乐人类学的未来走向
音乐人类学的学习和研究内涵非常丰富,传统音乐、民间音乐、东方艺术音乐、当代口头传承音乐以及音乐的变化、音乐的起源、音乐作品与即兴创作、音乐体系的比较等等[9](P3-4),都在其中。音乐人类学具有相当宽泛的范畴,既有“把音乐当作文化来研究”,也有“对音乐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以及“人类音乐行为的解释科学”等。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科之间相互进行融合,在音乐人类学的研究中也陆续出现了跨学科研究领域,并且几乎到了无所不在的地步。这种势头也吸引了不少专家学者的深入思考和热烈探讨。“国际传统音乐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raditional Music,简称ICTM)——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音乐人类学国际学术组织在斯洛伐克尼特拉布召开了第34届世界大会(1997年6月24日-7月1日),在最后一天的全体会议上,热烈讨论了有关Ethnomusicology的诸多课题,其中包括是否继续使用Ethnomusicology作为本学科名称,是否本学科已经完成历史使命而应被取消。美国的音乐人类学会学术刊物Ethnomusicology(《音乐人类学》)在会后也刊登了几篇相关文章继续围绕 “音乐人类学是否应被取消”这一议题进行了讨论。安东尼·西格尔(美国民族音乐学家、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非常关注这一课题,他认为学术界现有的学科划分都已经是陈年往事,绝大部分都是19世纪的历史产物,已经无法适应当今的发展形势。虽然从大学的科系划分的管理体制来看,至今还有不少价值,但是从当代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待,却阻碍了其发展和观点交流。因此从学术上考虑,他不仅更倾向于取消音乐人类学这门学科的界限,而且认为现今的其他学科区分也应取消。[10]
以笔者拙见,“音乐人类学”无论如何定义,如何深化内涵和拓展外延,其研究的内容、范围、方法以及角度均应从音乐与文化关系出发,立足文化视角,运用人类学方法对音乐学进行研究。例如可以借鉴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进行音乐学研究,建立多维网,并引入文化和全球的视角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当然,音乐人类学作为特定的学科,其以音乐为特征存在的文化,也有其自身特殊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11]
四、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
“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⑧,对音乐人类学署名权及一系列相关音乐文化问题的思考让我们重新驻足东方,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从我国音乐人类学的历史进程上来看,笔者认为音乐人类学在中国土地上的生根发展,是本土音乐研究、外来理论和方法,以及改革开放进程相结合的过程。
早在20世纪初,中国就出现了音乐人类学的萌芽。这个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以萧友梅和王光祈为代表的学者,本着对民族音乐的热爱,凭借自身对比较音乐学的认识,重新审视中国传统音乐的特殊价值与意义。接着,在20世纪30年代,以刘天华、杨荫浏为代表的学者,开始树立起建设音乐人类学的学科意识。他们梳理传统音乐的历史,整理传统音乐的形式,将实践、考察、采集等工作引入传统音乐的研究。与此同时,在延安还有一批为了创作而进行研究的音乐家。他们深入到民间采集音乐素材,对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创作了不少关于民间音乐研究的文章和乐曲。上海音乐学院洛秦教授认为,延安音乐家对音乐的研究“是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或者说‘本土化’的典型见证”[12],因为他们将民歌研究和音乐创作与抗战救国联系起来,扩展了音乐的政治功能。此外,这个时期民间音乐研究组织“山歌社”也为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进行了颇有意义的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传统音乐研究迅速发展。不仅仅在三个学院 (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东北鲁迅艺术学院)先后成立了民族音乐研究室(部),从学科建设上给予保证,而且注重传统音乐的“田野研究”,搜集一手资料,并开始关注其他国家与地区音乐的介绍与普及。音乐人类学(Ethnomusicology)的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传入中国的。1980年在南京举行了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研讨会”,由此展开了对Ethnomusicology的译法、学科范畴等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诸多学者针对中国的国情和传统音乐的特点,提出了对音乐人类学的看法,带来了音乐人类学思想的介绍和传播,出现了大批音乐人类学在中国实践方面的理论成果。
进入21世纪,中国大陆已经有不少高校陆续开始关注音乐人类学的研究。例如2005年,以上海音乐学院为基地的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研究院成立。该研究院的主要研究原则是学术的基础性、交叉性、前沿性和现实性,它立足于上海、扎根于中国、放眼于世界,以“中国视野中的音乐人类学建设”为目标,将“基础、原创和精品”为研究宗旨,深入研究“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这代表了中国音乐学研究的新走势,不仅推动了音乐人类学本身的完善,同时,也推进音乐学大学科的日臻成熟。
从启蒙到发展,这将近一个世纪的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包含了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反思,包含了对音乐的人文关怀,是中国传统音乐的转型,也是西方理论的中国化过程。
纵观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经验,我们得以清晰地看到特定时代和历史背景下,“西学东渐”、“洋为中用”后受西方文化体系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语境话语体系双重影响下,中国音乐人类学的独特发展道路,从这里我们可以对中国民族音乐学理论概念混乱、“署名权”含糊有一种善意的解释,即中国学者对固有文化的责任使然、操守使然。当前诸多学科出现多学科交叉趋势深化的现象,而音乐人类学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兼具音乐学和人类学的学科背景。此外,在我国的传统音乐土壤上生长起来的音乐人类学又具有跨文化的特点。所以,在未来中国音乐人类学的发展中,可以利用这些特点,加重对音乐人类学与各种学科、多种文化相结合的研究。比如将音乐人类学放在大众音乐生活,以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结合的视角下进行研究。由此,音乐人类学在中国将有更加的丰富内涵和作用,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而具体的操作原则上,则可以借鉴洛秦教授提出的“思想观念始终是学术发展的主导,人才队伍是学术发展和开拓的动力,学术机构、学科规划和运营机制是学科建设趋于成熟的保障”[13]。笔者相信,随着学科研究不断深入和细化,音乐人类学的发展将不断促进整个音乐学学科建设更为成熟、健全和完善。
注释:
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提及的“音乐人类学”在西方被称为“Ethnomusicology”。
②用王光祈的话说,即:“中国体系、希腊体系和波斯-阿拉伯体系”(王光祈:《东方民族之音乐》,音乐出版社1958年版,第275页)。
③王光祈对三大乐系的研究是 “在霍恩博斯特尔提出的世界三大体系的基础上,加以补充”(梅里亚姆:《音乐人类学》,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年版,第616页)。这在前文述及的两种说法外,又产生了“霍氏设定、王氏发展”的一种见解。
④Alan P.Merriam.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Northwestern,1964.
⑤Bruno Nettle.The study of ethnomusicology-twentynine issues and concepts.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3.
⑥Bruno Nettle.Theory and method of ethnomusicology.New York:Free press,1964.
⑦Mantle Hood.The ethnomusicologist.New York:Mc-Graw-hill,1971.
⑧“河东”即东方文化体系,季羡林先生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提出东西文化变迁中“西方不亮东方亮”这一前瞻性学术论断,用以概括人类文化发展的整体趋势。
[1]Alan P.Merriam.Definitions of“Comparative Musicology” and ”Ethnomusicology”:an historical-theoretical Perspective.Ethnomusicology,1977,(2).
[2]洛秦.民族音乐学,还是音乐人类学——论学科认识中的译名问题及其 “解决”与选择 [J].音乐研究,2010,(3).
[3](美)艾伦·帕·梅里亚姆.音乐人类学[M].穆谦,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
[4]萧梅,韩钟恩.音乐文化人类学[M].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5]Jaap Kunst.Musicologica.Amsterdam:Koninklijke Vereeniging lndisch Institute,1950.
[6]梅雪林.如何解读音乐人类学[J].博览群书,2011,(12).
[7]黄翔鹏.关于民族音乐型态学研究的初步设想[A].中国音乐年鉴[C].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
[8]洛秦.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A].启示、觉悟与反思: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三十年 (1980-2010)(卷2)[C].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
[9](美)海伦·迈尔斯.民族音乐学概论[M].秦展闻,汤亚汀,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4.
[10]杨沐.漫谈音乐人类学的定义与范畴[J].音乐研究,2000,(3).
[11]管建华.文化研究与音乐人类学[J].中国音乐,2001,(2).
[12]洛秦.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的反思和发展构想(上)[J].音乐艺术,2009,(1).
[13]洛秦.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的反思和发展构想(下)[J].音乐艺术,2009,(2).
【责任编辑:彭民权】
J60-05
A
1004-518X(2015)09-024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