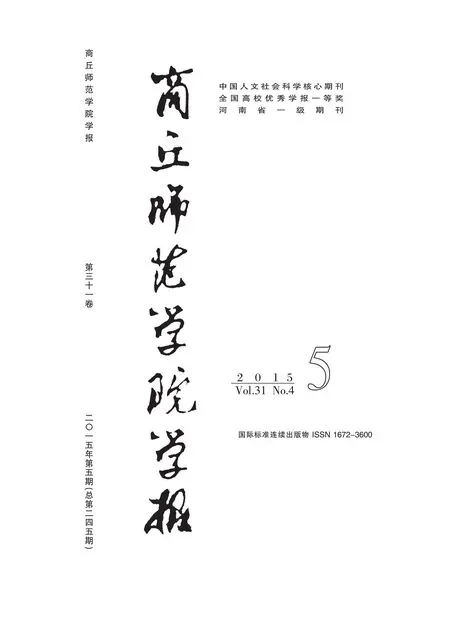论玄知①:道家的朴
2015-04-11任博克
[美]任博克
(美国芝加哥大学 神学院哲学与宗教系)
论玄知①:道家的朴
[美]任博克
(美国芝加哥大学 神学院哲学与宗教系)
在这里,我即将开始写作——实际上正在写作——但不知我会写出什么,或者在写作过程中自己究竟为何。我对能写出多少东西或何时止笔并不非常确定,这或许不足为奇。吊诡的是,即便确知将写出一些东西,我依然不知道自己会说出些什么。但是,当我说这话的时候,已然在第三句之中了。
无论如何,对于我将说出些什么的不知,并非消泯一切讯息的了无生机的空无。于之我并非一无所知。我对必须要做的东西有一些构思——要探究的主题,一些我希望引述的段落和文本——正如辅助或抑制、撄扰或激励我的物理与虚拟场域之中的其他因素,以及借由暗示或预兆、潜能或问题而呈现自身的东西。我发现了各种内在与外在因素从中心点进进出出的混乱,它们仅能片刻地组织起彼此之间的关联,招致了有益的推助或危险的病毒式滋生、尝试和含糊、设问和旋即转入黑暗之中的魅惑之路。我看到了可能性和危险,感受到了兴奋和疲倦,大量怒放而喧骚的探索性成长和努力,并伴随着接踵而至的意欲之潜流。
不知正是一个人在并非完全无知状态下的说或做:不是通过知或不知,而是通过玄知而前行的,我将说或做的是一系列边际模糊的关乎驱动力(torques)与敏感性(sensitivities)的可能性和或然性。既非确切的某物,也不是确切的无物,它是浑沦的。然而,使我们假定某物行将如此、正在如此或已然如此的东西,就其本质而言不是浑沦的、可议的、无常的吗?与之类似,某物在那里、是这样、是如此也可以这么讲。如果将这种模式施之于普遍的知识而非认知者会如何?如果说待认知的某物、如此这般的某物,既非可知又非不可知而是玄知的会如何?
然而,至少从原则上来说,不可知的东西并非事实,事实通常是可理解的,也被认为是可知的;按照定义,它在本质上是非常确切的,歧义在可能的认知者那里只会单独出现。正如常识和诸多哲学所说,我们经验到的歧义在认识论而非本体论上是必要的。歧义是经验的一种形态,与存在(being)无关。事物、事实和事件本身并不含糊;我们对其理解才会如此。如果事实只是隐微可知的,它们就只是隐微事实。它本应是一种事实,最基础的事实,其中存在有待认知的东西。大致而言,如果通常的事实只是隐微可知的,因此都不过是隐微事实,那么这也不过是一个隐微事实。
我预先非常确切地知道我将做些什么以及如何进行。接下来,我有时不得不丢弃一些垃圾(take out the garbage),我描述这些小插曲的方式或许接近其本义。其他东西则展示出了愿景与施行之间的巨大歧异:在世之跋涉关联到其他物和人,以及长远性的计划。一般而言,似乎关涉的事实越多——不管是其他事物和存在,或是更长的时间——我所预想的与实际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差异就会越大。但是,我的愿景和表现之间的巨大歧异,同样也从属于某些私人或私密的行为,例如,创作一首诗或一首乐曲。有人或许会说,当预想某项活动的时候,其价值取决于发生的事情与预想之间的匹配程度。这种假设似乎是很多一神论者思考神意与创世的基础。上帝知晓一切,确切知道己之所欲,并依其愿景而精确行事。一个完美与全知的心智,是知其所行的心智。一个完美与全知的代理人,所行恰能如其所愿。
如此而言,创世更像我丢弃的垃圾而非对语言和观念的竭力探求,下面我将使之与本文相协调。在创世之中,无论如何,不仅是垃圾,“丢”和“弃”也无中生有地被创造了;它们或许并未被发现已然作为有待克服的障碍而在那里了。上帝依照他的预想精确行事。上帝的知识和行动实际是齐一而等同的,迈蒙尼德(Maimonides)等人如是说。如果我们对此进行推理,或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无限境域之中,不存在任何与预知相符合的后续行动,而且,形象而言,说上帝行先知后与上帝知先行后应该是同等有效的。也即是说,两种构想都可能是错误的。这种悖反或许是斯宾诺莎引述的这种迈蒙尼德式观点的理论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传统的拟人化意象趋于增强有目的的行动的价值——也即此类知识先于、控驭并完全匹配接下来的行动。
类似的判断似乎也内蕴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知识概念之中。越清晰,越确切,矛盾与自相矛盾就越少,可资选择的理念、欲望、观点、特征的模糊性也越少,就会越好。知识即美德。知识越确切,对关于好以及更好的确切知识的形成就越有帮助。真实的实体,最真实的实体,是最富确定性的;真正的知识和德性同样也是最确定的。在行动之中,目标的不确定意味着善的不确定;善的不确定是一切恶的根源。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都以自己的方式揭示了这种关于确定性和知识的价值承诺是如何不可避免地逐步滑向超越的逻各斯、努斯或神这些原始一神论概念:超越精神(übermind)明晓事物的本质,理解本朴的真理,并依照充分预知的优先的、整全的决定性目的安顿万有。因为如果未能预设一个能够完全认知、彻底归类事物的绝对精神——实体因之而在矛盾的方式之中被实际经验或构想为真实的,就很难说断言事物本身是明确的有何意谓。事物自身毕竟从不放言证明自己是明确的——如果这样,其放言在某种意义上也不过是一种被某人特殊经验到的方式。因此,事物一定是清晰的;真实而清楚地认知它们定为德性之源;德性则定由预先确切知道自己所愿也即真正的善,以及付诸行动以全然实现这种愿景所构成。
还须说明的是,以上所述并非道家的立场,不是道家关于行动、存在、善或知识的观念。
尽管《道德经》是一个复合文本,对之进行分析和整理,还是会发现它展示出了一系列放弃了可辨姿态的主题和声明。我们关于特定的认知客体——不管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之特性的观念,都是源自将某物从其背景中剥离出来的心智活动。我们并非随意或无私地去做:对客体的择取是受欲望驱动的。价值和欲望实际上是相同的:赋予某物以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即为对它的欲求。同样,欲求某物也即赋之以价值。我们鉴别所领会和欲求的客体的方式,受制于语言及蕴于其中的价值取向。每当某物被注视、择取,别的东西就会遗留于其所由生的背景之中。早期道家文献将这种余留称为“朴”——一种从世界的基质之中择取事物的“开辟”之后的残余。这个概念表明,自然与被分解的诉求并不一致。自然能以一切可能的方式被分解,每一种都会遗留下朴的残余或背景。衍生这种朴之背景的是道:道路、过程或者说导向。
当我们明辨一种事物并称其为“本质”的时候,我们就将之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并判定了它迥异于其他事物的品质或特性。但一个事物如何区别于其他,并不取决于其全部的品质或特性,或者说最能成就“其自身”的东西。所谓的事物之本质并非使之如此的东西,也不是它真正是什么。我们知道,人类与黑猩猩的DNA有97%是相同的。如果我们以人类独有的3%的DNA来界定“人性”,称其遗传使我们如此这般,我们仅仅依靠独特的3%的DNA就能召唤出神奇的存在:这样的存在是无法存活的,不能成为任何一种动物,只剩下了孤零零的人性。当辨别事物的时候,当尝试界定本质的时候,我们将每个事物的最佳特性剥离出来,让眼睛易于将之从其玄暗的基础、并非独有的朴之基质之中辨识出来,而这些并不属于其特性,也无助于对之进行识别或与其他事物相区别。
早期道家文献暗示说,这种朴之背景是剥离之象或确定之物的根源。朴——做出任何关于确定之物的测定之后的残余——显然是浑沦的。朴是每当实体被辨识之后剩余的东西:你不会措意于它,也不会对之产生兴趣。在伦理上,当我们将事物与他者或模糊的虚无全然区隔的时候,就是将事物剥离了它的本根,而这恰是其价值与存在的真实本源。朴是这样的:
1.所有具体事物的看不见、不可见的——无论我们如何谛视、喜好、赋义——本源和归宿,事物由之而来、向之而去;
2.万物的过程,在其促使万物“复归”的意义上而言,呈现出钟形的图式,朝着看不见的本源(本源在定义上是看不见的,但借其使万物复归的引力中心的作用而显现;因此体现为“万物之过程”);
3.构成万物的质料(stuff)。
有价值的物体中看不见与未被注意的“朴”有两种重要意义。它是琢成物体之后被遗弃的碎屑,也是起始之前无价值、未雕刻的全部质料。道因此就同时是这两种意义上的“朴”。既为“反面价值”(disvalued),又是“尚未有价值或反面价值”。
经由对道的这种理解,可以引申出许多格言式的启示:事物越清晰,与绵延的真实就越远;我们对事物的认知越清晰,知识就越不精确;知识越模糊,就越类似于、越分享了事物的本相。浑沦的知识是浑沦的意志的功能。与道为一意味着不对自己的行动进行确切的认知,因此也就不去追究行动有何用。但再进一步,精神活动甚至原始冲动并不被摒弃。《道德经》描绘了这种引人注目而又颇有意味的图像:“婴儿不知男女之事,然而他的生殖器勃起了——至高的生命力!”(第55章)婴儿对勃起的目的并没有任何心理意象,但他依然勃起了。婴儿对勃起并不知其所然、所欲,然而的确需求——浑沦的、源初的。然而,这种异于认知的浑沦的、源初的需求,《道德经》认为是真正的根源、真正的进程,是生命力的真正本质,正如男女之合所实际获致的那样。
对于知与不知,伟大的道家作者庄子(前369-前286?)如是说:
“知道天在做什么,知道人应做什么,是最好的。”
“知道天在做什么”:天,作为天,是万事万物的显现。
“知道人应做什么”:用你的认知所知道的,滋养你的认知所不知道的。这样你就能获得自然的生命而不会中途夭亡。这就是认知真正的最好结果。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的认知只在与某物的依赖关系中才是恰当的,但它所依赖的东西却常常是非常不确定的。因此我怎么知道我所谓的天不是人呢?我怎么知道我所谓的人不是天呢?换言之,“真正的认识”只有在“真正的人”那里才是可能的。②
庄子所说的天是未知的、不可知的。在其著作的前面部分,他曾追问我们的情绪、思想、价值、观点以及事件缘起何处。答案是不知道。庄子说他无从辨识事件的任何特别来源或行动者。他还说,看上去根本没有认知的方法,因为认知无不生发于某个事件、某种观点之内。显然,没有任何认知活动能在其发生之后或之前存在,没有任何认知活动当下即是,换言之,事件自发显现。由于知识受制于生成后的状态,只能推究其存在之前以及由之而现的过渡状态。
仅在意识的既有状态中,思考和推理也会发生,而且依照蕴蓄于不同时间、地点及代理人——也即不同的知识-事件——之中的情绪、许诺和推理规则,它们的运行似乎是千差万别的。因此,特殊的认知活动看上去能够影响和敷饰其范围内的一切,乃至关乎它的起源的推断,一种它因之而显现为当下之所是的差异性,但将之施于其他认知活动中的情绪、许诺和规则的时候则是不可信的。其所由生的任何情境中的决定活动也深刻而无望地内蕴于它自身的呈现状态之中。它的“之前”是一种“相对于当下而言的之前”;它的“原因”是“作为业已内化于效用之中的原因的冲击所遗留之物的原因”。
庄子使用了“因”这个传统的词汇,意即天,但仅是消极意义上的。与庄子同时的儒家思想者孟子,提供了天的简要的功能性定义:“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5A7)孟子的意思或许是:“天是我们找不到其他原因的一切事件的行为者。”天意味着超出了人力所及的任何东西——典型的转换话题(passing the ball)式定义手法。超出人力的东西一定会在某人或某物的控制之下:拟人化的神,或祖先,或精神力量的松散聚合,或只是一系列客观的自然过程。但一些确定的事情,如果可知的话,是能够充分解释发生的现象和缘由的真正原因。无论如何,即便在孟子简约的天的定义之中,我们也能发现些许庄子对这个术语的更彻底的理解,这种理解让孟子的定义颇显直白:天不仅仅是超出了人力的东西,而且是使决定性的“控制”、“原因”、“决定者”等概念丧失效用的东西。
因此,庄子的文章始于关于人的知识之恰切分工的习见:知天——也即认识自然界及其可能具备的道德或宗教之维,了解什么超出了你的控驭范围,并清楚你能控驭什么,这或许就是真正的知识,真正的智慧。然而,庄子随后便习惯性地扭转了这种老生常谈:如果天或事物的属天方面是不可知的,这种分工最多也就仅意味着应该利用我们知晓的部分去养护——而非认知——我们与世界的不可知部分。其中“养”的关系是最高明的可能知识,与察觉自身的无知以及维系知与无知之间的确切关联是同类的:这种道家式立场或与稍早的《道德经》的概述相似:未知/不可知的是朴,是生命、成长以及存在的真正根源,我们的认知思维不能致力于从中获取信息,这是不可能的,而应究心于通过守抱不可见的“本根和土壤”——朴与光彩夺目的花朵之间的密切关系,以确保它能永久地活化已知之物。
但应如何存养不知道或理解的某物?我们对其照料和养育的东西必定有所了解!我们提供的养料或许对之是有害的,当它们返归于我们自身的时候亦然(可谓是不可知之物的废品)。改易对这种关系的说法并不能解决胜过一切的无知问题。更有甚者,庄子将无知的品质拓展到了知与无知的议题:“我怎么知道我所谓的天不是人呢?我怎么知道我所谓的人不是天呢?”这与《齐物论》中更为尖锐的问题遥相呼应:“我怎么知道我所谓的知不是真正的不知呢?我怎么知道我所谓的不知不是真正的知呢?”这种理论的深进看似彻底的不可知论者的归谬法——并且实际上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的相关论争是以这种方式呈现的:如果知识是不可能的,我们便无法知道知识是不可能的,因此宣称知识是不可能的不能避免自相抵牾,故而必须将之抛弃。
庄子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必须将之抛弃的论点。相反,他将无知问题的极端性视为自身内蕴的解决之道。在追问了那些“我怎么知道”的问题之后,庄子提供的结论有着劝导性的架构:“换言之,‘真正的认识’只有在‘真正的人’那里才是可能的。”在其著作之中,奇特而又极易令人误解的术语“真知”由此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和生存态度的敬辞开始被使用了。然后他继续描述这种态度:
什么是我们所谓的真正的人?古时的真人不厌恶自己的不足,不渴求完满,不预先谋划事务。以这样的方式,他们或错或对,但不会后悔或自我满足。因此他们能够无惧地攀登顶峰,潜入深水之中不会浸湿,进入火中不会感到灼热。这是他们的觉解能够做到的,在究极的层次,可以径直登升而入道之远景……
古时的真人对欣悦活着或憎惧死亡毫无察知。他们不为出生感到高兴,不对归化进行抗阻。骤然而来,遽然而去。从来不会忘却自己从哪里来,也不探寻将要往何处去。领受生命,满心欢喜;忘掉所有,还归大化。
这就是所谓的不用心思推求道,不以人性参助天。这就是我所说的真人。
这样的人——心思专注③,面容安宁,额头宽阔而平朴。他像秋天一样凄冷,像春天一样温煦;他的欢笑和愤怒与四季相通融。他适应遇到的任何事物;没人能准确说出他的可能的终极。因此,如果圣人使用武力,在毁灭敌国的同时,不会失去民心。他的仁慈与恩惠能泽被万世,却不是因为满怀着对人类的爱。
如此,他乐于为万物导夫先路,却不会成为“圣人”。对他人保持亲密,但不会成为“仁人”。他能应时若天,但不会成为“贤人”。不通乎利害,不成为一个“君子”。他能做自己的份位要求的事情,却忽视了个人的利好,不会成为一个“士人”。丧失了性命却没有丧失自己最真的东西,不会成为一个“役人”……古时的真人能够做到我们要求的任何东西,却不袒护任一党众。他们仿佛处于困境,却不会接受任何帮助。参与万物,他们是孤独的而非僵固的。
四处传扬,他们虚心而不浮华。愉悦,他们似乎怡然自得。向前推行,他们以不得已行之。他们含纳万物,但万物外在的表现完全如其所是。他们广泛施与,但万物似安憩于自身之德性。呈现出骇厉的症状,他们似乎觉得与他人并无不同。巍巍然,没有东西能控制他们。连绵不断,他们似乎更愿意遮蔽自己。漫不经心,他们将忘掉自己所言。
他们将……认知视为权宜之计……只在现状不可避免时才会产生……因此,他们喜欢的是事物的统一,但他们所不喜欢的也是事物的统一。他们的统一是统一,但他们的非统一也是统一。在其统一性之中,他们是天的跟随者。在其非统一性之中,他们是人的跟随者。
此即天与人均无法彼此胜出的原因之所在。这就是我所谓的既天而人,一个真人。④
这篇文章所呈现的不是规范性的,而纯然是描述性的——对庄子引以为傲的“真知”这一术语的行动和姿态之情状的描述。
真知究竟是什么?是对无知的彻底接受:不将表面上的需要视为真正的需要,因而不必拒斥它;不将表面上的成功看做真正的成功,故而不会因之而喜悦。既然人们对生存是否比死亡更好一无所知,只是从当下活着的角度看上去貌似如此,人们并不知道如何欣悦生命、憎恶死亡。素朴的无知引致出因顺并遽然进出于各种情境,遗忘之并继续前行,而不试图对此前或此后的东西进行认知或表态。文章在我所引用的最后几行中蕴蓄到了极致:“在其统一性之中,他们是天的跟随者。在其非统一性之中,他们是人的跟随者。此即天与人均无法彼此胜出的原因之所在。”无知就是知与不知、“人”与“天”的统一——或者严格来讲,不是能够暗示已完成的综合体的统一,而是知与不知自由流动的开放性,所以,彻底的“无法胜出”也不是问题的明确答案,“这是什么?是可知的还是不可知的?”既然每种视角只能明晓自身,所有知道亦为不知,不知也经常呈现出知的形态,因此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是什么。
我们在这里邂逅了庄子解决彻底不可知论——在其他传统中被严肃的哲学思考所驱逐的吊诡的方式。在庄子那里,对人的接纳意味着将此刻的观点视为此刻的观点,而非试图抵至泯除了所有时间中的一切观点的不可知的原始状态。对天的皈依意味着不去探察此刻某人的观点是否是真正的知识。在认知的不息迁变之中,知与不知的聚合就是可理解的了,但不是作为模糊的隐微认知,而是作为等效而精确的认知,这或许与康德对受制于现象领域的科学知识的展望类似:我们能够正确而精确地认知现象,但与此同时,这种知识对物自体一无所知。在康德式的处理中,一个人只在其认知处境所界定的存在范围内领受知识。
但是,康德的方式取决于一些完全不属于庄子之学的预设。首先,康德假定,我们所有人的理性(Vernunft)和理解(Verstand)能力都是相同的。对这种认知能力的单义性的拒斥,是庄子的整本著作的主旋律。庄子反对这种单义性,连同由此而生的关于有效性的共享信条,甚至此时的“我自己”与彼时的“我自己”——正如他梦见自己变成蝴蝶的著名故事之中,或者是一只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子?⑤因为我不会在任何时候都以同一方式对某物进行领会或思考,在我的体验形态之中存在着深刻的间断,无法被一个支配一切的知识裁定系统所统纳(任何这种系统都是自我包含的,并被某一种形态所限定)。
如果没有单义性假设,与之相符的现象性知识就不会精确。精确所需的再现性和可验证性要求相同的结果在大量的目击者那里能够再次甚至无数次复现。然而,庄子否认了再寻任何东西的可能。他尤其关注行动的伦理之维,关注人们对自己所做之事的无知。浑沦对富有生机的“真人”而言是一种助益:他们在行动的时候忘记了自己所做,他们不遵循任何一条常道,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究竟为何(“一会儿是龙,一会儿是蛇,随时而变,不肯保持任何单一的行动路线”⑥)。让我们再次回顾“不知男女之事,然而他的生殖器勃起了——至高的生命力”的婴儿。他对自己的冲动的“善”一无所知,对自己的目标毫无“记忆图像”,却有着无形无象、无知无识的原始冲动。也就是说,他知晓不确切的目的,他拥有不确切的目标。这就是“无为”,对将要去做的事情不存任何前见的行动。
在稍后的文本中,庄子讲述了一个算命巫师的故事,他仅仅通过相面就能明晓所遇之人的未来。他能对未来做出精确的、确定无疑的预言——这是庄子对确切的尤其是预测性知识诉求的讽刺画像。这个巫师在壶子面前遭到了挫败,壶子呈示出一系列前后矛盾的面貌,使得巫师不解、烦闷、迷惑,坚持让壶子整齐自己的状态,这样才能告之以准确的命运。最终,壶子展示了让巫师落荒而逃的某种形象。在被问询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壶子说:
刚才我向他展示了我还未从我的根源之处显露之时的形相——一种虚无而宛转绵延的状态,不容任何关于谁或什么的理解。因此他将之视为无定的颓陷和靡散,视为随波逐流。这就是他逃走的缘由。⑦
壶子所述即为“真人”观察以及感觉的方式——虚无,不容任何关于谁或什么的理解,宛转而绵延,无定的颓陷和靡散,随波逐流。庄子的总结体现出了如何将知识视为暂时的权宜——换言之,如何不带确定性地去做:
不要做,不要成为⑧名声的尸体;
不要做,不要成为计划的仓库;
不要做,不要成为事件的主持;
不要做,不要被自己的认识宰控。
知识无法成为行动的指南;作为行动的衍生物,它是次要呈现的。知识不能成为决定是非、应然与否、应做与否的主人。嵌入这种行动之中的此类知识只能是关于正在发生的玄知的认知。这种知识既不存在于我们丢弃的垃圾之中,也无法在与现实世界的原朴之广大的争辩或艺术工作的构成中发现。我们跃入一系列探索性的浑沦经验之中,不知道事情行将如何或我们真正的所欲所为。在这种意义上,道家的行动就是艺术性的行动,对任何可能出现的东西保持开放性。
在这篇文章中,庄子紧接着叙说了影响后来之中国思想的用心若镜的隐喻:
以这种方式,全力呈现着无穷,并在没有任何征兆的地方漫游,将所受乎天的东西完美呈现,但不措意于已得到的任何东西。只是虚无而已。
至人像镜子一样运用心智,不拒绝任何东西,不欢迎任何东西:反映而不含藏。因此他能克服万物而不受伤害。⑨
关键在于,不要将“他的心智像镜子”误解为要求心智客观反映“事情存在的真实方式”⑩。引文中镜子的本性并非其准确性或不失真的映照,而是反映与从不“含藏”图像。因此,知识不是一刻不停地累积,不具有确定性和连贯性,不会被迫于去关联并塑成一个不断膨胀的信息的巨大形体或系统。知识是免于呈示限定形态的浑沌——因此在庄子著作中,紧接着上文所引的“至人”段落,是真正反抗始源的令人惊异的终极寓言:
南海的帝王叫做倏。北海的帝王叫做忽。中央的帝王叫做浑沌。倏和忽经常在浑沌的领地相遇,浑沌总是很好地招待他们。他们决定报答浑沌的美德。“所有人都有七窍,并以之看、听、吃和呼吸”,他们说,“但唯独浑沌没有。我们给他凿出来吧。”
他们每天凿一个孔窍。
七天之后,浑沌死了。
原始的浑沌,朴,不能被当做知识的客体甚或主体。
就像浑沌那样,镜子是虚无的,但并非空白。其虚无——关于确定的身份、一贯的知识、明确的价值、已知的程式——使之反映它前面的任何东西。反映并非模仿或精确的表现;镜子有其本有的从情境的突现与布置之中衍生出的能与势。因为镜子有自己的位置、视角,使之能够克服而非映现置身其前的东西,并且避免了对自身或它所反映的东西的伤害。庄子关于猴子和养猴人的著名故事有助于说明镜喻的意涵:
但试图通过劳攘神明而使万物为一,却没有意识到万物本即相同(不论做此与否),就是所谓的“朝三”。
什么是朝三?一次,有个养猴人分配橡子,他说:“我将在早上给你们三个,晚上四个。”猴子们很愤怒。“那好,”他说,“早上给你们四个,晚上三个。”猴子们非常高兴。这种描述和配置的变化并未引发损亏,但一种情况引起愤怒而另一种则是高兴。他只是循着猴子们当下“如此”的“是”而行事罢了。因此圣人通过运用各类正确和错误而与他人和谐相处,并且在天之轮盘的中心安然留处。这就是所谓的走两条路。(I4)
养猴人针对猴子的“当下‘如此’”,“因是”而行,与镜子的“反映而不含藏”是类似的。养猴人看重的是当下的状况,而不关心正确或错误。正确和错误并不客观,其根基永远不会被知晓或证明。镜子映照或者说反映的是“当下‘如此’”。“不含藏”就是“在天之轮盘的中心安然留处”。通过进入虚无——或者用猴子的故事中的话来说,“在天之轮盘的中心安然留处”,镜子反映了所有(但一无所藏)猴子的形象或偏见或计划。镜子促进并增强了任一及任何计划,然而是在它自身的隐蔽特征中如此的。镜子自身的计划不比养猴人的更公正,两者开始无碍、无伤的流动。
《庄子》辑录了这样一段对话,在其中,庄子的后学藉某角色之口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如果我们计算事物的数量,不止万计,然而我们限定而称为“万物”——不过是因为它们数量庞大而以这种假定之名称之。因此“天地”只意味着形状中的最大者,“阴阳”只意味着动力中的最强者,“道”只意味着所有活动中的至公者。用(“道”这个词)来表示广大包容的假定之名是可以的;但一旦有了这个词,就意味着将道视为与某物相当或对照的了。在此基础上进行争辩即是将道与其他类别进行比较,正如我们在将狗与马的种类进行对照时所做的那样。这种做法的谬误不啻千里……(II0)
我们对事物的命名只是模糊的近似值,而非准确的。这种经验法则适用于过程、道路、道,但对最为特殊的个别事件也同样有效。对话者继续问道:“在季真的‘莫为’和接子的‘或使’理论之间,哪个是如实的?哪个只是对万物统一的部分理解?”所提供的答案对道家的“模糊知识”概念进行了很好的阐释:
鸡鸣狗吠——这是人们知道的。然而,尽管拥有最广博的知识,人们也无法用语言描述它们既已如此的根源,也不能用思想探察它们行将如何。我们可以继续深入分析事物,直到分类不再可能的精微、无法环绕的广大之处为止。即便如此,“或使”或“莫为”的理论并未超脱事物的境域,因此在本质上是错误的。“或使”蕴示着实质性的某物;“莫为”指涉着完全的空无。有名称、有实质的指的是事物的在场,但“无名”、“空无”仅仅给我们指出了事物之间的空白。我们可以言说并思考这些,但说得越多就会离得越远。
不能禁止未生之物的到来,不能阻止死亡之物的逝去。生命和死亡之间并不遥远,但它们的结合方式却无法被认知。“或使”或“莫为”等理论不过是你的疑惑所依靠的支架。我凝视其根本,其复归之过程无尽;我探求其最远的进展,其绵延之照临无止。没有终点、不会停息——这是在语言范围内的否定,因此只能在纯为事物的境域之中被分享。“或使”和“莫为”——是对本根的尝试性描述,但他们实际上是在事物运行的地方结束和开始的。道不能被理解为存有,也不能被理解为乌有。“道”这个名词,是我们为了使自己能循之而行而称示的。“或使”或“莫为”都只不过占据了事物之境域的一角,与大道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语言是完全充分的,我们终日所言均将为道。如果语言是完全不充分的,我们终日所言不过只涉及具体的事物。道和物的终极层次是不能被语言或沉默传达的。只有在既非语言又非沉默的地方,议论才能真正抵达其极点。(III-I2)
既非语言也非沉默:略似说了些什么,略似什么都没说。略似很有道理,略似毫无道理。略似知道事物之所是,略似不知事物之所是。略似知道你在做些什么,略似不知你在做些什么。
附言
在本文的论域之中,说一些关于佛教的话是必要的,尽管先要作这种惯常的声明:在整个浩瀚的佛教传统中对任何相关的理论发展进行全方位的叙述是不可能的。但佛教思想的一个中心思路可被概括为:执著,以及放下执著的解脱观念。
执著并不仅仅甚或在根本上意味着对物品的占有,对物质的贪婪,或对特殊处境和物之安置的系恋。它还意味着,也许最重要的是对观念的执著。然而,对观念的执著也意味着:事物有明确的可被认知的本质,观念有单一而确切的含义,我们认知事物之所以可能的假定——“这是什么”这个问题应该存在答案。任何回答都是佛教所谓的“识”;也即一种扭曲的、拙劣的、无益的姿态——执著。
观念亦为尘缘,佛教心理学将“意”视为六根之一。意念因偏爱、累积、发展以及持守关于事物的某种见解和立场而感到愉悦。这种愉悦无一例外地引生出了执著和沉溺。意念的官能中存在着一种悦纳物之所是之识见(views-of-how-things-are)的心理动机:获取观点,继而挫败其他观点,最终成为关于事物之真理的持有者,能够充分予人以稳定、安全、有力、真实的感觉,这种感觉形成了错误的——在佛教看来是灾难性的——结论,那就是人拥有或本即真实的独立自我。
决定即否定。决定即限度。决定即终结。斯宾诺莎如是说,尽管他是在纯粹逻辑的意义上意谓决定的:空间中确定的几何图形——方形、圆形、八角形——之所以如此呈现,取决于它们“取消”或排除的空间。它们“是什么”的本质即其界限。
决断即苦。佛教传统如是说。对此,说得最透彻的是《杂阿含经》XII.I5中令人讶异的简明宣告:
实体存在——就其本身而论也即确定性——就是苦。任何出生和灭亡的东西在时间中都有确定的界限:在X时刻之前它不存在,在Y时刻不复存在。X和Y就是规定其存在的界限。简单说来,如果它是这个而非那个,如果它排除任何可能性,它就是有待的:仅在那个缺乏的条件下才能存在。任何有待之物都是无常的。任何无常的都是苦——或者以无常的快乐的形式,或者以直接经验到的痛苦的形式。
奠基于整个佛教传统中的这种思维方式的关键前提,是任何经验到的东西既非独立自存的,也不取决于任何单一原因,而常常是多种多样的因缘和合的结果。多样化意味着原因有着不同的趋向、属性和轨迹(实际上并非作为独立量,而恰恰无法占有在一切关系中转徙的有限的系列属性;不存在任何确切的系列属性,结果就是,它们无从实施或保证总是拥有与其他给定的趋势常相一致的属性)。因此,原因在一些处境之中和时间点上并非有序而是单独或在纠缠中运作的。没有任何单一的原因是既有结果的缘由,这也便意味着不存在意志完全自由的自我,如果自由意志或自我被认作是在超出其控制的——超出其因果有效性的——其他处境不存在的情况下能够引发结果的原因的话。我的意之所图都不可能由意志单独完成,不管我的愿力如何强大。意志受挫让我感到痛苦。因为任何确定的东西都是有待的,都是苦。
什么不是确定的?这是佛教的谜题。然而,尤其是大乘佛教的一些流派提供了一种答案,即没有任何东西在真正严格的意义上是确定的: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是本体性模糊的(ontologically ambiguous)。这就是空(Sunyata)的学说,它否认了任何“自性”的存在。自性之缺失的真实意蕴是明确的身份的缺失。而且,明确的身份的缺失不过是叙说单独运作的单一因缘不会产生任何结果这一基本前提的另一方式。对于拥有明确的任一属性的实体而言,依照佛教否认任何单一原因的有效性的缘起并生观念,自主创造、显示甚至持有这些属性是不可能的。
作为具有某种属性的存在,我们在无知情态下的描述和体验是多因素的事件。这并不是说水是湿润的,因为水这一物质仅“有”湿润这一特性,不必多言。水不是湿润的。水没有任何性质。毋宁说,湿润是一种“次级属性”(secondary quality)(用伽利略、笛卡尔和贝克莱的话来说)。次级属性不属于物体自身,而只在与观察者的特殊方式相关的特殊联系中呈现。与观察者的联系是湿润这一经验暂时显现所需的第二个条件。湿润是两种原因结合的结果:动物的神经系统和水。两者转而同样也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事件(诸如此类,永无止境)。因此根本不存在基本的性质:所有性质都是次级的。事物没有任何属性。没有属性,就没有属性的占有者。因此,水这种东西根本不存在。同样的推理可应用于任何其他普遍的存在物。消弭一切性质的空无也不存在,因为空无也不过是受到单一原因“真实如实呈现——真相”影响的模糊的属性。当然,唯一的真相是浑沦。不是确切的特质,不是特质的明确缺乏,而是浑沦。因此,不知状况如何比确知一些东西更接近真实。
不管怎样,在一些佛教传统中,我们在被告诫不要去认知事物是什么的同时,也会被明确建议去体认行动:通过停止思考对事物是什么的认知来脱离苦海。这种建言的组合显示出自我指涉的悖论。这是庄子的困惑:“我在做什么”不也是本体性模糊的吗?这个问题划分出了佛教的流派。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处理方式的变形,或许我们能在中国佛教的一些形式中看到道家的影响——尤其是天台宗,一些禅宗的支流也讨论这个问题。至少在天台宗那里(多少受益于鸠摩罗什卓异的《妙法莲华经》中文译本的开放性),我们能看到应用本体性模糊于行动之中的新颖的指数级发展。或许可以说,其要点是关于如何才能“不知所措”的修行方法。
这种修行止于何处?不妨想象一下对上帝的狂热信仰。完全信任上帝的人会说:“我不知道终极计划是什么,但我对上帝的所作所为有信心,因此我将放弃控制事物的运行方式及它们究竟是什么的企图,而将之交付给上帝。”这种态度将知识托付给了他人而非自己,上帝是真正知晓善与未来之本质的唯一。这种态度使得知识愈发成为某些人的绝对标准,尽管有所迟滞。人们认为事物在原则上是确切可知的,甚至是确切已知的——在某个时空之中的另一硕美心智那里。我们可以将这种一神论视为试图超越知识的彻底溃败的权宜之计。我之不知汇入他者的认知之中,取消自身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投射荣宠而迟滞的形式,这种形式是我之一切所遇的绝对决定因素。我不知道我是谁或我究竟在做些什么,但是上帝知道。念及这种处境,不妨重审一下黑格尔对“苦恼意识”(unhappy consciousness)的分析,分裂并自我疏离,用被取代并向外投射的自身压制着自身。
但在这种论述之中,即便上帝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即便上帝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即便上帝也不知道你是谁、是什么,或你的目标是什么。上帝自己毫无目的。上帝是盲目之物,间或抛出一些关于别的东西在做什么、是什么、目的何在的不顾后果的假说——然后,迅速地忘记了这些假说并代之以其他说法。这是价值的(道德的)相对主义吗?它并非相对主义,而是超相对主义(hyperrelativism, überrelativism)、涡轮式相对主义(turbo relativism)、极致的相对主义甚至绝对的相对主义。因此,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在绝对不可知论的讨论中已然触及的问题:相对主义被认为是自我否定,因而是无效的。我想说的是,如果愿意的话,所有断言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各种论域中被分析为相对主义者与绝对主义者的原理的绾合。这种观点是我们所谓的本体性模糊的必然推论:以某些方式来看,它是相对主义;由其他方式而言,它是绝对主义;在某种或其他语境之中,每一种都是描述事件的合理方式。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实质上是密不可分的——并且它是绝对主义者的傲慢的题中之义,他们认为两者应该永被隔离,相对主义永远是绝对主义排斥的单义的相对主义。相对主义也是相对的,模糊自身是模糊的。
这种论辩思路看上去显得很轻率,因此让我更明确地阐述一下要点:任何价值系统都同时蕴含工具价值和终极价值。即使我的终极价值是非常具体的东西,比如说“散步”——意即我的绝对准则是“散步永远并绝对是好的,不散步永远并绝对是坏的”——我依然表达着一种关乎工具价值的相对主义。我不能说抬起左脚向前走是完全好的,也不能说抬起右脚向前走是完全好的。在某些时候与情境之中,两者都是相对性的好:在另外的时候,我的右脚更适于牢牢着地(说的是,当我的左脚前行的时候,为了我的终极价值——散步)。终极价值越是抽象、包容或模糊,我将越为相对的为貌似与之对立的行为做辩解——以至于是因为它们才获致终极价值的程度。如果我将“身体健康”视为我的终极价值,散步就仅仅是相对好的,只有到了它能够获得健康的时候。如果道德德性是我的终极价值,身体健康就只是相对价值——关系到对道德德性的帮助。即便是绝对的道德,在所有的下级层次上同时也是相对的道德。
相反,最严格的相对主义也能被建构为绝对主义;它一直有着所有相对之善所适合的一些条件。真正的问题是终极价值的模糊性究竟如何。这种模糊——越是抽象、包容,绝对价值就越不明确、特殊,系统就越是相对。为了敲定必然的道德绝对主义,柏拉图将其终极价值命名为“善”自身,从而开启了极致的相对主义者系统的大门(如果他能止步于此的话)。当我们谈论极致相对主义的时候,我们所说的是终极价值的极致模糊性。极致的模糊性绝对正是古典中国系统所拥有的。其终极绝对价值或是道、朴(意思是不能被化约为从整体剥离出来的任何特殊确定性),或是中(意为不会偏爱任何片面的极端或两个相对语词中的任何一个:非上非下、非强非弱、非此非彼)。中、中庸、道构成了绝对的善、绝对的价值以及绝对的真理,仅仅由于它们是系统性的玄妙,刻意地斥绝任何特殊而僵固的内容。这种类型的绝对主义与极致的相对主义是相同的。
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这里概述的道家-天台的立场,就必须追问,如果不假定特殊的分辨程序,这种关于事实的观念是否可被完全理解。对存在某种事物存在方式(way-things-are)的假定并非经验主义的。与之相反,我们经验主义的发现的是分歧——关于什么是什么、什么是有价值的以及我们在做什么——不断变化的混乱。面对这些歧见,许多权宜的解决方式已经提出来很长时间了:宣称有些人是正确的,同时有些人是错误的;有些印象是虚幻的,而其他的是正确的;某一观察者群体所认同的东西是真的,而忽略其他人持守的观点;某些程式的结论至少在某些时候可被验证或预测为真,然而所有其他观点都不被重视;上帝理解事物的方式是如其所是的,其他人的理解方式则仅在与上帝相一致时才是真实的。上帝的观点是正确的,这种最后的断言是因为他领会并知晓一切,但更是由于他对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有“所有权”:他是创造者并因此而决定着万物的真正本质及其目的。
这些论述策略显然是循环的,因此必须追问:有没有诉诸上帝之外的——也即不通过压倒一切变化观点的上帝之眼的视角——关于客体的系统性观念是真正清晰的?在我看来,举证责任在那些宣称,否则的话——如果有一线希望,这种证据不会诉诸那些有资质的体验者的共识,其资质只是由仅能以这种方式体验事物的循环指涉所认定的(“所有理性的/健全的/有能力的观察者都知道……”)。我们更期待一种证据,不将“说……是很奇怪的”视为一种论据——一种不会最终被归约为“我们所希望的就是我们所希望的”的证据。如果科学和宗教,或者某一声誉良好的团体(由那些的确说T的人所界定的)的所有成员都说T,但是我说Q,是什么——除了含蓄的强令正确(might-makes-right)的论证——胁迫我接受与我当下所见相异的事物状态?
然而请注意我所论述的庄子-天台宗的思路的要点:除非有上帝的确证,“上帝不存在”甚至也非事实。同样的说法当然也适用于“上帝存在”。如果没有上帝,两者就都不是真的。因此,庄子-天台宗就是唯一真正的无神论。真正的无神论不说“没有上帝是一个事实”。一个真正的像庄子那样的无神论者会说:“为何如此?这是什么?是万物的创造者——或是生化的过程——或是大块——或是阴和阳——或是道——或是天——或是浑沌——或者行动者或结局存在与否?我发现没有,我发现很多……”天台宗那样的真正的无神论者也许会说:“为何如此?这是什么?答案是:佛陀的慈悲伎俩——或不灭佛身的无处不在——或众生之业的相续——或反映了我之果报的事件——或作为鬼、阿修罗、神、蜣螂的在世活动,这个世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弥漫于并控制着所有可能事件,遍布着饿鬼道、阿修罗道、天道、畜生道……”这些说法并非不成问题(在其他地方,我曾试图予之以详尽的解释和辩护)。我仅希望,如果我们能在损弃确切知识——关于人类是什么、万物是什么以及人类的行为和欲望的本质——的陌生尝试面前后退一步,就会看到:对每一显现之事物的本然丰富多样性(muchness and suchness of whatever emerges)的必然流溢的致敬及迎合意图。
注 释:
①译者注:本文原题为“Onsortofknowing”,sort of的中文意思是有点、稍微、近似,sort of knowing的意思则是介于知与不知之间的一种似无而有、隐而不显的认知状态,因此本文采取了道家式的词汇,将之译为“玄知”。在后文中,也会随文而将sort of译为“隐微”或“略似”等语词。
②与当前讨论的问题的语境相关,大量改良性的英译出自我的Zhuangzi:TheEssentialWritingswithSelectionsfromTraditionalCom-mentaries, trans. Brokk Ziporyn (Indianapolis, IN: Hackett,2009), 39-40. 古代中国文献的英译的可变性更进一步说明了这里的论点。我们可以追问,“文本的本义是这样的吗?的确不是这样。的确不是这样。只不过略似意味着这样”。
③由于“专注”(志)在这里意义浅近,多数注家主张代之以“忘”,意思是“他丧忘了心智”。然而,正如方以智所论:“‘志’字的虚用是很奇特的。根本无从捉摸。唯有这种专志,所以他的面容才能安宁。”(译者注:方以智《药地炮庄》中的原文是“志字虚用,奇。谓不可得而窥测。唯有一志耳,其容寂。”)
④Zhuangzi:TheEssentialWritings, 40-42.
⑤Zhuangzi:TheEssentialWritings, 21.
⑥Zhuangzi:TheEssentialWritings, 84.
⑦Zhuangzi:TheEssentialWritings, 53.
⑧Zhuangzi:TheEssentialWritings, 53. 这种翻译试图在每句话中体现“无为”这一道家关键术语的双重意涵(“不做”,不假思索的行动)。
⑨Zhuangzi:TheEssentialWritings, 54.
⑩参见Richard Rorty,PhilosophyandtheMirrorofNature(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详尽阐释了欧洲传统中这个关于知识的隐喻及其使客观性模型成为可能的作用。这里展现出的是有趣的比较研究。
(译者:王玉彬,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讲师、博士)
【责任编辑:高建立】
2015-02-08
任博克(Brook A. Ziporyn),美国汉学家与哲学家,芝加哥大学神学院哲学与宗教系终身教授,主要从事道家思想、天台宗思想和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等。
B223
A
1672-3600(2015)05-002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