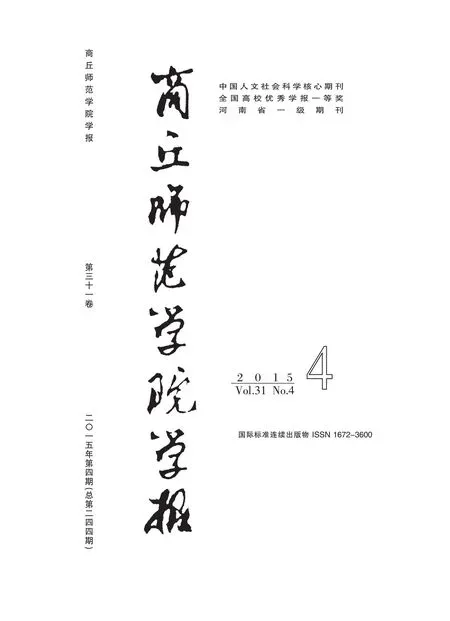试论法律援助实施的市场化运作
2015-04-11袁金华
袁 金 华
(商丘师范学院 经济法与法人类学研究所,河南 商丘476000)
试论法律援助实施的市场化运作
袁 金 华
(商丘师范学院 经济法与法人类学研究所,河南 商丘476000)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构建之始,即确立了由法律援助机构或法院指定法律援助工作者或律师的实施模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此种模式的弊端和不足日益凸显。法律援助服务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应该纳入市场化运作的范畴,政府可以通过向律师或社会组织 “购买”,以市场化的手段配置法律援助资源,从而更有效地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保障民生,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法律援助;市场化运作;经济合同
法律援助作为我国法律界的“希望工程”,经过近20年的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由于这一制度建设起步较晚,行政化的体制设计没有按预想发展,且受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尚不能满足社会贫弱群体的需求。面对我国法律援助实施模式的行政化弊端,如何创新机制以提供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是进行法律援助制度改革的关键,也是保障其良性长远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我国法律援助实施模式的现状及不足
(一)我国法律援助实施模式的现状
法律援助的实施模式即法律援助服务的提供方式,国外法律援助实施模式主要有私人律师模式、公职律师模式和混合模式(私人律师和公职律师混合提供法律援助)。有学者认为,我国法律援助的实施模式是“在形式上借鉴国外法律援助的‘混合模式’,选择既能体现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又最经济有效的专职法律援助律师与社会律师相结合的‘特殊混合模式’”[1]226。
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关于法律援助实施模式的规定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律援助条例》第21条规定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指派律师事务所安排律师或者安排本机构的工作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也可以根据其他社会组织的要求,安排其所属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二是《刑事诉讼法》第34条确立的“指定辩护人”制度,即由法院为特定被告人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担任辩护人。三是《法律援助条例》第8条规定的:“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同时,《律师法》第42条也明确规定了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是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义务。因此,有学者指出,“我国法律援助服务模式的多元化特征已十分明显”[2]71。
笔者以宁波市为例,在调研中发现,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法律援助的咨询、申请、审查、案件承办过程的监督以及结案后的归档等工作,几乎不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法院需要为特定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的,需要向法律援助中心发函,再由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社会律师来承办案件。社会组织比如妇联、残联等多是对非诉案件进行调解,其内设的法律援助工作站,只是代为受理法律援助申请,仍需要转交给法律援助中心审查以指派社会律师承办案件。结合其他省市法律援助模式的现有资料和以上分析可知,我国法律援助的实施模式在理论上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实践中则主要是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社会律师或本机构工作人员承办案件的模式。
(二)我国法律援助实施模式的不足
实践表明,在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初期,政府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法律援助实施模式中的“指派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当时国情。然而,随着国际法律援助理念的革新和我国民主法治建设进程的加快,法律援助现行模式已不再是制度的最优选择。
1.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能完全保证。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法律援助案件,经费只是部分办案补贴。尽管大多数律师基于职业道德和法律义务对法律援助案件勤勉尽责,但其作为市场主体,“行政指派”无疑会导致律师及机构工作人员积极性不高,甚至出现不调查取证、不会见被告人等现象。同时,法律援助机构的行政化思维导致有些地方的质量监控措施形同虚设,“对于政府而言,它热衷于设立法律援助机构,却并不是积极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更热衷于法律援助服务有与无,而不是需要多少,提供的办案质量多高”[3]。
2.法律援助服务资源不能有效利用。法律援助服务经费在我国本身并不充裕,地方财政划拨方面也存在一系列官僚作风问题。在实践中,多数社会公众不信任法律援助,许多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者比较清闲,法律援助服务资源并没得到有效利用。法律援助实质上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对法律服务资源进行分配,以保障贫弱残疾者不因经济能力、生理缺陷所限而平等地获得法律帮助的制度[4]31。而我国法律援助的实施模式在法律服务资源的再分配中相对来说是缺乏效率的,资源的浪费比制度的虚置更为可怕。
3.法律援助服务的提供忽视了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法律援助服务的供需失衡,除了我国法律援助资金紧张、偏远贫困地区法律援助人员缺乏等原因之外,正如有学者所言,“我国现有的相关制度设计和运作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恰恰就是对市场力量认识得不够充分”[5]。基于政府设立法律援助机构的行政性质和管理权限,一是其行政管理制度与市场难以接洽,二是社会组织既没有决定和指派的权力,又没有法律援助服务资源,不得不将责任再推给了政府。法律援助作为一项社会公共服务工程,应当需要更多的市场和社会力量投入才能满足贫弱者权益保护的需求和实现法律援助的社会化发展。
二、法律援助实施市场化运作模式的基础分析
(一)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
西方国家的法律援助发展经历了由个人慈善行为到国家责任阶段,进而成为福利国家社会体系的一部分。其起源于15世纪的英格兰,最初是个人道义和慈善行为。资产阶级革命后,受保障公民诉讼权利的理论影响,国家责任随之产生。二战以后,随着社会本位思想的发展,法律援助不仅被视为一种权利,而且被视为国家福利的组成部分[6]。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说明了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是国家的义务,享受法律援助也是符合条件的社会贫弱者的法定权利。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社会的文明程度和法治国家的完善,我国2003年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
(二)法律援助实施过程中的主体关系
在我国,法律援助实施的过程中牵涉到三方主体,分别是政府、受援人和法律援助服务的提供者(即法律援助工作者、律师或者社会组织)。其实质与如今多数公共服务领域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相契合①。三者关系可以看做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阶段。一是政府向符合条件的受援人提供法律援助阶段。法律援助服务在此是一个公共资源。所谓公共资源是指在使用上没有排他性,但在消费中有竞争性,一个人使用了公共资源就减少了其他人对它的享用。在这个阶段,法律援助服务本身没有排他性,即是由政府来提供,社会大众中符合条件者都可以免费来使用。二是政府出资获得法律援助工作者或者社会律师的法律服务阶段。政府提供法律援助是责任,但其本身并不擅于技术性较强的法律服务提供,实践操作中是通过出资获得法律援助工作者或者社会律师的法律服务,再由该第三方主体提供给受援人。假设有一个案件需要援助,那么也就只需要一个法律援助者或者律师来承办,此时法律服务作为提供者的“私有物品”就具有了竞争性,也具备了形成市场的基本条件。
(三)法律援助实施市场化运作模式的提出
由以上分析可知,现代法律援助以国家责任为基础,为法律援助提供经费支持是政府的义务,而法律援助服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都是私人主体。既然法律援助服务本质上具备商品的属性,那么在第二阶段就可以形成一个买方市场,即政府出资“购买”法律援助服务。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最佳方式,法律援助的提供者之间自然会产生竞争,竞争带来的是兼具较低价格与优质服务的胜出者,再由政府与胜出者签订法律援助服务协议,最后将法律援助服务提供给受援者,如此即是法律援助实施的市场化运作。
三、法律援助实施市场化运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法律服务商品属性的利益动机
有学者指出,“按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理论来构建法律援助制度必然缺乏法律援助内在的激励机制”[7]。我国现行的由政府“指派”和“定价”的法律援助实施模式限制了法律服务作为商品的利益动机。即使法律援助是以司法行政部门新设法律援助机构来管理和执行,依然不能改变其行政化属性。法律服务既然是商品,就应当由市场来定价和配置。政府的购买和市场的定价,无疑会激起提供者的利益动机。从法律援助未来发展趋势来讲,最大限度社会化是其必然出路,其中制度设计的市场化是一个重要的改革方向。将法律援助实施进行市场化运作,既可以优化法律援助资源的配置,又可以克服法律援助行政化的影响;既可以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提供者的积极性,又可以缓和法律援助与经费不足的矛盾。
(二)国外法律援助实施的实践经验
英国的法律援助近几年在危机中不断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以市场化为基础的法律援助运作方式。例如,英国在2007年引入了民事统一合同制度,规定提供民事法律援助服务需要通过招投标活动与法律服务委员会订立合同。时隔一年,又在刑事法律援助服务领域引入了刑事统一合同制度。与此同时,“法律服务委员会将进一步构建法律援助服务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法律援助服务工作中的自我约束、激励和淘汰作用”[8]。美国的法律援助提供模式包括专职律师模式、合同律师模式和私人律师模式。合同辩护律师项目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固定价格合同,另一种是个案定价合同。从国外的实践经验可以看出,政府引入合同制购买法律援助服务,由律师事务所通过竞标的形式和法律援助中心签订协议,并通过规定签约律师条件和法律援助中心监督其办案质量,提高了法律援助的质量和效率。
(三)我国法律援助实施市场化运作的社会背景
首先,在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不断推进的当下,通过法律援助保障社会贫弱者尽可能通过公正法律程序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具有深远意义,其不仅是保障弱势群诉权的实现,更是保障基本人权的制度体现。其次,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在我国的试点和发展,已逐渐凸显出其市场效益优势。2015年1月4日由财政部、民政部、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对外公布了《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并于2015年1月1日起施行[9]。如此,将政府购买服务进一步纳入法律规范领域,对于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我国社会管理改革创新具有重要作用。再次,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确立较晚,先天不足需要后天补足,各地法律援助机构在鼓励和促进法律援助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并不断探索在现有资源下的机制创新。最后,国家在“十一五”规划中将法律援助列入规范和发展商业服务业条目之中,其意图明显地是欲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改革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扩大购买服务,实现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的多元化[10]。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社会改革创新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加大政府购买服务。
四、法律援助实施的市场化运作设计
(一)法律援助市场化运作的经济法律关系定位
法律援助的市场化运作隶属于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其自身制度特点与经济法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之间具有天然的契合度。法律援助的市场化运作,实质即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由法律服务者提供给受援人。其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即是政府、法律服务提供者和受援人。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政府与法律服务提供者之间具有基于“经济合同”②的权(力)利义务关系,具体包括政府对法律服务提供者作为管理主体的经济职权和职责。相应地,法律服务提供者对政府具有谈判协商抗辩的权利,并有对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义务。二是受援人具有对法律服务提供者的服务质量进行监督的权利。三是受援者有对政府行政权力的监督权和法律服务的反馈救济权。
(二)法律援助机构作为公共管理机构的性质和职能转变
政府是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实现法律援助服务提供的市场化运作,既需要政府参与,也须纠正目前政府行政化过多的倾向。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应脱离政府职能部门,改革其行政机构属性,使其作为相对独立的第三方事业单位,参照英国法律援助委员会属于非政府部门的公共管理机构的设置,依法行使政府对法律援助的经济职权,负责对法律援助服务市场化运作的各环节进行基本的管理和质量监督。对符合条件的法律援助者进行资格审查,确定其法律受援权,负责援助过程中发生的撤销援助、办案过程中的监督以及结案后案件的审查和归档等工作,同时负责办理非诉讼类法律援助案件和日常的法律援助咨询等。
(三)实行竞标方式和定量分配签订经济合同
借鉴国外法律援助市场化的模式,仿效我国政府采购制度,依据我国《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招投标法》等,使法律援助的市场化运作以竞争性招标的方式与律师事务所或法律社团组织签订经济合同的模式来进行。首先,由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地域差别对本地的法律援助案件进行统计,估算近年来平均每年的案件数量和经费数额,估算社会律师基本可以接受的一年内案件的总价格。其次,以年为单位进行定量分配,将未来一年的不特定案件“打包”和标价,公开面向当地社会律师以竞争性招标的方式选择律师事务所或法律社团组织。另外,各地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将不特定案件划分为刑事、民事和行政类别分别进行“打包”等灵活的方式招标。最后,法律援助机构通过审查竞标胜出者的资格和条件,确保法律援助案件的承办质量,再与其签经济合同。经济合同的内容包括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标准和签约律师的权利义务等。“对于资金供应者来说,合同方式最主要的吸引力在于能够通过限定合同总额来准确计划来年的花费。”[11]32以市场来配置资源,采用竞标程序和固定价格可使签约律师积极追求诉讼费用的最小化,降低法律援助的总费用。
(四)法律援助机构的监督和质量控制
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是法律援助事业的生命。各个国家在质量控制方面采取了多种措施。其中,英国法律援助服务的契约化模式改革,虽然精简了法律援助的律师,但“其目的主要在于保证服务质量,而非通过市场竞争来压低价格”[12]70。与此相较,美国的法律援助在刑事辩护领域进行了契约化改革却造成了服务质量的下降。在欧洲国家,PPI模式(即市场化运作模式)有益于法律援助同时,也产生了诸如市场上公平的竞争环境、合同签订过程的合规性、PPI相关法律问题等③。因此,我国实行法律援助的市场化运作仍需要完备的质量监控措施。首先,制定《法律援助法》,并在其中明确规定法律援助市场化运作的主体、正当程序、法律服务标准、质量监控机制等,使其纳入法律规制。其次,法律援助机构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审查和评估竞标者的资格,保证合格者才能签订协议并保证合同签订程序公正合法。再次,在法律援助案件承办过程中,法律援助机构应采取分派监督员、定期听取报告以及错案纠正等措施来充分发挥其监督职能。最后,在协议期满后,对签约律所和律师进行整体评估,以决定是否续约和将个人律师评估纳入律师年度考核等方法来保证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
(五)我国法律援助实施市场化运作的制度配合
美国法律援助服务公司曾作过一个研究,结论是“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最好的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模式”④。澳大利亚的全国法律援助委员会在1989年审查并回顾了法律援助的现状后,致力于鼓励广泛的法律援助方式,包括社区援助、社会福利、政府资助的私人组织、法官、社会组织等[13]。可见,法律援助提供模式多元化是大势所趋。同时,由于我国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从我国法律援助的需求状况、资源状况和经费等方面考察,单一进行法律援助的市场化运作不可行也不符合我国实际国情。因此,我国法律援助的实施模式应当以市场化运作为主,以多元化提供方式为辅,包括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咨询等非诉讼法律援助、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以自身资源提供法律援助等。法律援助机构应将这些多元化方式共同纳入管理和监督体制以便发挥各自的作用且相互配合。
五、结语
政府在法律援助制度建立之初的推动作用符合法律援助的发展规律。目前,在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探讨法律援助实施的市场化运作,既是国际法律援助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良性高效发展的最佳路径。基于国情的特殊性,利用市场配置法律援助资源,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改革的新尝试,需要进一步理顺法律援助机构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完善内在制度和各方面的有效配合。若要达到理想的法律援助实施市场化运作的目标,仍需要大胆的试点、不断的探索和长期的努力。
注 释:
①政府购买服务(Purchase of Service Contracting,POSC)一般是指:“政府将原来由自己直接举办的、为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服务的事项,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交由社会组织或市场来承接,是一种‘政府承担、定项委托、合同管理、评估兑现’的新型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参见赵立波《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 推进民间组织发展》,载于《行政论坛》2009年第2期。
②经济合同(也称政府商事合同)是指合同一方是政府机构或执行政府政策的机构,缔约双方均对政府负责,直接体现政府意志或其他公共利益要求,为了实现政府的经济政策或目的而订立的合同。参见史际春,邓峰《经济(政府商事)合同研究——以政府采购合同为中心》,载于《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0年第4-6期。
③PPI is differ from classic arrangements between a buyer and a supplier where the public buyer pays a private undertaking to provide a public service.参见Inden, Tobias; Olesen, Karsten Naundrup.Legal Aspects of Public Private Innovation, European Procurement &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Law Review,Vol.2012, Issue 4 (2012), pp.258-267.
④参见Jeremy Cooper.《提供模式研究:给美国国会和总统的政策报告》.转引自[加]苏珊.查伦多夫等《法律援助的提供模式 各国法律援助理论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428页。
[1]宫晓冰.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
[2]张中.弱势群体的法律救助——法律援助服务及其质量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
[3]沈满云.法律援助办案质量控制制度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2008.
[4]张耕.中国法律援助制度诞生的前前后后[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
[5]曹明睿.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4.
[6]彭锡华.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从国际人权法的视角考察[J].法学评论,2006(3).
[7]李海明.法律援助制度的重构——[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7.
[8]朱 昆.英国法律援助制度概述[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0(4).
[9]财政部.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 [EB/OL].http://www.gov.cn/xinwen/2015-01/04/content_2799671.htm,2015-01-04.
[10]沈丽飞.以人为本视野下的中国法律援助运作模式[J].学习与探索,2009(6).
[11]Erhard Blankenburg.德国法律援助制度简介[M]//宫晓冰,杨勇.外国法律援助制度简介.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
[12]马栩生.当代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3]Fleming, Don.Rethinking Legal Aid Policy [J].Legal Service Bulletin, Vol.14, Issue 1 February 1989.
【责任编辑:李维乐】
2015-01-23
袁金华(1985—),女,河南周口人,硕士,主要从事经济法学研究。
D912.19
A
1672-3600(2015)04-01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