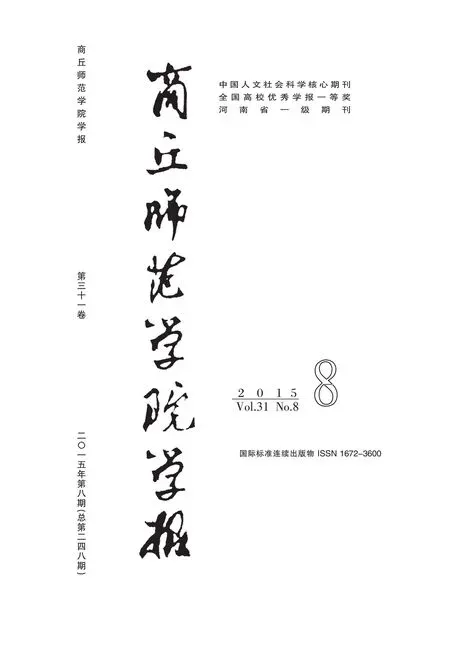当代社会认识论研究路径寻赜
2015-04-11姜文华
姜 文 华
(渤海大学 政治与历史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当代社会认识论研究路径寻赜
姜 文 华
(渤海大学 政治与历史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21世纪将是一个多元体系并存并行的世纪,社会认识论将对社会进步和发展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回顾30多年来社会认识论研究发展的概况,在此基础上指出社会认识论研究存在的缺陷,并对当代社会认识论研究之路径作出展望,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认识论;社会认识论;研究范式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影响当代社会认识论研究的一些外在因素,如21世纪作为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趋向以及一系列要求我们回答和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已经基本显现出来。毫无疑问,随着生活世界崭新的外在因素的基本显现,作为分支学科的社会认识论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这也使得我们寻赜当代社会认识论研究的路径具备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当然,我们也不易作出准确的把握,毕竟影响社会认识论研究的一些外在因素还没有完全显现。正因为如此,在当代社会认识论研究的过程中,要求学界在积极回应21世纪的时代语境的同时,更应积极创新适应当代社会认识论研究的新路径,这也是我们肩负的重要的时代使命。基于此,本文尝试对当代的社会认识论研究路径作出前瞻性描述。不当之处,敬请赐教。
一、30多年来社会认识论研究之概况回顾
按照欧阳康的观点,社会认识论就是关于人们怎样认识社会的学说。它以人们认识社会的认识活动为对象,考察人们认识社会的特殊活动结构、活动方式、活动方法、进化过程和特殊规律,揭示社会认识“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1]。我国的社会认识论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按照其研究的内容和研究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一)发端期: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到90年代初
这一时期,我国学者从基础层面对社会认识论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逐渐构建起自己的研究框架。如李剑锋、李庆的《应当开展社会认识论的研究》(1986.3),欧阳康的《社会认识论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1988.6)、《社会认识论刍议》(1988.4)、《理想社会的探索与建构——社会规划活动的认识论分析》(1989.5)和《关于社会认识论的对话》(1992.4、5),李明华的《认识论研究的新领域》(1992.3),安维复的《认识论的转换: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1992.5)以及王世达的《观念运动与观念建构——社会认识论的核心与理论生长点》(1993.1)等论文,为进一步探究社会认识论作了较为充分的理论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1989年4月,首届全国“社会认识论”学术研讨会在四川省乐山市举行,此次会议对我国社会认识论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第二年,景天魁、陶远华、欧阳康的“社会认识论”三书陆续出版,可以视为“我国社会认识论研究领域的发轫和奠基之作”。他们“从一开始就切近了社会认识论的深层内容,且具有深刻的理论力度”[2],使我们对社会认识论有了一个整体性的理解和把握,我国的社会认识论研究才有了基础并发展起来。
(二)推广期: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
这一时期,学者们在以往学识积累的基础上不断探索,虽然参与研究的学者不多,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均有所增进。主要表现在:一是关于研究方法的论述比较多,力求深化社会认识论研究。如景天魁的《社会认识论三难题》(1994.10),叶泽雄的《探寻深化社会认识论的研究思路》(1996.11),郑文先的《社会解释论纲——深化社会认识论研究的一个构想》(1997.3),欧阳康的《社会认识的发现模式论纲》(1994.2)和郑文先、叶泽雄的《社会认识方法论的合理思路》(1996.1)等论文;二是契合社会意识形态的需要,以哲学视角诠释社会认识论。如欧阳康的《面向21世纪人类文明的社会认识论》(2001.4)和《当代哲学视野中的社会认识论》(2001.5),曹昭的《社会认识论研究对象的辩证思考》(2004.3)等期刊论文以及毛卫平的博士论文《社会认识论引论》(1998);三是研究视野逐渐开阔,开始了对西方社会认识论研究的推介。如汤津红的《以社会认识论看图书馆和图书馆学》(1993.3),王秀山的《谢拉图书馆学思想的认识论问题》(1994.2),罗志勇的《论谢拉的思想体系及其价值》(1994.3)及张建华的《近年来西方社会认识论研究概况》(2001.4)等论文。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较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主要有李勇的《社会认识进化论》(2000),欧阳康的《社会认识论》(2002)以及由其主编的《社会认识方法论》(1998)等,这些著作、论文的出版和发表,有力地推进了我国社会认识论的研究。
(三)拓展期:最近十年来
这一时期,国内的研究群体不断增多,研究内容也渐次深入,逐渐形成了以华中科技大学欧阳康为代表和以山西大学殷杰、尤洋为代表的两个研究团队,取得的成果也迅速增多,他们将国内的社会认识论研究推进了一大步。此间,一些学者继续深入基础理论研究,如欧阳康、吴兰丽的《面向当代人类实践和社会问题》(2008.1),张登巧的《价值论视野中的社会认识论研究》(2009.2),殷杰、尤洋的《社会认识论视域中的信息与知识》(2009.2)、《社会认识论的理论定位、研究路径和主要问题》(2009.4)和《社会认识论的研究定位、涵义与划界标准》(上)(2010.6)、(下)(2011.3),郑祥福的《社会化认识论的问题及其发展策略》(2010.11),谷生然的《社会认识论在当代的价值追求》(2011.5)等论文;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以往研究的偏颇,开始关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问题,思考如何合理利用社会认识论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在这方面,殷杰、尤洋的《社会认识论视野中的认知偏见》(2007.4),王知津等的《当代情报学理论研究中的社会认识论思潮》(2012.6),欧阳康的《深入探索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之谜——社会认识论的回顾与前瞻》(2012.8),尤洋的《社会认识论视域下的陈词问题》(2013.6),丁五启的《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的认知基础——耶希·霍克·沙拉的社会认识论构想》(2006.5),江雅薇的《从谢拉的社会认识论谈中国高校图书馆馆员的知识结构》(2005.2)等论文均以创新视角为着眼点,积极开拓论域。此外,还有一部分学者更加深入地介绍西方学者的观点,如潘斌的《当代西方社会认识论研究的拓展与深化》(2008.1)和《论戈德曼社会认识论的求真性价值》(2011.1),殷杰、尤洋的《科学知识合法化的新解释——社会认识论的视野》(2006.4)和《当代社会认识论研究及其意义》(2008.4),谷秀洁的《图书馆与社会:对谢拉“社会认识论”的学与思》(2007.2),周鹏的《当代情报学理论研究中的社会认识论思潮》(2012.12),丁参的《从社会认识论视角看科学文化与主体性分离问题》(2009.6)等期刊论文以及丁五启的博士论文《当代西方社会认识论研究》(2007)等。另外,2012年6月,第一届“社会认识论与马克思主义新视域学术论坛”在武汉成功举办,会议围绕“社会认识论与马克思主义新视域”的主题展开探讨和交流。这次会议开阔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对进一步深化社会认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总体而言,以上这些论文和著作对社会认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将社会认识论研究提高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我国社会认识论的突出特点,是在20世纪80年代全面启动之初,即确立了自己的研究向度和研究纲领,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既立足于认识论研究的现代发展,又能掌握和运用科学方法论的基本理论。我们尚需进一步探明:在当代,社会认识论的研究方式、方法需要哪些创新?社会认识论研究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这些问题会对当代的社会认识论研究产生哪些影响?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根据各种现实情况和条件作出合乎逻辑的预测。
二、30多年来社会认识论研究存在的缺陷
我国社会认识论研究经历了30多年的探索和积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是毋庸置疑的。当然,从社会认识论研究的概况回顾来看,我国社会认识论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理论困境明显。人们的实践活动,特别是社会实践活动离不开理论指导,这也是30多年来社会认识论研究之所以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自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的生存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身处的世界更加开放,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各国的经济、政治往来越来越密切和频繁,所有这些迫切需要崭新的理论来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就我国而言,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发展中的诸多困惑,诸如公平、正义等失衡问题日益剧增,而这些现实情况都需要社会认识论作出导向性的回应。然而,由于整个研究群体对社会认识论层累知识的不足,抑或仅仅是套用已有的哲学理论范式,而导致我们的社会认识论研究逐渐走向机械化、模式化,理论创新方面尤显不足。
其次,与现实结合得不够紧密。从事社会认识论研究必须坚持一定的原则,既要尊重客观事实,又要服务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而不是抛弃现实性的形式主义而一味地形而上。应该说,国内学者付出大量精力对社会认识论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这些研究中存在着的机械化、模式化倾向,使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理论“移植”,而这种“移植”还仅仅处于理论处理阶段,与现实社会联系得并不紧密。因此,我们认为,社会认识论研究必须结合当前的社会问题,而要想使社会认识论研究与现实紧密结合,我们就必须以创新精神来融理论于实践之中,走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唯有如此,社会认识论的理论成果才能为我所用。
此外,30多年来的社会认识论探索依然浮于表面、深度不够。自社会认识论诞生以来,经过学者们30多年的不懈努力,社会认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令人瞩目的。但是,作为一种崭新的理论,国内学者的研究也还存在着诸如浮于表面、深度不够等突出问题。当然,随着研究群体的不断扩大以及研究视角的不断拓展,这些问题都将逐一解决。
三、当代社会认识论研究之路径展望
实践证明,任何一种理论成果在合理性方面都不是完全超越的。严格来讲,一切理论成果都不具有完备性,这就需要我们在新的语境下对旧有的理论或研究成果进行创新性的修正乃至重建,以适应新语境的要求,社会认识论也不例外。我们认为,当代的社会认识论研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其一,顺应时代发展之需要。任何理论的落脚点都在于其关注和解决现实问题,而要解决现实问题,必须在构建和创新理论的同时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同时,顺应时代发展也是体现社会认识论价值性的内在要求。就我国而言,目前我们面临的是建成小康社会和应对21世纪发展等多重任务,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理性化的理论体系来确立当代哲学之形态以应对复杂的社会现实,这也是当代社会认识论研究之路径选取的落脚点或基本要求。同时,更需将当代社会认识论研究落脚于构建和谐世界这一现实需求,努力找寻通达地球村的新方法、新路径。换句话说,当代社会认识论研究工作亦需多聚焦一些世界范围的共同关心的话题,应该体现一种全人类的关怀。
其二,综合创新多元化的研究范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认识论研究之所以成为具备了科学属性的新的学科分支,与学者们积极扩展研究范式密切相关。可以确定的是,作为认识论重要分支之一的社会认识论,其理论创新与方法论构建必然依赖于众多学科领域的知识,这无疑为社会认识论的理论构架预留了拓展平台。不言而喻,社会认识论的研究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的积极参与,需要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知识的合理兼容、共同参与。面对21世纪的全球一体化的社会现实,社会文化多元展开的当代新趋向日益明显,随之而来的是各学科、各领域的研究亦趋向精细化,社会认识论研究不可能孤立之外而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兴起与繁荣毫不相干。也就是说,社会认识论研究也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式。同时,由于社会认识论的研究路径还不十分清楚或不够具体,因而,当代社会认识论研究更需进行多元化研究范式的综合与创新,并为之进行各种探索性的研究尝试。
其三,多维度、多视角扩繁研究层面。社会认识论研究发展到今天,其呈现出鲜明特色的时代特征。它不但丰富了认识论发展的支系,同时也对其他学科如社会学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不同时代的哲学家,都是根据他们所处时代之精神即社会语境,而对其所从事的研究课题展开学术研究的,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学术研究的时代性。正如马克思所言:“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220随着21世纪崭新的社会语境的出现,社会认识论研究理所当然要“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这首先需要学者们多维度、多视角扩展研究层面以契合社会语境;其次,社会认识论的研究重心要从一般方法论层面转向具体的技术层面。这里,笔者要强调的是,针对已经发生变化的社会语境,展望当代社会认识论研究之路径必须要有强烈的现实感。这种现实感必将体现多维度、多视角的研究态势,进而适应于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一句话,当代的社会认识论研究必须将人类的现实生活世界作为关注的焦点。
四、当代社会认识论研究应注意的两个问题
在30多年来社会认识论研究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当代社会认识论研究要想在深度和广度上取得更大的发展,我们认为还应该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研究路径的选择和创新要坚持开放性原则。所谓坚持开放性,就是指研究者在学术研究中要与外界产生某种联系或交流,不可闭关自守,而是要积极接触、主动往来。目前,制约我国社会认识论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依然是本土科学理论的缺失。在西方哲学侵袭之下,国内的社会认识论研究不可能作为单纯受动的客体而独立存在,而是应该积极参入,体现其能动性的一面。因此,如何实现西方科学理论的“东进”是急需解决的课题。同时,要积极探索社会认识论研究世界性课题,重视中、西会通,积极争取与其他先进文化学习与交流的机会。由于中西学者社会认识论研究的侧重点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国内外学者的学术合作与交流,在“向内看”(合理整合国内本学科的研究资源)的同时,也不要忽略“向外看”(积极借鉴国外优秀的研究成果),以有效推进社会认识论的研究工作。
其次,加强学术队伍建设,理论与实践并举并重。第一,学术队伍建设是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前提和重要基础,脱离学术群体而进行的社会认识论研究,其最终结果只能是闭门造车。我们认为,不管选用哪一种路径展开社会认识论研究,都应该始终以学术队伍建设为基础,并借助新的学科划分理念和新的知识体系、新的学术视野,宏观地审视和剖析社会认识论论域,而不是以研究者个体为中心,忽视群体的重要作用。第二,社会认识论研究30多年来,学者们在学科界定、基本概念、基本问题以及体系构建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已经基本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使其成为认识论研究领域的重要的学科分支。下一步的社会认识论研究应将在服务社会实践方面发挥其作用,以便为我们更加科学、全面地认识社会提供方法论指导,实现“理论世界”与“事实世界”的良性互动。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理论研究和创新,二者应并举并重,共同促进和实现信息的交流与知识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的社会认识论研究理应在更高的层面上拓展论域,把社会认识论的理论体系与社会现实相结合,从而实现对于社会认识论的更深入的理解和阐发,并做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弥合,不断赋予当代社会认识论研究鲜明的实践特色。
总之,21世纪将是一个多元体系并存并行的世纪,社会认识论将对社会进步和发展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面对人类多元文化的发展趋势,随着世界范围内广大学者对社会认识论的广泛关注,当代社会认识论研究必将进一步走向成熟。
[1]欧阳康.社会认识论刍议[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4).
[2]李明华.认识论研究的新领域[J].哲学研究,1992(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李安胜】
2015-03-2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逻辑视域的认识研究”(编号:11AZD056);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基金项目“钱学森之问与我国当代科学精神的迷失和重塑”(编号:nkzxyy1109)。
姜文华(1974—),男,山东莱阳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人文学科方法论研究。
B023
A
1672-3600(2015)08-005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