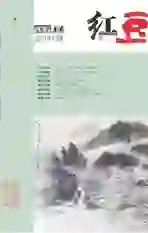怀曾敏之先生
2015-04-10潘琦
潘琦,1944年生,仫佬族,广西罗城人,毕业于中南民族学院,中国文联第九届全委会委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研究员。历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常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联主席。现任广西桂学研究会会长。
著有散文集《山泉淙淙》《琴心集》等十八部,小说集《不凋谢的一品红》,诗歌集《山乡晨曲》,歌词集《心泉集》,理论专著《大潮中的思考》《红土地上的探索》,并有书法作品集《墨海探笔》等二十余部。有《潘琦文集》(九卷),《笔耕集》(四卷),《潘琦文集》(十八卷)。
那是六年前,曾敏之先生应邀参加在南宁举行的“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当时他已92岁高龄,行动不太方便。我们几位老乡在金茶花公园边上的餐馆请他吃饭。老人身体还挺好的,思维依然敏捷,很健谈,席间他讲了许多自己的经历和对家乡未来发展的期望。我说陪他回罗城看看。他说,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未等会议结束,他便返回广州。之后,我几次要去广州看望他,都因抽不开身,没有去成。谁知那次见面竟然是最后一面。
今年元旦过后,我从微博上得知敏之先生去世的消息,当时一下子就懵了。上个月,我和《海外星云》的朋友聚会,大家都说他身体好好的。他们还约我一块去广州看望他老人家,顺便为《海外星云》创刊30周年作个专访。怎么突然就走了?我默默地坐在书房里,一幕幕的往事呈现在我的眼前,我眼眶湿润了。
敏之先生是罗城县黄金镇人,我们是老乡,他是我的长辈。我读初中时,就从老师那里听到了敏之先生的故事,读过他的作品。当时为家乡出了这样的文化名人,感到很骄傲,从心底里敬佩,把他作为榜样,希望有一天他回罗城能见到他一面,但二十多年过去了都没有这个机会。20世纪80年代初,我到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工作。有一次随自治区覃应机主席出访,经香港停留。敏之先生当时任香港《文汇报》代总编,知道我们到香港,特意到宾馆看望覃主席,我才第一次见到这位慕名已久的老乡。
那天上午,应机主席叫我在饭店大堂等候敏之先生。以前看过他的照片,还算面熟。十点钟,一位西装革覆,中等个子,头发花白、文气十足的老人从一辆黑色小轿车出来,我一看便认定他就是敏之先生。“曾老,我是覃主席秘书,来迎接你!”我忙上前扶着他说。“啊!你是潘琦!我们是小老乡!”敏之先生笑着说。“是啊!我小时候就听说你了!”“嗨,人怕出名,猪怕壮啊!”“罗城人为你而骄傲!”……我们说着话,进到覃主席的房间。两位老人是熟人、老朋友,寒暄了几句之后,便谈起广西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问题。当时广西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干部群众思想不够解放,改革开放意识不强,经济发展步履维艰。敏之先生凭着自己掌握的国内外大量信息,对广西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议。应机主席频频点头,有的意见后来区党委都采纳了。那次谈话,我对敏之先生的印象特好,果然名不虚传,他博学多才,才思敏捷,思想深邃,善于言谈,很有学者的风度、风范和风格。在他身上彰显出一种无可言状的魅力,这魅力有一种使人开颜、悦心和迷人的神秘力量,让人愿意同他交往、交谈。听了两位老人的交谈,我受益匪浅。
到80年代中期,广西自治区党委为提高领导干部的开放意识和市场经济知识,分期分批在香港举办厅级领导干部培训班。我是第三期培训班学员。第一次去香港感到什么都很新鲜。敏之先生每期都来给大家讲课。那天,他上完课,我上前去和他握手说:“曾老,来香港前,很多罗城老乡都托我向你问好!”“谢谢大家!有时间我一定回罗城看看!”我们简单地聊了几句。未了,敏之先生很热情地说,你第一次来香港,今晚请你吃餐便饭吧!我说不用了,培训班伙食挺好的。他笑着说,乡里乡亲的别见外啊,让我尽一下地主之谊吧!盛情难却,我答应了。他说,你人生地不熟,邀桂江公司老总一块去,带个路吧!
晚上六点半钟我们准时到达约定的饭店,敏之先生夫妇已在那里等候。我们四个人就在大堂一个小方桌边坐下。曾太太很快点好了菜,点的都是家常菜,但很有味道。酒是敏之先生珍藏十几年的正宗茅台。那天晚上敏之先生非常高兴,我们三人酒兴大发,竟很快把一瓶酒喝得精光。席间我们谈得很多,天南地北,因酒精的作用讲了一些什么,我现在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培训班期间,我和敏之先生还见了几次面。从打那以后,我们常有书信来往。
敏之先生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他怀念着家乡的山山水水。那年我在南宁地委工作,特地邀请他回广西看看走走,他很乐意地答应了。记得是1993年4月,我陪他乘车到北海考察。一路上我们说到一些旧事,也谈到抗日战争期间他当《大公报》战地记者的故事。当时他撰写编发了大量的军事、政治和社会性的报道,其中不乏轰动一时的重大消息和独家新闻。他以文学的笔法采写的一批特写、专访和长篇报道,有的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而成为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范本。
他还详细地讲述了当年采访周恩来的情况。敏之先生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府迁回南京,怎么样和平建设这个国家,国共两党产生了矛盾。因此,通过谈判,共产党派驻国统区的代表团长是周恩来,住在重庆。当时开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商讨共同建国纲领,他参加采访。当时就萌发了一个采访周恩来的念头。后来周恩来的秘书通知他,说周恩来很乐意接受采访。前后安排了两个晚上。
当年周恩来50岁,采访时他穿了一套新的、蓝色中山装,胡子刮得很干净。采访一开始敏之先生就请他谈形势,谈他的经历,谈今后中国的动向。周恩来的讲话逻辑性、条理性很强,记录下来就是一篇文章。当年没有录音机,只靠记录。当时敏之先生还年轻,记忆力特别强。谈话结束后,敏之先生很快写成了一个专访《谈判生涯老了周恩来》,这是中国第一个新闻记者以大量翔实的材料,述评了贯穿抗战前后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真相与经验,并以文字媒介向世人首次披露作为伟大政治家的周恩来的革命生涯和哲人风范,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轰动。讲到这里,我察觉到敏之先生脸上露出一丝丝自豪和宽慰。但很快老人的脸又沉了下来。他接着说,这样一来,国民党的特务把他列上了黑名单。1947年5月31日进行大逮捕,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后来通过营救才释放出来。未了,他感慨地说,平生经历许多坎坷、很多挫折,能够活到今天很不简单,因此要倍加珍惜今天的生活与工作,多为社会、为民众做些好事、实事、有意义的事啊!
讲着讲着,他给我讲述了抗战时自己在桂林一段非常唯美动人的爱情故事。那是1942年在桂林举办西南抗日剧展,通过一次采访,他认识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女演员,之后他们经历了战争年代分分离离、思思念念的恋爱历程,最后因为战争有情人未成眷属。这是他的初恋,终生难忘。后来我把他们的恋情写成散文,在《南国早报》发表。很多乡亲和朋友看了散文,都建议我改编成电影剧本,因当年工作忙,一直没写成。2005年,我退下之后,便以他为原型,经过改编创作成电影剧本。2012年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心中的天堂》。此事我曾对敏之先生提起,他很高兴。我答应影片放映之后,送一张光碟给他看。可是没来得及,他便走了。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我深感内疚!
我对敏之先生的身世和经历有过一些片断的了解。他祖籍广东梅县,生于罗城,15岁出任小学校长,16岁赴广州半工半读,并开始文学创作。1940年开始报人生涯。先后任《桂林文艺》杂志助理编辑,《柳州日报》副刊编辑、采访部主任,桂林《大公报》特派记者、文教记者,重庆《大公报》记者、采访部主任,广州《大公报》特派员,香港《大公报》华南版主编、评论员。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任《大公报》、《文汇报》、中国新闻社广州联合办事处主任,1961年初调任暨南大学副教授,任写作及中国现代文学两教研室主任。1978年再赴香港,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代总编辑,文汇出版社总编、评委会主任,香港作家联合会会长。1985年,他回广西创办了《海外星云》,当时在全国杂志界引起很大轰动。数十年的报人生涯和文学艺术创作,锻炼了他敏锐的新闻触角以及深刻的时事观察力。他凭着始终如一的爱国情怀与文采斐然的笔触,写了许许多多在国内极有影响力的特写、专访、长篇报道和文学著作及理论专著。先后出版了30多部著作,其中包括《望云海》《诗词艺术》《文史品味录》《观海录随笔集》《文苑春秋》《听涛集》《春华集》等等。敏之先生的作品,都会给人一种言近旨远、语浅情深、韵外之致的感觉。他不愧为一个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笔耕不辍的学者、导师、文学大家,使我无时无刻不感到钦羡与敬佩。他是罗城人的骄傲,也是广西人的骄傲!
敏之先生为人谦逊宽宏,性格开朗,耿直热情,喜怒常形于色,他看不惯那种与无私无畏、勤奋敬业、常怀感恩之心格格不入的东西,特别看不惯那种在生活和工作中患得患失、不求上进的人。他常推心置腹地和我交谈,对于社会上的歪风邪气,毫不留情地批评,尤其对当下文风不正,更是深恶痛绝。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为政不在多言,而在躬行实践。如今八股风盛行,讲话、写文章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很多套话、空话,让人感觉到千文一面的‘正确废话。这种风气不整掉,何谈文化的振兴?我们的老乡,恕我直言,你作为领导,要领头倡导好的文风!”这些话多少年来,一直在鞭策着我如何去很好从政行文。
几十年从事新闻和文学创作,敏之先生对中华民族文化有极其深厚的情感。他发起创建了香港作家联合会,后来又筹备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联合会,亲自担任世界华文文学联合会会长。他80多岁高龄,依然在香港与广州两地,主持香港作家联合会活动。时常邀请两岸三地的作家进行文化交流,为中华文化传播走向世界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常说,中国人一定要人心归顺,人心不归顺,就谈不到热爱祖国;人心归顺就靠文化,得人心者得天下,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我们要重视自己的文化,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敏之先生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他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奋斗了一生,难能可贵,彪炳千秋!
悠悠岁月,似流水逝去。敏之先生仙逝,是中国文学艺术界和新闻界的一个重大损失。作为一个热爱、尊敬、钦佩敏之先生的乡亲和生前好友,对于他的亲切关怀、关心、关爱,我一直看作是一位久负盛名的文学前辈、导师对我的谆谆教诲。对他几十年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新闻方面创造的业绩和声誉,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我不愿让那流逝的时光冲淡我心头的记忆,愿我这篇短文,作为一个花环,敬献在曾敏之先生的灵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