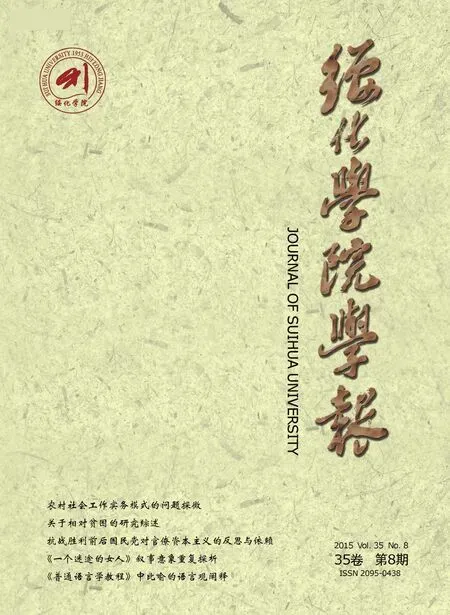《喜福会》在中国的研?究管窥
2015-04-10刘雪芳林晓雯江苏师范大学江苏徐州221000
刘雪芳 林晓雯(江苏师范大学 江苏徐州 221000)
《喜福会》在中国的研?究管窥
刘雪芳 林晓雯
(江苏师范大学 江苏徐州 221000)
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的20年左右时间里,著名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代表作《喜福会》曾经是国内文学批评界的焦点之一,相关研究在各级各类期刊上汗牛充栋,引发了褒贬不一的讨论。这场讨论极大地丰富了该小说的内涵的同时,也反映出国内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问题。
《喜福会》;小说研究;存在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华裔文学不断兴起,谭恩美是其代表人物之一,她的处女作《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于1989年问世,曾经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9个月,销量高达230万册,并获多项文学大奖,被选入《诺顿文学入门》教材。该小说于1992年由田青首次翻译成中文,也即刻获得评论界和读者的极大关注。据笔者粗略统计,自1990年至2014年,被知网收录的关于《喜》的论文多达六百多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一百多篇。这些文章从各个方面对《喜》(《喜福会》简称,以下同)进行诠释,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使中国读者接触到一种独特的美国文学的同时,也进一步了解美国华裔的历史、现状以及生存状态。本文尝试对其国内研究进行述评,以期从中发现规律、特点以及不足,为国内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一、主题研究
华裔美国人作为美国社会的少数族裔之一,长期以来处于美国主流社会的边缘地位,受到排斥和歧视,因此身份寻求是美国华裔文学与生俱来的主题,同时也与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社会的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大陆的研究者从中国视角出发,针对《喜福会》中母亲和女儿的文化身份和性别身份展开讨论。
《喜》中华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问题主要通过中国母亲和美国女儿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一隐喻展开,小说真实反映了两代华裔女性在中美两种不同文化夹击中的困惑、焦虑和选择。对此,中国研究者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他们从《喜》中他者身份构建出发,探讨了华裔母亲“失根”后的身份困境、母女间的失语状态、女儿们的身份困惑,以及她们在母亲帮助下积极地自我身份重建,最终获得母女之间的互相理解。例如,孙刚认为母亲们为摆脱旧文化的束缚,前往美国寻求新生,但美国的文化霸权并没有让她们如愿,反而陷入困境。顾悦指出:“谭恩美《喜》中突出表现了华裔女性的缺乏自我,而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家庭的产物,孩子必须按照父母所规定的样式生活”,“落水的经历不仅让映映体会到自己的安全感与归属感的丧失,更让她体验了自我的丧失”[1](P104)。美国主流文化的排斥、模糊的身份与来自家庭的冲突让母亲陷入身份困境,导致第二代华裔的矛盾与自卑心理,造成了母女间的隔阂。
第二代华裔女性经历了自卑与困惑的成长历程,开始了积极的文化身份重建,这与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胡亚敏指出:“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加快,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移民在全球经济文化交往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新一代华裔对处于弱势的本民族文化开始从一味的排斥转而表现出好奇和兴趣,对其文化身份有了新的认知。移民作家谭恩美的小说反映了华裔们的这一微妙态度和观念的变化。”[2](P73)胡老师把《喜》放置在全球文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下,认为小说中的华裔女性对中国文化身份的追求表现为美国人对异域文化的向往,她们从曾经需要竭力掩饰、压抑的东西汲取到了作为华裔美国人的自信,从而开始了积极的文化身份重建。
积极的自我认同在文化身份重建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华裔女儿们的文化身份重建的直接表现是对自身中国性的认同趋向。苗学华认为,尤其在以白人文化为主流的背景下,少数族裔的个人身份和民族身份无法得到认同,他们找不到心灵的归宿,从而寻找对本民族传统的回归。张素菊指出:“当他真正理解母亲带到美国的中国文化时,她才开始珍视母亲的文化价值观,同时也才真正发现了自我,接受了自己双重文化身份的现实。”[3](P131)易红用博弈论中囚徒困境和最优策略平衡两个概念证实了这种策略在华裔身上的可行性。笔者认为,认同是动态的、发展的和未完成的过程,具有开放性和建构性,寻根之旅是华裔女儿们重新审视自己文化身份的开始,进而重新找回自我,确立自己的独立身份,而谭恩美的成长和写作经历也正是一个民族身份寻求的过程。
谭恩美对第二代华裔女性文化身份重建的尝试引起学者们的热烈讨论。一些学者认为,《喜》中的文化身份重建是成功的,杨亚丽认为,第二代华裔女儿们经历了两种文化夹缝间的迷失,在母亲的引领下重构自己的文化身份,对自己华裔身份的正视是她们成长的重要里程碑。李晶认为,谭恩美认识并巧妙运用了飞散者边缘身份独有的优势,走出了困境,以自己的声音宣告了美国华裔女性一度迷失的文化身份,实现了自我的整合。蒲若茜和饶芃子则指出:“华裔美国女作家们在再现华族文化时,复制了美国强势文化的‘东方主义’凝视,在执着于女性主义斗争的过程中,歪曲或背离了自己的族裔性,最终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华裔美国女性身份。”[4](P23)在笔者看来,谭恩美在华裔美国人文化身份主题上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与早期的华裔美国文学作品相比,淡化了其中的族裔性,认识到文化身份的流动性,有“越界”的倾向,提出了自己多元文化身份的理想,从“既不是……也不是……”走向“既是……也是……”,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趋向,那就是离散的、拒绝固定疆界的身份认知。但华裔美国人文化身份的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将会对美国民族身份的建构产生深远影响。
《喜》中另外一个重要主题是性别身份问题。小说中四对母女轮流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让美国读者有机会认识这样一个在美国社会长期处于沉默、边缘地位的女性群体,倾听她们的声音。这也引起了大陆学者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学者们对性别身份的探讨首先是他者身份的构建,即父权制对女性压迫在《喜》中的体现。
《喜》突出了母亲和女儿的话语,男性在小说中作为陪衬形象出现,为夺回女性的话语权做出了努力。戴莉认为,《喜》的女性主义特征主要表现在以女性为主题的话语、第一人称的半自传性写作和诗意化的女性书写,《喜》表面上展现的是中美文化的碰撞和母女之间的冲突与沟通,但在深层次涌动的是一股女性主义的热潮,揭露男性霸权主义长期以来以或隐或显的对女性的压制。周隽指出:“尤其是在母女矛盾化解之后,在异族文化背景下的母女获得了一种共同的意识觉醒和默契,他们感到:在面对中西矛盾、母女矛盾、夫妇平权矛盾等多重矛盾的影响下,他们有必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获得尊重并寻找自己的价值。”[5](P74)母亲们在遭受了诸多困难后用不屈不挠的精神战胜困难,并将这种精神传给女儿们,鼓励女儿自立。美国华裔女性通过其特有的方式打破沉默,赢得自己的话语权,凸显女性解放的意义。沈非认为,《喜》用嫦娥奔月来揭露父权二元对立对于女性的他者化,指出:“女性作为他者在试图建构自己的主体性时面对的却是亘古以来通用的、女性必须加以解构的二元对立模式,而《喜》一针见血的剖析了这个悖论。”[6](P99)解构男女二元对立,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世界是人类共同的诉求,孙刚从生态女性视角出发,认为:“母女们不屈服于父权制的胁迫,不屈从命运的安排,女性自我意识逐渐苏醒,这正是生态主义批评家们所乐意看到的结果。”[7](P141)反抗唤起人们对自然和女性的尊重和理解,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和男女平等意识,呼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世界。
诸多学者亦对《喜》中的文化冲突与融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学者们认为母女的冲突代表了中西文化的冲突,归纳出冲突的原因主要在于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差异以及华裔在美国的处境。程爱民指出:“从文化角度看,我们认为,《喜福会》中母女之间的冲突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表征和小说结构框架,它所代表的实际上就是中美文化之间的冲突、一种东西方二元文化的对立。”[8](P89)陈科峰认为,《喜》中的文化冲突缘于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传统文化与个人主义文化的冲突。李前从吃螃蟹这一细节分析了中美饮食习惯上的差别,认为其中暗喻中美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过程。周聪贤认为,社会行为规范的文化差异是导致谭恩美小说中母女冲突的根本原因,且不论行为规范是不是冲突的根本原因,但它确实是造成冲突的原因之一。袁霞指出:“华裔在美国社会的处境也是造成《喜》母女两代人冲突的主要原因”,“西方霸权主义话语把亚洲人描绘成永远的外国人”[9](P84),这加深了第一代华裔与美国文化的对抗。
母女关系自冲突走向融合向我们展示了东西方文化从二元对立到解构二元对立的可能,在对待美国华裔的两难境地及文化认同的处理手法上,谭恩美打破了长期以来“中心”与“边缘”的对立模式,展现了一种积极的生活体验。《喜》的现实意义就在于:东西方文化需要互相理解,对彼此正确认识,取长补短,从单一的价值观逐步接受价值观的多元化,展现开放、多元和包容的后民族主义胸襟,因此谭恩美的作品更具普遍性,说明华裔文学正在走向成熟。
二、中国文化元素
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Geertz)认为,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之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待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即对生命的态度。《喜》中包含着诸多文化符号,尤其是中国文化符号。这是《喜》独具特色的内容之一,也是评论界热议的话题之一。
《喜》中弥漫着中国文化元素。但美国华裔作家所理解的中国文化并不等同于真正的中国文化,是他们在美国主流文化背景下对中国文化内涵和意义的理解、运用与书写,因此,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讨论。一些学者认为,《喜》中的中国文化是东方主义视野下变异了的文化符号。陈爱敏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谭恩美“不自觉”地步入了“东方主义的陷阱”,有意识地向西方基督教徒们呈现了中国文化另类的“他者形象”。林瑞韬和陈开富认为,中国文化在《喜》中发生了变异,是重构了的中国文化符号,是东方主义视野下的中国文化,迎合了西方读者的阅读口味,过于偏颇,没有展现真正的中国文化。他说:“《喜》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传达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然而,小说中所传递的如道家精神、阴阳五行、家族精神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一定差异。”[10](P145)
还有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小说是对东方主义的解构,传递着“中国魅力”,表达了华裔寻根的愿望,是《喜》中的中国元素造就了小说的成功。例如,陆薇并不赞同华裔美国文学是迎合白人读者的胃口,认为这一现象蕴藏着深层的学理原因,反映了文学经典发展的一些必然规律,这表明《喜》并不能被认定为东方主义的产物。马云霞指出:“东方文化特别是古老的东方文化,在西方人眼中有一种神秘色彩。中国文化可以在中国式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中反映出来,形成了本文所谈的‘中国魅力’。”[11](P435)对于西方读者来讲,陌生的中国文化符号,例如,中国饮食麻将、阴阳五行及神话传说等等,表现了中国文化的丰厚内涵、中国人崇尚的团圆美满的家庭关系以及中国式的做人艺术,谭恩美借此传递了中国文化。张瑞华探析了《喜》中的中国麻将,认为谭恩美借助中国麻将在作品身份主题与表现形式上达到了有机统一,谭恩美运用打麻将轮流坐庄的形式讲述故事是独具匠心的布局,“这一切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本人拥有敲开西方大门的‘无形的力量’,而她的‘麻将’或许就是那块敲门砖”[12](P100)。另外,何立群认为,《喜》的成功与五行理论的运用有极大的关系,五行理论使《喜》人物性格形象刻画栩栩如生,是展现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线索,并使小说充满东方异国情调,因此,五行理论是使《喜》达到主题叙事有机统一的因素之一。
这些中国文化符号亦体现了华裔海外寻根的愿望。张冬梅指出:“谭恩美在小说中以充满乡愁的笔墨表述着自己的祖国,在中国民间故事与传统习俗中寻求着精神文化之根。”[13](P139)。张老师联系谭恩美的成长经历说明《喜》所描述的是一次寻根之旅,其中中国文化符号的书写体现了华裔对传统文化的皈依。张军亦在文中阐释了母亲们对根文化的维系,女儿们对根文化的传承,认为这体现了谭恩美的理念,即“一个在被主流社会当作是‘另类或他者’的环境里,‘根’文化就是最后一个可以依赖的、无论如何也不能丢失的阵地”。
三、《喜福会》的艺术特色研究
《喜》的畅销不仅得益于深厚的主题意义,也归功于其精妙的叙事技巧。学者们分别从叙事技巧与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对该小说进行讨论。程爱民认为,文学批评要注意华裔作家在叙述层面上所常用的一些创作技巧或策略,要使美国华裔文学研究超越文化学、人类学或民族志学的研究视野,使美国华裔文学不致于成为文化研究的附庸,真正把美国华裔文学当作美国文学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单独一个族裔群体的特定产物。
自传作为一种文类,在东西方原本都是一种男性叙事,华裔女性利用自传这一男性叙事传统可以用第一人称强化“我”的存在,从中获取个体的独立性和随之而来的叙事权威,还可以赋予文章女性气质,为自传增添艺术性,族裔自传将社会学或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引入文学研究的视野。王毅分析了《喜》与一般传记文学的差异,传记文学作品通常都是讲述伟人等有一定影响和地位的人或有相当成就的成功人士的故事,但谭恩美创造性地把家人:外婆、母亲和作者本人化身为《喜》中的人物,清晰记录了母亲和她的生活,构成了“他者”传记文学作品。说故事也是谭恩美小说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喜》中有多个叙述者,通过叙述者和其他角色的对话将故事的各个层面逐一展开,程爱民认为,“这种多元的对话叙事结构是为了体现‘社会现实的多元性和矛盾性’”“这种对话型叙事结构:一来它与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结构有相似之处;二来,更重要的是,这种结构非常适于表现多元文化下不同文化所应采取的对话原则”[14](P60)。罗娴认为,故事就是个人的自我认同,故事使母亲找回了各自的声音,摆脱了长期失语的状态,塑造了引以为荣的个人形象,从而在排斥异族文化的美国主流文化语境中确立了自己是谁。
在叙事结构方面,学者们认为谭恩美采取了类似中国章回体的结构形式构建小说。程爱民认为,章回体小说结构的运用在《喜》里得到了最佳表现。徐劲亦认为,“谭恩美巧妙的运用打麻将的程序编排了她的故事,结构类似中国传统的章回体结构。我们称之为中国式的叙事模式。”[15]罗婷认为,《喜》是一部有复调特征的文本,十六个声音相互呼应相互补充以颇具中国传统特色的麻将游戏方式,有序的唱出一曲华裔女性的奋斗之歌。
独特叙事视角也是《喜》叙事艺术的特色之一。戴凡探讨了第一人称叙述者如何通过不同的思想、话语的表达方式进入他人的视角对自己进行评价而不丧失可信度,“为了表达上一辈人对自己的看法,June必须用她们的意识形态、心理眼光来做评判,这就要求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叙述超越自己的感知眼光而不致成为不可靠的叙述者”[16](P57)。王毅提出:“《喜》打破了传统叙事模式,虽也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但‘我’讲的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三个人的故事,讲的是关于‘母女’们的故事,《喜》中的‘我’和被叙事者的‘我’的故事使史实、虚构和现实的情节有机统一。”[17](P22)刘亚龙认为,谭恩美采用多个叙述者和不断转换的叙述视角,这种第一人称叙事只是讲述自己的故事,叙述者就更像一个认知受到限制的人,这也缩短了叙述者与故事、读者之间的距离。
此外,学者亦对《喜》独特的叙述话语展开了讨论。叶明珠分析了《喜》中具有东方色彩的象征,探讨了隐匿在表象之下的内心情感和理念及其反映的东方文化主题。李冰芷运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分析了《喜》中的人物对话,尝试说明小说中不仅存在中西文化冲突和两代人之间的矛盾,更有人物间深层次的对话。李红霞分析了《喜》中混杂英语的运用及其作用。张素娣认为《喜》中的叙述话语从“东方主义”到“生态女性主义”有明显的转变和进步。谭岸青认为,《喜》中的吴精美是“双重”叙事,一方面为其母亲叙述;另一方面讲述亲身经历的母女文化冲突。这些叙事手法有助于我们了解海外华人的生存状态,也可为我们提供一个反观自己的镜像。
四、国内《喜福会》研究的不足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谭恩美的研究突显了华裔文学与中国文学和美国文学之间的独特关系,反映华裔在美国艰难的困境以及抗争,从而唤起人们对这一群体的关注,丰富了华裔美国文学存在的价值。学者们的成果值得肯定,但依然存在着不足。
讨论美国华裔的文化身份问题首先要确定美国华裔作者所指的中国文化的内涵,华裔所指的中国文化。实际上是指美国华裔文化,并非我们所认识的中国文化,他们需要基于华裔生活经历建立独特的文化身份,要认识到认同是流动的、可变化的,不能以固定僵化的认知来评价美国华裔文学的作品。因此在对待美国主流文化背景下华裔作家对中国文化的书写时,可能不能简单地说这样的书写是东方主义化还是在颂扬中国文化。作为中国学者有责任关心中国文化在国外的接受和传播状况,但不管谭恩美的小说中是褒扬亦或批评中国文化,我们应该反省自身,借镜自鉴。顾悦坚持这样的观点:“谭恩美《喜》并没有一味褒奖中国文化,对旧中国妇女的悲惨境遇并不隐讳,因此常被批评为‘东方主义’的产物,然而勇敢的直面创伤记忆正是谭恩美写作的主要目的。”[1](P100)笔者认为这样的批评是中肯的,谭恩美的写作并非一味迎合“东方主义”或者讨好中国。
谭恩美曾坦言:“我写作是为我自己,如果不动笔,我说不定会疯掉,描述让我伤痛和焦虑的记忆以及那些秘密、谎言和矛盾是因为这其中隐藏着真相的诸多方面。”[1](P101)谭恩美在文中再现的是她记忆中的中国文化,是在美国这个大背景下感受的中国文化,她用这种回忆与再现治愈着心中的创伤。就作者谭恩美来说,她是位美国作家,她的目标读者定位为美国人,中国人只是她的潜在读者,她所写的小说首先是给美国人看的,并不是为了宣扬中国文化,也不是让美国人全面认识中国。有些读者误把文学作品当作历史来读,导致一种过度诠释。另一方面,有些读者将文本中“过去的中国”与“现在的美国”相比较,忽略了作家营造的时空跨越,也是导致观点相左的原因。
美国社会的华裔写作在表述华裔自我时都不得不面对主流话语的力量,考虑他们的接受。因此,在批评美国华裔作家作品时也应考虑到其写作的语境,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尽量避免民族主义的狭隘视野,以开放包容的心态阅读和评价美国华裔作家作品,充分挖掘其中的文学特性而不局限于政治文化主题。
结语
总之,中国学者们从文化主题、身份主题及叙事艺术与形象等方面对《喜》进行了多维阐释,极大地丰富了该小说的内涵,使我们对美国华裔文学,乃至美国华裔群体有了深入的了解,从中我们看到,对于美国华裔文学的解读,不仅需要中国视角,也需要将其置于美国文学的大背景下,分析其在美国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更加注重小说的文学性研究,丰富美国华裔文学的横向研究,延伸其纵向研究,从而充分认识美国华裔文学在美国文学中的独特性和普遍性意义。
[1]顾悦.论《喜福会》中的创伤记忆与家庭模式[J].当代外国文学,2011(2).
[2]胡亚敏.当今移民的新角色—论《喜福会》中华裔对文化身份的新认知[J].外国文学,2001(3).
[3]张素菊.两种文化身份的忽视与融合[J].戏剧文学, 2012(7).
[4]蒲若茜,饶芃子.华裔美国女性的母性谱系追寻与身份建构悖论[J].外国文学评论,2006(4).
[5]周隽.从沉默到觉醒美国华裔电影中的女性言说—以电影《喜福会》和《面子》为例[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4).
[6]沈非.“月亮娘娘”和映映——论《喜福会》中女性主体性在父权二元对立中的丧失[J].山东外语教学,2008(3).
[7]孙刚.《喜福会》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湖北社会科学,2010(11).
[8]程爱民,张瑞华.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喜福会》的文化解读[J].国外文学,2001(3).
[9]袁霞.从《喜福会》中的“美国梦”主题看东西文化冲突[J].外国文学研究,2003(3).
[10]林瑞韬,石云龙.论中国传统文化在《喜福会》中的变异及其缘由[J].中华文化论坛,2012(2).
[11]马云霞,赵秦梅.论《喜福会》的中国文化内涵[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12]张瑞华.解读谭恩美《喜福会》中的中国麻将[J].外国文学评论,2001(1).
[13]张冬梅.海外华人的中国文化情结——《喜福会》中的文化乡愁[J].江汉论坛,2008(9).
[14]程爱民,邵怡.女性言说—论汤亭亭、谭恩美的叙事策略[J].当代外国文学,2006(4).
[15]徐劲.在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上—评《喜福会》文本结构的特色[J].当代外国文学,2000(2).
[16]戴凡.《喜福会》的人物话语和思想表达方式---叙述学和文体学分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9).
[17]王毅.《喜福会》的叙事艺术[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
[责任编辑 王占峰]
I712.74
A
2095-0438(2015)08-0066-04
2015-03-22
刘雪芳(1991-),江苏徐州人,江苏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江苏省普通高校学术学位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KYLX-1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