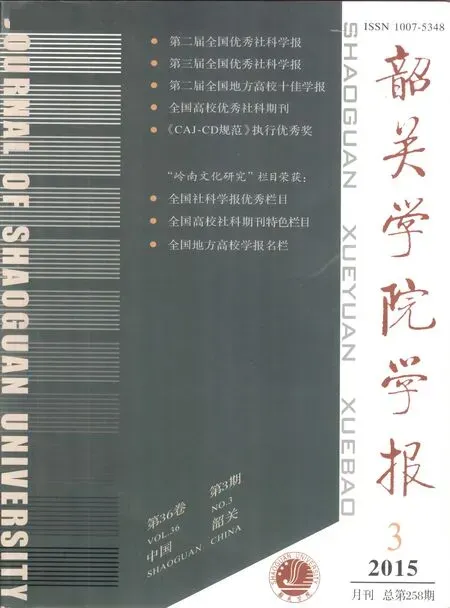从能动司法论民法法典化
2015-04-10潘丽文
潘丽文
(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从能动司法论民法法典化
潘丽文
(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民法法典化的主要意义有二:一是构造逻辑严密而不出现任何冲突的法典从而实现法典适用的“自动化”,进而实现立法权统一于国家立法机关的目的;二是更好地维护、实现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而无疑后者才是民法法典化最终的价值所在。但能动司法的客观存在,使这两者都似乎难以成立。从传统的法治理念来看,法典化与能动司法似乎无法共存。但若深入分析,尤其是就我国的法治实情而言,若要体现更好地维护、实现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的宗旨,实现社会的法治化,民法法典化与能动司法两者缺一不可。
民法法典化;能动司法;法治
民法法典化的原始意义之一,也是今天仍可能有价值的意义——构造逻辑严密而不出现任何冲突的法典,以达到法典适用的“自动化”,进而实现立法权集中于立法机关的政治目的;民法法典化在今天普遍认同的意义——更好地维护、实现民事主体的权利。但在能动司法的客观存下,民法法典化的这些意义似乎都失去了充分的说服力。如果说民法法典化的主要意义都因能动司法的事实存在而没有充分体现,加之民法法典化的成本又如此之高,那么民法还有必要法典化吗?
一、民法法典化的意义与能动司法的客观存在
(一)民法法典化的意义
追溯民法法典化的历史,可以发现无论是最原始的《国法大全》,还是后来的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其对法典化的追求都包含了现实立法权统一于国家立法机关的目的。查士丁尼编纂《国法大全》的目的,就是希望借树立《国法大全》是唯一有效的法律规范来恢复罗马法最初的纯洁与威严以及解决因罗马法的庞杂、法律之间存在各种冲突而难以适用的问题。为实现《国法大全》是唯一有效的法律规范这一目的,查士丁尼不仅禁止再行参阅其他任何法学家的著作,同时排除了其中收录的著述的原始权威,还禁止对其编纂的法典作任何评注[1]15。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都是在国家实证主义被奉行、民族国家蓬勃兴起的背景下制定的。在奉行国家实证主义和建立民族国家的强烈愿望下,西方国家立法权从中世纪分别由国王、教会、地方领主和市镇会议分割把持,发展演变成为最终由集权制民族国家统一掌握[1]16-20。尤其是法国当时的司法贵族制度不仅倒向土地贵族统治者,而且不能明确司法和立法的界限的情况下[1]21,为防止司法向其他领域的侵蚀,许多思想家提出了三权分立的构想,坚持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分立的重要性[1]21。正因为立法权集中于立法机关,而不允许司法机关染指,法律就必须实行法典化,以使法官不折不扣地适用立法机关制定的法规,而排除法官的司法解释权与衡平权。
就我国而言,虽然不实行三权分立,但立法权也是由特定的立法机关即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所掌握,法官没有造法的权力。因此,我国民法法典化的目的之一也包含了通过构建逻辑严密而不出现任何冲突的法典来实现法律适用的“自动化”,避免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的造法。
民法法典化除了上述的目的之外,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目的,也就是通过民法的法典化更好地维护、实现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民法是权利法,所有的民事法律都是为了维护、实现民事主体的权利而制定的,而民法的法典化通过使民事法律体系化,获得体系效益,通过体系内化规则间的矛盾,推出规则适用的优先次序从而更好地帮助法官找法,而这样的法律适用又会形成相应的解释学进而不断强化体系[2]。因为体系化的效益,法官能更好地理解法律、适用法律,作出更好的判决,从而更好地维护、实现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以上是实现民法法典化可能获得的主要价值,然而当我们的视线回到现实中,就会发现我们所认为的上述价值,在能动司法已经客观存在的事实面前难以立足。
(二)能动司法的客观存在
“能动司法”一词,是由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提出的,其本源应是西方的司法能动主义。对于司法能动主义的含义,有三种理解:一是违宪审查意义上的司法能动主义,这也是此概念的最初意义,它主张和坚持司法对于立法、行政等政治行为具有合宪性审查权利的司法意识形态;二是实用主义或现实意义上的司法能动主义,它最根本的特点是认为司法的根本追求是实现社会目标,进而在司法的依据上以多元社会规则、多重社会价值的标准取代法律这个唯一标准,在司法的方式上以灵便地适用各种方式和方法取代判案“法律——事实——结论”这个机械的三段论,在司法的姿态上从有效处理案件出发,自行地实施裁判行为去取代完全被动、消极地面对各个事实的做法;三是混合意义上的司法能动主义,它包含了上述两个司法能动主义的内容,只是不同的人对这两方面内容的强调不同[3]。从“能动司法”这个词的提出我们也可领会到,我国的“能动司法”与西方的司法能动主义是不同的。但两者在实用主义意义上的司法能动主义含义下是有重合内容的,可以说我国的“能动司法”是一定范围内实用主义意义上的司法能动主义,在总体上应当把中国能动司法看作是世界法治语境中的司法能动主义在中国的特殊形态[3]。
司法能动在西方国家的客观存在是无需再赘言的,而在我国是否存在能动司法却是还有争议。笔者认为,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都难以否认能动司法在我国的客观存在。
1.对法典的理论分析证明能动司法具有不可排除性
第一,从法典制定的角度而言,立法者至少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其自身的认识水平与价值倾向,二是其所处时代的限制。因此,这说明了制定的法典必然在某一空间和时间上存在缺陷或空白。但法条规定之外的客观事实存在,却不能因法条资源的短缺而拒绝民事主体的诉讼请求,这必然意味着最后裁判所用的司法依据是超越法律或不拘泥于法律的。第二,从法典本身而言,它存在着固有的弱点。关于法典固有的弱点,奥斯丁总结有14项之多,但最主要的是固定、不完整和内部的不和谐[4]。法典的不完整与内部的不和谐主要是由于第一个原因导致的。而法典的固定性,则可理解为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律的规范性、普遍性与稳定性。因此,它无法为差异化的个案提供良好的解决方案,若强行适用反而是与法律本来的目的相违背,损害法律的正当性、合理性,降低人们对法律权威的信仰。这意味着在某些空间和时间上,只有不受本本上法律的限制,才能真正实现法律。第三,从法律适用的角度而言,法律必须通过适用才能发挥其作用。首先,就法律适用者而言,无论法律规定得如何详尽,甚至是体系化的法典,不同的法律适用者对其还是会有不同的理解,这是无法排除的。况且这并不是一个机械,不可能只受到法律的影响,生活中的其他因素如政治、道德、情感等必定也会对其产生影响,因此法律适用者的推论是复杂的,判决的结果是多样的。把立法者制定的法律作为唯一的司法依据,只能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假想。其次,就法律适用的效果而言,任何法律的最终解释都不能离开法律适用者,法律适用者的判决具有现实的影响力。因为单纯的法条无法对具体的案件发生效力,单纯的法条背后也不存在“强制”作为后盾使其具有约束力,但法律适用者的具体判决后存在着“强制”[5]。真正发挥作用的法律,必定是经过法律适用者演绎过后的法律,可以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发挥其自身的“造法”权力。第四,就法律的目的而言,无论是把法律作为一个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还是希望它能维护、实现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都无法脱离能动司法。首先,因为正如经济、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以外,政治目的也在不断变化。也许正是因为经济、社会的不断变化,才导致了政治目的的不断变化。法律的修改、制定是复杂漫长的,对于法典而言就更是如此,而政治目的本身却又是适时的,这时就必须依靠司法的能动。即使能动司法对政治目的的实现也必须在制度框架中依照相应的程序进行,但相对于修改、制定法典而言,它无疑能够更好地实现目的。也许有人会质问司法不应是独立于政治的吗?通过能动司法来实现政治目的,那法律还是法律吗?无法否认,司法始终只是一个政治装置,是实现政治目标的一个工具;法院始终是国家政治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是民族-政治国家的权力网格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司法固然有独立的行为标准与活动方式,但并没有独立于统治之外的利益[3]。与其追求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倒不如从实现出发思考引导和转化、完善与规制的途径,也许这才是真正现实理想的途径。更何况通过能动司法来解释政治对法律的影响,客观上能够消除一部分人对司法乃至法治的忧虑,至少使实务界与学术界找到了对话的共同主题,从而把政治色彩浓烈的司法路线、司法方针和司法主张还原到法治语境中加以讨论和评说[3]。其次,就更好地维护、实现民事主体的目的而言,能动司法更是不可或缺的。笔者并不否认法条是为维护、实现民事主体而制定的,但法条无论怎样具体,相对于现实案件而言,它总是抽象的,有时甚至是缺位或荒谬的。但法律适用者却是真真切切地参与到了具体的案件当中,他更能体会和明白民事主体的需求所在,也能清楚明白法条所规定的“一般”与现实案件的“特殊”,在法律缺位或不应适用的情况下,根据法律的根本价值或内在本质,作出真正符合法律目的和维护、实现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判决。
2.我国司法实践说明能动司法的客观存在
司法立法应是能动司法的最高体现。但基于权力分立的理论与原理,司法立法在我国仍然是充满争议的问题。在我国,司法立法活动往往不被承认,而其相应的功能更多是通过“法律解释”等词语加以表达。但无论司法立法活动的形式是什么,都无法改变其立法的本质,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和刊登在最高法院公报上的判例正是最好的证明。
司法解释是中国特有的法律性文件。也许有人会说,目前中国司法解释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在于之前的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并与我国“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原则有关。但是事实上,无论是改革之初“无法可依”状态下作出的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还是后来相关法律已经颁行后的各种关于贯彻执行法律的“意见”、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或“规定”等,最高人民法院一直在扮演着创设法律或扩展法律的立法者角色[6]。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法律解释权,但在私法领域,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的解释,长期以来处于冬眠状态。最为活跃的则是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几乎到了“无法不解释”的地步[6]。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无论有多少种类型,无论存在多少问题,我们都无法否认它确实存在着司法解释形式的立法。
我国最高法院从1985年起开始定期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刊载具有典型意义的审判案例,并且同时说明该案件的判决“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可供各级人民法院借鉴”[4]。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不少法院非常关注上级法院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并在相似或近似案件的裁判中加以引用,而下级法院直接将上级法院或最高法院的裁判作为本院裁判依据的情况也并不鲜见。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也是如此,他们乐于寻找对自己有利的生效裁判作为辩诉攻防的武器[7]。这其实就说明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先例”的特征。
通过上述理论与实践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能动司法是无法排除且不应当排除的。那民法法典化的第一个追求——构建逻辑严密而不出现任何冲突的法典,以实现法典“自动化”,就不攻而破了。至于民法法典化的第二个追求也是最根本的追求——更好地维护、实现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由于法典在制定、其本身、适用以及目的上都存在某些问题或离不开能动司法,那么就目前的分析来看,似乎只要能动司法结合法律而非法典就已经能够实现这一目的。既然能动司法是不可排除的,而民法法典化又是高成本的,那民法还有必要要实现法典化吗?下面将通过论述我国要确保能动司法正常运行的做法,来说明我国民法法典化的不可或缺。
二、民法的法典化与能动司法的正常运作
(一)能动司法正常运行的约束因素
在我国要保证能动司法按照其本原目的运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应是司法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如前所述,司法与政治之间的融合,是司法向其政治本质的回归。司法是无法脱离政治的,我们只能通过制定制度框架和程序,引导和转化它们之间的关系走向法治化的道路,完善和规制它们之间的关系,使之符合法治的要求。应该明确任何在制度之下为实现权利而赋予的权力应该都是符合法治的要求的。在我国要解决司法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首先应正确理解司法所服务的“大局”。能动司法之所以要体现政治的要求,其正当性在于该政治目的是为大众利益的,从而在根本上与法律的价值一致。因此,必须要求法律适用者对法律的价值有深刻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判断正当的政治要求与不正当的政治要求,进而决定对该政治要求的态度。我们所追求的能动司法应是能够拒绝不正当的政治要求的能动司法,而不是政治的“仆人”。其次,解决司法队伍素质不高以及司法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3]。司法队伍素质不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法律原则、法律理念和法律知识的系统掌握不够;二是对政治要求的判断与态度存在问题,对社会生活的实际理解、感受和了解较为肤浅;三是在司法内在激励严重不足的情形下缺乏对强大的外部诱惑的抵制能力。司法运行机制的问题主要是法院内部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之间的关系没有厘清,从而引起司法活动中的各种弊端。
(二)民法法典化对能动司法的利与弊
民法法典化对能动司法最大的阻碍,应该是法典化所信奉的法条主义对能动司法排斥。
至于说民法法典化对能动司法存在促进的作用,应该是很有争议的命题。但笔者认为就我国情况而言,民法法典化确实可以促进能动司法的正常运行。首先,民法法典化对能动司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如上述,在我国要实现能动司法的正常运行,最大的问题是正确处理司法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由于历史和其他原因,在我国政治力量是较为强大的,无论是哪个行业、哪个领域的人都无法摆脱行政化的思维方式,而相对的法治观念却较为薄弱。在民法领域尤其如此,因为中国古代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法,民法可以说是舶来品。权利观念,法律至上的信仰即使在今天被大家所倡导,但相对于实现法治社会说需求的权利意识、维权意识仍然很不足够,这不仅仅是对广大的群众而言的,对国家领导人而言、对法律工作者尤其是法官而言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如何能实现前面所提到的正确把握司法的“大局观”呢?如果说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在社会中培养人们的权利意识,树立法律的权威,营造法律至上的氛围的话,就目前民法的法典化已经具备条件的情况下,还有什么比这更快、更好的途径吗?相对于通过其他途径缓慢实现提高人们法律意识、培养法律至上的信仰所付出的社会成本而言,难道民法法典化的成本还要更高?民法法典化除了在提高人们权利意识、营造法律至上氛围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外,由于法典源自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之手,在权利来源上有至高的权威性,同时在民事法律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因此其位阶仅次于宪法,其他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策命令等均不得超于民法典[8]。从这个意义而言,无疑是给予了能动司法主体拒绝不正当政治要求的权力。民法的法典化无论是对能动司法主体正确把握司法的“大局观”,还是对其拒绝不正当的政治要求都非常有意义。进一步说,通过民法法典化培养人们的尤其是司法工作者与国家领导人法律至上的信仰,对于实现司法运行机制的去行政化也非常有意义。如果说这些目标还有些遥远,那么民法法典化所能实现的基础的民法法律的体系化,必定也对司法工作者系统掌握法律原则等法律知识与深刻认识法律价值和目的带来巨大的帮助,从而提高司法工作者的素质,更好地实现能动司法。回顾法国法典、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等,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民法典的制定并非为了单纯地实现民法体系的完整性和民法结构的整合性,它实际上肩负着更加宏大的历史和政治使命。虽然今天我国无需通过民法典的制定来推翻旧政权或宣告国家的统一,但我们希望通过民法的法典化来推进我国法治建设重大进展。
其次,从消极作用而言,虽然说我国很多人的法治理念仍然停留在法条主义上,但是民众的规则意识还普遍淡薄。尽管这看起来是一个难以解释的悖论,却是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真实[3]。在这样的情形下,通过民法的法典化,提供较为严密完整的规则,强化规则意识,提高规则权威,无疑也是对能动司法异化的一种限制手段。
三、正确认识民法法典化与能动司法的关系
就传统法治理念与法典化的意义而言,民法法典化与能动司法是无法共存的。然而在中国法治实情下,要体现民事法律维护、实现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宗旨,两者就得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民法法典化的意义,它不应完全否定能动司法的存在,它的主要意义应该是通过构建体系化的民事法律,为民事主体提供基本的权利保障规范,同时树立权利意识,营造法律至上的氛围。在实现其自身价值的同时,也要促进能动司法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尽管无法排除能动司法的客观存在,实际上也不应当排除,但在司法与政治存在天然联系的情形下必须采取相应的制度和手段防止能动司法出现偏差甚至异化,尤其就民众规则与法治意识都普遍淡薄的情形下,更需通过民法法典化这个规则的最高形式把能动司法限制在一定框架内。
正确认识民法法典化与能动司法的关系,为现代法治发展的规律和特性所必须。当今世界两大法系的相互交融、趋同,也许就证明了法典化与能动司法的相辅相成才是真正实现法治的道路。
[1]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M].顾培东,禄正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2]苏永钦.现代民法典的体系定位与建构规则[J].交大法学,2010(1):59-93.
[3]顾培东.能动司法若干问题研究[J].中国法学,2010(1):5-26.
[4]徐学鹿.论非法典[J].时代法学,2005(4):70-78.
[5]刘星.法律是什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83.
[6]柳经纬.当代中国私法进程中民商事司法解释[J].法学家,2012(2):85-99.
[7]曹士兵.最高人民法院裁判——司法解释的法律地位[J].中国法学,2006(3):175-181.
[8]王利明.法律体系形成后的民法典制定[J].广东社会科学,2012(1):5-17.
Study on the Codification of Civil Law from the Angle of Judicial Activism
PAN Li-wen
(School of Law,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Hubei,China)
The main significance of codification of civil law there are two:one is the structural logic without any conflict of law so as to realize the code for“automatic”,so as to realize the legislative power in state legislatures;one is to better safeguard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civil subject.And the latter is the final value of the codification of civil law.But the objective existence of judicial activism,makes both of these seems so difficult to set up.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the rule of law,law and judicial activism seems unable to co-exist,but if further analysis,especially on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s situation,To achieve better maintenance,realization of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urpose of the civil subject, the rule of law society,the Civil Code and the judicial activism both are indispensable.
The codification of civil law;judicial activism;the rule of law
D923
A
1007-5348(2015)03-0129-05
(责任编辑:曾耳)
2015-02-16
潘丽文(1989-),女,广东韶关人,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民商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