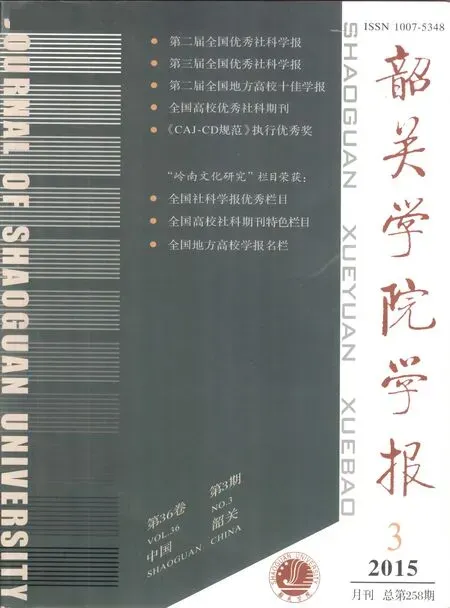战国士阶层起源与演变考述
2015-04-10钟云瑞
钟云瑞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曲阜273165)
战国士阶层起源与演变考述
钟云瑞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曲阜273165)
春期战国之际,政治上诸侯争霸导致上古三代贵族文化下移,“王官之学”散在民间,士由此兴起。从文字训诂方面考究,士在先秦时代可能泛指掌管事务的中下层官吏。古代贵族教育注重文武兼备,士阶层来源于卿大夫阶层的降黜和下层庶民的升迁。诸子百家作为士的典型代表,其执政理念虽异,但在“以道自任”的文化层面却一致,尤以儒墨两家论述显著。“游”是士的最大特点,即不附属于官僚政治系统,私门养客制度肇端于此。其在政治上的威胁性导致大一统王朝建立之初便限制养士,《云梦秦简》的出土佐证了秦朝对士的严格控制。
战国;士阶层;以道自任;儒家;墨家
“士”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及演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士作为中国古代社会阶层的一种精神风貌,其最核心的任务是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通过“士”这一阶层的历史发展,可以窥探中国文化的独特形态。本文通过梳理历史文献资料,探讨战国时代士阶层的起源及其演变,以期揭示“士”对中国历史文化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
一、关于士的起源诸说
关于“士”的起源问题,学者多从文字训诂入手,援引甲骨文、金文佐证,借助出土文献,考证出许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商周文献中关于士的记载屡见于《尚书》诸篇中,如《多士》“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俞樾《尚书平议》云:“‘王士’二字连文,‘王士’之称犹《周易》言‘王臣’,《春秋》书‘王人’,《传》称‘王官’,其义一也。”[1]261“商王士”泛指殷商的旧臣。又有“庶士”之称,如《大诰》“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2]510,在商周时代,士指具有国家官职的贵族阶级。
关于士的最初起源理论,见于《说文解字》:
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段玉裁注曰:“引伸之,凡能事其事者称士。《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故《传》曰:‘通古今,辩然不,谓之士。’”[3]20
许慎以“事”训“士”,从训诂学的角度尚可解释,但段玉裁释为“凡能事其事者称士”,能做一切事的都可称士,但“士”的具体身份却无从可知。刘向《说苑·修文》篇云:“辨然,通古今之道,谓之士。”[4]581这可看作是汉代对“士”的一种普遍解释,并没有阐释其原始意义。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三《释士》条下引吴承仕的观点对“士”进行界定:
士,古以称男子,事谓耕作也。知事为耕作者,《释名》释言语,云:“事,倳也;倳,立也,青、徐人言立曰倳。”……《汉书·蒯通传》曰:“不敢事刃于公之腹者。”李奇注曰:“东方人以物臿地中为事。事字又作菑。”……《汉书·沟洫志》注云:“菑亦臿也。”……盖耕作始于立苗,所谓插物地中也。士事菑古音并同,男字从力,依形得义,士则以声得义也。事今为职事事业之义者,人生莫大于食,事莫重于耕,故臿物地中之事引申为一切之事也。[5]112
杨树达又根据甲骨文进行补充:
树达按:士字甲文作丄,一像地,丨像苗插入地中之形,检斋之说与古文字形亦相吻合也。[5]112
根据二人的表述,士最初则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农夫。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一书赞成上述观点,并引《礼记·少仪》篇“问士之子长幼。长则曰能耕矣,幼则曰能负薪”,证明士不脱离农业生产[6]68。此外,徐中舒《士皇王三字探源》断定士、王二字字形相近,皆象人端坐,但士为官长,王为帝王[7]441-446。刘节在《辨儒墨》中认为士乃西周所特有的官职,即“卿士”与“太史”之官属[8]220-221。
对于士的原始意义,若仅从训诂角度考证,我们不能得到确切的答案,只能认为士在先秦时代可能泛指掌管某些事物的中下层官吏。
二、士阶层的兴起
顾颉刚先生《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一文认为士最初仅是武士,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然后转化为文士[9]85-91。余英时先生对此提出质疑,认为顾氏对于士的转化未能提出合理的解释[10]7-17。但顾氏“古代之士皆武士”的论断还是比较接近事实的,他认为古代的学校以军事训练为目的,这一观点得到杨宽的认同:“当时贵族生活中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有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但是,因为国之大事,惟祀与戎,他们是以礼乐和射御为主的。”[11]207
古代之士重射御,这是历史事实,但将文士的转化和演变归于射御之礼,未免略显单薄。《论语》中有两条关于“射”记载: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八佾》)[12]25
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八佾》)[12]29
“射”作为礼乐的一部分,在周代绝不完全是军事上的武射,而是作为六艺的一种,目的在于培养君子的道德人格。周代贵族子弟的教育注重文武兼备,如《礼记·王制》所载:
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13]546
又《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载了楚子及诸侯围宋,晋文公为救宋国而谋元帅一事:
赵衰曰:“郄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乃使郄縠将中军。[14]445
赵衰推荐能“说礼乐而敦诗书”的郄縠去作元帅,足见春秋时期贵族教育是注重文武合一的。但是,春秋时期是古代贵族文化的最后同时也是最高阶段,礼乐不再在国家政治中居于主导地位,贵族学习礼乐的习惯由此废止。以孔子为代表的士阶层发其肇端,将诗书礼乐传播到民间,这可看作是士阶层兴起的时代背景,也是其演变的文化渊源所在,因此文士从武士蜕化而来的说法值得商榷。士阶层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变化可从社会阶级的层面来考察,关注士这一阶级在整个社会阶级中的变化流动,即上层贵族降为士和下层庶民升为士两个方面。
(一)上层贵族降为士
关于士阶层在古代社会中的地位,史籍中的记载俯拾皆是,如《孟子·万章下》载:
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15]217
士是居于卿、大夫之下的一种爵位。但随着礼崩乐坏的发生,上古三代所确立的社会秩序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之下瓦解殆尽,这一现象在士阶层的反映,主要是上层贵族逐渐衰落而下移成为士。值得注意的是《左传·昭公三年》叔向与晏子讨论晋国公室衰落的情况:
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栾、郄、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晏子曰:“子将若何?”叔向曰:“晋之公族尽矣。肸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室从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无子,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祀?[14]1236叔向对晋国贵族的衰落表现出极大的感慨,春秋晚期是古代社会阶级制度崩坏的前夕,预示着新的社会关系的到来,各国内部的政治斗争是导致原有的阶级制度瓦解的原因之一,经过政权的不断交叠,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上层贵族则沦为较为低级的士。
(二)下层庶民升为士
处于社会底层的庶民在春秋末叶的社会变革中地位不断提升,成为士阶层的“新生力量”。春秋战国之际庶民凭借知识、技能而成为文士之人不乏其例,如《吕氏春秋·尊师》篇记载:
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卢参,东方之钜狡也,学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16]208
子张、颜涿聚等六人之所以成为天下的“名士显人”而使王公大人“礼之”,得益于其能“学”,而他们学习的内容绝不仅止于一般的社会技能,必然涉及到西周贵族的诗书礼乐,恰是他们掌握了这种能在邦国盟会时起关键作用的交际能力,才得以跻身于士的阶层。此外相关记载见于《管子》和《国语》中,《管子·小匡》篇云:“是故农之子常为农,朴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故以耕则多粟,以仕则多贤,是以圣王敬畏戚农。”[17]401《国语·齐语》曰:“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为士。”[18]320这两处记载说明农夫之子有秀异之材者可以为士,将庶民的身份转化为士,则是春秋晚期以来社会变动的结果,这样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有知识的士人,加之贵族特别是大夫阶层的地位下降,构成了士阶层的壮大,此即春秋战国之交士兴起演变的渊源所在。
三、士的代表——以道自任的诸子之学
先秦诸子百家的渊源虽同为王官之学,但在战国之际的交锋中却演化有各自的理论依据,由此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时代风貌。诸子作为士的典型代表,尽管学派思想不尽相同,但在“以道自任”这一士的文化精神层面却是一致的。儒、墨两家关于士的见解最为显着。
(一)士的先驱集团——儒家
孔子开办私学,收徒设教,成为诸子之学的先驱,为此以道自任的士精神在儒家表现得最突出。孔子议论士的言语在《论语》中可谓不少,如: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12]36
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宪问》)[12]141孔子的这些言论都在强调君子即士的道德修养与人格追求的最终目的是“道”,所以中国知识阶层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孔子便已努力给它贯注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的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10]25。
继孔子之后,孟子把儒家富有理想主义的精神发挥到淋漓尽致,将孔子的“道”与士紧密联系: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孟子·尽心上》)[15]297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15]292
孟子升华“道”的含义,将其解释为仁义,是对儒家核心观念的提炼,这便是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最高境界。
荀子是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限于时势与政治的压力,他必须把“道”与现实实际密切结合,才能在诸子之中脱颖而出,《荀子·儒效》云:
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天下之道毕是矣。乡是者臧,倍是者亡。乡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19]133
荀子认为“道”是成为圣人的必要条件,借此以与政治相联系,使之施行于邦国统治。在对士以道自任的认识上,荀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士应当有自己的价值取向,这是荀子乃至儒家对士这一主体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定义。然而荀子之时,诸子学派之争已日趋激烈,为取得一席之地不得不把“士”的概念高度政治化,但儒家为其最初兴起演变时所做出的界定,对后世士阶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尚贤”的模范——墨家
墨子是主张“尚贤”的,在《墨子》中“贤”与“士”意义相同,故“尚贤”即“尚士”。《墨子·亲士》开篇即论“贤”与“士”:
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20]1
很明显此处是把“贤”与“士”等而言之,而二者对于邦国治理同样重要。在“以道自任”的观点上,墨子主张士应参与政治,这与儒家的立场一致:
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则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尚贤上》)[20]48
诸子各家虽然立足学术的视角不同,但在对士阶层的认识层面上其理论依据却大体相符。作为士的典型代表,诸子从各自的学派渊源中可以找寻出其“以道自任”的学术归旨,这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性格的养成及中国思想史的进程都具有奠基性的作用。
四、士的结局
士最大的特点是“游”,即不附属于一定的官僚政治系统,凭借其所构成的社会集团性,作为宾士为某一私门服务,由此衍化出私门养客制度。《吕氏春秋·高义》篇引墨子的话说:
若越王听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于宾萌,未敢求仕。[17]1255
其中“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是对士的客观描述,因为士没有经济基础与社会依附性,他们必须依靠贵族给予的薪俸而生活,战国后期的食客制度大概来源于此。
战国时代的士来源于贵族卿大夫与下层庶民,他们作为社会的知识阶层,能够为其所服务的贵族带来政治上的优势,这恰是私门养客的目的所在,而这必然对上层统治者的政治权力构成威胁。《史记·春申君列传》载战国四君子云:“春申君既相楚,是时齐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21]2395“辅国持权”是贵族用士的最大优势,甚至可以左右诸侯王的施政,故秦王统一六国之后不再任用士。
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发现,为研究战国时代这一段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文献佐证。《云梦秦简》的出土,为研究秦朝律法呈现了详实的资料,其中亦有涉及士的制度,兹选录如下,以供参考。
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22]9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22]9
使者(诸)侯、外臣邦,其邦徒及伪吏不来,弗坐。可(何)谓邦徒、伪吏?徒、吏与偕使而弗为私舍人,是谓邦徒、伪吏。[23]33
以上诸多资料显示,秦朝的统一结束了游士的时代。在大一统的历史背景下,政治上要求君权高度集中,士乃至卿大夫不再具有议论朝政的行为,而文化上更是实行精神专制,“焚书坑儒”的高压政策彻底湮灭了“百家争鸣”的氛围,为此起于春秋末期,盛于战国时代的士文化阶层,终伴随着封建王朝的建立而销声匿迹。
五、结语
先秦时期的士特指“游士”而言,正是这个“游”字,强调了士作为文化主体的唯一性。春秋战国的时代主题是诸侯争霸,“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造成了文化的下移,“王官之学”的世俗普泛化使士能够汲取前代的统治经验和政治智慧,其行为造就了战国时代的文化与精神,依据这种精神可以批评社会政治、抗礼王侯,而这种精神的文化渊源却在“道”。如果把战国时代所有重要观念的落脚点放在“道”上,不仅儒家的思想根源可以探寻,其他诸子学派的理论同样闪现着“道”的身影,为此一个“道”字构筑了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核心内涵。
士作为一个社会集团,有着独特的社会属性、政治身份和知识背景,以道自任的精神形成了能够左右邦国命运的文化主导权,尊礼义、重德行的气度,将传统价值观转化为一种时代风尚,并对后世士大夫乃至文人墨客的文化心理与精神风貌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1]江灏,钱宗武.今古文尚书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
[2]孔颖达.尚书正义[M].孔安国,传.黄怀信,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4]刘向.说苑疏证[M].赵善诒,疏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5]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全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6]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7]徐中舒.士皇王三字探源[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四分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
[8]刘节.古史考存[M].香港:香港太平书局,1963.
[9]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3.
[10]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1]杨宽.古史新探[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3]孔颖达.礼记正义[M].郑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5]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6]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7]黎翔凤.管子校注[M].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4.
[18]徐元诰.国语集解[M].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
[19]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0]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2]云梦秦墓竹简整理小组.云梦秦简释文:二[J].文物,1976(7):1-11.
[23]云梦秦墓竹简整理小组.云梦秦简释文:三[J].文物,1976(8):27-37.
Study o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Stratum of Scholar during Warring States Period
ZHONG Yun-ru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Qufu Normal University,Qufu 273165,Shandong,China)
During the spring time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politics prince hegemony led to the ancient three generations aristocratic culture down,“Wang Guan Culture”scattered in folk and stratum of scholar rose. From the philology and exegetics,stratum of scholar may represent the middle and lower officials in charge of the affairs.Stratum of scholar originated from the bureaucrats to oust and civilian to promote.All classes of authors are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ves,which have the same thoughts of“Undertake Dao”,and Confucian and Mohist School were the most famous.“You”is the biggest characteristic of stratum of scholar,who did not belong to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private door raise guest system”began.The Qin Dynasty abolished the system,and Qin bamboo slips of Yun Meng can confirm the history situation.
Warring States Period;stratum of scholar;undertake Dao;Confucian;Mohist School
K231
A
1007-5348(2015)03-0078-05
(责任编辑:廖铭德)
2015-01-05
钟云瑞(1990-),男,山东潍坊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