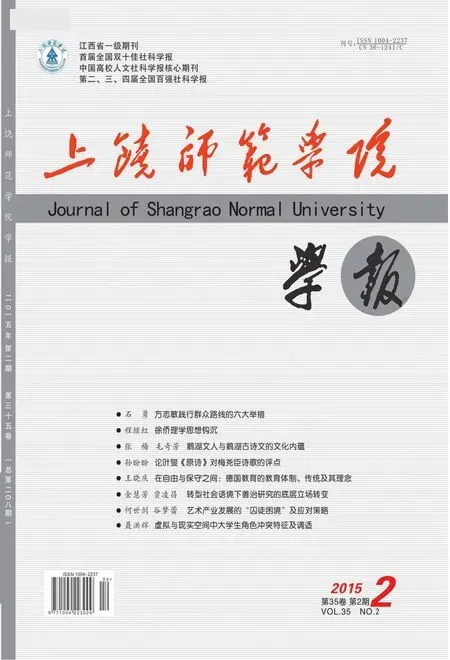徐侨理学思想钩沉
2015-04-10程继红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浙江舟山316002
程继红(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浙江 舟山316002)
徐侨理学思想钩沉
程继红
(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浙江 舟山316002)
徐侨,南宋理学家。他是朱熹理学在浙江的早期传播者 ,是宋理宗时期朱熹理学官方化的积极推动者,也是南宋后期继续张扬朱熹心性之学的重要学者。因著作不传,其理学思想隐而不显。今试从明刻《家传》以及其他史料中,对其道统、经筵、心性等方面思想作出钩沉与分析。
徐侨;理学;钩沉
徐侨(1160—1237),字崇甫,义乌人,南宋政治家、理学家。徐侨作为南宋浙江义乌儒学的代表人物,与朱熹有着直接的师承关系。他不仅是朱熹理学在浙江的早期传播者之一①,还以其晚年在理宗朝的地位为朱熹理学官方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他也是南宋后期继续张扬朱熹心性之学的重要学者。对于朱熹理学在异地之传播与局面之开拓,一传弟子所起的作用往往是非常关键的。《宋史》在《儒林传》之前特辟《道学传》,而《道学传》中又设《朱氏门人》,传主为黄 、李燔、张洽、陈淳、李方子、黄灏,此六人皆为朱熹一传弟子,其中黄 、陈淳、李方子为福建人士 ,而李燔、张洽、黄灏则为江西人士。福建是朱熹理学输出的根据地,而江西则是朱熹理学传播的主战场 ,这也许是《宋史·道学传》从朱熹理学传播角度选择此六人入传的主要原因。但《宋史》的考虑并不周详,因为朱熹理学传播的主战场除江西之外,浙江其实是一个比江西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另一个主战场 ,理应有浙江的一传弟子入《道学传》,至少徐侨、叶味道、辅广三人应该有此资格。《宋史》修成后常受后人诟病,与其著述不谨严有莫大关系,此即一例。朱熹在浙江的一传弟子中,徐侨不是最早的一位,却是最重要的弟子之一。因其著作不传,今试从明刻《家传》以及其他史料中对其理学思想略作钩沉与分析。
一、徐侨的道统谱系观
道统为儒家传道的脉络和系统。孔子向来重道,言必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孟子则建构了一个尧、舜、禹、汤、文、武到孔子的“道”之谱系。唐代韩愈作《原道》以排佛老,以仁义道德为儒家之“道”,其“统”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而他本人则以继承孔、孟道统为己任,为儒家正宗。到北宋孙复,将道统分为两个阶段来表述,他说:
吾之所为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1]
在孙复这里,从尧到孔子为一阶段,自孟子以下为另一阶段。这样划分的理由大概同于其弟子石介的《尊韩》:
道始于伏羲,而成终于孔子。道已成终矣,不生圣人可也。故自孔子来二千余年矣,不生圣人。若孟轲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祖述
孔子而师尊之,其智足以为贤。[2]
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中说: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 ,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大明 ,为功大矣。[3]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关于道统的论述不涉及道统的接传,对此清初学者费密有所揭示:
独言孟轲之传,开于唐儒韩愈。至宋蔡京遂以王安石上下孟轲,程颐又以程颢为孟轲后一人,而尚无道统接传之论也。南渡后朱熹与陆九渊争胜门户,熹传洛学,乃倡立道统,自以为曾氏独得其宗 ,而子思,而孟轲,而程颢、程颐接之。[4](卷上)
朱熹《中庸章句序》关于道统的认识,其最显著的特征是重视道统的“接传”,他认为尧之授舜,舜之授禹,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即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但以上道统的接传,主要在君臣之间进行,而自孔子始,则开启学者之间的接传,故朱熹云:
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 ,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说而得其心也。[5](P3674—3675)
道统接传之论,必然使道统的谱系进一步得到强化与凸显。那么,朱熹认为自己在道统谱系中的地位又该如何呢?他用较为自谦的口吻追述道:“吾少读程氏书,则已知先生之道学德行,实继孔孟不传之统。”[5](P3732)而在《大学章句序》中,朱子又说 :“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接乎孟子之传。……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 ,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5](P3673)朱熹以“私淑”二字较含蓄表达了自己得道统之嫡传的意思 ,而其门人则直接将朱熹与道统的关系明确化。黄 说:
窃闻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 ,至先生而始著。[6](卷八)
朱熹另一门人陈淳也说:
轲之后失其传,天下骛于俗学,盖千四百余年,昏昏冥冥,醉生梦死,不自觉也。及我宋之兴,明圣相承,太平日久,天地真元之气复会,于是濂溪先生与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觉之资,相继而出。……河洛之间,斯文洋洋,与洙泗并,闻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微言遗旨,益精明而莹白之。……盖所为集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统,萃乎洙泗濂洛之渊源者也。[7](P76-77)
在弟子们看来,朱熹不仅得周程之嫡传,而且还是道统的集大成者。在道统谱系的建构史中,徐侨承朱熹而来,进一步明确了“孟子师子思,子思师曾子,实接圣道正传之统”的观点。《家传》所载其与理宗的对话,得见出大概来:
上因论孟子传授,公奏:“孟子师子思,子思师曾子,实接圣道正传之统。曾子述《大学》以传之子思,子思又述所得于曾子传授心法谓为《中庸》以授孟子。其言中者天下之大本,诚者天之道,实发明理义之大原,其功为最大。子思顾乃从祀,而不得与十哲于堂上,古今阙典也。夫十哲者,夫子因念从于陈蔡者凡十人,偶不在门耳,岂谓弟子之贤哲止此十人而已哉?”上称善,曰:“前此所未闻。”又曰:“升子思而不及伯鱼,恐未安。”公奏:“此道统所系,非可以父子之私论。”[8]
应该承认,徐侨的道统谱系,大抵不出朱熹《中庸章句序》中的设定。那么,徐侨对于道统学说的贡献究竟体现在哪一点上呢?这要从庙祀说起。我们认为道统其实有两系:一为道统谱系,一为道统庙系。一般而言,道统中人士在庙祀中的地位,反映了他在道统谱系中的地位。道统谱系内部又有两个逻辑关系,一是时间逻辑,一是传接逻辑,由此反映了出道与得道的先后及其传接的次序。而道统庙系,则是从礼制立场,对道统谱系中人物,进行地位高低的辨证。徐侨提出将子思由从侍地位升为与孔门十哲同堂,在历史上首次从道统庙系角度将子思地位抬到最高。徐侨的建议是在南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提出的,第二年,礼部也有相同建议,将子思升为十哲。而到了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度宗又封曾子、子思为国公,配享孔庙。与此同时,又将子张升跻十哲,从而完成了四配、十哲制度。①徐侨从道统立场,为子思的升祀找到一个最充分的理由,并得到理宗的认可,这也说明当时的朝廷已是完全承认了道统合理性。
回想在高宗的时代,情形远非如此。南宋绍兴六年(1136),陈公辅上疏高宗,以程颐为攻击对象,以程氏之说为“狂言怪语,淫说鄙喻”。表面上看,陈公辅是在抨击程学,但实际上是在撼动道统,虽然“道统”之名在当时还未确立,可“道统”之实已是公认。那么,高宗对于陈公辅上奏态度又如何呢?高宗批复曰:
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览臣僚所奏,深用怃然,可布告中外 ,使知朕意。[9](卷一百七)
高宗所谓“宜以孔孟为师”,显然是提倡人人皆应直接从孔孟元典中获取真知,而不必听信程颐等的再诠释。“宜以孔孟为师”的言下之意是不宜以程颐为师,这就伤及本以程颐为师的程颐的弟子们,故胡安国上疏申明:
士以孔孟为师,不易之至论。然孔孟之道久矣,自程颐始发明之而后其道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9](卷一百八)
胡安国所云“自程颐始发明之而后其道可学”。“发明”二字是关键,他从诠释学角度为程颐争得道统之名。这就告诉人们,道统其实就是层层积淀的思想叙事脉络。思想从元典出发,经由无数后人的“发明”而成长,然后形成浩荡之洪流。洪流现,而脉络成;脉络成 ,而道统立。那么,胡安国所谓程颐的“发明”到底是什么呢?徐侨自有他的解释。《家传》曰:
一日 ,讲毕。上言二程氏理学之纯,公奏:“自孟氏没而正学不传,至我本朝二程氏出,发挥义理 ,于是圣道涣然复明,诚前代所未有。程颢氏言‘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 ,此正道理源头。愿陛下于一念虑之微,一号令之出,必悉合乎天理之纯,而不使纤毫私欲杂乎其间。久久,自然纯一之心固,而精一之道得矣。”上曰:“正赖卿。”又曰:“二程氏之学,自濂溪来。”公奏:“论其发端,实自周氏,而其自得之妙,则有非师友所能与者。”上又及横渠之学,公奏:“臣尝言张氏谓性为万物一原,其知性矣;《西铭》之作,其知天矣。但其晚逃佛老,故立言间有未及二程氏之纯处。”上曰:“《西铭》却好?”公奏:“此其文之最纯者,愿陛下勿徒诵其言,而必有以行其言。事事合天 ,则君道尽矣。”公又奏:“二程氏宜从祀于夫子庙廷。王安石学术颇僻,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害政坏法,卒基靖康之祸,愿废勿祀。”[8]
程氏之学虽然承周敦颐而来,但徐侨认为“程颢氏言‘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此正道理源头”,这就是徐侨所谓的“发明”。“发明”是中国思想史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前述黄 、陈淳等都将朱熹纳入道统之嫡传,而到了徐侨的时代,他从道统的立场出发,则建议理宗将北宋五子和朱熹列入孔子从祀,《家传》记曰:
上欣然开纳,且谓:“李埴亦请并祀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公奏:“邵雍氏之学,推数以明理,未及诸先生之纯,愿亟俞李埴之请,先以五人列诸从祀。”[8]
至此,道统谱系由道学家内部的自我肯定 ,而演变成朝廷的官方肯定。道统由高宗时代的大受怀疑,到理宗时代的备受肯定,中间隔了近百年。因此,只有到了徐侨的时代,道统说以子思升祀和北宋五子与朱熹的从祀为起点,才正式宣告得到官方确认。这中间,徐侨功不可没。
总之,无论是道统谱系还是道统庙系 ,经由徐侨的努力,不仅突出了子思这一环,更重要的是,还将北宋五子以及朱熹抬进了孔庙 ,这就在国家祭祀层面上为他们在道统中的位置寻求到了制度保证。至此方可说,理学的官方化始告全面完成。
二、徐侨与南宋《论语》地位提升
目前,关于《论语》学史的研究,着重于《论语》文本的注释与流传,以及在各时代所产生的《论语》学流派和《论语》解说与诠释的时代特色。笔者认为,这其实只是《论语》学史的线条之一。单纯从学术角度去总结《论语》学史,只是《论语》学史的一个维度。广义地理解《论语》学史,其实还包括另外一个维度,这就是历代帝王们对于《论语》的接受态度、接受程度与接受事实。因为《论语》的地位升沉,往往与当朝的意见有莫大关系 ,而这些意见又间接影响到《论语》研究与诠释的学术走向。
汉唐以来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宋代始称经筵,置讲官以翰林学士或其他官员充任或兼任。宋代以每年二月至端午节、八月至冬至节为讲期,逢单日入侍,轮流讲读,经筵制度至宋而臻完备。宋初经筵,《论语》并未纳入讲读范围,而是以《礼》等经书为主要,如宋太宗雍熙四年八月己酉,“侍讲邢昺献《分门礼选》二十卷,上采其奏,得《文王世子篇》观之,甚悦”。而《论语》还主要是作为东宫教育的基本教材 ,这似乎与宋以前的《论语》教育差不多相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二载宋真宗曰 :
上谓王旦等曰:“朕在东宫讲《尚书》凡七遍,《论语》、《孝经》亦皆数四。”[10](卷七十二,P1635)
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三肇邢昺侍讲情况:
昺在东宫及内庭侍讲,说《孝经》、《礼记》者二,《论语》十,《书》十三,《易》二,《诗》、《左氏春秋》各一,据传疏敷绎之外,多引时事为喻,深被嘉奖。[10](卷七十三,P1675)
由东宫的《论语》教育到经筵的《论语》讲读,仁宗朝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乾兴元年(1022)二月戊午,真宗崩于延庆殿,仁宗皇帝继位才13岁,这个年龄正是接受东宫教育的时候,但他的身份却又是皇帝,这便给《论语》由东宫的资善堂①走向皇宫的崇政殿提供了契机。因为此时太后及宰臣对于仁宗的教育虽然仍采取东宫教育模式,但此时仁宗已是皇帝的身份,故模式虽为东宫模式,但形式却必须是经筵的形式,且地点不可能仍在东宫 ,而必须改在崇政殿。由于这个缘故,《论语》自然而然由东宫教材升格为经筵教材。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九云:
辛巳,(仁宗)始御崇政殿西阁,召翰林侍讲学士孙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冯元讲《论语》,侍读学士李维,晏殊与焉。初,诏双日御经筵。自是,虽只日亦召侍臣讲读。王曾以上新即位,宜近师儒,故令奭等入侍。上在经筵,或左右瞻瞩,或足敲踏床,则奭拱立不讲,体貌必庄,上亦为竦然改听。[10](卷九十九,P2303)
同上,“十二月甲辰”条又云:“诏辅臣崇政殿西庑观侍讲学士孙奭讲《论语》,既而上亲书唐贤诗以分赐焉。”[10](卷九十九,P2305)第二年,即天圣元年(1023)九月戊寅,仁宗又诏辅臣于崇政殿西庑观冯摘讲《论语》。此后,仁宗对于《论语》的学习持续不断,数年之中,给仁宗讲《论语》的有孙奭、冯元、赵师民、杨安国等,皆一时俊秀。由于东宫教育与经筵讲读结合在一起,《论语》到了仁宗朝在经筵中的地位渐隆,对此吴国武评曰:
仁宗年幼即位,乾兴元年到天圣元年,皇太后及宰臣将《论语》列为讲经之首。天圣二年,群臣继之进讲《孝经》。二书(尤其《论语》)从东宫、诸王教育之内容,转而为经筵进讲之书,对于宋儒重视和发挥《论语》有很大影响。[11](P441)
嘉祐八年(1063)三月辛未,仁宗崩,英宗继位,一沿仁宗故事,经筵仍讲《论语》。到宋神宗时,《论语》成为考试科目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十一云:
中书礼房请令进士试本经、《论语》、《孟子》大义,论、策之外,加律义一道,省试二道。……从之。[10](卷三百十一,P7538)虽然史籍不见神宗朝有关经筵进讲《论语》之事,但到了哲宗,因其10岁登基,事实上又将东宫教育与经筵进讲合二为一 ,于是《论语》再入经筵。从元丰八年(1085)到元祐二年(1087),三年中《论语》进讲未曾中断,《论语》也成为哲宗常备之书。在哲宗朝,进讲《论语》者有程颐②、孙觉、范祖禹等人。由于经筵进讲的推动,北宋诸儒对于《论语》的研究与意义发掘 ,在《论语》学史上掀起一个浪潮。这时期重要著作有邢《论语正义》、程颐《论语解》、范祖禹《论语说》等。因此,北宋《论语》学的兴起,与经筵有直接关系,这个问题其实值得作出进一步探讨。
南宋建立之初,高宗即下诏恢复经筵进讲,由此可看出高宗在战乱之年仍不忘重建经筵的决心与意志。建炎二年(1128)三月,高宗在扬州首开经筵,诏讲《论语》,侍讲者为王宾。绍兴五年(1135),高宗又“诏侍讲孙近、唐辉仍讲《论语》”[9](卷八七),足见他对《论语》的重视程度。自此以后,《论语》在经筵中进讲,已为常态。
宋理宗是一位非常重视《论语》的帝王,对此《宋史全文》屡有记载,如:“丁亥宝庆三年(1227)正月已巳,诏:朕每观朱熹《论语》、《中庸》、《大学》、《孟子》注解,发挥圣贤之蕴,羽翼斯文,有补治道。朕方厉志讲学,缅怀典刑,深用叹慕。可特赠太师,追封信国公。”[12](卷三十一)由此可知,宋代经筵之讲《论语》,到了理宗朝基本上是以朱熹的注本为准绳了。在这个背景之下,徐侨于理宗端平二年(1235)以76岁高龄,授工部侍郎,除集英殿修撰,提举佑神观兼国子祭酒、侍讲。为此吴泳①、洪咨龟②对徐侨的学行有很高的评价。那么,徐侨之任侍讲,所讲内容又为何呢?应该是《论语》无疑。吴泳撰《鹤林集》卷七《徐侨授兼侍讲制》证明了这一点。而据《家传》记载,更可明了:
翌日,御笔兼侍讲,公奏:“起居舍人蒋重珍犹为说书,臣秩卑不当躐居其上。且昨在山间温绎《语》、《孟》,若使备数晚说,或可上裨缉熙。”万分再辞,不允。[8]
《家传》中提到的蒋重珍 ,系无锡人,字良贵。宋宁宗十六年(1223)癸未科状元。理宗朝,授蒋重珍宝章阁直学士。为提醒理宗防止权枚旁落,蒋重珍曾进《为君难》六箴,被授任为秘书郎兼庄文府教授。端平元年(1234),蒋重珍力荐真德秀、魏了翁。蒋重珍兼崇政殿说书时,每起草奏章,必斋心盛服,理宗称其为人平实。徐侨言“臣秩卑不当躐居其上”,足见出他对蒋重珍的尊重。因此,徐侨提出,若实在要于经筵中说书,亦只可忝列晚说,因其“昨在山间温绎《语》、《孟》”,“或可上裨缉熙”。即便如此 ,他还是要“万分再辞”,但理宗最终“不允”。然而,就在此时,理宗却接着又下旨升《论语》为早讲。《家传》云:
有旨径升《论语》早讲。公奏:“既升《论语》早讲,宜以《中庸》、《大学》、《孟子》列于晚说。”[8]
这给我们一个重要信息:在此前经筵讲读经史,由于时间安排不同,或可反映出不同经史之不同等级与地位。而《论语》既升为早讲,一个“升”字揭示了《论语》此前可能都安排在晚讲之中。由于资料原因,我们尚不能够很清楚地知道宋代经筵讲读时早讲与晚讲具体内容的安排情况,但从“有旨径升《论语》早讲”可以推定,《论语》作为经筵讲读题材,从东宫教育到帝王教育,从晚讲到早讲,其地位到理宗朝被抬到最高。这使徐侨异常兴奋,他在理宗面前对升《论语》为早讲一事,就《论语》在当前的境遇作了一次痛快淋漓的借题发挥,《家传》载曰:
又谓:“《论语》一书,实孔门高第记夫子之微言至行,以著明圣道之大原,通此经则六经可不治而明。今科试乃附于诸经命题之末,而谓之小经。太学讲书,则博士正录讲六经而《论》《孟》不与。夫《论语》者彻上彻下之道,成始成终之学,今直使视为童儒之习,稍长则弃之,理学不明,始基于此。”[8]
在此,徐侨对于当今《论语》的境遇作了深刻分析,并从三个方面对现状表示了不满:第一,科试视《论语》为小经而附于诸经之末;第二,太学讲学,只讲六经而《论》《孟》不与;第三,就全社会而言,仍将《论语》视为童儒之习,稍长则弃,以故理学不明。从政治学术史角度来看,徐侨的批评将使我们对于《论语》在宋代之境遇作出新的认识 ,这也是当今《论语》学史研究最乏力的地方。那么,如何来改变《论语》的此种境遇呢?徐侨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家传》云:
仍下礼部国子监裁酌,凡科试命题、学校讲说,并与六经一体施行,庶使天下咸知陛下升崇此经之意,以开后学之良知,以垂万世之丕宪。[8]
正因为当时对《论语》的认识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偏差,才使得徐侨对理宗升《论语》为早讲的举措表示了极大的热情。更重要的是,理宗对于《论语》的认识,也超过了此前历代帝王的认识水平。《家传》载曰:“臣昨奉圣训,谓《论语》圣经,欲易以嘉名。”[8]理宗既然将《论语》奉为“圣经”,便产生了要将《论语》“易以嘉名”的想法,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徐侨这里。于是徐侨便提出恢复《论语》初名或更名《鲁经》的建议,《家传》云:
在昔此书谓之《鲁论语》以别《齐论语》,若因其旧称谓之《鲁论》或《鲁经》,亦述而不作之义。[8]
众所周知,《论语》之流传在先秦的邹鲁地区和南方楚国已有口耳相传和辗转传抄两种情况。从战国到西汉,中间虽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但《论语》的流传仍绵延不绝。汉初陆贾所作《新语》对于《论语》的引用已经很多,叔孙通在为汉高祖制定礼仪时也曾援引孔子之语。汉代《论语》传本,据《汉书·艺文志》载有《古》21篇,《齐》22篇,《鲁》20篇。三种本子在文字、章句上有一定差异,故在研习与传授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师说家法。但到了西汉末年,三家并行的局面彻底改观,《鲁论》独领风骚。自汉代以后,《论语》之传播与接受史,事实上就是《鲁论》史。徐侨说:“《论语》一书,实孔门高第记夫子之微言至行,以著明圣道之大原,通此经则六经可不治而明。”[8]这是他将《论语》视为高于六经的明证。既然如此,将《论语》恢复古名就理所应当了。在徐侨开出的两个“嘉名”中,理宗最后选择了《鲁经》之名,《家传》云:“上遂定名《鲁经》。事下省部见谓迂阔,不行。”[8]遗憾的是,徐侨这个建议被礼部给否决了,理由是“迂阔”。但稍后于徐侨的金华学者王柏却很认同《鲁经》之名,并作有《鲁经章句》。数百年之后,徐侨上奏更《论语》为《鲁经》一事成为清代一些知名学者的话题。俞樾《茶香室三钞》卷十四《鲁经》云:
国朝周中孚《郑堂札记》云:“《宋鉴》,端平元年,太常少卿兼侍讲徐侨奏:《论语》一书,先圣格言 ,乞以‘《鲁经》'为名,升为早讲。”从之。《论语》之名甚古,何必作此变更?后惟王氏柏有《鲁经章句》,他人莫之从也。”[13](卷十四,P1186)
周中孚的原话见于其《郑礼堂札记》,云:
《论语》之名甚古,何必作此变更?况鲁为国名,岂足以概仲尼微言。《春秋》本鲁国之史,尚不可改为《鲁经》,施之《论语》,尤为失当。后惟王氏柏有《鲁经章句》,他人莫之从也。至近代朱竹土宅集中犹沿此名,难乎免于吊诡之讥矣。[14](卷一)
周中孚对徐侨奏更《论语》之名的批评,措辞比较激烈,但也有一定道理。需要指出的是,用《鲁经》来代替《论语》之名者,其实不止王柏。在当时还有喻品。《经义考》卷二百二十一《论语》十一就记载有喻品的《鲁经》,不过与王柏的《鲁经章句》一样散佚了。周中孚所提到的朱彝尊也喜欢用《鲁经》一名。如朱氏《上山东巡抚张公书》云:“《鲁经》曰:见义不为无勇也。”[15](卷三十三)又朱彝尊《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刑部尚书李公神道碑》云:“《鲁经》有言:一则以惧乌鸟之私 ,时萦寤寐也。”[15](卷七十一)再朱彝尊《文学沈君墓志铭》云:“《鲁经》取人必也狂狷,有所不为,斯择之善。思我故人,庶几可入作者之林,独行之传者乎?”[15](卷七十四)所谓《鲁经》就是《论语》。看来朱彝尊还是喜欢用徐侨提出的《鲁经》来称《论语》。他对于徐侨意见之尊重,在《谒泰伯庙四十韵》诗中有一句,可见其态度。诗云:“化被仁风厚,经传至德称。”[15](卷二十)该诗句就是咏徐侨 ,为此 ,朱彝尊诗自注云:“宋徐侨请更《论语》名为《鲁经》。”朱彝尊为何一直要将《论语》沿用徐侨提出的《鲁经》之名,其用意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
三、徐侨对人心道心的认识
南宋淳熙二年(1175)五月底至六月初,朱熹与陆九渊等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举行了一次著名的哲学辩论会,史称“鹅湖之会”。鹅湖之会以后,信州理学快速发展起来。在信州理学集团中,从学朱熹的人士有赵蕃、徐斯远、陈文蔚、余大雅、徐大猷和徐子融等,此外汪应辰、韩元吉、徐安国、王时敏等为朱熹同调。朱熹逝世后,其后学在信州仍然活跃,陈文蔚就是其中代表人物。陈文蔚(1154-?),字才卿,自号克斋,信州上饶人,尝举进士,师事朱熹,讲读铅山,隐居不仕。其学以求仁致诚为本,以躬行实践为事,有《克斋集》行于世。陈文蔚理学思想之表现,除了其9篇讲义外,主要就是他与其他理学家往还的论学书信。这些书信在《克斋集》中共有68通,其中与徐侨的书信有6通。徐侨于绍熙五年(1194)任上饶主簿,请陈文蔚馆于家中以教授子弟,故二人关系密切。因为徐侨的理学论著已经很难得见,故陈文蔚与徐侨论学的书信尤显得特别珍贵,从中亦可窥见徐侨的部分理学观点。
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二月,徐侨江东罢归,居义乌家中,陈文蔚从上饶有书来,与徐侨讨论“中庸不可能”问题。“中庸不可能”是南宋学者经常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朱熹、叶适对这个问题都有自己的理解。从陈文蔚信中可知,徐侨此前对“中庸不可能”曾与陈文蔚有过商讨,但具体内容已不可知了。嘉定十四年(1221)三月,徐侨继续居义乌家中。陈文蔚上饶书来,与徐侨论“性善”。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陈文蔚从上饶又有书来与徐侨论“人心道心并性理”说。紧跟着,陈文蔚又从上饶寄来《又答徐崇甫说》。绍定三年(1230)徐侨77岁,而此年陈文蔚已80岁高龄。该年四月至六月间,陈文蔚讲学于信州州学。徐侨对文蔚《信州州学讲义》表示异议,文蔚《答崇甫所辩讲义二条》,有关于“惩忿”“窒欲”和“仕”“学”的讨论。总体来看,陈文蔚与徐侨论学书信,时间跨度有10年,而这10年正是徐侨罢归居家之时。考察文蔚与徐侨有关论学内容,多涉及命、性、心、中、诚、仁等理学基本问题,诚如王祎在《义乌宋先达小传·徐侨》中所言:
其在人君前,论学则曰在正心,论治则曰在知人,其教学者以命、性、心、中、诚、仁为穷理之要 ,九思、九容为主敬之本。[16]
但综合来看,他们论析的重点仍在“人心”与“道心”上,故我们就此稍作分析。众所周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十六字心传,见于伪《古文尚书·大禹谟》。自北宋以来,“人心”“道心”常作为重点命题被加以讨论,是有其缘由的。陈来谓:“以理节欲本来是孔子以来儒家哲学的固有思想,宋儒尤其注重培养理想人格,要求提高道德自觉,努力使道德意识最大限度地支配人的行为。为了这一目的 ,理学从二程起,大力宣讲伪《古文尚书》中所谓‘人心'‘道心'问题,在这一点上朱熹是二程的继承者。”[17](P185)朱熹论人心道心最集中的表述在《中庸章句·序》。在朱熹看来,心其实只有一个,而又要分作“人心”“道心”来说,只是因为前者生于“形气之私”,后者得于“性命之正”,此皆“为知觉者不同”而已。故其云:“只是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18](卷五十六,P2680)又云 :“此心之灵 ,其觉于理者 ,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19](卷七十八,P2009)如此看来,“人心”“道心”无非只是一体两分。心觉于理,又觉于欲,觉于理者为道心,觉于欲者为人心;故两分之中,若以“人心”与“道心”相比较,似乎“人心”地位要见差一些,且受到道心的主宰。朱熹将道心比作是舵,船若无舵,纵然而行,有时入于波涛,有时入于安流,不可一定。惟有一舵以运之,则虽入波涛无害。此间人心与道心的区别,则分明不是一体两分,而是主次之分了,这样就有矛盾。对此 ,当时已有弟子指出,后人也多认为朱熹人心道心说存在义理矛盾。但钱穆先生发现朱熹对自己出现的矛盾后来作出过修正,其云:
朱子后来即不赞成自己这一说。因若如此说之,则道心为主宰,人心供运使,在一心中明明有了两心对立。朱子论宇宙,理气非对立。论理,善恶非对立。论气,阴阳非对立。凡说成两体对立者,皆非朱子说。故人心道心,非有两心,只是在一心中有此区别。此一区别,贵能浑化,不贵使之形成敌对。故曰:“有道理底人心,便是道心。”又曰:“以道心为主,则人心亦化为道心。如《乡党》篇所记饮食衣服,本是人心之发,然在圣人分上,则浑是道心。”……朱子思想,尽多先后递变处 ,在先如此说,在后如彼说,大抵总是后胜于前,此乃朱子自己思想之转进。[20](卷五 ,P1598)钱穆是比较重视朱熹思想前后变化的学者,故他的《朱子学提纲》常常能够在细处发微,给我们勾勒完整的朱熹思想影像。
以上用较长篇幅介绍朱熹“人心”与“道心”关系论,就是要由此找到徐侨“人心道心并性理”之说的由来。从陈文蔚与徐侨数通书信争论的问题,重点在理学的经典命题心、性论上。笔者认为徐侨的理解并没有错。无论“人心”还是“道心”,只是一个“心”,这个“心”即是“性理”。这一点钱穆辩得最明白。钱穆认为朱熹解释人心与道心有前后之差,在早期朱熹认为“人心”“道心”有别,但后来却不赞成自己这一说法。大抵陈文蔚继承的是朱熹早期观点,而徐侨则继承朱熹后期观点,这就是二人对朱熹接受层面之不同。徐侨“人心道心并性理”其实就是朱熹晚年的立场,徐侨曾诫叶由庚曰:“心体之流行,即天运之流行也,无乎不通,而塞之人其物矣。”[21](卷十)徐侨的心性说在南宋后期作为朱熹正宗观点的代言者和守护者,有较大影响。据《宋史·徐侨传》云:“侨尝言比年熹之书满天下,不过割裂掇拾以为进取之资,求其专精笃实,能得其所言者盖鲜。故其学一以真践实履为尚。”[22](P12614)这在当时学者中是非常难得的。徐侨虽然从未入川,但其学术思想却为四川学者所敬仰。端平二年(1235)四川学者阳枋,慨然万里,由川入京,“谒文公门人毅斋徐先生 ,闻人心道心之说”[23](卷十二),“徐以所得考亭存心之要语之曰:‘道心为主,人心听命,元只是一个心。人心不流于人欲,道心不流于虚无,便是察得精了。心与道一,一则不二,此便是中。'”[24](卷十二)阳枋于是欣然有得。徐侨对“中”的解说,联系陈文蔚书中所引,谓“惟危惟微者,俱未可以言中;曰惟精惟一者,必如是所以为中。若便指人心为人欲之私,其意义无乃太疏浅”[25](卷一),由此可知,徐侨“人心道心”之说是其学术的根本。明永乐中,有人还将其性命心说画成图谱 ,名曰《性命心说诸图》①,以便更直观地了解。可见徐侨性命心说,至少在明代还引起人们的兴趣。
[1]孙复 .信道堂记[A].孙复.孙明复小集[M].四库全书本.
[2]石介 .杂文[A].徂徕石先生全集(卷七)[M].清康熙五十六年刻本.
[3]程颐 .明道先生墓表[A].程颢,程颐.二程文集(卷十二·伊川文集)[M].四库全书本.
[4]费密 .弘道书(卷上·道脉谱论)[M].民国九年怡兰堂刻本.
[5]朱熹 .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M].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6]黄 .黄勉斋先生文集(卷八·朱子行状)[M].丛书集成初编本 .
[7]陈淳 .北溪字义(卷下·严陵讲义·师友渊源)[M].熊国祯,高流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8]徐侨门人.徐文清公家传[M].影明抄本.
[9]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四库全书本 .
[1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1]吴国武 .北宋经筵讲经考论[A].北京大学中文系.北大中文学刊2010[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2]佚名.宋史全文[M].四库全书本.
[13]俞樾.茶香室丛抄·三抄[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4]周中孚 .郑礼堂札记[M].清光绪刻本.
[15]朱彝尊 .曝书亭集[M].四部丛刊影清康熙本.
[16]王祎.王忠文集(卷二十一·义乌宋先达小传·徐侨)[M].四库全书本.
[17]陈来.宋明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8]朱熹.朱子全书(第二十三册)[M].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9]朱熹.朱子全书(第十六册)[M].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20]韩复智 .钱穆先生学术年谱[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21]宋濂.文宪集(卷十·叶由庚传)[M].四库全书本.
[22]脱脱,等.宋史·列传·徐侨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3]阳枋.字溪集(卷十二·附录·纪年录)[M].四库全书本.
[24]阳枋.字溪集(卷十二·附录·有宋朝散大夫字溪先生阳公行状)[M].四库全书本.
[25]陈文蔚 .克斋集(卷一·又答徐崇甫说)[M].四库全书本 .
[责任编辑 许婴]
An Exploration of XU Qiao's Thinking of Neo-Confucianism
CHENG Ji-hong
(School of Humanities,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Zhoushan Zhejiang 316002,China)
XU Qiao,a Neo-Confucian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was an early prophet of ZHU Xi's Neo-Confucianism in Zhejiang,an active promoter of the officialization of ZHU Xi's Neo-Confucianism during the period of Lizong of Song Dynasty,and also a very important scholar who continued to carry forward ZHU Xi's study of human nature in the late Southern Song Dynasty.Because his works were hardly passed down,his thinking of Neo-Confucianism was implicit.This article,according to Jia Zhuan printed in Ming Dynasty and other historical materials,tries to explore and analyze XU Qiao's thinking in terms of Confucian Orthodoxy,imperial speeches,and human nature.
XU Qiao;Neo-Confucianism;exploration
B244.7
A
1004-2237(2015)02-0009-08
10.3969/j.issn .1004-2237.2015.02.003
2015-04-01
程继红(1962-),男,湖北麻城人,教授 ,研究方向为宋代文学和朱子学。E-mail:cjh621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