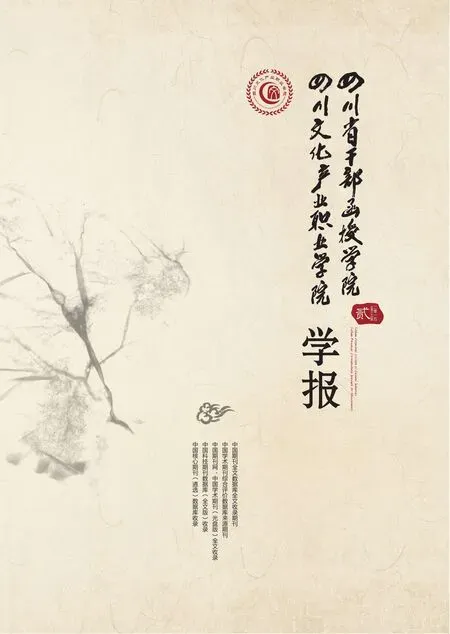论巴金与郭沫若的女性题材书写
2015-04-10马云鹤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四川成都610213
马云鹤(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四川 成都 610213)
与女作家故意遮蔽全知视角不同的是,男作家在很多时候,在全知叙述视角下,模仿女性视角,揣测女性心声而进行创作,想要替女性发声,替女性鸣不平。本文把视线聚焦于五四时期的巴金和郭沫若,通过对他们作品的文本分析来对比异同。
一、巴金的女性题材创作
巴金为我们塑造了很多著名的女性形象,他一直带着对女性关怀与同情的视角描写那些深受封建大家庭和礼教剥削压迫的女性。以其代表作《家》来说,其中的众多女性形象都寄予着巴金的同情和关注。作者把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女性纳入作品,他创作的女性形象往往是理想与现实的结合,这些形象或多或少都承载着巴金对完美女性的期许。
《家》中描写的女性,不论身份地位如何,无一例外地受到封建专制大家庭的迫害。如钱梅芬,一个美丽、善良的少女,她一直期待着与自己的意中人结成美好的姻缘,而家长的一时任性,就使她的愿望成了泡影,她虽然另嫁他人,但是她终身都浸润在错失真爱的痛楚中,最后抱恨而死。贤良大方的瑞珏,凭着自己的善良、贤惠,深深地爱着自己的丈夫觉新。虽然她身为高家的大少奶奶,也免不了受到封建势力的迫害。她临产时,高家为了避免“血光之灾”而把她赶到城外去分娩,最后瑞珏只有在难产中含泪而死。聪慧美丽的丫鬟鸣凤,她带着少女的懵懂和觉慧自由恋爱,却遭到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阻止,后来被逼着嫁给冯老太爷为妾,为了守护她心中活着的唯一希望爱情,她选择了投湖自尽。在高家,从身份卑微的丫鬟,到地位尊贵的大少奶奶,都无一例外地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孟悦和戴锦华说:“在五四时代,老旧中国妇女不仅是一个经过削删的形象,而且也是约定俗成的符号,她必须首先承担死者的功能,以便使作者可以审判那一父亲的历史。”[1]
在众多的女性形象中,因为鸣凤提早退场,留白的意味最大,作者用了全知视角来审视她,对鸣凤心理进行揣测。鸣凤被强制许配给冯乐山当小妾,打算投湖前也有大段的心理描写。鸣凤的女性意识因为深深地掩埋在巨大的奴性下面,所以没有来得及发芽就萎败在封建专制培养的奴性思维里。正是因为有不能逾越的性别差距,由男性作家描写的所有女性人物的心理都是通过揣测获得的。
通过作者根据鸣凤处境而揣测出的心理,我们不无悲哀地发现,作者对人物心理的揣测也是根据人物的阶级来进行的。因为鸣凤是一个丫鬟,所以她想要逃到的美好境遇就是像小姐一样。而已经身为小姐的琴,想要逃到的美好境遇就是像个男人一样。在巴金的笔下,这些女性人物构想的美好境遇的阶梯,也是按着阶级的顺序来搭建的。她们能看到的最远的地方,也不过是像个男人一样。而像个男人一样之后呢?还是如戴锦华和孟悦所说的那样,泯灭了性别,使女性这个词汇彻底消失在地平线以下了。
巴金是位充满了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女性悲惨命运的哀挽。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在那些被作者寄予了深刻同情的女性群像后面,作者指出的出路,也只是“死去”或者“像个男人一样。”但是,在前面已经阐释过了,无论是死去还是扮演男性都不能够获得属于女性自己的幸福。在《家》中,以充满了反抗思想敢于与旧家庭决裂的觉慧,在面对自己的爱情,也只是“他还不能不想到鸣凤,想到鸣凤时,他还不能使自己的心不颤动。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一定要拉住鸣凤。不,事实上经过了一夜的思索之后,他准备把那个少女放弃了。”而这源于“有进步思想的年轻人的献身热诚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2]这个在家中代表了正确价值观的正面形象觉慧,爱情对他而言也只是增加他身上“进步思想”光华的工具,当这份爱情违背到他的小资产阶级自尊心时,他还是会选择放弃。
学者李玲曾论到“作家和研究界长期把鸣凤投湖前的这种牺牲自己,成全爱人的心理与她对自我生命的怜惜混搅在一起,一股脑地予以圣洁化,诗意化,毫无辨析与批评,实际上是作家和研究界自身爱情观念现代性匮乏的表现。孰不知,前者不过是男性中心意识在女性形象上的投射,是性别等级意识的现代延续;后者才是男性作家对女性生命本体价值的爱惜,尊重,是现代人道精神的体现。”[3]
正是作者潜意识里的这种男性主体意识,把他笔下的人物鸣凤和觉慧拉开了距离。不但鸣凤觉得她和觉慧是不同世界的人,觉慧也一直觉得自己和鸣凤是不同世界的人。他经常想,如果鸣凤处在琴那样的位置,他们之间就不会这样障碍重重。但是假使,鸣凤处于琴小姐的位置,他们之间的爱情就能成功么?在这篇小说的第二十八章作者借助觉慧的梦境告诉我们,即使鸣凤是一个小姐,他们之间的爱情也还是会失败。在那个梦里,鸣凤突然找到一个很有钱的父亲,但是他们仍然不能摆脱要被鸣凤父亲追赶,最后不得不分离的命运。
为什么觉慧在鸣凤投湖自尽以后,会做这么一个梦呢,那是因为在觉慧的心里,他始终觉得自己和鸣凤的爱情没有成功,只是因为她们的阶级悬殊太大了,而不是因为他在内心深处,并没有把鸣凤当成一个有独立灵魂的性别个体存在。他只是把她当成一个被封建大家庭囚禁的需要他同情的物品。鸣凤在他心里的地位甚至比不上琴,琴还可以作为他们与封建礼教斗争的盟友。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巴金的阶级局限性。
在这个大家庭里遭到盘剥的女性不只有鸣凤,李瑞珏,梅小姐,这些已经处在鸣凤期盼境遇中的女性,最后都是悲惨收场。她们无一不对自己所爱的男人全力奉献,无所要求,只要自己深爱的男人还站在那片大家庭的阴翳之下,她们也会奋不顾身地投身而去。在这个小说中,女性只有两种出路,在等待被男性同情的过程中默默死去,或者像许倩如那样剪短头发,化妆成男性。我们在整篇小说中的众多女性形象中,依然找不到一个可以代表女性完整灵魂绽放的清晰面孔。而在前面已提及,这些女性都代表了巴金心目中对完美女性的想象。或者部分代表了他对完美女性的想象。这些女性,像鸣凤、瑞珏和梅那样忍辱负重,能够为自己喜欢的男人奉献所有,甘于淹没于封建大家庭的暗影之中,或者像琴那样,拥有新思想,要和自己喜欢的男性并肩作战,去推翻封建专制。
这些女性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天使的化身,所以他们是作者寄予同情的对象。李玲在《天使型女性——男性自我拯救的道具》中总结道:“男性作家创作中的女性形象,首先表现的男性对女性世界的价值判断,同时还可能还以性别面具的方式曲折地传达着男性对自我性别的确认,反思和期待。”[4]“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温柔、纯洁、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天使型女性形象,便是这类强大而虚假的女性群像之一……她们不过是男性启蒙、革命时代依然蒙昧从夫的封建妇德典范。她们所尊奉的奴性化的爱的哲学,慰藉着受难中、奋斗中的男性主人公;她们受难甚至于死去的悲惨命运,成为男性叙事控诉罪恶社会、封建家庭的有力证据;她们的出走、新生,表达的也只是子辈男性、受压迫阶级男性拯救自我的希望。文学作品中天使女性形象的存在,独独遮蔽了女性自己的生命经验,失落了女性的主体意识。这从性别意识角度暴露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不足的价值缺陷。”[5]
巴金作为一个深具人道主义精神的男性作家,当他对女性的日常命运投以关注和同情的笔触时,他试图软化他的男性视角,以女性的视角来观察世界,所以他用自己的揣测构建出了女性的内心世界。但是这样并不能够帮助他消除掉身为一个男性的主体意识。这些出现在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还只是作为一个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作者控诉旧社会的证据,作者并没有真正从女性的视角去关注女性的真实命运,而是在这些受苦受难的女性身上投射出作者的男性主体意识。
作者正是以化妆成女性视角的男性视角,在性别关系上维护了中国传统的夫权秩序,把符合男性理想的女性纳入启蒙革命这一历史进程当中。所以我们不得不说,虽然巴金为我们营造了一条落英缤纷的芳香小径,但这条小径并没有把我们领到我们原以为可以到达的地方。那禁闭了千年的女性灵属之地,还在那遥远的彼端,与文字绝缘,无论你以全知,还是非全知的视角指认,它都只是远远地漂浮在那小径的彼端,好像卡夫卡笔下的城堡,看得着,却依然无法触碰。
二、郭沫若的女性题材创作
与巴金取材于现实,力图靠塑造真实的女性形象来沟通男性与女性之间那巨大的性别鸿沟相比,在五四这片浩淼的文学星空里,还有半边星球与巴金遥相呼映。与一直奔走在大街上,靠撷取生活浪花来创作的巴金相比,在这个星球的另一端,有另一个人,施施然俯身在过往的历史长河里,或者抬起头从广袤的星空里,采撷能为他言说心声的女性形象。他塑造的女性形象要么是出现在历史剧中,要么是出现在神话里。比如王昭君、聂萦、蔡文姬,还有“女神”。
与巴金笔下的女性形象从出生起就带着“死者”的使命不同,郭沫若笔下的女性形象更像是化妆成了女性的男人。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个个勇往直前,在历史深处的,就要拨开历史漫卷的珠帘,露出坚韧不拔的面容;在神台上的,就要打破壁龛从神台上下来,创造新的光明;得了当权者恩宠的,就要把当权者的恩宠视作蔽履,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郭沫若笔下的女性形象,时间没有障碍,阶级没有特权。
我们以王昭君为例。在郭沫若笔下,王昭君不但拥有倾城美色,还耿直勇敢,她的耿直、勇敢正是投射了“五四”时期人的觉醒,表现了一种维护人的尊严的个性主义。她扇了无耻画师毛延寿的耳光,她也拒绝了皇上的恩宠:“你可以强索良家女子来恣你的奸淫……”。叛逆大胆,不畏权贵,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是郭沫若笔下王昭君的特点。我们不难发现,她实质上是“五四”时期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在古代美女身上的附丽。这个人物形象,其实是五四众多追求人权的青年人的缩影。我们又一次在这个女性群像丛生的文本中,与女性独特的性别气息擦肩而过。那游移而过的微弱的披着美丽女性外表的影子,只一瞬间,这个影子就冲破了,那条划分性别的界限,游弋到象征男权的另一边。戏散了,只留下扮演者尴尬地留在舞台上,卸妆做回男人,还是做一个披着新时代新思想女性华美外衣,继续做个斗士?这是一个问题。
与巴金为人物贴阶级标签不同,郭沫若的相关创作,其实是为了帮助这些有着男性特质的人物化妆成女性。五四是一个以解放思想为标杆的时代,谁最需要解放,当然是那些一直被压迫在最底层的女性才最需要解放。于是,历史转了一个圆圈,文字也经历了一场性别的轮回,我们妄图在男性全知视角下解套的女性灵魂,又一次被迫穿上男性的外衣,贴上了阶级的标签,又一次陷入大多数中国女性无法摆脱的花木兰境遇。
因为郭沫若是一个紧跟时代的作家。他的书写很多是为了歌颂新时代的风潮。所以我们在郭沫若身上,看到了过度政治化的女性书写,虽然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女性群像,而且他也一直高举女性图腾,但是正是因为郭沫若书写方式的过于阔大与紧随时代风向标,使得他的作品失却了女性视角的柔软与琐碎。也使得郭沫若对女性人物内心无暇顾及。所以虽然他的作品总是以女性为主要人物,但是他笔下的女性人物都是豪情万丈,锋芒毕露,都是经过化妆的男性的化身。
正是因为这样过度政治化的书写,反而遮蔽了女性的真实的生命经验。郭沫若笔下的女性人物都带着花木兰的影子,她们应时而生,是时代洪流中象征着为自由而战的女性战士的化身。所以这些经过化妆的女性人物形象,并不能帮助我们探测到广大的生活在真实生活中的女性的心路历程。于是,我们看到,无论是巴金还是郭沫若,虽然他们为我们现代文学创造出了一大批光辉的女性群像,但是这些女性人物并没有逃脱男性作者主体意识的阴翳。
就女性书写而言,巴金和郭沫若好似两个分割的半球,他们以现实和虚幻两种方式接近了那看似无限接近的女性心声。这两个象征不同风格的半球,用他们对女性的悲悯,来书写女性的心声。
五四时期,真正的女性文学的发展却走得异常艰难。无论是女作家贴近女性自身经验而进行地半遮蔽视角描述,还是男性作家进行的全知视角描述,对中国沉睡千年的女性性别的指认,都没有达到我们渴望到达的地方。毕竟千年的时光沉淀下来,那些存留在内心的礼教的条条框框本就不容易破除。但那些男作家在同情和悲悯心情下进行的替女性发声的尝试,还是让人觉得尊敬。
但是毕竟时代的洪流太巨大了,那些经过模仿的脆弱的细小的女性视角,太容易被时代洪流冲散,使得他们笔下的女性难免沦为凸显男性主体性的附属品。无论是巴金们还是郭沫若们,他们笔下的女性形象,都免不了成了时代洪流中奋勇泅渡的女性英雄,她们身上肩负着构筑新时代女性英勇形象的重任。
所以无论是巴金还是郭沫若,都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他们试图以权威全知视角来展现女性个体经验的行为,并不能弥补女性作家在写作时受困于性别困惑而自愿遮蔽一部分女性经验带来的缺憾。他们对女性性别的指认,虽然失败了,但是作为文学版图上两颗闪亮的半球,谁也不能抹杀他们为整个中国文学版图曾经带来的光芒。
[1]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2] 巴金.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4][5] 李玲.天使型女性——男性自我拯救的工具[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