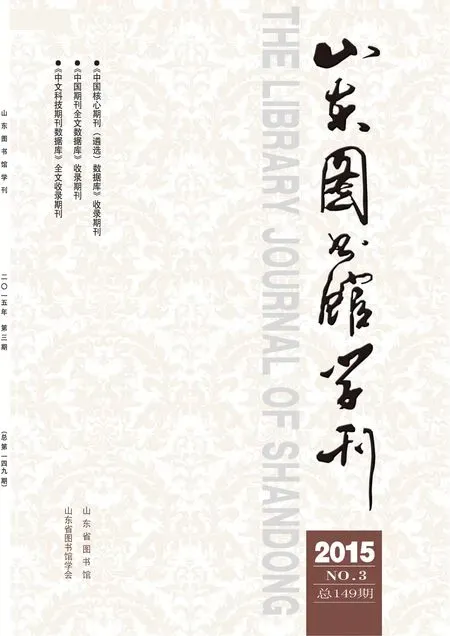寄情山海人文:于志斌的《山思海韵》
2015-04-10孙艳
孙艳
(海天出版社,广东深圳518000)
寄情山海人文:于志斌的《山思海韵》
孙艳
(海天出版社,广东深圳518000)
深圳海天出版社编审于志斌先生的《山思海韵》分为上、下两辑。上辑“江淮行记”是对江淮大地历史文化的走读札记,下辑“咏海诗札”是阅读历代歌咏海洋的诗歌札记。作者生长在江淮大地的庐陵,后客居南海之滨的鹏城,对山对海俱有深情。我揣测这是本书书名的由来。
就便向作者求证,方知书名的真正由来:书房背山面海。“写字还是对着海比较好”,于先生脸含笑意。到底是文人性情,文字流露生平趣尚不说,对写作环境也相当讲究,讲情求趣。细想也不奇怪。于先生单近几年就连续主持了《中国玉器通史》《中国花文化史》等书的出版,固然是工作所需,这里头当也有性情之所近。好古玩,好花鸟,好山水,全是文人的趣尚。
我常常觉得,中国的读书人,大抵是乐山好水的。但钟情山海,其审美与感受之深浅,实与文化修养有关。于先生的父亲是老报人,当过省报老总。他爱买书、会读书、好藏书、能写书,1966年“文革”初起时还冒着风险,往家捎带《红字》《约翰·克利斯朵夫》《基督山伯爵》《罪与罚》《红与黑》《茶花女》《飘》《巴黎圣母院》《人间喜剧》等外国文学名著。作者正是在这样一个书香家庭中长大。他十一、二岁就读了其父带回家的若干名著,在大学本科期间开始发表文章,并养成记日记和专题阅读的习惯。在《山思海韵》成书前的二三十年,就开始搜集前人歌咏海洋的诗歌。
专题阅读融入了作者的精神生命,“我以为自己的文字能够沉淀下来,并集腋成裘,专题阅读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另一个起大作用的,当是工作中的有心。“在审读《深圳掌故》一稿中获得新知,诗歌中的‘屯门’是唐代的军事重镇,在史册中名气很大”,由此得知,“屯门积日无回飓”,原来刘禹锡的《踏潮歌》是抵达深圳沿海时所作,“我不禁很是兴奋”。编辑工作和人文趣尚相互成就,多好。
下班回家专题阅读、写字,编辑工作也来成全。作者学养深厚,纸上山海了然于心,潜意识中都飘荡着五绝七律平平仄仄,《山思海韵》中,或诗或词,或联或赋,旁征博引,解读一步跟一步不马虎,转弯处亦驾轻就熟。
走访江淮有仙名山,心中荡漾的是儒释道传统文化;欣赏历代咏海诗歌精品与名作,关照的是海洋文化、蓝色文明。于先生说,年轻时曾立志著传世之作,现年岁渐长,心意淡了。这是年长的周全之辞吧,从《山思海韵》来看,情怀与壮志依然。对此,张合运先生的《序》中有洞察:于先生的书写,以“沉静的目光,回溯历史,遥望传统文化长河中的绵延灯火,缅怀这些诗篇中我们祖先的人格光辉和思想星光,引发我们对历史、对文化精神的回眸与反思,激励我们审视与思考前行之路”。诗词联赋,儒释道,蓝色文明,《山思海韵》中处处是文化,读一读,不管记不记得住,总是受点熏陶。
对我来说,这些都很要紧。
可是,对我来说,最开心的,是想到作者与山海、与自然对话的那种精神之乐。仿佛“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深圳,窗外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这一份乐,当可应付窗外的急促混乱。这一份乐,就够人留恋了,旁的不用。
孙艳,深圳海天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