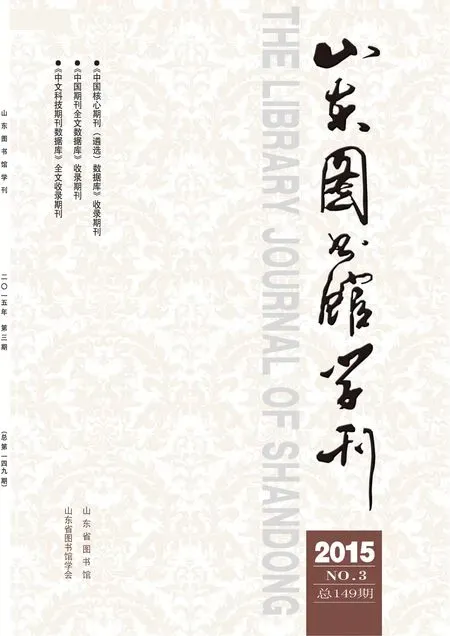和刻汉籍与中国刻本之比较
——以日本江户时期与中国清代之刻本为对象
2015-04-10郑晓霞
郑晓霞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200241)
和刻汉籍与中国刻本之比较
——以日本江户时期与中国清代之刻本为对象
郑晓霞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200241)
刻本汉籍在中、日两国都是重要的古籍版本类型,相互之间虽然有很深的历史、文化渊源,版本形态也有诸多相似之处,然本质上却是打上很深民族文化烙印的独立文化遗产,因此,在版本学研究中不能混为一体。本文以中国清代与日本江户时期的刻本汉籍为对象,对这一观点进行阐述。
刻本汉籍清代江户时期比较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对于精神文化领域的热情与投入不断增长,文化遗产的传承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受益于此,建国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备受冷落的古籍开始得到重视,从藏本保护到版本研究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国内的古籍收藏和研究已经突破了传统版本学仅限于中国古籍的藩篱,开始将域外汉籍即古代受中国文化影响较深的朝鲜、日本及越南刊印的汉文书籍纳入关注的范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笔者在长期的古籍编目工作中,不仅接触了众多中国古籍,也遇到了相当数量的日本刊汉文书籍,获得了一点对这两类古籍的粗浅认识。本文选取中国清代与日本江户时期的刻本汉籍为对象,通过对比,以期揭示出中日古籍各自独具的基本特点,藉此与业界同仁进行交流。
1 研究“对象”在版本学中的典型意义
大凡接触过古籍的人士,对中国古籍的刊印方式、形制特点、主要版本类型都有基本的认知,但对于日本古籍,除了少数专业人士,则往往知之甚少,因此,在本文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先对日本古籍作简要介绍。目前有关古籍版本学的论著中,对于日本古籍,普遍采用的名称是“和刻本”(不限于刻本,活字印本、石印本、影印本、珂罗版印本等均包含在内)。“和”,即日本。和刻本中,按内容通常又分为“汉籍”准汉籍”及“和书”三大类。具体到这三种类型书籍的定义,学界则存在不同的看法。[1]笔者在综合各家观点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分别作出定义。所谓“汉籍”,指的是日本刊印的中国典籍,包括附有日本人用汉语注解的中国典籍。所谓“准汉籍”,指的是日本人刊印的本国学者用汉语撰写的各类著作。所谓“和书”,指的是日本人刊印的用本国文字撰写的书籍。本文选取和刻本中的“汉籍”“准汉籍”为研究对象,统称“和刻本汉籍”。本文确立中国清代与日本江户时期之汉籍刻本为研究对象,在古籍研究中具有以下典型意义:
1.1“刻本”具有的版本学意义
在中日两国的书籍刊印史上,都曾出现过诸如雕板、活字、石印、影印、珂罗版印刷等版本类型,然就影响而言,任何一种类型,都不能动摇刻本的历史地位。首先,刻本是个人撰著第一次实现批量性复制的成果,也是最早具有现代书籍概念内涵的版本类型,在两国文明发展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次,刻本是两国书籍刊印史上活跃时间最久的版本类型。从目前两国存世古籍看,雕板印刷都已经活跃了上千年的时间,这样强盛的生命力,没有任何一种版本类型能与之相媲。
第三,刻本是中日古代最多刊印的版本类型。从两国存世古籍看,刻本占了绝大多数。存世时间也很漫长的活字本今天在版本界之所以更为珍贵的现象,也反衬出刻本的普及程度之广。
1.2汉语古籍代表的版本学意义
尽管中日两国的古籍类型并不只有汉语古籍一种,然就版本学而言,最具影响力的依然是汉语古籍。首先,就存世古籍数量而言,汉语古籍是两国最主要的版本类型。
其次,汉语古籍因为采用了共同的语言文字,使得中日两国各自独立的古籍版本学具有了最关键的契合点,从而相互交流,将研究扩展到更为广阔的领域。
1.3“中国清代”与“日本江户时期”在古籍版本学中的典型意义
严格意义上,中国清代起于顺治元年(1644)清世祖即位,迄于1912年溥仪退位,历时二百六十八年。日本江户时期起于庆长八年(1603)德川家康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在江户(今东京)开设幕府,迄于庆应三年(1867)大政奉还,历时二百六十四年。两个时代在时间上具有几乎完全的一致性。从版本学的角度看,这一时间段是两国各自出版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更是雕板印刷业最辉煌的时期。主要表现在:
(1)刻书机构最多。首先是清王朝,在经历了明末大乱之后,统治者为了重建统治秩序,特别强调思想教化的作用,图书出版作为传播思想文化的主要渠道,自然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清王朝不仅秉承唐宋以来历代王朝的传统,在中央设立刻书机构,大量刊刻经过审核的书籍,还将这种做法延伸到地方政府。特别是同治年间,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在各地广设官书局,大量刊印传统经史典籍。与此同时,在崇尚文治的国策之下,清代知识分子普遍精研学术,致力科举,私人著述成为风气,私家刻书与书坊刻书也极为兴盛。以北京为例,据统计,自清中叶到民国初年,仅琉璃厂就有书坊62家,有一时期同时开业的书坊竟超过300家。[2]
再看日本,江户时期幕府“定宋学为官学,第一次正式把儒学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对于中国儒家典籍的需要急剧增加。同时,由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庶民文化发达,对中国通俗文化显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亦使汉籍的需求量大量增加”。[3]与此相悖的是,“宽永七年(1630),江户幕府颁布命令,调查严惩基督教门徒及江户幕府禁止进口的书,开设德春寺,进行记录”。“宽永十五年(1638),又颁布锁国令,中国贸易船只限于长崎。翌年开始,医官向井元升(1609-1677)受命前往长崎,以‘中国船所带来的书籍须奉纳给幕府文库’为主要目的,开始调查进口书籍”。[4]巧合的是,清朝也于顺治十八年(1661)发布迁海令,到康熙二十年(1681)发布展界令其间,禁止一切船舶出海。双方的锁国政策造成了中国书籍输入日本的大幅度减少。在这种供求形势之下,日本国内的印刷业蓬勃而起,除了幕府、官学以及地方藩主主持的刻书机构外,商业性的书坊大量涌现。这一时期,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许多“刻书工人也开始经营出版业,京都一带,这类书屋林立,很快传遍大阪。到了元禄时代(1688-1704)出版界的中心已移到江户一带了”。[5]
(2)刻印水平更高。两国这个时期的刻本,相比前代,技艺和水平都更胜一筹。清代官刻“殿本”“局本”大都纸墨精良,私家刻书校勘精审,而坊刻则种类更加丰富。尤其是彩色套印,由于制版、镌刻、刷印各个工艺环节都有了新的提高和改进,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如康熙年间内府刻三色套印本《御选唐宋文醇》、五色套印本《劝善金科》,道光年间涿州卢坤刻六色套印本《杜工部集》,均色彩艳丽,配上洁白的纸张,读之令人悦目怡神。这种成就在坊刻本中也体现出来,坊刻的多色饾版套印版画集《芥子园画传》,其水平更令人叹为观止。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朝雕版印刷史上,还出现过蜡版印刷和面版印刷的新形式。
江户时期的刻本相对于前代,更为注重校勘,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刻本不仅都附有帮助阅读的训点,还附加有著名学者的注释,更注重学术因素。而彩色套板印本水平也极为高超,如翻刻中国的《芥子园画传》,色彩艳丽,其成就完全可以媲美原刻。不仅如此,此时的日本套印本,在技艺与色彩方面已形成浓郁的民族特色。
(3)刊印书籍数量最多。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出版书籍数量最多的时代,雕板印刷的书籍数量远远超过了前代所有出版物的总和,由存世古籍的状况就可以体会到这点。而日本江户时期的状况也一样,据已故长泽规矩也教授的调查,江户时期仅坊贾所刊印的汉籍就达四千种左右,平均每两个月刊印三种。[6]
综合以上方面,笔者认为选取中国清代与日本江户时期之刻本汉籍作为对象探讨两国的古籍版本特点,不仅具有典型性,还具有更广泛的文化意义。
2 清刻本与江户时期刻本汉籍外部形态之比较
本文所确定的外部形态范畴为纸张、版式、开本及装帧四个方面。
2.1纸张
(1)清刻本。清刻本的用纸,名目很多,常见者如罗纹纸、棉纸、竹纸、开化纸、开化榜纸、太史连纸、棉连纸、宣纸、毛边纸、毛太纸等,但从原材料讲,仍不过皮、竹两大类。而竹纸由于原材料丰富,价格较低,是清刻本尤其是中后期刻本最广泛使用的纸张。然无论是哪一类纸张,大都有纸面光滑、纹理细腻、质地轻薄的特质,且着墨性强,刷印省力,阅读美观舒适。当然竹纸也有缺点,就是容易发黄、变脆,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书籍的保存。一般官、局刻本的纸张都优于私家及坊间刻本。有关这一问题,李致忠先生在其《古书版本学概论》一文中有过详细论述,兹不赘述。[7]
(2)江户刻本。江户时期的刻本汉籍多用楮皮纸,此类纸张大多纸面粗糙,纹理粗乱,质地厚硬,着墨性不强,刷印起来应该不会很省力,手感及美观程度相对清刻本要逊色很多。这一点,如果有对和刻本加盖藏书印的经历,应该有明显感受。正如日本国学大师本居宣长在其《玉胜间》中写道:“日本各地出产的纸,或厚或薄,或坚韧或柔软,种类多样,但用于书写的纸张还是不及中国纸。”[8]然此类纸张最大的优点就是韧性极好,今天我们在翻阅这些日本古籍时,其间凡有破损,往往源于虫蛀、人为,很少如一些清刻本般,因为纸张自身质地的原因。官学、藩主主持刊刻的书籍,纸张质地虽然比不上清刻本,但一般还是优于书坊刻本。纸张是和刻本汉籍有别于清刻本的显著特征之一。
2.2版式
(1)清刻本。除了少数影刻、覆刻前代本,清刻本一般左右双栏,也有四周双栏或单栏的。大部分为白口,也有少数黑口,大多有鱼尾。除法帖、印谱及各类图谱外,行间基本都有界栏。
(2)江户刻本。一般白口,也有黑口者,大多有鱼尾。一般四周单边,当然也有左右双边或四周双边者。大多无行间界栏,这点在清刻本中很少见。
2.3开本
(1)清刻本。基本为长方形,一般官、局刻本及有实力的私家刻本开本都比较廓大,坊刻本则较小。至于那种可以置于袖中、口袋,作为随身读物的巾箱本,则基本是书坊的专营。
(2)江户刻本。与清刻本相比,此类书籍一般显得较为方正,陈正宏先生考察后认为“是纵横在26×18cm左右、纵横之比为1.4∶1左右的本子。换言之,如果一部日本江户时期刊本的高度跟中国明清印本的高度相等,则其宽度往往大于中国明清印本。由此连带出现的情况,是日本江户时期刊本版框外左右边的空白,往往较中国明清印本多,而上下空白则比中国明清印本少”。[9]这个论点极为中肯。此一点是和刻本汉籍有别于清刻本的又一个重要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官方机构,如学、藩刻本,在开本方面并不像清刻本那样,在私刻、坊刻中显得很特别。
2.4装帧
包括装订形式和外封两方面。
(1)清刻本。装订形式:一般将书页对折,在右侧采用双股白线四眼装订。
外封:清刻本一般用质地较厚的色纸,多为赭石色或藏青色,内府本多为明黄色,裁成书页大小,双折之后,作为封面和封底,称为“书衣”。偶有用质地较硬厚的色纸,裁成稍大于书半页大小,四周内折如书半页大小,靠内一面另粘附一张质地较薄、大小一致的他色纸,上面多印有书籍题名、责任者或版本信息,靠外一面作为书衣。书衣表面多粘有白色签条,印有书籍题名。清刻本书衣与文字页之间,一般另有一张与文字页相同之空白纸张,同样裁成书页大小,双折之后一起装订,作为衬页,使书籍另多了一层保护。
(2)江户刻本。装订形式:一般将书页对折,在右侧采用单股线四眼装订。这种装订时间长了,容易断线,造成书页散落。也许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和刻本常有将订口的上下角用藏青织物材料包住的情形,称为“包角”。这种形式清刻本也有,但没有和刻本普遍。
外封:和刻本的外封与清刻本有很明显不同,一般用较书半页稍大的厚硬色纸,四周内折,与书半页大小一致,然后将一张与书半页大小相同的薄纸粘于其上,另一面作为封面。很多坊刻本甚至直接将紧接封面和封底的书页直接粘于外封页上,开卷就是文字。和刻本基本没有作衬的空白页,显得过于注重实用,完全没有设计感和美感。此一因素亦是辨识和刻本汉籍的最重要依据之一。
3 清刻本与江户时期刻本汉籍内部形态之比较
本文所确定的书籍内部形态范畴为字体、注释、版权信息三个方面。
3.1字体
(1)清刻本。在字体上显示出明显的时代特点。清初期刻本,字体承袭明末风格,形体长方,横细直粗。康熙、雍正时期的刻本,多采用的是接近手书的软体字,且写刻上版多出于名家手笔,所以往往字体优美,刻印俱佳。乾隆时代,字体开始向规范统一的方块形式发展,流行一种硬体字,有点类似今天的仿宋字,这种字体横轻直重,撇长而尖,捺拙而肥,右折横笔粗肥,然而镌刻疏朗,阅读起来往往是一种享受。乾隆以后,字体则进一步向方正转变,文字的艺术特点基本丧失,字体变得呆板,世称匠体字,且除了官刻本和局刻本,绝大数书籍字体都变得小而密集,有了现代图书的气息。
(2)江户刻本。翻刻、覆刻中国本在字体上一般接近中国原本。绝大多数书籍采用的是一种具有日本汉字书法艺术特点的字体。相对于清刻本,这种字体形态比较肥短,笔势圆转,无论横直,运笔粗重,富有力量感,极具民族气息,是和刻本又一个显著特点。
3.2注释
(1)清刻本。大多采用文中小字单行或双行注,也有采用眉注或眉栏注的形式,但不管采用何种形式,与正文一样,行距、字数都比较统一。有时为了区分不同注释,还采用套色印刷,这样的设计不仅美观大方,阅读也非常舒服。
(2)江户刻本。常见有两种情形:一种为训点。除少数覆刻或翻刻中国本外,大多数和刻汉籍在汉字行间都有细小的日语训读符号。日本学者大庭修认为:“汉籍输入日本后,日本人为阅读这一用汉语写就的汉文,发明了通过在其旁添加各种符号和假名直接用日语阅读的技巧,这一仅通过变换语序来翻译、理解外语的‘汉文训点’术,可以说是日本人的一项惊人的创造。”[10]这也是辨识和刻本最主要的依据之一。
一为文字注释。和刻汉籍多采用栏外评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鳌头”注。这种注释不仅将栏外空白全部占据,文字排列并不整齐,且非常密集。亦有采用眉注的书籍,也是完全根据需要采用文字或文字加框的方式,并不在意行列与字数的整体划一。设计上似乎只看重实用,不很在意形式美观与迎合读者的阅读心态。
3.3版权信息
包括责任者及出版信息(刊刻者、刊刻年、刻工、发行者)。
(1)清刻本。责任者:清刻本的责任者往往置于正文卷端右下部,亦有少数置于目录首页右下端者。有时内封页也镌有主要责任者名,但并不详细。清刻本责任者署名非常详细,一般不仅列出撰(编)之人,就是注释、校对等人,也一一列出。如果是史志类,由于是集体工程,参与人数众多,一般于卷前有专页详尽列出。具体署名一般包括了责任者所处时代(本朝除外)、官职(或尊号)、籍贯(或郡望)、姓名及字(号)等基本身份信息。
出版信息:清代官、局本往往会在内封页或卷末以木记的形式标明刊刻者及刊刻年。部分私家和坊刻本以内封整叶镌刻图书信息,一般首行为责任者,次行著作题名,第三行为出版时间和出版者,有时出版时间会以横行方式出现在顶端。而大多数私家刻本和坊刻本对此项内容似乎并不太注意,有的仅在卷末镌刻出版者或出版年,有的干脆没有任何出版信息,需要通过仔细阅读序跋和通过板刻特点进行考证才能获知。清刻本少见刻工署名,主要由于清代前期文字狱很严酷,刻工们便很少象前代一般,愿意在书中镌上自己的姓名。到了后期,这种状况有所改变,比清末著名刻工陶子麟的刻书都会署名。在清代国人的意识里,大多没有完全将图书出版作为一种商业行为,各刻书机构多是自刻自销,图书发行很少受到关注,所以一般书籍很少有发行信息。
(2)江户刻本。在出版信息方面的情况要比清刻本繁复而含糊的多。
责任者:一般见于内封页、正文卷端右下方及封底页,然除翻刻中国本外,表述往往并不如清刻本那般完整、清晰。大多数或以字,或以号,或以通行称呼署名,对于不熟悉的读者来说,显得不够明确。如《毛诗补传》30卷,(日本)仁井田好古撰,责任者题“纪藩南阳任井田先生著”,通过阅读书中序跋,才可确定责任者的准确姓名为仁井田好古。
出版信息:出版者和出版年名常见于内封页,如《福惠全书》32卷,(清)黄六鸿著,(日本)小畑行简训译,内封页题“诗山堂藏梓”;封底页,如《诗人玉屑》21卷,(宋)魏庆之撰,(朝鲜)尹烟校,(日本)释玄惠训点,封底页署“宽永十六年己卯九月吉辰角屋清左卫门新刊”;内封、封底俱见者,如《芥子园画传》,(清)王概等撰,内封题“日本河南氏翻刻”,封底页署“堀川通佛光寺下町书肆植村藤右卫门、平安书肆河南楼、寺町通三条仧二丁目皇都书肆吉田勘兵卫镌藏”。亦有见于卷末,如《五车韵瑞》160卷附《洪武正韵》,(明)凌稚隆编辑,(日本)菊池东匀训点,卷末署“万治贰己亥末秋良辰京寺町本能寺前八尾勘兵卫刊行”;板心,如《史记评林》130卷,《补史记》1卷,首2卷,(明)凌稚隆辑校,(明)李光缙补,板心上端镌“宽文壬子年刊”,下端镌“八尾友春”。和刻汉籍与清刻本在这方面最大不同在于明显的版权意识。大多数书籍的封底页不仅有出版信息,还有发行信息,如《陆宣公全集》24卷,(唐)陆贽撰,(日本)石川安贞注,宽政庚戌(2年,1790)序刻本,封底页有这样信息:“发行书肆:江户日本桥通一丁目须原屋茂兵卫……大坂心斋桥通北久太郎町河内屋喜兵卫……京都麸屋町通姉小路上俵屋清兵卫、尾州名古屋本町通七丁目永乐屋东四郎。”这一特点的形成首先与当时国家在制度层面对于版权的重视不无关系。享保六年(1721),江户幕府承认书商行会,此后书商互相保护版权,严格禁止“盗版”“类版”。[11]同时,日本书籍刊印的浓厚商业性也决定了版权的确定势在必行。有时候,我们在这一时期的刻本中,会发现这样的情形,就是分属于不同刊刻者刊印的书籍,从题名、责任者、内容、字体、板式到出版年却完全一致,心里难免会产生疑惑,在书籍出版并不是易事的时代,为什么会有这种重复刊印的行为?其实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当时日本书坊间常有板片交易的情况,板片易主之后,就会对出版者信息进行剜改。此一点也正凸显了江户时期日本书籍出版重视版权以及商业化程度较高的状况。至于刻工,和刻本汉籍往往会在封底页出现,但正如前文提到的,江户时期的很多书坊就是刻工开设的,镌刻、出版一身而兼,要在封底页众多以出版发行人署名的人中确定刻工,确实非常困难。
4 结语
清刻本和日本江户时期的刻本汉籍作为历史同时期的文化遗产,虽在内、外形态方面都有很多相似之处,显示出相互间深厚的渊源,然也是在这些方面又有着根本的区别,打上了民族自身独特的印记,以独立身份成为人类文化遗产的构成部分,这一点在古籍研究中不应被忽视。
〔1〕(日本)中山步.“和刻本”的定义及其特点[J].图书馆杂志2009(9)
〔2〕(朝鲜)朴趾源.热河日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111,334
〔3〕〔6〕王宝平主编.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严绍璗序
〔4〕真柳诚.日本江户时期传入的中国医书及其和刻[J].中国科技史料,2002(3)
〔5〕(日本)李乃扬.中国典籍在日本之发展——和刻本溯源[J].社会科学战线,1992(2)
〔7〕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108-110
〔8〕冯彤.和纸的艺术[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03
〔9〕陈正宏.东亚汉籍版本学初探[M].上海:中西书局,2014:26
〔10〕王宝平主编.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大庭修序
〔11〕(日本)芳村弘道.日本江户、明治两代的〈文选〉版本简介与目录[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Comparison of Chinese Block-Printed Edi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With the Block-Printed Edition as the Object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Edo Period
Zheng Xiaoxia
The block-printed edi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is an important sort of ancient books both in China and Japan.There is a deep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origin,and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in shapes between each other.As a matter of fact,they are different cultural heritage with deep national brand,so they should not be mixed in the study of edition.This paper will expound this viewpoint with the block-printed edition as the object in Qing Dynasty and the Edo Period.
The Block-printed edition of Chinese classics;Qing Dynasty;The Edo Period;Comparison
G256.2
A
郑晓霞(1967-),博士,副研究馆员,现任职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