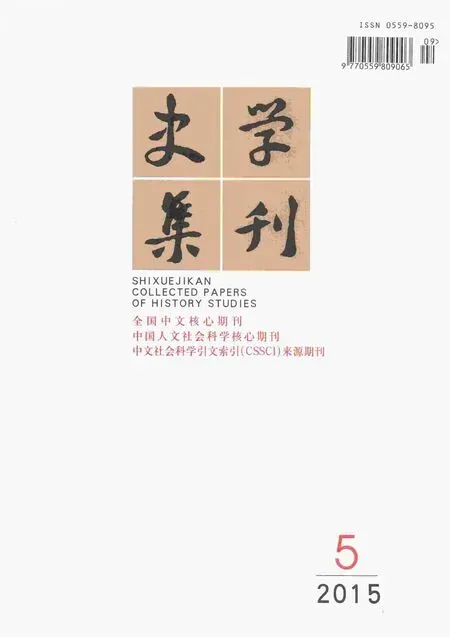社会主义实践对发展理论的贡献
2015-04-09陈晓律
陈晓律
(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平台,江苏南京 210093)
社会主义实践对发展理论的贡献
陈晓律
(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平台,江苏南京 210093)
发展研究与各国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利益诉求密切相关。1500年以来,发达国家占尽了先发的优势并获取了全球化的绝大部分红利。后发国家如何在这样一种格局中寻找自己的发展路径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社会主义实践为这样一种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它使世界的发展产生了多元化的可能,也使得发展理论本身更加丰富多彩。只有在多元化探索的基础上,构建一个以和平发展为主导的世界才有可能,而占全球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才可能真正分享到世界发展的红利,这应该是社会主义实践对发展理论以及世界发展本身最大的贡献。
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理论;多元化的发展路径
“发展是硬道理”是改革开放后国人的共识,发展研究则是二战后才出现的一个跨学科学术研究领域,我国学界在改革开放后对发展理论的各个分支如经济发展理论、社会发展理论与政治发展理论都等有了相当程度的研究,时至今日,发展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然而,发展研究从来不是单一的学术问题,它注定与各国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利益诉求密切相关。因而,不同的国家集团,甚至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对发展研究的重点也是不一样的。总体而言,目前的发展流派尽管数量众多,但如果从基本立场和服务对象进行分类,不外归属于两大集团: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二是西方发达国家。双方依然存在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对全球秩序与利益的不同诉求,只不过目前这条分界线在冷战后向东向北推进了许多,双方争执的焦点却依然没有改变:那就是全球发展的基本模式是标准单一的还是多元的?
对20世纪以来的发展理论进行梳理,我们不难发现,由于意识形态、理论与方法上的差异,发展理论的不同派别所产生的学术成果在体系和侧重点上有较大的差别。但总的来看,最重要的发展思想和理论基本上都被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之内。如果以时间为序对发展思维与发展理论的演变趋势做比较系统的评述和分类,在众多的同类著作中,J.拉瑞因的著作简明扼要,线索清晰,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他按时间将各种发展思想和理论做了如下归类:竞争性资本主义 (1700-1860年),代表性思想为两派: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帝国主义阶段 (1860-1945年),代表性思想为两派: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马歇尔、瓦尔拉斯、杰文斯,以及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卢森堡、列宁等;晚期资本主义 (1945-1980年),其中又分为两个阶段,扩张阶段 (1945-1966年),其理论为现代化理论,主要代表为罗斯托等人,以及普雷比什关于拉美经济委员会的分析和巴兰的新帝国主义;减速与危机阶段 (1966-1980年),新自由主义,以弗里德曼为代表;依附论,代表性人物是弗兰克和卡多索;世界体系的理论,代表性人物是沃勒斯坦;不平等交换理论,代表性人物是阿吉里·艾曼纽尔与阿明;等等。①Jorge larrain,Theories of Development,Capitalism,Colonialism and Dependenc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8,p.4.其余的著作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各类专著中基本上都包括了这样一些学术派别:古典主义、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现代化学派、现代化修正学派、依附论、世界体系论、新马克思主义、新政治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等学派。②Richard Peet and Elaine Hartwick,Theories of Development:Contentions,Augments,Alternatives,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2009,pp.ix-xii.也有以经济发展为主线,将发展思想归类为资本积累与工业化、二元主义和以农业为中心的发展、开放式经济发展、改革主义发展思想,等等。③参见 Charles P.Oman and Ganeshan Wignarja,The Postwar Evolution of Development Thinking,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1991.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关于发展理论的研究著作中,马克思主义及其思想流派都占据着重要位置。其中一些学者,干脆将马克思主义与受其影响的观点作为一个大类,名曰“非正统发展思想”。④参阅Richard Peet and Elaine Hartwick,Theories of Development:Contentions,Augments,Alternatives;Charles P.Oman and Ganeshan Wignarja,The Postwar Evolution of Development Thinking.而有些学者,则以专著的形式专门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对发展理论的影响。⑤参阅 Rune Skarstein,Development Theory,A Guide to some Unfishable Perspectives,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自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集团解体后,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低潮,为什么西方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在发展领域的兴趣依然浓厚?显然,马克思的思想在发展研究的构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对资本性质和资本主义体制的分析,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其潜在的思想价值和理论价值都毋庸置疑。⑥西方主流经济学历来有“三大经济学家”的说法,即亚当·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并认为要了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就要了解三位经济学家在看待资本主义时都看到了什么,因为“他们的看法仍然界定了经济学的领域”。参见郭广迪:《三大经济学家: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17日,A07版。然而,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在实践中互动体现出来的历史作用,人们似乎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中国官方几十年不变的教科书,其理论分析的角度和做出的解释也很难使人完全信服。所以,笔者认为,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发展理论的发展脉络,或许能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实践与发展理论之间的互动渊源,并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实践在发展理论体系中的地位有一个全面的解读。
一
大规模的发展理论兴起于1945年以后,但在此之前,有关经济发展的思想已经十分丰富。如果对经济发展作一个简要定义,可以理解为一定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结构的优化以及经济质量的有效提高,于是一切有关于国民的富裕、收入的合理分配、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问题便自然地成为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围绕着这些问题,发展研究已经开始涉及整个社会的不同层面。与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吻合、至今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思想,可以按照拉瑞因的框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梳理:
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阶段,也就是拉瑞因所说的竞争性资本主义。这一阶段学派众多,但最重要的是重商主义与古典经济学。重商主义的要点是,金银是一国财富的唯一形式,金银货币的多少便是一国经济富裕程度和是否发展的标准,由此出发,他们认为国内贸易既不能增加国内的金银货币总量,也不能将国外的金银货币引入国内,所以国内贸易是无足轻重的。与此相反,他们对对外贸易十分重视,认为只有在外贸中使自己的商品出口大于进口,才能有更多的金银货币流入国内市场,一国的财富总量才有可能增长。换言之,重商主义者认为外贸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他们之所以极力主张出口入超,一可以解决国内的产品积压问题,二可以增加货币数量,从而使利息率降低。此外,重商主义强调国家权力的重要性,主张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①[英]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49页。所以,重商主义者主张政府应采取种种措施来保护幼年工业,限制输入,鼓励输出,这些思想至今还对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的影响。
古典经济学是这一阶段的另一大类发展思想。这是一个庞大的学派,以亚当·斯密为代表,他认为国民财富的增长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专业分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二是人口与资本的增加引起从事劳动生产的人数增加,因此对人口、分工和资本必须进行重点分析;此外,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过程,应对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即经济发展前景进行研究。而李嘉图给后人的启发是,国民财富的增加有两种方式,一是用更多的收入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这不仅可以增加产品的数量而且可以增加其价值;二是不增加任何劳动数量而使等量劳动的生产效率增大,这会增加产品的数量,但不会增加产品的价值。马尔萨斯则强调了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第一次提出要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注意与自然环境的平衡。小密尔分析了经济增长对投入要素 (如资本、劳动力、人口增长、技术进步)价格的影响,这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常用的经济分析方法。②伍海华:《现代经济发展》,青岛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页。
作为古典经济学代表的亚当·斯密的思想影响最大。
斯密的经济学说,大致有三个内容:即分工、经济世界的自然组织与自由主义。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或许是经济制度的自发性。他的主要论点是,经济世界的现状是千百万人自发地行动的结果,他们每个人只服从自己的意志,然而最终却产生了严密的经济组织,这就在实际上表明了有某种“经济规律”在起作用,尽管这两者并不完全一致。
这种自然经济组织的产生不是由于人类的智慧,而是由于人类的需要。人们都想过上富裕的生活,于是为满足个人利益的需要去与别人交换自己无力生产的产品,由交换导致分工,由分工产生货币,由货币推动商品的生产。于是整个经济体系开始运转了。政府的干涉是很久以后发生的事,而干涉的目的也在于用一种标准来保证流通中的货币的分量与成色。
经济自由是这一看法所引出的实际结论,也是前述论题的自然发展。“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已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就完全可以自由地依照自己的方式去追求个人的利益,用自己的劳动和资本与别人或别个阶层竞争”。至于政府或君主,“就完全被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要履行这种义务,君主们极易陷于错误;行之得当,恐不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做到的”。③[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54页。因而,自然的结论就是:国家不干涉经济事务是明智的。事实上,光荣革命之后,正是议会制度对国王的权力进行了限制,英国的公司逐步由申请特许转为注册登记,充分激发了市场的活力,才使英国开始在世界经济中成为主导型力量。
亚当·斯密的学说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传播,经济自由主义学说的真理性与合理性,在英国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再到密尔、马歇尔,英国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一脉相承,逐渐成为英国经济学思想的主流,甚至也已经成为英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人们往往会忽略这种真理是在一种政治经济乃至综合国力占优势地位上的产物,是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主导位置国家的代表思想。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初期,西欧各国发展的差别不大,谁也不能操纵国际市场。所以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还都曾寻求国家的保护政策以免遭受他国优势产品的竞争,因此,重商主义是他们“初级阶段”的指导思想。但工业革命后这两国的经济有了迅速发展,技术水准也与其他西欧国家拉开了差距,它们开始有能力也有必要在国际市场上展开充分的竞争,这正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产生的基础。因此,经济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强者的“发展思想”。但当英法成为工业国家的第一集团时,其他试图赶上的第二方阵国家,由于其工业技术水平的差距,再盲目跟风自由主义的理论则有东施效颦的尴尬。由于这一缺陷,所以这一类“追赶者”国家必须“创造”适合自己发展的经济理论。
二
于是,发展理论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历史阶段,它大致相当于拉瑞因所说的帝国主义阶段。这一阶段产生的经济思想十分丰富,但我认为,从发展的角度看,最重要的创见不是马歇尔、杰文斯等人的理论,甚至也不是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理论,而是李斯特的学说。他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经济发展思想,对当今世界的经济格局,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自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发展的最为成功的地区,主要在英法两国,或者说英吉利海峡两岸地区。英法两国由于自身在工业上的优势,竭力提倡在国际上的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政策,其大量的廉价商品不仅冲击所有的后发国家,而且也对传统的欧洲大陆国家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其中,强烈感受到这种威胁并且在理论上做出反应的主要是德国。如何摆脱外国自由竞争的威胁,促进德国工业的发展,是德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斯密、李嘉图从其价值理论出发,认为在别国生产费用较低的产品就无须在本国生产,因为花钱向别国购买更为合算。李斯特反对这种说法,认为“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①[德]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8页。因此,为了发展生产力,国家政权必须对经济进行干预。由此出发,李斯特提出了两个著名的观点:反对自由主义者的世界主义观点,认为在人与人类这个总体之间,还有一个中介,那就是国家,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个人与个人发生直接关系,而是由个人构成的集团之间相互发生关系。每一个个人都是某一国家的成员,他的一切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他所处国家的政治威力。世界大同的理论虽然不错,但目前的形势是国家力量不等,利益不同,要完全做到平等相处是困难的。因而,个人只有通过维护国家利益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但现实世界中的各个国家是千差万别的,要使国家从野蛮转变到文明,弱小转变到强大,尤其是使它获得长期生存的保障,这些都是政治任务。而要完成国家经济发展,为它进入将来的世界集团准备条件,却是一个政治经济任务。②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57-158页。
换言之,现代经济发展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在这里,李斯特特别强调了“正常国家”的标准和概念。只有正常国家,才可能在陆上、海上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其独立生存以及国外贸易。一个正常的国家必须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字,广阔的领土,自己可以控制的出海口,多种多样的天然资源,合宜的国境和稠密的人口。国家农工商业和航运事业必须做共同的、按比例地发展;艺术与科学、教育事业以及一般的文化事业必须与物资生产处于等同的基础。它的政体、法律和制度必须对本国人民提供高度的安全与自由,对于宗教、道德和繁荣必须有所促进,总之必须以提高人民福利为目标。“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是正常国家的基本条件,也是文化发展、物质发展和政权巩固的基本条件。一个土地狭小、人口无多的国家,尤其是如果有着个别的语言时,它的文学、它的促进艺术与科学的制度,就不会是完善的。一个小国是绝不能使生产的各部门在它国境内获得充分发展机会的。在这样的环境下,一切保护制度不过是私人垄断性质。它只有靠了与强大国家结成同盟,并加倍的努力,然后可以有希望勉强保持独立地位。”③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58-159页。
李斯特的学说有两点至关重要。第一,在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单位是民族国家,经济发展不可能脱离这一载体而“自由发展”(在民族国家产生前或许有其他的经济载体,但民族国家产生后这样的自由区域即便存在,也不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第二则是指出了发展过程中大国与小国的地位问题。只有大国才可能真正独立自主地主导自己的发展,小国按照李斯特的分析,根本不是“正常国家”,也不可能主导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因此,一个国家是以小国还是以大国的身份进入全球化的轨道,需要对自身的国情和能力进行清晰的定位。
不过,李斯特尽管反对斯密的“世界主义”经济学,但他的思考和理论,却依然是在一个广义的“世界主义”经济体系中运行的,只不过在这个体系中,正常的“民族国家”成为主角。而英法尽管自己是这一体系的主角,却要竭力地淡化这一点,总是把自身的利益解释成“世界”的利益。德国显然并不认同这一点,它要获取自身的利益,就要挤进这一“正常国家”的行列,从而让“世界利益”的盘子中,有德国“合理”的份额。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在所有的条件中,除开其他成为正常国家的要素外,殖民地也被李斯特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要素。他甚至认为,亚当·斯密或许是故意地忽视了通过殖民地的开拓,英国取得了多大数量的资本 (据马丁估计这一项数额在二十五亿英镑以上)。①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95页。有学者计算,1500年前,西欧人均土地占有面积约为24英亩,地理大发现将这一数字扩大到了148英亩,增加了6倍。②E.L.Jones,the European Miracle,Environments,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82-83.殖民地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这种有利于一个“正常国家”发展的殖民地的分配,却并不“公平”。英法等第一批工业强国抢占了绝大部分,而后起的工业国却无法获得与其实力相匹配的份额。因为工业革命在欧洲大陆和北美扩展的结果,是美国和德国迅速成为在经济实力上超过英国的工业国家。在这样实力平衡被打破的情况下,德国成为英国最具威胁的挑战者。美国尽管实力超过英国,但其原材料来源和销售市场都不成问题,因此美国十分乐意维护英国主导的这种外部秩序。而德国地处欧洲中部,殖民地的面积也不大,所以,德国人的世界政策出台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在工业化时代里,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自身经济的发展,都开始积极地控制地盘、抢占资源和空间。法国殖民政策的倡导者费理曾指出,欧洲的消费已饱和了,只有实行殖民政策才有可能得到新的发展,否则工业国家就会遭受经济灾难和社会灾难。向海外扩张,获得经济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是当时发达国家的基本国策。英国在1860年时,拥有殖民地250万平方公里,人口14 510万人,到1914年上升为1290万平方公里和39 350万人。法国在1914年拥有殖民地1060万平方公里,55 500万人,比德、美、日本三国所拥有的殖民地总和还要多。③Stephen Constantine,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Development Policy 1914-1940,Taylor and Francis,1984,p.10.俄国到1914年从中国等国家攫取到的土地达1740万平方公里。19世纪工业和技术的发展成了一个现代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撑点,这种经济的特点决定了所有的工业国要么拥有殖民地,要么去努力获取殖民地。而此时经济上强大的德国仍然局限于欧洲大陆,两手空空,如果继续踩着别人的脚印走下去,也许永远都不会成为世界强国,也就是李斯特所认为的“正常国家”。这种局面使德国统治者认为“当欧洲外的巨人在欧洲外形成的时候,继续保持欧洲的均势,无异于宣判德意志人的无所作为,最后是宣判所有的欧洲人的外族统治”。④David Calleo,The German Problem Reconsider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78.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扩大殖民地,就必须争夺世界霸权,创造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外部环境,而德国自认为已经具有了这种能力。“有关德国扩张主义的重要之点,在于要么这个国家已拥有改变状况的实力,要么它已拥有创造这种手段的物质资源”。⑤[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55-257页。随着德国实力的增长,无论是德国的学界还是政治界,显然都认为自己拥有了这种实力和资源,与原有主导型强国的冲突终于不可避免。
于是,现代意义上的发展,虽然不是“全世界”的均衡发展,却是所有国家都在一个全球框架下的发展,其中的要害,不是要不要与全球化发生关系,而在于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进入这一体系乃至于主导这个体系。从一个长时段的角度看,近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压倒一切的决定性因素,还是英国工业主义的无比优势。在英国,这产生了自由贸易政策,而在工业比较落后的国家,则催生了有限的保护政策。结果,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经济政策的方式与目标,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到处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之所以如此,基本原因有三点:1.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和德国具有了向英国工业优势挑战的能力;2.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3.在大多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积累过程的矛盾成熟了。而作为垄断资本的特征以及对殖民地的强制性需求,使得自由贸易或有限的保护,渐渐地为无限的保护所取代;世界市场的自由竞争,为各国垄断的激烈竞争所取代。最终,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的时代。在这里,资本的利益直接和迅速地转变为国家的政策,因此,过去资本间的对抗,便以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冲突形式展开了。①[美]保罗·斯威齐著,陈观烈、秦亚男译:《资本主义发展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22-330页。李斯特经济学,本质上是应对这样一种发展格局的理论产物。或者说,自由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必须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理论。
三
在20世纪初,人类的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迫切需解决的问题是,所有被卷入全球化浪潮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如何获得正常的发展机遇。如果说在此之前的发展阶段,是从自由竞争到全球博弈,从个人到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再到世界市场形成了资本主义在全球的优势地位和世界体系,到20世纪,则是未能挤进工业化第一集团和第二集团的国家和人民必须尝试是否可以用另一种不同的体系来代替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体系了。因为原有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全球等级秩序与西方国家的领导权。如果说第二集团是要挤进分享原有体系的红利,只是涉及同一体系中不同国家座次的调整和利益份额的划分,那么,第三集团国家——即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在原有体系无法获得话语权的情况下,只能另辟蹊径,否则很难改变自己的从属地位。这显然是动摇原有体系根基的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种需求同样导致发展理论必须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因此,新阶段上的发展理论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它既需要理论,更需要能够使理论行之有效的实践。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能否出现这类成功的实践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这种实践,承担着对原有体系进行挑战的重担,那么,它也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实践。这样一个挑战原有秩序的国家,它要生存下去,获得成功,除开意识形态方面的旗帜以及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之外,它还必须具备一些其他条件方才有可能。首先它必须有足够的体量,能够与现有的资本主义强国抗衡,但并不是简单地在体系内替代原有的霸权国家,而是用一种新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来与原有的资本主义大国进行较量。这样一种较量,尤其是经济发展的思路不是按照原有西方大国的游戏规则进行的,所以它也必然引发原有国家体系的不安和动荡。这样一种思路的潜在逻辑是,除非改变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建立起来的以西方大国为主的国际体系,否则第三世界国家就不可能获得与原来欧美强国平等的发展机遇。
这样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只能由一个处于原有体系边缘状态的大国才可能承担——已经能够掌控局面的大国,不可能对整个体系进行破坏,而小国和第三世界国家则无此能力。原有体系边缘的大国中,只有俄国具备这样的资格和能力。当然,要完成这样一种颠覆原有体系的历史任务,它还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从理论或意识形态上对自己构建这一体系的合理性加以证明,并使其具有在世界范围内的感召力,因此,这一体系必须是普世的而非单独一国的 (俄罗斯从第三罗马的思想到共产国际,能够提供一种天然的理论轨迹);第二,构建其强有力的现代国家机器,使其具有高效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第三,建立起强大而独立的国防体系,使自己在与世界大国对抗时能保证自己安全;第四,运用一切方式,使自身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越传统的西方国家。最终,解放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使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发展的机会。
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给俄国这样潜在的有能力挑战原有秩序的大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构架。在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念中,资本主义是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当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发展生产力的桎梏,再也容纳不了其自身创造的生产力时,就会被新的生产方式所替代,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预测这一阶段究竟有多长。更重要的是,按照他们的看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应该由西欧资本主义发达、资本主义矛盾暴露得比较充分和深刻的国家中的无产阶级来实现。而不是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国内大多数人口是农民的国家来进行社会主义实践。只有在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才能进入人类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实际上,经济学大师熊彼特也主张在资本主义“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反对在不成熟的条件下通过暴力方式进入社会的下一个发展阶段。①[美]约瑟夫·熊彼特著,吴良键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31-339页。因此,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其他的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能改变现状、进入下一阶段发展的国家都与俄国这样一个落后大国无关。当然更不用说其他的第三世界国家了。而问题在于,所有的后发国家,它们怎样才能进入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在未能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前,他们应该做什么?有无可能推动本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按照西方大国的模式发展?或是耐心等待历史的这一阶段“自然”成熟?显然,发展中国家亟须解决发展的理论与路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熊彼特等人都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缺陷与社会发展的未来,但理论与实践如何结合,依然是一个问题。于是,社会主义的实践,开始成为发展理论进一步发展的一种新的驱动力。
实际上,社会主义的实践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在历史的长河中具有自然结合起来的需求: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面与原有世界体系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旗帜,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则给这面旗帜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但是,这种结合的过程却有一些“意外”,它不是发生在马克思认为可能性最大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发生在相对落后的俄国。
这是一个例外。因为著名的十月革命前后,无论是原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第二国际的主流观点,甚至布尔什维克内部的很多领导人,都不认为俄国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关于这方面的理论和历史文献十分丰富,这里不再重复。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确造成了俄国革命的形势,给布尔什维克党提供了夺取政权的条件。二月革命后,俄国出现的不是两个政权并存,而是空前的无政府主义。列宁很快意识到布尔什维克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夺权机会,这不是基于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和文化条件已经成熟,而是基于俄国因战争出现的危机。②姚海:《俄国革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这样一种窗口期转瞬即逝,但列宁抓住了这一时机,提前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③叶书宗:《苏联的革命与建设》,上海社联1986年版,第3-6页。
尽管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布尔什维克掌握了国家政权,但这种与马克思原来设想相反的情况,以及面临着国际资本主义国家重重包围的现实,使得一国是否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依然成为苏共党内不同领导人之间激烈交锋的战场。十月革命后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苏共部分领导人指望的“世界革命”暂时落空了。于是,苏共党内对此爆发的争论越来越激烈,最终斯大林通过党组织的形式给这一争论画上了句号:那就是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而党的类似决议甚至在此之前就已经公布:“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作为国际革命主要基地的工人专政的国家,应当把自己看作国际革命最强有力的杠杆和助手;另一方面,在这一国家内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竭尽全力去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并确信只要能保住国家,不使任何复辟企图得逞,那么这种建设就可能而且必将取得胜利。”①《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三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9页。转引自叶书宗:《苏联的革命与建设》,第114页。
实际上,西方列强积极支持布尔什维克对手的内战,使新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生存。但从它挑战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角度考察,这样的生存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生存,还意味着从发展的角度,它存在的本身就已经证明它有可能开辟另一种发展的路径。在发展理论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明显的规律,即每一种有着重大影响的发展理论,都与特定国家解决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有关。马克思主义能否解决特定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发展领域能否具有长远的、根本性的影响的决定性因素。
俄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大国,也是一个很早开始现代化的国家,但由于种种观念和体制因素的制约,直到一战爆发前,俄国依然是一个前现代式的、野蛮落后的国家。②Clive Trebilcock,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Powers,1780 -1914,London:Longmans,1989,p.205.正是由于这个特点,我国学者认为,当时俄国具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基本条件,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却又是不成熟的,十月革命并不是社会发展瓜熟蒂落的产物。③叶书宗:《苏联的革命与建设》,第4页。现在俄国史学界认为这是具有政治革命的条件,但社会经济条件尚未具备。从现代化的角度解读这一史无前例的革命,可以这样认为,十月革命是俄国试图通过政治革命来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次尝试,也是西方列强中相对落后的大国为了避免边缘化的一次特殊的现代化转型。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现实毫不客气地要求弱国和战败国承认弱肉强食的基本法则,而按照西方传统的路子俄国又无法摆脱自身的虚弱状态。于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从中寻找到一条现代化的生路,应该是当时俄国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我国学者余伟民的看法是合理的,他认为苏联模式的历史合法性首先来自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替代性选择”的需求。发端于西欧地区的现代化作为自然历史进程充满着人类社会固有的不平等,随着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动,传统社会的等级秩序被资本主导的新的等级秩序所颠覆,在资本社会奠基阶段,新的阶级关系表现出比以往更尖锐的阶级矛盾。同时,西欧国家凭借工业生产力的优势,以殖民主义方式向全球扩张,建立了早期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从而将世界大部分地区强制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上述过程蕴含的种种“不合理”因素是激发批判资本主义、诉求“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依据。马克思主义就是其中最为彻底的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作为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后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为起点、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正是表达了人类社会试图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选择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合理诉求。此种“替代性选择”的理论论证来自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和共产主义理想,其社会基础则来自下层民众和被压迫民族对早期资本主义阶段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反应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这是人类第一次试图按理论认识中的“历史规律”改变自然历史进程的努力,其中蕴含的理想主义曾发挥了强大感召力,尤其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严重时期以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的落后国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④余伟民:《替代性选择和比较优势》,《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11期,第32-33页。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为了巩固政权在运用历史合法性资源上做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效。苏联模式的建构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历史潮流是基本吻合的。苏联的工业化正当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严重经济、政治危机,因而即便是粗放型的工业化也在若干重工业指标上表现出独特的发展优势,并随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为具有支配国际事务能力的军事大国。苏联作为“世界革命”的基地,通过共产国际为东方落后国家展开左翼革命政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支持和帮助,从而促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觉醒和革命意识,并为这些国家独立后的发展道路选择提供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样板,正是通过苏联模式的输出,形成了冷战时期与资本主义世界对峙的社会主义阵营。可见,十月革命的成功 (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虽有偶然性 (历史机遇和革命策略),但革命后选择的发展道路及其发挥的世界影响却并非偶然,应该肯定,这是一种应对世界历史命题的特殊实践。在这个意义上,苏联模式的发生有特定的历史根据,也因此曾经一度获得国内外社会民众相当程度的认同和支持,从而获得其历史合法性。①余伟民:《替代性选择和比较优势》,《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11期,第33-34页。
当然,由国家政权超强干预而形成的苏联发展模式,即斯大林模式,其利弊得失也引发了学界长久的争论。学界一般认为,斯大林模式的本质是高度集中,国家不仅管理行政、外交、国防、治安、财政等事务,而且依靠垄断掌握的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全面管理生产和分配,还管理教育新闻、卫生体育、文化艺术等文化事业。国家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将全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置于自己的管理控制之下。其次,联共布是国家的领导核心,国家的一切大政方针都由党决定。最后,权力集中于党的领袖斯大林一人。这就是斯大林模式的主要特点。②徐天新:《斯大林模式的形成》,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5页。
在斯大林模式形成的过程中,无疑给原有的社会形态,尤其是农民,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也使很多民众遭受惨重的损失。尤其是斯大林要求全力实现工业化目标的过程中,农民必须“纳贡税”的指导方针,给农民带来了经济、生活方式乃至人口的根本性变化。在某种意义上,俄罗斯原有的农村已经彻底消失,农民真正为苏联的工业化“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同时,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借口下进行了大清洗和镇压,在肉体上消灭了大批有才能的军事家和一些知识分子,给苏联的建设和综合国力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尽管有这些失误,国家政权的强势作为并不表明这一模式的本质是一味蛮干,相反,这一模式依然在很多方面体现了其发展方面的科学性和预见性,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迅速构建起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普及了现代教育并培养出一支合格的教学、科研和劳动大军。早在1922年,列宁就指出,“不挽救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能成为独立国家”。③郑异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02页。换言之,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在斯大林模式粗暴的行政命令式的管理过程中,苏联的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依然在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尽管斯大林认为,多建一个工厂,就是多一个与资本主义作战的堡垒,但他却不反对对外开放、引进资本主义的资金以及西方的先进技术乃至管理模式。在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时,他对所有有助于实现自己目标的软件和硬件,都全部拿来为己所用。苏联利用自己有限的资金从西方大量进口机器设备、拖拉机、金属和原料,生产资料的进口占苏联进口总量的90%以上,其中机器设备的进口所占比例最大。美国这个头号资本主义大国,却是苏联购买机器设备的最大卖主,1931年苏联购买的美国机器设备占美国出口总量的50%。1929年5月,苏联设立了中央外国咨询中央局,统一领导外国技术力量的引进和利用。1929年10月1日,苏联政府批准了70项有关外国的技术援助和技术咨询协议,其中55项是与美国和德国签订的。到1931年春,项目增为124个。此外,苏联还以高薪聘请大批外国专家和技术工人来帮助经济建设,1932年在苏联工作的外国专家有1910人,技术人员有10 655人。此外,苏联还派出2000多名干部和技术人员出国考察学习。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的工厂、电站大多是在西方国家提供资金、设备和技术的情况下建成的。斯大林也承认,“在苏联,约有三分之二的大型企业是在美国的补助或技术援助下建成的”,其余的也大都是在徳、英、法、意等国的技术援助下建立起来的。④徐天新:《斯大林模式的形成》,第115页。
其次,这一模式在短期内“创造”出了自己的科技大军,包括科学家、技术人员和普通工人。没有这样的一支人才大军,即便引进了机器设备,也无法转换成真正的生产力。在这一点上,应该说,苏联政府做了很多事情,从20年代开始就启动了从大规模扫盲开始的文化教育工作。但直到1927年,苏联的识字水平在欧洲还排在19位。1929年,共青团倡议在全苏进行扫除文盲和向文化进军的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有百万人之多。到1939年,俄罗斯联邦9~49岁的居民中识字率已经达到89.7%。①徐天新:《斯大林模式的形成》,第151页。在两个五年计划期间,政府拨出大批款项,新建学校数万所。而大学教育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更是得到了飞速发展。1927-1928年度,全苏联有148所高校,1932-1933已经猛增至832所,而且其高校建设日益规范化。工人出身的大学生比例明显增加。1933年8月,联共布中央通过决定,禁止高校在上课期间进行非学习性的集会活动,学生参加社会活动,每人以一种为限,活动时间每周不得超过4小时。1934年,恢复学位和学衔制度,1935年,政治局批准取消过去一切有关限制非工农出身人员入学的规定。1936年,对高校一切工作做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要求贯彻校长一长制,校长必须受过高等教育,党政组织的责任是帮助校长做好工作。同时,不断扩大工程技术院校的比例。②徐天新:《斯大林模式的形成》,第154、155页。当然,苏联在全面发展高等教育,使大学生比革命前成倍增加的情况下,在人文社科方面出现了过左的风气,这些失误,既有体制性的因素,也有斯大林个人的原因,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国内相关的文章很多,这里就不深入分析了。③徐天新:《斯大林模式的形成》,第179、180页。
西方学者也承认,无论从何种角度看,苏联的经济军事成就都是一个奇迹:“苏联制造业产量和国民收入的增长——即使按照较为保守的估计,在工业化的历史上也可说是史无前例的。如果考察一下两个五年计划 (1928—1937),就会发现,俄国的国民收入从244亿卢布提高到962亿卢布,煤产量从3540万吨提高到1.28亿吨,钢产量从400万吨增至1770万吨,电力增长7倍,机床增产20倍以上。拖拉机产量几乎增加40倍。事实上,到30年代末,俄国的工业总产量不仅超过了法国、日本和意大利,而且可能超过了英国。”④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第397页。
纵观苏联在二战前的发展,可以说,苏联的工业化创造了人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奇迹。尤其是苏联在没有殖民地掠夺,基本上依靠自身力量的情况下,却取得了世界上史无前例的经济建设成就,显然值得人们将其作为一个现代化的独特例子进行深入考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苏联模式已经对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仅仅几十年时间,苏联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转变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是美国的两倍。美国学者也承认,这种状况不仅对美国和苏联人民的心理产生巨大的影响,还对全世界亿万欠发达国家的人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⑤[美]雷讯马著,牛可译:《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中央编译局2003年版,第139页。二战以后,社会主义运动已经成为真正的世界性运动,社会主义国家也由苏联一个变成了十几个,在东欧和东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从时间上看,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之久;从涉及范围上看,不仅有中国、朝鲜、蒙古、超南、老挝等亚洲国家,还有苏联和东欧各国。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地区“相当一部分民族独立国家的执政党提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或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据统计,从1955-1988年,在93个民族独立国家中就有55个民族独立国家的执政党提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占民族独立国家总数的59%。其中亚洲11国,非洲30国,拉丁美洲14国”。若论人口,世界总人口的半数以上卷入了这场社会主义运动。⑥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四
这场人类历史上几乎跨越一个世纪,使地球上三分之一的国家和地区卷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因值得人们深思。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这场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发展理论本身的发展是否会形成今天这样百家争鸣的局面。
首先,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其商业形态的大旗的,由于这种刺激,使西方大国相应地产生了其对应的意识形态:现代化理论。在二战后的美国学界,现代化的概念远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模式,它也是理解全球变迁的进程的手段,还是一种用以帮助美国确定推进、引导和指导全球变迁的方法。因为他们担心在巨大的非殖民化浪潮中,贫穷的、不稳定的政权会给马克思主义革命提供肥沃的土壤。①雷讯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第2-3页。
换言之,发展面临着两种道路的选择——社会主义模式或是资本主义模式。原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如何摆脱西方大国的控制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对这些国家历来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在综合国力不在一个层次上的国家,如何获得独立发展的机遇,依靠什么力量来推动发展,是很多第三世界先贤苦苦思索并需要解答的问题。而他们几乎最终都不约而同地得出了一个答案:发展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政权。而马克思主义不仅提供了经济分析的原理,也为这些国家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提供了理论的依据。对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一个实践问题而非纯粹的理论问题了。
实际上,在李斯特的学说中,现代国家的作用已经无法回避,而国家问题也已经构成发展理论的一个关键领域。也可以说,人类政治体制的优势开始在经济生活中得到体现,即在较为先进的政治文明基础上产生的国家机器,更有利于现代经济的发展。这种作用,不仅造成在欧洲各国之间的发展差异,而且也导致了中西方发展的差异乃至整个当今世界基本格局的形成。贡徳·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提到过,世界的经济中心很长时期都不在西欧而在亚洲。欧洲需要中国的商品,而中国需要白银。结果直到18世纪,欧洲才在一个世界经济的体系中脱颖而出。②[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中文版前言。在当时的世界上,尽管欧洲和亚洲已经具有了十分密切的贸易往来,但谁能够主动地“利用”这些条件,将“对方”的经济纳入自己所构筑的经济体系,把世界经济体系变为以自己为主导的经济体体系,使其余地区成为“他者”,确实却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尽管学者们有不少看法,其中也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但彭慕兰《大分流》一书中提到的制度性学派的各种观点依然是最有道理的,也就是政治权力的安排和架构对英国乃至欧洲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是导致分流的标志性事件。但它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还意味着一个国家拥有包括经济制度、价格机制、竞争机制、金融体制、管理体制等让整个经济运行起来的“硬机制框架”,此外还包括能够适合全体国民在这种框架下生活的文化“软机制框架”。换言之,其政治经济结构的“现代化”或许也可以说是其政治文明的优势,对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理解为何同样遭遇资源瓶颈后,东西方会产生不同的应对方式。③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也就是说,这种政治权力能够较为充分地调动其本国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无论通过何种方式,人们都能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合理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同时,还能有效地保护自己通过社会认可的正常手段获得的财富。这就意味着,这样的国家必须是法治国家,它们具有在制度方面极为刚性的特点,人民的合法权利可以得到确实的保障。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当然会继续存在,但各种社会力量可以通过一系列合法的程序来化解这些冲突,国家的权力机构也能够和平地提供保证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稳定的政治秩序。
进一步深入分析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政治权力结构,我们可以发现它们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它们率先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 (英国人自己很少提及这一点)。政治权力对经济的巨大作用,只有在一个有效运转的国家机器存在的前提下才能得以充分发挥。这样的国家机器,只能是现代的民族国家——它只是在1500年以后的欧洲才开始被逐步建立起来,很多欧洲国家也是经历了绝对主义的王权国家以后才逐步过渡到这样的民族国家体制。这样的民族国家,它对各种社会矛盾的协调开始形成较为成熟的解决方式,对未来的发展也有较为长远的目标,现代社会的种种诉求,也只有在这样的国家平台上才得以充分表达。按吉登斯的归纳,这种现代社会往往具有四种体制性特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商品生产、协调统一的监督和行政管理、工业化和集中的工业化军事秩序。吉登斯还认为,在现有的不同国家体制中,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最能体现现代社会的这四个体制特点。因此,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中也就扮演着一个特别的角色。常有人把现代化或全球化直接等同为西方化,或者西方资本主义化。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只是比较集中地体现了现代社会的特征,但并不就是现代社会的历史设计者。以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西方国家率先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现代社会,对其他社会的现代化形成了客观上的示范作用,不过是历史的偶然巧合。①A.Giddens.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85,pp.255-257.这样的民族国家,本身又是与商业和工业与贸易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在相互的竞争中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国债制度、议会制度,等等。
然而,即便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每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也是不平等的。因为它还涉及一个国家的体量及其发展对世界格局的影响问题,以及以大国的身份还是以小国的身份在世界体系中发展的问题。在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同一个全球体系时,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于这个体系之外进行自己的独立发展,由于这种特点,大国和强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小国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沃勒斯坦在他的《历史资本主义》一书中的解释很有见地。他认为,各国的发展是在一个整体世界中得以进行的而非孤立的现象。由于这一世界体系涉及的问题较多,沃勒斯坦将其归纳为十个问题:周期和趋势、商品链、霸权与竞争、地区性和半边缘性、融入和边缘化、反体系运动、家庭、种族和性、科学和知识、地缘文化和文明。总括起来,这十个问题主要集中在世界经济体系、世界政治体系和世界文明三个层次上。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是16世纪出现的,是一种单一的世界经济,其标志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在西欧形成。然而,只有大国才能在这个体系中起主导型的作用,而其余国家只能顺从这种大国意志的安排。因为在世界经济形成的过程之中,有三件事情非常重要:一是世界在地理规模上的扩张;二是对世界经济的不同产品和不同地区的劳动的控制方式的发展;三是相对强的国家机器的产生。这些国家也就成为核心国家。②[美]伊曼努尔·沃勒斯坦著,路爱国、丁浩金译:《历史资本主义》,社会文献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而世界体系的运作,也围绕着两个二分法进行:一是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二是经济专业化的空间等级,即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不等价交换和资本积累是这个体系运行的动力。而世界体系内的国家形成了三个地带:核心地区、半边缘地区和边缘地区。其根本性标志是核心地区与其他地区存在“不等价交换”。由此形成了世界体系的第二个特征:即多重国家体系。在他们看来,国家和国家体系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独特产物。尽管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产生之前也存在着各种政治实体,但只有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后才导致国家的产生,国家本身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在近代世界体系中,存在着两种政治,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国家为这些阶级控制和分配剩余价值提供了一种合法的机制。沃勒斯坦认为,国家从来就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它自产生就存在于国家体系中,而国家体系是一直在扩展的,在这样的变化过程中,几个国家利用国家机器在世界经济中使其利润最大化,成为“核心国家”,其余国家则逐渐边缘化和半边缘化。与经济两极化对应的是政治两极化,即中心地区出现强国,而边缘地区出现了弱国。强国控制的国家体系就是一种霸权体系。自资本主义体系产生以来,国家体系经历了三个霸权周期,产生了三个霸权国家,即荷兰、英国和美国。国家体系的霸权主要是指这样一种机制,即一个大国在这样的竞争机制中,能在很大程度上将它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甚至文化上的原则和意愿强加于国家体系中。尽管时代不同,但每一个霸权国家都有三个相似之处:第一,都是先在工业——农业领域,后在商业领域,最后在金融领域占有优势;第二,每个霸权国家在其称霸期间都奉行全球“自由主义”,反对重商主义对贸易的限制;第三,霸权国家的全球军事力量的模型是相同的,即霸权主要表现在海上 (现在是海上、空中力量)。沃勒斯坦指出,霸权虽然以经济和军事为基础,但不应该忽视政治方面。与广泛流行的自由主义理论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不是国家不干预市场,而是国家机器有选择地干预市场。资本主义的特征其实是生产要素部分流动,政治机器有选择地干预市场,霸权就是国家机器有选择干预市场的一个例证。①[美]伊曼努尔·沃勒斯坦著,路爱国、丁浩金译:《历史资本主义》,社会文献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11页。但霸权国家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际体系,使自己谋取最大利益的做法,必然遭到其他国家反对,因此,霸权不是一种永恒的状态,但追求霸权地位就像经济活动中追求利润最大化一样,是国家目标。因此,大国之间的竞争,也就是主要强国之间控制国家体系的斗争,构成了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战场。或者说,发展与争霸成为现代国家发展的一种主旋律。而一个国家是否是大国,或者说按照李斯特的标准是否是“正常国家”,也成为是否能够按照自己意愿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难看出,当德国等后起工业国崛起之后,人们已经意识到,发展不是一个单纯的国内发展的问题,而是一个在世界体系范围内各个民族国家相互竞争的动态进程。主权国家或是民族国家的作用,开始成为发展研究的重要对象。发展与争霸,或者说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能否成为规则制定者,已经是后起发展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而成为主导型大国,对于自身的发展显然是极为有利的。当然,这样一个大国的标准,基本上是一个现代的模板。在古代,判断是否是大国,主要取决于是否有众多的人口、辽阔的土地、强大的军队和巨大的历史功绩。到了近代,大国的标准有了变化。在大航海时代,西班牙脱颖而出,成为1500年以来最早出现的世界大国。诚然,人口和领土依然重要,但显然不及古代重要。在西班牙帝国鼎盛时期,总面积达1000多万平方公里,但95%为殖民地;人口达2000多万,远不及先前的古罗马帝国或古代中国。但西班牙还是堪称欧洲第一个成功登上世界大国宝座的国家。究其原因,一是海外扩张,以海盗模式攫取大量财富,以贩卖奴隶获取丰厚利润,以刺激欧洲海上贸易掀起殖民运动。马克思曾说,资本主义从头到脚沾满了血腥味。但即使如此,没有人否认西班牙在历史上的大国地位。这与时代背景有关。在西方史学家眼里,在当时技术相当有限、封建社会趋于瓦解的背景下,世界需要西班牙式的探索精神。但时代在变,竭泽而渔的殖民掠夺方式最终被历史所摒弃,西班牙式的大国之路走到了尽头,取而代之的是较为文明的英国和法国。这一方面与国家间实力的消长相关,另一方面也显现出大国行为方式的变迁。英法的殖民方式不是毫无节制地搜刮抢掠,而是将殖民地变成了廉价的原料来源地,并采取系统的榨取方式。与此同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文明,以格老秀斯《战争与和平法》为代表的国际法诞生,国际行为的基本规范也萌生了。18、19世纪时的大国已不再限于领土、人口、军队或者殖民掠夺,还要看它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②叶自成:《大国标准随时代变化》,人民网——环球时报,第11版,国际论坛,2005年11月28日。换言之,能够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主导型的作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
然而,要发挥主导作用,就必须成为主导型的大国,而这种主导型的大国,要在沃勒斯坦所说的三个方面占据优势,还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条件。第一是其体量的大小和有利的地理位置 (这一点可以参考李斯特关于正常国家的看法),第二是能够构建起强大有效的国家机器。有了大国的体量,就可以适时地运用自己的优势,逐步地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经济,然后在商业和军事方面齐头并进,跻身于强国之列;但第二个条件,却往往比较艰难。因为构建一个现代的有效的国家机器,本身也是现代化的一个基本任务,它既与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与传统有关,也与周围的国际形势有关。国家既是一个抽象的大观念,③从亚里斯多德的“国家是自然的”,柏拉图的“正义原则”,卢梭提出国家是人民的“总意志”,关于国家的抽象概念的争论是十分丰富的,在某种意义上,整个政治学的中心议题就是关于国家的争论。又是一个与观念有关的具体存在的实体:这个国家实体包括一切与国家有关的行政官员和公职人员,国家所办的各种经济实体,国家的军事力量,以及国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矿山等资源。德国学者博赞克特甚至认为,“国家是一个包括了决定人类生活的所有机构设施——从家庭到行会、到教会、到大学——的整体,它包容了所有这些机构,不仅是作为这些机构的范围之总和,而且是作为赋予政治整体以生命和意义的结构”。①邹永贤、俞可平等:《现代西方国家学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页。显然,国家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也是一个与社会有着密切联系的实体。由于国家这个特殊实体的存在,国家的税收有很大一部分被“国家”自身消耗了。也由于国家的这种实体性特点,国家具有自己的利益,所以,国家与个人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便产生了长期的、结构性的矛盾。但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任何一种取消国家的尝试都未能取得成功,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而现代化则对国家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国家的属性必须从王朝国家转化为民族国家,而且还要承担发展的任务,这是与传统国家的最大不同之处。因此,现代国家实际上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外部环境的挑战与内部发展的挑战。它要在全球化的冲击下生存和发展,就必然要建立一个有利于民族经济发展的市场体系,保护自己的幼稚产业,根据本国的情况制定长远的战略规划,发展本国的教育事业,提升科技水平,给国民提供基本的现代文明生活保障(这些都与李斯特的学说不谋而合),有较为先进的军事力量,能在国际事务中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从历史角度看,从19世纪开始,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试图通过整合行政机构、法律体系和教育制度而更加紧密地控制确定的领土范围,他们希望在地图上规划并调查他们资源和税收的范畴,并通过更加连续的方式来利用这些资源,并排外性地要求其民众对它的忠诚。②C.A.Bayly,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1780-1914,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2004,p.247.这与前现代国家只在某种特定状况下提出的类似要求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同时也与现代国家始终面临着全球性的竞争压力有关。也因为这个原因,国家问题成为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无论什么样的主张,如果忽视国家建设的问题,或者把这一问题置于无足轻重的位置,那么,这样的主张一定是祸国殃民的。
实际上,在整个现代社会中,国家自身还具有强大的经济作用。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往往认为,国家只应该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监护者,这固然是正确的。但他们往往忘了,国家实际上扮演着经济生活中的三重角色。国家既是比赛的规则制定者,也是裁判,同时还是潜在的运动员:当比赛对本国不利时,本国的政府往往赤膊上阵,直接参加比赛 (这一点在霸权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此外,从再生产的角度看,国家支出也具有重要意义。国家的支出基本上有三类:国家资本支出、国家的转移支付和国家的消费。③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第254-256页。这些支出,无论是商业立法还是公共工程,乃至军事设施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一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发展的方向。就美国政府而言,其消费支出已经占到整个国家的消费支出的1/3。其份额之大,对一国经济的影响可想而知。
那么,为什么在国际体系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几百年的历史过程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而不能在可预见的未来成为强国?在众多的发展理论学派中,以弗兰克为代表的依附论者从国际经济学方面寻求突破口做出的解释最有说服力。他们认为,不发达状态是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在恶劣的贸易条件下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导致的结果,第三世界的落后是当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所造成的。只有从这种国际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发展中国家面临困境的根源。从马克思,尤其是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论述看,依附论者至少得到了如下一些启示:第一,资本具有创造世界市场的倾向,帝国主义的扩张是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本质的反映;第二,由此扩张形成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各国在其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西方列强处于支配的中心地位,亚非拉国家则处于边缘的被剥削的地位。西方的发达是列强暴力分配世界市场诸价值的结果,是在很大程度上掠夺不发达地区剩余价值的产物。弗兰克使用了“都市中心”和“卫星”的概念:发达国家为都市中心,其他落后国家则是卫星。都市中心通过各种管道吸取卫星的血液和营养。而沃勒斯坦则以“核心”和“边缘”的概念取代了弗兰克“都市中心”与“卫星”,核心经济主要指制造业、银行业及相关的先进经济活动,而边缘经济则基本局限于初级产品的生。只有“中心”国家才能在世界中获利,而“边缘”国家却吃尽了苦头。①Bjorin Hettne,Development Theory and the Three Worlds,London:Longman,1990,p.86.因此,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世界经济而非民族国家的现象。②Immanuel Wallenstein,ed.,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p.15,19.即是说发达与不发达都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结果,而非某一地区和某一国家的现象。与弗兰克一样,沃勒斯坦的世界经济体系是由边缘的剩余价值流向核心构成的,但与弗兰克的区别在于,他不仅用国际劳动分工和技术领先来解释为什么北部核心地区能占有其余地区的剩余价值,而且考虑到了政治的因素,即认为政治力量的不对等强化了世界的不平等。核心经济能够发展出强大的国家机器,这种强大既表现在国内又表现在与他国的关系之中。边缘经济只能产生弱小的国家,意味着它们无力控制与国际经济相联系的条件,其从属经济的地位因此变得更为确定。③C.A.Bayly,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1780-1914,chapter 7.换言之,落后国家基本上没有可能建立起现代的强大国家机器。那么,它们在参与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其扮演的角色只能由原来的强国规定,而不可能有自己的发言权。尽管很多学者的思想,包括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的学说都产生于二战之后,但正是这一历史的距离,使他们的分析更为透彻和精辟。
显然,在发展的过程中,国家的作用极为重要,而落后国家无法建立起强有力的国家机器,也就意味着它们在原有的体系框架内不可能获得任何“公平”发展的机会。如何摆脱这种困境,是发展理论下一步必须解决的问题。
五
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以自己的独特方式解答了这一问题,那就是这样的模式可以在很短的时期内建立起一个高效的国家机器并通过它推动经济强力发展。尽管这样的体制有很多缺陷,但不可否认,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的实践甚至迫使西方发达国家改变了自己的社会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的苏联,通过计划经济模式,在一定的时期内集中了全民族的资源,产生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而这个奇迹中,对西方冲击最大的还不是其经济效益,而在于它完全解决了失业等西方十分头痛的问题。失业问题的解决,使社会主义对西方的工人阶级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并使发达国家的工人不断地希望通过推翻资本主义体系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尽管社会主义思潮在西方一直有着相当的影响,但真正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能性,只是在苏联成立后才变得现实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西方的政治机构一方面通过强制镇压工人运动,加强对社会主义思潮的压制等方式来避免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另一方面,也开始认真准备社会改革,甚至罗斯福和丘吉尔等人也认为,通过一步步的社会改革,是避免自身社会通过革命进入共产主义体制的唯一方式。1918年,英国内阁副大臣琼斯向首相劳合·乔治提出一份报告,要求政府把推行社会改革计划作为医治社会和政治动乱的药方,并认为如果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在真正愤懑不平的土壤中扎下根是危险的。劳合·乔治对此观点表示认同,他承认“我不怕革命,我也不怕布尔什维克,但我害怕它引起的反响”。④转引自:Duncan Brack and Robert Ingham,ed.,Dictionary of Liberal Quotations,Politico's Publishing,1999,p.111.换言之,社会主义实践不仅指出了另一条发展的路径,也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西方发展模式的根基。二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以及第三世界很多国家纷纷效仿社会主义模式,证明社会主义实践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而发展中国家自发地拥抱社会主义理念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落后国家的人民不愿意坐等历史自然地发展,等候世界强国“赐予”自己发展机遇,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改变或者至少也要冲击这样的国际体系,使自己获得一定时间和空间上的独立发展的机遇。
这种自发要求涉及的问题是——发展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我们已经探讨过,当代的发展是一种全球化的发展,而在这种发展态势中,各国的位置以及对发展红利的分享有着巨大的差异:发达国家在全球化的利益重组过程中可以说是占尽了便宜,其结果不仅在世界现存的贸易体系中使发达国家更富,还使得发展中国家更穷。
问题的实质在于,平等与公平永远是一个相对的口号。只要这个世界上有资源需要开发,有开发者和被开发者,就必然构成债务关系。而且债务关系的衍生必然会带来越来越不平等的对资源的剥削与掠夺。发达国家的发达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不平等的资源剥削累积的成果。在工业文明通过差距不断恶性膨胀的今天,布兰德认为这构成的是“一种奴隶制新形式”。①林希:《债务:4400篮桔子和“奴隶制新形式”》,《三联生活周刊》,1997年第24期,第7页。正因如此,在二战后的全球化过程中,尽管世界的财富总量急遽增长,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却越来越大。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7年,高收入国家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5.9%,其GNP却占世界GNP的79.5%,富国人均收入与穷国人均收入之比已从1960年的30∶1、1990年的60∶1扩大到1997年的74∶1,欧美国家居民每年花170亿美元给宠物购买食物,而发展中国家约有11亿居民缺少住房。②转引自李长久:《改革国际秩序,实现共同繁荣》,《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5期,第14页。不仅如此,发达国家在全球化的贸易活动中,还有意识地将各种公害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原田正纯在日本《世界》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公害有五种形式:1.将危险的公害型企业转移,印度聚乙烯醇农药泄漏事件就是将危险技术转移的一个典型例子;2.将在本国禁止销售和使用的产品出口,比如农药。目前发达国家出口的农药中,30%属于在本国禁止使用的,而全球每年因农药中毒的人数已经高达75万人;3.将产业废弃物转移至发展中国家;4.掠夺性大量进口别国的资源;5.因提供资金援助而导致破坏环境的结果。
举这些例子,决不是要反对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因为这种全球化浪潮,尽管有着种种世界强国将自己的意图强加于他人之上的实质,它与19世纪相比却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即在这种全球化的浪潮中,较为落后的国家只要自己能够有效地把握机遇,就能在这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获益。这中间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殖民主义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世界强国通过赤裸裸的军事占领或是其他方式公开掠夺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历史,甚至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也是得不偿失的。于是,这种优势转化为发展中国家生产低端产品,而发达国家控制高技术领域。这种分工依然是不平等的,但比起赤裸裸的掠夺,毕竟还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发达国家在这种全球化的过程中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进一步加大自己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等方面的差距,使自己永远保持在核心技术与其他关键性领域的优势,保持自己“标准制订者”的地位,并使自己的领地成为花园世界,至于会产生各种有害废弃物的产业,要么将其全部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要么将这些废弃物“卖”给发展中国家,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上文已经列出一些,我在这里就不愿意再列举了。那么,我们在这种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是否愿意成为别人的废弃物转移基地,愿意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世界工业化废品的垃圾场?
换言之,在西方原有的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大体上只能扮演集体打工仔的角色。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主义是落后国家实现自身现代化目标而选择的一种特殊的发展方式。苏联在被发达国家围追堵截的环境下,尽管有很多严重的失误,还是依靠自身的力量在短期内建立了现代的工业和国防力量,其发展速度是人类工业史上的一个奇迹。从历史的角度看,中俄两国都在这一巨大的变迁中获得了独立自主从事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建立了一个基本完整的现代工业和科研体系,奠定了两大民族现代化的基础,并帮助其他一些殖民地国家摆脱了被西方强国边缘化的命运。
一些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理解是,“现代性是少数人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水平建立在大多数人付出的代价之上的——由不平等引发的贫困——环境恶化、自然被摧毁、文化贬值,以便满足最富有的一小撮人的消费。对社会主义者而言,替代的方式就应该是通过集体所有制、公共控制、计划以及民主的推力来理性控制发展的进程。”①Richard Peet and Elaine Hartwick,Theories of Development:Contentions,Augments,Alternatives,pp.278 -279.
我们对这样的总结或许并不认为其十分全面,但重要的是,在发展研究的理论层面,社会主义的实践终于使“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目前的世界市场发展格局,基本上已经没有经济学原理上纯粹的市场国家:每一个国家,几乎都既有市场,也有国家力量的干预和调控,区别只在于调控的方式不同,力度不同,以及市场的发育成熟度不同,法治的建设是否到位等等。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终于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对自己发展道路的选择权。
近年来,中国发展如此迅速,让许多拉美国家羡慕不已。得知中国成功的秘诀在于找到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时,他们感慨不已——长期被美国的发展经济学所“忽悠”,后来又被告知只有靠“华盛顿共识”才能发展起来,让拉美国家走了那么多年的弯路。拉美一些国家实施的21世纪的社会主义,就是摆脱美国影响、探索走自己发展道路的尝试,可惜并未成功,政治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依旧。②王义桅:《拉美之行的十大困惑》,http://www.zaobao.com/special/zbo/story20150113-434753但他们的处境恰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主义实践在选择发展道路上的价值。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社会主义实践都使世界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路径,也使得发展理论本身更加丰富多彩。或许,只有在这种多样化探索的基础上,构建一个以和平发展为主导的世界才有可能,而占全球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才有可能真正分享到世界发展的红利——这应该是社会主义实践对发展理论以及世界发展本身最大的贡献。
Contributions of Socialist Practice to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CHEN Xiao-lv
(Department of History,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0093,China)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can never be a simple academic problem since it must always b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different models of development and different interests of every country.In modern history,developed countries enjoyed the most benefits of globalization and also made the rules of the modern world.In this situation,how to look for their own development path for late-development country in such a pattern become very urgent.Socialist practice offers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these demands.Socialist practice enables the possibility of multi- polarization in world development and enriches the theory of development itself.Only with this foundation is it possible to build a world dominated by peaceful development,and possible for peopl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who occupy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to truly enjoy the dividends of the world development.Perhaps that is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of socialist practice to the theory of development and to the actual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socialist practice;theories of development;multi-polarization in world development
2015-05-28
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从发展的角度重新评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意义”(12ASS002)的阶段性成果。
陈晓律,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平台长,南京大学欧洲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世界近现代史、英国史、现代化研究。
责任编辑:宋 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