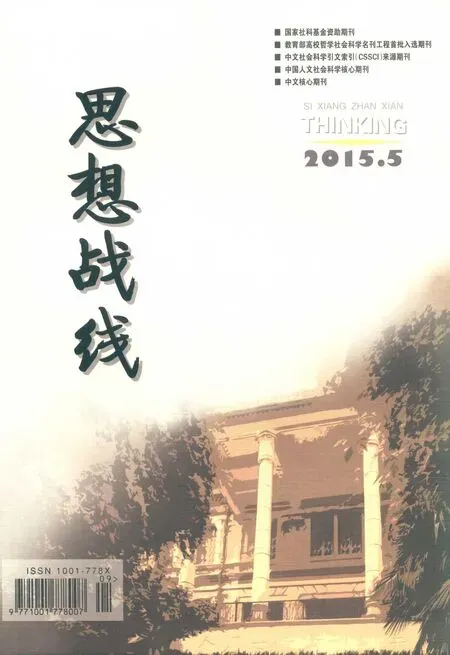引进与再造
——social anthropology在中国
2015-04-09张丽梅胡鸿保
张丽梅,胡鸿保
引进与再造
——social anthropology在中国
张丽梅,胡鸿保①
反观学科史,讨论 “social anthropology在中国”这样一个话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历史与现状。中国学人在引进西方理论和方法的过程中,一直都有主动选择、修正和再造的一面。中国社会学在其草创和初步繁荣阶段确实存在一种人类学传统,这既与功能学派在英国的特殊性有关,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学人引进social anthropology,再造中国本土社会学过程中的自主选择及创新。总体而言,当前中国社会学在理论和方法方面比人类学更具自觉意识。
社会人类学;社会学;功能学派;本土化
近年来,学界出现了 “民族学的中国学派”的提法,并围绕这种提法开展了一些研究和讨论。我们打算以此作为切入点,反观学科史,讨论一下 “social anthropology在中国”这样一个话题,以史为鉴,希冀对认识我们当前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发展起点积极作用。
一、当前中国语境中的 “社会人类学”
目前我们的学科专业设置是把人类学 (体质人类学部分除外)放在社会学一级学科之下,而民族学是与社会学并列的另外一门一级学科。一方面,争取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三科并列的意愿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在权威出版物中业内人士又是这样向公众解释 “社会人类学 (so⁃cial anthropology)”的:
(社会人类学)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人类各族群的社会和各种社会文化组织、制度进行比较研究,认识与探究人类社会生活通则与社会发展规律的学科。人类学分支学科。由英国学者J.G.弗雷泽在1908年为利物浦大学开设讲座时创用,主要在英国、瑞典、芬兰等国使用。20世纪初,其研究对象为非西方民族,是比较社会结构与功能、归纳社会通则的学科,故也称比较社会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其研究对象扩展到西方社会。一般认为,英国的社会人类学与美国的文化人类学、欧洲大陆的民族学是异名同义的学科。也有学者认为,社会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 (民族学)尽管都强调实地研究,但各自的旨趣与研究范围则有差异:前者着重研究社会组织和经济、宗教等制度;后者的研究范围比较宽广,除社会组织外,对物质文化、仪式、意义和象征体系等给予较多关注。所以,有人认为社会人类学是广义文化人类学中的一门专研究和阐释社会组织与制度的分支学科;但较多学者仍持社会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 (民族学)是基本相同学科的看法。①《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第2版第19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402页。
从这样的一些认识和解释来看,似乎social anthropology、cultural anthropology和ethnology在中国大致相当,只是分别来自英国、美国和欧洲大陆的不同国家传统而已。我们觉得,可以把英语世界的 social anthropology与中国语境中的“社会人类学”所指的差异做些对比描述,透过历史的发展来看中国学人对于social anthropology的引进所做的努力,以及在本土再造社会学的雄心。
二、中国学人对于social anthropology的引进与再造
众所周知,社会学这门学科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西方传入中国的,而翻译出版西方著作、引介西方学说则是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之一。但我们注意到,早期的社会学先驱在引进西方思想的时候并非简单地移植,而是结合中国社会现实和思想传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选择和改造,并由此开始了最初的本土化尝试。比如,严复引介西方进化论人类学思想时,就从保种救亡的时代需求出发,以 “原强” “保身治生”“利民经国”为基本框架,对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等人的进化论思想进行了选择、改造、综合与创新。他将赫胥黎 《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翻译为 《天演论》,但只选译了前半部分 (前半部分也有些内容没有译出),且多采用意译的方式,还增加了很多按语,直抒己见甚至对原作者的一些观点进行反驳。另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他还将道德的观念注入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中,宣传 “以人持天,与天争胜” “所存者善”,从而激励国人积极探索和追求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外的另外一种进化可能性。①陈国庆,刘惠娟:《严复对进化论的选择与创新》,《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吴浪平,都兰军:《西学在东渐过程中的中国化——以严复对西方进化论的改铸为例》,《北方论丛》2012年第1期。在 《群学肄言》一书中,严复将 “社会学”翻译为 “群学”,更是体现了其融通西方社会学思想和中国文化传统的自觉努力。正如李培林所言:“‘群学’在中国的产生,自然是西学东渐和中外文化碰撞、融合的结果,可它一经导入和产生,就完全被纳入中国的文化话语系统和观念系统;但作为新的种子,它也在改变着这一话语系统和观念系统。”②李培林:《中国早期现代化:社会学思想与方法的导入》,《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1期。
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引进的外国思想和学说的日渐增加,学者们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反思和本土化的重要性,更具自觉意识的本土化运动在社会学界逐渐兴起和发展。
费孝通在纪念吴 (文藻)老师逝世10周年的发言中,介绍了吴老师如何分析比较、反复权衡之后才决定引入英国功能学派理论,以纠正当时已经发展起来的中国社会学存在的偏差。“他把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功能学派引进中国,是想吸收人类学的方法来改造当时的社会学。因为人类学注意到文化的个性 (即本土性),因而强调研究者应采取田野作业的方法。吴先生提出社会学中国化就是着重研究工作必须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③费孝通:《开风气育人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9期。同时参见吴文藻 《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林耀华等 《吴文藻传略》,《民族教育研究》1994年第2期。在吴文藻看来,社会学要想实现彻底的中国化,一是要在功能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积极开展社区调查,二是要按照这种研究模式的要求,训练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并且能够独立开展高质量社区调查的社会学人才。④郑杭生,王万俊:《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年,第126页。换言之,吴文藻对英国功能学派并非简单地引介和移植,而是试图将该派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中国社会的实地调查研究之中,通过推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融合,来再造当时的中国社会学。在此过程中,不仅去掉了功能主义人类学原本具有的为英国殖民统治服务的成分,而且,打破了西方人研究非西方落后民族的学科陈见,东方文明人自己研究本文化成了人类学一大亮点。另外,有研究者撰文强调了民国时期社区研究理论的美国学术渊源,认为吴文藻等人 “在大力引介英国功能派文化人类学理论的同时,亦相当认可美国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社会学理论”,他们倡导的社区研究虽然主要以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为指导,但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的植入,但其现代社区研究理念、农村社区和都市社区的研究范式依然主要遵从美国学理。⑤阎书钦:《移植与融会:民国时期社会学理论体系构建的美国学术渊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阎书钦:《范式的引介与学科的创建:民国时期社区研究理论的美国学术渊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再联系吴文藻当时邀请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学派的拉德克利夫—布朗和美国芝加哥社会学学派的帕克来华授课,指导学生开展实地调查。不难看出,他在引进西方理论时,是有自己的主动选择和审慎思量的:他试图将英国功能派人类学的方法和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区研究范式相结合,来改造中国社会学、促进本土化。
正是在吴文藻及其弟子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功能学派”得以形成,并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学科史研究者看来,它既是一个社会学学派,也是一个人类学学派。费孝通自己则说过,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和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在中国 “一推一拉”就实现了两门学科的 “通家之好”。⑥潘光旦在 “派与汇”一文中就使用过该词,参见潘光旦 《潘光旦文集》第6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4~75页。其实,诚所谓 “对他而自觉为我”,当时中国是有多个学派共生的。从社会学史的角度看,与以晏阳初和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以孙本文为集大成者的综合学派,以李大钊、瞿秋白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相对,它被名为 “社区学派”或 “燕京学派”;①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01~171页。从人类学史看,它是“北派”,与 “南派”和 “华西学派”等相对。②李绍明:《略论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而其中突出的一点则是:惟独 “中国功能学派”带有浓厚的跨学科特色 (社会学与人类学)。
这与当时社会学与人类学在英国的紧密联系是不无关系的。当年为布朗的 《社会人类学方法——布朗文选》做 “导言”的印度学者Srini⁃vas说过: “美国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都形成了各有特色的研究体系,而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却被认为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如果这两门学科在不久的将来合并成一个,是没有必要感到奇怪的。”③[印]斯林尼瓦斯:《导言》,载 [英]拉德克利夫—布朗 《社会人类学方法》,夏建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12页。然而,若以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和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这两种刊物近期所发表的文章主题和内容来看,当前英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似乎还是各有侧重的。许烺光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此文中,社会学与社会人类学这两个词基本同义。现在中国,已经少有学者强调这两门原来不一样的学科之间的差异。在我们的大学中,社会学家可以讲授人类学的重要课程,纯粹人类学背景的学者也可以开设社会学的讲座。”弗里德曼注意到这一现象,并明确指出,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这种 “相互缠绕”产生于学科发展之初,与西方国家中两个学科经过长期的独立发展和相互采借,进而走向交叉和融合的路径有很大的不同。④Maurice Freedman,“Sociology in China:A Brief Survey”,The China Quarterly,no.10,1962,pp.166~173.
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学在其草创和初步繁荣阶段,确实存在一种人类学传统。这既与功能学派在英国的特殊性有关,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学人引进social anthropology再造中国本土社会学过程中的自主选择及创新。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界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批评时有展开。比如,文化社会学家孙本文曾发表文章批评潘光旦的优生学说存在四个根本错误,潘光旦很快撰文对孙本文的批评进行了商榷,之后孙本文又撰写一篇文章对潘光旦的商榷予以回应。⑤孙本文:《文化与优生学》,《社会科学杂志》(上海)1928年第3期;潘光旦:《优生与文化——与孙本文先生商榷的文字》,《社会学刊》1929年第2期;孙本文:《再论文化与优生学——答潘光旦先生商榷的文字》,《社会学刊》1929年第2期。潘光旦在为费孝通 《生育制度》作的书序里明确表示,自己与费孝通分属不同的学派 (生物学派与功能学派);同时也谈到社会思想分派的利弊,以及人的科学的新发展趋势,当是由派分而求汇合。不过,20世纪6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 《中国的社会学:一个概述》及 《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等文章⑥Maurice Freedman,“Sociology in China:A Brief Survey”,The China Quarterly,no.10,1962,pp.166~173;Maurice Freedman, “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4,no.1,1963,pp.1~19.的面世,引发了包括中国同行在内的学者的关注,并在很大程度上使得 “中国功能学派”成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在国际上的一个标志。另外,倡导 “社区方法论”的 “中国功能学派”相较于其他学派更加贴近社会现实、更具针对性和应用性,⑦参见黄向春 《中国人类学的南方传统及其当代意义》,《光明日报》2009年6月2日。再加上费孝通等知名学者的持续创新和影响,这一切使得一些学者对于该派的成就与不足缺乏必要的反思。
与之前的比较研究中一边倒的评介情况不同,近些年来对于民国时期社会学史的研究评价,显得有褒有贬。比如,王铭铭在一篇文章里就谈到对 “中国功能学派”及吴文藻本人的批评。他指出, “中国功能学派”面临着社会学“民族志化”和人类学 “社会学化”的困境。他也指出吴文藻与派克的社会学不同,认为,吴文藻对城市社会学的乡村化,导致了一个令人遗憾的后果:中国社会科学家习以为常地将城市描绘为 “中国的未来”。……吴文藻对派克城市区位学的 “诠释”,成为一个服务于社会学实践的没有内容的工具……。⑧王铭铭:《民族学与社会学之战及其终结?》,《思想战线》2010年第3期。再比如,李章鹏在研究社会学中国化时提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从创系到1934年,以Booth(布思)式调查为主导, “社区研究推行时期”是在1932~1937年。而 “吴文藻等人在为社区研究争地位时,总是尽力攻击布思式调查”,但吴文藻等人 “对所在系的学科改造并不是十分成功”,而且他们忽视量化调查的做法,不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来看都是不太妥当的。⑨李章鹏:《社会调查与社会学中国化——以1922~1937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例的研究》,载黄兴涛,夏明方 《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兴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7~91页。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孝通在晚年回忆帕克的文章里依然轻视统计方法:“要说明中国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只有实地观察,那就是社区调查。”⑩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另外,当时中国学院社会学中居正宗地位的主流形态,不是功能学派,而是以孙本文为代表的综合学派。⑪周晓虹:《孙本文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该派之集大成者孙本文,在1931年明确使用了社会学“中国化”和 “中国化的社会学”等概念,是最早正式地、明确地倡导社会学本土化的学者,并身体力行为社会学本土化做出了巨大贡献。①郑杭生,王万俊:《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年,第118~124页。不过,与吴文藻强调 “认识国情和改造社会”不同,孙本文更强调建立符合中国现实的综合性的社会学理论体系。②周晓虹:《孙本文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孙本文在引介美国相关社会学理论,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学术和现实条件,创造性地建构民国时期社会学理论体系的不懈努力和卓著贡献。
三、早期研究传统的断裂与传承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民族研究,实际上部分替代了原先社会学、民族学和社会人类学承担的任务。明显的变化是引进苏维埃学派及斯大林模式。③杨圣敏,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六十年》,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9~41页,第54~86页。不过,中国学者还是在引进过程中发挥了自己的能动性。费孝通后来总结当年的民族识别工作曾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的民族理论,特别是斯大林有关民族的定义,是我们进行民族识别的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但是我们国家有自己的具体国情。 “因此,在我国民族识别工作中,既不能搬用资本主义时期所形成的民族特征来作为识别标志,又不应该不把这些特征作为研究的入门指导。”④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纳日碧力戈也撰文反驳了墨磊宁所谓 “英国模式”的观点,认为民族识别是一项综合性的国家工程,不是所谓的 “苏联模式”,也不是所谓的 “英国模式”,而是各个模式在中国实践中变通,“洋为中用” “古为今用”的创造性成果—— “中国模式”。⑤纳日碧力戈:《重观民族识别:综合与变通》,《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20世纪60年代初,弗里德曼发表 “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之后,“中国功能学派”尽管在国内不再被提起,但国际声望却节节攀升。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学界片面强调了弗里德曼关于 “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的说法,却忽略了他对当时中国的功能主义式社区研究的忧虑和批评。在他看来,当时的社区研究,一方面忽略文献, “不那么具有历史学色彩”,另一方面对社区之外的 “更广泛的制度框架”关注不足,在强调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之余,一定程度上失落了社会学的视角。⑥Maurice Freedman,“Sociology in China:A Brief Survey”,The China Quarterly,no.10,1962,pp.166~173;Maurice Freedman, “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4,no.1,1963,pp.1~19.费孝通晚年时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在指导学生做盘村瑶族研究时,就强调在 “微型研究”之外,还必须关注社会变迁,并突破村落的界限 “以地区为研究对象进行综合研究”。⑦张丽梅,胡鸿保:《从功能论到历史功能论——兼谈经验材料对理论的修订功能》,《广西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
社会学与人类学学科在新时期的恢复与重建,同样离不开对西方相关理论学说的引介,这也是费孝通所言 “补课”之重要方面。文军曾说到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欧美社会学理论的引进,他指出,“中国社会学自1979年恢复和重建以来,其在理论研究方面大致经历了‘缺失—移植—融合—反思—重构’的过程”,“尽管其一直存在着经验研究 ‘过密化’和理论研究 ‘稀松化’的严重不足,但在其基本属性上却一直是坚持东方理论与欧美理论的融合与渗透,尤其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学理论在不断增强对欧美社会学反思性探索的基础上,开始重构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并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学在新世纪的发展”。⑧文 军:《从移植与融合到反思与重建:1980年代以来欧美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引进与发展》,《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5期。人类学尽管在译介西方成果方面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和成绩,对国外相关理论的评论和分析也日见其多、愈加精到,但与社会学类著述的翻译和评介相比,仍然略显落后。与社会学重视理论研究和理论提炼不同,人类学民族学似乎更多地关注田野调查本身,及其对相关理论的诠释或检验。这在近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指南中也可见一斑。以2012~2014年为例,社会学的课题指南中一直不乏能够体现跟进、反思西方理论方法,并在此基础上着力挖掘和建构中国社会学自身传统、成就和理论体系之努力的题目,如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构建的探索与研究” (2012年)、 “社会学在中国本土化的历程与经验研究” (2012年)、 “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借鉴与反思研究” (2012年)、 “当代中国社会学的成就、问题及趋势研究” (2013年)、“中国社会学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研究” (2013年)、“费孝通学术思想的当代意义研究”(2013年)、“西方社会学的新流派研究” (2013年)、“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新进展研究” (2013年)、“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研究” (2014年)、“中国社会学的社会行动史研究” (2014年)等;而人类学民族学的选题指南中,则几乎看不到类似的题目。以一斑而窥全豹,当前中国社会学在理论和方法方面,比人类学似乎更具自觉意识。
继费孝通提出 “文化自觉”之后,近年来郑杭生等学者十分关注 “理论自觉”的问题,强调要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进行 “建设性地反思”,为回顾、观察、瞻望中国社会及中国社会学提供新的概念工具和理论视角。①郑杭生等:《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社会运行学派则被一些学者誉为 “理论自觉历程中成熟的中国社会学学派”。②董翔薇,董驹翔:《社会运行学派:理论自觉历程中成熟的中国社会学学派》,《云梦学刊》2014年第1期。
人类学方面,郑杭生说过,包括费先生在内的老一辈社会学家,事实上是在做着发扬学派传统、推动新学派建设的工作,中国存在一个名副其实的 “费孝通学派”,但费先生对学派问题持非常慎重的态度,他很少从学派的角度谈问题,而中国社会学的 “实用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学派的建设。③郑杭生:《中国社会研究与中国社会学学派——以社会运行学派为例》,《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1期。杨圣敏曾于2008年尝试提出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功能学派”或 “民族学的中国学派”的看法,④杨圣敏:《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 (1978~2008)》(民族学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2页、第340~341页。然而,正如他在一篇回顾新中国民族学史的论文中所言,尽管 “创建中国学派是民族学传入中国百年来,我们几代学人一直在追求的一个梦”,但目前“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人类学学派尚未形成,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仍然是以西方学界的理论方法为主要依托的学科。因而,中国学派的建立任重道远”。⑤杨圣敏:《新中国民族学之路——从研究部起始的60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在2014年冬天召开的 “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学科建设圆桌恳谈会”上,杨圣敏再次强调,我们不能跟在西方人身后亦步亦趋,而是必须加强对中国社会实践的研究,在扎扎实实的实地调查中,解决中国当前的实际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创建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创建中国学派。⑥杨圣敏:《学科如何进步:四个方面的思考》,《西北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
总之,从实际情况看,经过近30年的努力,当前中国社会学界学派意识已经明显增强,学派的发育也要比人类学界来得更加充分。
四、结 语
学术的历史发展告诉我们,无论是后人对前贤的读解,还是国人对于外来文化思想的引进,都会或有意或无意地修正、再造。大的方面来看,中国近代 (现代)学术的建立,就使传统学术来了一个脱胎换骨。舶来的社会学、人类学不用说,即使是文学,也是今非昔比。⑦在传统的目录学中群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古今文学含义有所不同。古代的所谓文学容纳了今天看来不属于文学的一些体裁。
总之,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人为了促进本土学术的发展、更好地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一直注意引进西方比较成熟或者比较新近的理论和方法,且在引为己用的过程中进行了创造性的涵化。这种创造性的涵化,在对功能学派、进化学派、历史学派等西方学派的引入过程中均有体现,已成为人类学中国化的一个基本原则。
另外,对西方理论的选择性引进和创造性改造,一方面需要融入本土社会现实和历史传统,另一方面又会对新的本土传统的形成产生促进作用,而这种新的本土传统一旦发展壮大,完全可能对西方引入地的学术思想和路线产生影响。换言之,中西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影响,往往具有双向性。吴文藻等人对功能派人类学的引进和再造,不仅在中国造就了 “中国功能学派”以及影响深远的社区研究传统,还对英国人类学产生了可见的影响。
学科重建至今已有30多年,期间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均得到长足发展,制度建设、人才培养、域外成果译介、本土经验研究及理论探讨,均呈日渐兴旺之势。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以及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崛起,随着中国学人 “自觉”意识的进一步增强,以及“中国话语”的发展,出现一个 “中国时代(Chinese phase)”不是没有可能。
(责任编辑 甘霆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人类学的国家传统及其创新研究”阶段性成果 (12CMZ018);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基础性研究课题资助项目 “国家传统及其创新:人类学历史与理论研究的新视角——以英、中两国为中心的考察”阶段性成果 (141094)
张丽梅,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重庆,401120);胡鸿保,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