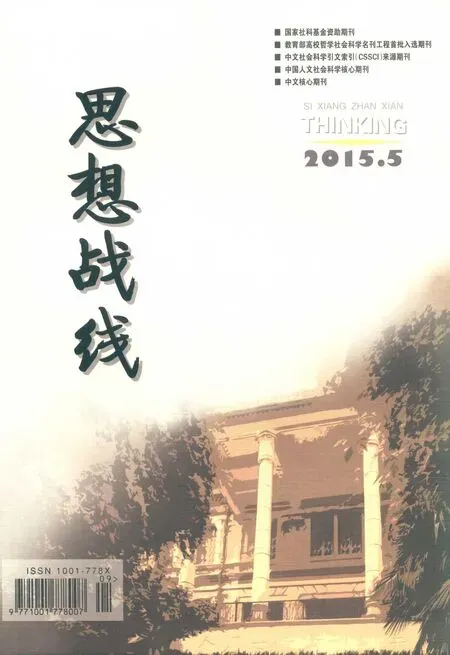论后藏“望果节”仪式结构及象征意义
2015-04-09才贝
才 贝
论后藏“望果节”仪式结构及象征意义
才 贝①
后藏 “望果节”仪式作为一个复杂而多义的综合体,其仪式结构和象征意义充满隐喻。结合前人研究、相关文献分析以及后藏 “望果节”的田野实践来看,显然 “王”的符号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正如 “仲德苯”的王政治理方式依然鲜活于民间,由此吐蕃王朝对于藏族社会的深刻影响昭然若揭。吐蕃王朝 “伪装”成各种符号而并存于佛苯之间,这就像谜语本身,对于打破佛苯二元论框架的藏族民间宗教及仪式研究,多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和研究视角。
“望果节”;仪式结构;象征;“仲德苯”;王权
一、引 言
南木林县位于西藏日喀则地区,在藏区的地理认同上属于后藏 (gtsang)。从山系与河流来看,位于冈底斯与念青唐古拉山脉的交汇处,雅鲁藏布江由南向东蜿蜒流过,其中湘曲①本文中的藏语音译以当地方言为主。(shangs—chu)河将县城一分为二,润泽着两岸的乡土。因此,藏族历史上这一片区域称为湘巴(shangs—pa)。日喀则地区作为西藏的 “粮仓”,河谷地带的丰饶,孕育了别具一格的湘巴农牧景观。本文所探讨的田野案例 “望果节” (vong—skor,转田)是由南木林县艾玛乡 (ae—mar)所操作展演的传统农业节庆仪式。艾玛乡位于县城南部,全乡辖区面积418平方千米,耕地面积共有14 817.46亩,平均海拔3 830米,以盛产土豆而闻名;全乡有1 259户8 539人,辖15个村委员会。吉雄 (skyid—gzho)、德 (bed)、阿荣 (a—ron)3村所在的一条沟称为 “牛”(nyug),德村为牛曲果林寺 (nyug—chos—vk⁃hor—gling)所在地,在当地传说中,牛沟还被称为切隆 (chos—lung),意为经沟,与莲花生圣迹密切相关。“望果节”仪式队伍需要穿越整个牛沟的神圣地理。笔者在田野考察时,意识到探讨该仪式的结构与象征意义,既要面对传统藏学关于佛苯的分类和认同问题,还应回归到现代藏学以及人类学对于神山及王权研究的脉络体系中。
意大利藏学家图齐在其考察西藏宗教的力作《西藏宗教之旅》中,将西藏的宗教分为佛教、苯教、民间宗教3个部分,并从面对神魔势力的人类、人类和房宅的保护、灵魂、死亡、神香和焚香、对未来的幻觉 (对一种行为的吉祥或不吉祥预兆的研究)、财产和畜群的保护等7个方面对民间宗教进行阐述,他认为,“在民间宗教信仰中,到处都可以感到一个斑驳世界的残存,它包括了雪国的所有生活方式和前佛教信仰”。②[意]图齐:《西藏宗教之旅》,耿 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185页。图齐阐述民间宗教时,更为关注土著传说和密教之间的相似性,他称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似的“心理气氛”,使得佛教在当时非常容易被吐蕃社会所接受,他花了大量篇幅讲 “世俗世界之神”被佛教赋予的新角色的过程,对萨满化的关注,又有了赛谬尔的一些味道。③参见Geoffrey Samuel,Civilized Shamans:Buddhism in Tibetan Societies,Washington D.C.: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93。图齐敏感地捕捉到藏族民间的一些重要概念,如灵魂(bla)、 预 言 (lung—ston)、 缘 起、 象 征(rten—vbrel)、净化 (vkhrus)、桑 (sngas,焚香)等的延续性。图齐曾发表一篇关于论述吐蕃王权的专题论文 《远古藏王的神圣性格》(“The Sacral Character of the Kings of Ancient Ti⁃bet”),利用弗雷泽 (Frazer) 的神圣王权 (di⁃vine kingship)概念分析吐蕃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神话,指出赞普的神圣性是吐蕃王国丰产力量的根源。④张亚辉:《亲属制度、神山与王权:吐蕃赞普神话的人类学分析》,《民族研究》2014年第4期。
藏族学者南喀诺布认为,上述这些古老的概念以及仪轨属于 “仲德苯” (sGrung—IDevu—Bon)的范畴,其实是没有在苯教中区分出所谓民间宗教;并认为 “苯”一词最初是指各种现存的、有神秘祭祀仪轨的宗教派别,极有可能是以泛亚洲的萨满教文化传统中常见的要素为依据。这里主要指十二智慧苯,构成了藏文化的基础。“仲”传统上用来指两类叙述形式:第一类涵盖了对古代历史事件的全部叙述,第二类仅由神奇、幽默或令人惊叹的故事构成;“德乌”一词具有才智或理解之意,运用符号、谜语和神秘语言传递知识交流与信息,实际上是一套独特的知识体系,南喀诺布称之为一门独特的学科;“苯”主要是指十二智慧苯,是对西藏修持的各类苯教的最古老的分类。①十二智慧苯为知救神苯 (mGon—shes—lha—bon)、知福恰苯 (g.Yang—shes—phywa—vdod)、知驱鬼之放鲁苯 (vGro—shes—glud—gtong)、知度亡之世间辛 (vDur—shes—srid—gshen)、知净化仪轨 (gTsang—shes—sel—vdebs)、知降神之仪轨 (sGrol—shes—lha—byad)、知利他医药 (Phan—shes—sman)、知未来之星算 (ITo—shes—rtsis—mkhan)、知诠释九垛 (sMra—shes—gto—dgu)、知跳神鹿 (IDing—shes—sha—ba)、知飞绳卦 (vPhur—shes—ju—thig)、知神行幻苯 (vGro—shes—vphrul—bon)。参见曲杰·南喀诺布 《苯教与西藏神话的起源——仲德乌和苯》,向红笳等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西藏王臣记》 《红史》等藏文史籍中均有记载,吐蕃王朝早期以“仲” “德乌” “苯”治理王政,这是藏族古典学中非常重要的书写及认同,南喀诺布在现代学科的意义上极大地扩展了 “仲德苯”的学术内涵,这给予本文极大的启发。
除了图齐,法国藏学家石泰安也给出了具有人类学意味的分析。石泰安将西藏宗教分为3个内容,无名宗教对应于图齐的民间宗教。石泰安从 “人间宗教”、歌曲和传说、誓词和墓葬、居住区、一年的节日、个人的地位、灵魂和生命等6个方面来阐述,②[法]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耿 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210页。“神仙宗教以人间宗教的阵地为基础,如同一个果子在那里生长一般”,③[法]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耿 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211页。他体察到神仙宗教 (苯教或佛教)对于土著宗教的融而不合,并进一步指明 “人间宗教”是某一位赞普德政的标志。④[法]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耿 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215页。这就从藏族无名宗教的研究延伸出王权与藏族社会关系的探讨。认为“仲德苯” “表达了古人的智慧,而且其真实性也证实了世界和社会的秩序、居住地的构成以及该地的居民集团”。⑤[法]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耿 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220页。石泰安关于吐蕃王权的考察,贯穿于他关于整个无名宗教的表述体系中。石泰安敏锐地捕捉到 “仲德苯”作为藏族王政治理方式,已渗透到 “王统世系”的表述、王与神仙祖先的亲属关系中,或者王即为神并与显圣物成为一个整体: “圣山是 ‘当地的主人’,犹如 ‘天柱’或 ‘地钉’”; “圣山也是战神,是 ‘首领’或 ‘赞’”。⑥[法]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耿 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227页。在年度节庆中, “王位空缺期间,以在一被驱逐的替身上排除陈腐的道德并在竞技中与之相对抗的方式,政权便可以永葆下去”。⑦[法]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耿 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241页。他对 “祖” [(g)tsug]这一概念,也做出了与麦克唐纳⑧参见 [法]A·麦克唐纳 《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耿 昇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不同的阐释: “祖”有时也与神山和祖神有关,一般是意味着 “头顶” (前顶、颈背等)。如 “木祖” 一词意为“不动的”或 “持久不变的”和 “吉祥的”。当歌颂神山,即政权的保护神时,人们也认为赞普的身体 “不会变化,永不轮流交替”。神山也为“国神”。⑨[法]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耿 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249页。在石泰安关于无名宗教的论述中,一些重要的概念都由 “神圣王权”引发,关于神祇的年度仪式也是确保王权更新的隐喻,王权与山野、家宅具有同构性,赞普通过 “身体”来调节自然与国家的节律。因此,石泰安对于无名宗教的讲述有一丝伊利亚德⑩[罗马尼亚]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王建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或葛兰言⑪[法]葛兰言:《中国文明》,杨 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的味道。可见,无论是图齐还是石泰安,都注意到了藏族社会中 “仲德苯”的知识结构以及赞普在确保丰产和宇宙秩序方面的功能,但都是点到为止,并没有进一步阐述。
正如石泰安所言: “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在很多情况下常常难以说清楚喇嘛教中非佛教特点的因素中哪些是土著的,哪些是外来的,哪些真正是苯教的内容,哪些不是。”⑫[法]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耿 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211页。那么,时至今日,在远离赞普时代的藏族社会中,如何看待民间的多维仪式作为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扬弃佛苯二元结构,藏族王权治理方式或 “王”的隐喻是断裂抑或是连续的?藏学古典学和人类学又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本文通过对后藏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艾玛乡牛沟的 “望果节”仪式中的象征结构的意义分析,试图揭示这些知识纠葛的复杂性及涵义。
二、“望果节”仪式过程
“望果”也称 “曲果尔” (chos—skor,转经),一般在藏历六月初四举行,但是牛沟的“望果节”通常在藏历六月初八举行,原因是六月初四这天寺院里的僧人要去甘丹孜姆山(dgav—ldan—rtse—mo)上供奉寺院护法赛赤(bse—khrb),所以曲果尔节日往后推了 4天。“望果节”一般持续5天:2天转田,1天演藏戏,2天唱 “协钦”(gzhas—chen,大歌)。
(一)“望果节”仪式队伍成员顺序及禁忌
1.举旗队
走在整个队伍的第一个人,必须是一个叫丹增 (bstan—vdzin,持教者)的人,手拿 “世间轮回图”唐卡 (srid—pa—vkhor—lo),当地仪式专家讲这幅唐卡由文殊菩萨在五台山掘出,有息灾免祸的作用;童男童女 (dpav—bo—dpav—mo)各1名,11岁,2人,女童手中拿着宝瓶洒净水 (起净化作用),男孩摇铃铛 (是为了向前方的神灵、各种地方神打招呼,表示 “我们来了”);大旗 (mdav—bo—che),当地人表示级别上比另一种旗达达 (mdav—dar,小箭旗)要高一些,每村出 1人;举红白蓝黄飘幡 (vp⁃yar—dar) 各 1人;2人举圣幢 (rgyal—m ts⁃han),2人举幡头 (vpan)。
2.度母佛法队 (Sgron—ma—nang—rten)
2人抬度母轿子,1人守护 (选拔条件是不喝酒的);拿桑者3人,第一个人是屠夫,是世袭的,在2013年笔者田野调查的 “望果节”仪式中,德村屠夫家的大儿子走在整个队伍的最前面,其他2位拿桑者则选长相古典,有辫子、穿藏靴、戴耳环,有传统打扮、年长一些的,但不是世袭的;拿花拿香、举宝幢各2个小孩,并新增加了2个拿旗子的小孩。
3.骑马队
年长且有地位的3位僧人;3位咒师,阿容村1位、德村1位、吉雄村1位 (手持1壶青稞酒,1个供净水的小碗,里面放青稞酒和青稞,供奉地方神域拉 (yul—lha),把碗拿到域拉旁边,不停地往碗里倒酒倒青稞,口中念着祈祷文);吉雄村村长身穿村里保留年代久远的绸制官服,据说有300年的历史,为一件藏青色彩云寸龙纹旧缎袍,头戴黄色垂红穗帽,右耳戴绿松石耳饰,足蹬黑靴,腰携一款长型藏刀,显然是旧时官员的打扮,其余人员多为红色围穗帽、黄段坎肩、绸制藏袍;另有还俗老经师1位。
4.僧尼法器队
12位僧尼,8位各拿粗细不同的法号,4位拿白海螺。之后是拿锣鼓的1个人,世袭富人家庭拿,因为材质贵重。拿法鼓的人有8个,拿法锣的人有8个。每个僧尼都有1个俗人来帮他们拿法器,走山路时,法器可以收缩起来,由俗人背着,快到有地方神的地方时就吹起来。
5.背经队
第一个背经人是吉雄村一个叫格桑 (skal—bzang意为幸运、良缘、善根等)的人背着经文“多地格桑” (mdo—sdej—skal—bzang)走在背经队伍的最前面,此经文据当地传说是传到西藏的最早的经文,是从天上掉到雍布拉康所在地的,500年后,雍布拉康在经文掉落处落成;然后按村落的顺序吉雄村背着甘珠尔,阿容村和德村的人背着丹珠尔,队伍中需要一位叫丹增或格桑的人在结尾处背经,招福 “央” (gyang,福气),最后背经结尾处是房名为卡仓家的(kha—tshang,齐全)出1人。
6.阿妈央金啦 (dbyangs—can,妙音)队
必须是家庭里的母亲来参加,没有小孩的不行,人数不固定。在各自的域拉边等候转经的队伍归来。阿妈们左手捧切玛,代表吉祥如意,右手持达达 (小箭旗)。有些家把羊蹄和羊的肩胛骨拴在箭旗下面,据说有辟邪的作用。
(二)转经的顺序和仪式时间
队伍出发的顺序是按照身、语、意的涵意走,举旗队、佛像队、僧尼法器队,最后是背经队。
路线按由地势低到地势高的方向走,由吉雄村到德村到阿荣村,由于牛寺坐落在德村,所以是整个牛沟的中心,最后整个队伍要返回德村;度母队和骑马队走大路,其他走山路,途中必须转3个村落所有的田地、村落保护神、生神(多为山神),其中吉雄村有4个保护神,德村有2个保护神,阿容村有3个保护神。
(三)支持 “望果”仪式的组织和分工
牛寺、尼姑寺院多杰扎普 (rdo—rje—sgrub—pug,金刚修行洞)、3个村委会,这5个组织一起商量仪式的举行,资金主要是3个村委会出。钱由县民政局给,主要花在给舞者的酬劳,寺院不用出钱,但他们出糖果点心招待重要客人,舞者跳完舞后,献给舞者哈达和饮料可乐;仪式队伍中僧尼、咒师、童男童女的伙食,按行走顺序第一天吉雄村管,第二天阿容村管,第三天德村管;各个村委会都要向村民收青稞酒和酥油,分发给舞者。
三、“望果节”仪式象征意义分析
(一)仪式成员社会等级及象征
除了像传统藏族社会中特定的阶层如僧人、尼姑、咒师、屠夫、还俗经师,村长代表贵族官员出席,俗人则由如背经者、文艺特长者 (藏戏表演者、跳协钦的歌者)孩童、母亲等五官端正、身体没有缺陷的人来担当,带有象征意义的姓名或历史记忆的房名 (khang—m ing)或家名 (grong—m ing),①在当地,房名和户名有相同的意义,但房名不是指房子的名字,而是指住在这所房子里的人家,类似于家族名。房名不会随居住空间的改变而改变,而是随着家户移动。房名由男性传承。如3个村的村名,其来源为家户名。有象征美好涵意的仪式角色具有隐喻作用,有些仪式角色是世袭的,显然是一种荣耀和特权,整个仪式有明确的等级寓意,一方不能取代另一方,位置不能出现混乱。正式的仪式队伍中除了女童,没有成年女性,作为人妻及人母的女性阿妈央金在队伍转到地方保护神处休息时作为迎宾出现。代表生育的母亲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官员成为秩序的隐喻。
在整个仪式中,佛法僧显然是权威和中心,首先是僧侣寺院而非尼姑寺院是整个牛沟的中心,仪式在这里开始并在此结束;仪式的前奏是僧人对寺院护法的供奉,供奉时对整个牛沟进行净化,对三界神灵进行净化及供奉;而 “望果节”仪式正式开始之后,这种权威不仅体现于整个仪式队伍中,抬度母的队伍最为神圣,而且背经队经过之处,人们都要顶礼膜拜。对于僧人来讲,首要任务是做好净化,仪式队伍中有净化者一老一小 (khrud—legs—pha),骑马队伍中老僧人尼玛曲吉负责给每个域拉净化,1个小僧人走在背经队前面,负责给整个村子净化。
咒师是代表与地方神沟通的巫术角色而出现的,屠夫在平常可能受到歧视,②如德村屠夫,xl,男,49岁,作为世袭的屠夫,其家族据说是日喀则地区一个屠夫世家后裔,这个家族据说是屠夫的正源。其宰牲畜的技术是11岁时由父亲传授的。现在家里有7口人,儿子和女儿都以打工、开商店作为生计方式。村里有人去世时,搬运尸体时,一般会请他跟在尸体后面,这样能把家里不干净的东西带走。报酬看对方家庭境况,富裕的家庭给六七斤青稞,两块饼子,一点肉。而在另一例访谈中,村民强调,选择结婚对象时,一定要看对方的身份 “出身是否干净”,若是以铁匠、屠户、天葬师家的人作为结婚对象,那是万万不可以的 (田野被访谈对象,jm,58岁,女,吉雄村人,访谈时间:2013年7月23日)。但在 “望果节”时,身处一个重要的位置 “走在最前面,可以挡住不干净的东西”,作为禁忌本身,对鬼怪及肮脏具有威慑或净化的作用。
藏族文化史上的象征,是通过丹智 (rten—vbre)的性能冥想事物本身与其所象征的吉凶对象之间产生的一种学科,③参见扎雅·罗丹西饶活佛 《藏族文化中的佛教象征符号》,丁 涛等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丹智本身不仅有象征之意,也表达了事物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浸透着藏族传统的审美道德伦理以及分类原则,好恶、善恶、吉凶充满隐喻,丹智在藏族人的生活中无所不在,也建构了一种价值观和仪式性质。代表吉兆的物质或意义体系 (姓名、房名、身体、母亲、僧人)以及代表凶兆、肮脏、危险或禁忌等的观念体系,构成一种二元对立,在仪式中维持具有张力的秩序,构成藏族社会的一种象征语言,表达其喜好。
(二)仪式结构
从仪式过程和目来看,作为一个年度节庆仪式,其关乎山川、大地、农田、河流、所有的地方神 (拉勒年赞lha—k lu—gnyan—btsan)、佛法僧 (知识)、圣迹圣地、巫师 (咒师)、一个藏族农业社会物资及人文的流动,如青稞酥油、过节的服饰、藏戏协钦等歌舞艺术、礼仪、象征性语言、智慧以及精神气质的彰显。仪式的目的包括大地的净化、招福,对妖魔鬼怪、不祥、坏运气的再一次铲除,对地方保护神的供养和反复的降服,以及佛教意义上对情器世界的法布施。因此,“望果节”仪式像一个大熔炉,既融合所谓的 “无名宗教、苯教、佛教”的各种因素,包容诸如负责战争、丰产等的高低级魔法,④参见 [法]杜梅齐尔 《从神话到小说:哈丁古斯的萨迦》,施康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又呈现出一种浓缩神圣时间的 “冷社会”的节庆涵意。
在赞普时代,藏文古籍记载当时的王政由“仲德苯”来统治,即叙述故事、谜语 (运用象征性语言传递知识及教育)和苯教 (古老的教义和仪轨)来统治,而在这个节庆仪式中体现了3者的融合,“阿姐拉姆” (藏戏)进行2天的表演,笔者在2013年田野看到的主要剧目为《智美更登》 (以施舍、布施为主题的佛教故事);协钦的演唱以及仪式中具有隐喻性的吉凶兆头 (象征性语言);一系列仪轨,既由咒师操作又由僧人操作,显然属于不同的领域和专业,又超出了苯的范围。
关于 “望果节”名称的两种说法。当地村民明确表示这一天对于僧人来说,是转经的节日,是释迦牟尼转佛法经轮的节日;对农民来说,是转田的节日,也是夏天娱乐的一个主要节日。有村民认为,“望果”和 “曲果尔”只是叫法上的区别,如果村里没有寺院就没有 “曲果尔”的条件,就像从电视上看到西藏其他地区,没有条件的 “节”不分男女都可以背着经文转田。可见当地人认为寺院的存在非常重要,意味着规范和秩序。从仪式展演的农业空间来看,无论从安多到环喜马拉雅一带,所谓 “藏传佛教文化圈”中 “望果节”的名称更改为 “曲尔果节”已经获得最大认同,但后藏的田野呈现了一些不同的隐喻,是地方性的或是藏文明结构性的?这是值得关注的。
(三)“望果节”中 “王”的隐喻
首先,牛沟 “望果节”仪式队伍具有庞大、整齐、规则的特点,更具 “展演性”。特别是举旗队的出现别有意味。旗的种类繁多,有大旗、小箭旗、红白蓝黄飘幡、圣幢等。虽然 “旗”的出现并不尽然是军队的象征,特别是旗帜的很多内容已被佛教化,但依然有军队的影子存在。骑马队伍中村官打扮为旧时的贵族官员,一件保存年代久远的官服在整修仪式队伍中有一种殊胜的存在,显然牛沟的 “望果节”并不仅仅是俗人的丰产仪式,而是大王巡山的隐喻,是王对于疆域的再次划定。神山作为吐蕃王朝疆域 (江山)的象征,已经在学界得到较为详尽的阐述,早期藏族9大山神名称与序列的变化,直接反映了吐蕃王朝领土的扩张,而较为晚近的藏族9大山神体系,则表达了藏族三区的 “手足”认同。①参见才 贝 《神与赞普:一种身体观》,载 《边疆社会的王权形态——历史与经验研究探索论文集》 (未出版),四川成都,2014年,第41页。牛沟 “望果节”举旗队的 “转田”实际也是转山 (山神),是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巡游隐喻。
其次,仪式中所穿插的两则神话作为谜语(idevu),具有解读性。第一则关于 “世间轮回”图的神话,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属于佛教体系,以 “六道轮回”这个对于藏族人来说是最熟悉不过的图案出现,具有威慑性,强调了积累“善业”的重要性。第二则是更为重要的关于“多地格桑”(mdo—sdej—skal—bzang)的神话。对照第一则神话之后,第二则神话的意义更加突显,显然属于另一个阵营。据当地仪式专家讲述,“多地格桑”是传到西藏的最早的经文,是从天上掉下来的,500年后,雍布拉康在经文掉落的地方建成。雍布拉康作为藏王的第一座建立在地面上的宫殿,也是藏族历史重要的经典“玄秘神物” (gnyan—po—gsang—ba)降临之处。《柱间史》记载:
拉妥妥日年赞把这件 “玄秘神物”安放在宝座之上,时时用御酒神饮和绿松石供奉,每天一边绕着转 (藏语为古拉),一边祷祝。据说,借此宝物的加持,已是年迈体衰、白发苍苍的赞普,居然返老还童了。他享年一百二十岁,称之为一生活了两世人。
在雪域吐蕃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祸患灾难,只要向我的 “玄秘神物”祈祷便消灾避难;若是想要祈福求善,尽管向它祷祝,定会随心如愿。②[古印度]阿底峡尊者发掘:《松赞干布的遗训:柱间史》,卢亚军译注,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第57页。
可见,“玄秘神物”具有 “返老还童”之魔力,是赞普 (政权)“长青”的象征。其能 “消灾避难”“祈福求善”,表达了经典的巫术力量。“多地格桑”在此处的出现,显然也是 “玄秘神物”的象征。在更多的藏文历史典籍及后来的研究中,一般将 “玄秘神物”作为佛教传入西藏的开端,而 “多地格桑”在牛沟的 “望果节”仪式中有不同的涵义,在神话中它出现时间更早,是传到西藏的最早经文,是第一座王宫落址的依据,可见 “多地格桑”在此处为王朝的隐喻而不是佛法的象征。这是整个 “望果节”仪式中较为明显的 “王”的符号的出现。王朝的建立,也是人类秩序的建立。
王都是超自然秩序的缩影及政治秩序的物化体现,它不仅是这个国家的核心、引擎或者支点,它本身就是国家。这种把王都等同于王土的做法,不仅仅是一个暂时的隐喻,而且还是对一种政治观念的陈述:即仅通过提供一个模型、一个典范、一个文明生活的完美图像,朝廷把自己周围的世界塑造得至少和自己大致一样完美。③王铭铭:《人类学讲义稿》,上海:世界图文出版公司,2011年,第97页。
有意思的是,藏族王都的表达以经典的形式来出现,这恰好说明神圣王权的 “重现”。
实际上,经典与王宫之间的关系在藏族历史上,总是呈现出一种张力。拉妥妥日年赞时期的“玄秘神物”是后来才被世人所破译的,而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正如上面所述,是作为具有魔法的 “圣物”来崇拜的,因此,这一时期的经典显然是具有巫术性的。
松赞干布时期,吞弥·桑布热受命前往天竺迎取佛经和文字蓝本,并偕天竺文人李秦回归蕃地,请回寻访到的 《宝云经》 《白莲花宝顶经》《五部陀罗尼经》 《十善法》等经卷。这些经卷加盖印章后封藏于钦瓦达孜宫的王库。后译成吐蕃文。④韦·囊赛:《韦协》,巴擦·巴桑旺堆译注,拉萨:西藏人民出版,2012年,第1页。钦瓦宫作为吐蕃早期的宫堡,据 《贤者喜宴》的记载,其建于布德贡杰赞普时期,有六宫,是历代赞普居住的主要城堡,松赞干布也曾居住于此。格鲁派建立噶丹颇章政权后,原钦瓦达孜宫所在山上设立了琼结宗政府官邸。⑤韦·囊赛:《韦协》,巴擦·巴桑旺堆译注,拉萨:西藏人民出版,2012年,第44页,注释16。不像11世纪产生的伏藏书 《柱间史》 《十万嘛呢遗训》,着力将松赞干布描述成观世音的化身,一生致力于弘扬佛法的伟大法王不同, 《韦协》的评介是 “上祖松赞干布所开佛法之宗仅此而已”,这无疑为独树一帜之说。①韦·囊赛:《韦协》,巴擦·巴桑旺堆译注,拉萨:西藏人民出版,2012年,第46页,注释31。因此,这一时期的经典内容虽已由语言学家翻译,但依然是束之高阁,无人问津,更谈不上传播,主要是印证“王法”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强调的是王作为社会秩序的一面,王是司法的来源。松赞干布迁都拉萨之后,很多文献记载,根据文成公主的相地之术,大量的神庙建立在作为妖女身体象征的神圣地理之上,体现的是土地与王权的关系,服务于王权的主流依然是巫术与魔法。
赤松德赞时期,桑耶寺的建立、莲花生大师一路的入藏降魔,经典从王宫入驻寺院,吐蕃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僧人和寺院,这时经典逐渐回归于 “佛法僧”应有的位置序列中,这是个过程。藏族认为触摸 (touch)经典就可以消灾避难的传统观念一直延续下来。如在上文中提到的第一则神话,从五台山掘出的 “世间轮回图”具有如此的功效,就不难理解了。
四、结 语
当在墀松德赞年间完成了一批佛经的翻译任务之后 “管氏大相说,陛下传播了神仙宗教 (佛教),现在,作为人间宗教的故事,陛下将赐给人类一些什么东西呢?”于是便赐给了人间君主的故事、国民划分(类别)、对宗教人士和三宝的顶礼膜拜、故事和历史、道德和王诰等。②[法]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耿 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216页。
不止是在赞普时代,关于藏族民间的一些重要概念如灵魂、预言、缘起、象征、净化以及超越了“仲德苯”范畴的仪式结构一直延续至今,并奠定了当前藏族社会民间宗教的形态和基本特征。
《弟吴宗教源流》在描述吐蕃早期王统——悉补野王统时指出:
对于每一位授封之王来说,要知道他的父亲是谁?母亲是谁?名字叫什么?王妃是谁?大臣是谁?王子是谁?宫殿叫什么?臣民有多少?授封的原因是什么?导师是谁?做什么事?调伏了哪些人?怎样降魔?战骑如何?怎样聚财?吃什么食物?穿什么衣服?武器如何?手持何种工具?佩带何种饰品?说什么话?源自何种姓?怎样行动?住何洲?何时出生?三界有哪些种族?四生中属于何生?寿数多少?身高多少?等等。③弟吴贤者:《弟吴宗教源流》,许德存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3页。
可见,世系、血统、衣食住行、魔法、战争等这些内容才是一个 “王”应该关心的,“王”的身份由这些来界定, “王”是自然与社会的统一。具有自然和社会两个面向的神性君王,既是大地丰产的来源,又是社会秩序的保障。霍卡所论证的一种将 “自然之神”与 “祖先之神”统为一身的代表了社会整体性之神圣王权模式,④张 原:《藏彝走廊的二重性——神山、王权与神圣性之比较》,载 《边疆社会的王权形态——历史与经验研究探索论文集》(未出版),四川成都,2014年,第20页。其关于王权类型的探讨对于分析吐蕃后期,割断天绳之后的王权形态是有启发性的。“黑头番人确需要一个比能够提供秩序与丰产的肋骨神等级更高的王”,因为 “王”还需要一位导师, “卡里斯马的最终担纲者”。⑤张亚辉:《亲属制度、神山与王权:吐蕃赞普神话的人类学分析》,《民族研究》2014年第4期。这是在图齐或石泰安式的研究中所忽略的。究其忽略的原因,笔者认为是佛苯二元论一直是藏学研究方法的程式化 (ster⁃eotype)框架,王权往往被淹没在佛苯冲突或融和的汪洋大海中,成为藏族 “神话时代”的剪影,似乎藏文明进入 “历史时期”之后,王权便烟消云散了。
回到个案,对于牛寺还有多杰智普的历史和曾经的教派归属,其历史的讲述呈现出某种断裂性,一是追溯到郞达玛灭佛,二是追溯到 “文革”,寺院几经毁灭、搬迁、改宗,寺主活佛也处于某种缺席状态,可见僧人佛教是断裂的,而无名宗教则没有。僧人的知识需要在无名宗教的仪式中点击和复活,佛教史需要在仪式中修复、链接,并通过年度仪式获得重生和权威的确立,无名宗教、苯教或佛教的关系很难做一个泾渭分明的区别,任何一种单一的考察都有失偏颇。冲破佛苯二元传统视角的束缚,从后藏 “望果节”的田野来看,显然 “王”的符号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正如 “仲德苯”的王政治理方式依然鲜活于民间,由此吐蕃王朝对于藏族社会的深刻影响昭然若揭。理解在民间,吐蕃王朝 “伪装”成各种符号而并存于佛苯之间,就像谜语本身,这对于打破佛苯二元论框架的藏族民间宗教及仪式研究,多了一份可能的视角。
致 谢:本文的写作受惠于中央民族大学张亚辉教授的赐教,在此表示感谢!
(责任编辑 段丽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藏族跨区域神山朝圣及国内外影响研究”阶段性成果 (14BZJ039);教育部项目 “社会变迁中藏族山神信仰及农牧社会秩序研究”阶段性成果 (13YJCZH004)
才 贝,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博士 (青海西宁,8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