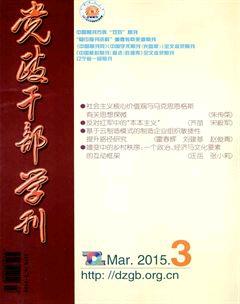近代沈阳诗坛创作特色论略
2015-04-09赵旭,刘磊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5)03-0077-04
[作者简介]赵旭(1975-),男,辽宁沈阳人,博士,沈阳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辽沈地域文学研究。
刘磊(1979-),女,辽宁大连人,博士,辽宁大学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本文系辽宁省社科联2015年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2015lslktziwx-26),2013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3BZW008),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WJQ2014053)。
道光二十年(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此后,清帝国逐渐陷入内忧外患的处境,辽沈政局也随之受到了冲击,作为陪都的沈阳更是首当其冲。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近代沈阳的诗坛,也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本文试对此加以探究,以就正于方家。
一、沈阳本土文人的诗作
被誉为“辽东三才子” [1]4604之一的刘春烺(1850-1905),字东阁,又字冬葛,号丹崖,奉天府承德县新民厅人。光绪八年(1882)中举。《北镇县志》小传中说他“读书独观大义,覃心于经世之学,凡舆地、兵事、农田、水利,以迄器艺之微,无不精究其蕴” [2]。曾由左宝贵推荐,治理新民柳河水患,“独任其事,堤堰至今尚完固” [2]。可见,刘春烺是一个重视实学的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主讲萃升书院,并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任盛京省学堂的总教习,为沈阳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其诗作多是即景抒情,感物言志之作。如《重九日沈阳城楼》,以“搔首不可问,重阳始何年。登城望东北,漠漠山川连”起句,登高远眺,见远天寒鸦,烟霭孤塔,怆然之感顿生。“世界万封蚁,强者为鸟鸢。蠢灵同吾族,欲拯愁无缘。又无羡门术,白日飞金仙。仰天百感集,落木正苍然。” [3]列强环伺,时局堪忧;欲济苍生,又无处着力,感时伤志之意充溢其间。
《听角行》则是一首更为直接的纪实之作:
沈阳城头角呜呜,老鸦飞上城头呼。大街小儿拍手笑,儿勿上城官人驱。
官人狰狞面貌粗,长鞭打人壮且都。问其姓名姓则无,但道将府兵与夫。
春风二月草木苏,鸣角朝夕摧封租。老农封租已向毕,锒铛枷锁尤盈途。
身有百口辩不得,谁欤梦见流民图。图亦不得见,罪亦不得除。
孤儿寡妻走边隅,路逢猛吏神仙如。锦衣大马出民庐,欢归酒肆听笙竽。 [3]
晚清吏治废弛,官府横征暴敛,屡增赋税;官兵亦为虎作伥,凶残粗暴。这首诗所述就是诗人在沈阳街头亲眼目睹之景象,“老农封租已向毕,锒铛枷锁尤盈途”,陪都尚且如此,余者可想而知。而朝廷大员们“锦衣大马出民庐,欢归酒肆听笙竽”的生活,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令人气愤填膺。
缪润绂是与“辽东三才子”同时的沈阳本土诗人。缪润绂(1851-1939),字麟甫,号东霖,别署吟溪钓叟、钓寒渔人、太素生、含光堂主人等,汉军正白旗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缪润绂出身于书香门第,其曾祖父缪公恩是沈阳著名文士,其祖父缪图箕、父亲缪景文及其叔辈缪景其也是有文才的人。缪润绂年轻时就表现出极高的才华,与韩小窗等人共同创建了著名的“荟兰诗社”,并与韩小窗和喜晓峰并称为“沈阳三才子”。《沈阳百咏》是其代表作。刊行于光绪四年,民国十一年(1922)又经作者加以修订出版,诗作和按语都做了一定的修改。从内容上看,《沈阳百咏》“摭拾旧闻,涉笔拈毫。窃以生居丰镐之乡,忝附缘饰沅湘之例,随时凑集,爰成百章” [4]自序1,采用七言四句的竹枝词形式来记录沈阳的民俗风物,共计100首,“是一部有关沈城掌故、风俗、起居、饮食、服务、婚丧、信仰等方方面面内容的诗集” [5]368。其中对当时的武备问题也有所涉及,如光绪本第二十首:
识字仍须学挽弓,教场昨夜换春风。诸童嬉戏将军怒,都在弯弧一笑中。 [4]40
这首诗通过形象的对比,在表面的嬉闹中,蕴含着对旗人武备松弛的感伤,很有些“含泪的微笑”之味道。
张之汉(1866-1931)也是一位爱国的本土诗人。字仙舫,署辽海老渔,宣统元年(1909)优贡。历任自治局顾问、谘议局议员、官银号总办、实业厅厅长等职,卒于东三省盐运使任上。《奉天通志》中载有张之汉为王永江《铁龛诗草》所作序文。序中写到他和王永江深夜对酌,“酒酣耳热,纵谈时局”,王永江“愤然碎杯起,目光电闪,吐气如长虹”;而两卷《铁龛诗草》,亦“大都感时愤世,托物见志之作”。 [6]张、王二人为至交好友,性情文章庶几近之。甲午战争时,金州厅南关岭塾师阎世开不屈于日寇,慷慨殉国,王永江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张之汉,张闻听后悲愤不已,提笔作《阎生笔歌》。其诗云: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奋椎难击博浪沙,抗节直比胡天雪。非椎非节三寸毫,竟凭兔颖探虎穴。千军直扫风雨惊,披肝沥血凝成铁。饮刃宁惜将军头,振笔直代常山舌。头可断,舌可抉,刃可蹈,笔可折,凛凛生气终不灭,吁嗟阎生古义烈!阎生著籍辽海东,系心家国身蒿蓬。……九连城头将星落,颓军断后谁盘矟?东南铜柱沉江涛,太阿倒柄凭人操。十万横磨岂不利,一割无用同铅刀。胡为乎!刀围大帐笋锋密,挺然独立阎生笔! [7]
这首诗慷慨悲愤,感人至深。其后流传极广,令阎世开的悲壮事迹广为人知,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爱国热忱。张之汉此诗,为飘摇动荡的晚清沈阳诗坛留下了一个挺立不屈的身影。
二、外来游历、求学、客居者的诗作
有清一代,沈阳作为“陪都”重镇,成为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着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到沈阳游历、客居、求学者也多了起来。
魏燮均生于嘉庆十六年(1812),“卒年尚未考证清楚,当在1890年左右” [8]。初名昌泰,字子亨,号芷亭。因慕郑板桥之为人,遂更名燮均,字伯柔,又字公隐,别号铁民,又自号九梅居士,著有《九梅村诗集》。《奉天通志》小传中说他“工书法,善古文诗词,负笈远游,多览名山大川。” [1]4602魏燮均大半生漂泊,风尘困顿,和社会底层较为接近,其诗歌中经常能看到当时社会民生的真实情状。如《李小南明经迁居小河堰》诗后小注中说“小南本乡居,因盗贼警迁居省城” [9]781,可见清末盗匪之患,已成常见景象。他在《沈阳客馆夜坐感怀》一诗中写道:“天街无月明,漏下禁宵行。人语远过巷,钟声高出城。岁寒犹在客,世乱每谈兵。自顾头垂白,愁吟对短檠。” [9]445次句有小注“时城中戒严,禁止夜行”。魏燮均生年至少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战火尚未涉及东北内陆地区,但连年的兵乱,以及吏治废弛,盗贼蜂起的内政,已经令诗人感到了乱局将至的风雨飘摇。以此为题材的作品苍凉沉郁,颇有杜甫“诗史”的味道。
客居沈阳的诗人,以刘文麟最为著名。刘文麟(1815-1867),字仁甫,号仙樵、衍阳山人。他是近代极有影响的诗人。《清史稿·刘文麟传》称他“论诗以婉至为宗,语必有寄托,英光伟气,一发之于诗。论者谓足继辽东三老。” [10]清嘉庆二十年(1815),刘文麟出生在辽阳东沙浒屯。9岁便能作诗。11岁随父亲入川。辽东文化和巴蜀文化共同濡养了这位少年才俊。道光十八年(1838年)春,刘文麟进京应进士正科考试,中进士,授官广东任知县。历史给了年轻的诗人一个表现的机会。刘文麟亲历了禁烟运动和鸦片战争,并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秋冬之际,根据所见所闻所感写成八首七律组诗,题为《感事·辛丑八首》。他称得上是“近代史上第一位亲历并参与鸦片战争,及时以诗歌反映这场战争,真实记录下这场战争实况的诗人。” [5]342
咸丰六年(1856),刘文麟受王晓坪之邀主讲沈阳萃升书院,至同治元年(1862),执教近六年。在沈阳期间,刘文麟悉心讲授儒家经典,热心教授学子,同时,自己也坚持写作诗歌。经刘文麟教导的学子中,有不少人成为了名士,如《清史稿》所载:“其门人王乃新,字雪樵,承德人。亦能诗,有《雪樵诗賸》。” [10]咸丰六年(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仓皇逃往热河。身在陪都的沈阳,正主讲于萃升书院的刘文麟当然会受到触动,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懑,写下《感成》三首。“漏卮枉用民膏塞”以“漏卮”来形容当时的国势,很有形象性。而一个“枉”字表达了内心对当权者无能的极大痛恨。在抨击当权者无能的同时,又冷静地想到“全局终思国手收”,热情呼唤救国人才的出现,这也为其在萃升书院的教学增加了动力。而对咸丰帝的出逃,也予以了痛斥:“海氛急扫孤衷切,天步足回万颈延。圣祖神宗疆域在,是谁陈策议东迁。” [11]表面上是批判怂恿东迁的臣子,实际上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
此外,与刘春烺并称“辽东三才子”荣文达和房毓琛也时常经过沈阳。荣文达有《沈垣旅寓养病》诗二首,其一云:
洋笳洋鼓沸城阴,郭笛溪碪寂不音。病客听鸡憎夜永,衰翁如鹤警秋侵。
乾坤怀古悠悠泪,欧亚伤时耿耿心。闻说翠华西返跸,荒原风露可胜禁。 [1]5036
以“洋笳洋鼓”喻指虎视眈眈的列国诸强,寂寥无声的“郭笛溪碪”则好比日暮斜阳的清帝国。当时荣文达正在病中,但直至深夜还忧心忡忡,思虑国事,真可称“欧亚伤时耿耿心”。
值得一提的是,在沈阳读书的周恩来也留下了诗作。1910年春天,他随伯父周贻庚来到沈阳,就读于奉天省官立东关模范两等小学校,度过了三年读书生活。就是在这里,他提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言。1911年暑期,他和同班好友何天章与何履祯去位于沈阳沙河一带的魏家楼子度假,这里曾是日俄战争的战场,日本在此建塔,俄国则在此建碑。在何履祯家居住期间,与何履祯的祖父何殿甲写诗应和,为沈阳文坛留下了重要的一笔。何殿甲是村中的私塾先生,经常和周恩来谈起日俄战争,并带他去附近的战场遗迹察看。年仅十三岁的周恩来通过实地考察,并亲耳听到乡邻谈到日俄军队在此犯下的罪行,极其悲愤,同时也认识到政府无能必然会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对自己,对青年的责任也有了思考。这充分体现在他的《村望》一诗中。当时,在烟龙山,面对战场遗迹,何殿甲老人含泪吟诵杜甫的《春望》,周恩来心有所感,依原韵改写《村望》一诗:
国破山河在,村残草木深。感时勿落泪,誓叫寇惊心!
烽火连岁月,捷书抵万金。白头休志短,患除贺更新。 [12]
此诗一反杜甫原作的深沉痛楚,诗中表达了激荡的少年豪情。面对眼前残破的战场遗迹,想到国家的衰弱,少年周恩来不是沉溺于悲愤,而是想到要不受欺凌,必须要自强,“誓叫寇惊心”,改变颓势,去取得胜利,“捷书”报喜。尾联更是对未来充满信心,即使是白发者亦有作为,国家除患兴盛日,就是青春再来时,当为新的时代继续做出贡献。这不仅是对杜甫诗歌的升华,而且也是对何殿甲老人乃至自己的激励。表现出少年周恩来宽广的胸怀和不凡的见识。对此,何殿甲老人深受感动,在《登东山歌》中写道:“登彼龙山兮山巅,望彼河水兮潺潺。忆甲辰年兮神往,想日俄战兮心酸。”“吾已生于斯兮长于斯,恨不能翱翔兮五湖烟。今我老兮有何志愿,图自强兮在尔少年。” [13]一老一小因国势所激而产生的诗歌交流,成为了沈阳诗坛的一段佳话。
三、《盛京时报》的诗歌主张与倾向
《盛京时报》是近代沈阳的主流媒体,由日本人中岛真雄创办于沈阳大东门里,1906年10月18日(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一日)出刊第一号,1944年9 月14日曾改名为《康德新闻》,至1945年日本投降后停刊,历时近40年。“据中岛真雄自述,《盛京时报》这个报名,‘是袭用俄国占领奉天时发行的俄文《盛京报》而定的’,并请清末进士张元奇(后任奉天民政使)题写报名。” [14]
从文学史角度看,主要发表在《盛京时报》“文苑”栏目中的诗歌,题材多样,数量众多,而且作者身份各异,既有守旧官吏,也有维新革命者;既有中国文人,也有外国作者;既有本土写手,也有外地投稿者。其复杂的写作状况,构成了当时沈阳丰富的文学生态,也是当时中国诗坛上重要的一环。同时,这份由日本人创办的报纸所刊载的诗歌又具有与当时社会时局紧密结合的特点,体现着当时社会的审美取向,具有重要的文化史意义。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七日,发表在“选论”栏目《圣人与诗人》一文,可以视为一篇关于诗歌社会功能的论文。此文极力鼓吹诗人之力量,首先将诗人与圣人并称,辨别其异同:
一言以蔽之曰:悲世之恶而知所以救之者,圣人也;悲世之恶而不知所以救之而唯思逃之者,诗人也。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滋,则一而已矣。
指出诗人与圣人虽然对世人的具体态度不同,但其内心的忧患则是一致的。然后进一步指出世人对诗人的不理解:“世之奉圣人如天神,其视诗人雕琢薄技而已。余乃以之与圣人并称,谁不以为狂惑?”然后表面自己的态度:“然吾忧圣人,吾爱诗人。”作者认为,圣人和诗人的共同点在于,面对严酷的现实社会:
其吐辞立义,或非世俗所能知。虽取相非笑骇怪,然能不以利害祸福动其心,道广大而尽精微,誉之不以为喜,毁之不以为忧;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洋洋乎,渊渊乎。故曰圣人参天地者也,诗人邈天地者也。世俗恶足以几之哉。……谈要之,推其识,性则圣人与诗人蔑不同耳。……见世之溷恶,人之沦堕,以为非吾徒也。乃冥想无际,上薄九天下彻九渊,不知所以寄其情者,而发为怪丽之辞,如屈原之《离骚》,和谟之古诗,李白、李贺之歌行,唐德之《神曲》,米尔敦之《失乐园》,格泰之优师剧。其他不可患述,大率用意相类也。
诗人和圣人的本性是一致的,但诗人更愿意追求个性的自由和情感的解放,古今中外都是一样。作者也清醒认识到,推崇圣人之道者,却有许多人“委曲阿世,则其志异于圣人。而所行或詹詹需需,竞利持禄,立身本末,每有不强人意者”。这样的生存状态,“何如诗人之洒然不可羁,为高洁之至者哉”。作者不是厚此薄彼,而是针对所处时代特点,主张人们多一点诗人的精神,远离污浊,远离庸俗,多一些独立精神。进而谈到文学领域中更需要诗人:
吾国夙尚文学,千百年来,其能完然无愧于诗人者,何其少也。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诗人斯可矣。诗人乎,岂寻常吟弄风月铺续景物者足以当之乎!
本文作者大声呼唤诗人的出现,而且明确指出,真正的诗人决不是吟弄风月者,而应该是具有独立精神者。此言掷地有声,可以视为《盛京时报》刊发诗文的一个纲领性的文献。可惜这篇文章并没有对《盛京时报》所刊发的诗歌真正起到指导性作用,因为所刊发的诗歌大部分还是吟风赏景,抒发个人情绪的作品,缺少时代精神。
总的来看,近代沈阳是一座重镇,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在此发生。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大量本土文人包括近代的一些著名人士或来求学、或来仕宦、或来客居,与沈阳发生了密切联系,并因为各种机缘在沈阳留下诗作,他们与沈阳本土文人共同构建了近代沈阳诗坛,为沈阳近代文学增加了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