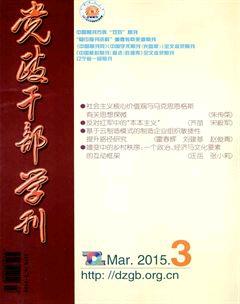洛夫的诗歌创作与现代中国新诗传统
2015-04-09王志彬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5)03-0072-05
[作者简介]王志彬(1973-),男,汉族,安徽灵璧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批准号:09BZW065)成果之一。
从乡愁萦怀的《魔歌》到壮阔通达的《漂木》,三十七本熠熠生辉的诗集见证了洛夫从青春到暮年的心路历程,六十余年孜孜不懈地艺术追求谱写了洛夫不断超越的诗路历程。那离散的经验、漂泊的行程、生命的悲剧意识以及繁复的诗歌意象的经营和语言秩序的营建,形成了洛夫诗歌独特的美学品质。洛夫旺盛的诗心,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对自我、民族和人类命运的关注,使他不断地向汉语诗歌的艺术高峰跋涉。洛夫深受现代新诗传统的影响,但其诗歌创作却是在与现代新诗传统疏离甚或是相断裂的时空环境中进行的。他的诗歌成就“不仅在现代诗的探索方面走得最远,而且在回归中国传统方面,对中国现代诗的诗学精神的探索与继承,所取得的成绩也引人注目。” [1]62洛夫的诗歌创作是当代海外华文诗歌的缩影,通过对洛夫诗歌创作与现代新诗传统的把握,能探寻现代新诗传统在海外的传承、变异和发展的进程。现代诗歌近百年的发展过程,形成了自身丰富的传统,而采用“自由体”诗歌形式和借鉴西方诗歌创作技巧无疑是现代新诗传统较为重要的内涵。本文将从洛夫诗歌创作形式和创作技巧两个层面,去探求洛夫对现代新诗传统的继承和超越。
一、洛夫的诗歌形式与现代中国新诗传统
现代新诗是现代思想和审美意识在诗歌领域觉醒的产物,是现代诗人参照西方现代诗歌艺术,以极大的创新精神对中国旧体诗的一次变构与解放。自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白话诗八首》以来,新诗在探索、构建和创设自身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新的诗歌体式、诗学形态、诗学观念等,而这些具有现代性质的诗歌体式、诗学形态和诗学观念在适应时代嬗变要求,反映现代人的情感、思想和生命体验之中,逐渐成为汉语诗歌的新传统。而其中,分行去韵的“自由体”诗歌样式不仅是现代新诗革新旧体诗的最显著的外在特征,而且也是现代新诗传统的重要内涵。洛夫青年时期就接触到冰心、徐志摩、艾青和冯至等人的作品,这些人的诗作对洛夫日后的诗歌创作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洛夫曾说:“‘五四’以后的诗人对我产生过影响的有两位,一位是冰心,一位是徐志摩,前者是正面的影响,后者是负面的影响。关于冰心,她对我的影响除了前面提到的那首《相思》之外,还有《寄小读者》。……至于徐志摩,他对我产生的所谓‘负面影响’,是我把他的诗视为不可学的反面教材。我一开始学作诗便不喜欢‘新月派’的诗,那种梦幻般的浪漫抒情,那种赫糊糊的调子,很不合我的胃口,更不喜欢太讲究格律,嫌它碍手碍脚。” [2]276-277在现代诗人影响下的洛夫,承继了现代新诗诗体解放的精神,反对诗歌创作遵格律、拘音韵,他力求在“自由”的现代诗歌体式中,追寻和展示汉语诗歌的诗性之美。
洛夫在创作实践中,把现代汉语新诗的“自由体”式进行了淋漓尽致地发挥,除创作了让他在“‘空’境的苍穹眺望永恒向度”(简珍政语)的三千行长诗《漂木》外,他还创作了轻灵简短、意蕴生动的小诗,情境相彰的图像诗,和“带着脚镣跳舞”的隐题诗等不同样式的诗歌。在《日落象山》一诗中:“好多人围在山顶/围观/一颗落日正轰轰向万丈深谷坠去/让开,让开/路边的雁子大声惊呼/话未说完/地球已沉沉地喊出一声/痛”。在这首诗中诗人不仅分行,而且也不再遵循现代新诗一句一行的分行习惯,将“围观”、“让开,让开”和“痛”单独成行,如此分行突出了场景、动作和感受,也让静默的文字产生了奇特的音效和力量。在《好怕走在他的背后当他沉默如一枚地雷》中他写到:“当蠹鱼吃光了所有的文字且继续产卵/他开始发愣/沉思/默想他雪一般的身世,惨淡/如一张白纸/一/枚无声的/地/雷,在最深处暗藏杀机”。在这首隐题诗中,为暗合了“他沉默如一枚地雷”,诗人将“一枚无声的地雷”切割成四句,诗不仅未因此而显得分散,而且诗歌的节奏、内涵和诗人的思想情感有机地结合起来。尤其是最后一句“雷,在最深处暗藏杀机”,为读者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在《午夜停电——兼怀胡适》中,他写到:午夜停电/他突然被推进/一方格之黑漆棺柩/大地无声而众花纷纷凋落/世人哪/你们可以开始任意议论了/当熠熠星光/隔窗逼射而下/把他狠狠钉在/历史的中央
在这首图像诗中,洛夫站在历史的高度去怀念胡适先生,无论世人如何褒贬评判,胡适在洛夫心中都犹如夜空中闪烁的星光,而原本柔和的星光在借助“隔窗逼视而下”的线性排列下,化无形为有形,化绵柔为凌厉,以显示胡适的文化与历史地位。洛夫对“自由体”的追求,并不必然地弃绝一切规范的体式,相反他还以现代语言佐以古典句法进行作诗。如《雨天访友》便模拟骈文的四六句法,如:雨天过访/什么样的天气/尚未敲门/什么样的乡愁/伞的水渍/满街只有风雨/溅入颈项/不见一瓣杏花/沿背而下/骤闻高楼有人/……“在洛夫看来诗永远是一种语言的破坏与重建,一种新形式的发现。因而,他对诗歌的形式有着深刻的自觉,千种文意他能设计出千般形式。洛夫所追求并不是现代诗体对旧体诗的表面“形式”上的解放——样式上分行去韵,而是在自由的体式中,追求诗歌形式的鲜活性和丰富性,以“活”的诗歌形式去承载现代人的思想、情感和想象。
洛夫在《重整诗的形式》一文曾指出:“任何一首诗都有它本身的形式,而且不同的内容都应该有它不同的形式。传统诗中的任何内容,都只以少数几种固定的框框来表现,这是违反文学有机原理的,故传统诗的格律是一种僵固的形式,不适于表现现代人较复杂的情感、思想、和经验。今天现代诗虽然放弃了旧诗的格律,但并不表示不再需要诗的形式,否则,诗与散文何异?”所以,“诗人为了表现某一特定的内容,就必须要创造出某一特定的形式,而且这一形式是独一无二的,别人不可能模仿的,……我认为每一个诗人都应该有一个抱负,那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去创造最佳的形式,以表现最佳的内容。” [3]185洛夫对诗歌样式上的追求不止在于观念上的阐发,更在于他的诗歌实践。洛夫通过对语言的重建,以分行、转行、标点符号的运用,以倒装、词语重构的方式,让诗歌形式和主体情感有机融合,从而使诗歌产生的内在张力和戏剧性效果,让每一首诗都有优美自足的结构形式,进而提升诗歌质量。在他的《冬天的日记》《湖南大雪》《长恨歌》《白色墓园》《石室之死亡》和《漂木》等诗作中,我们能领略他的诗歌形式之美,也能感受到他在诗歌形式探索所表现出的执着与勇气。在《白色墓园》一诗中:白的/一排排石灰质的/白的/脸,怔怔地望着/白的/一排排石灰质的脸/白的/干干净净的午后……/这里有从雪中释出的冷肃/白的/不需要鸽子作证的安祥/白的/一种非后设的亲密关系/白的
诗人故意以一整排“白的”并列,形成了一种视觉上的奇特效果,诗中的意象也仿佛化作了一处充满白色十字架和纯洁灵魂的静寂墓园。在《湖南大雪》一诗中:“雪落无声/街衢睡了而路灯醒着/泥土睡了而树根醒着/鸟雀睡了而翅膀醒着/寺庙睡了而钟声醒着/山河睡了而风景醒着/春天睡了而种籽醒着/肢体睡了而血液醒着/书籍睡了而诗句醒着/历史睡了而时间醒着/世界睡了而你我醒着/雪落无声”诗人以“雪落无声”作为诗的首末两句,中间加以十行严整、重复的“睡了……醒着”的构句,展示出一个雪花滑落的寒夜,无论是自然和人文,世间的一切都处于睡与醒、变与不变之间,诗人不仅让诗的意象充满着矛盾和张力,而且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也产生了一种张力。一切仿佛都是应该是沉寂和有秩序的世界,却又充满着对峙和沸腾。在现代新诗形式发展进程中,无论是构句和分行都是一个不断求新的过程,但标点符号却显然是被逐步淡化的,或者弃用或者以空白格代之。然而在洛夫诗歌中却启用标点符号,并赋予它们以特殊的功能,从而赋予诗歌形式以变化。在《漂木》中他写到:“西瓜。青脸的孕妇/凤梨。带刺的亚热带风情/甘蔗。恒春的月琴/香蕉。一篓子的委屈/地瓜。静寂中成熟的深层结构/时间。全城的钟声日渐老去/台风。顽固的癣疮/选举。墙上沾满了带菌的口水……”以一个名词或简单的意象,中间加以句号,而后以蕴含情思的句子附后,这样的形式能够引发读者的想像,增强诗歌表达效果。洛夫分析这种诗歌形式说:“上下两句看起来互不搭调,但似乎又有某种意义上的联系。就意象而言,犹如一幅幅绘世图,背后的形象看似错乱,却又给人十分真切的感受,这是对令人惊悸的现实所做的严肃而含蓄的批判。” [4]254洛夫以丰富多样的诗歌形式去提升诗歌质地,这正是洛夫对现代新诗传统的意义——不仅让诗歌自由地飞翔,而且还完善了“自由体”的内涵,成就了“自由体”价值。
二、洛夫的诗歌创作技巧与现代中国新诗传统
虽然现代新诗借鉴西方诗歌艺术实现体式上现代性转变,但现代诗人在精神情调和审美心态上难以完全承袭西方诗歌传统,也难以完全超越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因此,在汉语诗歌近百年的发展进程中,如何批判地继承外国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资源,进而推动现代汉语诗歌建设,一直是诗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艾略特在《叶芝》一文中指出:“一个有能力体验生活的人在一生中的不同阶段,会发现自己身处于不同的世界;由于他用不同的眼睛去观察,他的艺术材料就会不断地更新,但事实上,只有很少几个诗人才有能力适应的变嬗。” [5]169洛夫就是具备这样能力的诗人之一,不同的生存境遇给了他不同的生命体验。从离乡去台到离台“放逐”,在行路天涯的途中,洛夫的境遇和心境在变化,洛夫的诗艺也在变化,从高调地宣扬“超现实主义”到默默地回眸古典诗歌传统,洛夫以复杂多变的诗歌艺术表达出生命的孤绝、苦涩与凄楚,也表达出他对中西诗歌诗学精神的理解。洛夫继承了现代诗人借鉴西方诗歌艺术传统,积极推动岛内新诗运动,并努力从西方诗歌艺术中汲取艺术精髓。但洛夫对西方诗歌艺术并非全盘接收,他认识到西方现代艺术的不足,因此他接受了西方诗歌的艺术精神,但语言表达上却回到了中国。同现代诗人相比,洛夫对古典诗歌传统也并非全盘否定,在拒绝古典诗歌的格律形式的同时,他接受了古典诗歌的美学精神,“以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来沟通现代”。洛夫就是融合运用中西诗歌艺术资源,自觉探索诗歌艺术,让汉语绽放出了炫丽的诗性之光。
1949年洛夫带着冯至、艾青的诗集离乡去台,故乡已是“再也不能以仰姿泅回去了”的方向,而异乡漂泊的行程、残酷的战争和压抑的文化政治环境,却又让他的内心时刻承受着孤独、“放逐”和压抑之苦。为纾缓内心的压力,报复残酷的命运,洛夫将生命的悲喜全部忠实地反映于诗歌之中。虽然去台初期洛夫写下了如《饮》《芒果园》《灵河》等抒情韵味十足的诗歌,但在《投影》《我的兽》以后,他便跋涉于西方诗歌是艺术领域中,开始“超现实主义”诗歌艺术的实验与探索。洛夫之所以执着于“超现实主义”诗歌艺术,其中既有对官方战斗文艺话语的自觉抵制,也有对其时西方现代主义主潮的响应,尽管洛夫等《创世纪》的诗人们反对现代派的“横的移植,但“处于艺术贫血和渴求新的表现手法”的他们,还是“不自觉的乞灵于西方的缪斯”。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洛夫在接触约翰·丹恩、叶慈、里尔克、蓝波、尼采、沙特、贝克特等人的作品之后,发现西方诗歌艺术中意象、象征、隐喻、潜意识等艺术手法利于生命个体经验的表达,洛夫说“一开始接触西洋文学时,我即对浪漫主义作品产生抗拒,当时令我着迷的反而是那些风格近乎晦涩,读来似懂非懂,却又惊喜于那种奇特的表现方式的现代诗。” [6]54洛夫努力在西方诗歌艺术和现代汉语诗歌间寻求连接点,其里程碑式的《石室之死亡》便是这种结合的呈现,“只偶然昂首向邻居的甬道,我便怔住/在清晨,那人以裸体去背叛死/任一条黑色支流咆哮横过他的脉管/我便怔住,我以目光扫过那座石壁/上面即凿成两道血槽/我的面容展开如一株树,树在火中成长/一切静止,唯眸子在眼睑后面转动/移向许多人都怕谈及的方向/而我确是那株被锯断的苦梨/在年轮上,你仍可听清楚风声、蝉声”。诗人以苦涩而沉重的语言,用密集的意象去表现面对死亡、命运无从把握的那种彷徨、苦闷和恐惧的心理。在表达对亲人的情与念时,洛夫写道“而妈妈那帧含泪的照片/拧了三十多年/仍是湿的”(《家书》“母亲/我真的不曾哭泣/只痴痴地望着镜子/望着镜面上悬着的/一滴泪/三十年后才流到唇边”(《悼亡母》)。三十年未拧干的泪、三十年才流到唇边的泪,是那样“无理”而却又那样的真实。直至《魔歌》以前,洛夫都一直致力于超现实主义诗艺探索。那隐晦的语言和复杂的意象,不仅有效地传达了诗人生命的感悟和形而上的思考,也为中国汉语现代诗开辟了新的领域。
超现实主义借助想象、梦幻、潜意识等内在精神活动作用,使诗人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理性和意识的控制。然而诗歌的语言是感性的,也是理性的,完全摆脱理性控制,诗人的想象之翅是无法回到语言的“秩序”之内的,诗也就不能很好地传达诗人意图,也就更不能提升诗歌应有的品质。随着生命智慧和诗歌创作的累积,洛夫逐渐认识到超现实主义技巧的缺陷与不足,他在《超现实主义与中国现代诗》一文中指出:“对以语言为唯一表现媒介的诗而言,如采用‘自动语言’而使语意完全不能传达,甚至无法感悟,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我不认为诗人纯然是一个梦吃者,诗人在创作时可能具有做梦的心理状态,但杰出的诗最终仍是在清醒的状态下完成的。” [2]278因为“诗毕竟是一种灵智的活动,超现实主义者所标榜的非理性的自动语言,对于一首诗的完成是不可能的。诗可以‘无理’,只是必须产生‘妙’的艺术效果,这种效果大都体现在语言的趣味上,而完全不受理性控制的语言是无法产生这种趣味的。” [2]272因而《魔歌》之后,洛夫不断修正诗艺,开始有所批评、有所选择地运用超现实主义,探索将西方诗歌的创作艺术和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结合起来。洛夫在《月光房子》诗集自序中说:“我确曾一度倾心于唐诗的气象与妙悟,尤其在我实验超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时,经常因某些意象与句构暗合前贤而欣喜不已。我读唐诗愈勤,所得愈多;我从杜甫和李商隐笔下学到如何经营意象,从李白笔下学到如何处理戏剧结构,从王维与孟浩然笔下学到如何通过自然表现禅趣,从贾岛与崔灏笔下学到如何掌握生动的叙事手法。” [7]在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阅读和诗美的认识中,洛夫不仅发现西方现代主义的某些观点、表现技巧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有意想不到的回声,而且他还“惊奇地发现,古典诗中那种幽玄而精致的意象语言,那种超越时空的深远意境,远非西洋诗可比。除了探寻到唐诗中那种比超现实主义更为周延的‘无理而妙’的表现手法之外,我更从苏东坡那里找到了一把开启诗歌秘宫的钥匙。他主张‘反常合道’的诗观,正与我的修正超现实主义吻合。” [2]286从标举超现实的大旗到追求“无理而妙”、“反常合道”,洛夫逐步打通现代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的隔膜,探索出将西方超现实技巧和东方妙悟之境融合统一的诗歌艺术。在其诗作《金龙禅寺》中,就鲜明体现出他的这种诗艺追求。“晚钟/是游客下山的小路/羊齿植物/沿着白色的石阶/一路嚼了下去/如果此处降雪/而只见/一只惊起的灰蝉/把山中的灯火/一盏盏地/点燃”晚钟何以成为小径?羊吃植物何以咀嚼?灰蝉何以点燃灯火?这些看似“无理”语言结构和意象组合,却又构成了广阔、深邃、奇妙的意境。
“五四”以后,从早期的象征派到上世纪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群再到上世纪40年代的九叶派,现代诗人对借鉴西方诗歌艺术表现出强烈的倾向,并以之去改造中国旧体诗歌,建设汉语新诗。现代诗人融合西方现代主义观念、艺术和风格的诗歌创作,对现代诗坛造成了影响,也推进了汉语新诗的现代化进程。洛夫在去台之前就接触诗人冯至的作品,多年后他认为自己与冯至在诗艺看法上是同源相通的。洛夫对里尔克的推崇,对超现实主义诗歌艺术的自觉追求,冯至是有引介之功的,我们认为也正是经由冯至,洛夫承继了现代新诗诗艺的创新精神。但洛夫对西方现代诗歌艺术的态度和指向性是不同于现代诗人的,洛夫曾说:“我是最现代的,但也是最中国的。当年我向西方取经跋涉异域,那是一种偶然,而后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来,承袭先贤们的文化遗产,以谋求更优质的创新,这是一种必然。” [8]24洛夫对诗歌艺术探索的最终归宿是以现代诗歌艺术的眼光去观照中国古代诗歌传统,以西方诗歌艺术和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的融合,去实现中西诗歌以及传统与现代诗歌间的对话,推动汉语新诗建设。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任何诗艺都是成就诗歌意义之美的手段,最终都要通过语言来表现的,洛夫对西方诗歌艺术的借鉴以及对古典诗歌传统的回归,其指向在于变革现代新诗粗糙的语言,在建设现代美学规范下的语言的基础上,继承和丰富汉语诗歌的本质。从“横的移植”到“纵继承”,洛夫的诗艺路程正如他回顾《创世纪》发展历程时所言,“《创世纪》五十年来跋涉过西方现代主义的高原,继而拨开传统的迷雾,重见古典的光辉,并试着以象征、意象和超现实诸多手法来表现中国古典诗歌中那种独特美学,经过多年的实验,我们最终创设了一个诗歌的新纪元——中国现代诗。这不仅是《创世纪》在多元而开放的宏观视野中确立了一个现代汉语诗歌的大传统,而且也是整个台湾现代诗运动中一项毋庸置疑的傲世的业绩。” [9]84对诗歌艺术的探索与追求,并在多元而开放的宏观中确立了一个现代汉语诗歌的大传统,这也正是洛夫诗歌艺术对现代新诗传统的超越之所在。
三、洛夫对现代中国新诗传统的继承与超越的当代启示
传统是面向未来的活力范畴,它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创新。文学的薪火之所以能传承不息,不在于守成和复古,而在于超越与创新。纵观现代诗歌作品所呈现的现代中国新诗发展史,不难看出那其实也是西方诗歌传统和古代文学传统的对抗与对话的复杂过程。传统是发展的,是不能重回的,洛夫说他“向古典诗借火不过是一种迂回侧进的策略,向传统回眸,也只是在追求中国诗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权宜而已。” [2]280因而,我们认为,洛夫无论诗歌形式的创新,还是诗歌艺术的探索实验;无论是标举超现实主义,抑或回眸古代传统,其终极目的不是在推动西方诗歌传统本土化和古代诗歌现代化的转型,而是在为现代汉语诗歌寻求更适合的表现方式和角度,实现汉语诗歌的艺术升华,是在丰富现代新诗传统的内涵。洛夫对现代新诗传统继承与超越启示着我们:继承和发扬传统并不是简单地接受,而是要以创新的姿态去超越和发展传统,进而去建设真正的中国现代新诗。
自1949年以后,现代新诗拓展为当代大陆诗歌和海外华文诗歌两大流脉,两脉虽同根同源,但却呈现出不同的生命形态。这是现代新诗传统在不同文化政治和社会环境中传承、变异的结果,也体现了当代汉语诗歌的复杂性、多样性的一面。当代大陆诗歌在五六十年代经受政治话语冲击,而后又受到了欧风美雨的洗礼,新时期以“朦胧诗”发端,“新现实主义”、“整体主义”、“非非主义”、“新古典主义”等诗歌流派不断推陈出新,从狂热地借鉴地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与艺术到“文化寻根”,当代诗人们在迎接和反叛西方诗歌艺术中,进一步革新了诗学观念和诗歌技巧,实现了诗歌艺术的创新,诗歌语言也显现出空前的活力与韧度。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也有不少诗人对西方诗歌艺术和古典诗歌传统存在误解和误用的现象,比如在诗歌创作中过度强化个体的心灵体验,打乱古典诗歌传统中的意象体系,消解古典意境美,缺乏对语言的锤炼等等问题。沈奇在《重涉:典律的生成》一文中指出:“当代新诗的混乱,不仅因为缺乏必要的形式标准,更因为失去了语言的典律。格律淡出后,随即是韵律的放逐,抒情淡出后,随即是意象的放逐,散文化的负面尚未及清理,铺天盖地的叙事又主导了新的潮流,口语化刚化出一点鲜活爽利的气息,又被一大堆口沫的倾泻所淹没。” [10]1一些诗歌的表面化创新,可能是出于对时尚的追风,但最终偏离和伤害了诗歌的本质。而这样的问题在海外华文诗歌创作中也同样存在。现代新诗在追求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自身丰厚的传统,它和中国古代诗歌传统以及西方诗歌传统一起,共同成为当代诗歌创作最宝贵的艺术资源,当代诗人应该利用好、经营好这些宝贵的艺术资源。那么,当代诗人如何利用好、经营好这些宝贵的艺术资源,从而去进行汉语诗歌创作呢?洛夫说:“当代中国诗人必须站在纵的(传统)和横的(世界)座标点上,去感受,去体验,去思考近百年来中国人泅过血泪的时空,在历史中承受无穷尽的捶击与磨难所激发的悲剧精神,以及由悲剧精神所衍生的批判精神,并进而去探索整个人类在现代社会中的存在意义,然后通过现代美学规范下的语言形式,以展现个人风格和地方风格的特殊性,突现大中华文化心理结构下的民族性,和以人道主义为依归的世界性。” [11]102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交汇的今天,洛夫的创新精神,洛夫对新诗传统的态度,对建设汉语诗歌的责任,都为当下诗歌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示范。当代诗人不仅要审慎地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现代诗歌传统和西方诗歌传统汲取创新因素,而且要真正地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汉语现代诗。这样,才能保持诗人的尊严,保证汉语诗歌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