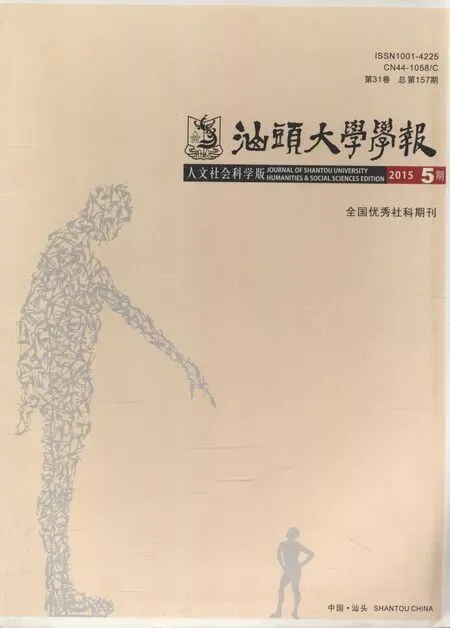私利与公义:近代来华传教士在苦力贸易中的曲折抉择
2015-04-03李彬
李彬
(中山大学历史系,广东广州510275)
私利与公义:近代来华传教士在苦力贸易中的曲折抉择
李彬
(中山大学历史系,广东广州510275)
近代以来,苦力贸易逐渐兴盛。自明代始,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开始接触苦力贸易,但传教士与苦力贸易的关系十分复杂。部分来华传教士对人口拐卖存在模糊认识和错误倾向,被西方拐匪利用。1850年以后,苦力贸易的弊端越发暴露,越来越多的来华传教士认清苦力贸易的真实面目,或利用小册子、报纸等方式大力反对,或者利用权力加以规范制止,或者深入险境解救受害者,显示其主流是持反对态度的。来华传教士主流的反思和进步,捍卫了人道主义和基督宗教的尊严。
苦力贸易;私利;公义;来华传教士
西方列强主导的苦力贸易,在1850-1880年达到高峰。其中,拐匪是苦力贸易中最重要的中间群体。拐匪乃非法拐卖和劫掠人口的群体,具有欺骗性和暴力性。拐匪群体的来源甚为广阔。以往历史研究中,来华传教士往往被指责为拐匪,或拐匪的爪牙。这一结论从建国以来一直保持到现在,并被部分学者继续引用着。真实的情况是否这样呢?实际上,传教士与苦力贸易的关系非常复杂。有关苦力贸易和传教士的客观研究,国内还相对匮乏。不过在国外,美国学者卫斐列和爱德华·V·吉利克对新教传教士卫三畏、伯驾与苦力贸易的关系,已作出一定的客观研究,指出他们对待苦力及拐匪的复杂态度。理清来华传教士和苦力贸易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深化苦力贸易的研究,廓清历史迷雾、澄清事实真相。笔者搜集相关史料,以晚清时段的华南地区部分来华传教士为切入点,揭示其复杂面相,辨析来华传教士主流群体对苦力贸易态度的整体转变,望方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传教士与苦力贸易的接触
苦力贸易最早可追溯到明代,但具体时间尚无定论。[1]明代中后期,天主教在东南亚登陆,努力向当地的华人传教,并试图入华传教。当时部分华南民众常借助帆船,到东南亚务工贸易。1552年,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St.Francois Xavier)抵达中国沙上川岛。他曾观察到华商与葡商做贸易,并欲借华商之手进入中国传教。[2]这显示,早在明代耶稣会传教士就已知晓华工出国之事。继他之后,耶稣会传教士陆续东来,在澳门逐渐站稳脚跟,对澳门的中国人进行传教和统治。“有历史家记载当时耶稣会士的日常事务,说得很清楚:每八天或者每十五天,轮流实行各样圣事一次,向一千名上下的奴隶讲解教理,为孤女或本地教民处理婚姻,为维持当地民众的健康,先向果阿遣送第一批奴隶妇女四百五十名以上,以后又遣送出第二批,约二百人。”[3]所谓的“维持当地民众的健康”,就是将中国妇女当做葡人的性奴隶,使多半华侨妇女成为娼妓。[3]从文献记载来看,耶稣会士传教士为了传教和维护母国利益,成为最早接触并参与苦力贸易的来华传教士。近代以来,耶稣传教士对澳门苦力贸易态度暧昧,有反对,也有保留。相比而言,新教和天主教传教士虽均有参与苦力贸易者,但前者主要出现在苦力贸易中期,而后者在前后都有。此点在后文将细述。
19世纪初,苦力贸易逐步兴盛起来,受到来华传教士的关注。据目前国内披露的资料,最早关注并记载苦力贸易的新教传教士,是英国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虽是最早的来华新教传教士,但对于苦力贸易却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马礼逊来华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早已在华南拐卖苦力,贩运到东南亚,一直持续到1834年。[4]1809年马礼逊曾进入东印度公司当翻译,协助对华贸易。[5]249-289由于资料缺乏,马礼逊是否知晓或者参与苦力贸易,尚存疑惑。不过马礼逊参与苦力贸易的可能性不大。他即便知晓苦力贸易,了解得也不深。因为他长期在广州—澳门的狭小地带活动,主要从事翻译、写作以及传教,工作繁忙,不常外出活动,不可能接触苦力贸易。长期旅居东南亚的米怜则具有这种可能性。自明代以来,东南亚就是重要的华工移入区,历史悠久。1812年米怜被英国伦敦会派往东方协助马礼逊,1813年首先到达马六甲,到华人社区中传教。[6]1821年,前往雅加达的中国苦力船只发生沉船事件。米怜听说后,于1822年1月29日,致信马礼逊,报道了这次海难,“一艘载有1600个移民前往巴达维亚的中国帆船,行经盖波斯海峡触礁沉没,只救起190人,其余1410人全都溺毙了。另一艘同行的中国帆船,见此情况,没有去救人,却径自继续航行驶走了。而那190人是被印度商船‘珍珠号’所救。唉,这就是所谓的异教徒强烈鼓吹的手足之情!这就是那些不信福音的人!”[5]151这封信是新教传教士记载苦力贸易的最早明确文献。米怜基于基督精神和人道主义,描绘了简要的细节,着重谴责了中国船商的见死不救,除此之外并没有提及更多信息。这封书信属于私人信函,当时并未公开,影响范围很小。
第一位公开报道苦力贸易的传教士,则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卫三畏于1833年被美部会派往广州传教,主要从事印刷工作,协助裨治文(Bridgman)传教和筹办Chinese Repository。卫三畏在华时间较长,他对苦力贸易的经历和反应是当时传教士的典型代表。1849年,主编裨治文迁居上海,编辑Chinese Repository的重任便落到卫三畏的肩上。[6]在工作中,卫三畏十分注意收集华南地区的时政消息。1849年,北美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到了广州。卫三畏注意到了这则消息对广州民众的诱惑,预测中国的“大量人口移居将带来俄勒冈州和中国之间贸易的稳定发展,也会吸引更多的中国人前往加利福尼亚”。[7]96卫三畏继续分析,认为广州民众的求富心理会成为出国高潮的一大动因。1850年,华工向美国大规模移民,出现高潮。这年向加利福尼亚移民的华工共约4000名,其中很多是从广东出发,经香港和澳门,被拐匪卖到美国西海岸或古巴和秘鲁等国。[8]卫三畏于1850年6月,在Chinese Repository首次报道这次移民高潮。兹翻译如下:
在秘鲁种植园工作的中国苦力已经引起了许多注意。金星门附近已经有几百人被鼓动组织起来,运往利马。对于苦力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苦力群体中,几乎所有人都未带家属。我们接到消息称,大约1000名苦力用他们的方式来到加利福尼亚。在加州,他们像在海峡殖民地一样,组建了同乡会社,并且雇佣了一名美国律师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在未来的年份,中国人向美国西海岸移民的速度会加快。[9]250
在第一次报道中,卫三畏首先表面总结了中国苦力移民的特征:远赴美洲、不带家属、同乡自卫。其次,他发现了海峡殖民地的华工移民同美洲移民之间的共同点:利用宗族同乡关系组成团体,出国务工。这说明卫三畏已经知道了华工向东南亚移民和组建同乡会的事实。第三,他提到华工雇佣美国律师的事情,显示了华工对美国法律的重视。第四,卫三畏对苦力贸易的发展趋势做出了准确的预测。当时的美国西海岸正值开发时期,美国实行自由移民的政策。其二,华工的求富心理也推动了苦力贸易的进行。但这则消息没有披露招工的手段和细节,也未提及相关弊端。从Chinese Repository的记载和马礼逊、卫三畏等传教士的日记来看,近代早期来华传教士对大清律例并不十分清楚。然而此时的苦力贸易尚未合法,华工被禁止出国,否则将被严惩。可见他们对苦力贸易接触不多、了解不深,且并非个别现象。
随着苦力贸易的推进,传教士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相关信息,对其认识逐步增多。1850年9月,Chinese Repository再次报道了中国苦力向美洲移民的情况。[9]516-517第二次报道的篇幅大大增加。卫三畏详细记录了这次华工出国的过程,包括目的地、工期、工价、苦力死亡等,特别提到了苦力暴动的事件。法国籍商船“阿尔伯特”号在航行途中,船长强剪苦力辫子并虐待苦力,苦力暴动,船长被杀,苦力迫使水手将船开回中国。卫三畏在文中,将暴动的苦力污之为“罪犯”或“强盗”。一年后,卫三畏仍然关注着苦力贸易,且向苦力移民分发教务册子,试图传教。[7]103在这期间,卫三畏对苦力贸易的理解逐步加深。他看到了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之间的关系。“鸦片贸易使中国越来越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只能靠偷盗、抢劫为生,或者向外移民以求生路”。[7]101鸦片战争加剧了白银外流和华南农村的贫困化,成为社会动乱和苦力移民的深层原因。Chinese Repository停刊后,卫三畏在家信中论述了苦力移民加速的原因。他认为华工的贪欲、性情等特点是苦力贸易加速的重要原因。他当时并不反对苦力贸易,希望苦力“能给中国带来改善”。但他在信中也说,“这些可怜的劳工并没有成为移民,只要想想他们去干的可怕的活儿就能明白这一点”[7]103,透漏出他对苦力的同情和隐忧。
1854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创办的《遐迩贯珍》,曾报道秘鲁船只“烈百达”经香港,载苦力移往美国旧金山,途中被人抢劫。之后,他又报道揭露了船上的少量弊端,如超载、苦力缺衣少食、船内污秽不堪,除此之外并无其他。[10]目前其他有关早期传教士的史料,除了郭实腊在游记中略微提及少量苦力移民,其他传教士尚未直接提到苦力贸易。[11]这整体显示,鸦片战争以后,部分来华传教士对苦力贸易的了解虽比以往加深,但表面性的理解仍居多数。尽管他们提到了苦力暴动,却并不清楚其中的弊端,显示这时期的部分传教士对苦力贸易仍然存在着模糊认识和错误倾向。这使他们易被西方拐匪所欺骗和利用。
二、传教士对苦力贸易的参与
19世纪中期,西方殖民者为了开发美洲等地,利用在华传教士诱招苦力。在出洋的苦力中,尽管有少数是自愿出洋务工的,但大部分都是被拐匪诱拐或者劫掠的。1859年,英国殖民部策划诱招华工,开发圭亚那种植园。香港维多利亚教区主教向“招工专员”奥斯丁推荐了威廉·罗布柴尔德牧师。罗布柴尔德在中国传教行医多年,“熟悉华工出洋情形”。罗布柴尔德设计了详细的招工方案,其中主要的措施是重金引诱华工及其家属,但他也制定了保护华工权益的相关规则。为扩大宣传效果,他建议奥斯丁印发中文传单,并愿意用个人声望和人际关系协助招工。在罗布柴尔德和其他传教士的大力鼓动下,英国共诱招约3000名华工,其中包括许多中国家庭和基督徒。[12]22-23尽管罗布柴尔德个人认为招工出洋的条件很优厚,能给华工及家庭带来“福音”,但在此之前他并未去过圭亚那,并不清楚那里的真实情况。而后来调查发现,等待华工的根本不是什么“福音”,而是圭亚那恶劣的工作环境。①当时的圭亚那流行黄热病和疟疾,被英国人公认为“最不健康、最危险的地方”。后来被贩运去的华工死亡率很高。详见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六辑《拉丁美洲华工》,中华书局1984年版,23-24,92页。
曾任美国驻华公使、长老会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也包庇过美国拐匪。伯驾于1834年被美部会派往中国传教,开创“医务传教”的模式,在华南活动多年,但传教效果并不显著。1852年,伯驾鉴于传教和资金问题,代理美国驻华公使。[13]22-26同年,他碰到了“罗伯特·包恩”号案件。美籍苦力船只从厦门开往旧金山的途中,苦力暴动,船长、两名官员、四名船员和几十名苦力在混战中死亡。幸存的船员和美籍官员掩盖虐待苦力的事实,污蔑苦力是“罪犯和强盗”。伯驾偏信了他们的说法,主张对苦力严厉惩处。可在调查中,伯驾发觉了船商羞辱虐待苦力以及强剪苦力辫子等部分隐情。尽管如此,他仍主张将犯有“严重的海上抢劫罪”的17个华工处死。广东官府据理力争,最后迫于压力被迫屈服,不得不关押这17人,但是仍然变相抵制。后来,1人被处死,1人死于狱中,其他15人无罪释放。在此案中,伯驾因不完全清楚其中的隐情,为维护本国船商的利益,恶劣地包庇了美国拐匪。[13]157部分传教士参与或包庇苦力贸易是不争的事实。这使得相关传教士的名誉受损,导致华南诸多民众将许多传教士及教徒等同于拐匪,为晚清教案埋下伏笔。1859年前往珠三角招工的中国基督徒,就被村民当成拐匪群起围攻,差点被杀。[12]3150年代中期后,拐匪泛滥,悲剧不断发生,很多苦力“生入地狱之门,死做海岛之鬼”。[15]中外拐匪的诱掠手段令人发指。有的拐匪以介绍工作为由拐骗;有以做合伙买卖为由拐卖到猪仔馆;有的强说对方欠钱,将对方强拉卖掉;有的以交易为由,请对方到船商看货或者交钱,趁机将对方拐卖;有的直接租买帆船,专门航行在珠江航道上趁机绑架;有的甚至直接大白天绑架等等。[16]74-75非法诱拐、暴力劫掠、虐待苦力及苦力暴动等惨剧,被人们广泛传播。苦力贸易的非人道性,被许多海内外报纸广泛揭发,引起了中外正直人士的愤慨。在这种情况下,诸多来华传教士纷纷清醒过来,基于人道主义和维护基督教的需要,整体上对苦力贸易持反对态度。
三、传教士在苦力贸易中的反思与改进
传教士在接触更多的事实之后,开始转变态度。1852年伯驾在处理“罗伯特包恩”号案件后,发现了苦力贸易的弊端,转而倡导规范的移民制度,反对“猪仔贸易”,对苦力贸易的认识具体化。1855年,伯驾返美后,悔悟增多,通过大量的细节,警示政府,希望政府和国会采取相关措施。但国会置若罔闻。[7]1571856年伯驾接任驻华公使后,向美国驻华通商口岸领事发出通知,“在过去几十年中,就美国或其他国籍船只运载情况而言,充满了违法、不道德、使人憎恶和不人道的暴行,同以往年代的非洲奴隶贸易极为相似,有些还超过了‘大西洋中段航道’的恐怖,强烈反对政府及美国船只参与苦力贸易”,知照“所有美国公民放弃这种不正当、不道德交易”,警告“那些参与苦力贸易的美国人,他们这样做,不仅得不到美国政府保护……将科以重罚”。之后伯驾通知并联合卫三畏等人士,共同反对苦力贸易,壮大了声势。[14]14-90伯驾退休后,经常力劝国会议员反对“卖猪仔”,为禁止苦力贸易做出了贡献。[13]157
而前文提到的罗布柴尔德等传教士,通过实际行动为他们的错误做出了忏悔。罗布柴尔德完成招工后,并不放心。1861年他亲自赶往圭亚那调查华工情况,结果令他大吃一惊。等待他的不是感谢,而是华工们的诉冤叫苦。被诱招的华工被“非常不妥善地分配到柯冷丁河谷的各种植园里”。这个地方偏僻荒远,“交通困难,几乎与世隔绝”,而且蚊子特别多,致华工于危险境地之中。这使得罗布柴尔德及教会十分难堪。他为此亲自写了一篇调查文章《中国人出洋前往西印度》,披露相关弊端。罗布柴尔德联合相关传教士,不再与招工机构合作。相反,罗布柴尔德等传教士接连发回有关苦力移民的负面报道,并在附近广泛宣传,给英国拐匪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使他们几乎招不到人。位于达濠埠地区的英国牧师琼斯在华传教多年,曾解救过七八十个猪仔,“使他们免于沦为奴隶”。由此可看出,他是反对卖猪仔的。但吊诡的是,该牧师后来被英国招工专员奥斯丁利用,在达濠埠建立招工分所。他本意改革招工制度,杜绝非法拐卖,也曾努力这样做,并自信能成功。[12]34-35平心而论,他杜绝拐卖的意图是值得肯定的,但各国招工所根本无法杜绝拐卖,因为“雇佣苦力贩子和掮客,并派遣他们进入内地去招人出洋显然是必不可缺少的办法”。[17]由于资料缺乏,该传教士和所谓的“招工所”的具体情况尚不清楚。但琼斯牧师的构想很难不沦为空想或者变相拐卖的借口。
19世纪50年代末,拐卖中心逐步向澳门转移,澳门成为了最大的苦力贸易基地,而广州、黄埔、厦门、香港等地成为拐卖的重要区域。[18]181-186西班牙、法国、葡萄牙等国竞相使用“人头钱”,刺激了穷困的下层民众,使拐匪群体中出现了大量与受害人关系密切的同乡亲友群体。[19]163-186广州的美籍传教士卜列斯顿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当事人同村人、做买卖的合伙人、同一家庭成员,同拐子和受害人都有关系”,即使把苦力释放出来,也会经常受到拐匪的恐吓、折磨,使很多苦力宁愿留在船上等候查问,也不愿下船回家。这说明这时期的苦力贸易已经黑帮化,从上到下形成了利益链。鉴于此,卜列斯顿及他的老师要求在反对苦力贸易的同时,谨慎选择反对拐匪的方法。[14]216这一方面反映了他对苦力贸易的憎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拐匪的猖狂。
传教士反对拐匪的立场赢得了部分华南民众的赞赏。许多受害民众纷纷向传教士求助。传教士利用特殊身份,冒着生命危险,前往“猪仔馆”调查情况,或者营救“猪仔”或者“猪花”,引起了西方拐匪的反感。曾有一位自称是华工朋友的传教士参观澳门“猪仔馆”。这位传教士利用参观的机会,大做反对苦力贸易的宣传,刺激被骗华工群起反抗,结果受到在澳拐匪的咒骂和威胁。[12]1611859年底香港暂时禁止了苦力贸易,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基督传教士和报纸编辑的猛烈抨击。香港传教士不仅猛烈抨击在港拐匪,也强列反对在澳拐匪,引起了在澳拐匪的忌恨。尽管如此,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传教士不惧威胁,抨击在澳拐匪。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澳门耶稣会传教士并没有几个跳出来与之争辩,客观上默认了对方言论。[12]153-154联系后来耶稣会传教士反抗卖猪仔的事件看,澳门耶稣会传教士的主流还是反对苦力贸易的。
1859年,卫三畏专门撰写了中文小册子《对卖身异国者的警告》,描绘了被骗华工的悲惨命运,揭露葡萄牙拐匪的卑劣手段,强烈批判葡萄牙拐匪和其手下的中国拐匪,奉劝人们不要出洋作工。小册子共卖出6000册,影响非常大。在小册子里,卫三畏提到“葡萄牙人非常残忍,但是他们手下的那些中国人贩子更比他们残忍十倍。”[13]221他站在外国人的角度,没有认识到西方拐匪是终极元凶,眼光有些局限。但他的部分论点也不是空洞无凭的。苦力贸易中,中外拐匪关系密切。西方拐匪不熟悉华南的风俗地理,也不愿直接出面招惹是非,因而多将诱拐事务承包给当地的部分秘密会党,后者成为西方拐匪最重要的工具。西方拐匪多幕后操纵,提供保护和资金,而国内拐匪多负责诱拐绑架、看守等具体工作,对待苦力十分粗暴,草菅人命之事常有发生。国内拐匪中,存在大量的“生人拐匪”和“熟人拐匪”,最令人恐怖的是“熟人拐匪”。众多拐骗案中,常有朋友、“素识”、同乡充当拐匪,甚至还有亲生父母、养父母、兄弟姐妹、邻居等。[19]176-245笔者推断,华南一带的拐匪群体中,国内拐匪的数目极有可能超过国外拐匪。不过,西方拐匪仍是苦力贸易的主导。1860年,卫三畏得知美国船只在港澳地区参与拐卖华工,十分震怒。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协助官方截获了一艘满载着强掳来的华工拐船,主持审问了300多人。这些人最后全部获得了自由。这和卫三畏的努力是分不开的。[13]221
澳门成为拐卖中心后,拐匪十分猖狂,而苦力命运凄惨。1855年,曾为新教徒的容闳由美回国,抵达澳门,“第一次遇见之事,即为无数华工,以辫相连,结成一串,牵往囚室。其一种奴隶牛马之状也”,晚年回想这件事“尤为酸鼻”。[20]1867年,法国天主教徒卢德维奇,旅游参观了当时的澳门,后来以此写成《爪哇、暹罗和广州》一书。他亲自参观了澳门的“猪仔馆”,目睹了苦力贸易的真实场景,看到被拐华工们“个个面色惨白,神色凄惶”。他强烈谴责了苦力贸易,认为“这贩卖中国人的交易实在是一部催人泪下的历史……为了获得所需的‘猎物’,人们展开了多么可怕的杀戮,进行了多么无耻的投机,因此此交易比它所取代的黑奴买卖还要残酷千倍。”而更令他触目惊心的是,“前方见到一个年轻的华人,死命拉住管理华人事务官的坐轿,嚎啕大哭……眼前这名可怜的青年不满18岁,根据法律,他的申请(出洋做苦力)遭到拒绝。落选者跪在华人事务官面前,不断苦苦哀求……他求大人让他出洋,如果把他退了回去,出钱买他的主人就丢了利润,他就会因此受到最恶劣的对待。”[21]1776-1785这说明卜列斯顿所言非虚,也反映拐匪的罪恶实在是罄竹难书。
澳门的苦力贸易激发了耶稣会传教士的良知。1867年5月14日,10艘装备精良的海盗船,将劫持来的越南人卖到澳门“猪仔馆”。这批越南“猪仔”中有少数是天主教徒,他们竟奇迹般地打动了“猪仔头”。“猪仔头”将其转交给了圣若瑟修道院的耶稣会传教士,但没有释放其他“猪仔“。香港耶稣会传教士得知此事后,立即报告给当时的澳门总督麦当奴,请求释放。同时他们发动香港各界,为越南“猪仔”募捐,买了一艘船,遣送他们回国,使得澳门当局颜面大损。[22]253-254澳门耶稣会传教士也强烈地反对人口拐卖,但却受到澳门拐匪及当局的仇视。徐萨斯神甫不得不感慨地说:“葡萄牙本国和他的一些殖民地新近废除死刑和囚犯劳动的人道主义精神没有传到澳门。”部分耶稣会传教士,因此被迫从澳门撤出。[18]546-5471871年,部分澳门耶稣会传教士因反对苦力贸易,同澳葡政府闹翻,出现“隆迪纳日记事件”。沙维尔·隆迪纳神父在日记中,披露了澳门苦力贸易中的不人道行为。他将日记寄给华政衙门,揭露罪行,希望澳葡政府能改邪归正。他的举措取得了一定效果。根据日记披露的线索,法庭经过审讯,相关涉嫌人员以及“显贵”均被判刑。但是隆迪纳神父不久也因此遭到报复。里斯本颁布敕令,要求“澳门各修道院中的教师只能葡国传教士担任”。葡澳政府以此强化对在澳传教士的限制。耶稣会传教士隆迪纳、托马斯·卡伊尔、若瑟·维尔吉里等人,以及他们的至交葡国教士冯塞卡·马托斯和多明戈·佩拉雷受到牵连,不得不离开澳门。后来300多名澳门人联名上书,且议会局也质问葡国政府,对该辞令表示抗议。但是他们的抗议最终不了了之。[23]181-182
从目前的文献来看,尽管澳门传教士十分清楚苦力贸易同基督精神的冲突,但经此之后,据徐萨斯记载,澳门传教士主流虽然反对卖猪仔,但受制于澳葡当局不再公开反对。之后澳门传教士与修女主要从事教会教育以及慈善活动等,如办学校、接济穷人或者收容遗弃婴幼儿。[21]1900-1924之所以会发生这种转变,是因为教会深受澳葡政府的挟制。苦力贸易所得的巨额利润是澳葡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葡萄牙是处于衰落中的老牌殖民帝国,同英美等国相比竞争力有限,不得不尽力维护有限财源,致使传教士们投鼠忌器。[21]1783再者尽管传教士是澳门精神文化的主导者,但毕竟不是实力派,对早已失控的苦力贸易作为不大。少部分澳门传教士在利益和正义的冲突中,选择了前者,放弃了后者,令天主教蒙羞,也把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直到民国时期,天主教神甫徐萨斯(Montalto de Jesus)在编写《历史上的澳门》一书时,才做出一定的反思和忏悔,终于还历史以正义。[23]252-259
相比之下,在公开反对卖猪仔上,澳门耶稣会传教士不如其他地区传教士做得出色。在反对拐卖的过程中,传教士经常采用小册子和报纸形式广泛宣传,为警示民众、反对拐匪做出重要贡献。1858年2月,一位英国传教士联合医生和船长致信《北华捷报》,揭露了苦力贸易的惨无人道。位于汕头妈屿岛被暴尸海滩的16具“猪仔”尸体以及被抛弃的有病“猪仔”,惨不可言,那些未被掩埋的16具尸体,“只等鸟兽来吞食,一般是喂狗、喂猪”,“还有两名苦力,快要饿死,其中一个发着高烧。”最后传教士等人把一部分濒临死亡的“猪仔”救了。[16]61由于《北华捷报》行销上海租界等地,且1851年以后传教中心逐渐向上转移,上海逐步取代广州成为来华传教士的中心,故《北华捷报》对外国舆论影响较大。[24]这则报道引起了中外震惊,不少人士受其影响纷纷反对苦力贸易。1865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湛约翰创办了的中文周报《中外新闻七日录》,揭露和批判了澳门的拐卖丑闻,引起了世人关注。[19]25-28此外香港传教士和部分编辑利用《中国邮报》,大力反对苦力贸易,其中大量文章被海外报刊转载,对粤港澳乃至海外影响很大,对禁止苦力贸易有直接推动作用。[25]1872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P·Martin),联合在京传教士创办中文报纸《中西见闻录》,设置“各国近事”栏目,在其中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专门批判和揭露古巴、秘鲁、澳门等在苦力贸易中的罪恶,赞扬埃及等国解放奴隶的举措,主张严禁苦力贸易。[26]《中西见闻录》每月发行大约1000份,大部分免费发送,直接影响了北京、天津等地。《中西见闻录》的相关文章也曾被上海的《教会新报》、《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等其他报纸书籍转载。《中西见闻录》和丁韪良主编的《中西见闻录选编》甚至还流传到了日本,对于反对苦力贸易具有较大的意义。[27]而丁韪良直到晚年,依然在回忆录里强烈批判澳门的苦力贸易。[28]
1860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加入到反对苦力贸易的行列,其中有些传教士如琼斯力主苦力贸易合法化、规范化,有些如伯驾和卫三畏等直接反对,还有些传教士深入“猪仔馆”勇敢救人。他们利用报纸、小册子、传单等形式,大力揭露苦力贸易的弊端,强烈谴责中外拐匪,力所能及地营救受害者。不少中外人士受其影响,也纷纷加入反对苦力贸易的阵营,使禁止苦力贸易成为世界舆论共识。总体上,苦力贸易中后期的来华传教士态度已明显转变,主流对其不支持或反对,甚至积极同中外拐匪进行斗争,值得肯定和赞赏。
不过,苦力贸易造成了深重的灾难,给闽粤民众和海外华工留下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部分民众基于民族主义和过激情绪,产生盲目排外情绪,使在华传教士受到波及。少数传教士有过拐卖人口的历史,自然难辞其咎。其他部分传教士虽然没有拐卖人口,但是在其他方面如司法、地产、风俗等方面,经常借助外国侵略势力,欺压民众,与当地官府和民众存在着很深的矛盾。清末时期,闽粤受北方义和团的影响,教案迭起。其中民众在反洋教斗争中,所持的一个重要借口就是育婴堂、医馆等与传教士有关的机构,拐卖儿童,做“挖眼炼银”、“镂人心肝”等非法之事。1899年,福建建瓯县出现“建宁教案”。五月间,建安东乡“有迷失幼孩情事,人心惶惑,疑系洋教所为……谣言四兴,通城鼓动,指称王云林系受洋人主使,纠众寻仇,将瓯宁县属英人医馆二间先后拆毁”,打死打伤医馆三人,直到官府弹压、多方解释才逐渐平息。事后调查,英国传教士医馆同拐匪王云林根本没有关系。[29]1890-1910年间,广东赤溪、顺德等地也曾发生类似教案。尽管大部分来华传教士站在反对拐匪的立场上,但在清末教案中却屡屡被民众视为拐匪加以反对,是传教士始料未及的。传教士虽多方解释,但是依旧被民众疑恨。这一方面反映了苦力贸易的影响之深,另一方面反映了在近代列强入侵中国的大潮下,来华传教士在闽粤民众心中存有挥之不去的负面形象。教案是教民矛盾长期积累的爆发,严重冲击了传教士的正面形象,也影响了人们对基督教和传教士的全面认识。部分后人在研究苦力贸易和相关教案之时,没有对其中的曲折详勘深察,多站在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有意删减材料,与传教士在其他方面的侵华史实混为一谈,对传教士在苦力贸易中的形象全盘否定,不符合客观事实。
四、余论
在目前所披露的史料中,有关活动于中国北方的传教士与苦力贸易的直接资料十分稀少。苦力贸易主要发生在华南沿海。北方地区的传教士,虽距离苦力贸易较为遥远,但从教义和个人利害角度来看,不支持或者反对苦力贸易占多数。这一点也可在晚清教案中看出端倪。在引发教案的原因中,传教士或者教会医院收留妇女和设立育婴堂,是激起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从《教务教案档》等所披露的史料来看,所谓来华传教士拐卖妇女儿童之事绝大多数是坊间谣言和误会。来华传教士设立育婴堂、收留妇女,是出于慈善和传教的考虑,跟卖人牟利风牛马不相及。这点在其他地区的教案中也有共性。①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教务教案档》,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2-7辑,详见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湖北、广东和福建等地区在咸丰—光绪年间的教案记录;程漱、张鸣:《晚清教案中的习俗冲突》,《历史档案》1996年第4期;李传斌:《教会医院与晚清教案》,《南都学刊》2007年第5期;赵树好:《晚清教案交涉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55-56页;苏萍:《谣言与近代教案》,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苏萍在该书中对拐卖妇女儿童的数量和真伪性,进行了量化细致研究,其结论与其他学者基本一致,即有关传教士拐卖妇女儿童多为谣言,造成谣言的主要原因乃是中西文化、政治、经济、民族等方面的差距与矛盾。这客观上说明北方等地区的传教士大多数是不支持甚至反对人口拐卖的,更不用说危害更甚的苦力贸易。
长期活跃在华南沿海地区的传教士,在苦力贸易中则经历了由参与到反对的戏剧性变化。在苦力贸易早期,部分传教士因接受的信息有限,易受到政客、商人的引诱和欺骗,再者他们自己也希望通过苦力移民,壮大本国实力,传播基督教,故而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拐卖苦力贸易,激化了中外民族矛盾,不仅直接威胁在华传教士的形象和生存发展,也影响基督宗教以及欧美各国在华的长远发展,弊大于利。传教士深浸基督神学和伦理道德,在精神意识和行为上具有鲜明的宗教特色,使得他们区别于政客与商人。再者从利益角度来说,他们大多数同拐匪没有直接的利益联系。随着事态的发展,他们通过商行、华南民众、报纸等渠道获得了更多的信息,认识到了苦力贸易对个人和传教的威胁,以及同基督精神、人道主义的冲突,促使他们总体上反对苦力贸易,其相对客观公允的立场和言行也逐步得到民众的赞赏和支持,以致部分民众甚至向其求助。在华传教士中,香港和澳门的传教士人数最多。港澳传教士主流与广东民众于反对卖猪仔上形成共识,在舆论上对澳葡当局形成了巨大压力,加速了澳门苦力贸易的禁止。[18][545-550,[22]252-259,[30]每个人都会犯错,而人的可贵之处是能反思改正进取,重走社会正途。来华传教士在苦力贸易中犯过错误,多数在中后期改过从新,用实际言行捍卫了基督宗教的尊严,解救了部分受害者,宣扬了圣福音,维护了人道主义。
革命史观下的传教士,几乎被全盘否定,而现在又有少数完全肯定的倾向。这些都是人们的价值倾向所导致的,没有经过具体分析。来华传教士对苦力贸易的复杂反应和前后微妙的曲折抉择,是对这种极端思维的批判和启蒙。传教士既是上帝的使者,也是活生生的人。是人就会犯错。可人犯了错误也有可能改过从新,并非一成不变。
苦力贸易的最终禁止,是中外正直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在反对苦力贸易的群体中,来华传教士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此,我们决不能忽视他们的存在,肆意抹黑他们,但也不能过分美化他们。传教士反对苦力贸易主要以言论为主,真正深入猪仔馆救人的属于少数。再者,有些传教士发出反对苦力贸易的呼声后,作用其实是有限的。1874年苦力贸易被明文禁止后,港澳地区的部分“猪仔馆”,打着“自由招工”的旗号,改头换面依旧拐卖。[18]189-193圣福音对拐匪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外国拐匪表面上信奉基督教,却并没有尊奉基督正教真善美的要求去做,不过是些假教徒甚至邪教徒罢了,是抹黑基督正教的重犯。外国殖民者主导的人口拐卖直到民国时期还依然存在,为中华民族所痛恨。苦力贸易被明文禁止之后,来华传教士参与者虽已大减,但也并未绝迹。这主要以少数来华天主教传教士为代表。清末时期,同西班牙拐匪有密切联系的天主教传教士苏玛索等人在福建省南台村等地,就曾经诱招华民前往留尼旺、墨西哥等地。[16]97-100该案例虽是苦力贸易消亡期的特例,但也证明还是有少数传教士昧心卖人。不过,类似案例在清末民国并不多见。参与苦力贸易的传教士在近代虽说不绝,但毕竟是少数。基督教的长期存在自有其主流和正能量做支撑。否则来华传教士都去干卖猪仔的勾当,那么会在晚清民国激起更多的相关教案,基督教也早已退出中国了。近代少数来华传教士参与苦力贸易,需要批判。但传教士主流对苦力贸易的反对,以及对中国人民的真诚帮助,对基督正教和公平正义的维护,值得学术界正视。
文尾之处,需要指出本文的缺憾和空间。纵观国内外有关基督传教士与苦力贸易问题的客观研究,严格来说还是块处女地,主要由于史料琐碎隐秘。本文以相关史料涉及较多的来华传教士为切入点,如米怜、卫三畏、伯驾、丁韪良等人,依据相关档案和报刊等史料,重点比较研究粤港澳地区传教士的言行转变,窥探晚清时段来华传教士对苦力贸易的态度转变问题。但诚如相关学者所说,近代来华传教士人数众多,教派亦繁,个中问题相当复杂。本文虽将来华传教士主流群体对苦力贸易的整体态度以及部分传教士复杂面相点明,但对其他更多传教士的论述却失之模糊。相关的完善,有待海外资料的发掘和同仁的批评指正。
除了本文所探讨的有限问题之外,还有以下诸多重要问题需要继续探讨:(1)除本文所追踪的传教士外,近代以来到底有多少来华传教士与苦力贸易有接触?他们与以上传教士的共性和个性问题。(2)基督宗教内部的各个教派与苦力贸易关系问题。(3)近代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其他区域的苦力贸易之关系问题。(4)来华传教士归国后,与海外华人华侨的互动问题。(5)民国时期来华传教士与中国移民关系问题。可以说,近现代来华基督宗教传教士与苦力贸易的客观研究,既是苦力贸易新的研究基点,也是传教士与中国移民研究的重要引擎,学术空间之广,不可限量。这些重大研究课题有待海内外新材料的发掘和仁人志士的共同努力。
[1]黄启臣.澳门通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192-195.
[2]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M].上海:上海书店,2003:55-60.
[3]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M].肖濬华,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10.
[4]Hosea Ballou 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M],Oxford Press,1926,Vol2: 288-428;Vol:16-378.
[5]Eilza Morrison.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影印版。
[6]雷雨田.近代来粤传教士评传[M].广州:百家出版社,2004:161-168.
[7]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M].顾钧,江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8]陈翰笙.美国与加拿大华工[M]//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2.
[9]Samuel Wells Williams.Chinese Emigration[N].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第19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影印版.
[10]沈国威,等.遐迩贯珍[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638-648.
[11]Samuel Wells Williams.Gutzlaff’Journal[N].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第1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影印版:28,127-145.
[12]陈翰笙.拉丁美洲华工[M]//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六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
[13]爱德华·V·吉利克.伯驾与中国的开放[M].董少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4]陈翰笙.美国外交和国会文件选译[M]//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
[15]王之春.国朝柔远记[M].台北:广文书局,1978:881.
[16]吴凤斌.契约华工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
[17]陈翰笙.英国议会文件选译[M]//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66.
[18]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9]可児弘明.近代中国の苦力と「猪花」[M].东京:岩波书店,1979.
[20]容闳.西学东渐记[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114-115.
[21]吴志良,等.澳门编年史:第四卷[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22]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M].黄鸿钊,李保平,译.澳门:澳门基金会,2001.
[23]施白蒂(Silva Beatriz Basto da).澳门编年史[M].金国平,译.澳门:澳门基金会,1999.
[24]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见——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187-208.
[25]刘蜀永.十九世纪香港主要英文报刊[M]//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六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153-154.
[26]丁韪良.中西见闻录选编[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集刊第3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2号、7号、11号、12号、14号、15号、16号、18号、21号、23号。
[27]王文兵.丁韪良与中国[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191-223.
[28]丁韪良.花甲记忆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M].沈弘,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2-14.
[29]张先清,赵蕊娟.中国地方志基督教史料辑要[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434-436.
[30]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M].香港:道声出版社,2009:169-255.
(责任编辑:汪小珍)
K252
A
1001-4225(2015)05-0073-09
2014-09-23
李彬(1989-),男,山东新泰人,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